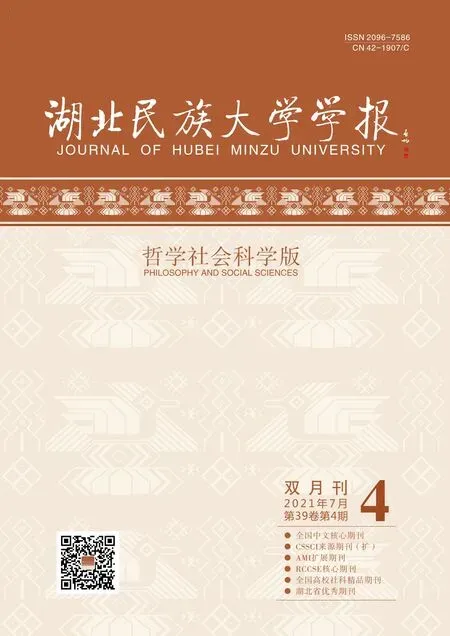族群的文化交融及其国家认同
——基于内蒙古牧区的田野调查
2021-07-15何生海
何生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精神动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国家认同这两个概念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在内涵上具有互验性,即缺乏国家意识或国家认同也就缺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提升国民的国家认同的过程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通过对国家认同的实证研究可为区域性民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具体的操作路径和改进方向。
目前,学界对国家认同的界定可总结为两种不同视角:一种是文化依恋(cultural attachment),强调与国家的情感归属,即对国旗、货币、国家形象等国家符号和文化符号的自豪。另一种是功能依恋(instrumental attachment),即对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服务程度和制度好坏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认同。两种不同视角决定了测量个体的国家认同会有不同的路径。侧重文化依恋的测量方法主要是从满意度着手,采用“认可”“亲密度”“自豪感”“归属感”等为衡量指标,如吴鲁平的“内隐测验”法(1)吴鲁平:《公民国家认同的特点及其与对外接纳度的关系研究——来自ISSP(2003)的证据》,《社会科学杂志》2010年第1期。;类似的研究如Sean Carey利用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调查数据,研究欧盟15个成员国公众的国家认同与欧盟认同(2)Sean Carey,“Undivided Loyalties:Is National Identity an Obstacle to European Integration?”European Union Politics,vol.3,no. 4,2002,pp.387-413.。Tom W. Smith 利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测量不同地区民众的“国家自豪感”,发现性别、年龄等都是影响国家自豪感的因素,但是影响程度因具体国家而有所不同。(3)Tom W.Smith,Seokho Kim, “National Prid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995/96 and 2003/0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vol.18, no.1,2006,pp.127-136.侧重功能依恋的研究则是以价值体系与社会政策为衡量指标,如陶蕴芳从国家政体、政策运行、政治价值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国家认同现状进行调研(4)参见陶蕴芳:《当前我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实证研究》,《求实》2013年第10期。;谢和均以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国家扶贫政策研究西南边境民众的国家认同(5)谢和均、李雅琳:《经济福利、社会保障与国家认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社会保障的实证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4期。。显然,单线的文化依恋亦或是功能依恋很难完整地测量出民众国家认同的整体水平。因此有学者开始把这两个维度整合在一起,如徐平设置了既有情感性指标又有对国家政策运行的评价性指标研究五个自治区民众的国家认同(6)徐平:《五个自治区国家认同的调查与研宄》,《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张群将国家认同操作化为国家感受、政策评价等两个维度(7)张群:《边疆地区农牧民国家认同现状研究——基于西藏农牧区的考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胡兆义从国家自豪感和对民族宗教政策的评价来研究撒拉族的国家认同(8)胡兆义:《撒拉族民族认同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显然,将文化依恋和功能依恋的测试相结合是一种出路,但是国家认同是一种很复杂的态度体验,除了受到与国家自身制度设置与政策运行产生的“供需机制”影响外,也与国内民族之间的互动有关,尤其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以及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关系的好坏会映射到国家认同上。因此,本研究把蒙汉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变量予以考察。借鉴帕森斯的系统理论,我们从三个维度构建国家认同的评价要素:认知性要素主要针对国家文化,倾注性要素针对国家的情感,评价性要素针对国家功能的评价。(9)帕森斯的系统理论认为系统内的价值取向可以归结为认知性要素、倾注性要素和评价性要素,参见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55页。这样会凝练成三个维度,分别为文化认同、国家政策与国家情感。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一)数据来源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近70名师生于2019年7月8日至7月30日进行了为期22天的田野调查,选取了内蒙古西部的乌拉特后旗和阿拉善左旗;中部的达拉特旗、杭锦旗、乌审旗和鄂托克前旗;东部的锡林浩特、巴林左旗、科尔沁右翼前旗、陈巴尔虎左旗等10个旗县,在每个旗县又抽样出4个乡镇(苏木),在每个苏木中又抽取3~4个嘎查,力求调研数据的多样性和完整性。本次调查涉及内蒙古自治区7个盟市、10个旗县、40个乡镇(苏木)、120个噶查村,访问牧民2600余人。考虑到牧区有被访者不能用汉语交流等原因,分组时把本学院社会学专业学生(以汉语为教学语言)和民族学专业学生(以蒙古语为教学语言)进行搭配,这样会在民族情感与民族语言上形成补充。本文仅汲取国家认同方面的调研内容,共获取了330份有效问卷和总计1180小时的访谈录音。
(二)样本描述性分析
样本数据包括抽样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如性别结构、职业结构、民族结构、宗教信仰、收入状况等。根据后续研究需要,笔者对相应的变量重新做了分类和编码。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以及分类编码
从样本的信息看,本次调研对象在性别、民族结构上基本平衡,职业主要以牧民居多;从受教育程度上看,初中、小学人数较多;从宗教信仰看,由于填写问卷时很多人表示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课题组成员依据其身份证的信息,直接归类为“无”,这样样本中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员占绝大多数;从收入情况看,以月收入3000元左右为主。整体上看,样本量从区域特征、民族结构、教育程度、收入状况、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具有北方牧区的代表性。
二、牧区民众的国家认同现状
国家认同首先体现在民众对国家法律法规的敬畏上,一个法律的越轨者何谈国家认同?其次我们思考的问题是牧区民众的国家情感浓厚程度到底如何?他们对国家现行政策哪些满意度较高,哪些较低?民族成员是否具有为民族与国家发展的责任担当?下文将通过文化认同、国家政策与国家情感几个维度进行研究。
(一)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属于认知性要素,Schatz 和 Lavine(2007)认为:“由国家符号、文化符号和历史符号等唤起的文化依恋将关注的是国家能为自己带来的自豪感和积极认同。”(10)Schatz,R.T.,& Lavine,H.,“Waving the Flag:National Symbolism,Social Identity,and Political Engagement,”Political Psychology,no.28,2007,pp.329-355.在现代社会,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密切相关,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存在的土壤,将个体与国家牢牢地联结在一起,“能为我们提供用来识别有价值的和有经验的眼镜”(11)Ronald Dworkin,A Matter of Principl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228.,但是文化认同的前提是文化认知,对此费孝通先生有精辟的论述,“文化自觉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12)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253页。。考察牧区群众的文化认同,首先要探究其文化认知,因为认同源于认知,若对某文化没有认知也就无所谓认同。认知有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感性认知是理性认知的基础,人们只有了解和理解了文化内容,通过感觉、记忆、思维等方式将“知其然”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知其所以然”的理性认识,才能达到对这种文化的认同。当然,在感性认知上升到理性认识后,不认同的现象也会有的。对于牧区而言,牧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源于环境熏陶、情感体验、心理诱导、榜样示范等方式,认知程度大致和认同程度趋于一致,这样会将情感认同上升到价值认同。反之,若个体对某种文化越排斥,就越不愿再了解,这样认知水平也会很低。
本研究设置了三个维度考察牧区民众的文化认同水平,即对古典文化(13)古典文化内容比较丰富,包括古典诗词以及经史子集等蕴含的精神文化,也包括古典园林建筑等物质文化,其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比较复杂,目前还没有权威的成果界定这两者的关系,毫无疑问,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为了便于测量与统计,针对牧区现实情况,课题组对古典文化的设计侧重于儒道思想和古典文化常识,而对少数民族文化侧重于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以及民族节日等方面。、民族文化(本文特指少数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同状况。笔者把选项答案与得分设定为“非常熟悉”(4分)、“熟悉”(3分)、“听说过”(2分)、“不熟悉”(1分),从排序上看,分数越高说明对该文化认同程度也越高,调研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牧区民众对三种不同文化的认同程度
从整体看,牧区民众对古典文化的认同最高,对西方文化认同最低,对民族文化认同处于中间状态。牧区民众对三种文化认同的差异除了与民族个体的情感关联之外,也与信息传播有着密切关系,如对古典文化的认知,人们最熟悉的是“王昭君”“清明节”和“京剧”这三种。在牧区,人们的文化认知主要来源于电视或其他媒体,对西方文化认知较低。一方面,西方文化与牧区生活比较遥远,另一方面,在媒体的传播过程中西方文化所占份额较少而且是用汉语传播。除受媒体语言影响外,也与个体的知识储量有关,如古典文化,民众最不熟悉的是《论语》《红楼梦》和“老子”。坦然而论,由于古典文化比较深奥,成为很多民众的认知盲区。值得关注的是,牧区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不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影响了他们对这类知识的了解。在少数民族文化中,人们最熟悉的是呼麦、那达慕和《江格尔传》,尤其在内蒙古,这三种文化与蒙古族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西方文化中,人们认知最多的就是肯德基与圣诞节,与这两种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力较大有关。
总体而言,牧区民众对古典文化与民族文化认同度较高,总均值都在3.0以上,而这两种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政策认同
政策认同属于评价性要素,研究发现个体在感性的爱国主义上得分越高,越喜欢国家的符号行为,如宣誓或升国旗,就在理性的爱国主义上得分越高,也越愿意了解政府的政策和社会新闻。(14)Schatz,R.T.,Staub,E.,& Staub,E.,& Lavine,H., On the Varieties of National Attachment:Blind versus Constructive Atriotism,Political Psychology,no.20,1999,pp.151-174.由此也反映出国家政策与民众的国家认同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同时,社会排斥与国家认同有重要关系,Verkuyten & Yildiz (2007) 以土耳其裔荷兰人为被试,研究发现个体知觉到社会的排斥越多,族群认同就越高,对荷兰的国家认同就越低。(15)Verkuten M.,& Yildiz A.A.,National (Dis)Identification and Ethnic and Religion Identity: A Study among Turkish-Dutch Muslim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no.37,2007,pp. 1448-1463.在中越边境的京族和越南的越族人同根同源,但是近些年来越南芒街一带的越族人,“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大节(日)小节(日)都要打出他们的国旗来,时时处处都要表现出他们是越南人,‘跟我们不同’的样子。为此,‘我们也需要表示一下(跟他们不同)’”,因此京族人逢年过节都会打出鲜艳的中国国旗,一则给越南越族人彰显一下威风,二则表达对祖国的认同。(16)吕俊彪:《京族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
舒茨认为国家政策直接影响国民的认同程度,他认为由政治体制、民生政策和经济发展等唤起的功能依恋将国家作为具体的功能系统,关注的是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实用性,以及这些体制能为国家公民带来的实惠。(17)Schatz R.T.,& Lavine H.,Waving the Flag:National Symbolism,Soci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Political Psychology,no.28,pp.329-355.中国学者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如“定居工程”对促进游牧民族的国家认同感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18)参阅彭庆军:《以公共服务促国家认同:后游牧时代少数民族牧民国家认同建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导论”,第3页。因此,“国民诉求—国家供给”成为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的建构机制。(19)卢鹏:《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以中越边境哈尼族果角人为中心的讨论》,昆明: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9页。为了掌握牧区民众对政策的评价,笔者设置选项答案及分值如下:“非常满意”(5分);“满意”(4分);“无所谓”(3分);“不满意”(2分);“非常不满意”(1分)。调研结果如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民族地区的各种政策中,认同度较高的依次是“把呼和浩特建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城市”“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双语教育”“国家的草原保护政策”和“土地确权政策”。分值较高的前三项都与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有关,这说明中国在保护民族文化方面的举措是正确的,得到群众的认可;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少数民族群众对本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关注度较高。群众满意度较低的有三项。首先是“工矿业在草原地区的开发”,这与近年来工矿业开发中破坏草原生态及因利益补偿等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有关。其次是“移民搬迁”。在访谈中得知,在移民项目中群众不满的主要方面有:对新搬迁房子质量的质疑;嫌自家的楼层不好;迁移到城镇后生活压力较大;部分老人觉得无法适应,还是牧区安静;质疑干部办事不公和腐败问题。(20)相关资料来自课题组2019年对内蒙古调研地的访谈。最后是“禁牧政策”。因为禁牧政策存在后期效应与当前需求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对牧民的当前利益有所损害。随着禁牧政策的实施,牧民要么转产,要么居家圈养。而圈养的成本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牧民对这些政策的认同,甚至出现个别群众抵触的情况。但从长远看,禁牧政策是利国利民之举,因此加强在牧区的政策宣传并做好群众的受损补偿,对于增强牧区民众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总体而言,牧区民众对国家政策认同较高,均值为3.89,国家政策处于满意状态,这成为内蒙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基础。

表3 对公共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评价
(三)国家情感
国家情感属于倾注性要素。国家认同的情感维度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依恋感、自豪感和归属感,以及在国际博弈中对自己国家权利的维护和国家发展的责任担当,既包含原生性的情感因素,也综合了工具性因素。原生性纽带主要涉及人种、语言、文化、领土等“自然”内容,工具性因素主要强调情境性和建构性,侧重国家与个体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建构,对于个体而言主要是为国家发展的责任担当。对于国家情感的调研,笔者设置选项答案及分值与表3相同,调研结果如表4所示。
从统计结果看,认同最高的几种表述是:“我觉得祖国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就像母亲”“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祖国”“当我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领取奖牌那一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升起,国歌被奏响时我内心很激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很重要”“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可以看出前几项是情感依恋,最后一项是责任担当。从整体上看,15个测试题均值为4.11,说明牧区民众无论从国家情感维度,还是责任担当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坦然而论,情感性因素既有朴素的“天生性”,又有社会的建构性。国家身份如同生身父母一样,是个体无权选择的,正因为如此,情感性因素在国家认同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牧民在生活上并不富裕,访谈中也得知他们在社会上也“遭遇”过不公正待遇,感受了部分地方官员的怠政,对现实常有一些牢骚抱怨,仍然没有失去国家认同的重要原因。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天生”的认同感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丝毫不会动摇,牧民与国家之间的感情同样需要精心呵护。只有培养起牢固的国家情感,树立起稳定的国家信念,才能使国家认同趋势呈连续性发展(21)张群:《边疆地区农牧民国家认同现状研究——基于西藏农牧区的考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同时,培育公民的国家情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

表4 牧区民众对国家情感的评价
三、牧区民众国家认同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
前文从认知性要素、倾注性要素和评价性要素方面讨论了牧区民众对国家认同状况,那么哪些微观因素会影响民众的国家认同呢?下文将从文化依恋(认知性要素)和功能依恋(评价性要素)两方面展开研究,需要说明的是倾注性要素的微观变量权重不好把握,测量出来的结果意义不是很大,本文主要以认知性要素与评价性要素为主。文化依恋侧重文化认同,主要以古典文化、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为因变量,功能依恋侧重国家政策的功能发挥,主要以公共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因变量。
(一)变量说明
本文把变量分为因变量和自变量两种。
1.因变量。因变量主要包括以下认同指标:(1)古典文化;(2)民族文化;(3)西方文化;(4)公共政策;(5)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本质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属于公共政策,但该制度具有稳定性与长期性,有别于其他公共政策,因此本文单独将其作为一项指标进行研究。各因变量根据问卷中反映各类认同的指标,笔者利用熵值法将反映不同认同的指标合成各类因变量,具体各类认同对应指标及权重如表5所示。

表5 因变量构成方法及指标计算
2.自变量。自变量分别选取了人口学特征变量,如年龄、性别、民族、教育水平,以及反映社会经济水平的收入和职业等指标,前文已经交代,此处不再赘述。
(二)实证分析及结果解释
1.实证分析
根据前文对三种文化认同、公共政策认同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认同的测算与分析,对影响他们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本文的因变量为连续型变量,故采用虚拟变量回归法,回归方程如下。
Yi=α0+α1AGE+α2RACE+α3JOB+α4EDU+α5ZJ+α6INCOM+α7JZ+ε
其中除年龄为连续变量外,其余均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ε为误差项。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2.结果解释
通过对表6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结果。
(1)从年龄上看,模型一到模型五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群体在民族文化与古典文化认同上并未表现出太大的差异,但对西方文化差异性显著。低龄群体较高龄群体在西方文化认同上较高,笔者认为低龄群体比高龄群体有更多的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对西方文化的认知较多,加之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传播的速度与广度更显著,如国内逐渐兴起的西方节日、西式餐饮等。国内另一项调查也形成对上述表述的验证:与传统节日相比,48%的中学生表示自己更喜欢过西方节日;与国产剧相比,58.1%的学生表示自己更喜欢看国外影视剧。(22)曾水兵、班建武、张志华:《中学生国家认同现状的调查研究》,《上海教育科研》2013年第8期。同时,本研究发现在公共政策方面低龄群体表现出更高的认同度,源于低龄群体受教育水平要高于高龄群体,他们对公共政策的了解较多,所以认同度相对较高。相反,高龄群体对古典文化和民族文化有更高的认同度。可见,从微观上看,“年龄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普遍存在”(23)曹娅:《国家认同影响因素比较分析——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研究对象》,厦门: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表6 民族地区民众对各种认同指标的回归结果
(2)从男女两性的差异看,相较于女性,男性的文化认同要高出女性0.0230个单位,但并不显著。在其他认同指标上男女未表现出在各类认同上的明显差异,大家对各类文化认同、公共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认同基本一致。公共政策针对的是民族地区所有人口,而且中国政府管理职能在不断调整,从管理型政府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性别倾向上表现出“无性化”。在“国民诉求—国家供给”的认同建构中并不存在男女性别差异,因此在国家认同体系中也具有性别的“无差别化”特点。
(3)从民族维度看,模型一显示,相对于蒙古族,汉族对古典文化的认同度要高于蒙古族0.2429个单位,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而模型二显示,相对于汉族,蒙古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度高于汉族0.4898个单位,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少数民族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认同是情理之中的。民族因文化而分野,文化因民族各具特色,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魂。模型三显示在西方文化认同上不同民族之间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但与个体受教育程度相关性很强。模型四显示对于公共政策,如“十个全覆盖”工程、禁牧政策、土地确权等民族之间差异性不是很大,这与民族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有关。模型五则显示,相对于汉族,蒙古族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认同度较高,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基于保障少数民族权益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设定,具有明显的民族指向性,获益较多的民族无疑对这种制度设置认同性较高,印证了美国社会学家派伊(Lucian Pye)的理论:“国家认同是处于国家决策范围内的人们的态度取向。”(24)马文琴:《全球化时代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7页。
(4)从职业情况看,模型一、模型三显示:相较于农林牧副渔从业人员,学生、事业单位以及一般工作人员对古典文化的认同和西方文化的认同明显偏高,一方面与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与这个群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关,因为在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是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传播的很少。农林牧副渔业从业人群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在牧区他们基本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对古典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接触及认知较少,文化敏感度较低。而模型四显示,与农林牧副渔从业人员相比,大学生、事业单位以及一般工作人员在对公共政策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认同上出现较为复杂的情况,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根据课题组的采访发现,整体上少数民族对民族地区的公共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较高的认同,但在同一民族内部出现了阶层化的现象。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即民族精英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地区的公共政策的期望值较高,他们对于本民族发展的责任心和迫切心较强,“求之急,心之切”,当与期待值有差距时,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斟酌政策设置的实效性,还需激发牧区精英分子的引导效应,充分利用他们的责任担当热情,提振牧区内源性发展动力。相反,农林牧副渔从业人员是受益于公共政策的直接群体,对其认可度较高。如“十个全覆盖”政策,解决了大多数老百姓的吃水、住房、就医、上学、娱乐与休闲等问题,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5)从受教育水平看,模型一到模型三反映出,与小学学历水平的群体相比,高中(包括职高)学历群体在古典文化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和西方文化认同上要分别高出0.5133、0.9469、0.5168个单位,且均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大专以上学历群体相对于小学群体在以上三类文化认同上分别高出0.5424、1.333、0.6895个单位,同样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不论是少数民族人口还是汉族人口对各类文化的认同度都会提高。这一点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即要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必先提高民众的认知水平,把感性认知内化为理性的价值观。显然,普及全民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6)从宗教信仰看,模型二显示,与未信仰宗教的群体相比,信仰宗教的群体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度显著偏高,高出0.5520个单位。宗教信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体现,宗教通过民族文化烙上民族特色,民族文化通过宗教又表现出地域性和民族性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民族文化和民族宗教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两翼”,对民族宗教的信仰在现实中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的遵从与恪守。因此,对宗教信仰的认同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呈正相关。
(7)从收入水平上看,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在各类文化认同,以及对公共政策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认同上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这很大程度上与本次调查群体处于牧区,而当地群众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社会阶层分化不是很明显,同质性较强有关,因此在各项认同指标上也没有表现出差异性。
(8)微信朋友圈中他民族所占比例可以反映出民族交往情况。模型一与模型二显示:在微信朋友圈中蒙古族朋友较多的汉族对少数民族文化认同较高,说明当地“蒙化”现象突出。这在蒙古族中也得到验证,在蒙古族微信朋友圈中汉族较多的人群对古典文化认同也明显偏高。此研究发现具有重要意义,说明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克服民族偏见和刻板印象、提升族际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而模型四、五并未反映出微信圈中他族朋友数量占比多寡群体在公共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认同上的差异。
(9)以居住选择方式反映民族交往情况看,模型二显示:“不愿和其他民族为邻居”(我们界定为“封闭式群体”)与“不介意与哪个民族为邻居”(我们界定为“开放式群体”)相比,“封闭式群体”对本民族文化认同较高,高0.8196个单位,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对其他文化认同较低。而“开放式群体”对各种非本民族文化认同都相对较高,两类群体对于公共政策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认知的差异性不是很显著。由此可见,“互嵌式社区”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学者认为提高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强化人们的国民身份。(25)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四、结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意识形态的建构,在现实中必须找到抓手,通过对国家认同的量化研究可以寻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操作路径与工作方向。
从认知性要素看,蒙古族对于民族文化认同较高,而汉族对于古典文化认同较高,说明不同群体基于民族文化情感、媒体传播以及文化感知表现出认同的差异性。微观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对三种文化认同都高,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群体对古典文化认同高。要使中华民族文化成为各民族精神家园,必须提高牧区民众的认知水平,正如前文所言,对文化认同就必须先有文化认知,而文化认知必须借助语言工具和媒介信息。因此,在牧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促使民众对国家产生文化依恋的重要举措。
从倾注性要素看,调查发现即使牧区民众在生活中可能会面临种种困境与挫折,有时也会遭遇社会的不公平对待,甚至对制度体系中的贪腐行为很愤懑,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质疑过国家,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国家的忠诚,仍对国家充满信心。但是牧区民众对国家的忠诚也需要精心呵护,他们对国家的认同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感受。基层政府是民众最接近“国家”的实体,直接影响他们对国家的看法与国家情感的形成,因此,要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需从改善民生和制度建设入手,让民众置身于国家制度所惠及的社会空间之中。
从评价性要素看,政策是“国民诉求—国家供给”认同机制中的核心,政策的合理性直接影响牧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首先,从调查结果看,牧区民众最为满意的三项(把呼和浩特建设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城市、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育)中,都与民族文化保护有关。民族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可见牧区民众对民族文化还是非常关注的,因此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进行民族文化的传承,正确处理好“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必然会提升国民对国家的情感依恋。其次,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精英表现出了较为复杂的认同倾向。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另一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实行以来修改较少,仍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内容。最后,对国家认同的实证研究发现,微信圈其他民族较多的民众对非本民族文化认同较高,并乐意与其他民族共同居住,这就说明“民族互嵌”是增进民族情感,推动社区互嵌向社会结构互嵌,增进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提振各民族“大家庭”意识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