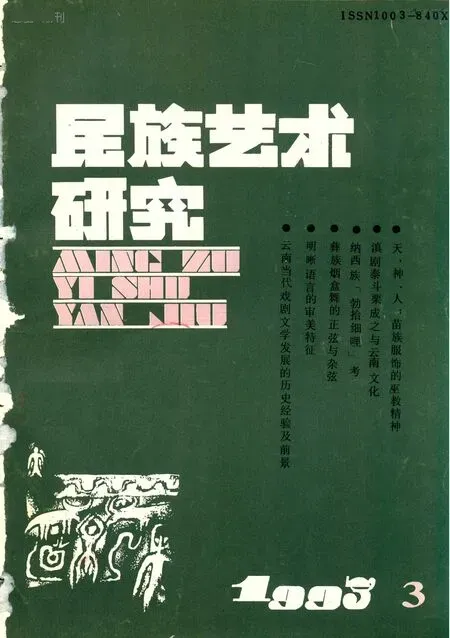历史与本体语境下的纪录片观念思考
2021-07-15徐锦,宋杰
徐 锦,宋 杰
历史的记录与研究,一直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所有的媒介,都具有一定的记录历史的功能。由于媒介材料的不同所导致的媒介本体差异,不同媒介记录历史的方式与形态自然有所不同。过往传统中,文字是记录历史的主要方式。但是,随着视听媒介的出现,一个从文字语言文化向视听文化的世界性转移已经在全球大规模地展开。从历史视野和本体论语境层面,分别对历史记录的两种方式(文字的和视听的)以及纪录片修辞中的两种风格(言辞的和视听的),从媒介语言的角度,进行一次语言学意义上的理性辨析,可帮助我们认识清楚作为今天历史记录主要方式的纪录片,是如何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去凸显历史的价值的。
一、历史记录:“推理性的”和“生物性的”
(一)历史记录的转向:文字向影像的转变
有关纪录片的界定,最早可以追溯到电影的发明国——法国。法国人拉·巴桑和达·索维吉在其撰写的《纪录电影的起源及演变》一文中写道:“据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考证,语言学家利特里编撰的《法语词典》于1879年收入documentarie一词,其词性为形容词,意思是‘具有文献资料性质的’。历史学家让·吉鲁指出,到1906年,该词便开始用来指称纪录电影,并于1914年成为名词。”①[法]拉·巴桑和达·索维吉:《纪录电影的起源及演变》,《世界电影》1995年第1期,第207页。
所谓文献,即指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类社会活动成果。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主要的文献资料是用文字记录的。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从上古的黄帝时期至汉武帝太初四年之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记录历史的方式是文字。
显然,文字记录的是看不见听不到的“过去”,它对历史的记录一方面受制于历史的资料(这些资料大部分也是文字的),一方面也受制于运用文字语言的作者的主观倾向。因此,以文字为主体的历史记录常常被认为是功能性的一家之言,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克罗奇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史”②参阅百度有关词条。参见[美]保罗·霍金斯主编:《影视人类学原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之所以能够得到众多历史学者的肯定,也是因为文字因其主观性能够恰当地表达书写者的主观态度。
19世纪初期,纪录媒介出现了,法国的达盖尔、尼普埃斯等人发明的静态的摄影术,因其能对现实进行图像的精确记录,顺理成章地被历史学者、人类学学者用来研究历史。那个时期的人类学家,已经开始大量采用摄影技术去获取田野调查的图像资料以辅助他们的研究。影视人类学的先驱者之一玛格丽特·米德以及马林诺夫斯基都曾拍摄过大量的照片作为其人类学研究的佐证。伦敦经济学院至今仍然保存了1100幅马林诺夫斯基早期拍摄的有关人类学研究的照片。
1895年电影出现之后,这种“通过光线的反射把摄影机前的世界提供给我们,从而代替抽象和概念性的文字符号”①[美]保罗·霍金斯主编:《影视人类学原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的手段,更是得到了人类学家的推崇。
事实上,电影摄影机是一种理想的工具,可以用来记录任何类型的文化资料。这些资料既复杂又是可视的:一个仪式,一场舞蹈,一种技术的运用过程或是一个人内部的互动情况。②参阅百度有关词条。参见[美]保罗·霍金斯主编:《影视人类学原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在这之后,纪录片的先驱弗拉哈迪把目光投射于遥远的异国他乡——用电影的方式去记录行将消失的、与都市生活差异巨大的人类生存形态;甚至在《北方的纳努克》等影片中用搬演的方式去重演历史,使过去的历史在摄影机前得以“复活”,通过摄影机前的现实去仿演过去的历史。
玛格丽特·米德、马林诺夫斯基、弗拉哈迪等人运用影像去记录历史的行为意味着一个重大的转变,即关于历史的研究或记录的主要方式由文字转向了影像,一种崭新的历史记录的主要方式——纪录片诞生了!
作为历史记录方式的纪录片的出现,同时也成为今天由文字语言文化向视听文化的世界性转移的标志性预兆。
(二)纪录片对历史的记录是“生物性的”
英国的格里尔逊关于纪录片的边界界定,是国内纪录片制作者最熟知的纪录片定义。格里尔逊对纪录片进行界定的首要条件即“根据自然素材制作的影片”③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500页。。这种“根据自然素材制作的影片”强调要用摄影机去捕捉现实,强调电影的纪录本性。虽然格里尔逊对此并未进行深入的探究,但三十年后法国巴赞的《电影是什么》和德国克拉考尔的《电影的本性》已经就此进行了清晰明了的理论阐释,即电影的本性来自摄影的本体④事实上,电影的录音和摄影一样,都可以对来自现实的声音,进行精确的记录。但无论巴赞还是克拉考尔都把声音看作是次要的、跟随摄影的元素,均未对声音录制的记录性进行过阐释。,作为机器的记录,电影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人为的干预(这是人类破天荒的第一次),其本体是对物质世界的复原。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按其本质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一样跟我们周围的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近亲性。当影片记录和揭示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⑤[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邵牧君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纪录片作为电影必然的派生物,之所以被称为纪录片,其根本本质在于纪录片是电影的记录本性的延伸。电影对现实的记录不同于文字、绘画等媒介的记录特点,体现为这种记录是精确而具体的。就记录的精确性和具体性而言,任何媒介都无法与电影电视等视听媒介相提并论。电影出现之后,人类可以相对完整地从视听两个方面对现实进行精确而具体的记录,而这种记录的基础就是有了电影这种仿生机器,即一种模拟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进行看和听的机械装置。这种由机器进行现实记录的优势是其他任何媒介都难以与它媲美的,由此也就在本体上确立了电影纪录片的所谓纪录性的本质。纪录片之所以成为20世纪的一种新的媒介类型,是建立在电影作为纪录媒介的本质性——纪录性基础上的。
电影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与文字、绘画、戏剧相比较,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性。电影不是全能的媒介,有些题材适合于用它来表现,有些题材则不适合。克拉考尔从纪录与揭示现实的电影特点出发,开列出一个“电影的”题材和“非电影”的题材清单。在他看来,有五种题材是“电影的”:一是未经搬演的事物;二是偶然的事物;三是能体现出人生之无涯、时空之无限、现实存在之无穷无尽的事物;四是保持现实的无名状态、保留着未经加工的物质现象的多种暗示性的含义模糊的事物;五是具有事件和时间连续性的、生活流的事物。
“电影的”题材,都来源于“摄影机前的现实”属性,即符合电影的本性,能够显示电影的记录功能、能够呈现物质生活连续性、能够传达事物原生状态的特质,呈现出一种感知性的多义性和含糊性:
“因为这种现实包括许多瞬息即逝的现象,要不是电影摄影机具有高强的捕捉能力,我们是很难觉察到它们的。由于每种艺术手段都自有其特别擅长的表现对象,所以电影可想而知是热衷于描绘易于消逝的具体生活——悠忽犹如朝露的生活现象、街上的人群、不自觉的手势和其他飘忽无常的印象,是电影的食粮。”①[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邵牧君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克拉考尔认为,现实的生活是随意的、偶然的、不确定的、粗粝的、开放的,并不像戏剧等艺术作品那样具有完整封闭的结构、明确的风格形式、较强的修饰与设计环节。因此,传统艺术对现实的变形与操控,与电影固有的与自然的亲近性并不相符,因而不要把电影看作艺术。即使退一步将电影看作艺术,那么电影也不是创造性的艺术,而是一种“存在”的艺术。因此,电影应该展示“非排演的现实”,呈现现实生活的偶然性、随机性,在“行动中捕捉自然”;电影的意义创造与安排,在于对“被发现的瞬间”的呈现。从“记录和揭示现实”的意义上看,纪录片才是克拉考尔心目中的理想电影!
从摄影机前现实的认识出发,克拉考尔将历史的、想象的、推理性等的题材归入“非电影题材”的范畴。以历史题材为例,历史的事件已经过去,摄影机无法捕捉逝去的时间,因此也没法通过摄影机去呈现它。如果采取搬演的方式,克拉考尔担心会违反电影的记录特性,将人们从摄影机前的现实引导至另一个违背记录特性的主观世界中。但克拉考尔并不反对用电影来记录或描述历史,就历史题材影片而言,他强调“最重要的是力求将重心从故事本身即影片所表现的过去的现实,转向摄影机面前的现实(给历史灌注摄影机面前的生活),并且要能暗示出我们所知的那条没有尽头的组成历史事件的因果线,或者善于利用被再现的过去时代的画面材料以力求给人真实可信的感觉”②胡星亮主编:《西方电影理论史纲》,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0页。。
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今天已成为纪录片制作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形成了多种样式。“利用被再现的过去时代的”视觉资料来描述历史的汇编性纪录片(如《二战启示录》),通过搬演“重现”过去的新纪录片(如《蓝色警戒线》),通过当事人回忆的口述历史纪录片(如《证词》),看起来似乎符合克拉考尔的电影化要求——“给历史灌注摄影机前的生活”,但是真正符合克拉考尔“电影的”标准的历史纪录片还是很少,如美国电影理论家尼克·布朗所言:“这些影片之所以未能达标,有时是因为其内在节奏的失调,有时是因为它们过于完整,过于雕琢。”③[美]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徐建生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事实上,这些题材的性质,生活的节奏、呈现生活的不完整性和体现生活的原生形态等,都来自其摄影机前的现实属性。
文字书写的历史从观念出发,为信息接收者提供一个意义明确的、主观性特定的、经过大脑整序的世界,使得人们疏离了感觉经验。克拉考尔对电影本性的认识,提示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即回到现实的混沌性和多义性中,从对物质世界的感知开始,最终走向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
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对历史的认识大都来自文字的记录。纪录片的出现,使得对历史记录的方式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的转变——其一,人们可以通过摄影机前的现实,去观照、仿演历史;其二,摄影机前的世界取代了抽象和概念性的文字符号。
总体上看,文字的历史记录由文字符号来承担,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其书写历史的方式本质上是通过历史的文献(主要也是文字性的文献)来进行推理,因此我们可以把采用这种方式记录的历史称为“推理性”的历史。其读者从文字的记录中所意识到的历史存在于读者的思维之中,是想象性的。纪录片由于机器的介入,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主观的倾向性。与文字相比,摄影机前的世界取代了抽象和概念性的文字符号,可以通过摄影机前的现实,去观照、仿演历史。因此,纪录片对历史的记录更多的是精确而具体的,观众从对纪录片的具体生动的视听感知中获取历史意象,这些意象融化在感知中,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历史的记录称作是“生物性的”。
今天,历史真相的探究由于纪录片的出现,多了一种维度和视角。人们常常将纪录片看作是国家的相册,这使得纪录片肩负起承载国家记忆的重任。每一种媒介的局限性,既是其劣势,也是其优势。由于媒介的不同,历史的文字记录与历史的视听记录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各自按照自己的原则去记录历史,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为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全面性提供着各自的文献,共同构成了今天历史记录的立体性图景。
二、本体论下的纪录片修辞
(一)象征性和艺术性
如果我们将视听媒介系统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的话,那么其镜头就是由各种符号元素(符码)组合融汇而成的。我们可以把这些符码大致分为以下四个类别。
1.自然符码:摄影机、录音机记录下来的自然存在物,如自然的声音符码脚步声、风雨声等。
2.共性符码:来自各种艺术语言,如表演符码、绘画符码、音乐符码、建筑符码等。
3.文化符码:这类符码具有一般符号的约定性,如文字符码、社会符码、商业符码、政治符码、交通符码、服饰符码、习俗符码等。
4.特性符码:这类符码是影视独有的,如摄影机取景、摄影机的运动、透镜的选择、剪辑以及电影相对时空中的视听关系等。
这些符码集合在一起,产生视听媒介记录现实、表达意义、讲述故事的表现性。从其功能上看,这个符号系统类似于传统言辞语言的准语言系统。
法国电影理论家让·米特里在其《电影美学与心理学》里谈道:尽管电影并不具有传统言辞语言的符号的固定性、统一性和约定俗成性,但是无论是从作为象征符号的影像(依照语言学的意义)和作为相似体的影像(依照心理学的意义)两个不同的角度上看,电影都可以具有这些符号的功能。①[法]让·米特里:《电影美学与心理学》,崔君衍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65—77页。因此,他把电影符号看作是具有双重功能的特殊符号,即具有语言学意义上的象征性和心理学意义上的艺术性的符号。
纪录片作为电影必然的派生物,自然有其不同于其他媒介的表现性特性。纪录片的制作者一方面发挥视听媒介的记录功能——记录摄影机前的现实;另一方面,在可控的范围内,它有权自由选择具有表现性的元素构成其意义群,其主要表现在影片的修辞方式运用上。
摄影机和录音机直接摄取的自然存在物,无须约定,它本身就具有天然的表达力。这种表达力来自存在物自身的力的结构,如:高耸入云的雪山呼唤出“巍峨”的意象,随风飘动的杨柳激起“轻柔”的感觉,粗大的桥墩给人以“稳重”“坚实”的印象。纪录片制作者一方面利用自然存在物的天然性表达意义;另一方面,也通过视听语言的修辞赋予自然的存在物二次元的含义,例如把杨柳多次穿插在纪录片中,有意强化杨柳与片中人物的关系,那么杨柳便成为片中人物性格的象征。德国著名导演文德斯在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去世二十年后(1983年),带着摄制组来到东京,拍摄了一部寻找小津痕迹的纪录片《寻找小津》。在这部纪录片的开始部分,文德斯首先呈现了小津的影片《东京物语》的开场镜头:火车从镜头前驶过,火车发出的声响不但简单有序,而且节律感十足。在展示了小津的《东京物语》中的火车后,文德斯把镜头直接转向了现实状态下的东京火车站,伴随着火车的声音是怪诞而刺耳的。通过两个不同时空的自然音响的对比,其象征性便自然地显现出来,如文德斯在解说里所说明的:“小津谨慎地在与西欧文化保持一定距离的基础上,以缅怀过去的心情,传诵着已经消失的东西。”
语言学意义上的象征性使得纪录片可以突破就事论事的简单记录层面,赋予影片更为深刻的含义。但是,作为视听连续体,作为非推论式的“生物性”记录历史的工具,纪录片所摄取的现实景象还包含了多种复杂的含义,要使这些含义为人感知和领悟,还必须像做艺术品那样,赋予影片艺术性,如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所言将人类情感转变为可见或可听的形式。①[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格里尔逊领导的英国纪录片运动,在电影表现手法、电影语言的探索上,大胆革新和实验,创作了一批富有艺术想象力和艺术创新精神的纪录电影。英国纪录片运动开启之时,有声电影刚刚出现。电影纷纷大肆引入声音,因此也破坏了无声电影时期建立起来的电影视觉表现力,好莱坞因此也陷入“百分之百有声电影”的泥潭。对纪录电影来说,解说和同期声的进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毕竟,言辞语言可以消除视觉符号的多义性,可以使其意义的表达变得更加明白和清晰。格里尔逊对声音进入电影十分敏感,但他并不主张滥用解说,他坚信电影的声音并不只是简单地为视觉画面提供显而易见的对话和音乐伴奏,而是能够做出更加丰富和独特的贡献。英国纪录片运动中产生的《锡兰之歌》《夜邮》《采煤工作面》等一批影片,对声音的表现力进行了艺术性的实验和风格化探索。《夜邮》的诗意语言运用,不但与赞美劳动的主题吻合,还使纪录片增添了浪漫的艺术色彩。从目的论上看,艺术的目的在于美,而纪录片的目的在于揭示真实,求美和求真是人类两种不同的追求,因此我们一般并不把纪录片看作是艺术。但不是艺术并不影响纪录片作品必须具有艺术性。英国纪录片运动对素材富有激情的艺术化处理,不仅在内容、思想和精神上令人耳目一新,同时在表现形式上也颇有新意和感染力,使得纪录片成为像艺术作品那样丰富的情感表达形式。
(二)言辞符码的明晰性与视听符码的多义性
电影接近艺术的符号性质,决定了其表达的形式更多的不是诉诸推理而是诉诸受众心灵上的领悟。镜头里呈现的含苞欲放的花蕾与枯萎的花瓣,自身就会有天然的表达力,无须约定,就会在接受者身上激起不同的心理反应。
可是,习惯了言辞表达的制作者,总会情不自禁地喜欢使用言辞的符码来表达,这种方式当然更经济、更具有概括性。一部关于老王生活状态的纪录片,可能要花几个月时间跟踪拍摄,最终形成的影片时间可能长达几十分钟。从经济、效率的角度上看,这是一件费力又并不见得讨好的工作。如果用简单和经济的方式去解释老王的生活状态,可能就是一句话:“老王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爱认死理,不善交往,因此他的生活并不如意。”可是,这样的概括,没有其生活的过程、细节,没有鲜活的视听动作去支撑,缺乏生活实感和现实的节奏。如果全片充满了这种疏离感觉经验的、干巴巴的、推论性的解释,自然就不能称其为纪录片。
言辞属于文化符码,具有文字语言的约定性。口头和文字语言所构成的言辞语言,是大脑思考或整序的产物,属于推论性的语言系统,它通过推论性的阐释,在大脑中形成模糊的意象,其思维方式依靠的是词汇按照严谨的语法规则进行线性的排列表达意义,其思维方式是线性的,其意义具有相对的明确性、单一性和透明性。
通过摄影机和录音机记录下来的自然符码,是连续的、整体的、生物的和物理的。这类符码在观众的心中激发的意义领悟或读解往往是多义的和含糊的。视觉景象包含了许多信息,这些信息转瞬即逝,在观众的大脑中只能留下深浅不一的印象(不像文学读者那样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慢读或重读)。镜头里一辆轿车急速驶过街道,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大部分人可能有一个大体的印象。由于镜头没有最小的信息单位,又汇集了各种视听信息,因此观众对镜头的感知是不同的:有的人把目光聚焦于走过的美女;有的人专注于街道边的流浪狗;有的人则注意背景中巨大的广告牌……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这个过程,其描述者只能选择一种具有比较明确指向性特点的事物加以说明,如“一辆轿车急速驶过大街”。这句描述语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导至轿车因速度所带来的冲击力上,消解了镜头的多义性和含糊性。再如文字语言描述的“一座坚实的老屋孤零零地立在田野边”,文学读者的反应可能大都局限于“孤独、坚强”,可是在没有文字提示的情况下,影视的观众可能会产生“冷漠、骄傲和排他的”印象。
镜头中的自然符码,具有天然的表现力和表现性,影像和声音丰富的暧昧性给观众提供了对其含义领悟的多样性,而这种多义性恰巧是电影符号的魅力所在。
关于文学修辞和电影修辞的差异,已故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周传基先生曾有过精辟的论述:
“文学需要对事件和人物进行描述;电影是发生在观众眼前的运动,也就是一种存在。观众是在观察一个过程,然后自己做出判断。
文学的隐喻需要修饰语;电影记录因其精确性与具体性取消了形容词。
文学的读者在文字中所意识到的形象存在于读者的思维之中;电影使观众意识到形象和感知的东西是等同的,思维融化在感知中。”①周传基:《视听语言教程补充教材(续一)》,《电视艺术》1994年第3期,第49页。
纪录片并不排斥言辞的解说,但是,电影由于记录的精确性与具体性取消了形容词。因此,其言辞的修辞最好是说明性的。镜头里呈现出一幅如画的高原风光,观众并不知道镜头里的时间和空间,用解说词可以加以说明:“这是云南高黎贡山的夏季。这里的景色显示出高原的特色。”至于高原景色是美丽还是壮丽,是否独具特色,是否具有魅力等,由观众根据自己的视听感知经验去做出独立判断,无须用解说越俎代庖。
在有关人物的影片中,我们常常听到类似于以下风格的言辞修饰语:“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映刻着岁月的痕迹;他高高隆起的皱纹里,记录着艰难的生命历程。”这样的文学味十足的修饰语,独立地诵读,确实是动听的美句;但是,在纪录片里,却是对观众的读解或判断力的不尊重。镜头中人物的脸是否饱经风霜,皱纹是否高高隆起,经历是否艰难,观众在观看影片后会自行做出判断,这就像镜头里的姑娘是否漂亮观众会根据自己的视听感知经验和审美观得出结论一样,无须制作者用言辞去修饰。
如今,“纪录片”一词已经成为一个被广泛套用的词汇。大量使用解说词的纪实性影片,都被冠名以纪录片。在这类“影像+解说”的宣导式影片中,作为文化符码的解说词在影片中占据了主导的位置。以拍摄一所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的宣传片为例,其解说词写道:“这是一所已经有156年历史的建筑,它虽然历经风雨,今天依然巍然屹立。在人们心中,它是一所具有神性的古老建筑。”我们不妨做一点分析:
“这是一所已经有156年历史的建筑”是说明性的,由于观众在呈现的镜头里只看到了房子的老旧的影像,并不了解这所房子建造的时间和历史过程,因此,这样的说明性解说是合理而符合视听基本特性的。“今天依然巍然屹立”“具有神性的古老建筑”是一种制作者主观性的判断,这种判断是由制作者自行做出的。事实上,镜头里的建筑有其自身的表现性,它是否“巍然屹立”,是否是“神性存在”,应该由观众自己去判断,而不是由制作者将自己的判断强加给观众。
在这里,解说显然具有高居现实之上的权威性,它可以直接地、明确地、单一地对摄影机前的影像进行阐释,即不仅说明现实,还解释、评价现实,甚至作为评判者裁判现实。至于这一建筑影像是否引发观众“巍然屹立”的感知,人们是否把这一建筑当作“神性存在”,是不需要解说词解释的。
在纪录片中,大量使用超叙事时空的解说词可以使观众接收到意义单一、明确或透明的信息。在铺天盖地的解说词轰炸下,观众没法冷静地思考或沉浸于其中,常常被动地接受,由此也不需要去思想。对于那些不想思考的观众而言,看有解说的片子对他们来说是件快乐的事,制作者已经为他们代劳了劳神费心的思考。但是,进行这种无须解释、至高无上地替代群体的界定或判断,显然是一种武断而又粗暴的做法,也违背了视听媒介自身的记录本性,由此常常引发的人们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也就毫不奇怪了。
(三)本体符码的主观性和暗示性
在视听符码的四个序列中,自然符码通过自身的天然表达力形成意义,共性符码运用其他的艺术语言表达意义,文化符码则运用约定的符码意义形成非本体的修辞关系。因此,四类符码中,特性符码是整个视听符码中区别于其他媒介或语言的本体符码。
纪录片的镜头来自摄影机前的现实,常规情况下的纪录片并不能虚构,这就限制了制作者对共性符码和文化符码的设计和运用。因此,自然符码和特性符码成为纪录片视听语言运用中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方面自然符码本身显示出天然的表现力,另一方面其制作者也通过具有特性的符码表达自己对摄影机前现实的主观态度和思考。
《巴卡老寨》是云南资深记录人谭乐水制作的一部关于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基诺族人的纪录片。影片开头,一辆拖拉机深陷斜坡上的泥地里不能前行,基诺族村民不得不下车推行。这个段落完全可以加上修饰性的解说强调自然环境的恶劣,但谭乐水并没有这样处理,他把摄影机置于推车人的身后,以低角度拍摄了人们推车的动作。镜头里,拖拉机的车轮陷入泥地后的车辙看起来像两道“泥墙”,镜头前推车人的“泥腿”被夸大,整个镜头形成了巨大的视觉张力。比起用解说词去阐释的修辞方法,这种摄影机角度选择的修辞手法的运用更具有生理和心理的冲击力,也符合媒介本体的纪录属性。
纪录片《寻找小津》里,文德斯视点下的东京充斥着各种嘈杂的声音。在有关嘈杂东京的一系列展现之后,文德斯将镜头转换到小津的电影里:电影是如此安静!即使有声,也是优雅而有序的。现实里的东京与电影里的东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两个段落的对比中,文德斯并没有用语言去解说,而是运用剪辑将两个时空并列在一起,采用这种视听对比的修辞方式,让观众自行做出判断,从而对小津电影里理想化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印象。
《老街映像》是笔者于2006年拍摄的一部有关云南省文山老街的纪录片。这部没有解说的纪录片长达四十多分钟,呈现了制作者视点下的老街。首先,为了突出制作者对老街那种陈旧的印象,笔者有意将摄影机的画面设置进行了减色调处理,同时多采用逆光拍摄,使得这部影片看起来好像是一部黑白片。其次,为了突出城市与乡村的不同,有意在线条上强调了城市景观的垂直线条和乡村景观的水平线条。在无言辞解说的情况下,观众通过垂直线条与水平线条所形成的力的结构,感受到城市的拥挤、压迫和乡村的开阔、舒展。
视听媒介的材料是光波与声波,由于光与声的生理刺激性作用,这种媒介是十分感性的。传统的文学或戏剧叙事,其结构表现出情节或故事的因果关系。但是,视听作品的结构设置却不一定遵循这个原则。法国的纪录片《人类》,从全球65个国家中选取了2020位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让他们在黑色背景前的近景中叙说他们的经历和故事,内容涉及爱情、生命、宗教、死亡、亲情、战争、杀戮等。影片无解说,也隐藏了叙说者的姓名、身份、国别等信息。擅长拍摄地球自然奇观的导演扬·阿尔蒂斯-贝特朗在被叙说者的自述间,别出心裁地将宏大、壮阔的地球自然奇观穿插其中——这种结构,虽然缺乏理性引导或戏剧性,但却更具有“生物性”或视听的和谐性。其从人物影像到自然景观的转换十分自然,观众的思绪因此从具体的人物命运被拓展到天地人合一的境界中,引发观众从更为广大、更为宏观的视角来审视人类和地球,从无限的时空流逝中对照出生命的参差。
与言辞相比,视听语言更具有感性的力度和心理的冲击力!作为较为感性的语言,视听的修辞方式首先诉诸观众的生理,然后引起其心理的反应,进而形成视听思维。由于在视听修辞手法的运用过程中往往进行对视听感知经验的模拟,因此其传达的方式是暗示。这种暗示性既保留了观众对事物多义性领悟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又可以表达制作者的主观倾向。因此,通过特性符码的修辞,通过模拟我们视听感知经验和主观思维活动的视听语言处理的纪录片,既遵循视听语言的基本规律、尊重视听思维的传播特点,同时又是符合视听媒介的记录本性的。
结 语
视听媒介的出现,为人类的历史记录增添了新的方式。与推论性的文字记录相比,视听的记录是“生物性的”。
视听符号包容了太多的子符码,纪录片制作人可以有多种的选择权,有些人关注情节、人物和对话,有些人忙于用解说阐释镜头,有些人热衷于取景、剪辑、摄影机的运动……由此形成了多种风格样式的影片。严格地说,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视听作品,从逻辑上讲,应该是充分运用媒介自身特性符码表情达意、讲述故事的结果,即所有的视听符码都融为一体,构成视与听、时间与空间完全化合为一体的新物质。但是,这样的影片还是太少。
但少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纪录片记录历史的重任。真正的纪录片一方面让摄影机前的现实自然地显示出其本身所蕴含的意义,同时运用电影、电视特有的符码(如摄影机角度的选择、透镜的选择、剪辑等)等进行修辞,表达制作者的主观态度或思想。
由于视听特性符码修辞具有暗示性和经验性的思维特点,其镜头呈现形式并不违背视听媒介的记录本性,从而使纪录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记录历史的路径:回到现实的混沌性和多义性中,从对物质世界的感知开始,通过符合视听本性的视听修辞,表达对摄影机前现实的思考和判断,在对事物的生理感知和心理领悟中寻找真相,最终认识和理解世界,进行对历史的真实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