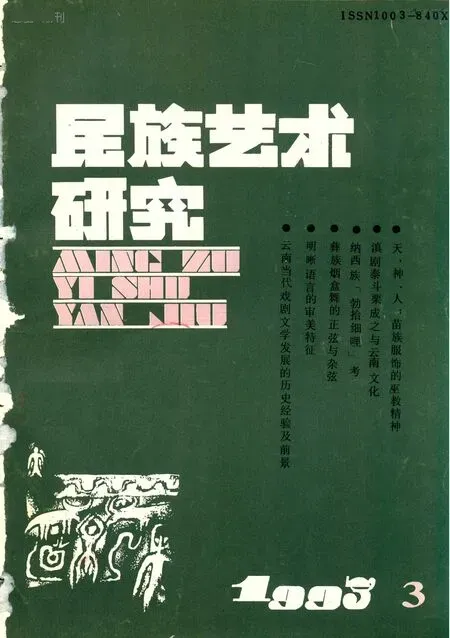当代中国舞剧叙事形态研究
2021-07-15董丽
董 丽
在舞剧成为一门艺术时,关于舞剧的本性是“舞”还是“剧”,便成为舞蹈理论界争辩的焦点。“舞”自不必说,这里的“剧”,指的是“讲故事”,即所谓的“叙事”。至于舞剧的叙事形态,则是舞剧叙事的全部要素所形成的舞剧整体性的精神品质和艺术特点,它包含着创作者对舞剧本质及其艺术特征、艺术手段等问题的认知与思考。本文就当代中国舞剧的叙事形态进行考察,旨在为当下“舞剧叙事”形态的发展提供参照,为中国舞剧的创新贡献内涵和新鲜特质。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当代中国舞剧”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末是客观事实,但本文所做的“当代中国舞剧叙事形态”研究将其时间做了后移,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舞剧创作实践。
一、以“哑剧叙事”形态为代表的时期
关于“哑剧舞蹈”或者说“舞蹈的哑剧叙事”,首先是由18世纪法国伟大的舞蹈大师、舞蹈评论家乔治·诺维尔提出的。他认为:舞蹈的生命和表现力是由“情节”和“哑剧”赋予的。在他看来,“哑剧舞蹈”是“动作舞蹈”的灵魂,而“哑剧叙事”的主要手段则是采用“手势”;百余年后的福金继承并发展了诺维尔的主张,进一步提出了“拟态叙事”的观点,即:“在一切场合上都要努力用整个身体的哑剧表演来取代手势,人可以也应该从头到脚整个身体都成为富有表情的”,①于平:《从“哑剧叙事”到“隐喻叙事”(上)——试述中国当代舞剧叙事的历史进程》,《艺术评论》2018年第4期,第83页。他认为要用“整个身体进行哑剧表演”来进行舞蹈的叙事;此后,经历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更是有诸多编导更新发展了“舞剧叙事”的进程,开始关注于如何“使哑剧服从于舞蹈动作的规律”以及“构成富有情节性的、舞蹈化了的哑剧手段……”
我们追溯原始生发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舞剧创作,发现其对于“舞剧叙事”的表达与认识,正是受上述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从“哑剧叙事”开始的。虽说这一时期是中国舞剧创作的初始期,却也成为中国舞剧史上的第一次创作高潮期,创作出多部具有代表性的舞剧。如现实主义形式下的“新舞剧”《和平鸽》《蝶恋花》《五朵红云》,传统主义形式下的“民族舞剧”《宝莲灯》《小刀会》《鱼美人》等等。其中,《和平鸽》被称为我国“大型舞剧”的“第一次尝试”,《宝莲灯》更被公认为鲜明成型的中国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剧。纵观这一时期的舞剧创作,我们发现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探索解决“如何在民族文化艺术的传统基础上,吸收外来的经验,创作新型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舞剧形式”,①黄伯寿:《回忆舞剧〈宝莲灯〉的创作过程》,载《舞蹈舞剧创作经验文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而这个探索最终的落脚点就是“哑剧叙事”的编舞理念。不仅在实践层面,当时的舞蹈理论研究也有不少关于讲述舞剧中“哑剧叙事”的文章,如耐石的《关于舞剧的戏剧结构》、晓符的《浅谈舞剧中的哑剧》、杨书明的《浅析哑剧和舞蹈》等,这些文章既有对哑剧构成形态进行的界定,还有对哑剧表现手段的功能、哑剧手段运用的“舞蹈化”问题以及哑剧与舞剧艺术的“民族化”问题等诸多方面较为详细的阐述。当然,文章的观点大都认为哑剧的表现手法比较适合舞剧用来表现对情节的叙述。此外,“更有论者认为哑剧是我国传统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中的重要表现手段,以至于对哑剧这一表现手段的运用甚至构成了这一艺术的重要表现特征。”②于平:《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哑剧叙事”形态的中国舞剧创作,对舞剧中“哑剧”手段的理解和应用是最为突出的问题,有观点就认为:“哑剧”是舞剧表现中不可缺少的手段,但切不可只“哑”无“剧”,也不可见“剧”不见“舞”。看来,“哑剧”问题在我国舞剧理论建设的萌生之期就已经开始被关注了,它的根本就是如何理解“舞剧”艺术中“舞”与“剧”关系的问题,而这也是至今我们仍然在探讨的问题。这一时期舞剧的叙事结构基本遵循了故事现象层的发展逻辑来铺陈剧情,即按照“引子、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线性时空结构进行,具体体现在情节叙述的完整统一以及“起承转合”的脉络清晰,呈现出“剧舞交融”的叙事形态特征。以1959年创作的大型民族舞剧《小刀会》为例,最能清晰地显示出这种叙事特征。当时创排该剧时,编剧张拓提出:“先把舞剧脚本按哑剧形式排出来……这种试排要求演员进入角色的规定情境,合乎逻辑地进行舞台行动,惟一的限制是从不准说话却要使观众看得懂表演的内容。预定有独舞和双人舞的地方,要求演员准备符合角色性格的内心独白和潜台词;需要表演舞的地方则暂时用其他情绪接近的舞蹈代替……”③张拓:《〈小刀会〉创作的历史回顾——兼论舞剧的发展道路》,载《舞蹈舞剧创作经验文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于是,这部舞剧的“情节舞”是以“揭示规定情境中角色的内心世界”为原则(舞中有剧),“表演舞”也意在“合情合理地存在于规定情境中”(剧中有舞);再如同一年创作的少数民族舞剧《五朵红云》,也是同样强调“以剧扬舞”“以舞言剧”并且同样致力做到“剧舞交融”。隆荫培对其评论道:“《五朵红云》舞蹈和戏剧情节的发展紧密无间地融合在一起,使得它们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④隆荫培:《充满革命激情的舞剧——评〈五朵红云〉》,《文艺报》1959年1月3日。
以“哑剧叙事”形态为代表时期的舞剧创作,虽说编导们已经开始关注如何更好地处理“舞”与“剧”的关系,但是由于对舞蹈自身规律的认识不足,因此仍有诸多问题存在。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此类舞剧无法离开哑剧来塑造人物、更无法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因而“影响着舞剧把握现实、特别是当代现实能力,也严重影响着舞剧作为一种独特舞台表演艺术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⑤于平:《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页。
二、以“交响叙事”形态为代表的时期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得国家在各个方面都遭受了难以弥补的严重损失,当然也给“舞剧创作”带来了浩劫。在“演革命戏,做革命人”的号召下,作为优秀样板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被推向了全国。“即便是‘优秀样板’,也无法遮掩创作的凋败和舞台的荒凉。”①于平:《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在这里我不多做赘述。转眼到了1979年,这一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年,同时我们也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庆典,这些都为中国舞剧创作的再崛起提供了历时性机遇。这一阶段,中国舞剧创作也呈现出蓬勃喷发之势,创作了大批优秀作品,包括《丝路花雨》《文成公主》《半屏山》《奔月》《铜雀伎》《凤鸣岐山》《大禹的传说》等等。创作上呈现的百花齐放之势皆源自作品在风格、流派、题材、手法上的不同,叙事形态当如是。
虽说这一时期舞剧叙事形态多样,但首要提及的还是“交响叙事”。实际上,这一从苏联借鉴而来的叙事手法不论是对此阶段还是之后的舞剧创作影响都是颇深的。于平指出,“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舞剧创作才在局部不自觉地出现了‘交响叙事’——起初叫‘复调式手法’。”②于平:《从“哑剧叙事”到“隐喻叙事”(上)——试述中国当代舞剧叙事的历史进程》,《艺术评论》2018年第4期,第87页。说到“交响叙事”,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交响化”。其实它是一种音乐戏剧形式,往往通过作曲家写一个性格主题,然后不断发展变化,并在不同场景出现,以此加强作品表达的意蕴。舞剧的“交响叙事”由此借鉴而来,表现为“编导对剧中人物心理进行多层次的剖析与舞蹈动作的线条、舞姿、韵律、空间的多样化的占有及节奏的转换、动与静的对比调节等诸方面作独特的组合排列。”③方元:《执着的追求——观舞剧〈画皮〉有感》,《舞蹈》1984年第4期,第12页。作为这一时期极为推崇的创作手法,众多编导们创作出了一批富有审美价值的舞剧作品,如舒巧的《奔月》、苏时进的《一条大河》、张守和等人的《无字碑》、范东凯和张建民的《长城》、蔡国英等人的《阿Q》等等。其中,创作了《无字碑》的张守和在《舞剧的交响诗化——交响舞剧〈无字碑〉的创作意识》一文中就写道:“交响乐是我们创作《无字碑》的主要支柱。全剧结构也正是深受其影响而构思设置,四幕的构成如同四个相互独立又有机联结的四个乐章;将几个侧面的心理状态、情感变化、矛盾对抗,交织成多层次、立体化的心理情态结构……”④张守和:《舞剧的交响诗化——交响舞剧〈无字碑〉的创作意识》,《舞蹈》1989年第9期,第12—13页。从剧中可以看出,“复调”的运用形成了戏剧构成的对话,而“奏鸣曲”的运用则完成了戏剧冲突的展开与解决。这部舞剧的成功也充分说明,采用“交响化”手段进行创作并没有削减舞剧的“戏剧性”,而是把“戏剧性”建构在了人物性格冲突的基础之上。和之前的“哑剧叙事”形态相比,我们发现,“前者更注重情节的线性发展、性格的线性成长以及冲突的线性展开,而后者更注重情境的多重意蕴、性格的多重组合以及冲突的多重交织。”⑤于平:《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可以说,“交响叙事”形态下的舞剧构成更符合舞蹈的审美,它提高了舞剧创作“生产力”的水准,推动了舞剧创作的进步。
虽说此时舞剧创作因“交响叙事”手法的应用而彰显出开创性,但是也有因沿袭并深化传统叙事手法并同样表现不凡的作品出现,如仲林等创作的《木兰飘香》。这部舞剧仍然采用了线性叙事结构,但是它较好地解决了“戏剧性结构的舞剧化问题”(哑剧叙事),使得舞剧在对题材处理、情节安排、人物形象塑造及性格刻画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它可以说是“民族舞剧”创作的一次重要挺进。除此之外,还有以“心理描述和心理结构”为叙事亮点的舞剧《祝福》《魂》《家》《林黛玉》等;有以追随话剧“戏剧处理舞蹈化”(尽可能避免“哑剧化”形态)结构的舞剧《雷雨》;有以具有“散文诗式”叙事结构的舞剧《红楼梦》《觅光三部曲》;还有以“戏剧性结构与主体意识有机结合”结构的《悲鸣三部曲》……正如傅兆先所言,这一时期的“中国舞剧在走向成熟阶段,舞剧的结构方式也早已打破了情节结构单一线状的形态,而有了多种新的结构方式的创造。”①傅兆先:《系统整合的舞剧美——评舞剧〈阿诗玛〉》,《民族艺术研究》1993年第1期。“舞剧结构方式上的演变促进着中国舞剧艺术形式多样化的发展。”②傅兆先:《略谈舞剧的民族化与现代化》,《舞蹈艺术》总第2辑。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舞剧创作的第二个大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叙事形态把触角伸到了之前传统叙事舞剧不能到达的地方。从只能讲述表层的故事或做出有限的心理探索,到能较为深入人物和故事的各个层面,舞剧的张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当然,肯定一种形式的创新时,也要看到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能否认,这一阶段也有一些舞剧过于强调叙事形态的“个性化”,结果变成“为叙事而叙事、为手法而手法”,使得剧情割裂得支离破碎,让人不知所云。然而不管怎样,以“交响叙事”形态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舞剧叙事确实为中国舞剧的探索提供了积极的力量,它不仅在当时,也对后来的舞剧创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以“心理叙事”形态为代表的时期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就在舞剧编导个人的创作风格得到有效呈现之时,一种新的舞剧叙事形态,即:“心理叙事”形态也以它的方式开始了表达。追溯其产生的背景,则是源于“舞剧整合的精细化必将由内向心理之维发展,舞剧对人的表现将会有内在深化的更高层次。”③傅兆先:《舞剧的整合性》,《舞蹈艺术》总第26辑。这一时期,不仅初步形成了舞剧叙事形态的理论体系,而且创作实践也开始走向了艺术的自觉。
首先,在理论上,胡尔岩从舞蹈创作心理学角度提出了“非传统式结构”理论。她阐述道,“非传统式结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受传统的戏剧式结构规律的限制,不强调故事情节的完整性,不依据故事情节发展线索进行场次安排,而是以人物的内心活动为依据进行场次或舞段的安排,强调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多方面开掘与表现。”④胡尔岩:《舞蹈创作心理学》,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页。这一理论观点无疑为“心理叙事”形态舞剧的创造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注脚。此时在实践领域,也确实创作出一批具有上述叙事特征的优秀舞剧。具有代表性的舞剧有舒巧创作的《红雪》《玉卿嫂》《胭脂扣》《三毛》《青春祭》,以及应萼定创作的《女祭》《诱僧》《倩女幽魂》《如此》等。胡尔岩就《玉卿嫂》曾评论道:“舒巧舞剧《玉卿嫂》作品具有感染观众的人物内心展示,在舞剧心理结构样式上,做了开辟性的创作探索。”⑤胡尔岩:《我看舒巧的舞剧营造》,《舞蹈论丛》1989年第1期,第15页。虽说舒巧、应萼定二人舞剧创作的构成方式不尽相同,但大概由于他们之前有着多年的合作关系,因此对于结构舞剧的理念还是相当一致的,即:以心理动机为推进剧情发展的动力。与此观点如出一辙的还有门文元、邓一江以及与舒巧在精神上达成某种默契的“现代舞”编导王枚。门文元创作的舞剧《阿炳》,“摒弃讲故事、交代情节的陈旧的创作思维方式,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开掘和揭示人物内心深处最隐秘、最真实的情感上来”;邓一江创作的《情殇》,“关注的不是‘戏剧性’赖以发生的‘环境冲突’,而是‘戏剧性’的‘心境较量’”;而王枚创作的《雷和雨》,则是“做了人物深层心理的剖析,使我们看到一部‘心理现实主义’的‘现代舞剧’”。⑥于平:《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页。以“心理叙事”形态进行舞剧结构,其优势还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可以运用内心直视的手法,深入到人物的内心,当然也就避免了忽视人物内心表现的非舞剧化弊病。
除“心理叙事”形态外,此时期也还有一些采用“交响叙事”形态创作的舞剧,但是在叙事上出现了一些革命性的变化,表现为更加追求“虚与实结合、心理描写与剧情发展结合”的特征,如周培武等创作的《阿诗玛》、肖苏华创作的《阳光下的石头——梦红楼》、陈维亚创作的《大梦敦煌》、张建民创作的《二泉映月》等。另外,还有一个编导不得不提及,那就是蜚声中国舞坛的张继钢。张继钢可谓是量多质高的舞蹈编导,他早期的舞蹈作品如《献给俺爹娘》《俺从黄河来》《黄土黄》《一个扭秧歌的人》《好大的风》等奠定了业内至高的地位,而其创作的舞剧《野斑马》《花儿》及后来的《千手观音》《一把酸枣》也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当然,他的舞剧叙事手法也在不断求索中得以多元化,直至《千手观音》所采用的“格式塔”编舞理念,更是开掘了“心灵的可舞性”。于平在文章中写道:“舞剧《千手观音》的‘舞蹈自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觉地舞蹈’,而是舞蹈作为一种造型媒介‘直指心灵’的自觉,一种把内心的意念外化成可感形象的自觉,一种把内心的情操外化成可感情节的自觉,一种把内心的视像外化成可感动态的自觉……”①于平:《直指心灵的舞蹈自觉——从舞剧〈千手观音〉看‘格式塔’编舞理念》,《民族艺术研究》2011年第2期,第5—6页。“当我们评价一部作品的优劣时,不能仅仅从结构样式的‘新’或‘旧’上论成败,而要看它是否深刻、生动、完整地同表现内容融为不可剥离的整体来进行综合的评价。”②胡尔岩:《舞蹈创作心理学》,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胡尔岩如是说。这些优秀创作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舞剧叙事形态的不断发展与变换,正是源于创作者们对叙事规律的不断探索。
与20世纪80年代的舞剧叙事形态相比较就会发现,虽然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叙事上仍然具有多元化特征,但是它们总体表现为更加注重情境的多重意蕴、性格的多重组合以及冲突的多重交织。即:能够注意表现丰富的现代意识,塑造立体化的形象和深入解剖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因为沉迷于自由叙事的愉快而忽视了对人物整体形象的塑造和对故事意义的深掘,也有部分舞剧给观众造成了像是一篇浅显的哲理性叙事文的印象。
四、以“隐喻叙事”形态为代表的时期
何为“隐喻”?“从经验主义角度来看,隐喻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理性。它使人们能通过一种经验来理解另一种经验,通过赋予由经验的自然维度结构化了经验完形来创造连贯性。新的隐喻可以创造新的理解,从而创造新的现实。”③[美]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页。借鉴这一概念,21世纪以来,中国舞剧创作也开启了“隐喻”叙事之路。
“隐喻叙事”形态的舞剧创作不再单以人物或相关事件为中心,而是着重于“叙事视角”的灵活转换和巧妙设置,如对其背景、情节、事件、时空进行提炼重组,根本目的在于“引导出某种观念目标或发人深思的主题”。事实上,对于“隐喻叙事”这一创作理念的最先运用,应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舞蹈创作界不遗余力推广“交响编舞”的肖苏华,他在1992年创作的舞剧《红楼梦幻曲》中就已初露端倪。用肖苏华自己的话说,这部舞剧“首次摆脱了讲原著故事而转向自我表达,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借题发挥’。”④肖苏华:《舞剧创作探索与创新——我的舞剧理念(上)》,《舞蹈》2014年第9期,第17页。其实,这里的“借题发挥”就是“隐喻”。而其在2005年现代舞剧《梦红楼》及2007年创作的现代芭蕾舞剧《阳光下的石头——梦红楼》(在“交响叙事”中也有提及),更是直接将表达的焦点移向了现代青年的生存状态,开创了我们在此文中所要表述的“以一个概念去建构另一个概念”的“隐喻叙事”形态时期。而这一时期,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舞剧创作最为蓬勃发展的时期,涌现出大批的代表性舞剧作品。例如韩真、周莉亚创作的《杜甫》。这部舞剧没有进行杜甫传记的叙事,没有设计情节因果的戏剧冲突,而是以体现杜甫一生伟大成就的诗歌进行架构,“提供了一个依托舞蹈本体展开舞剧叙事的契机”。①于平:《诗圣的痛苦 诗史的根——大型舞剧〈杜甫〉观后》,《艺术评论》2016年第7期,第83页。这里特别需要提及,舞剧用了幻觉(幻化出另外一个“杜甫”)的手段去努力地开掘人物的内心。虽然幻觉中的“杜甫”与叙事情节无关,但却是一种具有精神内核的人文指代(本我、超我的对抗与自我救赎),它让舞剧在叙事层面上获得一种更为饱满的情绪与意蕴空间,也使整部舞剧形成一个相对完整且涵意深厚的隐喻体系,所寄托的是导演对人性的参悟和期望;还比如上海芭蕾舞团聘请德国导演帕特里克创作的芭蕾舞剧《长恨歌》,其叙事结构是以“梦”为线索,通过“入梦、梦寻、现实、入梦”这一倒叙并首尾呼应的形式讲述了唐明皇与杨玉环的凄美爱情故事。此外,编导还从具体事物中剥离并抽象出来一个“意象化”的人物——“月宫仙子”,应该意在以她独特的存在方式告诫众生——相对于历史的滚滚车轮,再刻骨铭心的爱情也终归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浪花(人类的命运走向)。这个意象化“月宫仙子”,当然也是一种理性世界的隐喻和象征。在对上述作品进行叙事形态分析中,我们会发现,它们除了都采用“幻化”人物的手法外,在空间结构上也都具有相同的特征,就如张萍所述:“采取空间结构方式的舞剧,在舞台上不再受事件的顺序、倒序还是插叙等时间秩序的规限……空间可以自如穿梭、并置、交织、叠套,但绝不随意,舞剧结构的空间性取向唯一可参照的是舞剧叙事的逻辑。”②张萍:《求上得中,求中得下——“歌舞演故事”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当代舞蹈艺术研究》2017年第4期,第100页。而这一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胡尔岩提出的“时空互化”理论,她说道:“人物的主观意识活动可以任意穿插于现实性很强的场景之中;在时空关系上,打破现实生活中的时空顺序,把过去、现在、未来交织在一起,组成一种新的、人物的心理时空顺序。”③胡尔岩:《舞蹈创作心理学》,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6年版,第116页。总括而言,一部优秀的舞剧正是通过这种多层次的(包括“幻化”人物)、交错重叠的复杂的手法,才能最终达成“切中题旨”的“隐喻叙事”目的。说到这里,笔者认为还有必要提及一部“现象级”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对于这部被冠以“首部谍战”题材舞剧的叙事手法,编导之一周莉亚如是说:“舞剧采用时空上的叙事切割方法,在有些段落,本来有的画面全部打碎、重组;有些用了倒带,有些用了假定空间中的真实性,还有真实空间中的假定性。总之,用了非常多叙事上面的功能性的表现形式。”④李盛:《“真实”与“假定”交错中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海艺术评论》2019年第4期,第16页。可以说,《永不消逝的电波》以自身为最恰切的实践,为我们思索今后的舞剧创作该如何更好地叙事提供了绝佳契机。
总体说来,近年来以“隐喻叙事”形态进行创作并且取得成功的舞剧作品可以说非常之多,除上述作品外,还有包括《西施》《唐寅》《沙湾往事》《粉墨春秋》《水月洛神》《梅兰芳》《尘埃落定》《朱鹮》《醒·狮》《大禹》《天路》《草原英雄小姐妹》《打金枝》《赵氏孤儿》……同样,它们的叙事手段也非常多样化,影像交互、戏中戏,以及“蒙太奇”手法多次运用等等,这些不仅让舞剧叙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流畅与自由,也让舞剧有了一种“诗学性”的阐释,从而进入更加深厚的哲学层次。当然,有探索就会有失误,有些舞剧只顾探索新颖的叙事方式,甚至只为叙事方式的与众不同,难免会出现“形式与内容”本末倒置等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编导们对于叙事方式上的探索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不仅为舞剧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成果,更为舞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结 语
徐岱在其著作《小说叙事学》中提道:“在小说世界中,常态与异态,规范与超越永远是一对矛盾,但其结果却是艺术模式的自我更新于蜕变而不是退出历史舞台。”①徐岱:《小说叙事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纵观中国舞剧叙事形态从哑剧、交响、心理到隐喻的更迭演变,我们不难发现其规律与小说的演进相仿,也是常态与异态、规范与超越、模式与反模式之间的辩证运用。不妨说,一部中国舞剧叙事形态的发展演变史,也是一部中国舞剧发展的历史。换言之,中国舞剧叙事形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逻辑,参与和建构了中国舞剧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坚信,中国舞剧叙事的探索之路还在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