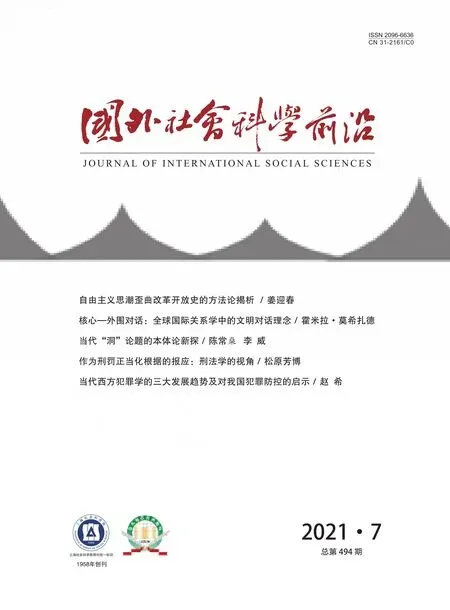当代“洞”论题的本体论新探*
2021-07-13陈常燊
陈常燊 李 威
在现代物理学界,爱因斯坦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洞论证”(hole argument),证明了任何广义协变的理论都要违背他所坚持的因果性原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因果决定论。这个论证既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又富有深刻的哲学洞见。无独有偶,在当代分析哲学界,特别是在形而上学家们讨论世界的本质结构问题时,自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分析哲学家刘易斯夫妇(David & Stephanie Lewis)的经典论文《洞》1David Lewis and Stephanie Lewis, Hole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48, 1970, pp.206-212; reprinted in David Lewi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I,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3-9.发表以来,哲学家们围绕“洞论题”(hole thesis)纷纷著书立说,激发了众多的哲学论争。
如果说,当代科学界对爱因斯坦的“洞论证”耳熟能详,那么,当代哲学界对刘易斯夫妇的“洞论题”则所知不多,因此有必要向国内学界进行介绍,并深入研究。“洞论题”在当代哲学家眼中并不简单,其研究价值不可小觑。直觉告诉我们,“洞”似乎是某种“缺失”(absent),一种不包含任何其他事物的“空无”(void),我们怎么能对一个“缺失”之物作出本体论承诺呢?但同时,我们的直觉又习惯于对“洞”作出本体论承诺,即存在“洞”;并且还对“洞”这一对象作了额外的承诺,“洞”具有倾向性属性(dispositional properties),它具有可被填充这样的一种倾向,而这样的一种属性也将“洞”作为一个对象置入了因果链条之中。当代分析的形而上学与“缺失”之物是不相容的,因为这门学科的主流是物理主义——只对典范的物质对象(paradigm material objects)作出本体论承诺,显然“洞”并不是这样的对象。“洞”问题对本体论框架造成了冲击,我们没有一种合适的本体论范畴来容纳“洞”这一神秘的实体。于是,哲学家们做了很多工作,试图为“洞”在本体论框架中找一个位置。笔者将这一工作称之为“洞”的本体论问题——即追问“洞是否存在”与“洞属于哪一类本体论范畴”。
一、“洞”的本体论问题:争论与原则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不会被“洞”问题所困扰。显然,直觉告诉我们,“洞”就像其他日常对象一样,总是如其所是地呈现给我们。思考这样的两句话:这条时尚的牛仔裤是有“洞”的;这个杯子的杯口是一个“洞”,从而我们可以把水倒进和倒出。这些陈述似乎对“洞”作了合理的本体论承诺,即“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我们说“牛仔裤上有一个洞”和我们说“牛仔裤上有一个小熊吊坠”其实是做了类似的工作。当代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也验证了我们这一直觉的观点,这些研究事实表明,婴儿和一些动物可以像成年人一样感知、计数和追踪(track)“洞”,就像我们对待日常对象那样。1T.Horowitz and Y.Kuzmova, Can We Track Holes? Vision Research, vol.51, 2011, pp.1013-1021.因此,我们的首要工作便是预备性的。一方面,笔者会提出一个关于“洞”的本体论问题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框架;另一方面,也会提出考察与评价这一框架内诸观点的方法论,即解释力、直觉性与经济性三原则。
(一)“洞”的本体论问题:反实在论与实在论之争
“洞”的本体论问题是对“洞”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范围的限制,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讨论“洞”的本体论问题。在当代物理学、认知科学、拓扑学以及相关的科学哲学等学科内部也有针对“洞”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洞是否存在”是对本体论的追问,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出现了“洞”的反实在论与实在论之争:反实在论也可以看作取消主义(eliminativism),其主张“洞”不存在,我们只是在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的意义上谈论“洞”;实在论则认为“洞”存在,其内部的分歧是由于在处理的是“洞属于哪一类本体论范畴”这一问题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有的哲学家持“对象主义”(objectualism)的立场。“对象主义”和“非对象主义”的区分出自菲利普•约翰•梅多斯(Phillip John Meadows)的观点。1Phillip John Meadows, What Angles Can Tell Us About What Holes Are Not, Erkenntnis, vol.78, 2013, pp.319-331.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梅多斯自称是“洞”问题的反实在论者,但其反实在的意义是在反对洞是一种“对象实在”的角度上提出的,在一阶的“洞是否存在”的问题上,他持的仍是肯定的态度,只不过是在属性和关系的意义上。因此笔者将这一观点置入了实在论阵营之中。有的读者可能会有一种看法,即梅多斯的观点与反实在论者有接近的地方,对此,笔者持开放的态度。认为洞是对象,为了使得“洞”能与“对象”这一范畴融贯起来,分别有紧缩论(deflationary theory)、膨胀论(inflationary theory)和约定论(conventionalism)三种观点。这一区分来自克里斯蒂•米勒(Kristie Miller)。2Kristie Miller, Immaterial Beings, The Monist, vol.90, 2007, pp.349-371.
我们需要注意,这里提及的“紧缩论”与我们通常在形而上学讨论中使用的“紧缩论”有区别。传统意义上的“紧缩论”主要认为实在论者的观点是琐碎的,是语词之争。而这里米勒对“紧缩论”的使用主要是指一种理论承认了更少的范畴,如用物质对象这一范畴解释了我们直觉上认为其不是物质对象的事物。米勒的“紧缩论”也可以被视为“一元论”。尽管如此,出于与“膨胀论”相对应的目的,笔者还是决定在本文中沿用米勒的用法。有的哲学家持“非对象主义”(non-objectualism)的立场,认为洞不是对象,而是抽象实体。在紧缩论者看来,非对象主义也应该是本体论膨胀的。因为紧缩论者只承认物质对象存在,并不承认抽象实体,如属性或关系。因此,这一框架是开放的。
“洞”的本体论结构图示如下:

(二)解释力、直觉性与经济性
“洞”的本体论问题的讨论纷繁复杂,每种观点又坚持了不同的形而上学立场,正如罗伯托•卡萨蒂(Roberto Casati)和阿希尔•瓦尔兹(Achille Varzi)所说:“在所有这些选择中,洞是受奥卡姆剃刀的影响,还是被简化为其他实体,还是只看表面价值,这取决于一个人一般的形而上学倾向。”1Roberto Casati and Achille Varzi, Holes,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holes/.进一步说,笔者认为,对于“洞”的本体论问题的考察,应该遵守以下三个原则的限制:
(1)解释力原则:一个理论是好的,当且仅当,它能满足理论自身的一致性,即有更少的悖论、不会自我反驳等;同时,它还应给予被解释者足够充分合理的解释。
(2)直觉性原则:一个理论是好的,当且仅当,它能够满足我们的直觉性认识。
(3)经济性原则:一个理论是好的,当且仅当,它能够遵守理论的节俭性美德,即奥卡姆剃刀的经济性要求。
这三原则之间并非三权分立,其中有权重上的差异。解释力原则具有最高的权重,一个更好的理论首先应该有更强的解释力。显然,如果一个理论自身充满漏洞,同时不能给予被解释者足够有力的解释,那么它就不能被严肃地对待。同时也应保有一个宽容的态度,有的理论尽管并不精致,但其存在的缺陷并不致命,或者说它的缺陷只是技术上的,那我们似乎可以对其抱有更高的期待。直觉性原则与经济性原则的权重则相对较低,同时,这两个原则也应服务于解释力原则,即一个理论可以为了追求更好的解释力而对直觉性和经济性有所放弃。但这里面存在一个程度的问题,过于的反直觉与不经济也会削弱一个理论的解释力度。总之,在实际操作中,这三个理论会变得更加清晰。
二、“洞”的本体论问题的反实在论立场
反实在论者认为“洞”不存在,对“洞”的本体论讨论是琐碎的,我们应该在形而上学的讨论中取消“洞”的实在意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体现这一立场。其中一种观点由弗兰克•杰克逊(Frank Jackson)提出,2Frank Jackson, Perception: A Representative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他认为洞就是“洞衬”(hole-lining)或“洞围”(holesurrounds),我们谈论“洞”实际上就是在谈论包围“洞”的物质,也就是在谈论我们认为有“洞”的那个物质对象,并不存在实体意义上的“洞”。如“牛仔裤上有洞”这句话就应理解为“牛仔裤上有洞围”,“我的牛仔裤上洞的数量和他牛仔裤上洞的数量一样多”就应理解为“我们两人的牛仔裤上有同样数量的洞围”。
另一种反实在论观点与前者相比更为精致,其借刘易斯夫妇经典论文《洞》中的虚构人物阿戈尔(Argle)得以表达。这一观点认为,“当我们认为某物上有洞时,我的意思无非是它被穿孔了”,“……被穿孔了”和“……是有洞的”是同义的形状谓词,我们在说“牛仔裤上有洞”时,我们其实是在说“牛仔裤是被穿孔的”,也就是说牛仔裤具有“被穿孔”的形状,这和我们说“一个苯环的分子结构是正六边形的”具有同样的哲学意味。而我们之所以在假装谈论“洞”,实际上是受了日常生活习语的影响,出于便捷交流的目的,才对“洞”进行了存在量化——“它有洞”。
彼得•范•因瓦根(Peter Van Inwagen)借虚构哲学人物阿伯特(Albert)之口将这样一种虚假的本体论承诺解释为维特根斯坦式(Wittgensteinian)的“语言游戏”。1Peter Van Inwagen, Alston on Ontological Commitment, Existence.Essays in Ont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37-152.他认为“哲学屋”里的空气比起日常生活的空气稀薄,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正常谈论的东西,如“洞”,就不能放进严苛的本体论之中进行承诺。他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来反映这种区别,当哥白尼走出他的书房后,他当然可以说:“太阳已经移动到榆树后了,天气变得凉爽了。”这并不是说哥白尼认为太阳围绕地球旋转,而是他在那样的一种语言环境下所自然而然的表达,我们需要借助上下文语境作出理解。
笔者认为,除了“语言游戏”的解释外,我们也可以将阿戈尔的观点理解为谓词唯名论(predicate nominalism)的一种。即当我们说某物有“洞”时,只不过是说,“……是穿孔的”这一形状谓词适用于这一事物,而“……是有洞的”和“……是穿孔的”这两个谓词并不涉及本体论承诺,也不指称“洞”这一共相,而只是一种语言内部的形状谓词转换。
尽管反实在论者看似很轻松地解决了“洞”的本体论问题,但他们没有得到大多数形而上学家的支持。一个直接的反对意见就是,如果“……有洞的”可以理解为“……是穿孔的”这一形状谓词,那么我们是否能够想象这样一种语言,可以包含所有关于有“洞”物体的必要形状谓词。考虑三种情况:
(1)我牛仔裤上的“洞”和你牛仔裤上的“洞”一样多;
(2)牛仔裤上的“洞”和书包里的书一样多;
(3)根据卡萨蒂和瓦尔兹的区分,洞有不同的类型:洞腔(cavities)、洞陷(hollows)和洞群(tunnels)等。2Roberto Casati and Achille Varzi, Holes and Other Superficialit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
这一区分受到了刘易斯夫妇的反对,3David Lewis and Stephanie Lewis, Holes, in David Lewi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I,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3-10; reprinted in D.K.Lewi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3-9.一方面他们认为这种区分是不严格的,他们列举了一些其他类型的洞的例子;另一方面,在笔者看来,刘易斯夫妇也会认为这种区分是琐碎的,因为这些类型的“洞”都是“洞”这一集合中的成员,这一集合内的成员是否应该分类讨论也值得商榷。笔者对这一问题持中立的立场。但如果对“洞”进行类型上的区分,的确有助于反驳反实在论者的观点。
针对情况(1),反实在论者会认为,这是由于两条牛仔裤是同一形状的,如都是“单穿孔的”、“双穿孔的”……,随着“洞”数量的增加,我们的形状谓词的数量也会膨胀,直到无法表达。正如阿戈尔所嘲讽的那样:“您知道很多不同的形状谓词啊!您是怎么抽时间把它们全部学完的呢?”1David Lewis and Stephanie Lewis, Holes, in David Lewi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I,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4.
情况(2)变得更加棘手。反实在论者为了缓解情况(1)的困难,需要借助二元谓词“同样穿孔”进行描述。但这样就会使得当我们把洞和其他日常对象的数量进行比较时,不得不将日常对象进行穿孔,使之与有“洞”物体具有相同的形状谓词,这一比较才能进行。这显然不是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
情况(3)反映出来“洞”这一概念的使用是模糊的。“洞腔”是内部中空,但没有外部入口的一种“洞”;“洞陷”是只有一个入口的“洞”;“洞群”则是有两个及以上入口的“洞”。形状谓词是否能满足“洞”的不同形态,也值得怀疑。
另一方面的反对意见来自更深层次的形而上学立场。当代分析的形而上学坚持的目标是要“从关节处切割世界”,也就是要从客观中立的立场处理不同的对象、属性以及事件,将它们置入合理的本体论范畴之内。而“维特根斯坦式”的“语言游戏”则并不注重客观实在以及物理学告诉我们的知识。相反,它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寻找一种语境下的共同理解。换言之,“维特根斯坦式”的反实在论者是将“洞”问题拿到了形而上学之外进行讨论,“洞”的本体论问题不能作为我们基本形而上学的一部分。这种取消主义的立场一般不会被我们视为对本体论问题的妥善解决。
在笔者看来,反实在论者在经济性原则上做得很好。他们没有承认更多的范畴和实体,只承认物质对象的存在,“洞”的本体论问题可以被还原为关于物质对象的命题。但其在解释力原则和直觉性原则上做得不够。一方面,如上所述,尽管维特根斯坦式的“语境论”是分析哲学中很核心的观点,但其不是一个合格的形而上学的解释方法。我们不能接受“语境论”在形而上学论题中的解释力,因为它在本质上对形而上学持“取消主义”的态度,大量实质性的形而上学论题都可以被解释为语境的问题,尤其是本体论问题。另一方面,反实在论者的观点也不符合我们的直觉。我们既不认为“洞”就是物质部分,也不认为关于“洞”的讨论只是一种“语言游戏”。恰恰相反,直觉会告诉我们,“洞”就存在在某物之上,尽管它是空无的,但它也应该是一种对象。这种直觉,在笔者看来,是对因果链条的直觉的延续,即直觉告诉我们,“洞”在一些因果链条中扮演了重要的因果角色。
三、对象主义:紧缩论、膨胀论与约定论
实在论的对象主义立场是处理“洞”的本体论问题的主流观点,其认为“洞”存在,而且是作为日常对象而存在。但显然,“洞”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日常对象有着巨大的区别。一张桌子存在,我们可以在物质构成(material constitution)的角度上说,一些基本粒子按照一定的排列方式构成了桌子这一日常对象。即使我们是物质构成的取消主义者,我们也可以说,尽管桌子作为一个日常对象不存在,起码构成桌子的那些基本粒子也是存在的。但“洞”却不同,我们直觉意义上的“洞”不由任何事物组成,恰恰相反,有“洞”存在反而说明那里一无所有,空无一物。那么我们如何去识别“洞”?“洞”的同一性条件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为了对象主义实在论者争论的焦点。
(一)紧缩论
刘易斯是最为著名的“洞”的本体论问题的紧缩论者。他的观点有两个基本的前提:其一,他坚持唯物主义和唯名论,即世界上只存在物质对象;其二,“洞”存在。根据这两个前提,他认为“洞”是物质对象,且是典型物质对象的适当部分和表面,“洞”即“洞衬”,换言之,“洞”不是物质对象所包围的那部分空无,就是包围空无的那部分物质对象。为了更明确地理解刘易斯的观点,我们需要在这里做一些区分和说明。首先,刘易斯和杰克逊的取消主义具有相似之处,即他们都注意到了“洞衬”对于“洞”定义的重要性,但二者却有本质区别。取消主义者认为不存在“洞”,我们只需要将“洞衬”识别出来即可,在本体论上不存在“洞”这类实体;而紧缩论者认为“洞”存在,“洞衬”是“洞”的识别及同一性条件,我们对“洞”进行的本体论讨论不是琐碎的。
借助物质构成的观点来理解,刘易斯持的是放任主义观点(permissivism),“洞衬”和“洞”是时空偶合对象(spatio-temporally coincide objects),两者共时空占位,且是两个不同的对象。杰克逊在物质构成上是取消主义者,只存在“洞衬”,而“洞”不存在。其次,刘易斯区分了同一(identity)和相同(sameness)。“洞”和“洞衬”是同一的,只有与“洞衬”相同一的“洞”才具有同一关系;而那些“共穿孔”的“洞”是相同关系,即“当两个洞有一个共同的部分本身就是一个洞时,它们就是相同的洞”。1David Lewis and Stephanie Lewis, Holes, reprinted in D.K.Lewi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pp.3-9.如图1,其中a是中间的空部分;b为“洞衬”,其与洞b相同一;b和c形成一个大洞衬bc,其与洞bc相同一。在刘易斯看来,洞b和洞bc相同,因为它们有共穿孔的部分a,且洞b和洞bc不同一,因为它们的“洞衬”不同一。所以当我们在说有一个“洞”时,其实我们指称了数量庞大的相同但不同一的“洞”。并且,刘易斯区分了“洞”的容积和体积。我们识别一个“洞”的大小时,是在识别其“洞衬”的大小,而非识别中间穿孔的空间的大小。

图1
刘易斯将“洞”紧缩为物质对象的部分——“洞衬”,看上去很好地回应了“洞”的本体论问题,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直觉代价,我们还是在谈论我们一直在谈论的那个“洞”吗?这种对直觉的放弃也招致了其他哲学家的反对。让我们来看图2、3、4。1Roberto Casati and Achille Varzi, Holes and Other Superficialit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 pp.27-28.

图2
在图2中,通常我们认为字母h位于“洞”内,字母l位于“洞”外。但如果我们将“洞”识别为“洞衬”,l处于“洞衬”内,于是就成为了“洞”里,h处于“洞衬”外,就变成了“洞”外。同理,直觉告诉我们图3中黑色鱼形状的部分为“洞”,而刘易斯则会认为白色B区域为“洞”。在图4中,直觉告诉我们,左边图形的“洞”(黑色部分)小于右边图形的“洞”(黑色部分),但刘易斯告诉我们,左边的“洞”是更大的,因为它的“洞衬”体积更大。

图3

图4
关于刘易斯的“洞”的反直觉之处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例举,因为他几乎颠覆了我们对于“洞”的所有直觉——“洞”存在这一直觉除外。反直觉并不总是一个有效的形而上学反对意见,为了追求解释力,我们可以在直觉性原则上作出让步。2刘易斯的可能世界理论也反直觉,但由于其在形而上学方面具有突出的解释力,我们通常不会以此拒绝这一理论。但刘易斯对于“洞”的解释离我们的直觉过远,以至于好像偏离了我们一开始要追问的事物,我们所要问的,或者说我们的“惊异”所起之处,是中间的空无之处能不能作为“洞”存在,而非“洞”的指称是什么。换言之,刘易斯只是告诉了我们“洞”是什么,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那片空无——直觉上的“洞”——是什么。因此,尽管刘易斯在经济性原则上做得很好,但他在直觉上放弃了太多。正如上文所述,过度的反直觉也会削弱解释力——我们已经不是在解释我们所想解释之物了。
当然,坚定的唯物主义唯名论者会成为刘易斯的紧缩论的拥趸,许多人正在尝试让刘易斯的观点变得更加精致。安德鲁•韦克(Andrew Wake)等人提出过一种新的观点,作为对刘易斯观点的修正和补充。1A.Wake, J.Spencer and G.Fowler, Holes as Regions of Spacetime, The Monist, vol.90, 2007, pp.372-378.他们认为洞是合格的时空部分且“洞”是四维实体——所谓“洞”的移动是“洞”时间部分的移动,“洞”的其他可能状态是其对应体的状态。笔者对其的反对意见在于:如果按照韦克等人的观点,我们是按照“时空中不连续的点”识别“洞”,那么我们怎么去识别“时空中不连续的点”?键盘的键与键之间是不连续的,那里存在“洞”吗?组成物质对象的基本粒子之间也是不连续的,我们能说那里也存在着大量的“洞”吗?这似乎偏离了我们对“洞”的直觉。因此笔者认为,针对刘易斯观点的回应也适用于这一观点。
(二)膨胀论
膨胀论,顾名思义,就是承诺了更多的事物和范畴,从而形成了本体论上的通货膨胀。持这一观点的哲学家主要有唐纳德•霍夫曼(Donald Hoffman)2D.D.Hoffman and W.A.Richards, Parts of Recognition, Cognition, vol.18, 1985, pp.65-96.等,他们将洞看作是其物质对象宿主的“负”部分,因此一个有“洞”的物体就是一个“混合的聚合体”,由其物质构成的“正”部分与洞的“负”部分组合而成。由于卡萨蒂和瓦尔兹在“洞”问题上做了大量细致且值得尊敬的研究,囿于篇幅,我们主要以这二人在其经典著作《洞与其他的表面性》中的观点为例,展开对膨胀论的论述。
卡萨蒂和瓦尔兹对洞的思考完全尊重我们日常生活的直觉,他们认为“洞”存在,且就存在于我们通常以为它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即那片空无之处。关于这种直觉,具体可以解释为以下4点:
(1)“洞”在我们的直觉中就是缺失,就是一个物质对象中间那“非”物质的一部分。
(2)“洞”在本体论上总是寄生的,也就是说它总要依附在某个物质实体——“洞主”(host)之上。换言之,“洞”总是具体对象上的“洞”,如牛仔裤上的“洞”、苹果上的“洞”,等等。没有宿主的“洞”是无法设想的。
(3)“洞”是可以被填充的。也就是说,“洞”具有倾向性属性,可以被“洞客”(guest)所填满,但如果没有填充物,“洞”也不会消失。
(4)直觉所理解的“洞”是三维的,具有自身的拓扑属性。如我们之前提及的“洞腔”、“洞陷”和“洞群”之分。
刘易斯为了追求本体论上的简约——只承认物质对象的存在——而不得不放弃关于“洞”的大部分直觉。卡萨蒂和瓦尔兹则完全相反,他们为了满足我们对于洞的直觉,不得不放弃本体论上的经济性原则,把“洞”置入一个新的、充满争议的本体论范畴——“非物质体”(Immaterial Bodies)之中。有的论文中将其称之为“非物质存在”(Immaterial Beings)。卡萨蒂和瓦尔兹首先区分了两种空间,一种是合格的空间,它具有附加属性(additional properties)对它加以限定。物质对象,如一张桌子,就是对于空间的这样一种限制;另一种是不合格空间,它缺乏物质对象的限制,因此在我们在传统形而上学中就会认为其是不合格的空间,卡萨蒂和瓦尔兹也称其为裸露的(bare)空间。裸空间也是空间,同时它具有被填充的潜能——所谓合格的空间不过是这一潜能转化为现实后的情况。1Roberto Casati and Achille Varzi, Holes and Other Superficialit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94, p.34.如图5所示:

图5
卡萨蒂和瓦尔兹认为,其中的阴影部分就是“洞”,它作为一个非物质体依附在其物质宿主之上,卡萨蒂和瓦尔兹将其比喻为“负面的蘑菇”(negative mushrooms),寄生在物质对象的表面。同时它也是一个具有潜能的非限定空间,具有被填充的倾向性属性。
针对这种膨胀论的观点,有两种反对思路。一种是认为,尽管膨胀论很好地满足了我们的直觉,但它在解释某些特殊情况时和紧缩论一样的反直觉,如梅多斯就认为非物质存在论在解释“洞”的数目时,并不比刘易斯的紧缩论更有吸引力。这种反驳在笔者看来并不致命,因为它只是指出了这一理论的不精致之处,我们可以通过对理论进行再解释以缓解这类反驳的力度。另一种反对则更为严肃,即我们是否能够允许在我们的本体论框架中存在“非物质体”这类范畴,且这类范畴和物质范畴具有同等的本体论地位。如果我们对于形而上学框架具有比较宽松的态度,那么“非物质体”似乎是可以被容纳的;如果我们是严格的唯物主义唯名论者,那么这种范畴的存在显然是无法忍受的——起码它没有满足我们的“形而上学直觉”——“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卡萨蒂和瓦尔兹是旗帜鲜明的刘易斯观点的反对者,他们走上了一条不同的解释道路,即为了满足“洞”的直觉而放弃了经济性原则。“非物质体”是一个可疑的范畴,且卡萨蒂和瓦尔兹对这一范畴的解释也是含混的。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卡萨蒂和瓦尔兹在解释力原则上做得比刘易斯好。一方面,卡萨蒂和瓦尔兹对“洞”做了更多的解释,几乎涉及了关于“洞”的所有形而上学问题。如“我们如何数洞?”“洞的因果关系及倾向性属性如何解释?”“洞的部分论结构(mereological structure)如何理解?”“如何看待洞的拓扑学组合?”等。另一方面,“非物质体”和物质对象的关系与元形而上学(metametaphysics)的奠基(grounding)理论很契合。奠基理论家乔纳森•谢弗尔(Jonathan Schaffer)曾在他的经典论文《论何物奠基于何物》中提及“洞”的本体论依赖(ontological dependence)问题并引用了卡萨蒂和瓦尔兹的观点。1Jonathan Schaffer, On What Grounds What, in Chalmers, et al.(eds.), Metataphys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9.
(三)约定论
约定论是米勒提出的一个观点,她将这种观点视作对紧缩论和膨胀论的一种调和:一方面,她认为所有的实体都是物质的;另一方面,她也支持洞的直觉主义——我们认为有洞的区域确实有实体。为了满足这一调和的观点,她把“洞”看作是更为稀薄的物质,因此洞也是物质对象,与雕塑、苹果这类物质对象没有质上的区别。让我们回到图2。在米勒看来,a和b都是物质,其区别并非“有”和“无”,而是“多”和“少”,b区域相较于a区域,基本粒子更多且排列更为紧密。同时,在物质组合(material composition)领域,她是一个普遍主义者(universalism),即除实体a和b外,还存在a和b部分论上的和ab。
米勒具有一种倾向,她试图通过“洞客”定义“洞”,换句话说,她认为“洞”必须存在“洞客”,“洞客”是对“洞”的限定。这在我们这个世界是可能的,因为根据我们宇宙的性质,没有一个区域的场值一致为零,看似空旷的空间实际上在量子层次上有着恒定的能量波动。但如果存在一个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这个世界里的基本粒子足够稀薄,以至于“洞”里根本不存在基本粒子,那么我们还能说“这条牛仔裤是有洞的”吗?尽管这条可能世界的牛仔裤上确实有一个我们直觉上所理解的“洞”。
尽管米勒认为自己的观点是膨胀论和紧缩论的中间路线,但在笔者看来,她仍是一个隐藏的紧缩论者,即只存在物质对象。所以她也面对和刘易斯同样的困境——坚持经济性原则,但在解释力原则和直觉性原则上做得不够好。也就是说,直觉告诉我们,“洞”可以是空的,并且这一直觉可以在可能世界里得到实现。为了满足这一直觉,我们需要一种可以将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融贯起来的解释理论。但米勒在她论文结论中却说:“我认为,一个洞并不是一种非物质存在,尽管也许某些世界里的一些洞是非物质存在。”2Kristie Miller, Immaterial Beings, The Monist, vol.90, 2007, p.370.
显然,米勒意识到了可能世界带来的反驳,她试图作一些妥协性的回应。但这一回应却削弱了理论本身的解释力,即这是一个只适用于现实世界的理论,而“洞”作为一个对象在不同世界的识别和同一性条件则是不同的。
四、非对象主义
非对象主义认为洞不是对象,而是某种抽象实体。如梅多斯认为它们是属性或关系;克里斯•麦克丹尼尔(Kris McDaniel)认为它们是关系实体“在之中”(being-in);1Kris McDaniel, Being and Almost Nothingness, Noûs, vol.44, 2010, pp.628-649; Kris McDaniel, Holes Cannot Be Counted as Immaterial Objects, Erkenntnis, vol.80, 2015, pp.841-852.克里斯蒂安•马丁(Christian Martin)认为“洞”是负存在的使真者(truth-makers for negative existentials)或正存在的使假者(false-makers for positive existentials)。2Christian Martin, How It Is: Entities, Absences and Void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74,1996, pp.57-65.梅多斯的观点更前沿,我们以介绍他的观点为主。他的论证过程可简写为:
(前提1)角(angles)不是对象,而是对象的一种属性或关系;
(前提2)角和洞具有相同的形而上学性质,属于同一形而上学范畴;
(结论)洞也是一种属性或关系。
进一步来说,梅多斯认为“角”就是物质对象彼此之间的一种关系,如曲阜孔府有著名的景观“勾心斗角”,《阿房宫赋》里也有“各抱地势,勾心斗角”之名句,这都反映出房檐之间有一种边角对峙的状态,“角”正是各房檐之间的一种关系或属性。“洞”也是如此,我们说“牛仔裤上有一个洞”的意思就是说,牛仔裤的物质对象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或属性,即“洞”。用梅多斯本人的话来说,即:“洞是物体各个部分之间的空间关系,根据这个关系,这些部分围绕着一个原则上不包含任何物质的空间区域。”3Phillip John Meadows, What Angles Can Tell Us About What Holes Are Not, Erkenntnis, vol.78, 2013, p.326.
既然“洞”是一种抽象实体,那么它是何种意义上的抽象实体呢?梅多斯列出了两种可能的选项,其一是大卫•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ong)的内在共相(immanent universals),另一种是爱德华•乔纳森•洛尔(Edward Jonathan Lowe)的四范畴论中的属性(attributes)和模式(modes)。前者认为抽象实体是一种共相,但同时共相不是超验的,而是内在于具体物质对象之中的。具体而言,“洞”作为共相是一种可重复的实体,它完全存在于每一个“洞”的例示所在之处。后者认为,模式或特普(tropes)4“ 特普”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抽象殊相,即其既是一种抽象对象,同时也以“束”(bundle)的形式构成具体殊相。一般的“特普”理论家们持有一种本体论上的一元论,认为世界是由“特普”构成的。是一类非实体殊相(non-substantial particulars),属性是非实体共相(non-substantial universals),属性被抽象殊相所例示。换言之,“洞”作为属性或关系,既有共相也有殊相,每个物质对象上的“洞”是对“洞”共相的例示。这样既解释了“洞”形态上的拓扑学差异,也把“洞”与作为物质对象的“实体殊相”(substantial particulars)和作为类的“实体共相”(substantial universals)区分开来。梅多斯对这两种观点的态度是暧昧的,但总体上,他对于洛尔的解释更为青睐。
梅多斯的看法使得“洞”不再那么特殊,“洞”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属性或关系,是事物的存在方式。但这种对“洞”问题的简化处理也带来了这种观点的缺陷。在论证“洞”和“角”的相似性时,梅多斯有意把洞做了二维处理,他从“洞”的二维切面与“角”的二维切面的类比开始,认为两者可以还原为“V”形,并且认为“……V形:一个有棱角的图形。不管这里有什么,它都会产生和三维洞一样的形而上学问题”。1Phillip John Meadows, What Angles Can Tell Us About What Holes Are Not, Erkenntnis, vol.78, 2013, p.325.尽管梅多斯作了很多论证的努力,但把“洞”抽象为二维图形这一前提是否合理,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按照我们的直觉,以及卡萨蒂和瓦尔兹的论证,“洞”是形态各异的三维实体,“洞腔”“洞陷”和“洞群”具有不同的拓扑学特性。二维的“洞”是否回避了大量实质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横切面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完全存在一个角度,从那里切开,我们无法把二维的“洞”识别出来。换言之,怎么切“洞”也是一种直觉的做法。此外,把“洞”看作抽象实体也与我们的直觉观点不符,如怎么解释“洞”似乎拥有的倾向性属性,怎么理解“由于有个洞,所以水从瓶子中流走了”这一陈述中,“洞”所扮演的因果角色。
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在笔者看来,梅多斯将“洞”处理为非对象实体具有很好的形而上学前景。首先,在解释力上,“洞”作为一种属性或关系,能很好地和当代属性理论家的观点相契合,如“内在共相论”“特普论”等。这些属性观点在形而上学讨论中很主流,且展现出了很好的解释力。当然,如果要让“洞是一种属性或关系”这一观点与这些属性观点契合起来,它还需要变得更加精致。其次,在直觉性上,“洞”是事物的一种属性或关系并不过度地违反直觉,尽管这一观点有滑向取消主义的倾向。最后,在经济性上,虽然梅多斯承认了抽象实体范畴的存在,但抽象实体并不是一个像“非物质体”那样突兀的范畴。显然,本体论者擅长争论抽象对象的存在问题,这一争论在当代仍旧是十分前沿且实质性的。
五、小 结
综上所述,“洞”的本体论问题在当代出现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借助解释力、经济性和直觉性三原则,我们对争论的诸观点进行了考察。可以看到,这些观点都具有“偏科”的特色——在某些原则上坚持得很好,但在另一些原则上又会做得不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重的。一方面,观点的选择和哲学家的本体论立场息息相关,有的哲学家习惯于为了追求解释力而反直觉,如刘易斯;有的哲学家则更喜欢保留关于“洞”的直觉,如卡萨蒂和瓦尔兹。另一方面,这一情况也源自“洞”本身的特殊性。它就像游牧民族,并不会直接介入一套本体论框架的构造,但一旦这一本体论框架被提出来,它就要受到来自“洞”问题的考察。出于捍卫自身本体论框架的目的,哲学家们不得不像古代守城的士兵一样,在深夜里慌忙备战,以应对意想不到的“攻击”。
“攻击”一方面是猛烈的,也就是说,“洞”的本体论问题是本体论者们不得不去处理的。另一方面,这一“攻击”也是持续的,“洞”的本体论问题的不断侵扰使得不同的本体论框架变得越来越精致。但不同的理论在处理“洞”的本体论问题时具有不同的潜能。在笔者看来,“非物质体”的观点和非对象主义的抽象实体的观点具有更好的本体论前景。前者和元形而上学的“奠基”理论相契合,也就是通过追问在本体论框架中“何物更基本”来缓解其所面临的经济性压力。将我们的本体论考察由扁平的(flat)变为层级式的(ordered),或许“非物质体”这一范畴就不再那么令人难以接受。后者可以和当代属性理论相契合,而究竟选择哪种属性理论,或者说,哪种属性理论能更好地解释“洞”,则是更进一步的问题了。关于“洞”的本体论问题的“奠基”解释和“属性”解释都很前沿且空白,这意味着这些论域具有更好的解释空间。换言之,如果我们想要构建一个新的“概念地图”(conceptual maps)来解释“洞”的本体论问题,那么这两种观点或许是不错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