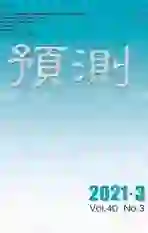亲缘利他水平提高会改善家族企业治理效率么?
2021-07-12谭庆美刘子璇孙雅妮
谭庆美 刘子璇 孙雅妮



摘 要:本文以2003~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主板和中小板家族上市企业数据为对象,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出发,探究实际控制人的亲缘利他水平对家族企业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治理效率与亲缘利他水平之间显著负相关;随着家族企业自成长期发展至成熟期再至衰退期,亲缘利他水平的提高对治理效率的负向影响加剧。进一步研究发现,面临较弱行业竞争的家族企业,治理效率与亲缘利他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无论家族企业面临何种行业竞争环境,企业生命周期的发展均会强化亲缘利他水平对治理效率的负向作用。实际控制人应根据企业面临的行业竞争环境及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家族企业治理效率。
关键词:家族企业;亲缘利他水平;治理效率;生命周期;行业竞争
中图分類号:F27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92(2021)03-0001-08doi:10.11847/fj.40.3.1
Does the Increase of Kin Altruism Level Improv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Family Firm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fe-Cycle Stage
TAN Qing-mei1, LIU Zi-xuan1, SUN Ya-ni2
(1.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2.School of Accounti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listed Chinese family firms on both Main board and SME board during 2003~2018,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kin altruism level of ultimate controlling owners on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family firm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fe-cycle stag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kin altruistic level of Chinese family firms. The negative role of the increase of kin altruism level on reducing governance efficiency is strengthe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irms from growth period to maturity period and then to recession period. The further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kin altruism level on governance efficiency is stronger in family firms facing weak competition.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life-cycle stag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kin altruism level works in both firms facing strong competition and firms facing weak competition. The ultimate controlling owners should adopt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help improving governance efficiency according to the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life-cycle stageof Chinese family firms.
Key words:family firm; kin altruism level; governance efficiency; life-cycle stage; industry competition
1 引言
家族企业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支撑我国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促进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通常会超越商业考虑而以亲缘关系为主要标准挑选企业管理者[1,2],使得实际控制人与家族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关系嵌入了亲缘利他行为[3]。家族企业的治理问题也由于亲缘利他行为而颇具特色,一方面,亲缘利他行为能够增加家族管理者对企业及实际控制人的忠诚度,从而尽心尽力为家族企业工作[4]。另一方面,亲缘利他行为也可能导致“自我控制”问题,使得实际控制人对家族管理者有所偏袒,导致家族企业内部人力资源扭曲[5]。受传统“家文化”影响,中国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对“外人”缺乏信任,更倾向于雇佣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经营[6],使得中国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的亲缘利他水平较高。实际控制人的亲缘利他偏好及水平会直接反应在企业决策过程中,从而深刻影响着家族企业的治理效率。实际控制人的亲缘利他水平对家族企业治理效率究竟具有何种影响?这一问题的探讨对于分析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及家族管理者的行为,规范家族企业治理,提高家族企业治理效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参与企业管理的家族成员数量以及与实际控制人的亲疏远近不同,在利他行为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在家族企业发展早期,参与企业管理的通常为核心家族成员[2,7]。随着家族企业成长壮大,不同亲缘体系的家族成员逐渐加入企业,使得家族企业的亲缘关系及治理问题变得复杂[8]。因此,亲缘利他水平对治理效率的影响可能随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而动态变化。企业决策无法脱离外部环境的影响,行业竞争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对管理者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9]。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能够通过给企业造成生存压力而有效约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促使管理者勤勉尽责,努力提升企业价值,从而缓解代理冲突。而较弱的行业竞争环境不能有效监督与约束管理者的自利行为,管理者提升企业价值的动机较不强烈。因此,家族企业面临的行业竞争环境可能会影响亲缘利他水平与治理效率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基于此,本文选取2003~2018年中国家族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探讨实际控制人的亲缘利他水平对家族企业治理效率的动态影响,并探讨行业竞争对亲缘利他水平、治理效率与企业生命周期之间关系的影响。
和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1)本文尝试从生命周期视角探究亲缘利他水平对家族企业治理效率的动态影响,结果发现随着家族企业自成长期发展至成熟期再至衰退期,亲缘利他水平的提高对治理效率的负向影响加剧。研究结果拓展了有关家族企业亲缘利他行为的研究视角,丰富了家族企业治理及亲缘利他行为相关文献。(2)从行业竞争视角,进一步研究了不同行业竞争程度下亲缘利他水平对治理效率的影响以及生命周期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面临较弱行业竞争的家族企业中,亲缘利他水平对治理效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出亲缘利他水平与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受家族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及行业竞争环境的共同影响,为亲缘利他行为与治理效率之间关系提供了额外的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实际控制人根据家族企业面临的行业竞争程度及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家族企业治理效率,实现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亲缘利他水平与家族企业治理效率
亲缘利他行为是指有亲缘关系的个体为亲属提供帮助或做出牺牲[10,11]。受“家文化”影响,中国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对“外人”缺乏信任[7],更倾向于雇佣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经营,使得中国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的亲缘利他水平较高。由于家族成员之间相互熟悉,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经营有利于沟通协作,减少信息不对称与监督成本[12]。亲缘利他行为以亲情和血缘为连接纽带,是纯粹的、不功利的[13],使得家族管理者之间相互信任与包容,也能够增加家族管理者对企业及实际控制人的信任与忠诚,从而能够为家族及企业长远利益而努力工作,有助于降低家族管理者的寻租行为及家族企业代理冲突[14~16]。因此,亲缘利他水平的提高应有利于提升家族企业竞争力,改善家族企业治理效率。
然而,利他行为也是一把“双刃剑”[17]。利他行为使得家族企业内部存在裙带主义,家族管理者内部会出现与盈利、效率等相冲突的无条件的关爱,从而无法建立基于绩效的理性制度,致使家族企业内部人力资源扭曲[18]。利他行为是盲目的而且是非理性的,能够导致“自我控制”问题[5]。受利他行为影响,实际控制人会超越商业考虑而以亲缘为主要标准挑选企业管理者,可能会雇佣不称职的家族成员[1,2,19],也难以客观公正地对家族管理者的业绩进行评价[12],容易导致家族管理者被“宠坏”,从而产生消极怠工和推卸责任行为等自利行为[2,13]。特别是参与企业管理的家族成员数量较多时,家族成员之间会面临更多的利益冲突[19,20],使得企业代理效率较低。此外,与实际控制人关系的亲疏远近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所获取的资源[21],在家族企业财富有限的情况下,实际控制人只能惠及核心家族成员,在差序格局中处于外圈的远亲家族成员容易产生不公平感,会不可避免地降低对家族及企业的心理承诺,从而出现在职消费、搭便车等自利行为[7],引发家族成员内部冲突。因此,亲缘利他水平的提高不但不能改善反而可能会恶化家族企业治理效率。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 限定其他条件,亲缘利他水平提高对家族企业治理效率具有正向影响。
H1b 限定其他条件,亲缘利他水平提高对家族企业治理效率具有負向影响。
2.2 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
在家族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规模及业务复杂程度不同[22],参与企业管理的家族成员数量以及与实际控制人的亲疏远近不同。在企业初创期,参与企业经营的通常为核心家族成员,核心家族成员由于长期生活在一起,有极强的互惠精神,能够相互包容与信任,容易达成一致性的决策意见[23,24]。家族管理者具有“管家”和“代理人”双重身份,核心家族成员会更多地扮演“管家”角色[25],对家族企业有很强的责任感,更愿意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努力。因此,在家族企业初创期,亲缘利他行为主要发挥积极作用,有助于减少代理冲突。随着家族企业逐步成长,获得一定竞争优势,家族管理者即使不努力工作也可以从企业获得各种资源,容易引发搭便车、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15,16]。此外,伴随着企业成长及规模扩张,不同亲缘体系的家族成员逐渐参与企业经营,致使家族企业亲缘关系变得复杂[8]。当参与企业管理的家族成员较多时,家族管理者将更多地扮演“代理人”而不是“管家”的角色[25],容易出现在职消费等自我谋利行为,也容易出现内斗等损害企业价值的行为[7]。因此,随着家族企业成长,亲缘利他水平的提升反而不利于改善企业治理效率。
发展至成熟期的家族企业组织结构不断完善,利润水平稳定,有丰富的现金流积累,实际控制人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受利他行为影响,实际控制人会利用企业资源为家族成员谋取福利[19]。家族管理者可能会专注于财富分配而不是财富创造,为了赢得实际控制人的注意与赞扬而引发激烈的竞争,从而引发家族内部冲突[8,20]。处于衰退期的家族企业,成长机会萎缩,市场份额和利润开始下滑,企业急需进行战略调整[22]。因此,衰退期的家族企业可能会吸入社会资本寻求转型,也会引入外部经理人加入管理团队。受亲缘利他行为影响,实际控制人难以公平对待家族管理者与外部经理人,使得外部经理人产生心理不平衡,从而降低工作积极性并做出在职消费等自利行为
[1]。外部经理人的加入也会引发部分家族成员决策权丧失,从而引发家族成员与外部经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因此,随着家族企业逐渐成长成熟再至衰退,亲缘利他行为的负面影响加剧,亲缘利他行为产生的代理问题可能会成为家族企业发展的桎梏,亲缘利他水平提高对治理效率的负向影响加剧(或正向影响减弱)。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 限定其他条件,随着家族企业逐渐成长成熟再至衰退,亲缘利他水平对治理效率的负向影响加剧(或正向影响减弱)。
2.3 行业竞争的影响
作为一种市场竞争机制及外部治理机制,行业竞争会影响实际控制人对管理者的激励与监督。激烈的行业竞争能够带来信息比较功能[9],降低实际控制人与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效限制管理者的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促使管理者付出更大努力为家族企业工作,有利于缓解代理冲突,提高治理效率。此外,在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中,家族企业会面临更多竞争对手的威胁,生产经营也面临更大挑战[9,26]。较高的经营风险会迫使家族管理者更为团结,能够进一步缓解代理问题,提高家族企业决策效率。而当行业竞争程度较低时,行业进入壁垒较高,企业面临的挑战与竞争者威胁较低,行业竞争对管理者的约束作用也较弱,不能有效监督与约束家族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家族管理者可能会更多地扮演“代理人”角色[25],专注于权力争夺及财富分配而不是财富创造,致使家族管理者之间出现利益冲突,导致治理效率低下。因此,与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相比,当家族企业面临较弱的竞争环境时,亲缘利他行为的负面影响加剧,实际控制人亲缘利他水平的提高对治理效率的负向影响加强(或正向影响减弱)。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 限定其他条件,当行业竞争程度较弱时,亲缘利他水平对治理效率的负向影响越强(或正向影响越弱)。
无论面临何种行业竞争环境,家族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组织结构及参与企业管理的家族成员构成不同,面临的代理问题也存在差异。在初创期,企业往往由核心家族成员控制与治理,人数相对较少但亲缘关系很强,利他行为将家族成员聚合为一个整体,有利于降低代理冲突。随着家族企业成长成熟及规模扩张,新的家族成员开始加入企业管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与工作积极性下降,也容易出现争夺权力及企业资源等内部纠纷与冲突[7],导致家族企业代理冲突增加。处于衰退期的家族企业,成长机会萎缩,内部治理结构过于复杂,组织灵活度降低,大量外部经理人取代家族成员成为管理者,亲缘利他行为可能会引发外部经理人的不公平感,从而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家族企业代理冲突加剧。因此,无论面临何种竞争环境,随着家族企业自成长期发展至成熟期,最终走向衰退期,亲缘利他行为的负向影响加剧,正向影响减弱。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4 限定其他条件,无论行业竞争环境如何,随着家族企业逐渐成长成熟再至衰退,亲缘利他水平对治理效率的负面影响加剧(或正向影响减弱)。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3~2018年间中国沪深两市主板和中小板A股家族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借鉴王明琳等[15],研究樣本必须符合如下标准:(1)企业最终控制者必须为自然人或某一家族,而且最终控制者直接或间接是上市企业的第一大股东。(2)企业股东或管理层团队中至少有2位或以上家族成员。本文所用样本数据剔除了数据缺失的企业、金融保险类企业以及ST、*ST企业。为消除极端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按1%和99%水平进行了Winsorize处理。其中计算亲缘利他水平所需数据通过CSMAR数据库及企业年报获取,其他变量来自于CSMAR数据库。最后,本文共计整理得到2342个样本数据。
3.2 研究变量度量
3.2.1 亲缘利他水平
亲缘关系包括血亲关系与姻亲关系,借鉴王明琳等[15],谭庆美等[16],以Hamilton亲缘系数度量亲缘利他水平。Hamilton亲缘系数是指两个生物体携带相同基因的概率。若以亲代基因总数为1,单向来看子代(第一世代)个体携带双亲各1/2的基因,即子代与单一亲代之间的亲缘系数为1/2。兄弟姐妹也属于第一世代,亲缘系数也同为1/2。祖孙、甥舅、叔侄等为第二世代关系,亲缘系数为(1/2)2。堂(表)兄弟(姐妹)为第三世代,亲缘系数为(1/2)3。同理,对于第n世代亲缘关系,亲缘系数为(1/2)n。实际控制人的亲缘利他行为通过多条亲缘纽带在家族企业内部发生作用,实际控制人的亲缘利他水平应为实际控制人各条通道亲缘系数的总和。首先确定实际控制人与家族企业董事、监事和高管(以下简称 “董监高”)之间的亲缘关系,接下来采用模型(1)计算Hamilton亲缘系数度量亲缘利他水平
KAL=∑(12)n (1)
其中KAL为Hamilton亲缘系数,n代表实际控制人与“董监高”之间的亲缘关系。血亲关系亲缘系数根据实际控制人与“董监高”之间的关系测度:设实际控制人自身基因总数为1,n取0;若实际控制人与“董监高”之间为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关系,则为第一世代,n取1;若为祖孙、舅甥、叔侄关系,则为第二世代,n取2;若为堂(表)兄弟(姐妹)关系,则为第三世代,n取3。姻亲关系以配偶关系为中介系数,将配偶之间的亲缘系数设定为与第一世代核心家族成员亲缘系数相同,即为1/2,n取1,根据配偶一方的血缘关系按照血亲关系计算实际控制人与姻亲方家族成员之间的亲缘系数。
3.2.2 家族企业治理效率
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改善企业绩效及企业价值,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借鉴贺小刚等[23],分别采用Tobins Q和总资产收益率衡量家族企业治理效率。
3.2.3 家族企业生命周期
借鉴Dickinson[27],采用现金流组合法划分企业生命周期。根据样本家族企业经营活动、筹资活动及投资活动现金流组合特征,将家族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三个阶段。
3.2.4 行业竞争
借鉴张传财和陈汉文[9],采用Herfindah-Hirschman指数(HHI)衡量行业竞争程度,计算见(2)式
HHI=∑ni=1(SALEit/SALEt)2 (2)
其中SALEit为第i家样本家族企业第t年的营业收入;SALEt为第t年参与估算的行业内n家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Herfindah-Hirschman指数越小,行业竞争越激烈。
3.2.5 控制变量
借鉴贺小刚等[23],陈建林[28],选择业主权威、两权偏离度、第一大股东持股、财务杠杆和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并对年份及行业变量进行控制。各变量的名称、符号及含义如表1所示。
3.3 实证研究模型
为验证假设H1a、H1b和H2,分别设计回归模型如(3)式和(4)式所示
FGE=α0+α1KAL+∑8i=2αiCV+δ(3)
FGE=β0+β1KAL+β2LCk+
β3KAL×LCk+∑10j=4βjCV+μ(4)
其中FGE为家族企业治理效率,分别采用Tobins Q和总资产收益率衡量;KAL为亲缘利他水平;LCk(k=1,2,3)为家族企业生命周期,包括成长期(LC1)、成熟期(LC2)和衰退期(LC3);CV为控制变量,包括业主权威(AU)、两权偏离度(SCF)、第一大股东持股(LSO)、财务杠杆(LEV)、资产规模(FS)、年份变量(Y)及行业变量(IND);αi和βj为回归系数;δ和μ为随机扰动项。
为考察企业生命周期对亲缘利他水平与治理效率之间关系的影响,首先将全部样本家族企业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三组子样本。接下来将三组子样本两两组合,在模型(4)中引入亲缘利他水平与生命周期的交互项KAL×LCk,考察生命周期对治理效率与亲缘利他水平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合并后的分组情况为:(1)成长期与成熟期合并为一组,若样本企业属于成熟期,则LC2取值为1;若属于成长期,LC2取值为0。(2)成熟期与衰退期两组子样本合并为一组,若样本企业属于衰退期,则LC3取值为1;若属于成熟期,LC3取值为0。(3)成长期与衰退期两组子样本合并为一组,若样本企业属于衰退期,则LC3取值为1;若属于成长期,LC3取值为0。
为验证假设H3和H4,按照Herfindah-Hirschman指数的均值,将样本家族企业分为高竞争子样本与低竞争子样本两组,对模型(3)和模型(4)进行分组回归分析。
表1 变量名称、符号及含义
变量类型变量名称变量符号变量定义
治理效率Tobins Q总资产收益率TQROA(股价×流通股股数+每股净资产×非流通股股数+净债务市值)/总资产净利润/平均总资产
亲缘利他水平亲缘利他水平KALHamilton亲缘系数
企业生命周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LC1LC2LC3样本家族企业处于成长期样本家族企业处于成熟期样本家族企业处于衰退期
行业竞争Herfindah-Hirschman指数HHI根据(2)式计算得到
控制变量业主权威两权偏离度第一大股东持股资产规模财务杠杆年份虚拟变量行业虚拟变量
AUSCFLSOFSLEVYIND实际控制人同时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取值为1,反之为0实际控制人的所有权/控制权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股本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总负债/总资产样本数据确定为该年度时取值为1,反之为0
样本数据确定处于该行业时取值1,反之为0
4 实证检验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亲缘利他水平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7.125和1.250,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985和1.671,不同样本家族企业的亲缘利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亲缘利他水平与Tobins Q(r=-0.103,p<0.01)及总资产收益率(r=-0.041,p<0.05)均显著负相关。控制变量之间以及控制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相关性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0.4,不存在相关系数过高问题。进一步进行共线性诊断发现,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与检验。
4.2 亲缘利他水平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首先以全部样本家族企业数据为基础,对模型(3)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根据表2中I和II列可见,Tobins Q(α=-0.085,p<0.01)和总资产收益率(α=-0.006,p<0.01)均与亲缘利他水平显著负相关,研究结论接受了假设H1b。这一结果表明,实际控制人亲缘利他水平的提高会破坏家族企业治理效率。
4.3 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的调节效应
为验证研究假设H2,将三组家族企业生命周期子样本进行两两合并,引入亲缘利他水平与生命周期的交互项(KAL×LCk),对模型(4)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可见,比较成长期与成熟期时,Tobins Q和總资产收益率与亲缘利他水平仍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分别在0.01和0.0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与处于成长期的家族企业相比,处于成熟期的家族企业亲缘利他水平提高对治理效率的负向影响加剧。比较成熟期与衰退期以及成长期与衰退期时,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表明与处于成长期及成熟期的样本家族企业相比,处于衰退期的家族企业亲缘利他水平提高对治理效率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由此可见,亲缘利他水平与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受家族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影响。随着家族企业由成长期发展至成熟期再至衰退期,实际控制人亲缘利他水平的增加对企业治理效率的降低作用逐步增强,假设H2得以验证。
4.4 进一步分析:基于行业竞争分组
按照Herfindah-Hirschman指数的均值,将样本家族企业分为高竞争子样本与低竞争子样本两组,对模型(3)和模型(4)进行分组回归,进一步检验亲缘利他水平对治理效率的影响以及企业生命周期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见表3及表4)。根据表3和表4中I和II列可见,当样本家族企业处于高竞争行业时,Tobins Q和总资产收益率与亲缘利他水平之间均不具有显著相关关系;而处于低竞争环境的样本家族企业,亲缘利他水平对Tobins Q(α=-0.151,p<0.01)和总资产收益率(α=-0.016,p<0.01)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家族企业面临的行业竞争程度不同,亲缘利他水平降低治理效率的强度不同。当面临较弱行业竞争环境时,亲缘利他水平的提升对家族企业治理效率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假设H3得以验证。
两组子样本中,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无论家族企业面临何种竞争环境,企业生命周期对亲缘利他水平与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均具有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证实了假设H4。
4.5 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本文进行了三项稳健性检验:(1)借鉴古志辉和王伟杰[29],以担任“董监高”的家族成员数量占“董监高”总数的比值衡量实际控制人的亲缘利他水平,重新进行回归分析。(2)分別以行业调整总资产收益率和行业调整Tobins Q衡量家族企业治理效率,重新进行回归分析。(3)为避免亲缘利他水平与家族企业治理效率之间可能的反向因果关系对实证结果造成的偏差,借鉴连玲燕等[21],将亲缘利他水平滞后一期重新进行实证检验。假设H1b及H2、H3、H4仍然得到了很好的支持,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主板及中小板家族上市企业2003~2018年数据为对象,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实证检验了实际控制人的亲缘利他水平对家族企业治理效率的动态影响,以及不同行业竞争程度下亲缘利他水平、企业生命周期与治理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亲缘利他水平对家族企业治理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实际控制人亲缘利他水平的增加总体上会破坏企业治理效率。(2)当家族企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亲缘利他水平增加对治理效率的降低程度不同。随着家族企业由成长阶段发展至成熟阶段再至衰退阶段,亲缘利他水平降低治理效率的作用显著加强。(3)与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相比,当家族企业所属行业竞争程度较弱时,亲缘利他水平降低治理效率的作用加剧。(4)无论家族企业面临的行业竞争程度强弱,企业生命周期的发展均会强化亲缘利他水平对治理效率的负向作用。
5.2 研究启示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研究启示:(1)受“家文化”影响,中国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的亲缘利他偏好明显。受亲缘利他行为影响,即使家族成员缺乏为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也能够在家族企业获得在其他企业不能得到的高职位。家族管理者虽然有利他动机但也具有自利性,也会追逐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利他行为阻碍了实际控制人对家族管理者的监督与约束,可能会纵使家族管理者偷懒、搭便车等自利行为。此外,亲缘利他水平增加往往意味着更多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经营,可能会引发家族管理者内部利益冲突,导致企业治理效率低下。(2)随着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的发展,参与企业经营的家族成员的亲缘关系变得复杂,家族管理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及凝聚力降低,更容易出现搭便车、推卸责任等行为。实际控制人也会根据亲疏区别对待家族管理者,家族管理者之间可能会因为自身利益而发生冲突,甚至导致代理问题恶化。因此,随着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的发展,亲缘利他水平的提高不利于改善企业治理效率。(3)当家族企业所属行业竞争程度较高时,企业的经营风险较高,能够给家族管理者带来破产清算压力,促使家族管理者团结一致为企业及家族财富工作,能够有效降低家族管理者的自利行为,有利于缓解代理冲突。因此,在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中,亲缘利他行为破坏治理效率的程度降低。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出,家族企业面临的行业竞争环境及所处生命周期阶段会共同影响亲缘利他水平与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实际控制人应根据家族企业所处行业竞争环境及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采取积极措施强化家族成员间的沟通协作,降低家族管理者的自利行为及家族管理者之间的内部冲突,改善家族企业治理效率,促进家族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存在如下不足之处:(1)利他行为包括纯粹利他行为、互惠利他行为和亲缘利他行为,本文仅探究了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的亲缘利他行为,对实际控制人与创业伙伴、校友及同乡等之间的互惠利他行为有待后续研究。(2)Gersick等[8]提出的家族企业三维发展模型,包括家族发展维度、所有权发展维度和企业发展维度,本研究仅考虑了企业发展维度对亲缘利他水平与治理效率之间关系的影响,对于家族发展维度及所有权发展维度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有待后续研究。
参 考 文 献:
[1]Schulze W S, Lubatkin M H, Dino R N. Agency relationships in family firms: theory and evidence[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1, 12(2): 99-116.
[2]陈建林.利他主义、代理成本与家族企业成长[J].管理评论,2011,23(9):50-57.
[3]Schulze W S, Lubatkin M H, Dino R N. Toward a theory of agency and altruism in family firm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4): 473-490.
[4]Chrisman J J, Chua J H, Litz R A. Comparing the agency costs of family and non-family firms: conceptual issues and exploratory evidence[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4, 28(4): 335-354.
[5]Lubatkin M H, Schulze W S, Yan L, et al..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altruism on the governance of family-managed firms[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5, 26(3): 313-330.
[6]Gold T, Guthrie D, Wank D. Social conn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Guanxi[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7]王明琳,徐萌娜.上市家族企业中差序格局的影响因素与治理绩效研究[J].浙江学刊,2017,(4):94-101.
[8]Gersick K E, Davis J A, Hampton M M, et al..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life cycles of the family business[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7.
[9]张传财,陈汉文.产品市场竞争、产权性质与内部控制质量[J].会计研究,2017,(5):75-82.
[10]王瑞乐,刘涵慧,张孝义.亲缘利他的不对称性:进化视角的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12,20(6):910-917.
[11]Marsh A A. Neural, cognitive, and evolutionary foundations of human altruism[J].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ognitive Science, 2016, 7(1): 59-71.
[12]Schulze W S, Lubatkin M H, Dino R N. Exploring the agency consequences of ownership dispersion among the directors of private family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46(2): 179-194.
[13]Chrisman J, Chua H, Pearson A W, et al.. Family involvement, family influence, and family-centered non-economic goals in small firm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2, 36(2): 267-292.
[14]王志明,顧海英.利他主义、代理问题及家族企业[J].社会科学战线,2004,(5):41-46.
[15]王明琳,徐萌娜,王河森.利他行为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吗?——基于家族企业中亲缘利他行为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4,(3):144-157.
[16]谭庆美,王畅,周运馨,等.家族企业亲缘利他行为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基于所有权发展阶段视角[J].经济问题,2018,(3):57-65.
[17]Dyer W G, Dyer W J, Gardner R G. Should my spouse be my partner? Preliminary evidence from 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12, 26(1): 68-80.
[18]范黎波,刘云芬,杨金海.家族化管理与企业绩效:规模与家族成员所有权结构的调节效应[J].管理评论,2016,28(5):96-106.
[19]Xiang D, Worthington A C, Higgs H. Family ownership, altruism and agency costs in australian small-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J]. Applied Economics, 2014, 46(32): 3907-3921.
[20]贺小刚,连燕玲,李婧,等.家族控制中的亲缘效应分析与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0,(1):135-146.
[21]连玲燕,贺小刚,张远飞.家族权威配置激励与功效:来自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1,(11):105-117.
[22]胡明霞,干胜道.生命周期效应、CEO权力与内部控制质量:基于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8,(3):64-70.
[23]贺小刚,李靖,陈蕾.家族成员组合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0,13(6):149-160.
[24]Ward J L. Keeping the family business healthy: how to plan for continuous growth, profitability, and family leadership[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7.
[25]Tosi H L, Brownlee A L, Silvap P.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of decision-making under agency controls and steward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3, 40(8): 2053-2071.
[26]Giroud X, Mueller H. Does corporate governance matter in competitive industri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0, 95(3): 312-331.
[27]Dickinson V. Cash flow patterns as a proxy for firm life cycle[J]. Accounting Review, 2011, 86(6): 1969-1994.
[28]陈建林.上市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代理理论和利他主义理论的争论和整合[J].管理评论,2012,24(5):53-59.[29]古志辉,王伟杰.创业型家族企业中的亲缘关系与代理成本[J].管理学报,2014,11(12):1806-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