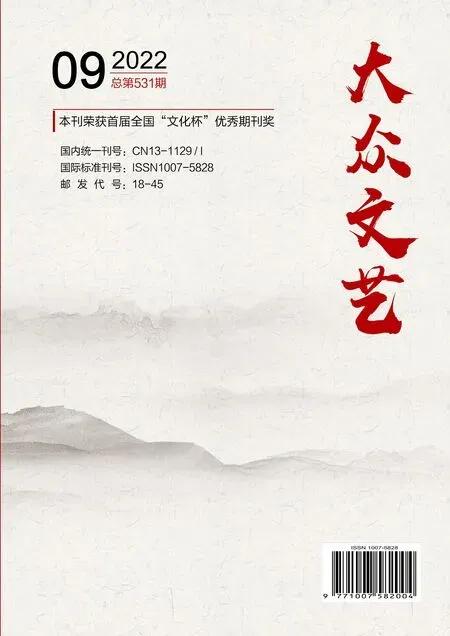神秘主义与中国艺术的灵韵
——以《庄子》对“道”的阐释为例
2021-07-12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81)
阅读古代典籍时,常常会遇到许多充满神秘感的论述,无论是《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离骚》中漫无边际的想象,还是《史记》中对于帝王命运的附会。当代读者虽多抱怀疑态度,但并不影响他们品读其中的灵韵与趣味。当今社会,科学空前发达,理性被不断强调,而人们却仍然乐于通过星座预知命运。“神秘”到底意味着什么?赋予了我们的文化怎样的特色?其对大众的吸引力又来源于何处?无疑是值得追问的。本文将通过《庄子》一书对“道”的阐释,探究神秘主义与中国艺术灵韵间的关系。
一、神秘主义的界定及成因
结合《韦伯词典》和《宗教百科全书》给出的有关神秘主义的定义,可以初步归纳出:神秘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主体对现象或理论的直接把握,这种把握往往是直觉的,主观的,不能凭借逻辑推理而理解的。而根据扎纳对神秘体验的划分,神秘主义又可以与不同学科结合起来,划分为哲学的神秘主义、审美的神秘主义和宗教的神秘主义,三者互相交错而各有侧重。哲学的神秘主义侧重的是对纯粹自我的本质直观;审美的神秘主义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宇宙的合一;宗教的神秘主义则注重在神秘体验过程中人格神的参与和启示。
为什么人们会趋向神秘主义呢?实际上,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成因。在原始社会,人们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认识能力有限,在理解世界时,往往会创造一些拟人化的超自然形象来满足基本的认知需求。而当认知水平逐渐提升,人们则渴望进一步探索未知,但在一定时期内,人的认知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人们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往往会超越实际认知水平,因而难免会在现有认识的基础上,建立一些主观联系,以求在认知层面增加世界的可把握程度,提升自我的安全感。例如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作者将方位、五行、四季、五音等一一对应,试图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对各类自然现象进行解释说明。而随着历史的推进,人们对世界的把握不断走向客观化,因而逐渐把对神秘主义的运用转向纯粹精神领域,以寻求心灵的寄托。值得一提的是,庄子虽生活在战国时期,《庄子》一书也呈现出神秘主义的倾向,但庄子在其中却并不执着于认识与解释客观世界,而更多的是在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与对生命的追问,彰显了庄子超越时代的眼界。
二、神秘主义在《庄子》中的体现
神秘主义在《庄子》中的具体体现,可以依据扎纳的观点,从哲学、审美、宗教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上文已经提到,哲学上的神秘主义,是指向内部的,主要涉及主体的思考与把握世界的方式。庄子不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诗人,《庄子》一书体现的哲学思想也是诗性的。“实在连他的哲学都不像寻常那一种矜严的,俊刻的,料峭的一味皱眉头,绞脑子的东西;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庄子的诗性哲学以“道”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中对于“道”的阐述,不仅表明了“道”的种种特点,还道出其为万物之先,万物之本的性质。在庄子看来,“道”虽然不可见,没有行迹,但却是真实存在的,是一切的本源,人若想悟“道”,就需要达到“心斋”“坐忘”之境界。
何为“心斋”?《人世间》一篇中,借仲尼之口,阐述了“心斋”的具体状态:“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在庄子看来,用耳朵去听不如用心去听,而用心听又比不上用气去感应。这里的“气”,指心灵达到空灵明觉的状态,这样便可以突破用耳和用心听的限制,将“道”纳入清虚的心境中来。《大宗师》一篇,则阐明了“坐忘”的内涵:“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堕肢体即离形,意指不受形骸束缚,摆脱生理的欲望,黜聪明等同于去知,意为去除智慧带来的烦恼,从而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均达到无欲无求的境界。同时,《大宗师》篇还表明,对道的彻底领悟需要经历外天下,外物,外生的阶段。虽看似循序渐进,但实际上则全凭心灵体会,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步骤。可见,在庄子哲学中,无论是对“道”的阐释,还是对闻道方法及闻道过程的论述,都没有遵循逻辑推理的方法,而是以直觉进行感知。这为庄子的思想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的同时,也赋予了庄子哲学独树一帜的魅力。
审美的神秘主义与哲学的神秘主义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尤其是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哲学虽然更多指向主体内部的思考,但庄子却有意将这种思考引向外部,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关于审美,《知北游》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做,观于天地之谓也。”天地万物的运行有自己内在的规律和法则,而圣人、至人则通过顺应自然来体察万物,从而达到对事物美的观照,看似写天地之美,实则讲的还是人需要具备超脱利害关系的空明心境。在这一审美过程中,万物虽然作为审美对象,但是审美目的的最终达成还是需要依靠作为审美主体的领悟,而无论是达成的方式还是最后呈现的审美状态,都难以步骤化、逻辑化、规范化,给人以不可把握的神秘之感,追求的是一种人无限趋向物的状态。而在《齐物论》一篇中,庄子又将这样的状态往前推进了一步“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虽然文中举“庄周梦蝶”的例子是为了说明物化,但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也体现了庄子在“道”的指导下对外物全然忘我的观照,这种物我无间、物我互化的状态无疑更是神秘的。
庄子对审美的阐释,不仅在于主体对外物的观照,还在于人在对外物的观照中所获得的创造的自由。如《养生主》一篇中,庖丁解牛时所达到的类似于审美的境界:“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与此类似的还有《达生》篇所讲述的佝偻者承蜩、吕梁丈夫蹈水等。实际上,无论是庖丁还是吕梁丈夫,庄子为了表现他们技艺的独到以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时高度自由的状态,对这些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神秘化处理,使得文章呈现出独特的韵味。
相比于哲学与审美的神秘主义,宗教的神秘主义在《庄子》中较难印证。虽然真人、神人一类的概念在《庄子》中时常出现,例如《逍遥游》中关于姑射之神的描写、《大宗师》中对真人的论述以及《齐物论》中对至人的阐发等,但是,这些与信仰并无太大关联,庄子也并不认为这样的人真实存在,他只是企图通过对这些形象的描写,表明超越生死利害后可能达到心灵境界,对这一理想境界的描写是写意的而并非写实的。实际上,《庄子》一书中并不存在人格神,其整体思想呈现出唯物的倾向,其思想的核心是“道”,而“道”并不具备人格意志。庄子的追求是得“道”,而不是长生不老或飞升成仙,他对生死的态度是释然的,《至乐》一篇便是最好的佐证。
三、神秘主义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通过上文对《庄子》的分析,神秘主义对艺术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单就文学作品而言,具有神秘色彩的文学作品,往往善于通过讲述离奇故事或塑造恢诡形象的方式来阐明思想,富有感染力。在文学萌芽时期,相比于常规的道德劝诫或说理性文章,此类文章的艺术性更强,为文学独立于其他功能性文体产生了促进作用。除此之外,在不同时期,人们对神秘力量的向往,也体现在雕塑、绘画等其他艺术领域中。而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当下,神秘绝不仅仅意味着蒙昧,其中还体现了生命的活力与创造力,对未知的好奇和猜测,对美好和强大的追求,正是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之一。
但神秘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一方面,蕴含神秘主义的艺术往往更强调审美主体的直觉,呈现的也多是主体的想象或主体对客体理解,从而容易忽视自然原本的规律,造成主观臆测的偏差;另一方面,富有神秘色彩的文艺作品往往还容易脱离现实生活,因而缺乏现实关怀,多数难以达到应有的深度。同时,还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过于神秘莫测而拒绝欣赏者,或是故弄玄虚、堆砌要素而丧失美感。
因此,如何在神秘与现实间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同时兼顾真实的深度和艺术的美感,既不让文艺成为现实焦虑的传声筒,也不让其流于纯粹虚幻,这不仅是《庄子》留下的启示与遗憾,也是历代文学艺术内部来回争论与不断追问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