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
2021-07-01安雅屈梅尔沈冲大梵
安雅?屈梅尔 沈冲 大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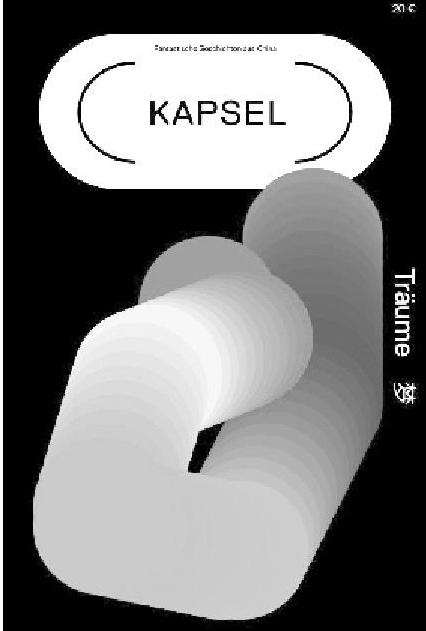
1.
蓝色的箭头应该指向某个地方,给我指出某个方向。这是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个念头。但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不断旋转的缓冲符号……
接下来很长时间内什么都没有。海洋世界一定是被重启了……或者自己启动了运行,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个木筏上。它是由许多树干组成的,做工不是很专业,有些歪歪斜斜——这让它显得古朴又迷人,不过看上去又不太牢靠的感觉。这一定是个新的想法。否则的话,浪花中灵活行进的总是那些易于操作的白色快艇,它们仿佛装有发动机,但事实上却悄无声息。说实话,关于怎么去浮城,我从来没在意是否有其他选择,只一心想着尽快到达。
今天,很长时间内都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我睡着了吗?昙花一现的梦境画面,站在一条大街上……没有同伴的身影。没有新消息。除了海什么都没有。蓝色的天空飘着几缕云。无风,无浪。无忧无虑,虽然时间长了有那么点儿无聊……
但这不是全部。感觉缺了什么,但我又说不出缺了什么。我做了各种手势,试图把控制界面调出来。没有反应。肯定有什么更深层的东西。代码有误?眼前只有树干硬朗的纹理,木头的摩擦声,两者间的缝隙。同时又有一种身体消失了的奇怪感觉。我依稀记得——在游戏和聊天的高涨热情中——我把一块口香糖嚼得太久,直到它开始在嘴里分解。此刻的自我意识就像那块口香糖。
细小的浪花舔舐着木筏,发出有节奏的声响,让人昏昏欲睡。既不热也不冷。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没有指令,也没有危险的迹象,我尽可能舒服地往后倚靠着,任由轻柔的海浪托举着木筏。我的眼睑内侧发出橘红的光,接着突然变暗,仿佛一朵云飘来挡住了太阳。水声由潺潺变成汩汩,就像水龙头在朝水槽里滴水,下面是堆积了几天的碗碟,水从一个盘子流入另一个盘子再到另一个盘子,形成一个微型瀑布——
我的家在哪儿?我几乎可以肯定,自己大声地问出了这个问题。我希望蓝色的箭头能够现形。我所以为的最后记忆,变成了最后之前的记忆,然后又变成了最后之前的之前的记忆……
街道自然是——空荡荡的。这些房子从外面看上去真丑,我想。肺部的空气在微微灼烧。但我没有窒息。只是喉嚨里有轻微的瘙痒。这一定是个梦;我连面罩都没有戴。不过,我还是转了几个圈,像在现实世界中一样,希望蓝色的箭头能给我指路。
在下一个(或者是上一个)记忆中,我在木筏上,正从一艘倾覆的豪华游轮前漂过,它在我身旁隆起,如同一条陡峭的、锈迹斑斑的岩石海岸。左边是一家旅馆楼顶往下的几层,破碎的窗上挂着海藻,屋顶上铺着一片满是孔洞的高尔夫草坪,上面覆盖着一层白色的盐盖……
我的手冰冷,我惊恐地把它从水里抽出来。大海依旧像银盘一样铺展在我眼前。这里有……有鲨鱼吗?有毒的水母呢?
在现实世界,我怀疑这些生物早就灭绝了。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转向左边,通常在我表述完问题之前,答案就会在那里展开。但这次什么都没有,没有承诺,也没有要求。视野无遮无拦,仿佛大海奔跑到了尽头,仿佛天空一直延伸到无边无际……
我连口水都咽不下去。口渴。被水包围着感觉口渴,多少有些奇怪。在我对海洋世界的记忆中,从没有口渴过。
此刻我才意识到,我的头正靠在背包上。我的背包?我不记得了。我为什么会有一个背包?
我打开背包,里面有两瓶水、水果干、坚果和海苔片。我打开其中一个瓶子,试着慢慢喝水。
这里自然没有道路,也没有任何形式的道路网。但无论如何得有方向……我想,即使在海上,船也会依靠蓝色的箭头定位。我愿付出一切!哪怕只给出个缓冲符号也好啊——那一圈每秒都会重新出现的小点。
米尔托海盆的侧翼最近重新变得肥沃起来,在那里,一片葱郁起伏的霍洛①由绿变蓝,向路过的人表明,它们已经达到了碳饱和度,可以收获了。与此同时,在睡莲4号②上,经过长时间的交流,形成房屋的霍洛和那些居住其中的霍洛达成了一致。
那是上一次产卵舞会后的明朗景象。也许这景象可以解释:一排死去的、破碎的霍洛向我们漂来时,我们为何并没有感到陌生,即使我们没有收到过它的任何信号。
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过被动的信号,那些信号只有身在附近的人才能感受出来。首先是一个微弱的漩涡,陷入温血霍洛的触须,三维的电流将其震动导向表面。单单凭借它,无法确定这个生物或物体是否在移动,如果在动的话,也无法确定它的动向。与此同时,一群霍洛颤抖起来,它们的电场扭曲了。然而,被探测生物或物体的导电性信息仍然模棱两可。我们通知了其他温血生物,它们的声呐系统也收到了奇怪的回声:又硬又软,半死半活……至少被探测者的位置几乎没有改变。我们靠近,最终,依靠底部浮起的深坑霍洛的热敏黏膜,被探测者生命属性才明确展示了出来。
记忆涌入:矩形或椭圆的东西,从阳光锉切的阴影中锐利地滑出,在它上面有一群数目不详的生物——虽然看不见,但是能清晰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它的出现,如此强劲,如此突然,以至于我们中的一些人兴奋不已,特别是那些离这种新存在最近的人。漩涡、气泡、交叉信号,通信过载接着崩溃。尤其是产卵舞会后这么短时间内,水中充满了鬼魂,甚至比往常更甚。在最后的黑暗中,那些既没有生物发光也没有变形能力的霍洛,无疑在代替死者说话。
船在狂风暴雨中倾覆。在水下无法呼吸的生物被淹死了。有时候,它们的设备比肺工作时间还长。在它们的存储器中,我们发现了它们的副本——笑着,跳着舞,但里面保存的也有可怕的战争、一望无际的沙漠和堆积如山的骷髅……我们逐渐学会了把它们的语言翻译成我们能理解的一些类比,即使其中经常有晦涩难懂的部分。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词来描述陆地上的霍洛和它们之间不为我们所知的互动。当这些生物和它们的仪器在下坠过程中不再相互分离,当我们意识到,有机物和无机物组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我们决定用“西姆”③来称呼它们。
代替死者说话的霍洛唤起的,不仅仅只是对溺水的共生体的哀悼;也是感慨我们对它们的认识仅限于几个微小的副本:它们短暂跳了会儿舞,随后瓦解——这些副本甚至比它们的有机身体瓦解得更快;还有对那些已经灭绝的生物的哀悼,代替死者说话的霍洛本可以拯救它们。在黑暗中,代替死者说话的霍洛让我们想起了半月形的霍洛——西姆本可以骑在它们强壮的背上,抓住它们三角形的鳍;也或者像有些两至三米长的两栖动物一样,背着坚硬的外壳上岸。
但是——共生体不也早就灭绝了吗?这个问题在刺眼的色彩和狂乱的声呐反射中来回窜动。我们是这么认为的,直到又有一个共生体生命出现在我们面前。
在一些老式的虚拟场景中,街道尽头突然什么都没有了,有那么一瞬间你以为自己掉进了深渊——但随后却被平稳地提升到了下一关……
这不是卡米卡兹-21①的声音吗?我肯定是打了一会儿瞌睡。正常情况下会有一个老式的绿色电话听筒符号逐渐失去轮廓,但我几乎已经习惯了只看着天空和海洋。
地平线略微弯曲,很可能(又有熟悉的回音传来)没有人关心后面是什么样子的。事实上,隐隐的恐惧曾从我心里涌起了几次,担心从世界尽头坠入虚无。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是,我会陷入一个总是相同波浪形式的循环中,反正没人会注意到——谁能区分一个个白沫呢?
有几次我注意到了太过规律的重复,比如每隔一刻钟就会有一只海鸥从右到左斜着从画面中飞过,翅膀正好扇动三下。现实世界中可能没有海鸥了,这里的天空中根本没有鸟。记忆中天空好像更蓝,更有力,更亮。此刻天看起来有些暗淡,就好像一个副本的副本的副本。海洋世界有夜晚吗?
通往浮城的路上,最大的危险来自室外人,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从室外人(经过未来几百万年)发展而来的、相互联系的超级智能水母。它们充满一氧化碳的漂浮身体相互连接,组成一道长达十米甚至十二米的长条。它们一边在海面上漂浮,一边将触手伸向海底,将汲满水的帆伸向天空。远远望去,它们看起来气势凶猛,像一个个巨大的鲨鱼背,有着五条、六条,有时甚至十条尖鳍。虽然我不知道,如果被它们抓到会是怎样一种死法,但这肯定比其他死法更加恐怖。我相信,我的想象力告诉我,它们会把我同化。它们带来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死亡,而是可怕的永生。
虽然这里远近都看不到那些鳍,不过我把脚趾浸在水里的时候,最好还是保持警惕。
我的脚一碰到湿漉漉的地方,天空中就出现了细长的云带,像发霉的绳子一样从一边散开。在远处,我仿佛看见了动物以优雅的曲线上下跳跃。但它们也消失了,被一幅更奇特的景象所取代:一艘饱满的船,配有划桨,还有松弛的帆,船首一个金色的马头熠熠生辉……我肯定是进入了这个游戏中我从未涉足过的一个环节,在这儿某个失控的子程序在自行运转。
洪钟般响亮的笑声响起。我一阵哆嗦。是我在笑吗?我了解自己的笑声是怎样的,短促、干脆、浑厚(这可能是因为我那笨重的转角沙发、厚实的窗帘和厚厚的地毯)。我又一次觉得口水都咽不下去了。要是这个疯了的程序向我进攻怎么办?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从内部重新编辑……
我的视野暗淡下来:闪着血红色光亮的波纹围住了木筏,波纹中夹杂着死鱼,它们的腹部像涂了流质的煤油一般闪闪发光。此外还有一股刺鼻的臭味,像烧焦的橡胶。我赶紧把脚从水里抽出来,一跃而起。木筏晃了起来。臭味消失了。这一幅末日的景象也随之瓦解。然而我的袜子却变得又冷又湿,之前不是这样的。我该把我把它们脱掉吗?现在就脱。我的脚底有几道伤口,像是被锋利的贝壳划破了……但为什么袜子上没有血迹?
木筏晃动,海变得模糊不清,天空突然停住,像是一个没有得到授权的版本。颠簸、冻结,接着世界倾覆。
伤口。已经愈合了一半,但仍清晰可见。
我们把感知到的全息投影传输给了侧行者,因为它们很少离开礁石太远。侧行者的眼睛长在触角上,可以向所有方向独立旋转,它们能够分辨出十几万种颜色。总之,它们的视力比我们发达很多,会把我们发送的电子脉冲、声呐波和热信号转化为光学图像。
半愈合的伤口。毫无疑问,我们中间有一个离开了网络的西姆。它没有动,但在呼吸,散发着热量。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没有了机械部件后它是否还能继续生存,还能生存多久……它是室内人变化而来的吗?
至少我们现在能让西姆保持在水面上。我们祖先相互联结的网络太弱,以至于在需要的时候,无法将许多的霍洛组成一个连贯的、共同行动的整体。没有什么补救措施了——但是仿佛出于集体记忆,我们还是长成了一块类似浮动地毯的整体。我们就这样带着西姆朝睡莲2号行进,如同那些链条一般连接在一起的死去的霍洛,而西姆到达了它们上面。
旅途中,我们尽全力将西姆四肢的重量平均分配到所有的悬浮体上。过去和未来的魅影在我们中间畅通无阻:曾是岛屿的浮动集市、锈迹斑斑的拖网渔船、鬼魅般的网、无数被勒死的霍洛。我们下方有两艘沉船,里面载着酒、香料和铜,在遥远的风暴中被摧毁。腓尼基人的东北贸易航线,与一艘油轮沉没的恐怖之地重合。我们默默地穿过这一死亡之境,满是窒息的长着鳞片的霍洛,有着羽毛但是无法飞行的霍洛,投射到未来的记忆。一望无际的藻类农场曾在睡莲2号周围延伸开来,也许将来还会继续延伸。我们不得不在绳索和浮标之间来回进行复杂的操作,将自己变成更加细长的形状。
从前到后,从后到前,神经网络开始发力。睡莲2号会是一个适合西姆的地方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当中无法在水下呼吸或者不能仅仅依靠水下呼吸存活的人,就在这里生活。我们就这样紧紧依靠在一起,通过纯粹的渗透共同回忆上次产卵舞会上所經历和听闻的一切(尽管用的是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的语言)。
几大港口城市沉没之后,睡莲2号成了新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没过多久,第一波浪潮和苏伊士运河的洪水让工程陷入瘫痪。私人投资者掺和进来,他们的想法是宣布所有的浮动城市组成一个国家,宣布独立,让自由竞争来统领一切。然后第二波浪潮来袭,接着是一小群室外人。他们根据自己的构造、喜好和能力分头工作,尝试使用有机建筑材料,经营藻类农场,藻类不仅提供食物,它吸收的氮和磷也逐渐重新恢复了周围的生态平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创造了生态,不是一切照旧——而是开创了新可能性的空间。
2.
一个深色的背——我的背?我最近一次看到自己的背是什么时候?——汗水在背上像蜂蜜一样流下来。睁开眼睛之前的最后一个梦境画面。蜂蜜——如此简单的一个词,虽然我不能完全理解它的意思,但我几乎能尝到它的味道。
我在水下醒来,身体周围包裹着一个房间大小的胶囊舱,里面有可供呼吸的空气。一列紫色的海螺正在清洗胶囊舱的窗户。这画面莫名让人心安。
在那后面——不知为何——我期待会看到色彩斑斓的珊瑚、橙白条纹的鱼和一只正向胶囊艙玻璃游来的海龟,但事实上我在浑浊的水中只看到了红色的藻类。它们在生态岩石上朝我挥动长长的、幽灵般的手臂。
我不知道浮城是否真的存在。有人说那是巨型的睡莲,有人说那是树长在一起形成的房子,还有人说是回收塑料做成的浮桥,或者太阳能发电场和扩张的藻类农场。有财富的地方,就有服务的需求。在海洋世界里,人们有明确的使命和格言。如果你不喜欢这里,大可以去别处——就像在游轮上一样。
在我脑海中出现了各种画面:绿色的玻璃穹顶、碧绿的澙湖、港口的滨江步道,不同肤色的人穿着商务套装,北非长衫、中东白褂或者印度长裙。有些人在打电话,有些人把欢笑的孩子抛向天空。天很蓝,海很平静。用你的房子投票——这是又一条印在我脑海的口号。明亮的白色六边形散开来,组成新的图形……
但画面里也会闪现出汗涔涔的背部、嗡嗡作响着震动的机房、难以忍受的酷热,橡胶鞋踩着滑溜溜的海藻……呜嘛咪、呜嘛咪……许多图片、文字、声音。梦里的一股腥咸的气味,混合着腐蚀性的汽油味,似乎还一直弥漫在胶囊舱里面。
要是能浏览我的时间线,我就能随时调出这一切了。可现在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被往事冲击,为了让我把它们记起来。如今我就好像把自己的记忆存放在另一个地方了,一个我无法进入的地方。或者更确切地说,往事从内心深处向我袭来,不成体系、断断续续。
平台故意将错误植入算法,而我恰恰将这类计划视为荒谬的谣言。可现在看来,一个这样的故障将我留在了现实生活。这个念头让我心头一颤,我真的可能会溺水而死……
这时,有什么东西从窗前划过。海藻样的手臂瞬间张开,一种透明的生物,它的轮廓只有通过留下的水涡才能看到。
我一直把室外人想象成僵尸一样的群居生物,他们无情地同化遇到的一切。他们救了我,这在我看来就像系统故障一样不可思议。窗外海藻样的手臂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在水里招摇。他们是在以无法预知、断断续续的方式跟我交流吗?还是水里有什么其他东西?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海底的光缆,它们将难以想象的庞大数据流在各大洲之间往来传输。如果在海底传送过程中丢失了一部分信息该怎么办?就像一个水下互联网:首先分解成百万微粒,然后,转瞬即逝的声音、符号、图片以及一切与水接触的东西,所有信息都转移到了水中。
闲逛一度风靡一时,随即又不再流行……
幸好还有霍洛,它们的经历比我们更接近这些陌生的话语。西姆的记忆一直停留在那个我们以为已经毁灭的世界。但现在西姆在这里,其他传输手段也开始发挥作用——我们猜测,这是一个不完全成熟的去优化策略的结果。正如之前那些垂死的机器,西姆的感觉、思维、梦境和记忆碎片逐渐成为海洋神经网络的一部分。
闲逛。这当然暗示着……得有腿、脚、支架,支撑的东西帮助睡莲2号上的两栖霍洛移动,得有适合陆上移动的四肢——反正比触须好。
一个更难以澄清的问题是,说“我”的时候,意味着什么。
根据我们目前的认识,海平面上升,空气污染加剧,尤其是第二波浪潮促成了室内人和室外人的划分。臭氧或硫氧化物造成的长期损害可以避而不谈,但急性感染的风险却不容忽略。鸟儿那么多,它们肚子里的存储卡上的对话信息那么庞大:室外病毒含量只有室内的1/19,但不是没有病毒。另外,在室内,独自一人,隔绝了一切相互的身体接触。但是,室内人绝非一个个自主的实体,相反,他们的隔离加速了彻底的网络化,也就赋予了平台无上的统治地位(它是鸟儿肚子里芯片的制造者,还有我们每天过滤的无数分解电路板的制造者),他们由无尽的内啡肽回路和雪崩般的反馈效应来获取能量。每一次反冲都有亿万次点击,每一次黑暗、每一次光明都有一亿张自拍在海底铜缆飞驰,化为自我的无数副本。
我们知道,自我暗示着非我。被服侍的舒适感,鱼腹中的垃圾变成造型时尚的寿司,泡沫塑料球,曾用于制造牛肉和猪肉的包装——这一切都在长羽毛、长鳞片、长犄角的霍洛的内脏里。所有这些名词被用于区分各种事物,用于命名,用于主次排序。即使是西姆也从不把自己当作一个整体——虽然它们跟我一样,彼此之间永远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自我的意义吗?一个细胞、一个吸盘、触须的末端、一小块翅膀或者鱼鳍,把它们分离开来,统统视为异物。一切都在那儿:一些西姆住在逼仄阴暗的地方,这样另一些西姆就可以住在明亮的中心地带;一些西姆吸入有毒的烟雾,这样另一些西姆就能得到新的漂亮设备,能让彼此更快地联网;一些西姆流汗奔跑烧伤四肢,另一些西姆惬意地坐着、笑着、吃着;一些西姆居住的岛上被投掷了有毒的炸弹。我们自问,自我无非就是自我免疫性疾病吗,一个有机体对于自身的攻击吗?自我毁灭的程度在我们体内层层加剧,如白日梦、回忆、塑料聚合物一般,被研磨成越来越小的碎片,直至消失。
从远处看,浮城的建筑由绿色玻璃组成,符号在空中闪烁,随即消失,它们是有机物和人造的纳米结构混合体。海藻外墙将空气中的有毒气体转化为氧气和沼气。
如果不能分享的话,我所看到的东西又有何用?如果没有后续影响,看还是看,想还是想,听还是听吗?
信息毫无阻力地穿过我的身体。梯形的灌溉系统,同时也能传输信息。我想,数据流有了全新维度上的意义。当然没有后果,没有评论,没有点赞,甚至连一个钩都没有,没有人看到过我看到的东西。
如此,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城市的中央,雨水被搜集在与海平面等高的澙湖中,为的是保持睡莲叶的平衡。澙湖周围长着树一般大的苔藓——这是藻类和真菌的生活群落,它们又与猿猴状的章鱼(或者说是章鱼状的猿猴)形成共生关系。虽然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我很快习惯了它们在我头顶上穿过树枝挥舞触须的景象。在城市之中或者城市地下,几乎没有一种生物不是生活在互利共生的群体之中。比如,海螺不仅吃船舱玻璃上的污秽,它们也吃红藻的死体部分,同时把它们的孢子传播到远方。
我是从自称霍洛的生物那里知道这一切的,它们把我带到这里。它们是半透明的变形体,在夜间发出荧光,相互之间通过变换颜色来交流。我只能通过数码化翻译它们的语言来猜测这些信息。我不再确定它们是否真的源自室外人。它们看起来既不像动物,也不像植物,也不像机器。它们中没有女王,甚至没有一个控制性的中枢大脑。它们行动的时候更像一只巨大的章鱼,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可拆解的肢体:每一个触须都布满了神经网络,能够独立感知和行动,同时又与其他所有触须相连——哪怕相距几百甚至上千千米。到达我这里的印象和感觉似乎来源于过去,但似乎又还未到来。声音和符号飘浮在空中,旋即消失。
我们生活在脆弱的躯体里。我们忘记这一点了吗?关卡、铁丝网、监控摄像头、资本的优越性是无法阻止粉尘、信息流和病毒的。
霍洛也可能是一个古老的物种。这些两栖动物拥有高度发达的智力,一直与人类共存,从第二波浪潮之后才得以自由地发展。
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竞争、侵占和恶意吞并?
天空寂静,黄昏降临。地面上却发出了熟悉的沙沙声:长矛状的多肉植物的叶子小心翼翼地卷起睡在里面的小小的猿猴章鱼。长大的猿猴章鱼则睡在灌木的周围,既保护自己的幼崽,也保卫植物免受掠食者的伤害。我背靠一窝苔藓坐下,闭上眼睛。霍洛之间的战争……我听见卡米卡茲-21的思绪,就好比砍掉自己的一根手指、一只脚、一个耳朵——或者一根触须。接下来我睡着了。
非洲大陆板块撞入欧亚大陆板块之下的地方,代替死者说话的霍洛被调高了音量。有一天我们将不再明白,大海的沉默是多么珍贵。
抑扬顿挫的地质构造震动发出低沉的吼声,组成了低音线。在那上面,爆裂的穴蚀气泡样本、军用声呐设备的低频声波、地震压缩空气大炮回响的爆炸,混合着我们祖先已经灭绝的语言和歌谣。轮船螺旋桨的单调响声、点缀着上扬的汽笛、试探性的点击声,以及时不时发出的一声充满渴望的嚎叫,悲痛而又美丽。这一交响曲越是在峡谷中回荡,就越难以区分个体的声音,扫雷船的声呐探测器收到来自灭绝物种的嘎嘎声、呼呼声、吱吱声:它们是巨型海豚、座头鲸和逆戟鲸。
我们将一遍又一遍诉说他们的名字。在产卵舞会上有着鳕鱼、鲑鱼、墨鱼和乌贼交配和死亡的舞蹈,以及各种共生的仪式。
在发光类生命体中,原本很难注意到的霍洛发出耀眼的光芒。它们从内部发光的器官在岩石周围曲曲折折地跳动着——六七条鳍留下了光的纹路,从中气泡般升起没有身体包裹的心脏、胃、大脑。而那些没有发光能力的,则借助发光细菌作为夜晚的装饰:为了在这一盛宴上分一杯羹,它们从五千米深处复制星空、流星群、火花雨。
发光信号不再是欺骗和伪装的手段,不再用于击败竞争者、成功地捕猎,或者吸引异性交配——而是用于交流、表达、共鸣和嬉戏。
每隔十秒就会有压缩空气从过去冲向海底。期间液压锤击打,将早已解体的风力地基打入海底。触手控制启动!千万手臂相互缠绕成霓虹黄的波浪。高频的声音射线打在闪着蓝光的雾气上,形成全息影像:一片菌类和发光植物组成的森林,在黑暗中与一个西姆融合。总有一天我们中间会出现西姆。
闪闪发光的线分割画面,一群霍洛完成了急速俯冲的深潜,水中泛起泥浆——磨碎的骨头、塑料微粒、故事。
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一切将会重新组合。
[责任编辑:艾 珂]
后记:
作者的话
来说说《梦》。《梦》是新近出版的科幻杂志《时空胶囊》(Kapsel)特刊的主题。我应邀写了一篇文章。这里的梦不是噩梦,而是对于未来的美好构想。而事实上我更加擅长写恶托邦①!几年前在接受L-MAG杂志采访时,我说过一句话:“我是一个悲观的人,喜欢没有欢喜结局的阴暗故事。”在采访出来时,这句话被特别标记了出来,后来这句话一直跟随着我……简而言之:写这么关于一篇美好梦想的文章,着实让我一度陷入写作障碍。
想想瓶颈的原因,或许我只是缺乏类似题材的文学榜样?当代德语科幻界充斥着奥威尔式的恐怖场景:独裁国家的全面监控、想要奴役人类的机器人大军,而人类则离开已经变得无法居住的地球去寻找新的家园……我几乎找不到一个我们愿意生活的未来世界的图景。我能想到的最后一批激进的新世界构想需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在Marge Piercy或者Ursula Le Guin的作品中。那之后呢?我们真的像福山②1992年所断言那样,已经到达了“历史的尽头”吗?还是说福山的假设甚至禁锢了可能性的探索,以至于后来的人们除了捍卫现状之外几乎不敢进行推测?
幸运的是,在诸多文学出版项目中时不时会闪现几颗难得的珍珠,它们虽然不全贴着“科幻”的标签,但却合乎主题——熠熠生辉的图景,乌托邦和恶托邦相互交织成一个视觉游戏,一会儿善一会儿恶,就看用哪只眼睛去看。它们成功营造了一种微妙的不安,却不设定具体的敌对形象,叙事者以令人迷乱的方式将顺从与反叛、讽刺与真诚结合在一起——毫不留情地展现我们所处的现实,这是一本“写实小说”几乎无法办到的,也比上述大多数“彻底的恶托邦”更具创造力。
近几十年来,少数几位当代作家不留情面地无视“科幻”与“文学”之间的鸿沟,Dietmar Dath就是其中之一。凭着惊人的创作输出,他活跃于独立出版商和大型出版社之间,以一贯的共产主义姿态和同样坚定地对“写实小说”的否定,将他另类的社会构想投射到未来。同样在高水平文学层次上探索可能性的作家还有Angelika Meier,她在怪诞的闹剧《偷偷地、偷偷地忘记我》(Heimlich, heimlich mich vergiss)中讲述了一个诊所,里面的医生和病人都是类似精神分裂的赛博格③。另一部卡夫卡式恶托邦小说《渗透》(Osmo)的故事则发生在加利福尼亚沙漠中的一座破败的太阳能工厂。
年轻一代作家中值得推荐的作品有:Juan S. Guse的大部头小说《迈阿密朋克》(Miami Punk),故事层层嵌套且充满哲学思辨;Le if Randt的《磁振星球》(Planet Magnon),讲述的是一个由仁慈的人工智能统治的行星系统;以及Juliav on Lucadous的处女作《高楼跳跃者》,这部小说构思精巧而富有深意,作者描绘了一座无边无际的超级城市,各色人物与这座城市缠绕交织为一体,直至他们存在的每个细枝末节。
所以说,未来构想的多元化是很有可能的。也许我们并没有像新自由主义所暗示的那样,生活在“后历史”时代?新冠疫情和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越来越让人们质疑现行制度的所谓别无选择和不可替代。就像在我写的这个故事中一样,我想在一种构想中打开各种可能性空间,它们互不相同,但并行不悖。生态恶化、疫情肆虐、经济萧条:各类危机会把我们变得更加依赖、孤立和自私吗?或者说,会令我们更加团结,同时更加自由?
我最近刚读过Donna Haraway的《与忧患共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作者是一位女权主义自然科学史专家,她在书中介绍并拓展了Lynn Margulis的共生体(Holobiont)概念。把不同的物种组合成一个复杂互动的生态整体,并把它作为叙事中心,这一点让我非常着迷。在我的小说《电子沉睡者之梦》(Trume Digitaler Schlfer)中,我已经构想了一个无性别差异的未来——现在我想进一步推进这个实验,从网络化和集体意识形式的角度来叙事,人类、机器、动物、植物和环境不再能清晰地被相互区分开来。正如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那样,要想淡化和退出全球性的整体关联,并不像我们有时希望的那样容易。基于一个末世后和后人类的世界,我选择了不同生命形态之间分开又重聚的模式:一方是技术优化的(赛博格)生物,它们之间通过数字化相互联结但又彼此独立行动;另一方是水生生命体,有着水母和章鱼的特征,同时也表现出人类的特质,共同构成一个整体的有机体。它们对时间的感知不是线性的,它们的交流是通过感应和渗透进行的,因此它们的叙述只能是碎片化的——以一种流体的形式,这其中梦境与现实,数字与模拟,过去、未来和现在不断交织:它们的每一个迹象都有可能打开通往其他维度的大门。
——安雅·屈梅尔
《时空胶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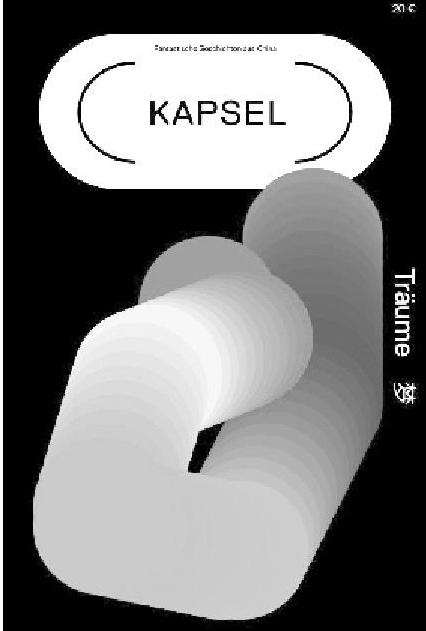
《时空胶囊:中国幻想故事》(Kapsel: Fantastische Geschichtenaus China)于2015年诞生于柏林,是一本致力于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在德语世界译介和传播的双语杂志。杂志的编辑兼主要译者为Lukas Dubro、Felix Meyerzu Venne(麦子丰)和沈冲。Frederike Schneider-Vielscker任学术顾问,Ruben Pfizenmaier负责项目的策划和推广,杂志的设计和排版则出自Marius Wenker之手。《时空胶囊》在以往几期中介绍过迟卉、夏笳和江波等中国年轻科幻作家的作品并与她/他们本人进行了交流。此外,编辑部已经策划和举办了多场围绕新出版杂志的研讨会和朗读会。2020年,《时空胶囊》邀请了陈楸帆、刘宇昆、宋明炜、江波、夏笳、王侃瑜来到柏林Acud艺术中心(由于疫情影响,部分作家通过线上参与)与德国本土艺术家进行对话和交流,并向德国读者讲述他们的故事。杂志于2021年2月底推出了第四期即特刊《梦》,其中收录了中德两国科幻作家的四篇故事,宝树、Anja Kümmel、Tim Holland和吴霜在各自作品中描绘了她/他们的未来构想。其中宝树和Anja Kümmel的作品还同步发行了有声版,由演员Niklas Wetzel和Pia-Micaela Barucki朗读,摇滚乐队Kadavar和流行歌手Ella Zwietnig配乐。
《时空胶囊》官网主页:
https://kapsel-magazin.de/
微信公众号:Kapsel Magazin
我们期待您的关注!
——《时空胶囊》编辑部
①霍洛,一种幻想生物,原文为Holo,从词源上讲,有全息之意。
②睡莲4号,一座漂浮城市的代号,后睡莲2号意义相同。睡莲(LilyPad)是比利時建筑师文森特·卡勒博(VincentCallebaut)设计的漂浮生态城市模型,旨在为未来的气候难民提供庇护。
③西姆,一种幻想生命体,原文为Sym,词源上有共生之意。文中的“西姆”其实是霍洛(它们只有集体意识,只会说“我们”)眼中的人类,也即那个主人公“我”。“我”和“我们”是两个交叉的叙述视角。
①另一个玩家,NPC,或者是主人公智能眼镜的名称。
①恶托邦(Dystopia)即反乌托邦。
②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此前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等。现居加利福尼亚。
③赛博格(Cyborg),人与电子机械的融合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