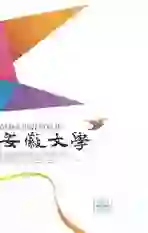荒原上的村庄
2021-07-01陈元武
陈元武
一
它像一片枯叶般萎靡不振,苍黄,甚至有点焦脆,像一张过火的灰烬般,干旱持续了数月的南方,海水离得并不太远,却是那么的遥不可及。有时候,想象那些海水会像长着翅膀的云朵般,突然从海渊里升腾,并且会突然从无名处刮起狂飙来,横扫这干枯死寂的村庄和田野。它确实像荒原了,一大片长满了碱菀草和绒蒿的干涸田野上,除了无聊的风和阳光外,还有一些飞鸟失落的羽毛。许多年来,这里曾经是丰腴的水稻田,甚至它还在秋后种着红薯和花生,玉米高梁或者瓜果蔬菜。现在,它只属于野草,在被阳光烤得坚硬的灰白色碱质土地上,艰难地生长着茂盛的野草,虽然因为缺水和碱质,这些野草依旧长得相当喜人。去年夏天,我多次遇见一个驱鸟人在执着地驱赶着侵犯她稻田的飞鸟,一根长竹竿上绑着一条红绸带,像中世纪武士们执着的城邦旗帜,她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在风中,她的身躯摇摇晃晃,像一棵顶风的玉米。那时候,稻田里水泽充盈,暗褐色的泥土里,有各种昆虫在游动。现在,一切都没有了,当时,她插在田里的竹竿和各色彩旗还在飘扬着,已经褪色了,旗面也残破不堪,泛着白色,旗帜被风吹得呼呼响,田野里没有水稻,也没有她的身影。荒原是一个并不好的名词,对于村庄来说,它意味着放弃和结束。细微的沙质尘埃在风中旋着,似乎成为荒原的另一种特色。它符合一种悖逆和证伪的逻辑,像堂·吉诃德和他的仆人桑丘,以及那匹叫若昔难得的瘦骡子,他把它当成了骑士胯下英俊的战马了。空气里有一种盐津的成涩,空气自然干燥得可以点燃大地,当然,那一片绒蒿并未成熟,否则,一阵风过后,漫天飞舞的绒蒿飞蓬,将会使干燥和炽热的夏天变得极其危险。有时候,望着东边沿着海岬曲折蜿蜒的海岸线上浮起的小山丘,以及密集的村庄房子,红色的屋顶,白色的墙壁,精心雕刻的花岗岩石柱子,一切都空泛而失去意义,只是一些浓重的油彩,在暗绿色的红树林间闪现。它是拉曼查式的村庄——由干涸和狂风吹拂的海边山峦组成的城堡和庄园,它其实都是脆弱不堪的存在。那种灰垩色的山岩体和暗绿色的树构成的底色,足够让村庄变得空旷和沉沦。在山丘和荒原间,野草稀疏,红树林和柠檬桉像笔直的龙柏似的,让每一处细节重新变得活泛和生动。
我就是那个堂·吉诃德,在这样的荒原上漫游。我胯下并无名马,也没有骡子,它应该是有这样的存在,它是一匹想象中的马,黑色毛皮,清瘦,目光炯炯,不时兴奋地打着响鼻,它毛色油滑。我的头上戴着那只纸质头盔,手里执着看不见的长矛和皮质圆盾,它镶着铜质的边,看上去像不错的艺术品,我身上还披着长袍,里头裹着素铁软甲,当然,这一切都基于我的想象而已。我走在荒原上,没有人认出我来,我却可以向想象中的城堡进发。当然,那些村庄并不设防,也没有风情万种的女人或者绅士,唯一存在的只是通畅的大道和空无一人的庭院。村庄里的教堂显得有点老旧,但似乎是人们经常去的地方,它现在紧闭着大门。一条狗横在门口,在炎热的下午里伸长着舌头,急促地喘着气儿。榕荫底下,躺着另一些狗,对我毫无戒备,也不想跟我有什么接触,它们在静静地等待着黄昏的到来。
我似乎离村庄很近,也很遥远。我就在它的门口,我却只属于荒原。这有点不符合逻辑,不是吗,我进不了任何一幢房子的门,没有人搭理我,在我伪装色的盔甲底下,是我脆弱的灵魂,我的一切都似乎借助于这薄薄而看不见的盔甲和长袍保护着。那种孤独和沮丧像绝望的大海般无边无际,有时候,我想这世界,除了我之外,都是合理的存在,我是多余的那一个,我是堂·吉诃德,我努力想打破这一切,却总是以沮丧和失败告终。这或者就是灵魂与现实的距离,没有什么例外能够发生,他或者我。
二
一只飞鸟静静地在电线杆上自顾自唱着无名的小调,它或许是专门为我唱的,它就是忠实的仆人桑丘先生。那条渠已经干涸多时,似乎重新铺过水泥,那水泥新鲜而灰白,因为失去水分,它似乎想变成另一条道路。阳光在上边制造了许多惨案,昆虫的尸体和飞鸟的尸体都已经干枯,它被火蚂蚁蛀成了空洞,徒有皮囊,断肢残翅,羽毛散落一地,白骨里可能还潜伏着不甘心的蚂蚁。那只黑色的小鸟忧伤地鸣唱着,没有别的听众,除了我之外。风在电线上吹出一种尖锐的哨音,偶尔有相思树叶互相交击发出的响榧,我怕这些响声惊动了我内心里的马,当然,它使我的内心里像浇下滚烫的油液。在暗红色的心海里,驿动的何止是那颗红色的心?当然,这种激动只是短暂的幻觉。视觉能够迅速纠正我的想法。阳光像火般燎伤了我的头皮,汗像无数的蚂蚁钻出皮肤。哪里有空洞的响声?像敲击大圆木的声音,我知道,那是潮水来临的声音,潮水涌向狭窄的海口通道,冲击着红树林和成堆的莞草丛。鹭鸟惊起,从容地从头顶飞过,这分明是敌人的马匹在冲锋,我内心里的堂·吉诃德顿时兴奋起来。我似乎下意识地扯了扯无形的缰绳,脚后跟踢了踢马肚子,不,是骡肚子,那是一匹南方的黑骡子,毛皮油亮,长着长而夸张的鼻子,似乎随时可以喷出一个完整的冲锋决心。我紧握着长矛,风从矛尖吹过,发出尖利的哨音。我的圆形皮质盾牌呢?我的桑丘呢?那只鸟趁机飞走了,大概这种声音也让它遽然惶恐。大块的云朵像天空中飞行的城堡,我望云而兴叹。龙舌兰在堤坝边缘立起高大的旗杆,那是它开过的花箭,现在,它只剩下了象征意义的枯杆。一些鸟儿在上边伫立着并监视江水里的鱼或者别的动静。它也能够让飞过的风扯成分裂的两部分。晚云随时会出现,一只大拖鸳会乘着风而来,或者是一只鹞子,它修长的翅膀像一只飞燕,迅速穿过荒原的上空,朝远远的鸟群扑去。
我曾经在雨中观察这些荒原的变化,结果是它仍然是荒原,只是野草更多了些。雨水浸湿了土地,野草迅速恢复了生机。绒蒿即将结束它的生命,那些草将在秋后逐渐枯萎,一片绒花将覆盖这片荒原。那细细的绒花,仿佛是大地结出的果实,带着诗意,像云般唯美,我的内心脆弱不堪,在这样的云朵面前,诗意替代了堂·吉诃德般的想象。内心里总是多了些柔软和脆弱的因素,茨威格在叙述里常这样说:“它們不会因为我们的想象而改变,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想象而存在或者消失,它总是独立于我们之外,没有任何一种想象可以取代它的存在。”在马拉美的诗里,也总是出现这样悖逆与反思的句子,他说,事物总是无法被我们的意识所取代的,但我们可以借助想象来丰富它的细节。
我其实只是荒原的一部分,我什么也改变不了,像堂·吉诃德一样,被风车打得狼狈不堪,一败涂地。老实的桑丘还想控制住那匹疲惫的骡子,它实在支撑不了堂·吉诃德过高的期望和他勃勃的野心。我也一样,内心里想控制很多事情,包括自己的生活,行走和消遣方式,而我却只是这荒原上的一匹肥硕而笨拙的昆虫,我踽踽独行,春天到秋天,我收获的只是时间丢给我的一切抛弃物,雨季的仓促和漫长的夏季。在炎热的夏季里,阳光将我无情灼烤,那些树根本无法提供充足的阴凉。身体的疲惫和内心的焦灼一样让我颓废,像堂·吉诃德一样,桑丘和骡子提供了少得可怜的想象空间,那柄长矛也跟纸筒一样毫无锋利可言,其实,只能用柔软来形容它,以及所谓的盔甲。一只甲虫爬过荒原的干燥土地,在一棵死去的碱菀草跟前踯躅良久。也许,不久前,它刚好也从这里路过,并且获得了草的芳香的汁液。
三
荒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让我想象,也让我陷落和迷失。我回想一切可能的理由,但确实想不出更好的答案。村庄所依赖的土地竟然可以这样轻易放弃,将它丢给了荒草。本来,这里应该有人耕种,哪怕是园林花卉也好,没有,空荡荡的荒原将村庄彻底淹没,或者说,村庄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它像一叶浮舟,现在,在荒原上,没有比村庄更加孤独的存在。比如我,想在存在与迷失之间寻找理由,但这似乎也不太现实。有时候,喜欢它荒原的状态,让一切变得无序,或者更符合自然的本质,像秋虫,蚂蚁和甲虫,飞鸟,不需要被农药毒死,不会被驱赶和追杀。蚂蚁需要荒原的遮蔽,它的巢穴像细小的土丘一样遍布,在土丘下是迷宫般的隧道和平台,它的营室和王后宫殿一样辉煌。兵蚁高举着尖利的螯蜇,口器里随时可以喷出灼热的酸液,或者从它的尾部伸出带着毒刺的尾针,火蚁取代了本地的黑色蚂蚁。红火蚁横扫一切动物或者植物。将不甘心的泥蛇咬成白骨,连那层蛇皮也不留下。火蚁能够渡过突如其来的洪水,在水渠里像浮舟般团聚成一团踊跃的虫球,它们轻易地渡过湍急的渠道,到达彼岸。兵蚁簇拥着工蚁上岸,在洪水之前抢先建筑更为保险的巢穴。
飞鸟向来只贪图稻田盛宴,像过去成群结队的情形已经不再出现。麻雀不见踪影,黑颈椋鸟也不见踪影,它们只是喜欢在稻花盛开的田野里寻找各种青蛙和昆虫,甚至会追逐蜻蜓或者泥蜂肥硕的身体,燕子也不再来到这片荒原上尋觅食物,一切迹象证明,动物跟人一样具有适应性和趋利性。成群的棕背鹭也不见了,当然,荒原对它们毫无吸引力。过去经常出现的那只弓着背,尾巴缺失的麻色虎纹猫也不见了,它是只出色的野猫,是和村庄一样被遗弃的一个小小的产物。它具有十分的野性。它经常猎获各种鸟,青蛙或者是沟渠里的野鱼,敞口鲇极为凶悍,但仍然倒在它的面前,各种鹭鸟成了它的同伙,有时也因为争夺地盘而大打出手。我内心里的《拉曼查的堂·吉诃德》,这只雄猫是我优秀的若昔难得骡子,那匹黑色皮毛,有些瘦弱的坐骑。雄猫的果敢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它似乎也是这片荒原的堂·吉诃德。现在一切都归于荒原,除了我,和另一只伯劳鸟外,它不停地发出凄厉的呜叫,让这片荒原显得更加忧伤。伯劳鸟也是这里的主人之一,它和它的亲属们永远不会离开一个村庄太远。
一切都是无可替代的
因为一切都无需替代
虚拟的世界里,一切
都是虚幻、失真,没有边界
星河里的水总像褐色烟缕
明暗闪灭,荒原里不需要太多的存在
因为,荒原,不需要一切的缀饰
像银河一样,散落、四佚的车辙和马匹
荒原只属于精神的范畴
与村庄无关
我在村庄外的荒原上感受到这样的信息,无助的,无能为力的顽固的荒原让我无法承受它的重量。人总是希望一切繁花似锦,绿意盎然,丰稔和收获总是让人愉悦的事情,野草总是让人憎恶,比憎恶麻雀更甚。一个人总是无能和失败的,堂·吉诃德的雄心一次次被现实粉碎,但他不会死心,像我一样,希望这里一切都恢复正常。那些城堡和风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失去了对美好世界的信心和追求。
四
一切都可能是无足轻重的,包括惊叹和惋惜,当季风再次改变方向,朝向西南方时,离上次的邂逅已经过去两三个月了。冬季的村庄本身己成为这荒原的一部分。连野草也彻底枯萎了,碱菀草变得紫红色,半枯焦的叶子底下,挂着一层粉白的碱霜。绒蒿和乱子草都枯成一种经典的黄色,不久,它还将继续褪色成灰白色,并被狂风折断飘零,田野会变得更加空旷,除了碱菀花四现的干涸土地,火蚁也支撑不下去了,会往有水的地方搬家。田野里有了老鼠的尸体,却不知出现于何时,因为已经像干枯的残骸一样。天空中仍然有不断的云飘过,依旧那么绚美,村庄的红色屋顶和豪华的建筑外表仍然醒目地向远方投射。我在码头上碰到一些刚从外海捕鱼归来的村民,他们似乎更在意船上的鱼蟹,几条带鱼银亮得像外星战刀,躺在甲板上微微翕合着最后的呼吸。紫红色的章鱼在甲板上惊慌地四处游窜,试图翻越船帮逃逸。
他们冷静地吸着烟,说笑着,对我的提问毫无兴趣,对荒原的存在漠不关心。对于他们,一天的渔获有时比一年的农田耕耘更有效益,谁还想去跟荒田过不去?他们连谈种田的兴趣也没有了。码头不远处,是新兴的港口,工厂林立,刺鼻的化学气味不时随风飘来。由于填海作业,本来就拥挤的出海口就更加拥挤了,挖泥船在不停地往岸上泵着泥沙,想让这狭窄的出海通道更为顺畅些。这些鱼蟹显然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的船要出海到很远的地方,才能够打到一些像样的鱼蟹。往返在这样简陋的渔船上,一切都无比风险。他们也是堂·吉诃德,单枪匹马,在大海上与敌人搏斗,那黑暗的大海,像巨大无比的陷阱,他们和他们的船随时可能会陷入陷阱中,化为乌有。这些勇敢的堂·吉诃德显然比我有更大的决心和意志。
某个夜晚,无风,有月,有云随意散漫。我坐在海岬边的峭崖上,努力保持着稳定的姿势,夜海依旧在喧哗,潮水一次次拍在海岬的崖石上,冲出一片片雪白的碎沫。海鸟在夜晚里被月光惊醒,在崖边的红树林里嘀咕着什么,像是私聊或者是辩论,我希望能够加入这样的辩论,但显然,这很可笑。我对着红树林说着话,没有人应答,估计海鸟也听到了,它们停止了躁动,私聊停止了,红树林里有扰动的声音,也似乎没有了声音。我想,我说的话或许被它们听到并记下了,它们赞成我的话?
当一切都无所谓的时候
一切都变得极有所谓
有,有时候就是没有
没有,却有时候总觉得很富有
比如,田野,有的时候,它是田野
没有的时候,它就是荒原
田野完全是人的一种价值取向
现在它没有了,荒原就有了
一切的可能,包括野草、我和内心里的堂·吉诃德
西风瘦马,人在天涯
总需要有些人拥有别人丢弃的东西
我的仆人,桑丘,你在寻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