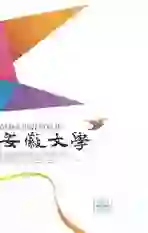寻找王强
2021-07-01洪文水
洪文水

你们要找到王强。
坐在沙发上的父亲开口说。两栋楼宇的缝隙问挤过来的太阳光,越过窗口,把房间一分为二:一半光明,一半昏暗。父亲恰好坐在明暗分界线上,坐成一幅毕加索的抽象画。我看着父亲一半明朗一半晦暗的脸,对他说,行李、干粮都准备好了,明天就出发。父亲偏转头看我,整张脸陷入晦暗。我从裤兜里掏出皮夹,打开里层,抽出一张窄窄的暗黄色的火车票,在父亲眼前摇了摇,说,你看,车票都买好了。父亲接过车票迎着光去看,整张脸瞬间光明。
父亲将左手边立在昏暗里的一只矮凳拉到脚前,这只矮凳立刻光明起来。我知道,这是要我坐下,父亲要讲他的故事了。
事情坏在一头驴子身上。
父亲现在特别喜欢讲故事,像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听故事一样。
你爷爷送我去砍山草。我那年十一岁,我十一岁砍山草。鸡叫头遍出发,天黑蒙蒙的,没有一星光亮。你爷爷打着马灯走在前,我踩着他脚步的影子一步一步跟。你爷爷隔一会儿“铿、铿”咳两声,不是真咳,是故意弄出声音。走夜路的人着急,就要有声音,我们走夜路都这样,有声音就有胆子。我们一直走,一直走,露水湿了裤脚,裤脚沉沉的,绞来绞去。走着走着,四面的山现出灰蒙蒙的影子。
走到一个三岔路口,路口有一块倒掉的大石碑,石碑光溜溜的,都是人屁股磨的。你爷爷说,我们歇会儿,吃口早饭。从怀里掏出一个蓝布包,拿出你奶奶烙的玉米饼。你爷爷嘴里嚼着饼,手向右一指,说,去黑石楼。向左一指,说,到牛集。所以这里叫分路口,这块碑叫分路碑。
牛集是大集,二、五、八、十逢集,沿河一条长长的石板街,两头立着关闸,早上开闸,晚上关闸。大人说,小孩子过闸,要把驴粪蛋子含嘴里,不然闸门就会落下来。南关外有个关帝庙,庙里有关老爷拿着一丈长的刀。我那时还没有去过牛集,只吃过你爷爷从牛集用草棍儿串回来的肉包子。那次我们就要去牛集,等我把草砍好了,你爷爷就拉车来,把草拉到牛集去卖。
故事我们听过多遍。如果无事,我们也会耐心听,并且积极回应父亲的讲述,父亲的兴趣被进一步激发,每一遍讲述就会增加新鲜的情节,变换不同的细节。但今天不行,今天我有一个会,是千万不能迟到的。现在作风整顿抓得非常严厉,上次有个哥们迟到五分钟,被直接罚站。我扬着手表对父亲说,爸,我要上班了。父亲伸出他常年辛劳而粗大的手,按住我的肩膀,说,今天是周末,你把你爸当傻子。
父亲居然记得今天是周末,他用目光将我按在凳子上,继续讲他的故事。
我们砍草的地方叫黑石楼。黑石楼并没有楼,是荒山上一堆黑色大石头。石头又黑又大,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架着一个,架出一间石头屋,屋里能蹲三二十人。荒山上矗着这一堆黑石头,老远老远就看得见,所以叫作黑石楼。黑石山是无主荒山,遍地荒草,只是山高路远,砍草容易运草难。砍山草的人要在黑石楼住下,白天砍草,砍下的草就地晾晒。几天后,草够一车了,也差不多晒干了,用稻草绳子捆起来,用架子车直接拉到牛集去卖。据说这楼是观音菩萨盖的,观音菩萨看夜宿荒山的人可怜,随手从灶王爷那要了几块锅膛砖,搭了这个遮风挡雨的黑石楼。我来的时候,黑石楼里已经有了四个干草铺。你爷爷选个地方,给我打了干草铺。一再交代,干粮一定要带身上,走一步带一步。三天后,他拉车来接草。
今天天气晴朗,阳光清澈,父亲的思维也清晰起来。我知道这很难得,我应该为父亲高兴,认真听他讲述故事,让他讲个尽兴。但我必须打断他。我心里愧疚,脸上却装出崇拜,打断父亲说,爸,你那时真是不容易,那么小就上山砍草,在山上过夜,等我下班,你再接着讲,我还要听。往常我这样一说,父亲就会说,好,等你下班,我再慢慢跟你讲。可是今天,父亲沉下脸,大手一挥说,你走,你们都走,你们都忙得很,你们就把我一个老呆子关家里坐牢!
大姐到现在还没到,我告诉她我上午要开会,叫她早点过来。我拿出手机,准备问她到哪了,却临时改变主意,发了一条信息:赶快打电话催我开会去。很快,我的手机响了,大姐撇着腔调说,会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不到!我开了免提,让父亲听到,这是我们常用的伎俩。我望着父亲等他发话。父亲说,什么开会,不就是打麻将。我说,爸,谁一大早打麻将?父亲说,刚刚吃过中饭,怎么是早上?
转眼之间,父亲又糊涂了。
父亲头脑糊涂有七八年了。母亲在时,都是母亲照顾他。我们偶尔去时,听他说些糊涂话,只当作笑话好玩,有时还故意逗他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母亲去世后,我们来陪父亲才知道这些年母亲有多难。父亲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清醒时说糊涂话,糊涂时说清醒话,弄得你无法分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父亲说的这个故事,我求证过大姑,大姑说,没印象。我问二叔三叔,二叔三叔说,你爸糊涂了,经常胡说。爸妈一直在农村,养育我们姐弟三人不容易,我们读书、工作、成家,都是父母为我们付出,我们没有替他们分担一点辛劳。现在没了母亲,父亲头脑也坏了,想想真是可怜,我们只能尽力对他好一点。我对着手机说,领导,请原谅,我父亲一个人在家无人照顾,我只能稍微迟到一点,十分钟后我一定赶到。姐姐在电话里说,我不要理由,十分钟不到,你就不要来上班了。语气严厉到连我都听不出是她声音。我关了手机对父亲说,你不能要你儿子下岗吧?父亲看看我说,你和什么女人说话?你是有家有业的人,我们是根本人家,你和别的女人不清不白,你是要被開除的,我们家不能出这样人。
父亲找到新话题,开始对我展开品德教育。我越要走,他越拦住我。不许去找那女人。父亲宽阔的后背紧紧靠在大门上。
我原本还想早点去,表现一下自己不落后,现在真的要迟到了。忽然,我想到那张火车票。这是一张十几年前的老火车票,是从一个搞收藏的朋友那里淘来的。朋友反复讲述搞到它的非凡经历,又不要钱,我只好请他一顿酒,这张票比它实际的价格就高出了无数倍。可是父亲认这张车票,这张票帮了我的大忙,只要我拿出这张车票,父亲就确定我要出发去找王强。现在的新车票不行,他不认。关键时刻,我必须用上它。我拿出旅行包背上,握着车票走到父亲跟前,说,爸,我去找王强。父亲接过车票看了看,连声说,好,好。将一把雨伞递到我手上。
终于逃出家门。我在小区门口小店寄存了包和伞,赶紧给大姐打电话,叫她陕来,告诉她见到父亲按照我说的话去圆,不要说漏了,惹父亲生气。手机打开,一条信息跳出来:因主要领导和另一个重要会议时间冲突,今天的会议暂时取消,时间另行通知。
我现在回去,父亲一定要问,你不去找王强了吗?你怎么回来了?你是不是在糊弄我?父亲现在一定要控制好情绪,不能让他躁怒,一旦躁怒,就会歇斯底里,思维完全混乱。我费尽周折从家里冲出来,现在却回不了家。我向大姐报告了情况,大姐说,你先找个地方转一会儿,等一会回家,父亲就忘了。我在小区附近转了一会,进了小区又转了一会,不知不觉转到我家楼下。抬头看到父亲正站在窗口朝外面看,那样一个孤独的身影,我的心一下就软了。我知道父亲在焦急地盼着他的子女,我觉得父亲一定看见了我,我只能上楼回家。我心里盘算着,父亲问,我就说去晚了,火车没赶上。但这样说父亲肯定会生气,会说我不把这件事当件事。我就说我把时间记错了,不是今天是明天,我太心急了,这样父亲会高兴。
开门进家,父亲果然等在门边。我微笑着等父亲来问,可是父亲接过我的包和伞,和往常一样说,下班了,准备吃饭。父亲已然把刚刚的事情忘却了。我的心里没有轻松,反而更加难受,我借着到卫生问洗脸,擦去两眼泪水。父亲忽然问我,你妈呢?怎么还没回来?赶紧做饭哪!我说,爸,你糊涂了,媽已经不在了,生病去世了,你忘了?父亲睁大眼睛说,你妈刚刚还在洗衣服,她是不是下塘汰衣服了?她关节不好不能下水的。父亲要我赶快把母亲找回来,我知道解释是没用的,我们只能跟着父亲的思维欺骗他,慢慢想办法让父亲的思维转移到我们的思维上来。我故意岔开话题说,爸,你给我讲故事,你说那毛驴怎么坏了事。我搬了凳子坐到父亲跟前,催促父亲赶陕说。
父亲说,你妈命苦,养你们三个,一天福没享到。她怀着你的时候,背着你姐在田里栽秧,一跤跌在烂泥田里。父亲的思路走上了这条线,不断地问,你妈在医院谁在陪?中午送什么吃的?一会时间里问了四五次。我不想让父亲沉浸在悲痛里,一次次岔开话题,都不管用。我只好拿出杀手锏,问道,爸,你见过王强吗?果然,父亲的注意力被成功吸引了。
父亲说,怎么没见过?没有王强我早死了。
我砍了三天草,我等你爷爷的车来。那四个人的草已经上了车,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是自己带车的,自己砍草自己运到牛集卖。他们比我大几岁,他们四个是结伴的。睡在我边上的那个人说,我饿一天一夜了,我一点力气没有了,我没法和你们走了。那三个人的干粮早完了,四个人一起的,当然不能丢下他,几个人急得要哭起来。我看他们也是没有办法了,心想你爷爷今天就要来,就对他们说,我这里还有一点点。我只剩下最后一张烙饼了,我打算分一点给他救个急,没想到那人见到烙饼就拼了命,一把抢过去,我哭着喊着,我就这一点了!那人不管不顾,狼吞虎咽往嘴里塞。几个人按住他从嘴里抢,手指都被他咬破了。
我没有粮食了,我一个人坐在黑石楼。
等了三天,你爷爷还是没有来。
你爷爷被人抓走了。
事情出在那头驴子身上。
你爷爷借了一辆驴车,在他站在路边撒尿的时候,这馋嘴驴子偷了一口庄稼。恰好一个半大小子看见,操起一根棍子就砸驴。你爷爷心疼驴,就训那小子。那小子不服,生拖死拽连驴带车拖到队长家。队长不在家,队长的老娘问了情况,就骂那小子屁大点事也来吵吵。那小子受了委屈,又来拿驴出气,说你吃庄稼我就打。老太太过来拦,被驴撞倒了。你爷爷就这样被人扣住了。
等你爷爷赶到黑石楼,我已经饿了五天了。你爷爷摇我摇不醒,急疯了,他一路上就担心我饿死了,一看我真的饿死了。他不死心,拉着我往牛集跑。驴车一颠,山风一吹,我醒了。爷爷说,你没死?你活着?我说,我以为我被狼吃了,狼没吃我吗?
我没有被饿着,却差点进了狼口。我饿得发晕的时候,来了一个放羊人,他一手拿着皮鞭,一手拿着书。他走到我跟前蹲下来,问我怎么了。我已经没有说话力气了。他取出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掰下一点放到我嘴里。甜丝丝的,可香了。他喂一点,我吃一点,喂一点,吃一点,我慢慢缓过来。他临走的时候,把那团黑乎乎的东西送给了我,告诉我,一点一点慢慢吃。他一边看书,一边赶羊,慢慢走远了。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却被一阵奇怪的风声惊醒了。我一睁眼,狼!虽然我没有见过狼,但我肯定那是狼。都说狼和狗差不多,不是,狼一看就是狼,看人眼光就是要吃人。我眼一黑就什么不知道了,这只狼居然没吃我,它为什么不吃我?
你爷爷搂着我,说,你命大。
像父亲这样年龄的人讲起故事,差不多总会和饥饿有关。在中学教历史的大姐夫分析说,一个人最深刻的记忆是童年的记忆,他们的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所以,他们的潜意识里深深地刻着饥饿两个字。我们不必计较故事的真实与否,即使他们把自己经历的或者别人经历的混为一谈,也是不妨的,他们的遭遇大抵是相似的。回忆是一种倾诉,一种超脱,苦难变得不再哀伤,反而有了一种淡淡的温馨。所以,就让他沉浸在往事中吧。
我问,那个放羊人是王强?
父亲说,你听我说。
你爷爷仔细看了我吃的黑乎乎的东西,说,这是山芋砖,这是槐树洼王先生家的。
你爷爷年轻时在王先生家做长工。王先生开私塾,他家的田请人种。槐树洼在长山里,山地多,旱粮多,活累人,一般人不愿种。你爷爷人勤快,田里事做,家务也做,王先生很喜欢他,有时还教他识几个字。每年收好多山芋,老先生说,稻麦米面都不能放长久,只有这熟山芋阴干了,可以十年二十年不坏,最耐储存,可防荒年。他教你爷爷做山芋砖,把煮熟的山芋,压在土砖模里,晾干后和土砖一样。撬开土砖墙,和土砖砌在一起,外表根本看不出。他不叫别人做,他只相信你爷爷。所以,你爷爷一眼认出了。你爷爷说,这个放羊人应该是王强,王先生的儿子,他和王先生一样喜欢拿着书。
我问父亲,你去过槐树洼吗?
父亲说,去过。
你爷爷临终的时候还在对我说,等日子过好了,你要报答王家,王家救过你的命。
等我去槐树洼的时候,王家早已经不在了,他们一家去了南京。他们家本来就是南京的,是抗战时逃难逃到这里的。
父亲第一次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兴奋极了,一双双明亮的眼睛发出惊喜的疑问,这是真的?父亲说,怎么不是真的?
我们这里和南京不过二三百里,一江之隔,抗战时期,的确有许多南京人逃到这里,他们多是有钱人。
我们愉快地讨论起来,如果父亲说的是真的,王家逃难到这里能够买田置地,应该是有一定实力的,他们什么时候回的南京?他们现在还在不在南京?
我们讨论得很热烈,做了很多联想和假设,却没有发现,在一旁的父亲早已生气了,说,你们想什么?我们说,啊呀,说着玩呢,到哪里找呀,人都没见过,就是找着了,人家还能记得我们吗?父亲说,是我们应该记着人家,不是要人家记着我们。
我们兴奋的热情很快就消退了,不要说父亲的话不敢当真,就是真的,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
说起这件事的缘起,还要说一个推销保健品的青年。虽然我们早有提防,但也不能不佩服这些人钻眼觅缝无孔不入的本领。总之,父亲喜欢上了这个憨憨的年轻人,他免费给父亲按摩,陪父亲扯东拉西。因为我们完全控制了父亲的经济,所以也不担心,有时甚至替这个终归竹篮打水的年轻人抱屈,希望他早点醒悟,不要白费时间和精力。我们一再申明不会购买,免得他日后纠缠,内心却希望他执迷不悟,替我们多陪陪父亲。就这样,到这位年轻人终于失望离去后,父亲彻底记住了这件事,年轻人顺水推舟的奉承,让父亲百分百相信这件事是真实的。大姐夫说,得失相依,我们享受了一段免费陪护的便宜,我们也捡拾了一个絮叨不休的麻烦。
父亲的脑子愈糊涂,对这件事记得愈清晰,反反复复旧事重提。我们也慢慢习惯了,父亲完全生活在旧时空里,就像这问旧房子,他一步不肯离开。我们都已买了新房子,我们希望他住到新房子去,但他去了新房子就要走,并且去过之后越发糊涂得厉害。只要回到老房子,慢慢又平息下来。所以只能让他住在老房子里,我们轮流来照顾他。
趁着父亲午睡,我回了趟自己家,妻子每天照顾小孙子,也是很辛苦。拿了换洗衣服匆匆赶回去,父亲不见了!前前后后找不着,我恐慌了,常常在各种场合看到寻人启事,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走失,这次临到我们了。赶紧联系姐姐、弟弟,爸爸失踪了!
父亲没有拿身份证,他连现在的动车票都不认识,所以我们重点查看各路公交车的监控,各个路口行人的监控。朋友圈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们通过各自的朋友圈发寻人启事,朋友又发朋友圈寻求帮助。我们以前也帮人发过,并且成功帮人找到走失的亲人。可是我们失望了,每一项努力都无效果,海量信息经过排查都不是。我们把重点放到乡下老家,二叔三叔组织人把附近的池塘水沟都逐一摸查了一遍。
从城市到乡下,天眼密布,一个大活人,尽管头脑糊涂,不可能不留下一点踪迹。小弟甚至对现代公安引以为豪的天眼系统产生怀疑。大姑则对我的失职忍不住抱怨,我们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只有二叔三叔看得开,当年要是饿死,早连骨头都没渣了,活到现在很好了,痴痴呆呆享福也不知道。现在只有等公安部门消息,看看哪里有寻尸的,收容流浪汉的,真找不到也是命。
五天后,父亲自己回到家中。
我们一边庆幸一边生气,抱怨他把我们吓坏了。问他究竟去了哪里,父亲不回答,一直呵呵笑,看上去很快乐。我们帮他脱下肮脏的衣服,给他洗头洗澡,看他一直沉浸在快乐中。
父亲究竟去了哪里呢?但只要他平安,只要他高兴,我们也不必问,随他好了。
我把父亲按在躺椅上晒太阳,父亲忽然神秘地说,我找到了王强。看到我们吃惊的样子,父亲说,我去了南京。
南京城中心是一个高大的古城堡,走进城堡里面还套着一个城堡,一个城门洞连着一个,往城墙里面通。城墙头上站着拿刀拿枪的兵,望着城墙下面的每一个人。穿过一道道城门洞,走到城门外,城门外一条大街,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来车往。大街前边一条河,河上一座长长的石桥。走过石桥,向左一条沿河街,顺街往前走,右手边一个大寺庙,隔着围墙,看见大树和屋顶,中间有座高高的塔。绕过寺庙往南,一条青石板街,走在街上看见寺庙大门,望见庙里大香炉上香火正旺烟雾滚滚,人来人往,大殿里传出敲打钟磬的回响。沿着青石板街往前走,街口立着一个石牌坊,两边旧式瓦房,各家店铺依次排开,卖竹器的,木器的,陶瓷的,打铁的,弹棉花的,卖糖食的,磨豆腐的,剃头的,做衣服的。
走进一家门面,迎门柜台后的香案上,不是骑着老虎的赵公元帅,也不是手握大刀红脸绿袍的关老爷,却是慈眉善目拱著双手的孔夫子。八仙桌两旁两把黑漆漆的太师椅,太师椅上铺着灰色垫子。穿过前堂,后面是一个院子,院子中间三棵老槐树,树荫下有石桌石凳。院子两边是库房,中间一个方形水池,院子后面一排大瓦屋。推门进去,团团雾气把我包裹了。里面的人全都光着膀子赤着脚,围着一圈粗白布。白色的汁液从大漏瓢里流入翻滚的开水锅,瞬间凝成晶莹透亮的山芋粉条。我正看得发呆,有人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一位须发全白的人一手端着茶壶,一手拿着书。
大姐夫拿着笔,跟着父亲的描述画图。小弟打开手机地图,对着大姐夫的示意图找起来,找着找着叫起来,中华门,长干桥,大报恩寺,正学街,啊呀呀,父亲说的全都对得上!
父亲真去了南京?可是,现在的南京怎么会有那样古老的街道,那样原始的作坊?可是父亲描述的路线清清楚楚,地理方位分毫不差!难道父亲是梦游,或者是穿越?对于老爷子种种出人意料的言论,大姐夫有过高论,幻想是人类消解痛苦忧愁最为便捷有效的方式之一,因为饱经忧患,所以常作幻想,因此有田螺姑娘,有天上掉馅饼式的民间故事,幻想是一杯安慰剂。倘若是完全不着边际,反倒可以解释,这幻想得和真实几乎一模一样,就让人无法理解。小弟问大姐夫,老头子到底去没去南京?大姐夫从容不迫,把香烟吸出嘶嘶的声音,说,两种可能,一是父亲曾经去过,二是爷爷曾经去过,爷爷给父亲说过,总之,他与南京确实应该有某种关联。
我们是要有行动了,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我们再不能把父亲寻找王强的愿望看成是意识糊涂后的臆想,我们开始相信,在南京的某一处有一个与父亲或者我们家确实存在的关联。
第一步,我们先找槐树洼。
小弟开车,在导航里输了槐树洼,一下子跳出来三四个。我们找到牛集,分路口,黑石楼,一路寻去,果然找到了槐树洼。扑面层层青山,乌黑的柏油路在青山绿水问蜿蜒穿行。导航把我们带到一个美好乡村,村前一个大荷塘,层层叠叠的荷叶问冒出朵朵红莲、白莲。塘边修了水亭,连着木制栈道和观景平台。一例粉墙黑瓦的二层小楼,连着小院,装饰着马头墙,配以古典门窗。村口广场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三个墨绿色大字:槐树洼。旁边一棵移栽来的大槐树,树上挂着一口旧铁钟。我们一下车就被农家乐迎进去。吧台里一位衣着入时的女子,一面指挥身穿印花蓝布的大嫂上茶,一面和我们攀谈。
槐树洼新村是包括槐树洼在内的十几个村庄合并到一起的。这里地势开阔,交通便利,原来的槐树洼在跑马岭后,槐树岭下,离这里隔着七八里山路呢。女子说,可巧了,我外婆家就是槐树洼的,我小时候常去槐树洼玩。村后是槐树岭,那时候长满刺槐树,开花的时候一山雪白,一个村庄就包裹在这雪白的香气里。我们爬上树摘槐花,吸槐花里的蜜糖,常常被蜜蜂蜇了,疼得哇哇叫。现在槐树没了,村庄也没了。对于我们打听王先生和王强,女子说,我没听说过,我叫我妈来,她或许知道。一会工夫,女子和一位穿着印花蓝布的农村大娘从后屋走出来,大娘说,没听说,这要问年长的人,我听说有树大爷还在村里,他或许能知道。
这个消息让我们振奋,我们决定赶往真正的槐树洼。
越往前走山势越险峻,道路也越崎岖。好在小弟的车是越野车,即使在砂石路上也能自由奔跑。路边的丘陵坡地全是山芋,一垄一垄的绿色向山腰伸展,像梳子梳出来一样。终于越野车也喘起粗气,我们上了一道小山岗,顺着山岗走,前边一个村庄的废墟,废墟边上,孤零零地立着两问小屋,门口坐着一个老人,浑浊的老眼打量着我们。
我问,您就是有树大爷吧?
嗯。
这个村子就是槐树洼?
嗯。
您一直就在槐树洼?
嗯。
向您打听一个人,就是你们槐树洼的,叫王强。
没有。
他父亲是开私塾的王先生。
没有。
他家是抗战时从南京逃来的。
抗战时我才出世。
大姐夫见我问不出,亲自上阵,问,你们村叫槐树洼,怎么落在山岗上?
老人家听到这一问,话题打开了。
你们过来时,有没有看到一个大水库?大水库把这里的山洼都淹了,原来在山洼里的村庄都搬到高处来。原来的槐树洼夹在龙虎山的缝隙里,藏得很深,出入都要经过龙虎斗,就是两山相对的峡口,水库的坝堤就修在那里。
你小时候,还有什么有趣的事?大姐夫一点一点往深挖。
老人想了想说,小时候印象最深就是来土匪。这里藏得深,战乱的时候,就有富人家躲到这里来。外面的人不知道,可是土匪鼻子尖,就来抢。其实那些土匪,都是附近的穷人,穷极生痞。白天都是平常人,晚上天黑,马虎帽头上一套,聚到黑石楼。结了伙就胆大了。我听说过,土匪抢一家,因为是熟人,不好吊人家主人,就吊他家小伙计。可那个小伙计是汉子,一个字没有说。后来主家送他钱、米和驴子,他回家盖了房,娶了媳妇,有了一家人。
大姐夫赶忙问,那个主家叫什么?小伙计叫什么?
老人说,不知道,都是听来的。
回来的时候,再经过那个大水库,我们停下车来,一湾蓝汪汪的水镶在层峦叠嶂问。那个真正的槐树洼,那些往事,那些人物,都深藏在水底了。
过了槐树洼新村,路边一个干净整洁的工厂,门口立着一块大石头,上写:甘薯之都。现代科学研究,甘薯可以抗癌、护心、控糖、抗衰、减肥,一下身价百倍。听人介绍,投资甘薯产业园的是南京人。我忽然生出联想:会不会与王强有关!
当我把这个带着冲动的联想说出的时候,大姐夫把那个小伙计和爷爷联系到一起,如果这些不是臆想而是巧合,是多么令人惊奇啊。小弟有个朋友在电视台,小弟立刻与之联系。
小弟的朋友在详细地听取小弟的报告后,十分兴奋,告诉小弟,产业园的投资人确实姓王,南京人。假如这些设想能够成立,可以拍成一部电视片。这位朋友兴致勃勃地带领我们探访甘薯之都,走进高大宽敞的厂房,看见新鲜红润的甘薯蹦蹦跳跳上了生产线,一路变化,最后包装成了一盒盒名目繁多的制成品。看着陈列柜里琳琅满目的产品,每个人不由自主发出惊叹,普普通通的山芋竟然可以做出这么丰富多彩的产品!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办公室人员,他拿了一盒特色产品请我们品尝,煮熟的红薯切条晒干,渗出一层细密的白霜。甜津津的红薯条,吃得我们心里甜津津的。在我们讲述了关于王强的故事和联想后,那位工作人员说,这个就不知道了,需要求证王总本人。
如何能见到王总呢?
工作人员说,恐怕很难,只在开业典礼的时候看到过一次,他的事业很大,这里只是其一,就是我们厂长也很难见到。
回程的时候,我们绕道去黑石楼。车到路口,失了方向,原来的三岔口变成五岔口,打开导航,才找到正确的路。黑石楼正在开发,沿着登山石道,一路到了山顶。我们违反告示牌上的禁令,顺着长满苔藓的黑石,一直爬到高顶,山风轻轻从耳边吹过,看见远方甘薯之都的幢幢厂房,槐树洼新村的排排屋顶,锁在群山之间的一片明镜—槐花湖。
记者真是神通,正当我们渐渐确信自己的联想纯属臆想的时候,小弟的朋友不仅找到了王总的府邸,而且通过关系获得了约见的许可。我们一路高铁呼啸南下,从南站进入地铁。到了安德门,地铁忽然窜上高架,瞬间阳光灌满车厢,一片通敞明亮。隔着车窗,我很快看见了雄伟厚朴的中华门,看见了巍然卓立的大报恩寺塔。我们从中华门站下地铁,马不停蹄,出租车穿街绕巷,把我们带到一个依山而建的高档小区。我们走进一座融合了现代风格的中式别墅,四合院中央有三棵丰姿秀拔的大槐树,树下有石桌石凳。中堂挂着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像,上面一块乌木匾,黑底蓝字:槐荫启秀。
王总是一位儒雅干练的人,显见稀疏的头发根根清晰流畅。他在书房接待了我们,亲自为我们布茶。寒暄之后,记者朋友拿出白色绸缎包裹的东西,放到桌上,一层层打开,露出一块小小的山芋砖,轻轻推到王总面前,问道,王总看看,可认识这是什么?
王总慢慢锁起眉头,轻轻拿起,细细看了,仍旧放回,抬起眼睛看着我们,说,你们从槐树洼来?
我们三人相视一笑,同时点点头。
王总没说话,起身打开身后的橱柜,从里面拿出一块白绸布包裹的东西,放到桌上,一层层打开,露出一块几乎一模一样的山芋砖。我的心感觉一下子要从喉咙蹦出来,像与组织失散多年的人,突然间接上暗号。
望着我们三张无限惊喜的脸,王总问,你们认识马一民?
我和小弟摇摇头,记者朋友说,甘薯之都的马厂长?
王总转身拿了一本画册,封面上一排胸戴红花,手拿剪刀的人,是甘薯之都的开业典礼。
我和小弟一眼看出一张憨憨的笑脸,这不是那个推销保健品的年轻人吗?
王总细长白皙的食指轻轻敲击发出暗光的桌面,缓缓地说,我是叫王强,但我们家从没到过槐树洼。又轻轻拿起山芋砖细细端详,继续说道,当然也不会做山芋砖。停了半晌,他将山芋砖重又放回绸布上,双目炯炯看着我們三张写满惊愕的脸,接着说,不过,我相信这故事,因为我们家确实有过类似经历,所以,这个故事打动了我。正是山里人的那种淳朴,让我决定在那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