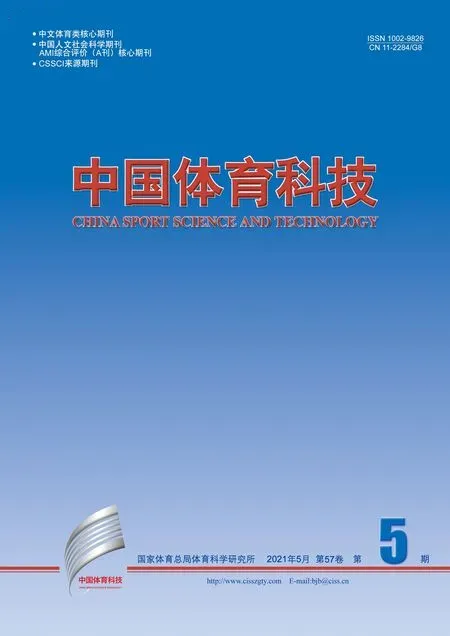略论民国时期射箭运动的发展及其启示
2021-06-25陈雨石
陈雨石,贠 琰
射艺作为我国传统的射矢活动与射矢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商周以降,射艺呈现出“礼射”和“武射”两个向度。前者经由儒家文化的阐释,成为维系礼制的重要载体;后者则转为军旅武艺的重要素养,进而分化为步射、骑射、车射等技艺。近代以来,火器的普及使冷兵器与战争的关系日益疏远,弓箭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奥运项目现代竞技射箭(modern competitive archery)的射法、射器与中国传统射艺差别较大。近10年来,民间爱好者及体育界同仁开始共同推动传统射艺的复兴,在文献整理、文物复原、技术研究、历史考证等诸多方面成绩斐然。然而一个关键问题却少有合理解释:如果冷兵器的退场导致传统射艺衰亡,那么何以英国、美国、日本、韩国、土耳其、匈牙利等国皆保留着一套传统的射箭技术及弓箭制作技艺,而中华传统射艺在清亡以后却逐渐衰落?出现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其原因还须通过回溯历史进行考索。本研究认为,民国时期射艺的发展史直接形塑了今日中国射箭运动的存在形态,使现代竞技射箭成为该项运动的绝对中心。
1 传统射艺的竞技化转型
民国时期,传统射艺活动在成都、上海、南京、天津等少数地区零星举办。射艺被“再发现”来自国术界。只不过,其与“国术”的关系并不稳固,仅附带作为“国术”之一部被引入我国最初的现代竞技体育赛场。民国时期的全运会拉开了传统射艺竞技化转型的序幕,主要表现在:1)以“土洋兼容”为目标,国术界制定了竞技射箭比赛的规则;2)以新文化运动为背景、女子国术运动蓬勃开展为契机,女性射箭运动员亮相于竞技场。
1.1 国术体系中的射艺
中国传统武艺在清末民初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称谓,或称“武术”,或称“技击”,或称“技勇”等(季培刚,2015)。民国初年,北洋将领马良开创“中华新武术”体系,统合“拳脚”“摔角”“棍术”“剑术”四科,影响甚深。1928年,中央国术馆成立,“国术”一词替代“武术”得到认可。
中央国术馆最初制定的国术项目中并无射艺。1928年10月,第一次国术国考科目设置分“学”“术”2科,其中“术科”分拳脚、摔角和持械3项(李臣等,2016)。斯制与马良的“新武术”基本一致,唯将其中的“棍术”与“剑术”统合为“器械”。1929年,修订后的《国术考试规程》发布,术科中又增添了“搏击、劈剑、刺枪”3项,未见射艺(徐诚堂,2016)180。射艺是清代武科枢要,民国初年精通射艺之人想必不少,何以国术一开始未纳入射艺一科?
本研究认为,这一疑惑可从褚民谊对国术的定义窥见端倪。时任行政院秘书长兼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的褚民谊认为,“国术”的范畴应为“我之所有,人之所无”(徐诚堂,2016)183,即归为“国术”的武艺应是中国独有。若说射艺为我国专有,较为牵强,各国均有射术,唯儒家射礼可算我国特色。而在彼时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国术界并不提倡古礼,反致力于让武术融入现代竞技体育之中。或正因此,国术馆同仁起先未把射艺归为国术,后又发现射艺中的竞技元素,遂将其引入新式运动会,成为“射箭比赛”。因其须与“国术”范畴契合,传统拇指射法(或称“蒙古式射法”,mongolian draw)和传统射箭器具(沿用清朝样式的弓箭及扳指)得以保留。
1933年第5届全国运动会,射箭被正式列入国术项目。此番也是国术作为正式锦标项目第一次亮相全运会。1935年第6届全运会中又加入了女子射箭比赛。随着射箭成为全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一些地方国术馆也开始推行射箭运动,部分国术家也致力于提倡射箭并从事射箭的教学。
1.2 竞技射箭的规范化
全运会作为民国时期国内规格最高的竞技比赛,在项目的规则设计上致力于对接国际标准,民族体育项目也不例外。全运会国术比赛规则由大会组委会和中央国术馆共同制定,其中就包含有完整的射箭比赛规则。从第6届全运会射箭规则看,其形式已完全不同于清代武举,而是引入了一些西方因素。如比赛分射中及射远两小项,其中射远非中国传统,而是英式射箭的竞技项目。射中比赛所用环靶及其数字计分规则,又凸显出中西合璧的特色(图1)。

图1 民国第6届全运会射中比赛所用箭靶式样(第6届全运会筹委会,1935)Figure 1.Target Form of the 6thNational Games of Republic of China
我国惯常以“侯”指称箭靶。周代的侯为方形,其正中标的被称为“鹄”。传统的计分规则是只计中或不中鹄(陈槃,1950)。类似于现代竞技射箭用的设色环靶在宋代即已出现,《宋史·兵志》载“画的晕五重”,即指一种五环靶。其中心为红色,次白色,次苍青色,次黄色,最外围为黑色。清代继承了此种靶制,《皇朝礼器图式》载一种“皇帝御用布鹄”,分大小两类,大者“径一尺二寸,凡五重相比如晕,外红次白、次蓝、次黄,其的红牛革”,小者“径七寸至四寸”,“外红中白二重”。这种环靶的靶心是活动的,被箭击中即会坠落(《皇朝礼器图式》卷十四)。现代竞技射箭五色环靶系英国人首创,19世纪已在欧美各国被广泛使用(Ford,1887)73-76。自1900年巴黎奥运会始,射箭比赛就一直使用环靶计分。中式环靶在历史上是否附有数字计分的规则,目前尚未有史料佐证,故暂且认为全运会的计分规则参考了西洋射箭运动。因中、西靶制大体相似,故全运会射箭比赛采用环靶,一方面尊重了传统,一方面又尊重了国际规则。
射距方面,传统一般用“弓”这一单位来衡量(1弓≈1.23 m),全运会则全部改为新式长度单位,以“公尺”(米)来规范射程(男子射程30 m,女子射程20 m)。不过,全运会比赛用弓的拉力仍沿用清代单位“力”(1力≈4.7 kg)。因全运会采用清朝制式的传统角弓,这些弓在制作时仍循旧制,在角片上标注其“弓力”,故一时不便改用新式单位。另外,规则中还明细了属于“犯规”的行为,比赛时运动员的技术动作由中央国术馆派出的裁判负责监督。此规则似乎表明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现代体育之间可以融合。
1.3 女子射箭运动的发展
与“强国强种”的思潮相呼应,女性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晚清以来掀起的“天足运动”拉开了女子解放身体的序幕。新文化运动期间,妇女解放思想继续发酵,“新女性”要求挣脱家庭束缚,与男子一道参与公共生活,其中就包括参加竞技体育运动。中国妇女界也有意识地宣扬女性应摆脱“柔弱”“病态”的印象,转而以身体上的健美为新女性的标准,使得女子体育发展在此时期获得长足进步(游鉴明,2012)。中央国术馆及地方国术馆在这一风气下也着力培养国术女将,女子射箭运动即在此背景下开展。
受西方影响,民国时期最早的女子射箭运动出现在教会大学。1920年代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燕京大学等教会学校中就有女子射箭社团,唯尚未进入竞技赛场。教会学校一般采用英式射箭,使用英格兰长弓(longbow)与地中海式三指射法(mediterranean draw)。19世纪以来,女子射箭在欧美较为普及(Ford,1887)154-278,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首次将女子射箭列入比赛项目,可证其发展已臻成熟。不过,我国女子竞技射箭最终并未西化,而是在国术界的引导下采用传统射法。
1933年第5届全运会尽管未设女子射箭项目,但江苏省的全运会预选会中却有女子射箭,并分设了男女比赛规则。而全运会的正式项目中又没有女子射箭的缘由尚待考证。不过,一些地方国术馆确已开始培养女子射箭运动员。例如,1935年,青岛国术馆的石秀兰与张文秋在青岛市级的射箭比赛中夺得锦标。
当时亦有学者在理论上宣传女子射箭的益处。如1934年的射学专著《弓箭学大纲》指出,射箭“在生理上是极合于妇女的”,射箭的站姿“优美柔和”,这种偏静态的运动女子更易习练,并且,不少女子运动项目需要专门制作运动服,而女子射箭运动对服装要求不高。可见在1935年第6届全运会举办前,女子射箭已具备一定的实践及理论基础,增设女子射箭比赛基本已无障碍。
因第6届全运会参赛女运动员人数暂无法详计,仅知进入射中决赛者8名,进入射远决赛者7名。射远决赛时,上海运动员陈金钗因故临赛弃权,故实际仅6名进入决赛。进入决赛的女运动员,地域性特色较明显(表1)。

表1 1935年第6届全运会女子射箭决赛排名Table 1 Ranking of Female Archery Final,the 6th National Games in 1935
河南队3名女运动员教练马仁甫系前清武探花,时任开封骑射会弓箭总教练,也是河南运动员马瑞莲和马瑞兰的父亲。射远比赛上海队3名女运动员系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学生,其教练为摔角及射艺名家佟忠义。马仁甫和佟忠义皆为清代骑射传统下成长起来的武术家。可见当时女子竞技射箭在技法上也完全沿袭传统,具有鲜明的国术特色。
自第6届全运会始,女子射箭正式成为竞技运动项目之一,中国的竞技射箭运动也因女子射箭运动员的加入而更趋完善。自此,标准化规则的制定及打破性别界限的运动员选拔,使传统射艺初步实现了竞技化转型。
2 射箭技术的科学化探索
2.1 射箭技术科学化的背景
由于射箭的军事实用性,中国古代有关射箭技法的书籍繁多,自两汉以迄清代的“射书”约120余种(马明达,2004)。但古代有关射箭技法的论述更多是一种经验性的总结,其多以模棱两可的“口诀”形式呈现,再辅以养气导引式的“心法”,练习者往往只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无法形成系统的科学训练法。近代“体育”概念的出现,亦伴随科学的运动训练学理论输入中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勃兴后,欧美的运动生理学、卫生学、心理学及体育理论大量输入中国,并融入了中国的体育学学科建构之中(罗时铭,2008;王颢霖,2015)。
新学科建立背后的推动力量,是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价值观的猛烈抨击及对“科学”的大力提倡。再经由“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等舆论上的宣传,“科学”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
这一思潮也影响了以弘扬国粹为己任的国术界。1928年中央国术馆的成立宣言中,馆长张之江宣示:“自从近数十年来,许多同志们,用了科学的方法,来估计我们国术的价值,才晓得我们的国术,不但不是反科学,而且在科学的立场上,还有崇高的位置。”尽管张之江(1931)在阐明国术的作用时,仍高擎“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等话语,但与马良提倡“新武术”时不同,此时科学已开始为国术的发展铺陈。1930年代国术的倡导者,必须要强调国术是一门科学的运动,且符合现代竞技体育的竞训标准。推动国术竞技化的其中一项要务,即实现国术训练的科学化。1930年代“科学”的射箭技术体系,即在此背景下出现。
2.2 张唯中对射箭技术科学化的贡献
近代最早对射箭训练进行科学化探索的体育家,当推张唯中,前述他所著《弓箭学大纲》即民国时期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射箭的典范之作。他研究“弓箭学”的目的即“是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张唯中1920年代就读北大,显然受到过胡适等新文化派健将的熏陶,对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及背后的学术理论较为熟悉。胡适(1998a,1998b)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张唯中亦提出要用科学的方法“整理过去的弓箭”“再造未来的弓箭”,这些方法包括“生理学、运动生理学、物理学、教育学、教授法,以及其他有关各科学。”
张唯中活用科学知识阐明射箭的动作原理,体现在《弓箭学大纲》的如下内容中:1)引入力学知识,提出射箭能否平稳,与站姿有很大关系;2)引入运动生理学知识解释“射箭运动与身体上各部器官的关系”,分“足部、腿部”“腰部、胸部、背部”“肩部、臂部、手部”“眼部、耳部”“肺部、心脏”等5大部分依次详论;3)引入物理学中“弹性极限”原理解释中国传统弓反曲设计的优点,并对比了几无反曲的美式直拉弓和日本和弓,以证明中国弓性能最为精良。诚然,若以更为精准量化的科学范式审之,张唯中之论述仍稍嫌单薄,但其方法及视野在当时都是具有开创性的。
基于对射箭动作原理的探索,张唯中又设计了初、中、高3级练习法。初阶是用15 h即可初成的方案,将射箭动作分解为“执弓、上箭、开弓、撒放、收弓”5段,每段又分2个动作单元,叙述清晰,易于实操。中阶则介绍了几种不同的执弓法、勾弦法和站立法,并说明哪些适合于初学者,哪些适合于进阶者。高阶中最具原创性的是“动的”练习法,即射移动靶的方法。另外,在高级射法部分,张唯中仍保留了属于传统射书话语的“养气法”,但他将“养气”与体育竞赛的心理建设联系起来,力图古为今用。张唯中完全抛弃了传统口诀式的射箭技术表述,代之以详细的体育动作分解说明,且配以照片辅助,其规范性和系统性已较符合现代竞技体育的标准。
张唯中对科学范式的运用虽然存在局限性,例如他提出可在军中推广射箭,以替代射击训练,其初衷是为国家节约子弹,但将两项运动的技术混为一谈并不可取。但他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射学经验,又融合了当时最新的西方科学理论,其射箭训练法既有益于射箭竞训,也便于推广普及。王颢霖(2014)认为,民国时期的国术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但若以中央国术馆的标准,把射艺归入广义的国术范畴,那么张唯中的《弓箭学大纲》显然是国术科学化的一次重要尝试。
3 射箭运动的发展困境
3.1 射箭运动员的地域及年龄分布问题
1930年代,尽管在国术界的推动下竞技射箭已步入正轨,但比之田径和球类运动,射箭却仍属边缘运动,其普及程度不甚理想。
第6届全运会男女射箭共4个项目,冠亚季军共12名,其中河南一省有8名,且男子射远前6名皆来自河南和北京。
除地域性问题,男子射箭运动员的年龄构成也甚不平均。《申报》曾以《老人射箭大比赛》为题报道了第5届全运会的射箭比赛,称:“各运动员除北平(现北京)之徐士骧年轻小外,余均40以上,至60余岁须白齿缺、精神尤健”。参加射中决赛的9名运动员中只有1名青年,不免令记者感叹:“可见箭术不传者,已数十年矣。”并且,这种情况到第6届全运会时仍未改观。
3.2“土洋体育”之争的悖论
国术(包括射箭)等“土体育”不如田径、球类运动等“洋体育”流行,这一现象引起一些国术家的不满。张唯中就忧心球类运动和田径中“锦标至上”的思想不利于大众体育的发展。彼时有志于射艺推广的国术家和军人,大多怀有一种与西方体育争胜的抱负,如热衷推广射艺的川军将领邓锡侯认为“射事为中国之最良国民运动”,优于欧美的足球、网球、棒球。张唯中也比较了体操和球类运动只注重“发育大肌肉”,而不似射箭不仅锻炼肌肉,还可“涵养德性”。
无论是邓锡侯还是张唯中,皆有尊己卑人之嫌。张唯中称射箭可培养“协同、沉毅、忍耐、果断、勇敢”的品质,事实上很多体育项目都有益于这些品质的习得。客观而言,篮球、足球等球类运动最利于训练团队精神,而国术中拳术、器械一般为二人对练,射箭更可独自习练,其群育功能恐要大打折扣。民国时期的国术家习常采取抑人扬己的论述方式,吊诡的是,在竞训体系、技术理论和效度评判上仍要向西方取经,以至于造成学习和批判的对象囿于同一事物的矛盾境地。
为何会出现这一困境?事实上这与“国术”生成的时代思潮密切相关。在新文化运动中即有主张东西调和的“东方文化派”,他们并不反对西方科学,但力争保留国粹(罗志田,2016)。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东方文化派式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如“国术”这样的“民族体育”得到政府青睐。然而,中国毕竟须继续融入西方建构的现代世界体系,在晚清还是一个纯粹“他者”的西方到了1930年代已深嵌于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之中,无论是制度或文化,都难以离开西方的影响。不过,这种“嵌入”正如拿他人器官植入我之身体,若不能完全适应则必引发排斥反应。当这种反应波及体育界,即出现“土洋体育”之间既试图融合又彼此拉锯的现象。
可见彼时的“土洋体育”之争有双重面相:一方面在国家现代化的大语境下,“土体育”积极借鉴“洋体育”的经验,以维持自身作为“科学运动”的存在合法性;但另一方面,本土体育家仍难以调和东方“国粹”和西方“科学”之间的话语之争,使得科学化的“国术”仍杂糅“非科学”的因素。这种矛盾实际反映出西方的竞技体育模式无法完全契合中国的文化语境,在西方体育自清末传入中国的半个多世纪后,以国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仍难以找到与西方竞技体育的共处之道。
事实上,时人已隐约意识到,若竞技体育无法实现彻底的“土洋”融合,则不如另辟一种新模式。张唯中因对锦标至上提出质疑,故而提出一种新的射箭比赛方案,即把“射箭成绩“和“德行考察”结合起来判定运动员的优劣。这种评定范式也是日本武道段位评级制度的原则。日本弓道的高段位即要求申请者德艺兼备,要取得最高等级的“范士”称号,必须“德操高洁”(全日本弓道連盟,2017)。
4 近代射艺发展的当代启示
4.1 趋向单一的竞技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射箭始与国术脱钩,转变为一项独立的竞技体育项目。和民国相较,此时射箭比赛的群众参与度已大大提升。1956年,全国第1届射箭表演比赛在北京举行,37名参赛运动员含满、蒙、回、藏、汉5个民族,职业上包括工人、农民、牧民、教员、学生、医生、手工业者等,在运动员的民族多样性和职业多样性上远超民国时期的全运会,显示出新中国在多民族体育和全民体育的实践上成果卓著。
为与国际赛制接轨,我国射箭运动员在1959年开始专练西式三指射法,同年举行的新中国第1届全运会的射箭比赛全部改为国际通行标准。自此,传统弓箭和传统射法退出了主流竞技赛场,而生产和售卖传统弓箭的商号,在新中国初期也只剩下了北京的聚元号(韩春鸣,2014)。
新标准的建立意味着旧标准的废弃,出现这种二元对立的局面亦源于民国时期“国术”与“竞技体育”未能真正调和。民国时期射艺的发展路径仍较单一,且始终处于国术的边缘。国术虽强调民族主义话语,但其本身对科学化的要求又使之与传统儒家思想若即若离,射礼从未受到国术界的重视,也缺乏民众基础,更谈不上恢复。民国时期的射箭运动既未继承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精神基底,也没有发展出有别于竞技比赛的体育模式,更未能深入大众,于是彻底转向国际竞技标准成为射箭界的必然选择,以免再次陷入“不土不洋”的尴尬处境。
李小进等(2018)认为,现代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享有共同的“原质”,即技击技术,故两者不应是对立冲突的关系,而能融合共生(李小进等,2018)。移之射箭研究,现代竞技射箭与中国传统射艺可否共存?事实上,近年来中国体育界已开始从射箭技术层面反思此问题。射箭毕竟是一项以“射准”为目的运动,现代竞技射箭发展至今,其器材已经过科学改进,现代竞技反曲弓与复合弓在射准上远较传统弓为优。若要复兴传统射艺,首先必须肯定传统射箭技术有助于现代竞技射箭。徐开才先生提出:“一个好的反曲弓或者复合弓运动员不一定射得好光弓,但如果光弓练得好,便能成为一个好的反曲弓或复合弓运动员”(张天昱,2015)。此处的“光弓”即指无附加任何辅助射准工具的传统弓,需运动员凭身体技术完成射准,所以光弓运动对身心要求更高,光弓训练有裨于现代射箭。徐开才先生身体力行,编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1部系统讲授中国传统射箭文化、技术及训练方法的著作——《射艺》(2015年),冶”传统“与“现代”为一炉。技术问题解决之后,下一步即须面对更复杂的文化问题,而邻国经验正好可资参照。
4.2 日、韩经验的启示
韩国和日本的传统射艺与现代竞技射箭按照两套标准、制度并行发展,且形成了良性互动。韩国将传统射箭称之为“国弓”,将现代竞技射箭称之为“洋弓”,正是“国弓”之繁荣,铸就了其在奥运射箭赛场上的强势地位。韩国认为,无论古今何种射箭形式,运动员都要奉持相同的操守。其圭臬,正是根植于儒家文化的“弓道九戒训”(元万中,2017)。再看日本弓道,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与严格的段位评级制度已使之成为日本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之一。日本弓道同样沿用了“礼射”和“武射”两条脉络,且衍生出诸多技术流派。同时,日本弓道在校园和民间的社团化推广、组织及训练模式深受西方竞技体育影响(五贺友継等,2018)。此外,日本民间还存在射箭祈福、射箭成人礼等多样的传统民俗游艺活动,实现了多种射艺形态并存的理想发展模式。
4.3 中华射艺未来发展建议
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行动指南,我国体育管理部门应把握机遇,在现代竞技射箭之外着力推进传统射艺的复兴。在此过程中,可选择设立段位制作为传统射艺的评价标准。须指出的是,段位设置要展现“中国精神”,形成“中国风格”。应尽可能保留传统射艺中的仪式规范,并将射箭运动员德行作为评价指标之一,回归儒家“射以观德”的文化传统。
以“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为探索方向,借助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冷门”“绝学”研究全面复兴的良好契机。民族传统体育学界同仁应系统考镜与总结传统射艺的技术原理、训练方法、演变历史、文化内涵,并将其成果全面转化为传统射艺复兴的力量源泉。
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发展动力,我国体教界有志之士应注重探索传统射艺的学校和社区的普及之道,此间日、韩两国民间射艺团体的运作模式可资借鉴。目前中国已经有部分高校开设传统射艺课程,可继续在既有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该课题的研究和实践。
以“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最终目标,各级政府部门应力掘与传统射艺有关的民俗文化活动,如投壶、射柳及成都“射金章”等,加以宣传普及,与既有的弓箭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等)相结合,重构为有广泛大众参与的民间文体活动。
5 结语
回溯民国时期射艺的转型之路,本文得出“中华射艺应着力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的结论。射艺的复兴不应仅仅建立在器物层、技术层,更应完成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化层。未来中国射箭运动的发展路径探索,还有赖于相关学术研究的进步。
民国时期传统射艺朝现代射箭运动的方向转型,今日已出现反向复归的趋势,这种复归并非复古,而是朝着更多元化的形态演进,射箭研究也理应朝着多元化的进路拓展。未来研究者应在整理分析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开放眼界,积极研究别国射艺发展的历史经验,在比较史学及体育全球史的学术框架内继续深挖射学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