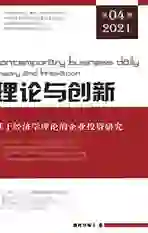唐代渤海“营州道”考证与影响
2021-06-24张宁殷铭徽
张宁 殷铭徽
【摘 要】交通是区域文明进步的表现,能够促进两地之间的交流互通,为地区发展提供便利。营州道是唐时期从渤海国到唐朝的一条陆路交通干线,在东北的历史地理发展中起到了稳定地方政权,促进地方发展的作用。它是古代中原王朝与东北少数民族政权相沟通的纽带,在历史上间接推动了两地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促使中原王朝稳定边疆局势,促进双方和平共处。
【关键词】唐渤海;营州道;历史地理
1.营州道的早期情况及发展历程
营州位于今辽宁朝阳(东经118°50′至121°17′和北纬40°25′至42°22′之间)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处于高原向平原过渡的阶梯分界地带,主要地形特征为低山、丘陵,地势为北及北西、西南偏高,向东变低。营州之名最早可追溯到黄帝时期“皇帝分制九洲”,“分青州东北、辽东之地为营州”在唐之前,营州的建制沿革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据《通典》卷一七八《州郡八·柳城郡》所载:营州在殷时期是孤竹国的领土,春秋时归属山戎管辖,战国时隶属燕,秦朝兼并天下后,营州隶属辽西郡,两汉时期以及晋朝皆沿袭秦朝对营州的划分。鲜卑首领慕容皝认为柳城的北面,龙山的南面,是福德之地,于是就建造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并迁都龙城,把新宫殿称作“和龙宫”。后燕的慕容宝与北燕的冯跋都相继把这里作为都城,后魏设为营州。后周周武帝平定齐国时,营州仍被高宝宁所占领,隋文帝平定高宝宁后,又把此地改为营州。在隋炀帝时期废营州设辽西郡。唐时又改为营州,又称柳城郡。
营州位于交通枢纽,得天独厚的军事战略位置使其自古以来便为兵家必争之地。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军事形势与民族环境,它一直作为中原王朝经略东北的重镇,设置军政管理机构,以行使边疆管理职能、关注东北少数民族政权动态。
“营州道”在唐以前便已有道路的基本形态。王绵厚、朴文英先生在《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一书中曾指出“唯由唐代“营州”至“安东”的陆路交通,唐代以后有所拓展。”这说明营州道的形成与完善应在唐以后,唐以前存在的应为“营州道”的部分道路,比如隋唐时期,出兵高丽时的陆路进军路线,经由幽州、大凌河,后渡辽水进入辽东。这一路线与后期的“营州道”大致相似。再如唐朝征高丽时,“永徽六年(655),營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出“营州”,取北路攻辽东,破高丽于“贵端水”(今浑河)。”由此可见,营州道在渤海国未建立之前就已经初具雏形。唐时期,营州道正式形成并成为唐与渤海沟通往来的主要路线。
2.隋唐时期营州道的基本情况
唐以前,营州道位于安东都护府辖内。安东都护府为唐朝灭亡高句丽后设置的管理地方政权的军政机构之一,初隶河北道营州都督府,从地理位置看,构成营州道的营州、盖牟、新城、汝罗守捉等地都隶属安东都护府治下,营州道大部皆在其境内。安东都护府与新罗、靺鞨等少数民族势力相接壤,营州道这条交通线路的存在对于中原王朝对东北地区进行行政管理,稳定地方局势有着重要作用。仪凤元年,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至辽东,成为唐朝治理辽东、渤海国等地的军政机构。
唐以后,渤海与唐朝建交,营州在维系这段友好关系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与营州道的顺利通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营州隶属河北道北部,武德元年时将隋朝柳城郡改为营州总管府,下辖辽州、燕州与柳城县武德七年,改营州总管府为都督府,下辖营州、辽州。开元年间,在营州设立平卢节度使。天宝元年,营州改为柳城郡,营州都督府改为柳城郡都督府。乾元元年,又改为营州并设平卢节度使司治所。营州一直作为朝廷管制东北的重镇,其界内有多个少数民族分布,关系复杂,为便于了解边疆动态,防止地方势力崛起威胁中央政权,中央先后在营州设立营州都督府与平卢节度使府作为东北最高军政机构,对东北地区进行直接管理,紧密掌控少数民族局势,稳定边疆关系,作为核心地带,营州的重要性逐渐凸显,营州道这条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政权的交通要道的出现对于两地交流、地方治理等方面有着非凡意义。
营州道是渤海王城上京龙泉府通往唐朝营州的陆路交通要道,是渤海的交通干线之一,在《新唐书·地理志》中对这条路线有明确记载:《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皇华四达记》云: “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度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故汉襄平城也……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城临忽汗海。”
“安史之乱”(755—763)前,渤海与唐联系常通过营州或由此转赴长安(今西安)。其走向大体为: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出发,经“旧国”(今吉林省敦化县敖东城),沿牡丹江上游河谷西南行,越威虎岭后取道长岭府(今吉林省桦甸县城东北8华里之苏蜜城),再沿辉发河经吉林省之辉南、海龙等县抵新城(今辽宁抚顺市北高尔山山城),再经古盖牟城(故址在抚顺市劳动公园,一说在今沈阳市附近),西南行至安东都护府治(今辽宁辽阳市),复西行渡辽河,经汝罗守捉(在今辽宁北镇县境内,一说在义县东南大凌河西岸)、燕郡城(今义县附近大凌河旁)抵达营州,全程约2000华里。“安史之乱”后,营州被乱军占据,渤海与唐交往改由“朝贡道”。
营州是唐与渤海交往中这条重要交通路线的起点,将唐王朝与渤海国紧密相连,便于唐王朝对地方政权的管理与对话。营州的军政机构将唐王朝旨意传达至边疆并督促落实,掌握边疆动态“量事奏闻”上报朝廷,在中央统治边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有利于中央统御东北少数民族。
此后营州地位更加重要,逐渐成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挥着中央控制东北地区的重要作用。据宋人《五经总要》记载:“因受东百八十里,九递至燕郡城,自东行、经汝罗守捉,渡辽河十七驿至安东都护府约五百里”营州道上所设九递十七站,承担着中央向东北地区传递信息的任务,同时也作为中央王朝管控地方、收集信息、发布指令的利器。大大缩减了营州至东北地区的距离,确保传达指令的时效性,同时地有驻兵,震慑东北少数民族以防叛乱,在维系中原王朝与边疆部族的君臣关系、稳固中央统治、促进东北民族融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营州道对于东北地区的历史作用
营州作為边防重镇,位于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接壤处,地有驻军,并设有较完善的地方管理机构,例如营州都督府、平卢节度使府等,是唐朝控制高句丽、突厥、契丹、新罗、室韦、奚、等少数民族的关键,是中原王朝通向东北交通最重要的一环。历史上中原王朝王朝曾多次通过营州平定边疆叛乱,比如唐平定高丽时,便从营州经燕郡城经安东都护府,直接抵达战场。同时它也是中央王朝掌控地方情况的监测器,公元718年,突厥袭击奚,平卢节度使管辖下的押藩使薛泰迅速将情况上报朝廷,朝廷即刻向契丹可突于下达命令,告知其联系与营州都督共同筹划,做好防御。有力的抵御了突厥的侵袭,维护了边疆的稳定。交通缩短两地间的距离,营州道在传达政令与地方动态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营州道的出现,成为了连接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纽带,推动中原王朝与东北少数民族政权友好互通,增进双方了解,客观上对两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营州道作为一条中原王朝到东北边疆的要道,稳固了中原王朝的统治,它将边疆与中央相连,及时掌握地方动态,设立治所加强边防,对边疆部族起到威慑作用,行使中央对地方的管辖权。渤海等东北政权通过营州道入中原进行朝贡,维系两地间和平友好的交往关系,为双方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在政治和平的局势下,双方的友好往来在营州道的通行下也促进经济得到长足发展。除官方贸易外,沿途的市场交易动也推动了两地间的经济攀升,使东北地区经济得到提高。经济的富足在客观程度上促进文化繁荣,文化需求显著提高。如在唐时期,渤海通过营州道派遣使者入唐学习典章制度、文化礼仪、儒家思想。中原文化的冲击催动了渤海文化与唐文化的交融,促进东北少数民族文明开化,通过这条文明之路,唐文化源源不断渗入渤海,推动了渤海国在政权建设、制度科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传播佛教与儒家文化,使渤海国的文明更加先进。东北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融合加深。
4.营州道对后世的影响与意义
营州道是东北古代交通的基石。在古代,营州道一直作为沟通中原王朝与边疆各民族的主要交通道路,尤其对唐王朝与渤海的交流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于契丹势力崛起,营州道多次受阻,此后渤海与唐王朝的交通则不再取道营州道,而是改为鸭绿朝贡道,营州道在此时期走向衰落。渤海国灭亡后,营州道继续被后世所沿用,比如明代“纳丹府东陆路”、清代“进京大路”,都是在营州道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此窥见营州道对后世道路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作为一条交通要道,营州道对于中原王朝起到了维护统治、巩固边防、安抚少数部族的作用,是治理边疆的一剂强心剂。而其对于东北政权来说,则是一条发展之路,它推动了东北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间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和平的成长环境,同时也将中原的先进文明、优秀文化引入到东北地区,推动了东北文化建设,在东北的历史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
这条从营州至东北的道路,加强了中原王朝与东北地区的联系,无论是在双方的政治或商业往来,还是中原王朝对于东北民族的治理,营州道在交通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清]顾祖禹.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 [唐]杜佑撰.王文锦点校.《通典》卷一七八《州郡八·柳城郡》,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8 年,第 4716 页。
[3] 王绵厚、朴文英.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01.
[4]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三十九:志第一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宋]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99.
基金项目:吉林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渤海国古城遗址分布特征研究(202010205038)”成果、吉林省社科规划项目(吉林省高句丽研究中心)“唐渤海文化遗址时空演变与人地关系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宁,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8级历史专业学生;殷铭徽,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北历史地理。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长春 13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