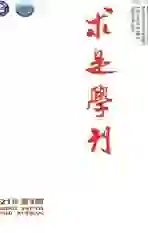民初湖湘士民的苦难书写
2021-06-17孙之梅李香月
孙之梅 李香月
摘要:民国初建,湖湘士民遭遇了新制度的镇压与军阀混戰的摧残,《红薇感旧记题咏集》与“醴陵兵燹题征”就是1913年和1918年两次大动荡的诗歌书写。这两次诗歌创作活动的参与者大多数是南社成员,主持者是南社湘籍社员傅熊湘。前者表现袁世凯窃取总统大权后对辛亥革命志士的镇压;后者表现护法战争中南北军阀混战,轮番屠戮湖南民众的恶行以及张敬尧主政湖南实行的暴政。诗人们在《题咏集》中尚且能逞才斗艺,展现自己的名士风流与龚诗风调,“题征”则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控制诗歌体式,有效地发挥诗歌的叙事功能。这两次诗歌活动是民国后南社应和时代风云最有效的创作,凝聚了南社湘籍社员,刺激了濒临解体的南社社团的活力。“题征”发生于新文化运动前夕,延续着“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诗歌传统,肩负起以诗纪史、补史的使命,相较于此后中国社会乱象丛生中新诗缺乏有力反映的现象,用自己的创作实绩说明古典诗歌并非“死文学”。
关键词:《红薇感旧记题咏集》;醴陵兵燹题征;傅熊湘;南社
作者简介:孙之梅,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 250100);李香月,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济南 25010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南社文献集成与研究”(16ZDA183)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3.015
诗歌创作与事件关系密切。民国前南社往往制造事件带动诗歌创作,民国后则常是已发生的事件促成诗歌创作。《红薇感旧记题咏集》与“醴陵兵燹题征”是典型的已发生事件引发的群体性诗歌创作活动。它们都由南社湘籍社员傅熊湘发起并推动,得到南社诗人们广泛参与,其活动持续的时间长,造成的影响大,无疑是民国初年诗歌史上的两件大事,更是南社史上的大事,但是无论文学史还是南社史对此都付之阙如。本文的撰写目的就在于发覆南社历史,发覆文学史。
一、《红薇感旧记题咏集》与“醴陵兵燹题征”的本事
辛亥革命爆发,湖南是最早响应并宣布独立的省份,民国建立后,湖南籍的革命党人被荼戮也最为惨烈。《长沙日报》因主张民主共和,反对独裁,遭到新政权的迫害,报纸被封1,主编傅熊湘,编辑、撰稿人文斐、罗介夫等人遭到通缉。傅熊湘与龚尔位、黄钧逃回醴陵,但县中缇骑如织,在危急时刻,他们得到妓女黄玉娇的帮助与庇护。黄玉娇(少君),醴陵人,是傅熊湘友人刘骧的故交,性豪侠,此时她刚脱籍,待嫁于玲珑馆。其间黄玉娇对傅熊湘格外敬重,产生了爱慕之情。1914年春,傅熊湘听闻黄玉娇嫁人的消息,不无怅惘之情,作《红薇感旧记》一文寄示柳亚子,并请其与俞剑华、高旭题和。柳亚子遂作《玉娇曲为钝安赋》,刊发在《南社丛刻》第十一集,并向社友广征题咏,《红薇感旧记》题征由此拉开帷幕。所谓“红薇”即傅熊湘避难期间的化名,“感旧”是因为文章写于事后,感怀、感恩玉娇在危急时刻出手相援的护佑恩情,感慨玉娇的侠情义胆。
黄玉娇出嫁不久就被夫家主妇逼迫离开,傅熊湘得信后多方寻找,8月,傅熊湘、龚尔位、刘骧等人与黄玉娇重聚玲珑馆。此后三年他们每年都有一次相聚。1917年,黄玉娇再次嫁人,临行前寄信与傅熊湘诀别。他们每次相聚与离别,傅熊湘都有诗词纪之,有的刊于《南社丛刻》,也成为南社社友唱和的原作。
1917年春,傅熊湘把社友们的题和之作编为一集,湖南督军吴光新遣盗纵火,《长沙日报》馆被烧,此集化为灰烬。傅熊湘复“冥思力索,复追写为一册”2,寄给柳亚子,柳又辑补社刊、报纸所存之题和作品,题为《红薇感旧记题咏集》,并于1919年出资刻印。该集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题咏集前,有柳亚子序、傅熊湘序、《红薇感旧记》《玲珑馆词十首》《后玲珑馆词八首》和《集定庵句自题感旧记后并答痴萍》(此诗附《浣溪沙》词九首);二是题咏集,有总目、文三篇(包括王竞《题红薇感旧记寄屯艮海上》诗后附书信一通)、诗190首、词10首、曲4支、画2幅3;三是《钝安记》。从傅熊湘避难玲珑馆到《红薇感旧记题咏集》刊印,历时7年,其间中国正经历着政体转型带来的政治动荡,傅熊湘与南社诗人们围绕着此故事不断更新着乱离悲歌。
“醴陵兵燹”,是护法战争带给醴陵的兵灾。湖南作为西南五省门户,在1917年7月到1918年6月的护法战争中成为主战场,而醴陵是战争通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毁坏。北军第一次攻湘,皖系倪嗣冲配合傅良佐攻打衡山,由醴陵往返攸县,醴陵成为兵匪蹂躏之地。1918年春,北军二次攻湘,南军在岳州之役中败退,北军趁势追击,醴陵再度遭受屠戮。醴陵知事曹濂溪(安武军所委派)施行暴政,张怀芝、李传业、张宗昌等部络绎席卷而来,“大掠县城,继以焚毁……正街一带,烧毁略尽,死者数千,剖腹刳心,焦头烂额,至不忍睹。而渌江大桥,亦同时焚断,猝不得渡,多溺于河,或凫渡登洲,兵且跻至,索银搂女,哭声震天。即被奸掠,终不免死”4。傅熊湘《来台集序》云:“丁戊(1917—1918)之交,南北构衅,北兵既重挫于攸县,忿无所发,乃尽烧醴陵城乡民屋万数千家以走,杀人至二万,劫掠所失不可胜计。而始倡纵火者则为县令。”5兵燹后的醴陵县城惨不忍睹,屋毁栋折,白骨遍野。更可怕的是战争引发了次生灾害:政府机构瘫痪,溃卒土匪勾结,恃强凌弱,民命如蚁;洪灾、瘟疫频发,民众无处求告。1918年3月,张敬尧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他上台后不仅没有整顿秩序,却是虎去狼来,5月,率第七师攻陷株洲、醴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醴陵全城万家,烧毁略尽,延及四乡,经旬始息;株洲一镇,商户数千家,同遭浩劫;攸县黄土岭一役,被奸而死者,至女尸满山;杀人之多,动至数万”6。张敬尧带领他的三个胞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依仗武力无所不为,湘人恨之入骨,其谣曰:“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1在湘未满一年的时间,积累财富数千万。第七师官兵羡慕长官发财,争相到民间掠夺,为了使之合法化,成立清乡队,纵之县乡,蹂躏百姓。此外他包办选举,扰乱金融,哄抬物价,蹂躏学校……三湘大地犹如鬼魅地狱一般。2
1918年夏,傅熊湘与南社社友刘泽湘、卜世藩等人着手善后。3歲末,得知南北和会将在上海召开,傅熊湘与文启灥、袁家普赴沪,请愿和会,为醴陵告灾。傅熊湘编《醴陵兵燹纪略》《醴陵兵燹图》《湘灾纪略》印送南北当局及各界人士。《醴陵兵燹图》是文启灥等人在灾区拍摄的三十幅照片;《醴陵兵燹纪略》记录南、北军队对醴陵的蹂躏,以及战后百姓无以为生的状况;《湘灾纪略》则实录两年之中湖南遭遇的战事、军暴、匪祸、天灾等。傅熊湘将这些图文呈递和会,呼吁求恤、求偿、求蠲、求惩,同时呼吁南社社友,借助报刊进行舆论干预,他表示“猥以吾舌当勇拳”,“得假高咏相连绵”4。社友们被湖湘大地发生的悲惨事件所震动,纷纷发表“题《醴陵兵燹图》”“题湘灾”的诗文,为驱逐张敬尧和善后事宜推波助澜,据不完全统计,南社社友参与这一创作活动的作者有30余人,发表诗词120余首。
《来台集》是唱和活动中的衍生品。1919年春,傅熊湘、汪文溥、文启灥等人在爱俪园集会,告哀求援,邀请王廷桢参加。5傅熊湘发表演说,听者强半落泪。汪文溥作《春日爱俪园王子铭酒座,傅屯艮痛陈湘醴兵灾,听者强半隳泪,不独昔日文通黯然神伤也。酒罢写此,示屯及文湘芷并同座诸子》诗,用来台韵,傅熊湘和诗四首,赠诗四章。此后,南社社友用此韵反复唱和、联句。同年,汪文溥将来台韵诗辑录成集,命名《来台集》。共有作者25人,诗词204首,序3篇。
傅熊湘从1918年12月赴沪到1920年6月回湘,不到两年时间里,“醴陵兵燹题征”构成南北战争期间的诗史。
二、名士风流与诗史叙述
袁世凯窃夺民国总统大权以后,迅疾推行专制政治。胡朴安《南社诗话》说:“二次革命失败,民党报馆关门已尽。我等二三等革命文人,亡命是必不可免的。”6这种情况在湖南更甚。汤芗铭受命督湘以后,以“抄”“押”“杀”作为政治方略7,大兴党狱,屠戮士林,谭人凤、程潜、杨德邻等辛亥元勋均列缉捕之册。文斐这样描绘当时湖南的状况:“东南日月黯无光,金陵不守赣城亡。虎狼千万来三湘,驱逐人类如驱羊。”刘泽湘把严酷的舆论控制拟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皇吞并七雄毕,有诏焚书坑儒术。偶语腹诽都弃市,刊章逮捕争告密。”民国的功臣们逃亡四野,《红薇感旧记题征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一段跌宕起伏的浪漫插曲。这段插曲首先感动了男主人公傅熊湘,他念念不能忘怀,借助多种文体功能表达自己言说不尽的情感。《红薇感旧记》描写黄玉娇的倾心相爱:
倾城艳质,施弱腕以扶将;绝世佳人,矢素心而薰沐。……君也环珮其间,婀娜入抱,色授令千日醉,眉语作九连环。有酒如渑,既浅斟而低唱;爱才若命,亦痛惜而温存。虽宋玉未许东墻,而香君已连复社。
傅熊湘作为受助者、两性情感中的男主角,不能忘怀当属自然,难得的是他意识到这一故事所具备的共鸣功能,他要把这个故事放在公共空间,作为一个公共事件引起舆论与文学的关注。正如所愿,这个故事又感动了柳亚子。柳亚子即刻作了《玉娇曲为钝安赋》长篇歌行,渲染其情事;1917年傅熊湘把黄玉娇的玉照寄给柳亚子,柳亚子复作《钝安贻我玲珑馆主玉影为题四绝》,后又赖其出资,使其文献有赖以存。
这个故事一旦走向公众,妓院别馆中的黄玉娇与躲避锋镝的傅熊湘所复制的香艳大戏,迅疾感动了南社一众诗人,傅熊湘《红薇感旧记题咏集》有70人发表了诗词曲文,作者们调动储存的名士美人典故,营造浮想联翩的情景。他们称赞女主角:“红颜别擅凌云气,素手能弹变徵声。”(柳亚子)“天生慧侠艳如仙,激浊扬清意慨然。”(高旭)妓女史上的红拂与李香君成了最热门的比附,红拂的典故出现了17次,李香君出现了12次。“独怜红拂天涯老,惆怅他年李卫公”(柳亚子);“望门投止怜张俭,红拂宵奔李卫公”(吴恭亨);“他年雪苑成名日,愿筑高楼号媚香”(刘师陶);“秣陵都说媚香楼,公子侯生为淹留”(方荣皋);“望门投止荆江老,一朝走遍乡关道”(孙璞)……红拂女的慧眼与李香君的见识义气汇集到黄玉娇的身上;李靖的英雄气概、侯方域的名士风流、张俭望门投止的岌岌可危比附到傅熊湘身上;此外也挦扯了朱家、郭解和藏壁赵岐的故事。其实这些典故用得最恰切的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的典故。南社成立伊始,其模仿的社团原型就是明末几社、复社,南社的文化精神与文学思想可概括为“几复风流”。1
傅熊湘逃亡中的艳遇也引发了社友们相似经历的展现:汪文溥被瑞澄通缉时,资水女子清河君“舣舟岳麓之麓,愿脱走,有陂有塘,有田有园,请与君偕隐”;蔡守于1905年、1914年两次因文字触怒时忌,柳君、刘春出手援助,“柳意能教秋气春”,“解使梁鸿姓运期”,终使蔡守化险为夷;孙璞在逃亡时,“未邀红拂垂青眼,空被萧娘笑赤贫”,得遇女性庇护。这些美人救英雄的故事与傅熊湘的故事互相生发,似乎在诉说着乱世中的一点温情,正如叶楚伧所言:“世无游侠宁从妓,生负艰难解说诗。”从妓与赋诗或可寄托希望破灭后的痛楚。“鼓声已死风雷哑,日薄无光革命旗”(吴恭亨),共和体制建立并没有让它的开创者获得荣华,反而被迫逃窜四野,处于荆天棘地、日暮途穷、党锢横行的困境和“鸱鸮取子倾巢日,吾辈惊心破胆时”(龚尔位)的恐怖中。“红薇”的命运不仅是傅熊湘的自我写照,也是国家体制转型中抛弃旧制度投身新社会热血青年的缩影,因此“红薇”的感旧引发出经历了民国后被戕害的南社社友的共鸣。
《红薇感旧记题咏集》犹如一个平台,南社文人风流名士式的旧时代印迹得到了一次集中表现。南社文人跨越清末与民国,他们既是旧制度的掘墓人、新制度的开拓者,也是旧文化的承递者、新文化的随行人。不少人参加过科举,中过秀才、举人,身上不可避免地保留着旧式文人的作风,名士风流是很多人对自己的期许。民国成立后,南社人曾有过短暂的喜悦,但很快被失望、绝望、颓废等负面情绪所左右,排泄的渠道之一便是传统的追捧优伶,如柳亚子之于冯春航、陆子美,雷铁崖之于郭凤仙、小子和等。王德钟解释:“美人香草,岂真文士之寓言;醇酒妇人,大抵英雄之末路。……志士穷途,几点血泪,无处可挥,不得已而寓之舞衫歌扇间耳。”2这种排解方式与明末复社、几社的名士们如出一辙,与南社从成立伊始就预设的“几复风流”一脉相承。《红薇感旧记题咏集》中不少诗把傅熊湘比作杜牧,“为爱美人心爱国,风流漫拟杜扬州”(田兴奎),“况复伤怀如杜牧,悲吟直过四愁诗”(简易),就是源于过于关注风流放浪的一面而导致的比拟不伦,忽略了斧钺高悬的危急,也贬低了黄玉娇的义侠。
“醴陵兵燹题征”记录了“在场”的细节与“不在场”的震惊,堪称“诗史”。南北两军之战争和张敬尧的暴政,使醴陵之灾烈于全湘,南社湘籍社友是兵燹的亲历者,他们的诗诉说着民众的苦难。刘泽湘《哀荆南》(亦作《题〈醴陵兵燹图〉》)写北军:“避敌仇民来健儿,滔天兵祸仓黄起。健儿攘臂初下车,星月无光夜不哗。狠似天狼狂似虎,朅来舞爪还张牙。张牙舞爪将人攫,初劫市尘后村落。缣帛千箱掠入营,金钱万贯抄充橐。搜牢频数十室空,比户萧条付祝融。烈焰障天三百里,茅檐华屋光争红。王谢堂焦燕巢覆,衔泥从此依林木。……吞声哭久天不闻,震地枪声响入云。刀光旋逐火光耀,死别生离骨肉分。”1所谓的政府军犹如盗匪,在醴陵劫掠烧杀,无恶不作。吴恭亨《醴陵灾一百韵》写南北军对醴陵的洗劫:“醴既非战地,乃尔殃鱼池。……南军来饮马,北军来择肥。北军乍弃甲,南军旋卓旗。荡荡百里内,水涸山为陂。……西行涉沅澧,南行瞻衡岳,东行缅郴桂,北行岳鄂陲。不见异风俗,但见游魅魑。刀下幸逃死,存者骨与皮。”2诗人以醴陵为中心,环视四方,战争蹂躏湖湘大地,暴虐横肆。李澄宇《题〈醴陵兵燹图〉》描写:“醴陵城中火烛天,醴陵城外无人烟。渌江桥上鬼啾啾,渌江桥下泪痕流。岁维戊午春三月,天地反覆杀机发。杀人盈野复盈城,盗贼水火而刀兵。”3卜式藩《戊午五月十六日,小住县节孝祠,和约真四首》写自己的经历:“一炬还烧到楚人,如今三户不亡秦。空山恶木蛇横路,废苑荒村鬼结邻。”“垂老遁荒依草莱,家贫谁散鹿台财。绿林夜雨还行劫,瓘斝融风不救灾。”自注:“三月二十七日夜山居被劫,约耗三千金。迟数日,县城别墅兵燹。”4刘谦写自己携家人避乱的经历,其《戊午集》读之令人心酸。其《杂诗十首》写他们逃难到萍乡的遭遇。第一首写避乱到太平山,注云:“太平山事起,醴人避乱附近者复相率奔避。”第二首注云:“太平山之役,村舍被焚者八十余家。”第三首注云:“醴人避萍,不下十万,额际咸作黝色。”第四首注云:“萍民方闹荒,醴人购米不得,多流为丐。”5战争过后,民众的苦难并没有结束,刘谦的《除夕杂忆诗》写湘民的悲惨情景:
渌江江上碧磷飞,已觉人烟百里稀。岁暮可怜闺梦冷,尚携稚子望夫归。
不堪策蹇过前村,凭吊苍凉野烧痕。一幅流民谁画得,有人牵屋住山根。
朔风萧瑟妇无裈, 骑犹闻夜打门。却把牛衣作姜被,深宵七子悄同温。
大兵未已更凶年,楮钞纷飞欲化烟。莫讶哀鸿遍中泽,即今斗米十千钱。
“渌江”诗自注:“自三月以来,醴陵死兵者不可胜记,有春季被掠应役,至今不可卜存亡者。”丈夫成了战争的炮灰,生死未卜,“望夫归”的少妇和稚子如何生存?“不堪”诗自注:“城乡庐舍毀后,往往编茅为垣,倚山作屋,甚或曳舟岸上以居。”以前和平安静的村庄被毁坏后,百姓们无以为居,作者勾画出一幅流民野居图。“朔风”诗自注:“附郭民家常寒夜被兵攫衣被而去,有一家八口不得一絮者。”战后是秋冬,一家八口忍受饥寒交迫。“大兵”诗自注:“春兵秋螟,田收大歉,纸币低落,直同冥镪。民不聊生,于此为极。”6兵燹后,秋季遇到了螟虫之灾,张敬尧政府不但没有恤灾,反而扰乱金融秩序,发行名目繁多的流通货币,导致物价飞涨。战后百姓的生存状态在作者笔下历历在目。
战争是政治的极端表现,最后双方坐到了南北和议的谈判桌上,却互相扯皮,开开停停,“有人不签字,疾避饮鸩杯”(熊自镜);“已怨开迟开又歇,重开终恐易飘零。……仙字枉劳镌玉牒,神幡谁与系金铃”(傅熊湘)。正如孙中山在辞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之职时所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和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名,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7政客弄权,武人争雄,他们的利益之争要“湖湘万家血”8来承担代价。
傅熊湘与湘籍南社社员赴沪告哀,震惊了舆论界,激发了湘外诗人们的桴鼓相应。上海的梅问羹云:“皇纲解纽海宇沸,枭雄盗柄崇骄诬。似土黄金使贪诈,如山白刃歼穷孤。钧天梦醒长已矣,余毒一肆天下痡。最苦衡湘绾南北,连年兵燹嗟剥肤。醴陵当冲祸尤酷,鬼魂夜夜啼津途。贼来梳汝兵篦汝,偶有健者皆流逋。”1柳亚子、高旭、胡朴安、孙小舫等人发表诗歌,谴责南北军阀的无法无天,同情醴陵民众的不幸遭遇。湘灾也让诗人们思考一个问题:国家向何处去?“大同不必期,非种或可锄。是亦吾族耳,自残胡为乎?”2“非种诛必去,同舟敌奚来。”3推翻了专制体制,本以为目标实现会带来家国安康,但是民国建立,五族共和,自相残杀却如此残暴,一代人所追求的社会文明显然还没有现出曙光。
三、定庵风调与诗体控制
龚自珍在近现代的经典化过程是一大学术课题,其间南社这个环节不可忽视。龚自珍被追捧首先是思想,然后才是文学;文学又先是文,其次才是诗。咸同时期,龚自珍以其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抨击专制政治呼吁变革的凌厉姿态让读者“若受电然”4,而龚诗并非普遍被看好,谭献说其“不就律,终非当家”5;李慈铭说其“不能成家”6。光绪中后期,政治变革已成大势,龚自珍诗歌的经典化进入新时代。徐世昌说:“光绪甲午以后,其诗(龚诗)盛行,家置一编,竞事摹拟。”7张荫麟回顾:“甲午、庚子前后,凡号称新党,案头莫不有《龚定庵诗集》,作者亦竞效其体。”8“竞事摹拟”“竞效其体”的人除了诗界革命派之外,南社无疑是最大的诗人群体。1906年,19岁的柳亚子就有《集定公句十二截》诗,后两年《定庵有三别好诗余仿其意作论诗三截句》,第三首盛赞龚自珍“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9。高旭、傅熊湘、黄人、俞剑华等同样对龚自珍心追手摹。“诗可以群”,南社成立后,龚自珍成为社团诗歌写作的偶像。傅熊湘说到这一现象:“定庵诗为一时所宗尚。朋辈中言诗者,大抵皆祖述定庵者也。”10胡朴安亦云:“当时社友,多喜读龚定庵诗,以其才气纵横也。”11南社诗歌集龚、和龚、效龚的作品比比皆是,已然成为一种现象。12
《红薇感旧记题咏集》可以说是龚诗风调的一次集中表现。首先是文体,200余首诗多数是七言绝句。绝句是一种极具风情意韵的文体,更重要的是龚自珍为近代的七绝圣手,他的存世作品除了《己亥杂诗》这一组七绝外,其他诗也以七绝为多。《红薇感旧记题咏集》中七绝有161首之多。其次是有意识的拟龚,拟龚中又有集句、化用两种。《题咏集》集龚诗28首,通过对龚诗的重新排列组合而赋予其新的诗意。傅熊湘先有《集定庵句自题感旧记后并答痴萍》(此诗后附癸丑、甲寅《浣溪沙》18首),如同集龚的一个开场白,接着诗人们竞相逞才斗技,蒋同超《题钝安红薇感旧记集定庵句》达14首之多,刘筠《红薇感旧记题词集定公句》也有4首。集句诗最能表现作者对所集对象的熟悉,而熟悉的背后是推崇和喜爱。郭长海《龚自珍对南社的影响》一文以《南社诗集》为据,统计1907年到1922年间343位南社诗人集龚诗374首,其中并不包括《红薇感旧记题咏集》中的集龚诗。化用龚自珍诗的意象、句子、词语更多,如傅熊湘的“宥情尊命都无著,便反祈招志亦荒”,白炎“指挥侍婢带韬略,呓语我闻龚定庵。设想眉痕故英绝,眼波得伺亦奇男”等。“剑气”“箫心”“琴心”“侠骨”“美人”“荡气回肠”等龚诗语触目即是,挦扯龚诗之绮靡悱恻语,构成缠绵婉转的风情,南社年轻的诗人们在现实压迫下“无端歌哭”的情感状态通过《红薇感旧记题咏集》得到了一次展现。
醴陵兵燹这一段历史,史家关注的是南北政府的势力消长、战争胜负,以及张敬尧的去留、军阀们的军事行动与政治心理,醴陵民众的苦难在几句判断中被遮掩。而阅读“醴陵兵燹题征”的诗歌,我们才能感受到人民大众在这场兵燹中所遭遇的逃难、毁家、被掠掳,以及与之相伴的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在“告哀”的请愿活动中,南社湘籍社友们自觉承担起为民请命的使命,编辑史料,公布事实,奔走呼号,告哀南北政府,呼吁社会舆论的关注与同情。但这是历史作为,而题征则是文学行为,诗人们通过创作,让后人走进历史叙述不能烛照的罅隙,体会受难大众在政客、军阀们屠刀下如蝼蚁一般的人生,凸显诗歌的史性。诗歌的史性离不开叙事性,而南社诗人的长项是政治抒情诗,此次诗歌活动由于主题需要,诗人们对诗体进行了选择和控制,从而实现叙事性的强化。
首先是选择即事名篇、缘事而发的乐府诗体。罗世彝作《今乐府》14首,其中《哀醴陵》写醴陵兵燹:
哀醴陵,哀醴陵,一夕兵燹惊,满城哭声,满野枪声。扶姥襁稚争死生,火龙穿屋,摧栋崩桷。无何陷为火海,黑烟四突,如浪相逐。郊野膏血,断脰折骨,死伤枕藉生人绝。将入城,城中大火犹恣横;欲适野,野外飞弹若雨下。行渡江,渌江桥焚,水淙淙,桥头死人如麻,弱者亦不得降。天明望城市,但見焦壁赤立,烬柱赭扛。1
诗中以“一夕”“无何”“将”“欲”“天明”为关节,醴陵城一夜之间城毁人亡情景如在目前。《客军来》写南北军队作战湖湘,“客军来,客军去,人辍耕,鬼守墓。客军来,客军去,妇欢室,乌啄骸”2,南北两军来来去去,都是湘民的灾难。吴恭亨作《新乐府》一卷,诗27首。1920年初刊时吴恭亨后记里云:“右二十七篇,十八九为张敬尧罪恶史。”《铜圆来》写张敬尧滥发新币、掠夺民财的罪行:
楮币去,铜圆来,十钱直圆一枚;今铜一圆直二十钱,重量略等而价相悬。况辅币,凌主币,又格里森原则所忌。官贪馀利,百姓承敝,恶货币驱逐良货币。绝迹彼囊,而括我汗与血。楮币楮币,去日之日,挤人深渊;铜圆铜圆,来日之日,难斗高天。供过于求,铜圆亦楮币,梃刃杀人何异焉。金融整理,下关民生,上关国计。第一金银定本位,第二辅币发行严限制。
作者引用格里森货币原则,言市场上多种货币并行时良币必为恶币驱逐。《卖湖南》写张敬尧把湖南矿产全部卖给外国资本,谋取暴利。《战溃卒》写溃卒如溃川,“蔽野汹如蝗蔽天,浃沅上下村无烟”,所到之处,“逢村掠村,逢屋火屋”。张敬尧的暴政终于引发了湖南学潮,作者《长沙学生》写学生罢课,呼吁奔走,发动驱张运动。《清乡军》写永保、龙桑二县被清乡队搜刮的情形。3无名氏《清乡杂咏十六首》专写清乡队的恶行,清乡队如刀俎,百姓如鱼肉,“我产既尽搜,我屋亦多毁。移弹堕民身,敢谓非其罪”,“清乡实倾箱,箱空等探囊。……腰缠多累累,遍索花姑娘”。政府军的腐败令人瞠目:“犒酒行军令,招娼列席歌。日西犹未起,沈醉烟花窝。烟有阿芙蓉,花胜芙蓉色。遑计被兵人,骨立脂膏竭。”4刘泽湘《哀荆南》叙述了两个故事:一是自己避难到深山,遇到了北军,紧追五里许,开枪两响,均掠耳过;一是避难翁姓老者,携子避兵,藏于薯窖,被兵士发现后枪杀其子,老人负尸返,“自言家在山之南,有媳十五女十三。昨被逼奸都毙命,只今藁葬又中男。长男被掳驮军器,少男年小不更事”。1南北之战和张敬尧的暴政给百姓造成的苦难,通俗自由、善于叙事的乐府诗确实是最佳的表现载体。诗人们在写作时不无以备采风的目的,《清乡杂咏十六首》诗前编者按云:“所言颇为翔实,诗亦有古谣谚风,足备轩之采。”2作者们在乐府诗的写作中突出其供采风的功能。
其次是七言长篇诗。七言长篇诗从乐府演变而来,基本特征就是叙事性强。吴恭亨《醴陵灾一百韵》表现出作者自觉的诗史意识,如诗中用准确的时间节点叙述历史事件:“六年月日某,初起零陵师。反对易名帅,合肥实嫌疑。会蚌与复辟,罪首兼功魁。”“明年岳州溃,遂又空壁回。旋进复旋退,两俱道路疲。”“四月二十七,铸错高须弥。”“四月火县市,南军犹未来。”“五月县市火,南军退先时。”“吾闻四月火,渌江桥魏巍。”战争的起因,醴陵城、渌江桥之毁,以及南北双方相持相战,在时间叙述中得到明确无误的表现。又如诗中指名道姓,毫不逶迤。“合肥实嫌疑”,合肥指段祺瑞。段祺瑞借张勋复辟,获鹬蚌相争之渔利,又是南北战争之祸首。后面写醴陵县令:“军中版县令,县令饕餮儿。堂上鹰侧目,堂下狐假威。”“煌煌知事曹,映字燈在帷。”写带兵的将领:“抱头李传业,束手张怀芝。”3作者斩钉截铁,不避讳,无假借,让那些应该承担责任的人无可回避。
再次,以韵集诗,构成主题式的叙事抒情,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汪文溥编的《来台集》。由于此集以次韵为主,如果说乐府诗、长篇诗的优势在于叙事,而《来台集》则长于反思与抒情。哀痛、哀哭几乎是该集的主旋律。傅熊湘的《奉酬汪幼安县长于酒坐听余演述湘醴兵灾之作叠次原韵》颇有代表性:“已分身如叶,频经浩劫来。……嘉定三屠痛,扬州十日哀。”“望治群生亟,昭苏奚后来。犹闻侈军阀,枉自筑謻台。野有千家哭,人怀九土哀。”文启灥诗云:“家山纷赤帜,瓜蔓泣黄台。”“厌乱天无语,还乡梦亦哀。”“哀”是此集的中心词,“鼓角哀”“泽鸿哀”“沸鼎哀”“庾信哀”“风雨哀”“沧桑哀”等触目皆是4,即便写游览、风物之作,也笼罩在感伤之中。胡朴安认为:“秋弥海宇,一室难春;哀入文心,千篇悉怨。兹篇方之,固足以发当世之哀,而堕后人之泪也。”(《来台集序》)傅熊湘《来台集序》概括此集:“闵乱既亟,言哀已叹,所以寄微旨,戒将来,备采风,资信笔也。”《来台集》除了表达“哀入文心”的时代情绪外,同样有比较自觉的以诗备史的意识。傅熊湘等人在上海的“告哀”活动在诗中多有反映:“接席包胥哭,披图郑侠哀。”(汪文溥)“千古伤心文士笔,湿襟细把汴围编。”5“要留此卷衡功罪,三百年间两献忠。”(王大觉)申包胥哭秦廷、郑侠编《流民图》、白愚编《汴围湿襟录》,古代士大夫为民请命的故事与傅熊湘等人的行为相呼应,为其在历史的序列里确立意义。除了上面所论外,“醴陵兵燹题征”有时采用夹注、尾注的形式,扩大诗歌的叙事空间。1918年刘谦携家中妇孺逃往萍乡,他把此年逃难的诗作编为《戊午集》,很多诗借助注叙述情事,诗史兼具。
乐府和长篇诗,虽以叙事为主,但诗人们的董狐义断会非常明确地表现出来。吴恭亨《新乐府》写张敬尧祸湘的桩桩件件,其盗寇本质令人发指。诗人们直为其定性,柳亚子云:“平西卖国诚堪杀,营窟臣佗亦盗名。”6在诗中议论仍然不足,吴恭亨又于《新乐府》后记剖析事实:“张之祸湘固不止如兹之所云,然即兹已稀见罕闻矣。夫张敬尧,强盗也。强盗而祸平民,其饕暴,天赋也;行其饕暴,又盗之手术也。……惟授强盗以督军省长之职务,其先拥兵,又无尺寸功绩可言;湘人呼謈,亦即数数矣,乃非法政府如痴如聋,一无闻睹,必待执兵者群起以逐去之,于是湖南又受一重痛苦矣。”1张敬尧主湖南军政,使政府和军队的非法行为合法化,官府和“王师”竟然成为公开的强盗,湖南焉能不成为人间地狱。作者指出“饕暴”是张敬尧的天性,其人又无尺寸军功,然而这样无功无德的人如何能主政湖南?主政湖南后恶迹昭昭,湘人并没有作沉默的羔羊,“呼謈数数”,而中央政府装聋做哑,一无闻睹。湘祸的责任究竟是谁?作者把矛头直指段祺瑞北洋政府。《醴陵灾一百韵》客观叙述南北战争,但是作者的南军立场还是鲜明的。北军攸县之败后纵火醴陵县城和渌江桥。其诗云:“醴既非战地,乃尔殃鱼池。四月火县市,南军犹未来,五月县市火,南军退先时。问火何自种,非天乃人为。此火果人种,正义可信哉?吾闻四月火,渌江桥魏巍。”醴陵之火谁之罪?通过时间与事件发生的排列,显然北军是纵火者。再如关于两军的描写:“南军殉战斗,北军殉货财。掠妇使荐枕,捉男使具炊。辍餐灶无釜,栖主龛无牌。死塘空无鳞,乔林濯无枝。哭野鬼无首,摸金棺无尸。”2一个“殉战斗”,一个“殉货财”,掠妇、捉男等恶行显然是北军所为,客观叙述,褒贬自见,正是史家笔法。
四、两次诗征的社史與文学史意义
《红薇感旧记题咏集》与“醴陵兵燹题征”,无论史事还是诗歌创作都是南社史的大事,傅熊湘是南社湘籍的领袖人物,湘籍社员多数是醴陵人,但是南社史的叙述对此付之阙如。柳亚子1936年撰写《我和南社的关系》一文,将其视之为南社“一部廿五史”3,遍查始终,对此没有一笔涉及。是柳亚子当时不知道这两件事的发生?显然不是。刊发于1914年8月的《南社丛刻》第十一集《文录》有傅熊湘的《红薇感旧记》《书红薇感旧记后》,《诗录》有柳亚子《玉娇曲为钝安赋》,此后《红薇感旧记》题征诗多数出现在第十三集,第十四集《诗录》里有方荣皋《题红薇感旧记》,第十六集《诗录》有黄钧《题钝根红薇感旧记》。关于醴陵兵燹,第二十一集《文录》有吴恭亨《慈利李君死战碑记》、汪文溥《〈醴陵兵燹图〉叙》,《诗录》有傅熊湘《南北和议将始,与湘芷赴沪,为澧告灾,发长沙,次湘芷韵》《撰〈醴陵兵燹纪略〉成缀以一绝》、吴恭亨《诸将五首》《病中读曹锟经略四省府令愤书二首》等。这些《南社丛刻》除第二十一集是傅熊湘所编外,其他均是柳亚子所编。此外,以湖南为战场的南北军政府之战是当时中国的大事,全国各地报纸发表驱张时评和社论有17篇,全国各地学校学联、留美留日学生声援驱张运动的团体有18个。4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一文,侧重点在记录南社的18次雅集与《南社丛刻》《社友通信录》的编辑与出版,其中夹杂了一些内讧经过,其区域中心是上海和江浙,而占据南社鼎足之势的广东、湖南所发生的社事所记甚少,他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南社丛刻》里收录有关诗文,不过在撰写南社史时却意识不到这些事情的重要,而只记载以自己为中心的历史,这大概就是撰史者视角上的盲区。
柳亚子的《南社纪略》对后来的南社史叙述影响很大。首先是郑逸梅,其《南社丛谈》除了《南社社友事略》《南社社友著述存目表》等之外,基本上是复述《南社纪略》,自然不会关注到这两次事件。但是郑逸梅提到了傅熊湘逃亡事由,并提到了《感旧记》与《玉娇曲》,但无“醴陵兵燹题征”。郑逸梅对傅熊湘评价颇高,其《南社丛刻和它的蜕变》提到社中的“尤著者”,第一个是吴恭亨,第二个就是傅熊湘,并称他们是“文章之渊薮”5。所以他对南社史叙述的缺失除了受《南社纪略》的影响外,可能是没有阅读《南社丛刻》造成的。当代杨天石、王学庄编著的《南社史长编》可称宏制,对这两次历史事件以及文学活动也没有涉及。他们的问题与郑逸梅相同。此外南社人所写的一些回忆性文章如朱剑芒的《我所知道的南社》、胡寄尘的《南社的始末》、徐蔚南的《南社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等文或由于视野或由于篇幅也不曾提及。湘籍社员们的这两次规模可观的文学活动竟然被尘封到社史背后的烟云里。
历史上的人与事大多数要被遮蔽,而被遮蔽的未必都无足轻重。从南社史言,这两次事件相对于“陆子美”“三子游草”“迷楼”“酒社”等都要重大,是南社史上名副其实的大事件,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也同样比前面事件所衍生的更有价值。在媒介发达的近代,重要的历史信息总会被后人发覆,我们在拨开历史烟尘的过程中发现了南社史这一不应该忽略的事实,其背后隐藏着湘籍社员最终独立门户,成立湘集与新南社分庭抗礼的蛛丝马迹。南社成立之初,有号召力的组织者是陈去病、高旭和宁调元。《南社》创刊,宁调元发表了具有纲领性意义的《南社诗序》,又是通过宁调元发展出湘籍一干社员。因此我们称宁调元为南社创始人之一是无疑义的。民国后革命领袖黄兴、宋教仁的入社,大大提高了南社的社会声誉,骤然间社团得到大幅度发展。接替宁调元的领袖傅熊湘无论是学识还是才华都不亚于前任,他在南社的影响力同样不容忽视。他致力于南社的发展,引荐新社员加入1,并敦促其创作2,在南社解体之际,湘籍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醴陵兵燹告哀事件与题征为南社的凝聚提供了契机,其间傅熊湘与高燮、胡朴安有《京锡游草》的产生,“当时朋辈,互相传观,宾虹善画,且为图以张之。……而亦南社中一故事也”3;傅在沪期间还成立了鸥社4;1919年底,傅熊湘入京告哀5,京中社员雅集中央公园,在京一月,南社社员吴梅、黄节、刘三、陈匪石等相聚唱和。以傅熊湘行踪为线索产生的活动在南社史上掀起一轮波澜。与此同时,《南社丛刻》第二十一集无人主持,傅熊湘负责编辑,其中湘籍社友作品顿增,总数达到377首,占此集总量的43.48%,看出湘籍在民国后有成为主力的苗头。但是南社的发展其实在民国之初就进入多事之秋。首先出现了体制的改革,柳亚子强烈要求实行主任制,受到了高旭等人的阻挡,他宣布退社,南社出现了裂痕。一是诗学异同的力量在聚集分化,倾向同光体的人不断发表言说,如姚雏、诸贞壮、朱玺等。在这种背景下湘籍社员在长沙烈士祠举行了临时雅集,1916年湘籍社员连续举行了两次雅集,后一次雅集选取的时间竟然与上海的雅集是同一天。但是这些并不能表明湘籍有独立门户的打算,在1917年的诗争中,当广东籍社员意欲推翻柳亚子另换南社主持人的关键时刻,傅熊湘率领21人发表启事,称赞柳亚子的道德文章,“断不容一二出而破坏”6,维护南社的统一,给予柳亚子有力的支持。新文化运动冲散了南社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南社冠之以“新”,湘籍社员独立门户为“湘集”,二者在文化观念上分道扬镳。《题咏集》与“题征”所关注的两次事件被《南社纪略》所忽视,其中的名利恩怨等不可道之处亦非不起作用。
南社诗在民国前多为政治抒情诗,较少民生疾苦与个人困厄遭遇的作品,诗歌表现对象的转向正是在民国初年,其中四川富顺的张光厚诗在南社诗史中值得注意。出版于1914年8月的《南社丛刻》第十一集里收录张光厚《蜀恨》《老父叹》《寡妇叹》《哀蜀》,根据《南社丛刻》出版时间,知诗中所写情事发生在癸甲(1913年、1914年)之间,显然是袁世凯政府对革命党人迫害的情景。此后,张光厚陆续写出四川兵匪之乱、武昌兵变之乱等诗。袁世凯策划称帝,张光厚揭露其阴谋,抨击筹安会的无耻:“暗里黄袍已上身,眼前犹欲托公民。纷纷请愿真多事,个个元勋肯让人。”“来许加官去送金,奸雄操纵未深沉。袁公路有当涂谶,石敬瑭真卖国人。篡位岂能逃史笔,虚文偏欲骗民心。寻常一个筹安会,产出新朝怪至尊。”1张光厚在南社算不上很重要的人物,但是民国后他的诗对表现党人逃捕、民众受难却有开启之功。《红薇感旧记题咏集》和“醴陵兵燹题征”大规模书写民国开创者们断头沥血的经历和民众白骨蔽野的悲惨,以及反袁反军阀的呼声,其文学精神与张光厚一致,他们肩负起以诗纪史、补史的使命。相较于此后中国社会乱象丛生中新诗却缺乏有力反映的现象,南社诗人用自己的创作实绩说明古典诗歌并非“死文学”。这些诗歌在近代诗歌史、民国文学史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而不应该被学术界所忽略。
[责任编辑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