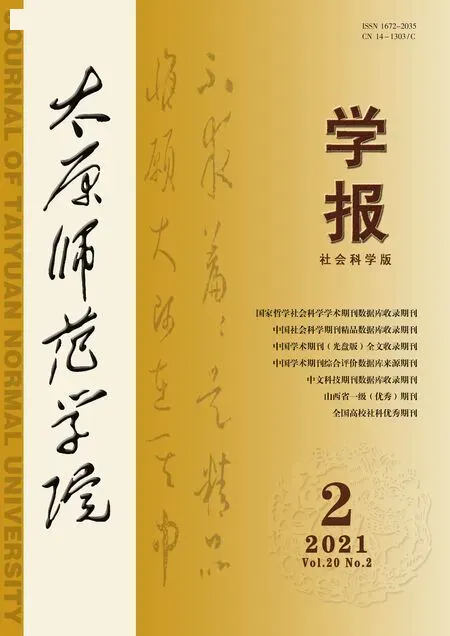圣王登仙:论先秦时期黄帝神仙形象的生成
2021-06-15张雁勇
张雁勇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真灵位业图》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系统的道教神仙谱系[1]272-282,该神谱第三等级左位列有以黄帝为首的儒家五帝,依次为黄帝、颛顼、帝喾、舜、尧,其中黄帝的道教化名号是“玄圃真人轩辕黄帝”[1]275。他之所以能够位列早期道教神谱,并在早期道经中神迹频现,与先秦时期既已萌发的神仙形象密不可分。傅勤家[2]102-103、王明[3]、陈子艾[4]、赵世超[5]、钱国旗[6]等学者从古史传说、神话纬书、道教仙传等方面简要梳理和分析了黄帝文化形象的源流;干春松将黄帝列为“后天仙真”之首,梳理了黄帝的修道故事[7]144-146;张广保对唐以前史籍与道经所载黄帝修道登仙说的繁衍作了较为系统的考辨,指出黄帝入列道教仙传谱系受到了原有传统和佛教的双重影响[8]。学界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深入认识早期道教中黄帝神仙形象的生成颇有助益。本文拟在借鉴前辈时贤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详细梳理和分析先秦时期黄帝从部落联盟首领到上古圣王进而修道登仙的轨迹,以期为探索早期道教神仙体系的构成提供一个典型案例,如有不妥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从部落联盟首领渐成上古圣王
“黄帝”最早是以同蚩尤作战的显赫武功见于载籍的,此后又出现了因其有功于民而受到祭祀的记载。《逸周书·尝麦》:“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9]731-733《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前635)记载王子带之乱时晋文公令卜偃占卜,“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10]431,即是此战在解读兆纹时的运用。关于黄帝战蚩尤的传说,晁福林认为“非经历一个漫长世代不足以定型,很可能它是五帝时代就有的说法,历经夏商两代而至周初才被写入文献”[11],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左传》和《国语》还有三条关于黄帝的较早记载。《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5)载郯子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杜注:“黄帝,姬姓之祖也。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百官师长皆以云为名号,缙云氏盖其一官也。”[10]1386《国语·晋语四》载司空季子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12]356《周语下》载太子晋说华夏诸族“皆黄、炎之后也”[12]107,此为一种追祖认宗的行为。从这些记载来看,黄帝是中国上古传说时代部落联盟的一位杰出首领。或如赵世超所言:“黄帝为传说中的英雄,被奉为人文初祖,历史上如果实有其人的话,他只不过是原始社会后期一位杰出的部落首领罢了。同时,也很可能仅代表一个时代,或由某部族的名号渐渐转化为帝号。”[5]《国语·鲁语上》载展禽言及“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因有功于民,故有虞氏和夏后氏有“禘黄帝”的“国之典祀”[12]166,黄帝始具圣王风范,《礼记·祭法》因袭之[13]1587。《吕氏春秋·十二纪》提到黄帝在季夏受祭:“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14]315《礼记·月令》亦踵其说。[13]1371-1372此说虽“出明堂阴阳、邹衍五运”[15],但也透露出当时人们对黄帝的尊崇。
《史记·封禅书》提到秦人有黄帝郊祀上帝的传说,并述及秦国自春秋秦襄公以来祭祀白帝、青帝、黄帝、炎帝,其中“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16]1626-1633。陈槃认为从来源上看黄帝是“乌有先生”,并指出:“我们现在看来,黄帝就是‘上帝’!因为先有黄帝的传说,所以他们又创造了些‘白帝’、‘青帝’等等,凑凑热闹”[17]。陈槃此言虽颇有疑古意味,但黄帝由人帝而受到“上帝”待遇的奉祀则是事实,已渐有尊神的色彩,成为凝聚秦人的重要神灵。徐旭生认为秦灵公时并祀黄炎二帝“大约是旧废祠的复兴”,“因为是多数被统治的人民的信仰对象不得不加以崇奉”。[18]241-242范瑞纹进一步推测“先祀白帝而后青帝,而后黄、炎二帝,这和秦王朝的发展的实力与自信有关”,认为“已有天子祭天祀地之味”。[19]137徐、范皆谓并祀黄炎缘于秦国势力的扩增,所言合理。

二、圣王的神话化

黄帝的求仙努力是颇见成效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34]270这反映出黄帝已是当时长寿者的典范。岂止寿考,已然登仙。《竹书纪年》说“黄帝既仙去”[35]2,《庄子·大宗师》云“黄帝得之,以登云天”[20]252,“得之”即得道之义。酒井忠夫言其“是以绝对的道”将黄帝作为信仰客体“圣帝”来崇奉[36]52。《楚辞·远游》亦曰:“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王逸注:“黄帝以往,难引攀也。轩辕,黄帝号也。始作车服,天下号之,为轩辕氏也。”[37]145-146在时人看来,黄帝的地位为仙人王乔所不及(不过二者的位阶在《真灵位业图》中出现了倒转。王乔即王子乔,是周灵王的太子,在《真灵位业图》中位列第二等级右位的第二位[1]274)。《韩非子·十过》载师旷曰:“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34]65这里的黄帝有群臣环侍簇拥,已俨然一副尊神气派,学者据此视之为“众神之统”[29]。因黄帝曾战胜蚩尤,此时的黄帝与蚩尤已是君臣关系。《庄子》所载黄帝访真问道的叙事模式在后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十大经》和传世文献《管子》也有关于黄帝问道或引领诸臣的记载。如《十大经》有力黑(敦煌汉简作“力墨”,即力牧)见于《观》[38]205-206《正乱》[38]249《姓争》[38]263《成法》[38]286《顺道》[38]326,阉冉见于《五正》[38]233,太山之稽见于《正乱》[38]249,果童见于《果童》[38]241,这些都是战国中期或之前出现的人物。《管子·五行》载“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六相是蚩尤、大常、奢龙、祝融、大封、后土,分别负责察辨天地和四方,[39]865《地数》又有黄帝问道于伯高之事[39]1354,他们同《庄子》中的广成子、大隗、“七圣”和牧马童子等寓言人物,《韩非子》中的蚩尤、风伯、雨师一道,成为了后世进一步神化黄帝的原始素材。
关于黄帝相貌的特殊之处,仅见“四面”的描述。马王堆汉墓帛书《十大经·立命》:“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立(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陈鼓应指出:“‘宗’,尊崇,师表。因黄帝‘能为天下宗’,故又呼之为‘黄宗’。”此谓“黄帝初始时以自身形貌特点作为万物的法象”。[38]196-197《尸子》所载子贡之言也印证了这一点。《尸子》:“子贡问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呼?’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40]67孔子将黄帝相貌的传言作了世俗化的解释,认为“四面”只是黄帝命臣分治四方。不过这一解释也未能打消时人的丰富想象,前述黄帝诸臣皆可入列,服务于后世黄帝的神话化。
《山海经》赋予黄帝颇多神异色彩,是先秦时期记载黄帝神话的重要文献。晁福林概括出《山海经》中黄帝的四个特点:第一,只是诸帝之一,而非诸帝之君;第二,“以人的形象出现”;第三,“类乎《山海经》里的‘不死民’,但并非神仙”;第四,“有些神异的表现”,“有一定的权威,在诸帝中有较大的影响”。[41]笔者对此基本赞同,也略有一些不同意见,试举几例予以说明。《山海经·西山经》有黄帝服食白玉膏、为天地鬼神培植瑾瑜之玉的记载:
(峚山)其上多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密,浊泽有而(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42]37
黄帝服食的白玉膏实为不死之药,这是“借外力以求不死”[43]207的途径,启发了后世道教制造黄帝服食神丹而成仙的神话。
《海内经》中黄帝之孙韩流有异貌:
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42]372
《大荒北经》描述的黄帝战蚩尤已经不是早期的部落战争,而是踵事增华,完全变成了术士斗法的场面:
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鄉。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42]362-363

黄帝被称为“轩辕”,始见于《世本·帝系》记载的“少典生轩辕,是为黄帝”[28]11。《大戴礼记·五帝德》因袭其说,有孔子所言“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44]117,《帝系》说“黄帝居轩辕之丘”[44]127。据常金仓先生考证,“轩辕”与“黄帝”本无涉,考虑到《山海经》中《西山经》《海外西经》《大荒西经》诸经所记“轩辕之丘”或“轩辕之台”位于昆仑一带,两者合指一人可能源于《庄子》中黄帝的行踪多与昆仑有关,又因轩辕在战国时为星宿名,故合体的年代当在战国《甘石星经》之前。[45]“轩辕”与“黄帝”一旦合体,有关轩辕的文化元素自然也就可以服务于塑造黄帝的文化形象。《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轩辕之国在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42]201-202《大荒西经》:“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畏轩辕之台。”“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42]337-338轩辕之国,其民有异相,活八百岁仅是寿命的底线,还有射者畏惧的轩辕之丘或轩辕之台。如此,轩辕就成为神异和长寿的象征,黄帝自然也一样了。后世往往“轩辕黄帝”连称,正是发端于神仙风靡的战国时代这两种文化元素的新综合。
三、余论
以上我们梳理和分析了先秦史料所载黄帝由人到神的演变过程,行文中其实已经暗含了历史神话化的研究思路。探寻黄帝神话,无法绕开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神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20世纪以来先后主要形成了两种研究先秦时期黄帝神话的不同取向:其一,坚信黄帝始为神灵,后来才转变成历史人物,此为学界流行的观点。此说有将其考证成原为天神上帝者,有将史书所载纷繁零散的黄帝传说与神话“缀合”在一起进而还原为神话者,甚至还有求诸域外而充分发挥想象,走出了一条黄帝神话“国际化”道路者。这种取向或因疑古过勇,或暗受西方单线进化论思维的牵引,以顾颉刚[46]431、童书业[47]3-6、杨宽[48]105、袁珂[49]80-123、朱大可[50]545-559等为代表。其二,认为黄帝本是上古传说人物,后来才出现了神话化。这一观点是在反思前一种研究取向的基础上提出的,考虑到中国文化的现实主义精神,按照各种文献出现的顺序讨论问题,走出了一条黄帝神话本土化的道路,其代表是王仲孚[51]229-241、常金仓[45,52]、刘毓庆[53]5等。常金仓先生在讨论《山海经》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时指出:“战国是神仙之风煽扬很盛的时代,上自贵族下至平民多有致力于修炼以期羽化升天者。”“为取信诸侯而为历史人物制造神圣故事便使战国时发生了一场造神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角即是方士。本世纪(指20世纪——笔者注)前期学术研究中令学者们感到人神难辨的传说人物,其神异色彩多半是在这场运动中被涂抹上去的。”[54]《史记·封禅书》说战国秦汉时期方士“不可胜数”[16]1638“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16]1670,黄帝这一传说中圣王的神话化即是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