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热带雨林》荐读
2021-06-11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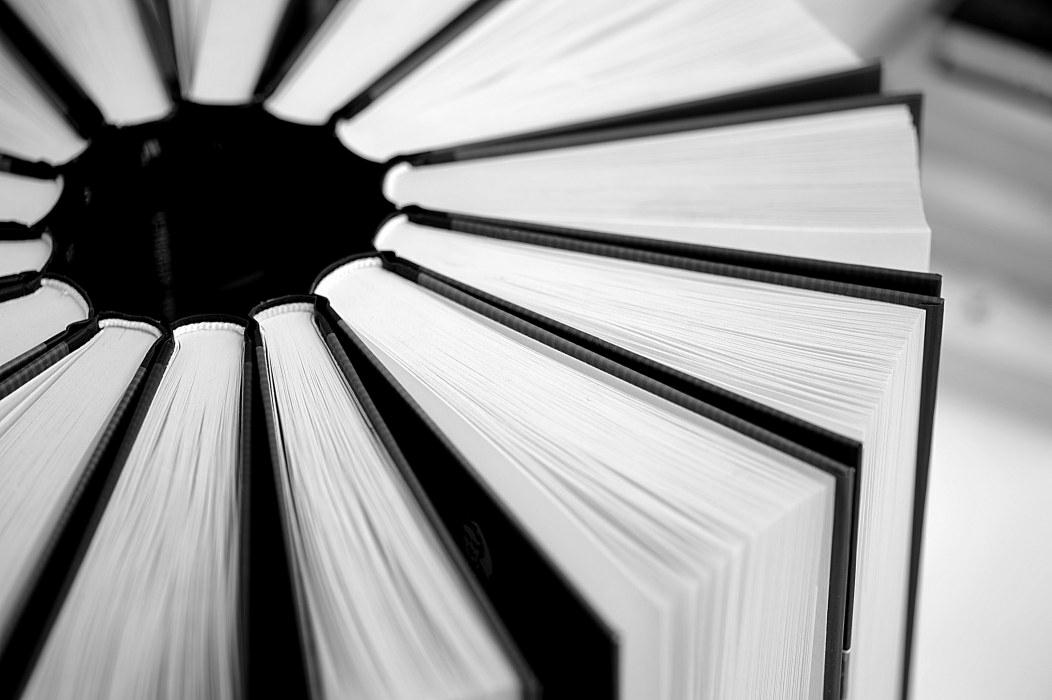
【原文】
转眼就迎来另一个时期。各类出版物比以往多出几十倍上百倍,花色、品种及数量已经超出了几代人的记忆,人们不得不接受读物泛滥和选择困难这样一个现实。一般的文字工作是这样,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则产生了灾难性的结果。我们如果稍稍注意,就会发现到处都是文字垃圾,它们正日夜滚动在屏幕及各类印刷物上。兴之所至的涂抹、昏妄的呓语、不知所云的喧嚷,以及恶意的发泄,晦暗不明、意思暧昧、稀奇怪异,全都出现了。正常的人只要耽于这种阅读区区十分钟,就会心生感叹:怎么会有这么多无聊、阴暗、丑陋和恶意?美与善何在?污浊和拙劣与一个时期的商业主义和利益集团结合,运用金钱向前推进,生出锥心之痛。
语言艺术最后连一个口实都算不上,在一部分人那里只是胡言乱语的代名词。需要垃圾填充的版面太大,以前是纸质的,现在则是由无限量的光电承载。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参与涂抹。几千万人从事广义的“文学写作”,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散文、诗歌、书评,短篇、长篇,各种题材和体裁相加,多到前无古人。各种文字像潮水一样涌来,不是目不暇接,而是直接淹没。无论是网络平台还是纸质媒体,文字的潮汐无时无刻不在涌动。午夜和凌晨都有新作发表,黎明时分已阅读十万,跟帖八千,不知刷新了多少次。“文学”洪流滔滔不绝,与其他文字一起汹涌。敏感一点的作者和读者,面对此等情状可能觉得恍若隔世。
在网络时代,写作和阅读方式发生了改变。人们开始热衷于碎片化阅读,在小小的屏幕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内容芜杂,主要是社会信息的流动。人类的好奇心首先需要得到满足,审美也就放到其次。人们愿意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信息,虽然大多无关乎自己。它们作为意趣而不是意义被人接纳。这就占用了大量时间,受到伤害的不仅是文学阅读,而是整个的精神空间、生存空间。
碎片化浏览占据整个阅读生活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种趋势还在加重。智能手机的危害与功用同在,人们不分场合地使用手机,在候车厅、候机厅和一些休闲场所,甚至是开会或行走中人们都在滑动屏幕。人几乎不能让眼睛闲下来,也不能沉思。屏幕上的闪烁跳跃具有传染力,会像病毒一樣入侵,让我们上瘾,产生从未有过的依赖。我们从此把与生命同等宝贵的时间耗损一空,却少有回报。
大量的电子片段堆积在大脑中,损害无可估量。某种神经依赖症一旦出现就无法治愈。说到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那是另一个话题;就“读取”这个单项来看,它造成的后果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无法阻止的流言,难以辨析的消息,耸人听闻的事件,浅薄与恶意,淫邪和罪愆,都在小小的屏幕上汇集。欣悦少于沮丧,绝望大于希望,人一天到晚淹没在极其恶劣的心情和接二连三的恐惧中。这里流动的文字大多是即兴的、未经打磨的,语言品质之低下、心绪用意之阴暗,几成常态。这种气息熏染下的精神生活使人向下,而不是向上。
这种特异时期形成的视觉侵占引起了普遍的忧虑,这不光是文化的忧虑,而是更多方面的担心。一旦深度渗透的数字生活走向了极端化,我们也就失去了深入关注事物的能力和机会,而所有的发现和创造,都离不开这种关怀力和探索力。我们不再专心,而审美力是更高一级的,它即将涣散。在闪烁的光标下,文字的判断力会出问题。事实上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对语言艺术的误判这样大,有时即便大瞪双眼可就是分不出拙劣与精妙。我们对语言变得迟钝,实际上是麻木。词汇在机械连缀和光电运行中失去了生命。就文学来说,这种损伤是根本性的。最可怕的是生命品质的改变,是集体无意识地陷入轻浮和草率,丧失理性思考力。这最终引起什么后果,似乎不难预料。可见数字传播引起的改变,已经远远不是阅读本身的事情。同理,也不仅仅是文学本身的事情,它关系到更本质和更久远的未来。
有人把网络时代日夜翻涌的语言文字比作一场“沙尘暴”,透露出十足的悲观和恐惧;也有人喻为语言文字的“瓢泼大雨”,比起荒漠里偶落的雨点,确像遭遇了一场倾盆大雨,大水漫卷之灾令人惶恐。如果能够再达观一些,是否还可以有另一种中性的描述,比如想象我们正走进一片语言文字的“热带雨林”?这里是一个强旺生长的、繁茂重叠的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各种各样难料的状况,更不乏巨大的危险。这样说似乎比“沙尘暴”和“瓢泼大雨”要准确一些,也较为直观形象。
进入了这样的“热带雨林”,那么所有的行进者都要提防了,要有相当过硬和完备的行头。因为这里有大动物出没,有蜘蛛和蟒蛇,有葛藤和食人树,还有藏了怪兽的沼泽水汊。当然,这里还有美到让人惊异的花卉和果实,有惊人的繁殖和生长,高大的绿植铺天盖地。
一个心神笃定的写作者不会在这样的时刻放弃。他会再次出发,开辟自己的路径,而不会追随潮流。一个经过了漫长劳作,同时又亲历过诸多风云变幻的长途旅行者,自会冷静坚卓。他会愈加严苛地对待笔下的每一个字,滤掉一切泡沫,压紧每一方寸。身处这样一片雨林,干练和警觉、操守和禁忌,还有必要的给养辎重,力求一无疏失。既不存幻想又远离悲观,与轻浮草率划清界限,对诱惑保持最大克制。不堆积,不急切,不趋时,不彷徨,更不能困顿,不能在昏沉中流出口水。
每个写作者都是这样的“行进者”,他如果按照过去的方式毫无准备地踏入丛林,可能连半途都无法抵达。他将从头设计重新选择,强化手中的器具,应对茂密的纵横交织;扎好营地点起篝火,将利器打磨锋锐;极其谨慎地行动,许多时候以静制动,在合适的时刻出击。方法和机会多种多样,或是绝路,或是另一种生存。
必须具有坚硬的本质和锤炼精神。文学的表象即语言,要把它冶炼成一种钢蓝色。这是一个缓慢的、收敛的、紧缩和汇聚的状态。最终形成强大的意志力,固化冷凝,以此抵抗迅猛的狂潮。一切急速追赶、踉跄狂奔,都将倒在带刺的葛藤下边。在浑茫的阴影里必须止步,不要迷恋,不要倨傲;不要急躁,也不要散漫。把真正的价值放在时间里,却又不能把时间当成敷衍的说辞。生存的弹性不能变成策略,而是要弯成一张弓,让其具备强大的发射力。一个写作者最好的状态还是先安静自己,先让自己满意,先回到心灵。在这个悲伤多难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安放自己的灵魂更为重要?这种自我注视和自我满足,不自觉地就会将专业标准和精神标准设定到一个高处。那个高度,外部施予的善意和恶意都难以触摸到。
此刻的谨慎持重是必要的。阅读作为一种生活的不能割舍,在任何时代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选择。我们不难想象有多少人随波逐流,日夜抓拾碎片,不忌粗拙,解除寂寥。但一定有一些人避开嘈杂,退回闭塞的角落,关闭魔器,享受书香。文字和书是这样成形的,先是写于树叶和龟甲陶片,进而是棉帛和纸;笔由从动植物身上取来的材料做成,最后才是铅笔、钢笔。人的情感一笔笔记下,手工连接的心思有一种天生的淳朴,感染力代代延续;直到印制成书装订起来,其物理还是接近原初。而今通过无线信号接收数字,于掌中演变成形,走得太远。一种无法言喻的飘忽感,很难在心里植根,来去匆匆,像一层灰尘,轻轻一拂就没了。
就语言艺术享受来说,看似小小的区别,后果却是严重的。有人说这种很难察觉的差异会在习惯中被克服。可是不要忘记,这个根性深植于生命之中,不可能在一代或几代人中改变。我们的阅读方式延续了几千年,人眼适应反射光历经了几万年的进化。
就文学欣赏来看,屏幕这个窗口未免太小。声光技术的遥不可及,阻隔了人的情感。我们虽然在读文缀句,意思也能明白,但总有一种不够踏实的感觉。思想深邃、风格迷人的语言艺术,只能是沉静默守的独对,是一次心灵相遇。它需要一种起码谐和的形式,比如捧起一部纸质书。屏幕上的文字無论多么清晰,仍然与深入的领悟相对冲,折损诗意,排斥幽思。
对于经典而言,纸质阅读是一种标配。经典是由当代写作一点点积累下来的,所以经典也不能取代当代写作。经典如果不能与当下交接,也会走入迷途。好的写作者一定与经典对话,好的阅读也是如此。现代科技催促我们寻找时尚,其实是犯了大错。请将经典放在手边,它们常读常新。
人是一种奇怪的生物,最容易遗忘,一两百年过去就感到遥不可及了,喜欢追逐国内外最新的流行物,以新为好。被眼前的时新强烈地吸引,其实其中绝大部分只是泡沫,是光线下的泛光。我们遗忘了十九世纪前后那些经典,更不要说再早一些的,多么可悲。这实际上已经是离我们最近的积累了。《诗经》《楚辞》之类的作品以千年计,也没有显得特别遥远。这么快就疏离了人类的杰出创造,怎么能令人信赖?怎么能积蓄伟大的文明?
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作家和作品,一百年也就那么多,不会更多。即便那些已成定论的文学艺术经典,也要经过后人多轮选取,接受没完没了的质疑。像《在路上》《尤利西斯》这一类,像毕加索后期的创作,许多人认为它们实在被高估了。
不要以为参与艺术的人多了,就一定是艺术的大时代。随着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物质主义的盛行,参与者的数量和品质,还有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都会受到影响。以某些淫书为例,它们作为禁书,一致被判为有害人类文明,却在网络时代受到推崇。许多类似的书都获得了越来越高的评价,就此可以明白一个时代的偏嗜。有人强调它们的“认识价值”,但这里或可反问:这种价值能够独立并代替其他?另外,所有的人间大恶都有很大的“认识价值”,我们却不会拿来审美。
今天,对精神叙事保持一种敏感的、更高的要求,是至为重要也是至为困难的。文学不能走向物质化和娱乐化,它毕竟不是可乐也不是汉堡。我们每天被各种荒唐离奇的信息、无数悲喜交集的事件淹没,正常的情感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文学即便一再提高自己的分贝,哪怕变得声嘶力竭也无济于事。数字荒漠中,悲惨的不觉得多么凄怆,奇迹也懒得赞叹,神经刺激过度了。也正因为如此,当今的文学究竟该怎样书写,就变成了一道费解的难题。精神的起伏跌宕,情感的两手颤抖,不可忍受无比喜悦、夜不能寐的爱与恨,仿佛都不再动人了。
毁灭情感和自尊的高科技加物质主义,走到了一个极端且无法遏制。作为文学,尾随就是堕落,就是一钱不值,类似的文字不读还好,越读越乱,引起厌恶,觉得卑贱。一个民族拥有这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不幸。
我们曾经专注于精神,写人的失败、勇敢和抵抗,写人的尊严。人受到侵害之后多么痛苦不安,他们退于绝地,日日独坐沉思。而今,仅仅独坐沉思当然不够,且起来做工,着手从未有过的复杂而艰巨的事项吧。
(石人选摘自张炜《语言的热带雨林》,原载《芙蓉》2020年第4期)
【荐读】
在21世纪的今天,目不识丁、完全不通文墨的人一定很少了;但如果要说及而今语言和文学世界的状况,认真思考过的人肯定不会太多。对此,著名作家张炜用一个精彩的比喻做了概括:热带雨林。顾名思义,“热带雨林”就是地处热带湿润气候条件下的森林群落。那里会是怎样的场景?张炜的描述是生动而鲜活的:“这里有大动物出没,有蜘蛛和蟒蛇,有葛藤和食人树,还有藏了怪兽的沼泽水汊。当然,这里还有美到让人惊异的花卉和果实,有惊人的繁殖和生长,高大的绿植铺天盖地。”这是作家笔下的生物学世界。如果要描绘语言、文学世界的状况,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其实,张炜已经用自己的笔做了十分具体的描述。《语言的热带雨林》原文共八节,约一万一千余字,其中有三个整节,都是在叙说他对电子信息时代人们写作、阅读状况的观察和分析。网络时代,手执智能手机这个“小小魔器”,人人都能方便快捷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其中也不乏真、善、美的传递;但从整个信息世界的面貌来说,毋庸讳言,这里是芜杂喧嚣、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对于识别鉴赏力还不强的普通人,尤其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让人目乱神迷、辨不清方向。
对于当代的写作者,张炜给出的药方是“坚守”。他自己便是一个“经过了漫长劳作,同时又亲历过诸多风云变幻的长旅者”,是曾写下过《九月寓言》《古船》《心在高原》等有广泛影响作品的杰出作家。他要求自己和伙伴们“心神笃定”“冷静坚卓”“对诱惑保持最大克制”,在写作时“愈加严苛地对待笔下的每一个字,滤掉一切泡沫,压紧每一方寸”。而对于广大的阅读者,张炜的期望则是他们能有谨慎的选择。最好是能回归“延续了几千年”的阅读方式,“关闭魔器,享受书香”。“捧起一部纸质书”,这是一种找回深植于生命的“根性”的方式,更是阅读经典的“一种标配”。这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更是找回关怀力、探索力和理性思考力,找回灵魂、安放心灵的方式。(荐读:石人)
【作者简介】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14年出版《张炜文集》48卷。作品被译为英、日、法、韩、德、西、俄等数十种文字。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获茅盾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多种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