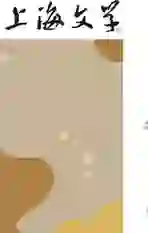一个两千两百万座孤岛组成的群岛
2021-06-01邓一光刘洪霞
邓一光 刘洪霞
刘洪霞:邓老师,自2009年,你移居深圳以来,写了许多城市文学作品,出版了《深圳在北纬22°27′~22°52′》《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深圳蓝》《坐着坐着天就黑了》等中短篇小说集,这与你以前以战争题材为主要书写对象不同,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您对城市的思考,使您华丽转身?
邓一光:我没有转身,早期的写作比如《蓝猫》《八岁》《流浪者》《猜猜我的手指》《一只狗离开了城市》,这些小说集里收录的都是城市故事,我管它们叫当代故事。那会儿人们的注意力在我写的现代故事上,也就是你说的战争题材。写完《我是我的神》后,大约六年时间,我只写过一个短篇,实际上停止了小说写作,直到移居深圳的第三年恢复写作,陆续写了一些当代故事,它们比较集中地发表出来,人们看不到我的现代故事,能看到的只有当代故事,所以,是人们的关注“华丽转身”了。
刘洪霞:你的划分有意思,战争题材叫做现代故事,城市题材叫做当代故事。我们换个角度,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深层的原因激励着你去书写我们生活的城市,你对城市的思考是怎样的?
邓一光:城市是人类智慧和想像力的最高体现,无所不能,理论上,任何个体都拥有在城市中得以完成进化、快速改变命运的可能,对写作者,它构成最显现的时代样板观察、经验处理和叙事表达的价值。不过,在我看来,这不是城市的全部,它同时也是孤岛效应最集中的地方。听起来很矛盾,有一种荒诞的逻辑,但这恰恰是城市的真相之一。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小说家对城市戏剧性变化的嗜好,有心的作家会在故事中织入不安分的叙事轨迹,揭开人类孤岛现实的秘密,在连续性的叙事表达中拒绝作为个体的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的意志和愿望,进而分享人的内心解放经验,这契合个体书写和时代书写的双重动力,进入现代之后,小说的世俗功能和终极目的都在这儿。
刘洪霞:确实,你之前的写作——没来深圳之前,也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在关注现代都市的各个层面,你创作了《城市的冬天没有雪》《老板》《红色贝雷帽》《独自上路》《我们走在一座桥上》等作品。那个时期是中国城市化的开端,而现在的中国仍然在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因此,你那个时期的城市文学写作与现在的深圳城市文学写作应该有所不同,可以具体谈谈有哪些层面上的不同吗?或者说,从这两个时期城市文学的写作上,是否可以看到中国城市化的诸多问题以及演变?
邓一光:我早期的城市题材依赖于生活体验和感受,那会儿我是新闻记者,题材大多直接取自社会观察,对某些题材感兴趣,新闻无法满足表达,就把它们写成故事。我个人的经验,城市的性质决定了它们浓厚的政治构成、商业功利和大众文化诉求,之于写作者,在创作主体感受和投射上都有着强大的规定和约束力,它们诱惑写作者在社会意义上作出努力,即建立政治立场、市民要求和生活愿望上的现实主义写作,比如你一定不陌生的市民经验与城市诉求的同构。这样的写作,表达视域相对比较窄。
刘洪霞:你是说,这是你早期写作建立的基础。
邓一光:嗯。这些年,因为时代剧烈变迁和个人生活的动荡,作为写作主体的我和观察客体都在变化,书写对应地发生了变化。你提到的城市文学写作,以及中国城市化问题和演变,我理解指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典型经验在文学上的反映。这是学者课题,文学相反会警惕它的外部彰显内容,比如说那些很容易用数据或概括性手段进行表述的城市建设成就,以及城市与个体之间的利益性冲突,这些内容对小说会形成表达视域的制约。我的兴趣在于,深圳产生于一次虚拟,在建立之初没有得到前经验的加冕,甚至没有得到多数居住者的授权。相当长时间里,它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受到质疑,内部博弈也很激烈,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前经验和前现实的背叛上的。实际上,和其他写作者不同,我不认为它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市场经济奇迹,而是把它看成一座“叛逆者之城”。
刘洪霞:哦?这是一个有趣的视角。
邓一光:这么说当然有些简单,事实上事情比这个要复杂得多。四十年来,数以千万移民来到这里和离开这里,他们割裂和背叛了自己的前生活,在一座完全建立在虚拟之上却得以快速发展的城市中,没有什么文化基因可以帮助他们连接现实生存和抵达理想,直到现在,人们仍然在不断抛弃阻碍自己前行的那些既定的东西,创造全新经验。你在内地任何城市都能看到一些数十年没有太大变化的人,他们甚至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着,但深圳没有,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维持衡常状态,历史在这儿迭代得非常快,包括原住民也在经历这种变化。经过四十年的城市化发展和改造,这座城市几乎没有剩下多少显在的原住民文化了。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十年,只结识了三位原住民朋友,谈不上对他们的历史有多少了解,这显然让我难以对城市有整体性观察。我曾把我的一位原住民朋友称为“活化石”,他比我大几岁,我叫他“小梁”,他很高兴,也乐于做我的老师,我想你可能也没有多少原住民朋友吧?
刘洪霞:是的,我在深圳的确没有原住民朋友,我的朋友和我一样,也都是外乡人。
邓一光:这正是多数城市移民的现实生存境况,也是写作面对的问题,我们不再有一个熟悉过去、文化遗传清晰、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经验援助的舒适区,甚至找不到一个整体性存在的观察对象,这就意味著我们的写作要进入无人区。所以,我更愿意把深圳看作由两千两百万个体组成的共同体,一座两千两百万个孤岛组成的群岛,写作不是面对一个整体,而是面对无数割裂状态下的个体。
刘洪霞:我理解你所说的孤岛,其实我们生活在这座崭新的城市里,都是一座孤岛,我想正是因为这座城市带给我的这种感受,才有了你到深圳以后创作的改变,这种改变也正是印证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邓一光:可以这么理解。
刘洪霞:作家是极其敏锐的,每一个时代细微的改变都会被捕捉,更何况这种轰轰烈烈的城市化道路及其带来的人的心灵和观念上的改变。你所说的“叛逆者之城”某种意义上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这座城市的内心。
邓一光:您提到了文学的关键所在。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不思则不得。不从情感、思想和精神这些角度去考量,城市是没有意义的,文学也就不在场了。
刘洪霞:那么,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写作会有重大的差别吗?难道这些城市不是统一的城市化进程中的结果吗?网络上就有“千城一面”的说法。
邓一光:我不同意城市是统一进程的结果这个判断。我们习惯于把城市当成一个复制品——事实上,的确存在大量这样的复制品,中国内地的三四线城市复制比例非常高,从现代化进程看,深圳也在大量复制外部世界,甚至一度有“山寨”城市的批评。但真正的复制不在现代性必然导致的规范性观念、模式和路径的效仿上,而在于城市化进程中,深圳传统的海疆文化、耕读文化等基因被快速稀释掉,几乎无从辨识;在于现代精神对前历史毫不犹豫的贬低和断裂上,这是作家应该关注的。但也应该看到,外部世界是复杂的,城市发展的内部动因也是复杂的,重要的是,统一进程这样的观察忽略了“人”这个重要因素,包括城市的设计者和施建者,以及具体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制式化不是唯一的构成要素,城市仍然有不同的魅力和致命性,即使看上去似乎相同的城市,住上一段时间,你仍然能区别出城市的独特性,而且是本质上的不同,这需要观察者具备耐心和热情。
刘洪霞:你是否认为,深圳这座城市有自己独特的气质,比如王安忆的上海、金宇澄的上海、小白的上海都是不一样的,邓一光的深圳与其他深圳作家的深圳也是不一样的,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
邓一光:如你所说,上海和深圳都有非常强烈的、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气质和城格。从发展史看,上海开埠后受殖民文化影响,既得益于欧美近现代工业文明文化,又保留了江南传统的吴越文化,属性非常明显。深圳早期是边远海疆,鸦片战争后加了个陆疆,两次鸦片战争中,直接冲击地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造成了广州一口通商的结束和上海的开埠,这两次战争,英国人的舰队都是从深圳边上过去的。那个时候深圳只有几个不起眼的兵营,就这么被历史忽略掉了。和内地城市比,深圳除了地处南洋边,毗邻香港和澳门这个地缘条件外,没有任何先天优势,完全凭着早期建设者的强烈进取、不走循规路、情绪饱满和不安分闯出了一条路,这种气质与它的“年轻”和缺少积累如出一辄,这种情况在内地城市几乎看不到。上海的开埠可以说是顺天应人,半殖民地文化快速落地,几乎整个中国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快速聚合。深圳的崛起却没有这些条件,中央不给钱,内地体制质疑,理论界批判,完全是一个不情不轨的逆子形象,你想想那句深圳文化基因中的口号,“杀出一条血路”,颇有些决绝。这样的两座城市,可以说基因和发展模式完全不同。还有一种情况要看到,上海早期移民主要由江浙人构成,当代以后才开始多元,深圳移民以广东和两湖地区的人为主,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形成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以城市发展史考量,几千万上亿新老移民在这两座城市里生活过,对城市塑造留下或多或少的痕迹,这是城市基因,构成城市的隐结构。提到城市文学,上海是内地城市文学的集大成者,尤其“五四”之后那批作家和出版人的书写,应该是最早的城市文学文本的提供者,当代作家中最优秀的一些,也有不少生活在上海,他们的城市书写方兴未艾时,深圳的文学还没有起步。
刘洪霞:虽然当前各个城市的建设被严重地同质化,然而作家却能发现其中的不同,这是文学的魅力,作家看到的那个城市是“看不见的城市”。关于你的“深圳文学地图”是许多研究者都很感兴趣的话题,您的城市文学写作使用了大量深圳真实的地名,例如,“香蜜湖漏了”、“宝安民谣”、“光明定律”、“出梅林关”、“杨梅坑”、“欢乐谷”等等,这都是深圳人耳熟能详的地名,把它们连缀起来可以组成一幅“深圳文学地图”,但这种书写只是表层的意义。
邓一光:嗯,即使在地理、历史、民俗和语言这些文化学领域下足功夫,仅仅对城市的标志性符号作表征上的描摹,也远离了小说创作的要义。小说家是生活的观察者,也是命名者,他编织故事地图的兴趣不是他想做一个故事的旅游者,只满足于历史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常识内容,而是他靠故事的写作,拥有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命名的权利和能力,进而在人类精神与情感领域建立个人叙事。
刘洪霞:这正是我要说的。我想你把深圳地名写进作品的时候,肯定有更深层的想法,例如《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一直走到莲花山》这三部作品,涉及到了深圳的三个很著名的地名——“红树林”、“万象城”、“莲花山”,它们在这里不简简单单是一个地理标识,而是某种意义上的指代。
邓一光:城市与人物、与文化是一种镜像关系,投射的是人与城市、与文化的内在肌理,以及更为真实的精神气质,如是,小说家就不会让故事停留在实际的地名上,而是把空间位置的自然或人文地理的实体名称作为一种特殊的含义给予重新命名,比如作为一种矛盾因素植入人物的生存环境和精神纠缠,使单纯的冲突情节因异质物的刺激,分泌出复杂和尖锐的新的故事成分,戏剧创作中叫延宕。比如你提到的,“红树林”写的是个体命运与关联生命、历史创伤与现实困境这个主题,“红树林”对应的是主人公所处的整体背景,所以在故事中,主人公念念不忘的是生活在红树林中的、脚下的那些人类史前生命砗螺、三角藻、水狸和刺水蚤,你不知道和主人公彻夜对话的是“看不见的男子”、黑脸琵鹭还是主人公自己。“万象城”写一个身处城市主流生活场域中的卑微人物的希望、纠结、羞涩和忍耐的故事,“万象城”对应的是华麗事物和现象与价值的悖论。“莲花山”在城市中心地带,具有城市象征的公共空间,本是最该出现共情和同理心、获得个体生命赋权的地方,人们却怪异地产生身心分裂,深陷归宿匮乏的黑洞,“莲花山”对应的是失衡的价值取向和关系。其实对故事作如是解释并不高明,好故事有一种弥漫能力。
刘洪霞:好故事会留给研究者更多的阐释空间,也就是你所说的弥漫能力,它肯定不是单一的故事主题,而是有多重的理解角度,故事是立体的,而不是扁平的,它所勾连起的事物仿佛是错综复杂的3D空间地图,会令人迷失,也会令人清醒。另外,我在你的城市文学作品中发现,你似乎非常喜欢动物与植物这两个意象,你几乎是被作家事业耽误的动植物专家。
邓一光:很遗憾,我没有动植物学专业背景,但的确喜欢,而且有时候会习惯和它们——主要是动物——没来由地说几句话。说起来我的生活很乏味,不是林区居民、海洋中人、野外生存者或者任何动植物保护组织成员,和动植物既没有共居生活条件,也没有固化的他者观念。
刘洪霞:《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出现了马和蝴蝶,还有《勒杜鹃气味的猫》中的猫,《深圳河里有没有鱼》中的鱼,《家乡菜,或者王子厨房的老鼠》中的老鼠,还有红树林、百合、勒杜鹃等植物,这些意象包含了怎样的隐喻?您是否是在建立一种城市生态文学的主张,还是另有更深层的原因?
邓一光:写作时我不带传统意识形态的城市生态文学考量,唯一例外的是《就像一块即将消失的陨石》,那是去年疫情期间,在得知深圳湾航道疏浚工程环评事件丑闻后,因为愤怒写下的。新界那边把环深圳湾当作城市垃圾场,蛇口这边把环深圳湾当作人造观光带,我觉得人们毫无收敛,太欺负原住生命了,我就想,别给我谈抽象的城市发展,那是谎言。那个故事我完全不考虑技法,就是呐喊,那就是它,它就得这样。
刘洪霞:作家直抒胸臆的呐喊,摒弃了各种技术层面的考究,这样也许力量来得更强大,这是知识分子的写作和担当。
邓一光: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生态文化突破了人与自然的传统整体主义,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殖民话语中人类的他者,而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甚至内化为自我。但我不尝试这样的写作。大概念上我是动物,和其他动植物区别不同的是思维及文明方式,如果这是进化论意义上的优势,反过来,我的生存能力远远不如它们,缺乏它们所具有的自然活动范围、种群尊严和神秘感,比如我不能像黑白秃鹫和大天鹅一样在万米高空飞翔,像葡萄牙鲨鱼和狮子鱼一样在万米海底游动,这是一种遗憾,我做梦都希望拥有那样的能力,但能力的匮乏也许是幸事,这样我就不得不放尊重一点,不会为所欲为,同时在一种未能满足的共生情节中关照个人的孤独情结。我觉得我还能找到,至少在视野、命运观照和情感中找到现实关联依据,这个你可以在《如何走进欢乐谷》和《北环路空无一人》中看到,那两个故事里写了两只狗。
刘洪霞:有印象,一只有着北极狼基因的雪橇犬,一只苏俄猎狼犬。
邓一光:对,它们和主人公没有同化和顺应机制,并非内化关系,人只是视角和投射,那就是我的立场。
刘洪霞:在《离市民中心两百米》中,你写到了高知的夫妻住到了市民中心附近,而在市民中心附近工作的保洁阿伯多少年来却从未走进市民中心。市民中心是这座城市的CBD,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您是不是从城市空间的角度来谈阶级的差别。
邓一光:私有制出现以后阶级就出现了,可以说阶级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秩序,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个层级不但没有打破,反而更为细致和固化。不过,我在故事里写到动物时并不影射阶级差别,阶级差别是现实,不具有象征意义,我不打算从人类历史基础症结开始故事,至少短故事做不到。我只是在某个话语境域中展开命运,由此不断梳理人的真相和社会真相,如果人物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会怂恿他去做不甘的抗争。
刘洪霞:所以说,你的城市文学所反映的事物是非常复杂的,绝不是表面意义上的讨论,这需要批评家给予更深层次的关注。
邓一光:阐释的过程是阐释者与文本的共谋关系,别忘了,批评家也是故事的创作者,他们观察和分析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安放他们自己焦虑不安的话语,那也是故事。
刘洪霞:你的《家乡菜,或者王子厨房的老鼠》在如何讲故事上做足了功课,因此对研究者或者读者提供了多重的阐释空间,而不是直接的单一主题的东西,作品有丰富的层次而对研究者又提出了智力与经验上的挑战。
邓一光:传统小说不是没有好故事,现代小说也没有过时,我读蒲松龄、读卡夫卡和格里耶,只能在白天读,夜里读会脑子异常活跃,睡不着觉。作为人类系统性的高级表达,他们的经验恐怕难以穷尽,甚至将是智能人学习的内容。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也在进行各种新形式的探索,现实主义不可逆地发展到新现实主义,寓言写作发展成新寓言,在人的生存状态的困境和人际隔阂、极端物质主义的批判方面有不少佳构,而且这种发展没有停止,还会不断进化。但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处时代之于前文明是颠覆性的,人类文明几千年来建立的价值和伦理体系已经不能解释当下时代的现状。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不但强行建构起人的多维生存空间,也促使人类不得不建立起多维认知、精神和思想空間领域,小说家要回答这些问题,让传统故事的“1”构成现代故事“N”的可能,就不得不蜕变,提供多维故事结构,否则之于人类生存现实描述和未来想像是无效的。
刘洪霞:你说的有效故事指什么?
邓一光:视创作冲动和素材定,不尽相同。有时候是故事自身特质欲望的单纯满足,有趣或典型意义人物、激励想像力的情节、巧妙而增值的结构,有时候是营造一个精神或思想的裂变装置,故事能释放出强大的裂变反应,由此激发阅读者的精神或思想能量,形成阐释冲击波。
刘洪霞:形势所迫,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小说的历史也过于漫长,作家也被“逼迫着”不断创新,生产出更新的艺术形式,小说是一个生命体,它也在不断生长。不同的作家会有各自不同的方法。
邓一光:是的。
刘洪霞:我发现有些作家的创作是无意识的,而我感觉你的创作是有意识的,其实你故意在作品中埋了许多个“宝”,令研究者去欣喜地发现,构成了作家与研究者之间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或者说实现了作家与研究者之间的心领神会,这是非常愉悦,同时又具有挑战性的阅读体验。
邓一光:除了少数天才作家和诗人,并不存在能透视历史真相,同时具备整体性把握的写作者,我属于后者,好奇心使然,不满足单纯的故事写作,对感兴趣的素材会条件反射式地思考,拆分、质疑或者干脆放弃。不过对短篇来说,这个思考的过程非常快,甚至很难说是在思考,一个人每天要做多少个动作?恐怕细算起来在数十万之间,那个思考更像条件反射,受制于思想经验的习得。
刘洪霞:你是否觉得自己的创作非常理性?
邓一光:理性对写作是重要的,尤其长篇写作,需要对题材和素材作出清晰的判断和分析,拥有明确的思维方向和思想依据,这个过程通常发生在动笔之前,那会儿尽可以做逻辑推导工作,反复否定与怀疑,一旦动笔,更依赖持续的情感动力。我没有一部长篇写过提纲,我不能说服自己妥协于已有规律和内容的强化约束,守住确定结果,那是一种很枯燥的工作。我希望人物和故事打破先在经验,完成他们和它们的奇妙旅程,理性往往是旅途中的限制性陷阱,我会警惕,尽可能看护住他们和它们,小心别掉进去,否则就废掉了,我的长篇半数是这么废掉的。
刘洪霞:你是否认为写作完成后,此时作家已经被“杀死”,阐释权完全掌握在研究者手中?
邓一光:小说家在故事形成时拥有至关重要的言说权力,故事结束后最好远远走开,不再去谈论它。这么说的原因不是对阐释学的尊重,而是故事自有生命。没有哪位小说家能如实地把微妙的文本生成过程复原出来,清晰解释体系和方法这些内容,在文本形成时,亚里士多德说的那种“神之消息”是带着超越意志出现的,往往超越了小说家动笔之前确定的历史、哲学、宗教、语言和结构这些前置设想,也就是文本最终的意义部分,和文本设想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
刘洪霞:你这个表述是一种被动的主体态度,这么说不是被“杀死”,更像是“自杀”。
邓一光:你这么理解?那我换一个说法,小说家通过人物寓意、情节迷宫、结构路径和精神视域的创造性工作,使故事形成了增值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故事具备开放的阐释现象,而故事作为文本,创作者其实是三类人,小说家、故事和阐释者,只有當他们全部完成对故事的创作和阐释,这个故事才活过来。所以,好故事就像九命猫,通常会有无数解读版本,相当于无数生命,前提是它的确是好故事,而且遇到了同样具有创造性能力的阐释者。
刘洪霞:是的,我们再把话题拉回来。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的城市文学是1920年代到1940年代的海派文学,代表作家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张爱玲等,之后,就来到了城市文学的枯水期,几乎是乡土文学一统天下。当城市文学再度兴起时,已经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直到现在。乡土文学永远也代替不了城市文学,两者是现代性的一体两面。那么,深圳的城市文学总是含有乡土文学的影子,因为不仅深圳的前身是一个处于岭南尽头的戍卫边镇,现在城市的人口来自于乡村的也占较高的比例,你如何看待深圳这座城市与乡村这种同构的关系?
邓一光:你分析了深圳的人口来源地情况,应该看到,深圳移民数量超过原住民七十倍,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原住民,很多是上世纪中叶才来到深圳的国家工作人员、驻军和移民,对多数人,文化基因在深圳书写中不是顺理成章的传承,而是剜肉剔骨的断裂。深圳移民作家和诗人中,有一部分下意识的前经验写作者,一部分在融入城市化过程中感到艰涩的写作者,他们在写作中保留家园情结不光是惯性使然,更是生命经验的守护和精神抚慰的获得策略。新的书写者还在源源不断到来,这种情况比其他内地城市要明显得多,书写中的城市与乡村经验同状况构会一直延续下去,这种情况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会处于一个挣扎和博弈的过程,但在深圳不同,它是绝望的。
刘洪霞:为什么这么说?
邓一光:深圳2004年就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渔业、林业、养蚝这些传统的乡村生活场景的维系者现在基本是移民,你完全找不到乡村生活的历史和现场,持续的乡村书写,要求写作者在精神性和经验上首先完成在地化的接续和超越,写作史上有这样的例子,深圳目前还没有看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写作者的悲哀,现实的城市和回忆的乡村根本就是一种虚假关系,建立在这个虚假关系之上的理想生活完全不存在,这使书写成为一种全面的回忆和想像行为。这种现实书写的最大悖论在于,人们在城市里生活,精神的剧烈冲突在当下经验中发生,却习惯于乡村文化和价值观回忆,这种路径依赖的写作恐怕会一直存在。
刘洪霞:据我观察,你说的这种情况不是唯一的写作类型,而且不是最有价值的写作类型。
邓一光:你指的是那些有所准备,希望拥抱城市生活经验,让个体写作与城市发展形成同构讲述的作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逃离了经验茧房,却没有逃离观念茧房,即使书写着城市故事,却满腔乡村思绪和精神,对现实言说无力,对未来无从想像,这种现象的确具有研究价值。我指的不是题材,而是文学意象和价值观,所以你会看到在深圳的加工业时代和制造业时代,那么多写作者写出了大量对生存环境和阶层结构的诅咒,同时写下牧歌式的对家乡的思念。那些故事相当鲜活,汗涔涔,血淋淋,充满了对冰冷的金属秩序的批判,有些篇什才气逼人。但这不是城市与乡村的规律性同构关系,加工业和制造业与乡村经验的冲突不唯血汗冲突和身份认同撕裂,写作的扁平和同质化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刘洪霞:你觉得问题在哪儿?
邓一光:我们在城市化之前从来没有遇到如此复杂和深刻的处境,城市将人们分配在现代性专业化网格中,乡村经验中相对完整的时空世界和价值体系完全消失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在未来的想像中也不存在,人们一方面要扮演自然人、家庭人、职场人、社会人、经济人和公民的复合角色,建立新的生活秩序和价值体系,一方面又面对着个人角色的严重分化,在信息爆炸时代里个人经验的极度碎片化,以及变革时代中个人前经验的快速老去,每一组关系都是纠结甚至冲突的,这才是人们面对的全新经验,而过去那一套文学观念和方法论根本无法描述这一切,甚至我们从传统文化那儿习得的世界本质性真理都不存在了,模糊和诞妄才是人们的常态生活。
刘洪霞:听起来有点悲观。
邓一光:不,这正是文学的入口。工业化之后,文学对人类世界本质的探究远不如科学对自然世界本质的探究走得远,但它的确在人性的复杂和深度的描述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条路并没有走到头,人们在当下时代不但面对着前经验和处境的坍塌,也面对着新经验和处境的重组,这些都会在时代精神和情感上表现出来。终极意义上的写作不是对现状的入骨描述,而是对经验中尚不存在的希望世界的描述和叩问。我个人会等待另一种城市与乡村同构关系的书写,那是对这座城市历史和文化脉络的探源,故事中有大量我们不熟悉的、我们生活之地鲜活生动的前史细节,同时它会提供那个时代人们的经典情感与精神,它会让我们触摸到这座城市神秘而狂野的本土基因。我知道这样的故事会出现,因为我知道有人正在书写中。
刘洪霞:你在书写了五十多部中短篇城市文学作品后,又推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作品书写了1941年的香港保卫战,这场战役的发生地也在深圳附近的区域里。为完成这部作品的书写,据说你查阅了许多历史资料,因此,你是否对深圳这座城市的历史给予过特别的关注?
邓一光:深圳是我和我的家人目前的生活地,对我来说有亲切处,有好奇,也有纠结。我来深圳后关注过两位写作者,一位是南兆旭先生,他写了很多有关深圳自然资源的书籍,至今我仍在關注他新的出版物。另一位是廖虹雷先生,他是原住民作家,写了很多民俗著作,他的书我都读过。我几年前弄到一套《深圳旧志三种》,包括明代天顺年间修纂的《东莞县志》、清代康熙年间修纂的《新安县志》和清代嘉庆年间修纂的《新安县志》,还有一些深圳考古书籍,没事就翻翻,阅读时间应该说早于对香港文献的阅读。
刘洪霞:对进入深圳历史有障碍吗?
邓一光:对文献上的历史了解不存在障碍,但历史这种东西,证实和证伪都不那么容易,不过倒也算一项有趣的工作。真正的障碍来自精神认同和批判支点的确立。“魂乎归来!居室定只。”是这个。
刘洪霞:批评家与研究者把深圳文学命名为“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城市文学”、“非虚构文学”,你同意这样的命名吗?
邓一光:从线性规律上讲,研究者找到了一种有效途径,便于当下对深圳文学进行言说,可以说是“深圳式”的文学研究途径。
刘洪霞:能展开谈谈吗?
邓一光:中国的现代城市史不过百年,城市文学研究没有太多积累,研究者大多借鉴的是赵家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思路。深圳文学史研究对应的是中国当代城市发展这一时期,实践上有吊诡之处。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不是自然发生,甚至不是完全自由市场的产物,大家都没有经验,深圳因历史和地域条件充当了前行者角色,第一个冲出起跑线。目前深圳是中国唯一百分之百城市化的大都市——上海的城镇化率不到百分之九十,北京和广州的城镇化率排在上海之后,这种情况对个体研究对象有两个存在和辨识向度。一个是新深圳人——暂且借用这个说法——无论来自哪儿,内地乡村、城镇或城市,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如今的生活环境完全没有了乡村内容,根本不可能靠那点乡村经验的脐带血活下去;其次是他们的经验在内地没有借鉴甚至无法参照,不像传统文化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他们连传统文化都没得借鉴,所以你看深圳办了无数个讲堂,内地学者如过江之鲫来深圳讲传统文化,但讲的基本是新儒学。
刘洪霞:你的意思是,深圳文学是建立在全新言说基础上的?
邓一光:对,从整体言说上,深圳文学是断裂的、全新的、创世纪的经验书写,即便你前面提到的乡村经验书写,在深圳也不纯粹,那种乡村经验不是整体性的,研究者想在文学史的既成谱系中找到研究逻辑,即使做到了,不是驴头对马嘴,也是隔靴搔痒。
刘洪霞:这就是“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城市文学”出现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邓一光:是的。“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城市文学”这几种样式,最早都出现在深圳,或者与深圳有关。比如深圳曾是“打工文学”重镇,有非常大的写作者体量,出了一批作家和诗人,这几年有些变化,把旗帜换成了“劳动者文学”;“底层文学”的命名源自深圳作家曹征路的《那儿》和《问苍茫》;《特区文学》和《新城市文学》较早提出了“城市文学”概念,早在1980年代,《特区文学》就有意识地推出城市文学作品。深圳是建立在想像基础上、由数千万移民共同创造出的产物,历史和个人从断裂到创造的接续努力,正合辙这座城市的发展类型和精神命运,这使研究者的命名具有了现实依据,也符合深圳的整体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