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
2021-05-30杨绛

《我们仨》是杨绛撰写的家庭生活回忆录。1998年,钱钟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杨绛在92岁高龄的时候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家庭63年的点点滴滴,结成此书。不论暴风骤雨,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是杨绛一家人的庇护所。愿读到这里的你,也能从“家”这个字眼中获得力量。
一九七八年,阿瑗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她出国一年,我们想念得好苦。一年后又增加一年,我们一方面愿意她能多留学一年,一方面得忍受离别的滋味。
这段时期,钟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几次。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我们偶然出门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带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說:“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钟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 worked me hard.”(瑗,你让我很辛苦。)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才”,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钟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钟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摘自《我们仨》,出版: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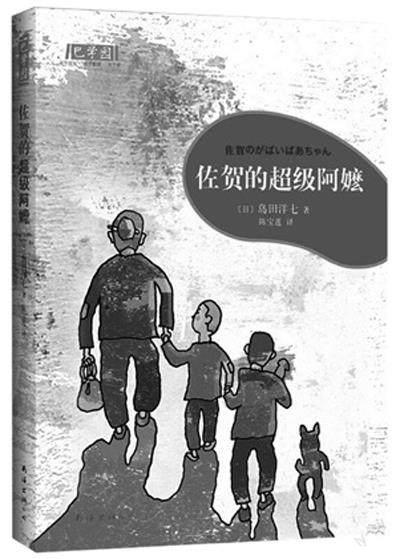
《佐贺的超级阿嬷》
作者:[日] 岛田洋七
出版社:南海出 版公司
这是一本令人心底浮现淡淡的忧伤,也令人感到温暖的书。因为无力扶养,母亲将年仅8岁的昭广寄养到佐贺乡下的阿嬷家,没想到迎接昭广的却是一间破烂茅屋。在那物质匮乏的日子里,乐观的阿嬷总有办法让生活过下去,始终让家里洋溢着笑声和温暖。阿嬷说人到死都要有梦想,不实现没关系,毕竟只是梦想。她让昭广明白,人生不会被悲伤打败,而是应该努力向前,快乐面对。

《我还记得》
作者:亦邻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亦邻的妈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以前“无所不能的超人妈妈”变成了一个被剥离了记忆、情感和正常认知能力的懵懂老人。作为一名插画师,亦邻试图用绘画帮妈妈抵御遗忘、留存记忆。看到妈妈被画里以前的场景唤起回忆,开口说出“我还记得”,亦邻深受触动,于是坚持每天给妈妈画一幅画,画爸爸妈妈相亲相爱的时光,画自己和姐姐妹妹小时候的故事,画妈妈曾经的理想……三姐妹在共同照护患病妈妈的过程中,逐渐懂得了,爱的本质是相互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