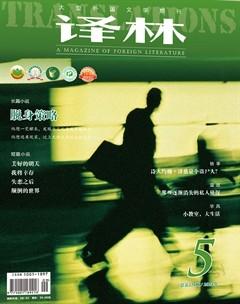告白
2021-05-30罗伯特·麦基
〔美国〕罗伯特·麦基

1
我骑车驶入撒切尔家的车道,熄灭了摩托车的引擎。放下车的边撑后,我没有上楼——暂时没有。半小时前简打来电话,说查理病重了,想见我一面,她让我马上赶来。我匆忙赶到他们的住处,但现在到了这里,我没有上楼,而是跨坐在摩托车上大口大口地深呼吸。雨刚停,茉莉花香弥漫在深沉的夜色中。查理·撒切尔很是以他的花园为傲,我告诉自己,我只是试图偷取片刻来享受查理所种的茉莉在夜晚绽放的清香。但这只是自欺欺人,因为在这个想法还没能成形时,我就知道它是个谎言。
门廊的灯亮了起来,而我的车停在它黯淡昏黄的灯光之外。简打开前门走了出来。“普莱?”她喊道,“是你在那儿吗?”
“是的,”我边说边从摩托车上跨下一条腿来,“是我。”
她走下台阶来接我。“不敢相信你居然骑摩托车来,”简说,她伸出手掌,“难道你没有注意到下雨了吗?”虽然尽力微笑,但她的脸肿胀至极,所以不太能笑得出来。
“是啊,我知道,但我想骑车。”事实上,我在沮丧的时候才喜欢骑摩托车,而那晚的消沉如查理所种的茉莉的花香一般围绕着我。我耸耸肩说:“有时候这让我好受一些。”
我这么说的时候,简的表情突然扭曲,然后失控。“噢,普莱。”她叹息道,快步跑向我,伸出双臂抱住了我的腰。她将头枕在我的胸前,发出了一阵阵低沉、难过的声音。虽然被我防水雨衣上的雨水浸湿,但她看起来并不在意。“它来了,”她说,“来得太快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伸手抱住她,将她拥紧。一个多月前,查理被诊断出肝癌。一周前,他开始住院治疗。但两天前,他不顾医生的反对,坚持让我们带他回家。
“他让我打电话通知你,”简说,她抬起头看着我,“他说和你的谈话非常重要。虽然很痛苦,但他拒绝服用任何止痛药,因为他想在和你说话时保持清醒。”
我紧紧拥抱了她一下,双手仍放在她的肩头,我把她推远了一步,低头看着她。“没关系,我来了。你还好吗?”我问道。
她用双手拭去泪水说:“我不是很好。除了在查理身边以外,我总是以泪洗面。我还没在他面前哭过。他已经承受了这么多,不需要再看见我歇斯底里。”她解释完,露出了另一个不太对劲的微笑。
我们朝家中走去,到了门廊,我脱下雨衣,抖了抖上面的雨水,然后挂在走廊的栏杆上。“他透露过任何想法吗?”我问。
“没有,他一直都守口如瓶,但我能看出来这对他很重要。”简打开前门让我进屋。“他说一旦有机会跟你谈谈,就会向我和孩子们解释一切。”她朝楼梯点了点头让我继续上楼,眼中闪过一丝母亲般的责备。“要不是你骑着摩托车来,”她说,“我就给你啤酒了。”简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让我知道她觉得摩托车很危险。
我紧紧抓住结实的橡木扶手,努力把自己拽上楼梯。撒切尔的家位于距离巴尔博亚公园一个街区的第五大街,是一个修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巨大且漏风的建筑。这么多年来,查理一直是我的二把手,我出手自己的安保业务后,新的老板提拔他为总经理。那时候我以为他和简会卖掉他们在圣迭戈的这座房子,搬去北郡,那里有公司主要的办公室。但是我提出这个建议时查理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我们在这里抚养两个男孩长大,”他对我说,“我们也会继续留在这里。”
走到查理房间外的楼梯平台时,我又一次犹豫要不要进去。茉莉的气味已经消失殆尽,所以我不得不接受现实。查理·撒切尔对我来说就像叔叔一样亲近,我没法面对他即将离去。
一个嘶哑的嗓音响起:“进来吧,德萊尼神父。”我咽了一下口水,推开门,抬脚进去。
“我以前还从没被错认成神父呢。”我说。查理在一张病床上,床被调整到他差不多可以坐起来的高度。
“哦,天哪,瞧瞧谁来了。是那个机车废物。”查理来自纽约的皇后区,对于我这个习惯西海岸口音的人来说,他听起来和老电视剧里的阿尔奇·邦克(美国电视剧系列片《全家福》中的人物,著名的偏执狂。——译注)一模一样。除了体形以外,他甚至看起来也很像阿尔奇。不过查理的块头大多了——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体重远超过两百磅。至少在他生病以前体重超过了两百磅。现在的他日渐消瘦。距离上次见面仅仅两天,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他看起来掉了二十磅,老了二十岁。
我用尽全力挤出一丝笑容说:“我的天,查理,你看起来糟透了。”
“多谢。直到刚才我都有些伤感,但你真的很能让人打起精神来。”
我拍了拍他的手。“这点事微不足道。”
他低声嘟囔着:“最近,微不足道的事也举足轻重。”查理很不待见我悠闲的生活方式。我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出头都在忙于发展事业。等我卖掉公司时,我们的业务已经非常全面:统一制服的保安,守夜人,防盗警报的安装,私人调查。这些年的创业经历使人筋疲力尽。现在我终于可以花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包括在西海岸的家乡随心所欲地骑摩托车。努力勤奋的查理·撒切尔不认为这是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结束了刚见面必要的调侃,一瞬间气氛开始凝固。查理打破了沉默。“大夫估计我活不过一周。”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身体非常沉重,任凭自己滑落到床边的直背椅上。“也许时间更短,”他接着说,“一开始我不相信,但我知道这是真的。这很奇怪,你知道吗?就好像我能感觉到自己渐渐枯竭。”
我开始告诉他我有多难过,虽然我即使不说他也知道。查理总是能读懂我的心思。我们相识已经超过十八年。他刚从海军退伍时,我就雇他在纳雄耐尔市的一个零售商场当保安。那个地段治安很差,但查理完全能胜任这份工作。为那个地方提供安保是我的第一笔生意,所以从一开始查理就和我共事。
他抬起一只手指向门,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约翰,我们谈话期间能一直关着门吗?”我的名字是约翰·普莱尔,而大部分人叫我普莱,查理总是叫我约翰。我去关上门,回来之后他对我说:“我以为你可能是德莱尼神父,因为我让简妮(简的昵称。——译注)给你们俩都打了电话。神父的住宅就在几个街区以外,我还以为他会先赶到。”
“你肯定忘了我对限速的鄙视。”
他对我的小玩笑匆匆报以一抹微笑——其实真的不好笑——但是我可以察觉出美好的时光已经结束,有一些事萦绕在他脑海里。“这样更好,”他说,“我正好也想先和你谈谈。”
“什么事?”我问。
他凝视着自己干枯、结疤的双手很久很久,最后终于摇着头用虚弱的声音说:“我不是个好人,约翰。”
我坐回椅子,双臂趴在病床的护栏上。“那真是疯了。你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人。”我不只是这样说说而已。查理·撒切尔是一个可敬、无私的人,是慈爱的父亲、忠实的丈夫。他是童子军的领队,是少年棒球联盟的教练。他一周会花一晚上在集市的收容所发放羹汤。他是十几个弱势儿童的老大哥。“该死,查理,”我说,“你可是这个国家每个浑球政客都在假扮的人。你说你不是一个好人,是什么意思?”
他转头看向我,泛红的眼眶在暗黄的面容上尤为明显。“我不是,约翰。我想当一个好人,我试着成为一个好人。”他又转头望向窗外后院的黑暗。“我想弥补我所犯下的过错,但是我没有办法弥补。”
“你到底在说什么?”我问道。
查理回头看着我,脸上痛苦的神情不是身体的病痛造成的。他的痛苦有另一个源头。“我是个杀人犯,约翰。三十五年前,我杀了一个人。”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勉强说出话。“你在开玩笑,对吧?”当然这个问题很蠢,查理甚至不屑于回答。
“你是我说出这件事的第一個人,但现在是时候告诉所有人了。德莱尼神父——”他的声音嘶哑了,“——简,孩子们。我早就应该告诉他们了。”
“发生了什么,查理?”我问道。我还是不相信他。我没法将查理想象成杀人犯。这样的形象就是没法成立。
他把头靠在身后的一堆枕头上,望着天花板上的某处。“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还在海军服役。当时我在圣迭戈东部的一个酒吧喝酒,因为一些原因——我不记得为什么了——这个人想找我干架。我那时是一个性格暴躁的野小子,所以我们就去了一条巷子打。”
我问:“这发生在那场斗殴中?”
“算不上斗殴。那个人块头和我差不多,甚至更高大,但他不是个打架的好手。”查理看着我,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我给了他几拳,他就重重倒下了,后脑勺猛地撞到地上。这本该就此打住,但我身体里的一些东西被点燃了,你知道吗?有一种——我不知道——一种怒火,燃遍了我。我停不下来。我打倒他,骑在他身上让拳头不停、不停、不停地落在他脸上。我恢复理智后开始逃跑,直到跑回船上我才停下来。第二天我听到收音机说这个人死了。”
“你被警察盘问了吗?”我问。
“没有,我不认识他。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甚至不记得这个争吵最初是怎样挑起的。我们在酒吧里好像只聊了十分钟左右,我估计没人注意到我们。那些日子圣迭戈很混乱,尤其是那个地段。几天后报纸报道了这件事,他的名字叫杜安·特拉戈维奇,是个彻头彻尾的罪犯,已经被捕好多次了,所以没什么调查。我觉得条子没把查清这家伙的死因看成紧急重要的事。”
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我试图忘记这件事,”查理终于说,“但是我做不到。也许特拉戈维奇是个罪犯,但他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什么,而我是个杀人犯。”
“报纸上说特拉戈维奇有个老婆,叫玛莉,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法从脑海中抹去她。我不仅对特拉戈维奇犯了罪,也对她犯了罪。直到我在圣迭戈没法继续待下去,我想如果我能离开那个地方,也许就可以将这件事抛在脑后,所以我自愿前往越南,在一艘巡逻艇上服役。”他看着我,眼睛湿润。“我没法不去想这件事,约
2
我避开高速公路,从使命湾绕远路回家,经过拉由拉市的太平洋海滩,飞驰过多利松的峭壁。持续的换挡、刹车、启动本应让我无暇思考,但即使我尽了最大努力,在驶下位于德尔马家中地下车库的斜坡时,脑海中仍旧思虑不断。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查理所交代任务的合适人选。我已经退出这个行业三年多了,不仅如此,因为这件事对查理很重要,我害怕我会让他失望。
我从车库的楼梯上楼,进入房间,将一张十字军乐队的旧CD丢进播放器,在玻璃杯中倒了一些白兰地,坐在电脑前。邮箱里还是一如既往的垃圾邮件,我把它们全部清理掉,然后上网搜索了“玛莉·特拉戈维奇”,一无所获。真的,对此我并不惊讶。这么多年过去了,就算她还活着,也很可能改嫁了。即便是现在,女人结婚后仍会冠夫姓,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间离婚率居高不下,她的姓有可能改了不止一次。
我离职时网络正进入寻常百姓家,所以我从未充分利用过它给私人调查者带来的便利。不过我知道我曾经的公司调查处广泛使用网络,并且他们拥有一些数据库的权限,而我并没有。办公室24小时有人手,所以我迅速发出一封邮件让他们帮我彻底检索一下。我喝到第三杯白兰地的时候,他们写信回复说什么都没找到。
捷径到此为止。
第二天我的早饭包含一个水煮蛋、两杯咖啡和四片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我前一晚多喝了几杯白兰地的代价。
我不确定我有足够的能力完成查理交代的任务,但我知道必须尽最大努力,我打給了阿尔·布鲁恩警官——一个在圣迭戈警察局的朋友。我们是同龄人,也在差不多的时间来圣迭戈混饭吃。我俩有多年的交情。
“该死,普莱,”他说,“我居然都不知道查理病了。”
“是啊,病来得很快。”我告诉了他三十五年前的这桩命案,没有提到和查理有关。他说他会派人去仓库的档案里搜寻一番,运气好的话,今天之内就能给我一份拷贝。
“你的传真号还是一样吗?”阿尔问。我说是的,然后我们就道别了。
我又喝了一杯咖啡,迅速冲了个澡,随后骑上摩托车往圣迭戈城驶去。那一年查理还是个年轻人,这座城市这些年变化很大。那些日子脱衣舞酒吧和宰客夜总会在百老汇大街边并排而立,穿着亮晶晶服装的滑头小子会站在这些营业场所前沿街物色他们想敲诈的水手。市政府成员在七八十年代肃清了这类现象,同时,和在所有美国的主要城市一样,这些骗子转行把精力放在了一种更精明的骗局上——对游客敲竹杠。
我骑车沿百老汇大街行驶,越向东边,街区就越破旧。这座城市在整治市中心上一掷千金,但明显有钱的大佬对城市边缘视而不见,这些地段发展得并不好。
昨晚我离开查理前,他多给了我一点信息。在凶杀发生的地方仍有一个酒吧。它处在街区中央,我快速掉了个头,把摩托车的后轮停到路边。这个地方叫“丝绸之帽休息厅”,在前门上方有一个没点亮的礼帽形霓虹灯——或许有些俗气,不过在这个更俗气的街区里仍是一个亮点。这个地方还没开门,但我透过窗户能看到一个女人站在吧台后数着酒瓶,并在一张纸上做着笔记。
我敲敲窗户来吸引她的注意,她喊道:“我们十一点开门。”
“我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不会耽误太久。”
她是一个看起来六十出头的红发女人,胸部像瓜一样饱满,尼龙上衣快被撑破了。很显然她看到我停下了哈雷戴维森摩托。“我不喜欢机车党,”她说,然后像赶苍蝇一样反手在空中挥了挥,“滚吧。”
我将手伸进牛仔裤的口袋掏出一些钞票,抽出一张二十美元对着平面玻璃晃了晃。我想安德鲁·杰克逊(第七任美国总统,二十美元上的肖像。——译注)在他的年代应该是一位杰出的公共演说家,因为如今钞票上的他也很有说服力。她盯着钱看了一会儿,把烟熄灭,绕着吧台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件紧身的、火烈鸟粉的长裤,腰肢纤细得出人意料。“给你一分钟问你想问的,”说着她打开了门,“二十美元就能买那么多。”
她伸手来拿钞票,但我缩回了手。“六十秒之后就是你的了,”我说,“假如你有东西卖的话。”
“你想要什么,机车男?”她带着尖酸的语气说出“机车男”三个字。
“信息,”我说,“这地方是你的吗?”
她看起来很警惕。“是啊,关你什么事?”
“你开了多久?”
“大概十五年。在那之前我在这儿干了八年。”
即便现在连耀眼的晨光都拯救不了她的面容,我敢说遥远的过去某些年里这个女人肯定充满魅力。
我问她从谁的手里买下了这家酒吧,她说了一个名字。“这家酒吧他只经营了几年。我买下酒吧时很划算,因为他急于出手。”她微微一笑,脸上的皱纹增加了三倍。“他遇到了酒吧行业的普遍问题。”
“嗯哼,是什么?”我问。
“他把挣的钱都拿去喝酒了。”她将手伸进裤子前的口袋,掏出一包一半被压扁的温斯顿香烟,用一只镶在镀铬支架中、边框是塑料翡翠的一次性打火机点了烟。“他从帕克·希斯的手中买下了这个酒吧。帕克经营它将近三十年,他从朝鲜回来后就盖了这个酒吧。”
她转眼看着那二十块钱。
“等等,”我说,“别那么着急,你还有十五秒呢。希斯先生在附近吗?”
“看情况。”
“让我猜猜。要看我为什么想知道,对吗?”
“你真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不是吗?”她看了我一眼,像是在说她以后不会再对骑摩托车的人另眼相待了。我想她这些年来对不少男人都用过这个伎俩。看我没有回答,她耸耸肩说:“我在帕克手下工作了很多年,我觉得随随便便帮谁逮到他不太好。”
“我只想要几个答案。”
她用嘴深吸了一口烟,从鼻腔送出。“二十块,”她挑明,“能买几个答案,地址要额外付费。”
我听见查理的时钟滴答作响,没有时间讨价还价。我掏出另外一张二十块,将两张钞票都递给她。她把钱和温斯顿一起塞进口袋,用两根手指夹起烟,指了指我左肩后的一个地方。我转过身,看见街对面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公寓楼,一个老男人在二楼窗边盯着我们,津津有味地大嚼着三明治。
帕克·希斯的房间有一股油炸香肠的味道。他让我进屋的时候,三明治只剩了一半,一坨蛋黄酱明显藐视地心引力,粘在他下巴的胡子茬儿上。我说我无意占用他太多时间,但需要为三十五年前发生的一些事逗留一会儿。听我这么说,他咧嘴一笑,暗示着自己享受谈论过去。
我跟着他穿过客厅,走进一个小厨房。他拿着三明治的手朝桌边两把塑料包裹的铝制椅子中的一把摆了摆,“请坐。”我拉开一把椅子坐下。“你很幸运。”他说着看向桌边爬着苍蝇的窗户。从他那里看向百老汇大街另一边的酒吧视角极佳。“很少有家伙能穿着裤子从艾琳那儿逃出来。”听他迸发出老年人尖锐的笑声,我忍不住笑了笑。
“看起来她在风华正茂的年纪是只母老虎。”我认同道。
“很多年前她就不再风华正茂了,但她依旧是只母老虎。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关于艾琳的传说,我可以的。”他拿起盘子旁的玻璃杯,喝下一大口牛奶。“想来点牛奶吗?”他问。
“不了,谢谢。”我用拇指指了指大街。“艾琳说这酒吧以前是你的。”
“是我的。在1953年的夏天我亲手盖起来的。”他用指关节敲了敲自己的右太阳穴。“因为一枚手榴弹,部队不得不在我脑袋里植入了一块钢板。我当时已经出院六个月了,但每次爬那个该死的梯子时还会头晕目眩。”他朝下望了一眼酒吧。“不过我还是把它建起来了,”他说,“我做到了。”他伸出一只灰白的手擦掉下巴上的蛋黄酱,嘬进嘴里。“1982年的时候卖出去了,但我搬到这里,好随时看看它。”他伤感地凝视着窗外,“老习惯很难改掉,我猜。”
“希斯先生,你还记得有一次,在60年代末有一个叫特拉戈维奇的男人在酒吧外被人杀了吗?”
“当然,我记得。”
“关于那件事你能告诉我些什么吗?”
他摇了摇头。“没有什么可说的,真的。特拉戈维奇只不过是一个经常在附近鬼混的小矮子,仅此而已。我一直不喜欢他。没人喜欢他。”
“你还记得在命案那晚见到他是什么情况吗?”
“天哪,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把最后一点香肠三明治一下塞进嘴里,丝毫没有放慢语速,“我大概只记得有人发现了尸体,救护车到的时候,顾客一窝蜂跑出去看他被装进车里。那大概是在打烊前的一个钟头。救护车刚走,大家就一股脑回来了。我那晚最后一个小时卖出的酒,比之前或之后任何一个小时都要多。死亡让人觉得口渴。”
“你能回想起那晚特拉戈維奇有和任何人交谈吗——也许他卷入了与一个水手的某种争辩?”
他把小拇指伸进耳朵,然后仔细观察掏出来的玩意儿。“我记得条子们第二天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一些在街角分享同一瓶酒的酒鬼说,他们看见一个水手在酒吧后的巷子里把一个家伙痛扁了一顿。但是,不,我一直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时不时就会有人打架。那只是这一行的常态。见鬼,很多水手进进出出,尤其是当时有和越南的那档子事。”
“据我所知特拉戈维奇结婚了。”
“是啊,他结婚了。他老婆有时候也来,不过不经常来。她还不到能喝酒的年龄,那其实正好。我敢肯定,特拉戈维奇是那种有一点钱就去喝酒的人。我不太记得她,只记得她是个小个子。挺漂亮,我觉得,但是胆小。”
“她后来怎么样了?你知道吗?”
他缓缓摇了摇头。“我不知道。”然后又凝视着窗外,“她只是众多来来往往的人中的一个。”一丝忧郁爬上了这位老人的眉梢。“这些年来我认识了成千上万的人,”他说,“成千上万的人。”过了一会,他清了清嗓子,转头看向我,皱着眉头补充道:“我甚至都不记得她的名字了。”
“玛莉。”我说。
“是那个名字吗?见鬼,你可能在糊弄我。不过我的确记得她几个哥哥有段时间是那里的常客。根据我的回忆,也是讨人喜欢的家伙。”
“你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他挠了挠军队给他植入钢板的地方。“小子,”他说,“你让我捡陈芝麻烂谷子,是吗?”
“任何你能记起来的事都会有帮助。”
他沉思了一会儿,嘴角折出一个笑容。“阿伯特和科斯特洛。”他说。
“阿伯特和科斯特洛。”
“对,大家过去都那么叫,因为他们的真名
是巴德和路易斯(巴德 · 阿伯特,路易斯 · 科斯特洛,美国喜剧片《两傻查案记》中两位男主演的名字。——译注),懂了吗?阿伯特和科斯特洛。”
我点点头。“当然,明白了。那个很老的喜剧组合。你记得他们姓什么吗?”
“姓什么,哈?现在加大难度了,是吗?”他停了很久,然后狡黠地看着我。我把手伸进口袋找另一张二十块钞票,这对付街对面的艾琳很管用。但在我掏出钱之前,希斯笑着说:“我不想要你的钱。”然后他告诉了我,此时我才意识到停顿只是一个老酒保制造悬念的小把戏。过去这些年,他和成千上万的人闲聊过,知道怎样让对话变得有意思。“比克曼,”他说,“巴德·比克曼和路易斯·比克曼。如果不介意我问问,你为什么要费劲深挖到那么久以前?”
我耸耸肩。“只是尽力给一个朋友帮忙。”
“一个朋友,”他点点头,“那很好。”
虽然这个老头的一些话说不通,但很明显他把知道的全都告诉了我。即使这样,我还是得问。“你还记得其他什么事吗?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找到玛莉。”
“找到她,哈?我估摸三十五年过去了,早就杳无音信了。”
“是啊,”我应和着他,“是这样。”
“我没什么能告诉你的了,”他说,“人们来了又走,事情就是那样,你再也不会见到他们。”
我从桌边推开椅子站起身来。“很好,多谢了。希斯先生,你帮了我大忙,我很感激。”
“他们来了又走。他们就是那样——来了又走。”
我独自走出去,就在关上公寓门以前,我再次感谢了他,虽然我认为他没有听见。他没有回应,只是坐在那里喝着牛奶,出神地望着窗外的“丝绸之帽休息厅”。
我用手机打给人名地址查询服务处。在埃尔卡洪市的名单上有一个名叫路易斯·比克曼的人。我拿到了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但我决定不打电话,而是亲自骑车过去。我发动哈雷摩托,找到了通往高速公路的路,然后向东驶去。
比克曼的住宅在城市近郊,很小却整潔。在我按门铃的时候,我感觉可以听到家中某个地方发出了电视比赛的声音,但是没有人来开门,于是我写了一张便条,说,如果住在这里的路易斯·比克曼家中有一位名叫玛莉的妹妹,请给我打电话。我说我想和她谈论一下她丈夫杜安·特拉戈维奇的死。我留下了我的名字、住址和电话号码。我在便条结尾写道:“情况紧急,我要立刻和特拉戈维奇夫人说话,请尽快回电。”
我把便条塞进比克曼的信箱,骑上摩托车回家。
把摩托车的钥匙丢在电脑桌上时,我注意到了阿尔·布鲁恩的传真。一共有六页纸,我可以辨认出它们原本是用手动打字机打出来的。一些字母颜色更深或是比同一排上的其他字母略高一些。这是一个令人怀念的、不那么矫揉造作的时代的印记。答录机上的指示灯不停闪烁,我按下了“播放”,在倒带的时候,我快速浏览了这份三十五年前关于杜安·特拉戈维奇命案的档案。
“普莱,”答录机的喇叭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我是阿尔。我刚把我们手头关于你所询问案件的文件都传真了过去。你可以从报告上看到,其实没多少东西。一个酒吧的顾客叫来了救护车,但他们到的时候这个家伙已经死了。好几个酒鬼说那晚早些时候看见一个水手在揍某个人。穿制服的伙计们问询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酒鬼,但没得到太多线索。刑事侦探第二天就此事在街区附近问了一些问题,也没有什么头绪。特拉戈维奇有一个妻子,很年轻,当时只有十七岁,显然在她丈夫的死上非常歇斯底里。当然,他们也问她话了,但是从她那儿同样没得到什么东西。她说据她所知,她和丈夫都不认识什么水手。这个案子一直没有结,但也没什么进展,看起来他们对此并未多做些什么。我同时发过去了一份特拉戈维奇的犯罪记录。从记录上你能看出来他肯定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痞子。我想那些调查这个案件的家伙对他很熟悉,他们好像没有拼了命查这个案件。我还发过去了他的尸检报告。不出所料,死亡原因是颅骨破裂。
“我知道的东西不多,但这是我们手头的所有资料。如果你需要别的东西就给我打电话好了。还有,告诉查理我们都祝愿他好起来。”机器跳到了停止键。
我把阿尔发的传真拿到外面可以眺望海滩的桌子上。我倒进椅子里,用脚脱掉靴子,把脚搭在扶手上。读那点东西所花时间不长,但读完后我掌心冒汗,如鲠在喉。
我把这些纸摊在腿上,望着大海。海面上有一个不怕死的年轻人在冲浪板上尽力冲破一个蹒跚涌向海岸的浪花。他的体形真的非常小——渺小。冲浪板对他来说太大了,他毫无运气,只能不断努力。我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拿起文件重读了一遍特拉戈维奇尸检报告上对死者的描述。
那晚我等路易斯·比克曼打来电话等到六点。我把座机转接到手机上,以防他在我外出时打来,然后我返回埃尔卡洪市。我把摩托车停在比克曼住宅前,朝有些破裂的门前小径走去。停车位上有一辆皮卡车,我能从房屋正面打开的成排的窗户里听见声音。他们一定听到了我踏上三级台阶到了小小的门廊,因为声音戛然而止,我正要抬手去按门铃,一个高大的男人来应门了。
“你想干吗?”他问。他的肩膀又宽又壮,脖子和我的大腿一样粗。
我听见一个柔弱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是他,对吧,路易斯?”
“没事,”这个男人回过头说,“我来解决。”他至少比身高六尺一寸的我高两英寸,而且肯定比我重六十磅以上。“先生,你在想什么呢?”他问我。
“我是约翰·普莱尔,”我说,“我是今天下午在你家信箱里留下便条的人。我在找一个名叫玛莉·特拉戈维奇的女人。”我不敢肯定这就是我要找的人,但我打算虚张声势。“我知道你是她的哥哥,比克曼先生。我想和她谈谈上世纪60年代她丈夫的死。”从他脸上袭来的表情我断定自己找对了人。“我无意伤害你或你的家人。我只是需要找到你的妹妹,仅此而已。”
那个声音又响起了。“求你了,路易斯,让他进来。”
他转身侧向玄关的一边,我有机会看到他身后的女人。如果她是我认为的那个人,她不会超过五十二岁,但她看起来还要老十岁。她既瘦弱又娇小,双手靠在一个铝制的助行架上。“你要相信我,”比克曼说,“这是个糟糕的主意。”
她语气平和,带着无奈。“你一直都是个好哥哥,路易斯,但是,请你,就让他进来吧。”
比克曼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往回退了退,我走了进去。
“请坐。”这个女人说。她指了指房间对面的一个长沙发,我在那里坐下。她穿着绒布浴袍,把它在自己矮小的身体上又裹紧了些。她摸着自己柔顺的头发说:“我的背有问题。有时比其他问题更糟。”我把这看作她外貌苍老的原因。“最近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她把自己安置在沙发对面的一把椅子上,补充道。比克曼继续站在前门口,两只巨大的手臂交叉放在胸前。
“你的名字是玛莉,对吗?”
她紧紧握着浴袍的翻领,关节都泛白了。“是。”她说。
“你还姓特拉戈维奇吗?”我问。
“是,”她又说,“杜安死后我没有再婚。”
我朝房间对面的比克曼看了一眼。“巴德呢?”我问。
“我们没必要和这个人说什么,玛莉。”
“我知道,但是没关系。巴德1983年死于心脏病,”她说,“你为什么来这里,普莱尔先生?你想要什么?”
“我不想伤害你,特拉戈维奇夫人。如果不是为了一个朋友,我根本不会出现在这里。我认为我知道了你的丈夫怎么了,至少,知道了一部分。”
“过了太久了,”她说,“感觉像过了一辈子。”
我等她继续说下去,她没有再说话。我说:“和杜安·特拉戈维奇生活在一起很艰难,是吗?”
她没有说话,只是很快点了点头。
“他以前经常伤害你。”
“是的。”她喃喃道。
“我看了他的记录,特拉戈维奇夫人。他因为暴打你被起诉了十几次。两度因此入狱,但他没有住手,是吗?”
她摇了摇头。
“最后他因為太频繁地打你,你或是你的哥哥杀了他。”
比克曼放下了双臂,走到房间中央。“玛莉,你没必要跟他聊。你没必要告诉他任何事。”他转身朝着我向沙发走来,低下头说,“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居然敢这样来这里。”
“我不是警察,比克曼先生,我也没打算去报警。我是为了朋友来这里,仅此而已。我读了那些报告,特拉戈维奇夫人,我认为那时你的丈夫不是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在‘丝绸之帽休息厅背后的小巷里被杀害。我认为他是被你的哥哥抛尸在那里的。”我看着比克曼说,“巴德有多高,比克曼先生?”
他迟疑了一会儿,最终回答道:“我不知道。五英尺八英寸,五英尺九英寸的样子。一百七十五磅。”
我点点头。“我相信你和你的兄弟想甩掉警察。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你们当中的一个——我认为是你,比克曼先生——与一个醉酒的年轻水手挑起了打斗。你希望这场斗殴被人看见,同时你也知道谁将会看见,所以你相信他们没办法给警察一个非常好的案发描述。”
这个大块头沉默地站在那儿,低头看着我,瞪大双眼,连眨都不眨一下。
“你挑起了斗殴,比克曼先生,但是你从未打算打赢他。你只是希望那群酒鬼看见有人在巷子里被放倒,这样,特拉戈维奇的尸体被发现时,警察就会搜捕一个水手。”
“你不可能知道那些。”比克曼说,但他说得很轻,没有力气。
“和你打架的那个水手是我的朋友。他向我解释说那晚和他打架的人块头很大,但是根据那时候开‘丝绸之帽休息厅的家伙说,杜安·特拉戈维奇是个小矮子。尸检报告上写他身高五英尺四英寸,体重一百四十磅。我朋友说那晚他不停地打那人的脸,但是特拉戈维奇的面部没有任何创伤。唯一的伤口在颅骨后侧,好像他的头在打斗中砸到了路上一样,或者——”我看向玛莉·特拉戈维奇,“——也许有人用什么东西从后面击中了他。”
“他只是在猜,玛莉。”比克曼说。
玛莉低语道:“不过,他猜得很准,对吗,路易斯?”她说到这里时,一股气从这个高大的男人身上溜走了。他瘫坐在沙发上。我们三个人沉默了很久。
比克曼打破了沉默。“好吧,聪明人,”他说,“我杀了那个狗娘养的。你猜出来了。真不错。”
“噢,别,路易斯,”玛莉说,“别说了。你和巴德一辈子都在照顾我,哪怕到了要你们牺牲自己生活的地步,但我是时候面对所发生的事了。”她转向我。“我的哥哥会为我做任何事,普莱尔先生。他们一心扑在我身上。他们会很乐意杀了杜安——巴德甚至威胁了不止一次——但是他们没有。是我杀了他。我当时才十七岁,但每次我一动,都会因为杜安的暴打疼痛不已。他会打我背上一小块特别痛的地方,但那里的伤痕不会显露出来。最后一次尤为严重,我至今没有恢复过来。因为那次挨打我这些年来都与阵痛做伴。但那也是他最后一次打我,普莱尔先生。杜安转过身去,我从厨房灶台上抄起一只平底炖锅砸向他。我就砸了他一次,但我砸得够狠。我意识到他死了,就给哥哥打了电话。他们说他们会处理好,也这么做了。他们料理好了这件事,从此之后一直照顾着我的生活。”她向哥哥伸出小手,把手搭在哥哥粗壮的前臂上。“一个人去世了以后,”她继续说,“另一个人就独自照顾我。”
我点点头,露出了微笑,希望向他们表示我十分理解。
比克曼用粗大的手指向后理了理头发问:“你想干什么?”
听到他这么问,我向他的妹妹解释了我需要她做什么。
3
比克曼不得不把玛莉扛到查理的房间。这些年里她已经做了三次背部手术,对她来说上楼梯是不可能的。她生活在阵痛之中,但她和哥哥都认同她至今还能走路简直是一个奇迹。我们一到门廊,比克曼就把她放了下来。
“让我先进去,”简妮说,“我会告诉他你来了,普莱,还有你要见他。”简脸上的浮肿甚至比那晚还严重,她敲了一下门就走了进去。
“现在,我必须独自做这件事,路易斯,”玛莉说,“不要担心,你和撒切尔夫人一起等。我不会有事的。”比克曼看起来对此仍然很抗拒,但显然他愿意顺从妹妹。
简妮再次出来的时候,她当着我们的面大哭起来。我猜她不再向查理隐藏她的眼泪了。“别太久,普莱。他今天的状况急转直下。”
我点了点头,她和比克曼走下楼梯。我面向玛莉。“你准备好了吗?”我问她。
“好了。”她说。她看起来的确准备好了,甚至很急切。
我把手放在门上,在推开门以前,我说:“这对查理来说将意味着一切。”
一缕微笑牵动了她的嘴唇。“真有意思,是吧?他将要向我告白真相,但事实是,真相正好相反。”
“我想谢谢你。他一辈子都对这件事心怀愧疚。”
玛莉的双眼噙满泪水。“愧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她说,“相信我,普莱尔先生,我知道。”
(郑洁晏紫:上海外国语大学,邮编:201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