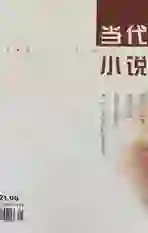隐秘角落的感官书写
2021-05-27周子敬
周子敬
在埃德蒙·伯克看来,“美是身体的某种品质,借由感官的介入而机械地作用于心灵”。可见,人的审美反应与审美心理同感官有着密切联系。优秀的文艺作品总能通过独特的视角、敏感的观察、准确的传导来调动起人们丰富的感官体验,使人产生微妙而奇异的心灵震颤。在下文所观照的小说中,既有五感知觉的充分觉醒,也有濒死体验的深度沉浸;既有对生活本相的感受,也有对历史底片的发现。最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潜入参差多态的世相之下,走进人生、社会与历史的隐秘处,将那些角落里的人与事娓娓道来。这些故事题材舛殊、风格迥异,紧贴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脉搏,抚触形形色色人物生存、生活与生命的肌理,引领我们进入一个个光怪陆离而又真实立体的感官世界。
王苏辛《火兽》(《青年文学》2021年第3期)的故事背景是一座正在“下沉”中小城——云城。这座城市就像一座常年燥热的火炉,流金铄石,浮尘漫天。故事从主人公林莫可找到小说家倾吐回忆开始,掉入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叙事回环:在这个故事中,叙事者频繁转换,叙述的片断也随之跳跃或闪回。现实与回忆、真实与想象、历史与当下在不同叙事者的口吻中狂乱而恣肆地勾连、交缠,汇成了一条在语言地表以下暗自汹涌的巨流。小说中,感官体验被放大到了极致:酷热的气味,燃烧的气味,腐朽的气味,焦土烟烬的气味……故事仿佛从始至终被烟与火的气味笼罩——混沌,浓烈,刺鼻,催化出诡谲奇肆的美学氛围。可以说,整篇小说就是感官知觉的一次大爆发:作家的笔下不仅是一个“火”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感受力空前敏锐的感官世界。“火”是生的附属,也是死的诱引;是情感的迸发,也是欲望的毁灭。《火兽》告诉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火种,或许是一种原始而野性的激情,或许是一种隐秘而涌动的渴望,它以铺天盖地的汹汹来势席卷每一块枯瘠的土地,并留下“悬浮大地上空”而永不坠落的浮灰。小说通过“盗梦空间”式的环扣叙述法,艺术化地再现了人与“火”共存、与“火”抗争、与“火”同构的精神历程。
赵仁庆《香气扑鼻》(《北京文学》2021年第2期)从主人公闻到一股香水味开始,又以香水作结,百般况味,尽在其中。主人公酒后偶然与昔日学生林小红相遇,此时的林小红已是一名美艳少妇,却对“我”这个年逾五十的中年人殷勤有加,不免令“我”生疑。原来,她是某“大号首长”的小妻,担心“首长”早晚出事,便与“我”密谋转移财产。正当“我”以为计划进展顺利时,“我”听闻消息:“首长”没倒,林小红自己却因诬陷罪进去了,自尽身亡。得知她的死讯,“我”怅然若失,不禁又回想起了初见时的香水。小说叙事節奏稳健,生活气息浓郁,转捩之中更寓人生情味。小说中的林小红,是一个试图把控命运却终被命运玩弄的悲剧女性。她有世故与圆滑的一面,深知如何利用自己与生俱来的“武器”达到目的;但实际上,她相当单纯、天真、自信以至自负。自以为占据主动权的她,最终还是没能全身而退,甚至连“鱼死网破”的结局都不过是她一厢情愿的妄想。这一生,林小红“赌”输了;而对于“我”来说,这不过是生活中的一道波折。那叫不上名字的香水味,就成为了她来过这世上、与“我”相识相处过的唯一凭据——优雅、热情、梦幻,又像风中飘零的花瓣一样短暂易逝。小说结尾令人唏嘘,余味深沉,通过香水的隐喻引发读者对当代女性生存处境与社会独立问题的种种联想与思考,富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李师江《老骨头》(《福建文学》2021年第3期)讲述了一个独居老太在家不慎跌倒,在地上艰难求生的故事。范桂凤是个退休教师,她一生最投入的事业就是规划子女的人生。儿子米书华想要回乡创业,被她一口否决。于是,米书华背着母亲偷偷回到家乡,与朋友共谋事业。一日凌晨,范桂凤在家中重重地摔了下去,四肢动弹不得。此时,与她同处一城的米书华却对母亲所处的危境浑然不知,一心惦记创业。在饥饿、寒冷与疼痛之中,范桂凤一次次陷入绝望,又一次次燃起信念。过往的记忆一幕幕浮现在她的眼前,死神不紧不慢地在她孱弱无力的躯体旁踌躇往复……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对主人公内心情态及其细微变化的描写尤为出彩。作家着力展现范桂凤在求生中的种种知觉、痛觉与幻觉,通过类意识流的手法,将这个痛苦的历程写得既扣人心弦,又相当真实、细腻。经历了这一遭濒死体验,古稀之年的范桂凤仿佛重新过了一遍人生,也完成了真正意义上“对人生的发现”。作品表面上是探讨代际隔阂与独居老人的社会问题,实际上关切与省思的是人的“活法”:每一代人都面临人生的困境与岔路,都要择一“活法”;而怎么活、活得怎么样,全由自己决定。没有设定好的人生,更没有完满的人生。意识到这一点的范桂凤,终而用尽全部力气在地上写下了“自由”。这两个字,正是她站在死亡边缘回望半生坎坷后酝酿成熟的答案。
李杰《独肾女人》(《四川文学》2021年第2期)同样是个关于痛觉的故事。女人生来只有一个肾,为了给男人生二胎罹患尿毒症,只能靠透析过活。男人跟一个“小妖精”搭伙过日子,剩下她一人拉扯子女。她认了命,但,生活还得继续。于是,她周旋在男人和“小妖精”之间,维持着一层脆弱的关系。她整日盼着用拆迁款换肾,可房子没划在拆迁范围内,希望化为泡影。此时,男人还要求她出去住,给怀孕的“小妖精”腾地方。这天,正当她准备搬走时,她突然倒下,身体抽搐,满口血沫……小说剖开社会底层残酷的世相,塑造了一个长期受病痛折磨却隐忍单纯的女性。“五年了,17G的穿刺针雷打不动,一周两次地在此剪径筑寨,长期开合,进针的口子便不再痊愈,肥大增生,鼓起紫乌的肉瘤,像一粒粒半熟的桑葚。”然而,她从不咀嚼自己的苦难,只是咬着牙接受命运给予她的每一次阵痛。小说的成功之处,是没有将她塑造成一个饱受苦难的“病人”,而是将其还原为一个要生存、要生活的“人”。这不是一个人们喜闻乐见的“伟大的母亲”或“坚韧的女性”,她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女人。她有实实在在的痛觉,尽管这种痛觉已被生活磨去了棱角;她心中所想的,是远比“感受疼痛”分量更重的事情。小说在驳杂世相中呈现出一抹现实的血色,不仅展现了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之痛,更揭示了“人”作为一种原型最为刻骨的痛苦。
黄孝阳《县城报告》(《雨花》2021年第2期)由三篇独立的短篇小说组成,聚焦县城与农村里的人与事,其中《马胖》一篇尤具特色。招娣高二辍学,跟了一个叫猴子的混混,无论受其怎样的虐待,仍不离不弃。猴子与当地一个凶神恶煞的马胖斗殴,招娣操起锄头敲坏了马胖的脑袋。从此,马胖变成了一个傻子,只会画画;奇怪的是,画的都是招娣的脸。于是,街头巷尾都是各式各样的招娣,招娣本人也知道了这么一个“白痴天才”。几年后,人们竟发现:招娣嫁给了马胖,两人开了家饭馆,日子平淡美满。小说将县城里的奇人异事写得格外真实、生动,如同一部反映县城生活的微型纪录片。黄孝阳曾说:“追忆只是一个维度。县城倒更可能保留了更多关于人的本真与传奇。”在黄孝阳的笔下,县城的色彩、线条、气味、质感,甚至是某种氤氲的情绪,都被十分精准地捕捉与复现。这是一座可看、可听、可触摸的县城,它对于每个读者来说,都是立体可感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小县城里也有大人生——数不尽的故事在这方舞台上上演,说不尽的人情在这座熔炉里沸涌。它们深藏在县城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兀自诉说着人世间的纷纭与沧桑。在《县城报告》系列作品中,黄孝阳为当代中国城镇化進程下的小人物进行速写,以独到的观察力、共情力与表现力,唤起了我们对县城这一庞大叙事空间的关注与想象。
余一鸣《湖与元气连》(《人民文学》2021年第3期)则是对民间历史的一种独特感知。小说双线并行,一条线写王三月到上元村担任村书记的见闻与经历,一条线写解放前三湖县的历史与往事:当年,上元村与魏村不顾水利教授陈大先的反对,坚持筑圩围垦;几十年后的今天,上元村的防汛形势空前严峻,水位不断上涨,终致溃坝破圩。万幸的是,洪水并未给当地村民带来重大损失。亲历此次抗洪后,王三月对当地的民风民情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也有了新的思考。小说指出了退耕还湖、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但并非刻板说教,而是以人物为串联,在民间历史的底片与乡土生活的日常中发掘人性的光点:水利系毕业的高材生陈大先出于公心反对两村筑圩,遭遇不测;种子站退休的技术员陈玉田在外人眼里疯疯癫癫,却以超常毅力苦寻几近消迹的野稻;原村主任刘四龙在洪水袭来时不顾个人安危,舍己救人,不幸牺牲。他们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们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甘愿付出,各自坚守。正是这些平凡的人们,构成了历史的主体。作家以其独特的历史感知,深入民间历史的表里,挖掘历史缝隙处的故事,并将这片土地上独特的民风、民俗展现得淋漓尽致。“湖与元气连,烟波浩难止”,这是古人对丹阳湖的高妙叹咏,也是今人对生态建设的殷切期待——待洪水退去,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余波也随之平复,一幅美丽和谐的乡村画卷在人们的诗意想象中缓缓展开。
本栏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