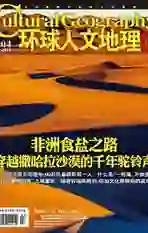桃花水来了
2021-05-26龚静染
龚静染
一、
阳春三月,开车走在岷江边上。
天气很好,阳光高照,车子缓缓地开着,在过一座大桥时,朋友突然说了一句:“桃花水就要来了!”我转头去看桥下的岷江,还是断流的样子,有些地方露出了滩涂,河面一片萧索,好像还未完全走出冬天的景象。但他这句话戳了我一下,心里猛地一缩。是的,只要后面的日子来一场大雨,河就又会涨水了。
人们把开春后第一场雨带来的涨水称为桃花水。
一年之计在于春,岷江好像也不例外,桃花水的到来预示着冬天的过去,一个生机勃勃的江河即将出现在人们眼前。不知道现在民间还有没有相关的祭祀活动,但桃花水在人们的心里一定是带有仪式感的,它让河里的鱼虾、船只和人们的生计都具有焕然一新的寓意。而正是朋友的这句话,让我从桥上俯瞰岷江的同时,思绪已经沿着岷江飞得很远……
桃花水,也叫桃华水,桃花水来临就叫桃汛。古人把不同时节出现的涨水分为凌汛、桃汛、伏汛、秋汛等,《礼记·月令》中说:“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唐初的学问大家颜师古解释道:“盖桃方华时,既有雨水,川谷冰泮,众流猥集,波澜盛长,故谓之桃华水耳。” 河流是大地上的一棵巨树,“波澜盛长”,犹如蓬勃生长的植物,这是从天空的视角才能看到的意象。
过去,在春汛来临期间,岷江流经的地方都会举行一些与河水相关的仪式。如在都江堰,每年清明这天都要举行隆重的放水仪式;清朝时期,每年农历三月底各地官员都要亲赴灌县,饬令成都水利同知开堰放水。但要是遇到这年雨水不丰,百姓就得去请愿,“如水来甚缓,或发水不足,则乡民千百成群,赴道台衙门,击鼓求水。”(傅崇矩《成都通览》)这个场面非常震撼,鼓声雷动,群情激昂。
二、
车继续沿着江边开。朋友是个钓鱼迷,有空闲就会去河边塘前钓鱼,桃花水一来,他又得忙上一阵了。在车上的时候,他不断给我讲他钓鱼的故事,但像他这样有钓鱼爱好的人毕竟只是少数,现在人们的生活与自然实际上有隔膜,就在他说得津津有味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个人与江河的联系只剩下一根鱼竿了。
都江堰放水时,真是壮观之极。记得有一年,我站在都江堰宝瓶口下的一座小桥上。只见下面清浪翻滚,如一匹柔滑的巨幅绸缎,扬起阵阵凉风,有种说不出的快意。一种奔流的水声,朝着远方而去。岷江水就这样进入到广阔的成都平原,我想那些干涸土地上的禾苗在灌溉下,一定会发出“咕咕咕”的吃水声,农人一年的期盼就是从这股水开始。
四川岷江水系沿岸,每年桃花水来临,河水一涨,就要忙碌开堰的事,这几乎要涉及每一段江、每一条渠、每一道堰,而一年的盛事就源于这开年之后的桃花水。
兴修水利一般会在桃花水来临之前。桃花水一到,人们就得抓紧时间在汛期来临前做好一切准备,对河道、沟渠、堰塘加以疏浚淘挖,以免带来堵塞的后患,《汉书·沟洫志》中说:“来春桃华水盛,必羡溢,有填淤反壤之害。”
小修堰,大修堤,古代官吏以修出政绩。四川乐山是个古城,三江合围,水常有冲堤之患,“洋雅徒岸,坏民之所,为患甚矣。”古嘉州城苦于年年为水所困,岁岁修修补补,人们总是想要找出一个长治久安的办法。明成化九年(1473年),嘉定知州魏孔渊进行了一次大修,调用民工数千人,在大渡河与青衣江汇合的下游处修堤,这在当时是个巨大的工程。魏孔渊为此动了不少的脑筋,他调用了“县之讼狱者”,又“下铜山之木,琢濒江之石”,最后修了一道“广一丈有奇,高四仞,长三百九十八丈”的长堤,人们将之称为“魏公堤”。而它就是治水的功绩,自古为政者皆以水事为重。
桃花水也带来了河运的旺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白秋练》中写道:“至次年桃花水溢,他货未至,舟中物当百倍于原直也。”也就是说,河水上涨后,船的运载量也随之上升,运送物资的能量增大,这在以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意义重大。
三、
桃花水主要影响的还是农事。在中国,农耕为本,农业的产出与水利紧密相连,而广大乡村中随处可见的渠塘是最能反映这一关系的景象。每年春天一到,河水初涨,很快会进入到如毛细血管一样密布的渠堰之中,而这些“毛细血管”是否畅通,能否让上下游同享水源,就要看沟堰是否通畅。
过去,四川农村的水车随处可见,一架筒车可送水数里,脚踏翻动,几百亩田得以润泽。但水车的拥有情况常常与庄户人家的经济收入水平相关,大户人家田多,可以自置水车,小户人家田少,一般是与邻家合修。家家户户都要用水,便构成了一道“通堰大局”,如果说阡陌纵横的乡村有一种复杂而又井然有序的关系,那么渠塘就是最直观的呈现。
筑塘引水的活儿始于冬闲时,以免于春耕时缺水。筑堰开塘除了灌溉,往往还有副业之惠,塘内可种菱养鱼,坎上可蓄竹栽树,实为乡村田园的一道风景。范成大就曾经在《吴船录》中描绘了一番春季“连日得雨”后的景象,透出一种丰收在望的喜悦之气:
西行秦岷山道中,流渠汤汤,声震四野,新秧勃然郁茂。前两旬大旱,种几不入土,临行,连日得雨。道见田翁,欣然曰:“今岁又熟矣。”
“流渠汤汤,声震四野”,这是多美的乡村啊!记得过去每次坐车走旧道从成都到眉山,经过新津时就会看到岷江上非常有名的唐代古堰——通济堰。它是仅次于都江堰的又一岷江灌溉体系,表面上看来却很平常,并无特别之处,但内里的学问可不少。比如在古法制堰中如何筑堤拦水、如何筒口分水、如何加淘堰沟、如何安设筒车、如何岁修摊派等等,都体现了古人的智慧。通济堰有千年以上的修堰史,至今还灌溉着50万亩良田,这一带岷江边还有蟆颐堰、鸿化堰,均为唐代古堰,可见古代水利工程之发达,沿岸还有成百上千的大小堰渠,蜀地桑麻为之所系。堰是水利之钥,也可以说是乡村之钥,它们其实是在牢牢地锁住我们的土地,不让田禾的膏腴流失。
过去,农村的孩子有不少是在堰塘里学会游泳的。芦苇深处,荷叶瓣下,水中还有老牛、鸭鹅相伴,堰塘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乡村記忆的一部分。岷江蓄满了大大小小的沟渠堰塘,桃花水也流过了那个漫长的农耕时代。
“桃花水就要来了”,我们的车已经开得很远。
桃花水,也叫桃华水,桃花水来临就叫桃汛。古人把不同时节出现的涨水分为凌汛、桃汛、伏汛、秋汛等,《礼记·月令》中说:“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唐初的学问大家颜师古解释道:“盖桃方华时,既有雨水,川谷冰泮,众流猥集,波澜盛长,故谓之桃华水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