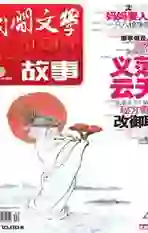小河南记事
2021-05-25丁秀红
丁秀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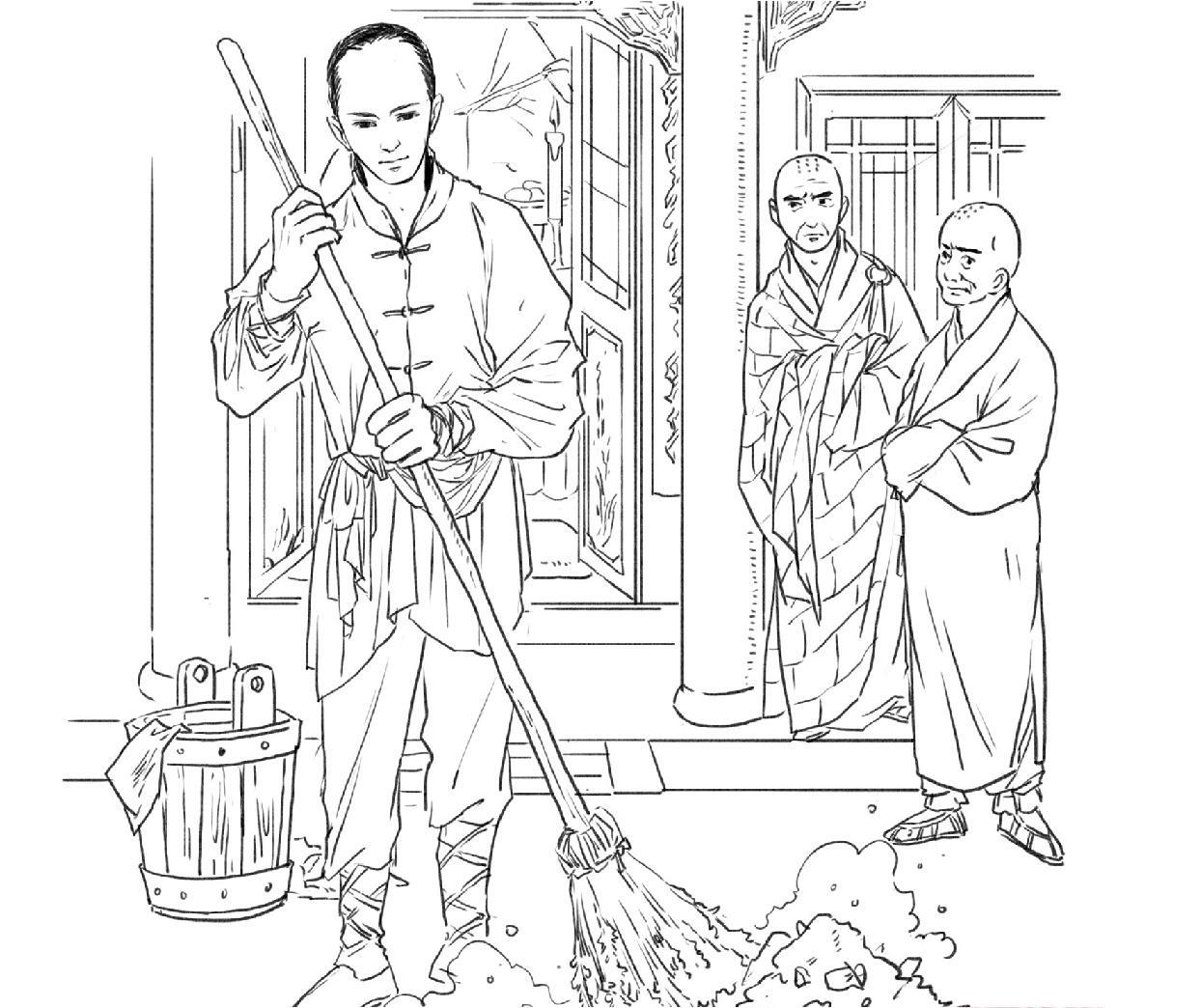
早先,在诸城西南方枳镇潍河北岸,有个上清观,此观坐北朝南,占地二十多亩,能容纳几百人。乾隆年间,偌大的道观,仅有几个道士支撑着。当家住持姓林,八十多岁了,银须飘飘,精神矍铄,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人们都称他为林道爷。
上清观周围的几十亩地是道观产业,林道爷领着徒儿留下几亩自种自收,其余租给周围农户,收点租子用于道观修缮。林道爷在观里的西厢三间小屋开了一个“来鹤轩”学馆。附近村里的小孩儿谁愿意来念书,老道爷就教他们念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学费没有硬性规定,学生家长看着尽心给点粮食就行。家境富裕点儿的几斗不嫌多,手头拮据的一升不嫌少。实在是家中穷得揭不开锅,孩子又喜欢读书,不但免费,晌午头儿还管一顿饭。老道爷认真教,孩子们认真学,有些成了童生,还有的考中了举人。
林道爷还懂得医术,悬壶济世,有求必应,救人无数。大家都把林道爷和他的弟子们看成是自个儿的家里人,有什么好吃的好用的都分给他们。
这年春上,一天吃过早饭,孩子们像往常一样到上清观跟道爷师傅学习,没过多久,就惊慌失措地跑回了家。他们说道观里没看到道爷和他的徒弟,有两个把门的光头和尚不让孩子们进门。家长不信,便到道观去看个究竟。这一看不要紧,可就发现了大问题。就见观门大开,从里到外张灯结彩。一队身穿袈裟、手敲法器的和尚从院里走了出来。他们摘下了“上清观”的招牌,换成了“上清寺”的大匾。
这不伦不类的门头,让明白人觉得蹊跷。“上清”属道家的名讳专用,而“寺”是佛家专属。这几十个身披袈裟的光头和尚怎么会连最起码的当家规矩都搞不清?大家感觉太蹊跷了,就想到里面看个究竟,却被把门的和尚以里面正在举行隆重法事为由给拦住了。人们说要来请教林道爷,和尚没好气地说:“老道把道观转让给我们了,这里已经没什么林道爷了。赶紧走开!”
林道爷和他的徒弟们到哪里去了?道观岂能是随便转让的?即便是林道爷另寻出处,也应该事先和学习的孩子们说一声,怎么能招呼都不打就突然不见了呢?况且林道爷在这里修行几十年,道观就是他的家,怎么会舍得离开?
和尚占了道观不久,周围村子夜里就经常莫名其妙地遭贼。无论粮食还是牛驴猪羊、鸡狗鹅鸭等牲畜,无一幸免。更让人恐怖的是晚上同睡一个炕上的大闺女、小媳妇,天明以后也不见了。苦主纷纷到县衙报官,新任县太爷刚刚到任,忙于交接,无暇顾及此事。他自己没露面,只是象征性地派衙役到现场了解一番,便以贼人流窜作案,暂时无法捉拿为由草草收场,成为悬案……
官府不作为,苦主们前思后想,觉得和尚有重大嫌疑,就想到上清寺打探一下。
上清观变成了上清寺,道士换成了和尚,供奉的神君却没变,但是香火寥寥无几。和尚既不化缘,也不耕种,每天日上三竿时分,就在门前空地上舞刀耍棍,伸胳膊踢腿,擒拿格斗,一个个看似武功高强,让人望而生畏。寺庙只有正前厅开放,偶尔有人前来上香,有和尚在旁边盯着,祭拜完毕立刻离开,不准随便走动。俗话说:怕人无好事,好事不怕人。和尚如此作為,就更引起人们的怀疑。
有一天,从西南方向来了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少年叫花子。他一手端着一只缺边少沿的破碗,一手拿着打狗棍,来到了上清寺门口儿。守门和尚二话不说,就上前驱赶:“叫花子,这里不打发要饭的。别弄脏了佛门圣地,赶紧滚远点!”
叫花子一口河南腔儿,看起来也就是十六七岁的年纪,可怜兮兮地说:“俺家在中原,黄河发水淹了村子,一家人只有俺逃出来了。因为走投无路,只好出来逃荒。如今饥肠辘辘,实在是流浪够了,就想找个落脚的地方。只要能挡风避雨,有地方睡觉,有口吃的就行,不要工钱。俺不怕吃苦,啥活儿都能干,恳求师傅慈悲为怀,替俺问问当家的,能不能留下俺……”
把门的和尚听了小叫花子的话,仔细地看了他几眼,觉得这小叫花子还不烦人,便说:“你等着。”就转身离开了。一会儿,他出来喊小叫花子进去。小叫花子进到里面,被领进一个房间里。里面有一张八仙桌,围着桌子坐着三个和尚。为首的和尚五大三粗,一脸横肉,身披大红袈裟,手持佛珠。见小叫花子进来,大喝一声:“你是什么人?竟敢冒充叫花子!说,来这里干什么?”
小叫花子被这一吼,吓得六神无主,急忙咕咚跪下,连喊:“佛爷饶命!佛爷饶命!”然后战战兢兢地把在门外说的话又说了一遍,一边说,一边流下泪来。三个和尚相互对视了一眼,为首的和尚哈哈大笑,说:“起来吧。我佛慈悲,看你可怜,就暂时留下你,在寺里干点儿杂活。”然后让另一个和尚把他领到一个杂物间,让他在这里住下。没有床铺,就地铺上一层厚厚的麦秸,算是有了栖身之所。和尚告诉小叫花子,除了干活,不许随便走动,一日三餐,有人送过来。晚上拉撒有罐子,在房间里处理,如果嫌拘束,就趁早走人。
小叫花子喜出望外,连声说非常满意。小叫花子就这样成了上清寺的小打杂,因为他一口河南腔,和尚们便称呼他“小河南”。
小河南年纪虽小,却还真是一把干活的好手。每天天不亮就起身打扫院落,担水劈柴。和尚们把本该他们做的杂事都交由小河南。很快,寺院里的一切环境,小河南都熟悉了,干起活来就方便多了。只要他发现哪个地方需要整理,不用和尚吩咐,他就会见缝插针地去做好。只有和尚想不到的,没有小河南做不到的。
寺院西南角有一个小阳沟。小河南对和尚说转眼就到了汛期,阳沟小了排水不顺,还是趁早把它挖大些好。和尚见他办事这么细心老道,更加喜欢,就说:“你看着办吧。”小河南得到允许,便用铁锨将阳沟挖到能钻出一人之阔。然后找块木板堵上,不上眼外人根本看不到。
小河南只知道闷头干活,除了见人咧嘴笑笑,从不多言多语。和尚们夸他是个有心人,对他的态度自然好了许多。
转眼三四个月过去了。小河南每天从早干到晚,累得像个陀螺,但在这里有吃有住,看起来倒是心满意足。和尚们给小河南送来的饭菜也逐渐有所改善,那些剩饭剩菜里,有了肉渣,有时还有肉块。这就奇怪了,和尚应该吃素,怎么会吃肉呢?平日里也没见他们采购肉类,这些肉是哪里来的?小河南便处处留心起来。
寺院西北角有个偏院,说是住持和各执事议事重地,闲杂人员不准靠近半步。小河南好奇心重,越是不让靠近,越是想知道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是个什么样子。可是,院门紧锁,围墙太高,怎么才能知道里面的底细?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借打扫卫生,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将一块砖缝用树枝抠开一个豆粒大小的空隙,觑着一只眼往里看,里面的情景尽收眼底。
那个院子非常宽敞,占地至少有半亩多。靠西墙建了一排房子,只有南边头上一间是开着的,其余的都上着锁。院子的空地凹凸不平,有两个和尚正在用铁锨挖坑。他们挖坑干什么?这样出力的粗活,应该找小河南才对,怎么会亲自动手?一会儿,新的情况出现了。两个和尚抬了一大包东西从房子里出来,向挖坑的两个和尚走来,然后把包里的东西往新挖的坑里扔。小河南看清了,是牲畜的毛皮和骨头。天呐,这些东西是怎么弄进来的?难道是晚上?
以往和尚把饭送来,等小河南吃完顺便把碗筷带走。说也奇怪,每当吃过晚饭,小河南就瞌睡得不行,一觉睡下,直到天明才慢慢醒来。他还以为是白天太过劳累呢,现在看來,一定另有原因。
这天晚上和尚又送饭来,小河南正在门外对着便罐呕吐。看那架势,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他呕吐一阵,就抱着肚子回到房间,对和尚说:“恶心,肚子……肚子疼,饭一时吃……吃不下。你先把饭放一边,过后我好点儿再吃。”说着一头扎到铺上,直喊难受。和尚见小河南病得不轻,看他吐的东西也觉得恶心,就把饭放下,说:“饭一定要趁早吃,过会儿我再来收拾。”说完就匆匆离开。
和尚一离开,小河南的病立刻好了。刚才的呕吐,是他故意用手抠的嗓子。他赶紧把饭菜抓烂倒在便罐里,又找了块小棍棒搅了搅。和尚没发现便罢,若是发现了问起来,就说吃了马上又吐出来了。过了些时候,和尚果然又来了,看到饭碗空了,小河南也躺在铺上睡着了,笑了笑没吭声,便放心地走了。
小河南没吃饭菜,果然不再犯困。他大睁着双眼瞅着屋顶,集中精力听着外面的动静。没过多久,一阵杂乱轻快的脚步声传了过来。小河南爬起来,从门缝里看到和尚们个个身穿夜行衣,匆匆忙忙出了寺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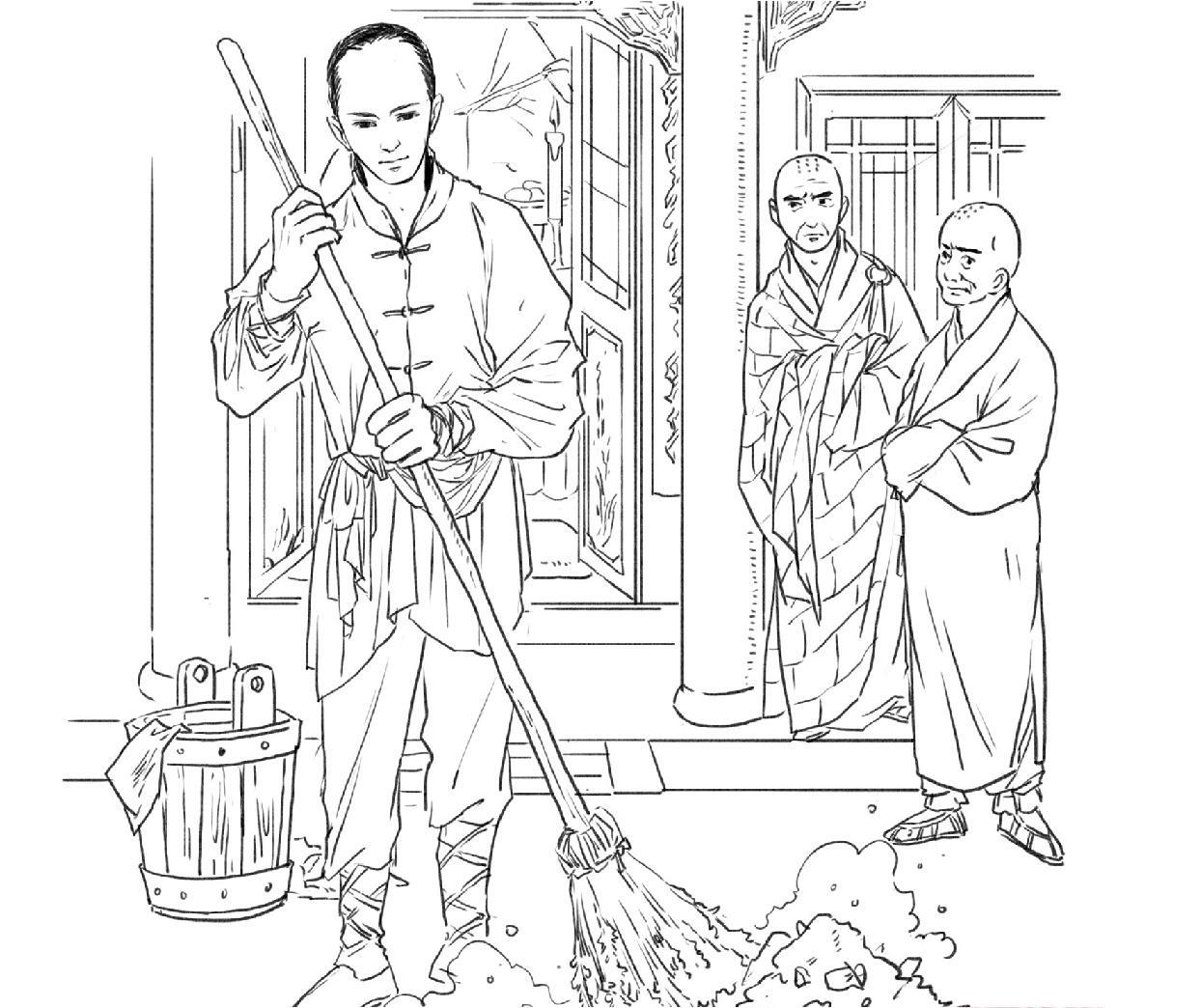
大约两个时辰后,寺门响动,踢踢踏踏的声音进到了院里,只是脚步杂乱而沉重。小河南不敢怠慢,赶紧爬起来又去扒门缝。借着明亮的月光,首先看到几个人牵赶着两头驴、三头牛进来了,驴牛背上都满满地驮着东西。有头牛背上驮了条布袋,布袋在牛背上直劲儿扭动。赶牛的人朝布袋拍了一把:“再不老实就弄死你!”
旁边一人拉住他说:“轻点儿,别吓死她。这个妞比上几次弄的俊俏多了,可舍不得弄死。大王稀罕够了咱还得……”
“嘿嘿,也是。喂,小妞,都到家了,你还是省点儿力气吧,反抗没好果子吃!”
这些畜生,简直是禽兽不如!小河南看着这些,恨得牙根儿痒痒。但是,此刻他要是出去,无疑是以卵击石。身处狼窝,绝不能轻举妄动,因小失大。他继续观察,后面的贼人手提肩扛也陆续进了门……
小河南等到外面安静下来,才悄悄地推开门,小心翼翼溜出来,找到墙角的阳沟,拿开木板,爬了出去……
天将放亮的时候,和尚们还都在睡梦中。突然,从县城里来了一队官兵,将寺庙围了个水泄不通。
小河南从队伍里的一匹马背上跳下来,熟门熟路地从阳沟爬进了寺内,将庙门打开,密州防备营的三百个官兵神不知鬼不觉进了寺,直奔目标,进行清剿。另一队潍州防备营二百骑兵负责外围,以防贼人狗急跳墙成了漏网之鱼……
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贼人晚上作案已经非常疲惫,回来后又大吃海喝了一顿,折腾够了,天也快亮了,才死猪般沉沉睡去。官兵打进来时,他们正做着美梦浑然不觉,一个个被猪毛绳捆了个结结实实。
原来,这些僧人是盘踞在九仙山的土匪。匪首叫于飞龙,师爷叫肖算计,带领上百匪徒,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朝廷派官兵围剿追捕,端了他们的老窝,只剩下大小头目三十余人,仓皇逃到这儿,钻进庙山的一个山洞里,昼伏夜出,一待就是三个月。山洞里阴暗潮湿,实在不是人住的地方。他们看着风声已过,觉得上清观是最好的栖身之处。于是,到外面购置了行头,准备就绪,便在深夜袭击了上清观,杀死了林道爷和他的徒弟,就地埋到观中后院,然后连夜清理道观,剃光头发,装扮成和尚改换门头,粉墨登场。
他们贼性不改,入住道观没几天,就迫不及待地干起了老本行。白天踩点,夜深人静时进入附近村庄,首先往目标周围的住户院子里投放带有迷药的食物将狗迷翻勒死一并带走。清除障碍后,进到院子,用手指戳开窗纸,点燃迷魂香吹入,将人迷昏。如此一来,入户作案,如入无人之境。往回返的时候,把大件财物和猪羊等小牲畜弄死放到大牲口的背上驮着,大牲口的蹄子用布包好,走起来不但没有蹄印,连声音也极小。他们又将牲口屁股也用布包住,以免路上拉撒暴露了行踪。其余的匪徒尽力捎带不空手。无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没有度牒的假和尚,自觉做得天衣无缝,还是败在了一个小叫花子手里。
匪徒们占住上清观后,生怕事情败露,除了严防死守,还特意在大门外演练武艺,虚张声势,将外人唬住。当初小河南上门找活干,他们好逸恶劳惯了,见是一个外地小叫花子,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对他们构不成威胁,又白捡一个苦力,岂有不收留之理?每天晚上,他们都在小河南的饭菜里下药,让他昏睡过去,一夜不醒。
匪首于飞龙气急败坏地对看押他们的官兵喊道:“叫小河南过来!事情不弄明白,老子死不瞑目!”
他三番五次地聒噪,看押的官兵只好去找小河南。
小河南来了。
于飞龙一开口就破口大骂:“好你个兔崽子!老子管吃管住收留你,你竟然恩将仇报!你说,官府给了你什么好处?”
小河南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的职责。”
“呸!好大的口气。一个臭乞丐,还说什么职责!”
小河南轻蔑地说:“你作恶多端,人人得而诛之。如今被捉,罪有应得!”
师爷肖算计见小河南出口不凡,料定有些来头,便说:“小河南兄弟,鄙人待你不薄,做人都要知恩图报不是?你只要对县太爷美言几句,放我一条生路,我就把私藏的钱财全给你!”
小河南笑道:“识时务的赶紧将赃物交出,先交代清楚罪行的,就有机会免于一死……”
匪徒们唯恐自己的罪行被别人揭发后罪加一等,为了自救,也不用审供,纷纷将他们做的恶事交代了出来。
根据匪徒们的招供,官兵从封闭的后院里找到了还没来得及宰杀的牲畜,还有一些暂时没吃完被腌制风干的各种牲畜的腊肉。挖出了埋藏于地下的几大瓮金银珠宝。又从和尚的禅房地下室里救出了几个捆着手脚、塞着嘴的年轻女子,全都被折磨得痴痴呆呆,有的已经奄奄一息。她们正是附近村子里失踪的女子。还有没有找到的女子,都被这群畜生活活折磨死了,和林道长师徒的尸体一样,被埋在后院的墙根下……
十天后,就在上清寺东墙外的打麦场上,诸城县太爷升堂问案。
匪徒们一瞧这位县太爷,不由得大吃一惊:县太爷就是小河南!
没错,小河南就是新任县太爷萧冠雄。
萧冠雄是河南登封人,自小天资聪慧,十八岁考中进士,二十岁被委任诸城县令。他刚刚上任,就接到当地乡亲的状子,经过反复斟酌,他料定这些案件似乎都与上清寺的和尚有关。
常言说得好: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萧冠雄想好了对策,为了麻痹匪徒,事先只是派衙役走走过场,并放出风去说贼人流窜作案没法捉拿。然后利用当地人对他样貌不熟的条件,加上自己身材瘦小,虽然二十岁,看起来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便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潜入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