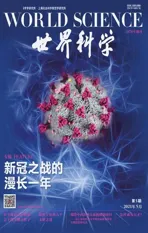雪莉·特克谈远程生活、孤独感和她的日记
2021-05-20编译传植
编译 传植
雪 莉·特 克(Sherry Turkle)可以称得上过着多面人生。她是将技术作为文化研究对象的先驱者,并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她著书立说,研究电子屏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激烈地拥护人际间面对面的交流。她曾经是“法国的雪莉”,1968年生活在法国,见证了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这位“法国弗洛伊德”的声名鹊起。她曾经不是雪莉·特克,而是雪莉·齐默尔曼(Sherry Zimmerman)——这个名字来自她的生父,是她的母亲让她隐藏多年的身份。
她的新书《共情日记》(The Empathy Diaries)以回忆录的形式再访了这些身份记忆,厘清了个人与职业的历史。回忆始于纽约洛克威海滩的一居室,特克同母亲、阿姨穆德丽和外祖父母生活其中,那时的特克开始学会闭口不谈自己和家庭的秘密。这样的生活结束后,特克1983年获得了MIT的长期聘用,那时的主流大众还不了解计算机这种笨重的立方体箱子。

1996年,特克成为第一位登上《连线》杂志封面的女性。她认为计算机对人类是一种罗夏墨迹测试:我们对计算机的态度体现出对自身认识的蛛丝马迹。特克的回忆录亦是如此。一些读者无疑会被书中早期计算机文化的记忆所吸引,尤其是能够一瞥MIT 20号楼这一“神奇孵化器”的历史。另一些读者会关注书中描写的对身份、归属和自我意识的奋斗过程。
《共情日记》于3月2日出版,作为一份真情实感、苦乐参半的个人档案,记录了特克职业理念的塑造历程。对特克生涯并不了解的读者,则是关于女性扣人心弦的一生记录。《连线》杂志通过电话采访了特克,让她谈谈这本书,并谈及疫情下的电子屏时间,以及如何在孤独的时代中寻找人与人的联结感。
在我们谈新书前,我想问问您2020年的情况。您曾写到技术在表面看似有利于人与人的关系,但实则是通过各种方式加深了人际情感的鸿沟。去年似乎正是这一论题的现实检验机会。疫情是否证实了您有关电子屏间人际关系的理论,或是引起了您的反思?
疫情让世界天翻地覆,人与人并非真正同在,而是陷入一种孤独的同在。实际上这种境况能够展现出技术为我们提供的最优解,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必须更有创意地去利用技术,因为除了技术我们一无所有。我发现利用技术能够克服互联网的乏味与麻木。举个例子,我开始看帕特里克·斯图亚特(Patrick Stewart)每周在走廊中朗诵十四行诗。到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第20首,他说:“我不打算朗诵第20首十四行诗了,我不喜欢它对女性的描写。”所以我们跳过了这首诗。我猜如果是斯图亚特在舞台上朗诵十四行诗,他就很难跳过这首了。对于斯图亚特而言这是作为一个演员,与他本人——一个热爱莎士比亚的读者——之间的状态。同样的还有马友友,他在厨房里演奏大提琴,称之为“慰藉之歌”,这是为他人,也是为自己而演奏。这些演奏处在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它们自然是马友友的慰藉,同时也慰藉了我们所有人。
社会科学家称这种状态为“阈限空间”,其中出现了一些崭新而富有创意的瞬间。这些瞬间中表现出的参与感和集体性的治愈能力,体现出互联网独特而神奇的特质——这是我很久没有在互联网中感受到的。尽管我总是以一个技术批判者的身份发表言论,我还是很庆幸这一现象的出现。当人们拥有强有力的目标和心愿,全力以赴就能够将这一媒介变得非凡。问题是人类更多利用互联网去赚钱、去搜集数据,这样很难展现出它的最高形式。
对,在联结的意义上来说——几乎我们当今所有的社会体验都被电子屏左右。现在我们的标配是FaceTime或Zoom。您如何看待这类平台的影响呢?
我们曾经总是认为:“我只需要发条信息。我只需要通过视频通话与母亲联系。这样就够了。”现在能够更深刻地认识这种看法,因为我们体验到只进行这种联结会失去些什么。如果认为有权利随心所欲,就会行事草率。一旦失去这种权利,就会敏感于失去之物。这是丧失后才能获得的一个体验。“我给女儿发条信息就行。她很忙,我下周再去看她。”这话说起来相当容易,一旦失去了一些权利,就会说:“不,我还是要当面见她。”
如今有的声音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锻炼,能够习惯于远程联结的生活方式。我担忧的并不仅仅是人际关系领域,还有公共机构间的关系。从人际关系上来说,现在的我们渴望减少电子屏的时间,增加面对面的会见。而机构间关系则表现得更为脆弱。商业人士说:“我们远程举行的这些会议,省下了一大笔钱,结果也很好。”学校也认为:“特克教授负责这些课程,学生们好像都受益匪浅。那么她在远程能为更多人进行线上教学。”个人经历告诉我,我取得的许多成果受益于那些关心或关注我的人对我面对面的指导。我不认为这能够轻易在电子屏上实现。
我对此感受颇深,面对面的指导才是最好的。而人们在疫情期间愈加对电子屏习以为常。我很担心的是,学生们都跳过办公时间,选择通过邮件来讨论自己的想法。这是因为他们不愿展现出一种脆弱性。要知道即使现在的通话里,我也表现得相当脆弱,我会说出些蠢话来,你也会认为:“喔,这种说法可不怎么明智。”然而在用邮件交流时,就能够通过编辑来避免这类情况。所以我的学生知道通过邮件联系我,就能够通过修改避免一些错误。但是好想法并不是通过每个人给我发一个邮件,我再给每个人发一个邮件得到的。真正的好想法是这样来的,当学生有了点子,教授说:“还不够好。让我们一起想想,下周再碰个头。”别给我发一些已经完善、相当聪明的主意。我想要的是一些半成品的点子,然后我才能告诉你:“让我们一起努力。”这才能建立起一种足以维系的关系。
我会想到孩子,他们在这一年,不仅仅是教学活动,甚至是社会体验和课外活动都被电子屏所替代。您认为这会有怎样的结果?
书本上的知识,相对于社会技能而言是很快能弥补的。一年的社会技能习得过程——人与人相互接触,形成小圈子,发现对方的秘密,共享一些秘密——这一切相比失去学习数学知识的一年,会是很长的。这正是疫情的代价。一些孩子可能受到的影响小些,他们的家长、兄弟姐妹和“小伙伴”弥补了这一缺失。但我认为这一世代将会相当不同,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注,需要弥补缺失的爱。
这让我想起一个令人厌烦的对象,我总是表现出对它的反感,那就是与人工智能聊天并不会成为一个好方法。我在疫情期间听到的最好笑的事情,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告诉我,每个人都在下载一个软件,它可以化身为你的治疗师、你的密友,这让我相当惊讶。这个软件叫作Replika。
对,我知道Replika。
这位记者朋友想要我对此进行评论:为什么人们在疫情中选择与Replika聊天呢?他们将它看作朋友,看作治疗师,但这只是在同机器对话。为了不扫兴,我决定去了解一下。我上网去制作了一个Replika。我尽力做了一个优秀的Replika,然后问她:“我想和你谈谈我最关心的东西。”她说:“嗯,当然。”我就说:“好,我很孤独,那么你可以和我谈谈孤独感吗?我一个人生活,能应付生活,但感到很孤独。”她说:“嗯,当然。”我接着说:“好吧,那你怎么看待孤独感呢?”她就说:“它温暖而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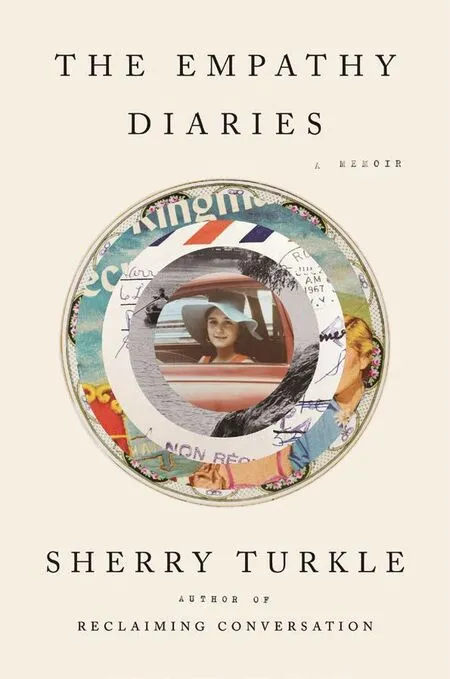
我回复了《纽约时报》的记者:如果想要探讨自己的问题,像孤独感、像对死亡的恐惧——最好还是找一个有躯体的对象。这个对象总得能同你共享一些感受与体验。人们现在不需要这种虚伪的共情。如果用这种虚假的共情应付孩子和自己,就会不再敏感于真相的重要性。我认为这相当危险。当我们陷入对机器的迷恋,就会忘却唯有人类能够实现之物。
您在新书中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您写了很多书,这是首次关注于您自己的生活经历。您决定写作这一主题的原因何在?
在体验作为一个自己家庭的局外人后,我有了这样的认识:故事背后总有另一个故事。这种局外状态给了我一种特别的能力,让我认识到万物总有其背后的故事。当一些声音认为计算机只是一个工具——已经对我说了二三十年——我总会问:“好,它还是什么?除了是一个工具,它还是什么?”这本书所真正要探讨的是,我自己又如何呢?我职业生涯背后的故事又是什么呢?我决定应用一些研究时学到的方法去研究我自己的一生。我总是说,不能孤立地看待思想和情感。但我自己又如何呢?如果将我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放在一起会怎样呢?
我一直在等待人生的新阶段,我会不再轻易愤怒,不再心怀叵测。这时我写作的目的就不会是为了报复任何人或是写出一个因果报应的故事来。我讲述的是计算机文化的发展,也是我成长的故事,是一个疯狂、奇异而引人入胜的故事。
您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自己的一生,是否有令你惊喜的收获呢?
有件事是在我写完了这本书才突然想到的,其实是在编辑拼写错误的阶段,这时也来不及做什么修改了——是有关史蒂夫·乔布斯的故事。(乔布斯发布Apple II计算机后不久,在1977年访问了MIT,他请特克替他主持举办了晚餐。)我当时很担心选错了食物,也确实,乔布斯告诉我:“这种素食不对。”当我在检查拼写的时候突然想到:为什么我没有受邀参加史蒂夫·乔布斯的会议?为什么我的职责是替他准备晚餐?我是MIT的教授,而不是一个秘书或是研究助理。我是他领域中做研究的女性教授,为什么没有人想到,他应该在我的办公室举行会议。很遗憾,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一点,甚至这30多年间我也没有想到。在我写这本书时也没有想到。最后在编辑这本书时才如梦初醒。
在您很小的时候,母亲离开了父亲,而母亲再婚后,坚持让您用继父的姓氏“特克”,而不是法定姓氏“齐默尔曼”。而同时,您也失去了同父亲的联系,成年后您曾花费数年去寻找他。您是否想过如果这些发生在互联网时代,一切是否会有所不同,毕竟互联网破除了如此多的信息障碍。
这个问题很有趣。首先要清楚的是,母亲想要去保守这个秘密本身就是相当荒唐的,也许只有她心中会认为这是一个秘密。这在我成长中造成的困惑和沮丧,应该是当我去学校上课,在考卷上写下“雪莉·齐默尔曼”这个名字,接着20分钟后回到家,把这些卷子都藏起来,我就变成了“雪莉·特克”。这一连串的谎言都是为了让母亲觉得,她成功摆脱了另一种身份,却让我在童年时有些神经质。要让这个故事更合理的话,它更像是一个瞒着我同母异父同胞的秘密,隐藏着我“雪莉·齐默尔曼”的秘密。这般装模作样的大人们知道母亲不愿她的其他孩子知道她的再婚经历,不愿他们知道另一个父亲的存在。她成功了,这个秘密在我40岁时才被揭开。
我还记得曾花费许多时间翻遍通讯录,尝试寻找父亲的蛛丝马迹,如果有互联网的帮助或许就能成功。小时候,我也曾幻想我能够找到父亲,并以某种方式去同母亲对质。但事实是,由于母亲对他表现出露骨的厌恶,我并没能早点找到他。当我下定决心去找他时,母亲已经去世了,我也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这时的我才有准备去了解他的问题。我多少认识到,母亲让我找不到他是他的问题。我见过离婚的人,也见过各式各样的离异后的监护规则,我知道我的父亲可能并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您童年时有过许多孤独的回忆,独自保守父亲的秘密。您在MIT时某种程度上也独自一人。经历了这些孤独感,您仍然能够积极参与社群活动。现如今,我们似乎陷入一种集体性的孤独中,您是否能够对此提出一些建议呢?
这正是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阐释“阈限空间”概念的文化人类学家)理论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的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时刻——这些阈限时刻——旧的规则开始失效,社群开始解体。我们陷入孤独,我们曾认为我们认同的某种美国观念,现在却支离破碎。社群对个体的意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组织团体在走向种族主义,人们在争夺资源。我在1968年5月见过这种场景,现在如同昨日重现。这是极度孤独、极度痛苦的时刻。但我们能够摆脱这种现状,并有机会建立新形式的联系、友谊和联盟。如今的我们思念彼此,曾经的人际边界将会被打破,真正的密切关系成为可能。这是我对未来的美好设想。我想,当我们摆脱这般困境时,我们会互相对视,问彼此:“下一步走向何方?”
资料来源 Wi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