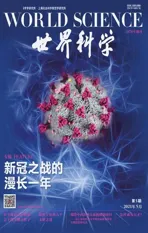新冠之战的漫长一年
2021-05-20编译刘迪一
编译 刘迪一
无论有没有准备好,从新冠疫情暴发开始,全球医疗系统就在持续不断地大量接收COVID-19患者。2020年初,世界各地的医生全力应对新疾病的猛烈攻势——这样的遭遇战或许是他们职业生涯的首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
加拿大韦仕敦大学的重症监护医师罗伯特·阿恩菲尔德(Robert Arntfield)表示:“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就像电影中忧伤的小调响起。”
中国的医疗和科研团队与其他各地区的研究者竞相发表关于COVID-19的奇特症状以及治疗方法的报告。
在东京,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感染者被送入了日本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的医院。传染病医生诺里奥·奥哈马加里(Norio Ohmagari)取消了他的最佳治疗计划:一项针对引起中东呼吸综合征的冠状病毒(MERS病毒)的计划。他表示:“实话实说,我们不确定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在英国卡嫩河谷,一名男子来到诊所接受常规血液检查,并表示自己发高烧外加咳嗽。当初级保健医生克里斯·巴特勒(Chris Butler)准备评估这名患者时,他“正摘下手套”, 因此感到“非常紧张”。
在接下来煎熬的一年里,大量关于如何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证据涌现,数不胜数的见刊论文、预印本网站论文以及相关新闻稿几乎令人看花了眼。众多医生一边等待着大型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的结果(它们被认为是临床证据中的黄金标准),一边又急于为他们眼前的重病患者提供医疗帮助,纠结万分。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健康科学统一服务大学呼吸与危重症科医师丽莎·摩尔(Lisa Moores)如此说道:“这些聪明的医生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发病,丧生;他们感到无助,也渴望竭尽全力帮助患者。”

一名美国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的护士正佩戴口罩
未经验证的药物进入一线治疗方案。美国范德堡大学的重症监护医生马修·塞姆勒(Matthew Semler)表示:“成千上万的患者接受了无效或有害的治疗方法。”他引用了被广泛用于COVID-19治疗的抗疟药羟氯喹的案例——现已证实该药物对新冠肺炎无效。

医师们的治疗指南几乎一天一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Penn)研究卫生保健的重症监护医生梅根·莱恩-福尔(Meghan Lane-Fall)表示:“当全世界都在致力于某项工作时……科学证据的发展变化很快。每次我面对新冠患者……我沉下心思考,‘好,我们现在在做什么?’甚至时至今日,我们也没有统一的治疗标准。”
然而,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大流行的12个月后,医生们对新冠肺炎的病理学原理及其治疗方法有了一个粗略的认知:疾病早期的护理策略应该是通过阻止病毒增殖来预防重症;随着感染加剧,主要的敌人就变成了过度活跃的免疫反应,它们会对人体器官造成严重破坏。
一小部分药物和疗法——大多是旧药新用——成为对抗新冠的明星。地塞米松,一种廉价而常见的类固醇药物,在一项随机试验中展现了挽救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生命的神奇功效:研究人员发现它可以将呼吸机病人的死亡率降低约1/3,将仅吸氧患者的死亡率降低约1/5。另一种抗炎药托珠单抗也有救命的奇效。部分研究显示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已被广泛用于住院患者)似乎可以加快病人的恢复速度,不过另一些研究并未得到此类结果。与此同时,单克隆抗体也被寄予厚望:专家认为新冠康复者的血浆中存在对抗病毒的抗体,而通过克隆单一细胞的方式大量生产得到的此种抗体,即单克隆抗体,能有效帮助感染者击退病毒,不过它们很难给门诊患者使用,而且某些抗体对抗新病毒变体的效力较弱。除药物外,重症监护病房(ICU)里的护理体系也有了极大的水平提升,毕竟重症新冠患者的器官衰竭问题相当普遍。
COVID-19仍然是神秘的,甚至致命的,但治疗方式的改变似乎有所帮助。今年3月发表的一项针对美国555家医院的近20万名患者的分析报告显示,新冠患者的死亡率从2020年3月的22.1%降至8月的6.5%。当然,能有如此进展,除了要感谢居功至伟的新疗法,其他诸如医疗资源压力得到缓解等因素也发挥了作用。
大约10%~15%的患者会发展为重症,其他人则面临持久的、有时甚至致残的症状的威胁。初级保健医生们要为患者健康保驾护航,他们训练有素,能够应付从疣目到肠胃感染的一系列疾病。南卡罗来纳州的内科医师、美国家庭医师学会(AAFP)主席艾达·斯图尔特(Ada Stewart)这样说道:“我的病人是我的家人。”

家庭医生艾达·斯图尔特会观察她的COVID-19门诊病人是否有病情恶化的迹象
初级保健和传染病医生杰奎琳·楚(Jacqueline Chu)为马萨诸塞州切尔西市的工人阶级(受新冠肺炎影响严重)提供医疗服务。她所在的诊所隶属于麻省总医院。楚这样说:“那些新确诊的患者来到诊所问我,‘您现在能不能给我开些什么,来帮我缓解病情?’”
门诊治疗通常是很基础的。楚医生提供的护理建议很常规,可应用于任何病毒感染——补液,休息,以及服用具备止痛和退烧功效的对乙酰氨基酚。不过现在医生们知道哪些新冠患者更有可能发展为重症。他们密切关注老年人以及患有心脏病、糖尿病或肥胖症的病人。当美国克利夫兰诊所的科学家通过健康系统整理分析了所有COVID-19检测阳性者的数据后,他们发现了另一种诱发重症的危险因素:生活在最贫穷糟糕的社区。在得到此发现后,医疗团队对那些地区的患者开展了为期两周的每日检查,以便快速及时地发现症状。
医生们还发现,即使是在某天看起来已康复的健壮年轻人也可能第二天就病情再度恶化。脉搏血氧仪已成为新型温度计,被广大家庭用于检测患者血液中的氧气含量是否下降。
负责英国PRINCIPLE试验(面向居家的新冠高风险人群)的克里斯·巴特勒表示,在新确诊患者身上测试实验性疗法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些临床试验难以招募到志愿者,因为社区诊所与试验的基础设施之间彼此分离。
迄今为止,PRINCIPLE项目获得的最大成功是排查出了无效治疗方法:他们曾尝试用抗生素阿奇霉素和盐酸多西霉素治疗COVID-19,因为它们具有一定的抗炎和抗病毒特性,但今年1月下旬,项目组宣布这两种药并不能加快新冠门诊患者的康复速度。
其他试验也遭遇了失败。在敦促康复者捐献血浆数月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3月份暂停对轻中度患者进行的恢复期血浆试验,因为他们原以为这些富含抗体的血浆在被注入其他感染者体内后能发挥抗病毒奇效,结果却发现事实远非预期的那般。另一项同期的大型试验也并未报道恢复期血浆疗法确实帮到了住院患者。
此类失败具有指导意义,能帮助医生划去那些可能对患者有害无益的治疗方法。美国亚利桑那州钱德勒市的家庭医生安德鲁·卡罗尔(Andrew Carroll)说道:“我的一些患者从墨西哥购买了新冠治疗包,这些治疗包声称含有抗生素、类固醇和维生素,但它们都没有任何研究基础。”
AAFP委员会的委员长莎拉·科尔斯(Sarah Coles)在菲尼克斯从事家庭医学方面的工作。AAFP委员会曾向其13.6万名成员发布新冠治疗指南。之后,科尔斯持续追踪着一种颇有前景的疗法——前文提及的单克隆抗体——的数据。实验室制得的单克隆抗体可模仿人体自身的免疫反应,阻止病毒附着于细胞。2020年11月,中期试验数据表明单克隆抗体可将住院风险降低2/3,也能减小死亡风险,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了由再生元制药和礼来公司生产的单克隆抗体的紧急使用授权。
如果采用单克隆抗体治疗,抗体必须在患者出现初始症状的几天内即完成输注,这是后勤方面的挑战。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C)的传染病医生戴维·沃尔(David Wohl)怀疑UNC提供的1 800剂单克隆抗体只占实际需求的小部分,他正努力扩大产品供应。艾达·斯图尔特的那些在南卡罗来纳州农村的患者由于运输困难压根就得不到抗体。与此同时,药物的供应量波动。另一方面,部分单克隆抗体有些跟不上新冠病毒变异的脚步。
更重要的是,官方指导就抗体的说辞显得模棱两可。随着临床试验的进行,NIH发布的治疗指南称“目前尚无足够的数据推荐或支持”大多数单克隆抗体——尽管他们在今年3月2日建议为那些出现症状没几天的、有较高重症风险的患者提供礼来研发的新冠单抗鸡尾酒。有的医生认为NIH的指南太过保守,不过科尔斯倒是希望先从更多参试者那里看到结果,然后再决定是否完全接受单克隆抗体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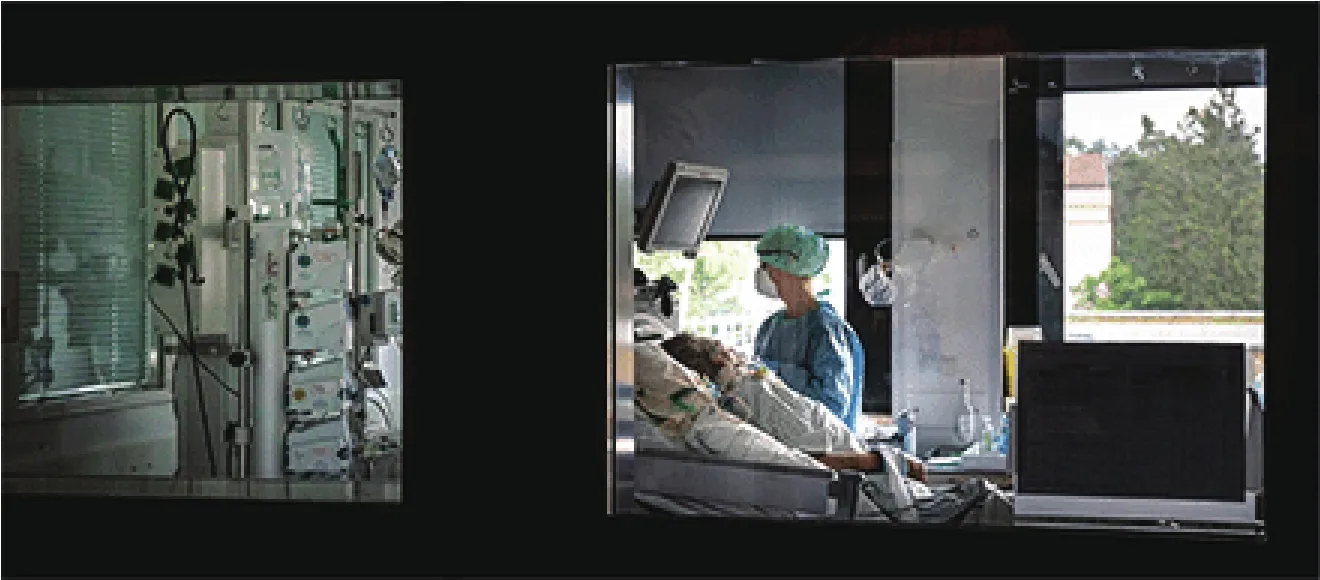
在意大利米兰,ICU的医生和护士组成团队收集信息,以协作开展对COVID-19患者的护理
科尔斯和斯图尔特等医生的武器库不算丰富,她们的主要诊治方式就是仔细聆听病人的讲述,指导患者注意关键症状,给出针对性的健康建议。斯图尔特的一名病人曾在确诊一周后表示自己出现了严重的疲劳和胸痛。斯图尔特对其状况越发感到担忧,并建议她去医院。之后,医院方面发现病人的双肺都出现了血液凝块,于是迅速收治并把她移交给了一个新的医疗团队,尽力保护她免受严重疾病伤害。
血液中的免疫信号分子水平升高是危险标志。匹兹堡大学的传染病专家瓦里迪·诺里亚尔(Varidhi Nauriyal)表示,最明显的危险预兆就是血液中的氧饱和度低于94%,因此,对于COVID-19住院患者的初步治疗方法就是氧气输送(一般通过呼吸面罩或鼻导管进行)。
众多患者还都使用了瑞德西韦——目前唯一一种被FDA正式批准的可用于治疗COVID-19的药物。2020年初,实验室研究显示这种抗病毒药物具有抑制SARS-CoV-2的能力,引起研究人员的注意。到4月份,一项由NIH赞助的国际试验报告称,瑞德西韦可将患者住院时间缩短几天。然而在10月,世卫组织领导开展的更大规模的“团结”试验,并未发现病人的恢复时间或死亡率因瑞德西韦而有所改善。NIH的治疗指南建议人们使用瑞德西韦,WHO方面则没推荐此药。
纽约诺斯威尔健康中心的肺部和重症监护医师曼加拉·纳拉辛汉(Mangala Narasimhan)说道:“它似乎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神奇药物。”但另一方面,纽约大学朗格尼健康中心的研究员莱奥拉·霍维兹(Leora Horwitz)也表示,由于瑞德西韦几乎没有副作用,而且在大流行初期就建立起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它仍是大多数医院病房和部分ICU中的标准治疗方案:“我认为它不会给人们带来任何伤害,但也不会产生很大好处。”
针对并发症的治疗也是少不了的。血液凝块是COVID-19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估计有约17%的住院患者和近30%的ICU患者会形成静脉内的血凝块,它们可以到达肺部,切断通向心脏或大脑的血流,从而导致中风。许多医疗指南要求给予大多数入院患者以低剂量的预防性抗凝剂。
不过随着病情恶化,医生们为是否增加抗凝血剂用量而苦恼万分,因为抗凝血剂会增加胃肠道和颅内出血的风险。三项试验——分别为英国方面的REMAP-CAP、美国NIH主导的ACTIV-4以及加拿大的ATTACC——快马加鞭地验证其中的风险和收益。
到2020年12月,三项试验都因担心失血问题而停止招募ICU患者。于今年3月在预印本网站发布的初步结果并未发现抗凝血剂能给ICU病人带去生存优势。不过1月份的中期结果(超过1 000名非ICU患者参与研究)显示抗凝血剂似乎很有希望:相比预防级的低剂量,全剂量的血液稀释剂可减少非ICU患者对器官支持的需求,还能降低死亡率。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的住院医生、抗凝血管理项目负责人托德·赫希特(Todd Hecht)表示,如果这些数据站得住脚,它们是“相当有意义”的。在赫希特看来,也许ICU患者病得实在太重了,以至于大剂量的抗凝药也无效。
大型随机试验是确定COVID-19治疗方案的最佳方法。但医生有时会寻求更快速的方法帮助患者。2020年3月,底特律亨利·福特医院的新冠患者病情不断恶化,这促使医生考虑采用当时还未经证实的药物:皮质类固醇——被用于减轻包括从哮喘到过敏的各类疾病所引发的炎症。传染病专家马约尔·拉梅什(Mayur Ramesh)及其团队分析了来自中国的新证据,并决定进行所谓的“类实验”。从3月下旬开始,他们为所有需要氧气的COVID-19患者提供了为期3天的甲基泼尼松龙(一种皮质类固醇)疗程,并将其结果与较早入院的患者做比较。
诺里亚尔表示,团队曾为是否完整地进行一项临床试验展开辩论。(当时的他正帮助指导亨利·福特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工作。)许多人对类固醇疗法抱有很高期望,想将其放入对照组。
到4月初,他们在数据中看到了重要信号:较早收治的81名未接受类固醇治疗的患者中,有44%被移至ICU,26%的人死亡;而在后入院的132名接受了类固醇治疗的患者中,这两项数据分别为27%和14%。拉梅什坚信此疗法可以挽救生命,因此他呼吁其他数十家机构的同事进行推广。然而,由于缺乏严格的随机试验和同行评审数据,鲜有医院愿意做出尝试。
亨利·福特医院的医疗团队继续为患者提供类固醇、其他药物以及氧气,许多病人的情况得到了改善。但病情恶化的患者也到处都是——由于肺或其他器官衰竭,他们被转移到了ICU。
美国方面的记录表明,入院的COVID-19患者中有近30%被转移至ICU。那些重症患者的肺部和其他器官发炎。许多人出现了多个血液凝块,有些人甚至需要靠透析支撑告急的肾脏。
一年前,当遭遇肺衰竭的新冠病人开始塞满ICU,许多医生选择借鉴多年来应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经验。肺部因创伤或感染等原因导致积液往往就会引发ARDS,严重的可危及生命。UPenn的重症监护医师乔治·阿内西(George Anesi)说道:“如果有人告诉我,‘你将会听到很多内容,但它们毕竟只是针对ARDS的经验,’ 那么医生们就能打消很多顾虑。在COVID-19治疗中,一些重症监护医学的基本原理确实有效。”这些基本措施包括俯卧位治疗锻炼(长时间趴在床上以改善肺活量,帮助排出肺部积液)和机械呼吸机的调度使用。
对呼吸机的设置选择难度不小。让过多氧气进入肺部可能会进一步损坏它们;然而,较少量的限量输送会使患者呼吸窘迫——通过镇静减轻不适感也会导致其他方面的问题。塞姆勒说,达到适当的平衡“不是新药研发或其他高大上的东西,它就是你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更大的难题是确定哪些患者需要第一时间戴上呼吸机。因为COVID-19患者的血氧水平可能突然崩溃,以往的经验是在病人首次出现相关迹象时就给他们插入呼吸管。相比无创方法,使用机械呼吸机似乎更容易控制住病毒粒子,带给医护人员的感染风险也更小。然而,长时间依赖于呼吸机的患者通常也会面临更长的康复期。医生们逐渐开始更节制地使用呼吸机。去年4月中旬发布的预印本研究表明,较保守的氧气疗法并未增加空气中传播的病毒颗粒——这令一些医生放下心来。
意大利米兰Humanitas研究医院的重症监护医师马西米利亚诺·格雷科(Massimiliano Greco)表示,有些医院没有给病情恶化的患者配备呼吸机,而是尝试了所谓“试验期”护理——病人戴上氧气面罩进行高流量吸氧,同时医生对其进行仔细的监测;“试验期”时长6~24小时。格雷科说道:“我们了解到,其中有一些患者其实是能恢复得很好的。”不过莱恩-福尔指出过早插管明显存在风险,这种随机试验是不道德的。(尽管临床试验或许能确定精准的插管时间点。)
随机试验的结果已经让人们对皮质类固醇地塞米松建立起极大好感。牛津大学领导的“康复”计划招募到了数以万计的英国住院患者参与,试验内容就包括涉及地塞米松的一系列潜在疗法。
对于病情最重的患者群体来说,机械通气治疗的效果是惊人的。“康复”计划里大约1 000名接受有创机械通气的参与者入院28天后的死亡率为29%;相比之下,那些只接受常规护理的患者的同期死亡率高达41%。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重症监护医生肯尼思·贝利(Kenneth Baillie)说道:“鉴于那么多药物都在面向重症患者的试验中折戟,机械通气治疗的出众效果已经远远超高于项目资助审查者心中的合理标准。我将整个职业生涯都投入到医学研究中,而一篇关于类固醇的论文可能会是最重要的。”
亨利·福特医院的拉姆什团队在去年6月得知“康复”计划发布的结果后欣喜若狂。距此一个月前,拉姆什和同事发表了他们甲泼尼龙试验的结果。地塞米松和甲泼尼龙都是具有相似作用方式的类固醇,这表明亨利·福特医院的押宝尝试看起来有戏。
然而,“康复”计划里来自没使用呼吸机的吸氧患者的结果并不那么出彩:他们的死亡率为23%,该数据在未吸氧患者群体中为26%。UPenn的重症监护医生努拉·迈耶(Nuala Meyer)指出,氧气需求和病情严重程度的差异很大,这使得患者的受益情况存在些不确定性——这是“康复”计划为自己的简单设计所要付出的代价。
对于入院时无须补充氧气的“康复”计划参与者来说,地塞米松的使用实际上反倒与死亡率增加有关。拉梅什表示,这可能是因为在疾病早期,类固醇会阻止免疫系统清除病毒。他担心一些急诊室和急诊医生过早给患者使用地塞米松:“如果你不能掌握好用药时间点,你就可能伤害他们。”
2021年2月,“康复”试验的另一部门发现使用托珠单抗可以降低死亡率。托珠单抗是一种新型、更昂贵的抗炎药,通过白介素-6分子阻断炎症信号,已被批准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些结果呼应了英国REMAP-CAP试验的正面结果(首发于1月份的预印本文章)。
威尔康奈尔医学的传染病医生罗伊·古利克(Roy Gulick)表示,大多数参与“康复”和REMAP-CAP试验的患者也正接受地塞米松治疗,地塞米松可减轻炎症,利于托珠单抗发挥作用。
将研究转化为实际治疗建议并非易事——无论对于托珠单抗还是单克隆抗体来说,这一点都成立。古利克表示:“从现有数据中得出的最大问题是,哪一组患者更受益?”经过数周审议后,3月5日,NIH的专家组建议将托珠单抗和地塞米松联合用于在氧气需求、炎症标志物和其他因素等方面与“康复”或REMAP-CAP参与者相似的患者。
新冠大流行的一年来,使医生精疲力竭的时间更长了:首先是可以阻止患者到达ICU甚至医院的治疗方法。纳拉辛汉说道:“我们在这一年看到的死亡人数真的可怕。”世界某些地区已推出疫苗遏制疫情,但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有许多人感染新冠。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今年早些时候对《科学》杂志表示:“真正的治疗方法是直接使用抗病毒药。”肯尼思·贝利则指出,还需要能让导致炎症的精确细胞信号沉默的药物。
资料来源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