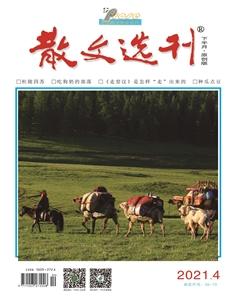羞涩
2021-05-19潘鸣
潘鸣

似乎很久很久,没有念及“羞涩”这个词了——那种因害羞引发的内心的胆怯、憨涩、难为情;延伸至行为上的局促、扭捏、汗颜、慌乱失措。
而曾经那些时光,羞涩是一种原生态的世俗表情,它如同乡野阡陌上蔓生如茵的麦麦草那样寻常。
我也曾有过羞涩。
二十出头的光景,曾恋上县剧团一位二胡琴手。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女孩儿约我去家中做客。母亲知道这种登门的实质,提前为我准备了一网兜水果、点心,叮咛我对人父母礼数要周全,尽量热情一些。可是,当一跨入女友家门,见到对方父母兄姊济济一堂的阵仗,我脑袋轰一下热了,羞涩的情绪顿然令我乱了方寸。我嗫嚅着“伯父,伯母”地打了个招呼,放下手中的礼物,木头一样戳在堂屋里,一时竟没了语言。女友见我窘迫,赶忙将我领进她的闺屋。我躲在里面心如小鹿乱撞,抓起一本旧杂志茫然地翻来翻去,龟缩着久久不肯出门。临别时女友送我,隐约听见她母亲悄声嘀咕:这小伙长得挺精神,就是显得木讷了一些。一点儿星星火,就此熄灭。
在乡校任教时,一次去县城办事,中午饥渴,到南街小食店买了一份肉臊水面——当时这对于低薪的我已算是“打牙祭”了。先在柜台付钱领一绺儿印签凭证,然后去厨灶边排队领取。好容易轮到我,一锅熟面刚刚捞完。掌勺的师傅顺手收了我的纸签儿,丢入那只专用于浸润票签的水碗,边搅和新下锅的面条边说:“等着这一锅吧。”谁知这时生了意外,铺门口那边店长一迭声催喊掌勺师傅马上跟他去糧站进货。师傅应声放下勺子,忘了交代,抽身便走,由后厨另一师傅出来接了勺。又一锅面熟了,新师傅麻利地逐碗捞面,调好作料,吆喝一声:“凭票端面!”我傻眼了,后面的人都伸长了手举着那张纸签儿,唯有我两手空空。我想向厨师解释:前面的师傅已收了我的票签投入水碗了。但抬眼一看,属于我的那一绺儿已在水中濡为乌有,口说无凭啊。想请后面的食客做个证明,又怕别人不明就里,不肯随意担责。更担心新厨师会误以为我是舍不得那一角二分钱,想来这里浑水摸鱼白蹭吃。那样的误会一旦发生,我该如何面对?莫不是要找一条地缝儿钻进去?那一刻,羞涩与自尊交织在一起,化为虚怯与隐忍。一阵纠结之后,我空蠕着喉结,悄没声地从拥挤的队伍里退出来,神情黯然地走出了小食店。
有时候,我的羞涩总是伴随着一些尴尬、挫伤和落魄的,甚至因羞涩而导致过腼腆拘泥,缺少了应有的骁勇与果敢,蒙受了一些委屈和损失。但是,在羞涩袭上心头的时候,灵魂中随之衍生出来的单纯、善良、谦恭、谨慎、矜持、内敛、明底线、不妄作,这些善与美的因子却让我浸润于一种温馨明媚的波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