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火气里的汪曾祺
2021-05-17丁志磊
丁志磊
汪曾祺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为沈从文先生的及门弟子。1940年开始发表散文及小说。从抗日战争时在炮火连天中读书,到1997年去世,汪先生一生所经历的大事,遭受的磨难颇多,但他却始终旷达平和。
生于江苏高邮的汪曾祺,祖父是有功名的,还是位会治眼病的大夫,父亲是画家,也会刻图章。家里有2000多亩地,两个药铺,还有一间什么铺子,我记不得了。汪先生早年的散文《花园》里写过他们家废弃的花园,“带点回忆性质,也有点描写景色气氛”,从这些文字来看,汪先生家至少是现在说的小康之家。
1940年到1997年,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里,能看出汪先生骨子里是不求显贵,不想刻薄人,只想平静温柔的享受生活的人。他不喜欢规矩,《受戒》里,小和尚也有了爱情,但他没去指责他们,因为他们自然纯净。他的文章也不着急,文人气里混杂着烟火气,烟火气里透着熨帖人心的暖意,像是跟人在聊天。这就是他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
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实在是值得一读再读。
看《无问西东》时,对这样一个情节记忆深刻:日本的飞机来袭,西南联大拉响警报。当别的同学都开始“跑警报”的时候,沈光耀却拿着白搪瓷茶缸,走到锅炉房,不紧不慢煮着母亲带给他的冰糖莲子。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是有历史原型的,就记在汪先生的文字里。
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鍋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跑警报》
汪曾祺对这种不在乎的态度是极为欣赏的。“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汪先生说。
但是汪曾祺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沉静自如的。
他早年的作品,也华丽,也冲突,也现代。比如《庙与僧》,比如《鸡鸭名家》,那是因为他正处在恃才傲物、飞笔凌云的年纪。
而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他60岁之后所写。年纪到了,修养到了,境界自然也就到了。
比如《异禀》,他描写一个熏烤摊主和一个药店伙计各自命运的故事,虽然此作一如汪先生其他小说一样有着和谐温存的情致,但确是对苦涩人生的悲悯与忧伤。这种故事,他早年写过,晚年再修改时,基本上看不见有什么激烈冲突的东西了。他晚年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圆通融和了。
他的小说,也有一些是半戏弄式的叙事表达。比如《八千岁》,文章从头到尾没说八千岁的真名,却有些嘲弄地叙写了“八千岁”一生为钱劳碌又破了财的结局。比如《岁寒三友》,虽然以植物的别号来命名小说,可压根儿没写这三种植物,他写的是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这仨人,通过叙述他们的命运,让我们看尽人生的大起落,是恻隐里带着温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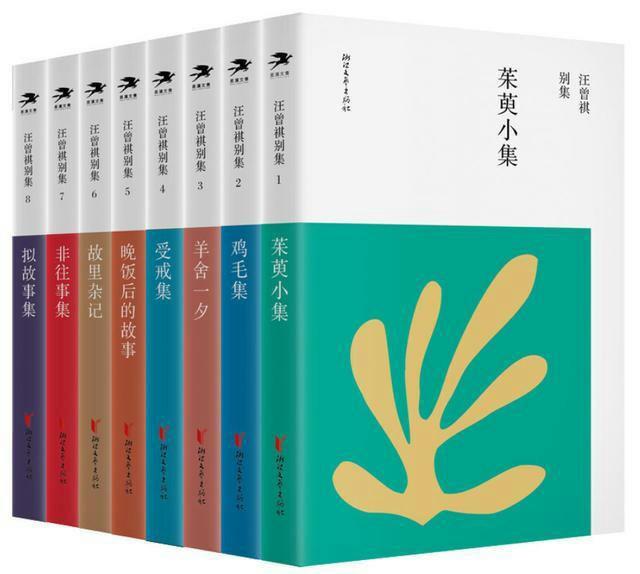
他也写在北京生活所见的东西,比如《听遛鸟人谈戏》,比如《国子监》,比如《古都残梦——胡同》。也写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北京京剧团当时的五大头牌。
他写马连良时,“他的一双脚,照京剧演员的说法,‘长得很顺溜”,写他“在出台以前从来不在后台“吊”一段,他要喊两嗓子。他喊嗓子不像别人都是‘啊——咿,而是:‘走唻!我头一次听到直纳闷:走?走到哪儿去?”
他写谭富英时,“听谭富英一个‘痛快。谭富英年轻时嗓音‘没挡,当时戏曲报刊都说他是‘天赋佳喉。而且,底气充足。一出《定军山》,‘敌营打罢得胜的鼓哇呃,一口气,高亮脆爽,游刃有余,不但剧场里面‘炸了窝,连剧场外拉洋车的也一齐叫好——他的声音一直传到场外。”
他写张君秋时,“君秋在武汉收徒时曾说:‘唱我这派,得能吃。这不是开玩笑的话。君秋食量甚佳,胃口极好。唱戏的都是‘饱吹饿唱,君秋是吃饱了唱。演《玉堂春》,已经化好了妆,还来四十个饺子。”
他写裘盛戎时,“盛戎睡得很晚,晚上他一个人盘腿坐在床上抽烟,一边好像想着什么事,有点出神,有点迷迷糊糊的。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以后总觉得盛戎的许多唱腔、唱法、身段,就是在这么盘腿坐着的时候想出来的。”
他写赵燕侠时,“我们的‘棚在一座小楼上,只能放下一张长桌,几把凳子,我们只能紧挨着围桌而坐。坐在里面的人要出去,外面的就得站起来让路。我坐在赵燕侠里面,要出去,说了声‘劳驾,请她让一让,这位赵老板没有站起来,腾的一下把一条腿抬过了头顶:‘请!”
他写这些,驾轻就熟,无需多表。
但真正见功力的,也是汪曾祺先生明显投入心力的,是他那些谈不上有情节的,叙述回忆生活的小说。比如《茶干》,写的是连万顺酱园的故事,这部小说虽不长,但却被认为是汪先生打破小说和散文的界限,即小说呈现出散文化特点的重要代表小说。还有,比如《如意楼与得意楼》,简直是把两个楼菜单讲完就结束了,但小说里却透着如意楼胡老板的自信自强与得意楼吴老板的萎靡不振,这也是导致他们命运不同的原因。
还有,不朽的《受戒》,汪先生将散文笔调和诗歌的意境营造手法引入小说创作,以纯朴淡雅的语言、自然洒脱的笔调,充满感情地抒写南方水乡的自然风光,写人的美,写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写明子和小英子富有情谊的共同劳动,薅草、车水、打场、看场,掰荸荠和他们萌发的爱情,从而构成了一幅原始浑朴的诗意化图景。
1985年,汪先生说: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这三篇也是短小说。《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所以,他的小说越到后来,越是清新自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跌宕起伏故事,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结构框架,只呈现景象。这样写看似容易,其实极难。因为作者要保证情节本身的自然,又要保证文笔的动人,节奏的连贯。
如果看得足够多,你就能够感受到汪曾祺先生的变化。从早年的锋芒毕露,到《鸡鸭名家》的温厚平淡,但这时候的平淡里还有起承转合的迹象。再之后是《茶干》和《受戒》,斧凿痕迹没有了,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是信手写出来的,只能说,他的功力到了,到了你一点都看不出来斧凿的痕迹了。
晚年的汪曾祺先生绝对是将生活过得最有滋味的老头:品品茶,喝喝酒,听听曲,写写字,做做菜……汪先生曾说,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