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异”和“热爱”的哲学地位
——张世英先生哲学观简析*
2021-05-13张祥龙
张祥龙
一、引子:张世英先生的哲理新境
张世英先生的思想历程,活生生地展现出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转折,即从跟随传统西方哲学的思想范式,转到通过当代西方哲学的新视野而重新理解中国自家哲学。体现这个转折的著作,比如《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和《哲学导论》,都以各自的方式清楚地表明了张先生思想转变的方法轨迹,即从“纵向的超越”转向了“横向的超越”(1)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10页。。
“超越”意味着当事人不满足于局部的、实用的关怀和认知,而要超出之,获得根本性的整体领会。“纵向”与“横向”则指不同的超越方法。所谓纵向超越,说的是从具体的东西向上抽象以达到普遍性,即以主客二分为起点、专注于抽象概念和在场之物的哲学方法;而横向超越,意指关注“境”(情境、语境、时境、生境)、找到在场与不在场(无、隐蔽、过去)交融的方法(2)同上,第8—10页。前一种方法导致了统治西方两千多的“概念哲学”(3)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导言第5页。,使得哲学思想具有外在性、对象性、抽象性(4)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第51页。;后一种方法则是“超越主客关系的合一或物我交融”的渠道(5)张世英:《哲学导论》,导言第6页。,它在当代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中占主导,但各有特点。张先生最为认可当代西方哲学这种经过概念哲学或主客二分洗礼的后概念化哲学,认为只知追求“最普遍规律”的概念哲学已经或应该“终结”了;而中国古代哲学则需在经历主客分离思想即科学和概念哲学的粹炼后回复本性,获得自己在当代生活世界中的诗意境界、“民胞物与”的精神和“万物一体”的见地(6)同上,导言第5、8、10页。。
可见,张先生对当代西哲的汲取有整体视野中的方法自觉,不同于那些仅仅因为对某一当代西方哲学学派的研究而获得的认知。在这类研究中,有的甚至因自己理解的偏差(往往源自当事人依然持有的主客二分方法)而导致偏离和肤浅化,比如胡适对当代西方哲学流派之一实用主义的研究就未得其真谛,常常沦为实证主义,缺少以上所述的第二种方法的特质。而张先生对中国古代的哲理境界的回归,更让我们看到当代中国哲人的反省、再创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以前,张先生的哲学兴趣和所用方法,比如他为人所知的对黑格尔乃至新黑格尔主义的研究,基本属于上述的纵向超越的方法论范围。而改革开放以来,张先生的哲理研究的重大转变,既与新时代的自由空间和信息交流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归为他的思想素质和敏锐感受力,因为经历了同样的开放时代的许多其他哲学研究者们,并没有发生如此自觉和深刻的内在转化,特别是方法上的自觉转化。
在张先生的这个转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到海德格尔及相关哲理思潮的影响,这从他的书中对于海德格尔的频繁正面提及,对海氏(及相关哲学家比如约翰·萨利斯、奧托·柏格勒)的观点和著作的多次征引,尤其是他对海德格尔的高度评价——比如视他为“划时代人物”(7)张世英:《哲学导论》,第8页。——中可以见得。以下将通过审视他的哲学观,来深入理解张先生的这个转折。为了在有限篇幅中看出其中的思想脉络,将集中于两个词及它们牵涉的思路。这两个词就是“惊异”和“热爱”,西方古典哲学家们用“惊异”来说明哲学的开端,而张先生、海德格尔等横向超越的哲人则有深一层的看法,并牵涉出“热爱”(爱智慧之爱)的思想含义。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更进一步,以它们为桥梁来重新理解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
二、哲学的开端是惊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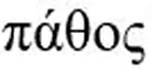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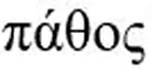
三、惊异只是哲学的开端还是持续地支配着哲学?
正是由于哲学的开端是惊异这种情绪,这个开端在西方哪怕是大哲学家那里也就只是开端,因为他们心目中的哲学本身只能是概念化的,根本没有情感的地位。在他们构造的“纵向的”概念体系中,无法容忍像惊异这样掺杂着非理性因素的东西。张先生与萨利斯一样,注意到亚里士多德讲惊异为哲学开端时(《形而上学》982b12),只讲到它的“‘现在’与‘过去’”(即上引吴氏译文中的“古今来”),而不言及其“将来”,其原因就在于“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追求必然引导到惊问开始时的‘反面’(《形而上学》983a15,19),即不再惊异、不再无知”(18)同上,第129页。。
张先生通过阐述他所熟悉的黑格尔的相关观点,来找到这种始热后冷的原因和后果。他引述黑格尔的话:“直观只是知识的开端。亚里士多德就直观的地位说,一切知识开始于惊异(Verwunderung)。在这里,主观理性作为直观具有确定性,当然只是未规定的确定性;在此确定性中,对象首先仍然满载着非理性的形式,因此,主要的事情乃是以惊异和敬畏来刺激此对象。但哲学的思想必须超出惊异的观点之上。”(19)同上,第130页。张先生认为,黑格尔将惊异只看作未得到思想规定的直观,而且是对象化的感觉直观,是“非理性的”,因此“否定之否定”——即黑格尔那里的“思想规定”——的辩证逻辑必然要将惊异这种仅止于“刺激”的东西抛在开端处。“在他[黑格尔]看来,惊异只属于直观这个初级认识阶段(他干脆把亚里士多德的惊异界定为直观的地位),一旦认识越出了直观的阶段,惊异也就结束了。而且黑格尔非常强调认识进展过程中的否定性的作用,认为‘推动知识前进的,不是惊异,而是否定性的力量’。这就比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把知识、哲学的目的与惊异对立起来了。”(20)张世英:《哲学导论》,第130页。说得很对,黑格尔已经基本丧失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残存的“调音”见地,将惊异只归于他心目中的盲目直观,因而与知识和哲学没有什么正经的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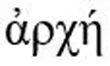
四、具有审美意识的诗意哲学
从读解海德格尔的这些文本及他人对它们的诠释中(25)张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参阅了两本书:(1) John Sallis, Double Truth, Albany, New York Stat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2)Reading Heidegger: Commemorations, ed. by John Sallis,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张先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不仅“哲学本质上应具有审美意识的惊异”,而且哲学就应该是“有审美意识的诗的哲学”(26)张世英:《哲学导论》,第134、133页。。上文已经阐述了这里讲的“惊异”与哲学的本质联系,但“诗”或“审美意识”是怎么回事?它与惊异是什么关系?实际上,上文讲哲学的调音向度时,已经隐含地触及到这个关系,但还需进一步探究。
张先生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明他的观点。除了引述并阐发以上第二节涉及的那些内容之外,他还写道:“海德格尔说:‘哲学就是与存在者的存在相契合。’(27)孙译:“哲学就是响应于存在者之存在。”(See Martin Heidegger, Was ist das-die Philosophie?, S.23.)又说:‘诗人就是听到事物之本然的人。’(28)Martin Heidegger, Hölderlins Hymnen “Germanien” und “Der Rhein”, Gesamtausgabe , Band 39, Frankfurt am Main: V. Klostermann, 1980,S.201.”(29)张世英:《哲学导论》,第134页。张先生是从Reading Heidegger: Commemorations (S.185)上转译此引文。那么,诗人所听到事物之本然,与契合于、响应于存在者之存在——即作为调音的惊异(30)本文第二节引用了海德格尔的一段话,表明作为调音的惊异是对存在者之存在的响应:“惊讶是一种调音[Stimmung〗,在其中,希腊哲学家获得了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响应[Entsprechen]。”([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第603页;Martin Heidegger, Was ist das-die Philosophie?, S.26。)——有何关系呢?当然有,但不是平行关系,而是源与流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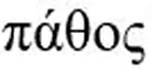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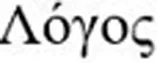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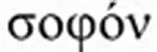
在张先生引用过的《海德格尔全集》第39卷中,海德格尔追随荷尔德林,将诗人称作“半神”(Halbgott),也就是位于神和世人之间的倾听本源(Hören des Ursprungs)者(39)Martin Heidegger, Hölderlins Hymnen “Germanien” und “Der Rhein”, Gesamtausgabe , Band 39, S.196.。神以怜悯的方式来听,海德格尔称之为“Erhören”,即应许之听,由此而将本源释放出来满足人的需要;世人则以“不能听到”(nicht-hören-können)的方式听,是为“Überhören”(漏听、没听见、听腻了)(40)Ibid.,S.200.。两者一高一低,但都听不到本源自身(Ursprung sich selbst)的声音,只是一个以赐予的方式,另一个以遗忘的、逃避的方式而对本源失聪罢了(41)Ibid.,S.200-201.。诗人的听既不是神的应许之听,也不是世人的漏听,“他的倾听承受着这受到约束的本源的极可怕性(hält der Furchtbarkeit des gefesselten Ursprungs stand)。这个承受着的倾听就是酷爱(Leiden,痛苦、激情、热爱)。而酷爱是半神[即诗人]的存在”(42)Martin Heidegger, Hölderlins Hymnen “Germanien” und “Der Rhein”, Gesamtausgabe , Band 39,S.201.。诗人的存在或本性就是酷爱,或承受着痛苦和可怕的源热爱。通过这种承受着的倾听,也就是痛苦之爱,诗人听到了本源性的本源(der ursprüngliche Ursprung,源本源),即那样一种本源,它还被约束在刚起跳(Anspringen)但还没有跳出而断裂(noch nicht springenden)的状态,所以还是那保持着自身完整性的本源(Ursprung noch ganz bei sich selbst),“诗人听到的就是这个本源”(43)Ibid., S.201.。哲学家通过惊异是否能听到这样的源本源,就要看其能否从惊异回溯到酷爱。如果这事成就了,那么张先生讲的“诗意哲学”也就得到实现。
五、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忧惧
如果在张先生的意义上来使用“哲学”(其中包括海德格尔讲的纯思想)这个词,那么我们的确可以有内在根据地谈论“中国哲学”。它既不会限于冯友兰等学者心目中的按科学和逻辑的概念所形成的中国哲学,也不会散漫到把什么文化的东西都放到哲学之中,以至于讲起“旅游哲学”“餐饮哲学”。中国哲学的逼真形态,同样是在情绪兴发中倾听源本源(der ursprüngliche Ursprung)之学。
那么,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什么样的情绪使人不甘世俗而被惊醒呢?首先是“忧惧”或“忧患(意识)”。《周易·系辞下》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的确,整部《周易》充满了这种情绪,“惧以终始”(44)胡远濬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易》六十四卦,一言以蔽之,曰‘惧以终始,其要无咎’。”(《劳谦室易说·读易通识》引自《周易》,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41页。),因为“天”“天命”“天道”或对中国古人而言的源本源,没有可以遵守的常规,“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不能以任何对象化的知识来测度;所以要听到天的声音,只靠祭天崇礼是不行的,“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同上)。但这天也不是任性的主宰,“聿修厥德,永言配[天]命”(同上)。可是,如何修德以配天命呢?这天命不是“靡常”的,因而让所有依凭现成者的努力几乎无效吗?在这个显意识和因果化理智失效之处,人的自发情绪或情感却还可以前行。“忧惧”所提示的,或在这种临危恐惧而生的忧思中,或可听到无声之音,并以身心与之共鸣和协调,则可能化险为夷。“夕惕若厉。无咎。”(《周易·乾·九三》)
《周易·系辞下》的一段话总结了这几层意思:“《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易》离我们不可远,因为一旦远了,就会将它当作传授占筮或道德知识的书来看待,也就体会不到其中的“道”或“天道”的微妙。这道屡屡迁移、变动而无定居,因为它的发生和维持结构乃阴阳刚柔、互补对生、生生不已,以至于追寻此道的卦爻之象并非象征某些现成者,而是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因而不可为典要,也就是不能将此《易》结构当作某种最高的原则和纲领。但就在这阴阳的刚柔相易(阴阳爻的交换、转移、变易)中,有那仅仅适合于此变易、也就是“唯变[变爻]所适”的“响应”式的认知产生,呈现为“度”,即阴阳相交而成韵的尺度。
更具体地讲,此度要在“出入”的变易中达到,并与“惧”(恐惧、畏惧)有内在关联。“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中的“出入”与“外内”互文,不仅“出”与“外”、“入”与“内”相关近义,而且“度”与“惧”与它们都相关。韩康伯曰:“‘出入’犹行藏,‘外内’犹隐显。”(45)[清]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67页。“外”指显现,“内”指隐蔽;所以“出”就是从隐蔽处“行”到“外”边,而“入”就是从显现处返回或“藏”身到“内”里来。为何在此“出入”中会产生超规律的“度”呢?因为“外内”或“显隐”的天然结构使人“知惧”,由此而感受到先于“典要”的东西。那为何“外内-显隐”会让人畏惧呢?因为其中“内”“隐”的那一维,就如上面引用的“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的那层隐藏着的天意,使任何现成者都失效,以至于每一次形成尺度都要从隐到显、从内到外地生成,或者说是隐显、内外交织着生发出来,唯变所适,没有什么预先的规定、后门、权势可用,所以让当事人知道畏惧、戒惕,于是以其全部身心投入其中,感受到阴阳变易的尺度。只有在此“惧”中,才会有“度”。
“明于忧患与故”的“明于忧患”既可以解释为“明察忧患”(此为不少注家的看法),又可解作“从忧患中得到明察”,就如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的两个“于”(於)字,意向相反。根据上下文及《易》作于忧患的意思,本文取第二种诠释,于是此句可解为“对易道的明察缘自忧患及其事故”。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出自忧患恐惧的易道理解是非理论和非对象化认知的,所以其发生就无需“师保”、但有“父母”,不仅因为这里“父母”可看作阴阳之天父地母,而且就在与生身父母的源关联之中,也会产生丰富的非对象性明察。
六、儒家哲学中的忧与爱
由于这个大背景,在儒家传统中,对于“忧惧”就有了两种对立而又互补的态度。一种是主张“不忧”“无忧”,如“仁者不忧”(《论语·子罕》)、“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在下位而不忧”(《周易·乾·文言》)、“无忧者,其惟文王乎”(《礼记·中庸》)。另一种则说圣人、仁者、君子“有忧”“明于忧”,这点上节已经反复征引和阐述,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忧。前一种是对象性的忧,也就是担忧于某种对象的缺失;而后一种是非对象性的忧,比如面对不可测之天命的忧。这个区别在“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这样的表述中得到直接呈现。非君子为了个人钱财的缺失也就是贫穷而忧,君子不忧于此,而只担忧大道不行于世间。而后一种忧的非对象性也就是不忧于现成者,使之与乐和爱内在相关。“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周易·系辞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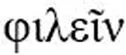
明代大儒罗近溪形容此爱最为亲切:“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声,想其叫时只是爱恋母亲怀抱,却指着这个爱根而名为仁,推充这个爱根以来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若做人的常是亲亲,则爱深而其气自和,气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恶人,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时时中庸而位天育物,其气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浑然也。”(46)[明]罗汝芳撰,方祖猷、梁一群、李庆龙等编校整理:《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74—75页。罗子讲的“啼叫”中的“爱恋母亲怀抱”,既是痛苦也是欢乐,既是先天也是后天,自发浑沦,实乃人类之源爱或爱源,所以被称为“爱根”。至于仁爱、对智慧之爱、对神之爱、民胞物与之爱,虽然宏大高远,却也只能“指着这个爱根”来成其爱、来“位天育物”,与天道本源相通相和。
此亲亲之爱与海德格尔讲的诗人之酷爱、思者之智爱,虽有相通之处,但毕竟有重大不同。后者即诗思之爱的直接体验者,是个人;而前者即亲亲之爱的体验者,则不止于个人而在亲人之间。海氏阐发的诗-思之爱,位于神爱与世人物爱之间,可称之为“半神”者对于源本源之爱,极为稀少。而亲亲之爱则全属于人间,为人人所共有,就是源本源之爱。它虽与赤子之身不可分,与人生实际经验、首先是家人经验共起伏,但其纯真性和可升华性,也就是提升自身境界的潜能,成仁取义的趋向,并不输于诗思酷爱。罗子称其为“赤子之心”:“天初生我,只是个赤子,而赤子之心却说浑然天理。”“真是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而直见乎天地之心,亦真是推之四海皆准,垂之万世无朝夕。”(47)[明]罗汝芳撰,方祖猷、梁一群、李庆龙等编校整理:《罗汝芳集》,第74、73页。《周易·复·彖》曰:“复[生生爱意的回旋复现],其见天地之心乎?”由此看来,在尼采、海德格尔等人那里发生的从“纵向超越”向“横向超越”的转向,在华夏的儒家这里是更加彻底化,因为诗人与世人的纵向隔膜,已在赤子之心与世俗之心的毕竟一体的区别中被横向超越化。
七、结 语
张世英先生认为,哲学的基本思想方法应该从传统的纵向超越转向横向超越,也就是从概念化、普遍化和主客二分化的方法转向境域化、显隐交融化和审美诗化的方法。而能说明这种转化的一个范例,就是西方哲学家们对“惊异”与哲学的关系的看法。为了显示它,张先生利用了海德格尔的阐述。由此,就在希腊思想刚刚进入纵向超越的哲学之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建立研究范式者都提出,惊异是引起哲学活动的开端。他们的看法来自更古老的热爱智慧者们的思想,而不同于后来将哲学完全概念理智化的主导倾向。惊异是一种揭蔽式的、而非仅仅心理意义上的情绪,它使得即便陷于迷途的人们也能在某些机缘中被震惊,感到自己的无知而去求知。但这两位哲学家毕竟是纵向超越式哲学的大师,不能容忍这样的情绪深入哲学腹地,所以都否定惊异对于哲学本身的意义。海德格尔则在惊异中看出哲学本该具有的思想素质,即对于源本源(存在者之存在的劝说或逻各斯)的响应,所以惊异(去蔽而揭示真理)不止于哲学的开端,而应是主导哲学、贯通哲学始终的本原动力和理解形态。
海德格尔指出,还有一种比惊异更原本的思想情绪——对智慧的热爱,主导着前柏拉图的古希腊思想者。这种智慧体现为“一即一切”的洞察,而只有诗人式的酷爱——让万物和生命相互占有式地结合起来的情感——能够与之共鸣。张先生从中看出了华夏的民胞物与和万物一体的睿智和哲理境界,所以提出“具有审美意识的诗意哲学”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既响应本源,也在某种程度上响应着人类历史所朝向的实际。传统那种通过概念化、体系化、力量化和操控化的抽象而形成的金字塔结构,正在丧失活力和控制力,而横向超越的“网”“境”“叠加”“(非定域)纠缠”等思路和实践,却在日新月异地发端和扩展,并在老结构失控处维持着一种横向的秩序。当然,这种现实中是否有张先生憧憬的“审美意识”和“诗意”,还是大成问题的。
如果我们遵循张先生的思路,在广义上使用“哲学”这个词,让它也包含海德格尔所谓的纯思想,那么就可以在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中看到两种情绪,即忧惧和亲爱(亲亲)始终发挥着开启和引导的作用,甚至(就亲爱而言)具有源本源的地位。忧惧让人感受到天命的深邃难测,唤起至诚意向,从而听到天道的无声之音。而忧在儒家那里的两面性——“君子忧道不忧贫”——引出乐的同等地位,并在爱、首先是亲爱那里找到自己的本源。只有亲爱使人可以对亲人同时又喜又忧,让赤子之心直现天理。而诗人和真正的哲人,即不失其赤子之心者。总之,哲学在横向超越的视野中,既是惊异之学,又是诗化思想之学;既是忧惧之学,又是亲亲而仁、万物一体之学。用罗近溪的术语和思路来讲就是:亲爱生成赤子之心,而赤子之心就是天地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