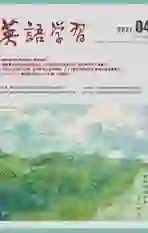梅仁毅教授访谈实录
2021-05-07姚斌李长栓黄磊
姚斌 李长栓 黄磊

姚斌:梅老师,201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将举办高翻学院成立40周年院庆活动。我在档案馆找材料的时候,看到您1974年9月曾和法语系的薛建成老师一起随中国代表团去美国纽约参加第29届联合国大会,并考察了当时联合国中文翻译的情况。你们回来后撰写了一份报告,详细记述了当时联合国翻译工作的情况,还对同声传译(以下简称“同传”)人才培养提出不少建议。所以我们想请您给我们讲讲那段经历。
梅仁毅:好的。我们当时是跟着外交部代表团一起去的,领队是时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黄华是中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我们作为外交部的工作人员随代表团一起去了联合国。我和薛建成老师的任务就是盯着翻译处的情况,重点关注笔译和口译两方面。
我们听了大会的翻译,之后翻译处又专门拿来一份联合国秘书长年度报告的中文稿让我看。我看了以后,挑出了一二十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还不是一般翻译上个别字词错误的问题。我把这个发现跟翻译处见面一谈,那边就“爆炸”了,后来我们代表团的人跟我说“你在那边放了一颗‘炸弹”,甚至还传说我要去接任翻译处的处长了,实际上学校根本没这个安排。
本来的计划是我们考察完成后,如果外交部同意,就可以跟联合国签约(指建立“联合国译员训练班”,以下简称“译训班” )。但回国后,由于国内的环境所限,外交部没有再提这个事,所以就压下来了,一压就压到了1979年。要不是改革开放,这件事还不知道要被压到什么时候。
我们完成了国家布置的考察任务,还带回来了比较有用的材料。现在可能学校还保留了当时联合国大会发言的最原始的录音材料,是我们当时用钢丝磁带拷了三四十盘带回来的。
姚斌:学校档案馆里陈列着一台可以放钢丝磁带的钢丝录音机,但钢丝磁带我没看见过。
梅仁毅:校史馆有一张1974年中国政府赴联合国代表团的合影(见文末图2),乔冠华、我和薛老师都在内。
李长栓:您当时去考察了联合国的口译情况,笔译那边考察了吗?
梅仁毅:笔译那边就是我看的这些材料,比如秘书长年度报告的翻译,然后再跟翻译处的人沟通。
姚斌:我们在《人民日报》的数据库里找到了关于那次代表团出访的报道,还有当时代表团的名单1。您能谈谈当时代表团在美国的活动吗?
梅仁毅:大概因为当时中美两国还没建交,我们在联合国考察时的活动被限制在方圆几公里内,在这个范围里出行不需要报备。但是要去像新泽西州植物园这样的地方,就必须报美国国务院批准,不批根本就去不了。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姚斌:我还在档案馆里面看到了一份手写材料,不知道作者是谁。材料记录了当时俄语系给莫斯科的联合国译员培训班打了一通电话,了解了莫斯科那边1973年至1974年译员培训的情况。
梅仁毅:当时去联合国考察时在全世界只有一个位于苏联的译员培训中心。我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联合国就想在中国也建立一个译员培训中心,于是外交部便动了心,让我们去考察。
我们当时在联合国考察时有一个很突出的感觉就是不改不行。如果不培养我们自己的翻译人才,实在不行。当时联合国的中文译员,比如口译组的人,基本上是来自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他们用的很多词汇都是港台地区的常用语,一听就不是我们大陆(内地)的用词。光这一点,要是不改过来,就很难办。
当时口译组有一位叫熊元夏、外号“小熊”的译员,他的口音非常标准,但用词还是改不了,因为他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当时联合国的文件,包括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翻译都是他们按这条路子翻下来的,让他们立即改变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要马上取代他们。我们心里很明白,没有人能够一下子取代得了这些譯员,尤其是口译员。我们当年培养出来几个口译员,就是周珏良他们给外交部培养的那一批。但是这些口译员已经是领导干部的译员,不可能再让他们到联合国去。所以我们要培养一批新人,可要这批新人要达到老译员那样的熟练程度,没有10年左右的时间是不行的,所以只能慢慢替换。
李长栓:2002年,我第一次到联合国做了3个月笔译。我是2001年考取笔译资格的,2002年第一次去。我去的时候,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下简称“国民政府”)继承下来的翻译都已经退休了。当时,甚至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71年后新招聘的翻译也已经退休了。我不知道新招聘的翻译是1971年后马上招的,还是过了几年又招的,但这批翻译是从全世界各地招募的爱国青年。他们有的在国外读书,有的长居中国香港,英文都很好,招聘他们也是因为他们英文好。但是他们没有专门学过翻译,或者没有实际做过翻译工作,到联合国去的时候,他们其实也不知道翻译该怎么做。
我曾经跟一位名叫叶卫南的老先生聊天,他说你们现在来联合国的这些年轻人,水平都很高,我们当时进来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翻译,是要翻译大致的意思还是要逐词翻译?起初,我们把每一个词都翻译出来,但发现这样翻译出来的话读不通。后来我们才慢慢知道是要把意思翻译出来。尽管如此,当时我们翻译联合国的文件还是有点逐词翻译的倾向。当然,这也是联合国文件的特点之一,灵活性不高。您去联合国考察时,在联合国做翻译的译员,全是从国民政府留下的翻译,还是已经有了新的译员?
梅仁毅:全部是国民政府留下的,因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才两年多一点,另外中美也还没建交,所以翻译处基本上没动。我们培养的最早出去的一批翻译可能就是周育强2他们这一批。他们大部分是1973年入学北外,1977年毕业留校,1979年进入译训班的。
姚斌:2019年是北外高翻学院成立40周年,但北外在翻译人才培养方面的历史应该再往前推。可以说,北外在我国高级翻译人才培养方面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梅仁毅:是的,北外培养高级翻译人才的主要推动者是周珏良,因为他参加了外交部的很多次国际谈判,包括日内瓦会议,所以他有经验,深知我们需要翻译方面的人才。还有一个关键的外国人,就是大卫·柯鲁克,伊莎白的先生。此外,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回来的熊德輗也很重要。这三个人的英文绝对没有问题,目标也很明确,就是给外交部培养翻译人才。
姚斌: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联合国秘书处跟中国政府提出建立译员培训机构,但是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很积极地回应。但到了1973年、1974年时,我们就在做一些准备工作了,是这样吗?
梅仁毅:对,就是这样的。联合国当时只知道北外,因为当时我国派驻联合国的两个翻译施燕华和她的先生吴建民都是从北外毕业的,施燕华是英语翻译,吴建民是法语翻译。所以联合国方面觉得北外有条件成立这样的机构。但是,我们从联合国考察回来以后,这件事被压下来了。另外其实学校也知道,光靠学校是办不成译训班的,当时学校没有跟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谈判签约的资格,必须要通过外交部。所以这件事就被搁置了,要不是联合国1978年重提这件事,可能还不知道要错过多少年。
姚斌:联合国当时很着急,谈判的时候他们希望译训班1979年春季就开学,中方坚持要延后,因为当时什么设备都没有。所以第一期译训班是1979年9月正式开学的。
梅仁毅:第一批耳机等设备都很紧张,因为采购设备需要钱,但这笔钱是由外交部批还是教育部批?1980年后,北外归教育部领导,需要教育部批。1980年前北外归外交部领导,当时外语学院在西院,俄语学院在东院。
李长栓:我在咱们学校网站上看到俄语学院建院之初,目标就是培养军事翻译。所以北外培养翻译的传统其实是从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外语学院的立院之本其实是翻译,是吧?
梅仁毅:是语言和翻译。我们当学生时,学校每周会组织一次国际形势报告,外交部的司长轮流来做主讲,包括王炳南等都来过。地区和区域研究的内容是必学的。
李长栓:北外所有学外语的学生都要学翻译吗?
梅仁毅:是的,翻译课一般在三、四年级开设。
姚斌:您在1974年去联合国考察之前,对同传有多少了解?
梅仁毅:我了解同传主要是通过周珏良他们培训“翻译班”3的那些人。我们当时有两个高级翻译班,但是当时更多的是交传,还不是同传。后来浦寿昌4来到北外,我和他比较熟,他跟我们聊到了这些,我们才对同传多了一些了解。
李长栓:所以当时北外的高级翻译班既有笔译,也有交传,还有同传?
梅仁毅:好像沒有同传。
李长栓:但是有口译是毫无疑问的?
梅仁毅:是的,但更多是交传,因为我们当时根本没有同传设备,包括在国际会议上做翻译,也都是发言人讲一段,我们翻译一段,没有用同传。
姚斌:所以您当时去美国参加第29届联合国大会,是第一次听人做同传吗?您有什么感觉?

梅仁毅:我感觉就是听完了同传的翻译以后根本连不起来,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好在我事先都拿了稿子,所以好办一点。我会先看稿子再听,这样稍微顺一点。当时口译员的翻译是不够顺畅的,我说的那位外号“小熊”的口译员的翻译是少有的让人听着很舒服的。尽管他的用词和我们不一样,但是我知道他在讲什么。
姚斌:我看您报告里面也提到了翻译处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两点,一是说政治意识不足,二是他们不熟悉我们的词汇。
梅仁毅:对,因为当时的口译员是国际组织的人转过来的,感觉他们翻译出的“皮”和“毛”还没附在你的身上,就是这么个分离的状态。所以我们的代表团跟翻译处的这些人只能客客气气的,无法干涉人家的工作。我们也没派人去,直到后来才有所改变。
姚斌:后来您提了大概六七条建议,包括北外应该在英语系本科高年级开设同传课程,还特别提到了翻译要熟悉各种带口音的外语,还说要购买设备等,这些建议后来落实了吗?
梅仁毅:后来北外成立了高级翻译班,这些建议才开始逐步得以落实。当时也有一些设备,但还是很原始的,不是很先进的设备。另外我提到的注意不同的口音这一点也很重要,比如很多南亚人的口音很重,尽管他们可能都是牛津、剑桥毕业的,文笔非常好,但就是改不了自己的口音。
李长栓:当时您是否有对译训班的课程设置或教学提出一些建议?
梅仁毅:当时联合国培训翻译没有一套固定的教材,如果有的话,我们肯定买回来。其实在中国办译训班对联合国来说也是开创性的。另外,联合国对译训班成员有一个要求,即所有翻译都必须会第二、第三外语。但这得靠你自己去想办法,他们才不管你,联合国没有这套培训机制。所以最后译训班完全是我们自己从零开始摸索出来的。
我们当时在联合国录制几十盘磁带,重点不是记录标准的英美音,而是专门搜集各种奇怪的发音。那些磁带里至少有一半是属于这一类型的。这样一来,至少开办译训班时有点物质上的材料。否则我们说了半天,也形容不出一个南亚人的发音来。
姚斌:我看您以前对翻译这方面是很关注的,还做过有关翻译的讲座。从北外翻译人才培养的历史来看,您对我们高翻学院整体的翻译人才培养有什么建议?
梅仁毅:因为联合国的发言是有一套固定模式的,所以我觉得翻译培养要关注两点。第一,学生的起点要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进来的学生水平不能太低,太低是培养不出来的。因为翻译是很challenging的任务,既需要输入,还需要输出,是“青春饭”。第二,除了了解联合国以外,学生可能还需要学习一点其他的内容。因为翻译或用英文演讲,本身是一种power,用词越精确,越能准确传达idea。所以我们要让学生知道,一下达到熟练的翻译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有点追求。学生有了这个意识,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放心了。
李长栓:我们还有不少学生通过联合国考试到联合国工作的。1992年之后,联合国就不再资助译训班了。我是1993年进入译训班的,虽然我花的钱还是联合国剩余的经费,但是联合国后来就没有再给过了。所以实际上,我不算译训班毕业的,我应该算高翻学院的第一届学生。我的老师所用的教学材料全部都是联合国的材料,所以我对联合国比较熟。后来我又通过了考试,可以去联合国工作,但没有去,而是远程做任务。联合国每隔大概3年会招一次笔译,每隔5年会招一次口译。他们现在招聘翻译时不是仅面向北外,而是面向全世界。我们的学生当然也有不少报考的,每次考试的成绩也非常好。前些年大概每招10个人,就有5个到5.5个是北外毕业的,其中5个里面又有4个是高翻学院毕业的。2020年,联合国中文处共招聘30个人,这是历来最多的,其中有12个是北外的,包括8个高翻学院毕业的。所以还是有这样一个传承,我们对学生的要求其实还是按联合国的要求;我们要求学生所达到的标准,也都是最高的标准。
梅仁毅:你们的集中训练还是不一样的。有些翻译系会设置很多理论类的课程,我对此从来都有所保留。我认为翻译这个工作,如果没有几十万字的翻译经验就无从谈起,也不会了解翻译的酸甜苦辣。翻译更多的是一种实践,所有的理论都是后期提炼出来的,没有人在做翻译的时候会想着理论。
姚斌:您当年是我国最早一批去联合国考察同传工作的,可以说是高翻学院的奠基人之一,能否请您从您的角度给高翻学院一些寄语?
梅仁毅:从我跟薛建成老师去联合国考察同传工作到现在已经过了40多年,高翻学院也成立40年了。一路过来是比较曲折的,但是经过努力,现在高翻学院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同传培养经验,目前在全国应该说是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的。祝贺大家!同时也希望大家不断努力,保持这个荣誉。因为翻译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所以大家要补充知识。特别是进入了新时代,现在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革时代,这意味着翻译人员也承担着更重大的任务。中国的声音不通过翻译是难以传达给世界的,所以翻译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努力,未来前景更好!
梅仁毅,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导,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姚斌,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副院长,入选201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卓越人才支持计划。
李长栓,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副院长。
黄磊,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助理翻译。
1 详见1974年9月26日《人民日报》第1版专栏《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我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等离京赴纽约 邓小平副总理、姬鹏飞外长等到机场送行》。
2 周育强,联合国译训班第1期(1979—1981年)毕业生,曾任联合国驻维也纳办事处口译科科长。
3 “翻译班”指北京外国语学院根据外交部制定的“培养高级翻译的十年规划方案”于1958年开始举办的专门培训外事翻译人才的研究生项目。
4 浦寿昌,江苏无锡人。1942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国务院总理秘书,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负责人,国家计委外事局局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