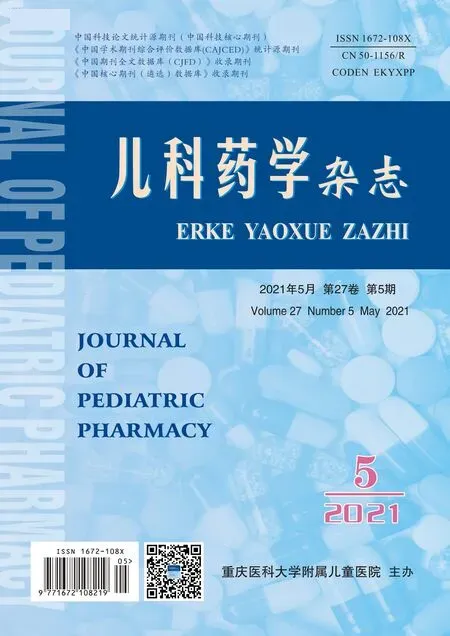某院144例儿童不良反应报告分析
2021-05-06杨文杭永付谢诚
杨文,杭永付,谢诚
(1.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安徽芜湖 241000;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苏州 215006)
我国儿童人口数量庞大,0~18岁儿童约3亿,占总人口的22.48%[1],但儿童专用药品缺乏[2]。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旺盛阶段,身体各组织器官发育尚不成熟,相关代谢酶及免疫系统发育尚不完善,药物在体内的药效学和药动学与成人差别较大,更易发生药物不良反应(ADR),是临床诊治的特殊群体。我国目前存在儿童专用药品缺乏[2]及儿童处方药说明书中临床试验、儿童用药、不良反应等多项内容缺失严重等问题[3],儿童用药安全及ADR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本研究对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收集的144例儿童ADR报告进行统计分析,探讨其发生特点与规律,以期为儿童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1 资料和方法
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2012-2018年收集的144例儿童ADR报告。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按照ADR与药物关联性评价、患儿性别年龄、药物分布、累及器官/系统及临床表现、临床转归等信息录入Excel表,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ADR与药物关联性评价
ADR关联性评价标准:(1)用药与ADR的出现有无合理的时间关系;(2)ADR是否符合该药已知的不良反应类型;(3)停药或减量后,反应是否消失或减轻;(4)再次使用可疑药品后是否再次出现同样反应;(5)反应是否可用并用药的作用、患者病情的进展、其他治疗的影响来解释。依据此标准,144例儿童ADR关联性评价为肯定3例(2.08%),很可能35例(24.31%),可能106例(73.61%)。
2.2 ADR患儿性别及年龄分布
144例儿童ADR中,男81例(56.25%),女63例(43.75%),男女比例1.29∶1;患儿最小1 d,最大18岁;学龄前期发生的ADR最多,共43例,占29.86%,ADR发生率最低的为新生儿期(<28 d),共11例,占7.64%。见表1。

表1 ADR患儿性别及年龄分布
2.3 引发ADR的药品种类分布
144例儿童ADR报告中,涉及药物品种61个,其中抗感染药是引发ADR最多的品种,共64例(44.44%);其次为中成药,共29例(20.14%)。抗感染药引发的ADR中,抗菌药物为57例(89.06%),抗病毒药物为7例(10.94%),其中抗菌药物以头孢菌素为主,共26例(40.63%)。引发ADR的药品种类分布见表2,引发ADR的抗感染药类别及分布见表3。

表2 引发ADR的药品种类分布

表3 引发ADR的抗感染药品类别分布及具体药品
2.4 ADR累及器官/系统及主要临床表现
144例ADR累及全身多个器官/系统,最常见的为皮肤及其附件损害,共74例(48.37%),其次为消化系统损害,共49例(32.03%)。本研究中有3例(2.08%)关联性评价为肯定的ADR,包括乳糖酸红霉素致腹痛 1例、氯雷他定致乏力及嗜睡1例、氨溴索致皮疹伴瘙痒 1例;3例(2.08%)罕见ADR,包括头孢曲松及甲氧氯普胺致手脚颤抖/抽搐各1例、布洛芬致视觉异常1例。其中9例ADR累及2个器官/系统。见表4。
2.5 ADR临床转归
144例ADR患儿在出现临床症状后,予以停用可疑药物或抗过敏等对症处理,痊愈94例(65.28%),好转47例(32.64%),不详3例(2.08%)。

表4 ADR累及器官/系统及主要临床表现
3 讨论
3.1 ADR与药物关联性评价的关系
本研究ADR关联性评价中,肯定及很可能数量较少,可能数量较多,与部分文献[4]报道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儿童作为用药的特殊群体,临床上在发现或怀疑ADR时,出于用药安全考虑,往往会停用疑似药品,导致肯定ADR的数量较少。本研究中20.14%的ADR由中成药引发,而中成药说明书中“不良反应”多为尚不明确,国内外也缺乏相关文献资料,导致较多中成药的ADR关联性评价为“可能”。另外联合用药及反应可根据患儿的病情进展进行解释时,也会导致无法准确评判ADR关联性。综合以上因素,ADR关联性评价中肯定和很可能的数量偏少,可能的数量偏多。
3.2 ADR与性别及年龄的关系
144例儿童ADR中,男女比例1.29∶1,与郑新等[5]报道相似,可能与我国儿童性别构成比相关。发生ADR的患儿主要集中在6岁以下,与汪洋等[6]研究结果一致。儿童身体各器官发育尚不成熟,免疫系统功能相对较弱,缺乏足够的防御能力,肝药酶系统不完善,药物在体内代谢可能不完全,肾脏对药物排泄能力较差,以上因素都可能引起ADR。
3.3 ADR与药物品种的关系
144例儿童ADR中,抗感染药物引起的ADR在药品种数(17例,27.87%)和例数(64例,44.44%)方面均为最多,与既往[7]报道一致。其中又以头孢菌素类居首位,大环内酯类其次,与闫虹等[8]研究结果相似。也有研究[5]表明大环内酯类是引发儿童ADR较多的抗感染药,可能与原患疾病及医师用药习惯有关。本研究144例ADR报告中,114例(79.17%)患儿原患病为感染相关疾病,以呼吸系统疾病为主(103例,71.53%),符合相关报道[9]。庞大的基数导致抗感染药使用频率高,ADR发生也增多,抗感染药的不合理使用也可增加ADR的发生率,此外,由于儿童组织器官发育不成熟,可能导致药物蓄积,血药浓度的波动也易诱发ADR。
中成药引起的ADR共29例(20.14%),仅次于抗感染药,与相关文献[4]一致。中成药成分较多且复杂,稳定性较差,有效成分无法标准化,部分成分含有较多的致敏原,易诱发变态反应[10]。儿童专科处方药品的缺乏及使用的限制较多,临床可选用的儿童药品范围较窄,因此在儿科病区中,中成药的使用量较大,ADR发生率也随之增加,且部分医师及患者认为中成药更加安全,导致中成药滥用,进一步增加了ADR的发生率。目前对儿童中成药ADR的报道较少,临床重视不够,应规范中成药的合理应用,尽量避免使用中药注射剂,以口服制剂为主。
3.4 ADR与累及器官/系统的关系
我院患儿ADR以皮肤及其附件损害为主,主要临床表现为皮疹、瘙痒及潮红等,与既往报道一致[11]。其次为消化系统损害,如恶心、呕吐及腹泻等,可能与皮肤黏膜系统及消化系统的损害症状较明显、易发现有关。由于表达能力较差,儿童患者往往不能准确描述ADR的表现,这就需要医务人员密切观察,加强监测,充分与患儿及其家属沟通,以获取准确的信息,并及时对ADR进行处理,减少对患儿健康的损害。
本研究中有3例罕有文献报道的ADR患儿。(1)注射用头孢曲松钠1例:患儿静脉滴注头孢曲松10 min后,出现四肢颤抖、脸色发绀、口唇发紫表现,立即停止输注并予以高流量吸氧,30 min后,症状逐渐缓解,考虑为头孢曲松引起的ADR。其具体机制不明,可能是由于β-内酰胺类药物可竞争性抑制大脑中γ-氨基丁酸活性,导致神经刺激阈值下调,进而引发颤抖、抽搐样症状[12]。(2)甲氧氯普胺注射液1例:患儿肌肉注射5 mg甲氧氯普胺5 min后,出现手脚震颤、颈硬伴后倾表现,立刻静脉补液加快排泄,肌肉注射0.3 mg东莨菪碱5 min后,症状逐渐缓解,考虑为甲氧氯普胺引起的锥体外系反应。其机制为甲氧氯普胺作为多巴胺(DA)受体抑制剂,可通过血脑屏障,阻断DA受体,胆碱能受体兴奋,表现为震颤、面容呆板等症状,儿童血脑屏障发育不成熟,多巴胺产生不足等因素更易导致ADR的发生[13]。(3)布洛芬口服液1例:患儿口服8 mL布洛芬口服液后,渐感视物不清、模糊,无眼痛、眼胀,遂停服药物,1天后患儿视力逐渐恢复正常。发生机制可能为布洛芬作为环氧化酶-2(COX-2)抑制药,可抑制前列腺素(PGI2)释放,进而抑制血管内皮细胞分泌NO,使视网膜血流量下降,此外,COX-2抑制剂尚有降低眼内压的作用,以上因素共同导致视觉异常ADR的发生[14]。
综上所述,儿童作为特殊用药群体,由于独特的生理特点,其ADR的发生率较成人高。医务人员应对儿童用药密切关注,患儿家属应正确认识ADR并积极配合治疗,在多方协作的情况下减少儿童ADR的发生,提高儿童用药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