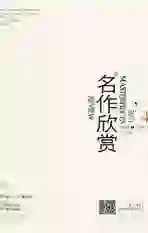浅析《聊斋志异》之“双美”理想
2021-05-04刘佳玥
摘 要:《聊斋志异》中,有不少篇目同时出现了两个女子形象,如《莲香》《娇娜》《小谢》等。蒲松龄利用人物之间的对照关系,塑造了或性格迥异,或德貌双馨,或知心至情的双女形象,来寄托其“双美”理想。这种“双美”理想不仅仅停留于美貌之“双美”,还表现出蒲松龄对女子品德之“双美”的进步认识,对女子才情之“双美”的肯定和赞扬,以及对理想中“知己之爱”的深入思考。本文围绕“双美”理想之丰富内涵,浅析其背后蕴含的作者遭际之投射和社会文化意蕴。
关键词:“双美”理想 内涵层次性 社会文化意蕴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抒情写志的载体。“联系作者蒲松龄一生的境遇和他言志抒情的诗篇,则不难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由他个人的生活感受生发出来,凝聚着他大半生的苦乐,表现着他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憧憬。”a《聊斋志异》中的双女形象同样寄寓着蒲松龄的理想。学界关于《聊斋志异》“双美”内涵的研究主要是从男性幻想、男性立场或者男权印记的角度来分析,如《男性视角下的爱情幻想——〈聊斋志异〉中的“双美”故事》《浅析〈聊斋志异·香玉〉中的“双美”模式》《同枝异花 各擅其妙——论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双美情结》等论文。这些研究不论是提及情人、腻友还是妻妾,都将“双美”单纯地认定为只是男性性欲的幻梦,并未对“双美”理想之丰富内涵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分析。
本文意图补充《聊斋志异》之“双美”研究,从貌、德、才、友四个层面进行分析,认为《聊斋志异》之“双美”理想不仅仅局限于坐拥“双美”的情欲渴求,还抒发了作者对德才兼备的女子的衷心赞扬,表现了作者对纯洁的“知己之爱”的美好幻想。而这种“双美”理想,又与作者本人际遇、社会主流思想的变化,以及文化渊源是密不可分的。
一、绝色佳人之“双美”理想
《聊斋志异》出现双女形象的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描写了男主人公与两个女子的爱恋艳情。不论结局男子是否实现了坐拥双美的理想,他们都曾经拥有过两段难忘的艳遇,在同样貌美无双但性格各异的女子那里得到情欲的充分满足。
《莲香》通过对比的手法,刻画了两个性格鲜明的女子——狐女莲香和鬼女李氏。莲香心胸坦荡,面对桑生诘问,并没有否认,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狐的身份,反而有理有据地辩驳:“纵狐何害?”b而李氏则心思细腻、小心谨慎,对自己鬼女的身份遮遮掩掩,一再叮嘱桑生不要泄密。听到有人说出她的真实身份,她坚决否认,以断绝与桑生来往为要挟。莲香发现桑生因与鬼女交往而身体衰弱,便为他细心医治,为了桑生尽快痊愈拒绝交欢,尽显成熟稳重;而李氏为了一己之乐,夜夜与桑生欢好,导致他染上重病,略显轻浮莽撞。莲香脾气火爆,因为桑生不愿听从劝告与李氏断绝来往,怒而离开,但她有情有义,带着灵药回来救桑生;而李氏性格柔弱,暗自落泪来证明自己并非鬼物,在莲香面前羞于与桑生“接口而唾之”c。莲香也有开朗活泼的一面,揶揄李氏:“妹所得意惟履耳!”d这更像是姐妹之间的调笑。李氏因无法陪伴在桑生身边而抑郁不乐,只能远望即去,百般躲避与桑生相处,让人读来对她多了几分怜爱之心。“作者每由此而及彼,又由彼而及此,处处双写,又处处由同中见异,表现人物情感的变化极细腻,而表现人物性格的差异也极明显。”e
关于“情”,性格差异明显的莲香与李氏都钟情于桑生,出于爱生而复死、死而复生,给桑生带来情感的慰藉;关于“欲”,两个女子为了心爱之人的健康,拒绝与桑生欢会,对欲的克制正是爱的彰显。这表现出作者对爱的推崇和向往。
类似《莲香》这样坐拥“双美”的篇章不在少数,如《荷花三娘子》《萧七》《翩翩》《巧娘》《阿绣》《陈云栖》等,但并未都能如《莲香》一样达到为爱禁欲的高度。如《萧七》中,徐继长见到萧七后,“神魂眩乱,但欲速寝”f,趁六姊醉酒轻薄她,没有半点儒生的矜持守礼。他对美色的欲望表露无遗,而看不到半点情爱的痕迹。在这里,作者绝色佳人的“双美”理想以美色为基础,在对肉欲与情爱的渴求之中摇摆不定,意图追求爱欲兼得。
绝色佳人之“双美”理想的形成原因,一方面与作者密切相关。文学的功能之一就是作为文人士子内心缺憾的补充方式,为他们平淡枯燥甚至贫困窘迫的现实生活带去精神补偿。作者在《小谢》故事的结尾以“异史氏曰”的方式感叹:“绝世佳人,求一而难之,何遽得两哉!”g作者在这类篇章中寄寓的“双美”理想更侧重两位绝世佳人的美貌,她们为男主人公孤独寂寞的生活带来感情上的欢愉和肉欲上的满足。
现实生活中,蒲松龄的科举之路并不顺畅,以县、府、道接连第一进学的他却在乡试上屡次受挫,他的大半生是在坐馆授学中度过。因长年在外教书,蒲松龄与妻子刘氏聚少离多,屡试不中的痛苦、孤寂的生活、现实的残酷让他只能在文学作品中寄托自己的幻想。《聊斋志异》中孤独寂寞的书生形象无一不是受到作者本人心境的投射,“双美”的设定是作者编织出两个美貌的女子自荐枕席的幻梦,来作为落寞生活的精神补偿。所以,绝色佳人总是成双成对地出现在《聊斋志异》中,给予书生不一样的情感慰藉和欲望满足:有不苟言笑的嫦娥,便有狡黠活泼的颠当;有痴情火热的香玉,便有理智冰冷的绛雪;有多愁善感的巧娘,便有含蓄羞涩的三娘;有调皮大胆的秋容,就有安静柔弱的小谢。
另一方面,古代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为绝色佳人之“双美”理想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大家闺秀般的妻子是贤淑温良,小家碧玉般的小妾是美艳可人;妻子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小妾极尽风情、吟诗弹琴。这才是文人心目中理想婚姻的最佳状态。”h文人士子对妻贤妾丽的幻想不断地在文學作品中表露出来,作者蒲松龄也未能免俗,塑造了不少妻妾和睦的绝色佳人,如《陈云栖》《嫦娥》《莲香》《小谢》,等等。
作者不满足于与两位绝色佳人的一时欢会,意图将“双美”纳入家庭轨道。然而让两位绝色佳人走入家庭的设定,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两个女子之间的关系。书中或塑造理想化的拥有不妒美德的妻子形象,如徐继长的妻子、嫦娥;或使妻妾之间拥有姐妹情谊,如云栖与云眠、庚娘与唐氏;或制造变故使两人消除妒忌,如小谢与秋容、莲香与李氏,为绝色佳人之“双美”理想安排了一个家庭和美的结局。
二、贞烈贤德之“双美”理想
作者蒲松龄的“双美”理想并不仅仅停留在外在美色的层面上,还涉及了内在品德之“双美”。在女子多以美色侍人的时代,蒲松龄敏锐地发现并且书写女子具有的高尚品德,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的女性观念。这类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对理解作者及其所处时代女性观念的细微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庚娘》刻画了忠贞节烈的两个女子——庚娘和唐氏。机智的庚娘察觉到王十八的歹意,劝告丈夫金大用不要与他同行,但是丈夫却因一时不忍没有推却,导致全家遭难。庚娘遭逢巨变却临危不乱,假意答应与王十八归家,趁他醉酒之时手刃仇人,继而自尽。庚娘表现出的冷静、睿智、勇敢,足以称得上是“女中丈夫”。作者也不禁称赞道:“至如谈笑不惊,手刃仇雠,千古烈丈夫中,岂多匹俦哉!谁谓女子,遂不可比踪彦云也!”i她的节烈品行感动了众人,得以风光大葬。而王十八的妻子唐氏也是一个知晓大义的女子,得知丈夫谋害金大用一家、霸占庚娘,她愤怒地喊出:“便死休!诚不愿为杀人贼妇!”j在古代,作为妻子首先要遵守的就是三从四德,唐氏没有对丈夫一味顺从,而是公然指责丈夫的所作所为,甚至以死抗争,令人敬佩。她在被人救起后,声称自己是金大用的妻子,既是出于愧疚,也是表明与贼夫王十八决裂的姿态。
作者在《庚娘》中塑造的这两位女子都具有忠贞节烈的美好品德,体现出女子的聪明才智和刚强骨气,全然不输于男子。她们的美包括但不局限于外在的美貌,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美德光辉。作者为我们呈现了“双美”理想更深一层的内涵,不再只停留于对美色的欣赏,而是进一步涉及女子品德之美。
认识到女子的独立个性以及价值,是女性价值观转变的标志。从社会背景来看,随着王阳明心学的传播,“妇女解放”的新观念在在晚明思潮中涌现,一些知识分子从女性立场出发为女性发声。如李贽《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k晚明以来,进步的女性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蒲松龄,他在《聊斋志异》中刻画描绘了许多个性鲜明、独立意识强烈的女性形象,书写女子身上的道德闪光点,衷心赞美她们的光辉品德。
而蒲松龄的个人经历对《聊斋志异》中倾向于品德的“双美”理想也有一定影响。科举失意的蒲松龄因生计所迫,长时间在外坐馆,妻子刘氏独自一人辛苦持家,上养公婆,下育儿女,支撑起本不富裕的生活。“受到孤独寂寞煎熬之苦的蒲松龄对刘氏充满了敬重和感激。”l刘氏具有中国女子的传统美德,是蒲松龄的贤内助,不仅知书达理,还有着乐观豁达的人生识见,常常给予失意的蒲松龄以宽慰,这让他对女性内在品质的思考更为深刻。如《白于玉》中那个倔强坚强的葛氏女子。吴生因与紫衣仙女的露水情缘,有出家归隐之志,想要推却与葛氏女之婚约,但是葛氏女态度坚决,定要从一而终,嫁过去后“女外理生计,内训孤儿,井井有法”m。哪怕吴生决意出家,她也不似一般女子设法挽留,反而坦然处之,独自将养子抚育成人。葛氏女心意之坚定,处事气度之不凡,绝不亚于男子。葛氏女的身上仿佛可以看到刘氏的影子,但又不同于传统礼教下只知三从四德的妇人,多了几分坚忍和果断,是经过作者理想化的新型女性形象。
总而言之,在社会思潮和作者个人经历的双重影响下,蒲松龄认同封建礼教约束下的女子德行之美,又意识到她们具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和高尚情操,将女子的品德之美纳入其“双美”理想之中,较之于美色之“双美”更深一层。
三、知文晓乐之“双美”理想
作者蒲松龄的“双美”理想既以色为美、以德为美,又以才为美。他把对于女子才情的美好希冀寄托在《聊斋志异》之中,塑造了颇有才情、通晓音乐的双女形象,编织出对于“红袖添香”“琴瑟和鸣”的幻梦。
《小谢》构思巧妙,描写了女鬼小谢与秋容对陶望三由调笑戏弄,到拜师学文,再到相恋相守的故事。小谢与秋容虽然“并皆姝丽”n,但性格各异:秋容大胆戏弄陶生,实施恶作剧,而小谢只是笑着观看;秋容心思细腻,敏感易妒,妒忌陶生教小谢写字,为自己不如小谢而惭愧落泪,而小谢茫然不觉。两人在学业上也大有差别,小谢书写娟好,而秋容却在读经作诗方面聪颖非常。两鬼一人因书文结情,不可谓不奇。读书写字成为他们关系变化和情感加深的一个契机,《小谢》中的两位绝世佳人以学生的身份常伴陶生左右。陶生对小谢和秋容悉心教导、鼓励宽慰,两个活泼调皮的女鬼变为认真好学的女学生。文中并没有侧重美色盈于目的感官享受和情欲色彩,反而充溢着读书写字的风雅之气,因学结情,而非因貌生欲。
与之类似的还有《宦娘》这一篇,宦娘因温如春的悠扬琴声而倾心不已,却因人鬼殊途不能如愿结秦晋之好,只能暗中帮助温如春,为他匹配佳偶;善筝的良工同样也是闻琴而心动,对温如春芳心暗许。温如春与良工最终与宦娘相见,宦娘如愿学到了温如春的琴法。三人切磋研习音乐,大有知音的惺惺相惜之感。两人一鬼因琴筝结缘,不可谓不雅。小说中,宦娘和良工都具有知晓音乐、善弹琴筝的突出特点,都能与温如春进行音乐上的精神交流,超越了基于性欲渴求而塑造的双女形象,更为侧重男女之间精神、志趣上的和谐一致,表现出作者蒲松龄对女性之美更高层次的思考。
《聊斋志异》中女子的文人化倾向不单单体现在这类双女形象的篇章中,琴棋书画不再是大家闺秀的专属特征,甚至狐女、鬼女、花妖精怪,都可以吟诗作对、抚琴下棋。這种文人化的女性形象寄寓着包括作者在内的文人士子对美好女性的希冀,期盼与情人之间具有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交流。在此基础上,作者的“双美”理想在品德层次上更进一步,探讨才情之“双美”。《聊斋志异》中这些成对出现的女子对文化和音乐有着孜孜不倦的热忱,马瑞芳称其为“华夏雅士风采”,认为“留仙常将女性置于深邃的华夏文化氛围之中”o。才情之“双美”使得作者的“双美”理想实现了从外至内、从表及里的层层攀升,已然到达女子才智的高度,全然不同于着眼于双女美色的“双美”理想内涵。
四、红颜知己之“双美”理想
作者蒲松龄的“双美”理想之最高层次应当是对红颜知己的幻想。在那个男女大防非常严格的时代里,蒲松龄对男女关系有着自己的独特思考。在《聊斋志异》出现双女形象的篇章中,他认可、艳羡男女之间纯洁的友情,如《娇娜》《宦娘》;也赞扬“知己之爱”的美好,如《香玉》《连城》,艳妻良友是作者所追求的最高理想。
《娇娜》描写了孔生与娇娜共患难的友情。孔生与娇娜的初次相见,是娇娜为孔生疗疾,生“望见艳色,嚬呻顿忘,精神为之一爽”p。孔生冒死救下娇娜,颇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意味;而娇娜同样拼力救治孔生,使他死而复生。孔生与娇娜的友情经历了多次变故的考验,生死相托,虽然没有成为夫妇,却成为良友。作者评价:“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q孔生同时得到了娇妻和腻友,实现了作者蒲松龄在《娇娜》中寄寓的一妻一友的“双美”理想,但他并没有混淆友情与情欲之间的界限,孔生与娇娜之间的友情是不掺杂性欲的。作者高度赞扬这种男女之间的纯洁友情,肯定其存在,并且认为其远胜于情欲关系。作者试图跳出男女情欲关系的框子,将女性形象从单纯作为男性性欲工具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塑造与男性平等交友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具有一定进步意义。
《香玉》塑造了香玉和绛雪两个势均力敌的女性形象,表现出爱妻良友的“双美”理想,但混淆了友情与情欲的界限,将其二者视为可分可合的关系。香玉热烈痴情,自荐枕席;而绛雪性情疏落,对黄生避犹不及。香玉身死,反而使得黄生与绛雪得以接触,两个人为香玉而悲叹,和诗言情,祭奠香玉。绛雪严正声明:“然妾与君交,以情不以淫。”r作者借绛雪之口,说明了红颜知己的交往标准是“以情不以淫”,作者将“情”与“淫”严格区分开来,认为男女之间存在的知己之情应当不涉及淫欲。但是,作者又安排了绛雪代香玉慰藉黄生的情节,等到香玉归来,绛雪笑称:“今幸退而为友。”s可见,作者在红顏知己的思考上不时会混杂对绝世佳人之“双美”理想的追求。书生在红颜知己身上,不仅可以得到精神上、感情上的慰藉,还可以在艳妻缺位时得到肉体上的满足,知己之“爱”与“欲”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
《连城》中,作者对红颜知己的矛盾态度得到了完美融合,提倡建立在“知己之爱”基础上的婚姻,妻子和知己在连城这个人物身上实现了统一。乔生虽生活贫苦,但重情重义,才气过人。连城长于刺绣,熟习诗书。但《连城》并没有落入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的固定模式,两人的相知相恋以情不以貌。虽然还没有见面,连城却能以诗相知,逢人便称赞乔生的才华,还赠金帮助他读书。因此,乔生也同样视连城为知己,甚至不惜为素未谋面的她割肉疗疾,报答知己之恩。乔生不追求美色、不贪求成婚欢好,死后仍希冀见连城一面,这种完全出于知己之爱的痴情,令人动容。在这篇作品中,宾娘是作为连城与乔生“知己之爱”的陪衬出现的。虽然结尾依旧落入了“好事成双”的俗套中,但是“这种寄托了作者满腔热情的知己之爱,显然超出了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婚姻观念,闪耀着民主主义的熠熠光彩”t。
作者红颜知己的“双美”理想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男女情爱的固定模式,但是由于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其作品又存在着反复和动摇,会不时混淆友情与爱情,甚至将友情作为情欲的代替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新旧思想交替过程中的矛盾与徘徊。
综上所述,《聊斋志异》中的“双美”理想可以分为由浅入深的四个层次:一是美貌之“双美”,是作为作者现实生活的精神补偿,幻想性格各异的绝色佳人来消遣孤独寂寞的时光,是站在男性立场上塑造的充满情欲诉求的双女形象。二是品德之“双美”,相较第一层次已经有所深入,超越皮相的比较,看到了女子内在的美德,并且热情地加以赞扬,表现出作者较为先进的女性观念。三是才情之“双美”,赋予女子深厚的音乐文化修养,可以与男主人公实现精神上的交流和共鸣。作者的“双美”理想已经产生了由貌而德,由德而智的变化,可谓层层深入。四是一妻一友之“双美”,表现了作者对于男女关系的新认识、新思考,作者认为男女之间既存在纯洁的友情,又可能在“知己之爱”的基础上发展为爱情,但是对此的认识仍旧存在一定模糊和矛盾之处。在《聊斋志异》中,作者蒲松龄从貌、德、才、友四个逐渐深入的层面表现了其“双美”理想。探究不同层次的“双美”内涵以及隐藏在背后的社会文化意蕴,对我们理解作品主旨更有帮助。
a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2002年重印),第321页。
bcdfgijmnpqrs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第95页,第95页,第341页,第331页,第164页,第162页,第144页,第328页,第24页,第26页,第675页,第677页。
et 马振方主编:《聊斋志异名篇评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1页,第130页。
h 王锐:《美与德的结合——〈聊斋志异〉“双美”婚姻模式再解读》,《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8期,第20页。
k 〔明〕李贽:《焚书·续焚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9页。
l 尚继武:《〈聊斋志异〉叙事艺术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0页。
o 马瑞芳:《幽冥人生: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3页。
参考文献:
[1] 蒲松龄.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马瑞芳.幽冥人生:蒲松龄和《聊斋志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3] 马瑞芳.蒲松龄评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4] 马振方主编.聊斋志异名篇评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5] 尚继武.《聊斋志异》叙事艺术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
[6]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7] 李贽.焚书·续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聊斋志异鉴赏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9] 王锐.美与德的结合——《聊斋志异》“双美”婚姻模式再解读[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J].2013(8).
[10] 曾丽容.同枝异花 各擅其妙——论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双美情结[J].蒲松龄研究,2013(2).
[11] 吴琼.《聊斋志异》同篇双女情节及其文化内涵[J].蒲松龄研究,2007(3).
[12] 姚颖.“双美共侍一夫”故事模式的背后——以《聊斋志异》和子弟书“志目”为例[J].蒲松龄研究,2011(4).
[13] 杨麟舒.男性视角下的爱情幻想——《聊斋志异》中的“双美”故事[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4(10).
[14] 孙亚男.浅析《聊斋志异·香玉》中的“双美”模式[J].鸡西大学学报,2014(5).
作 者: 刘佳玥,首都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