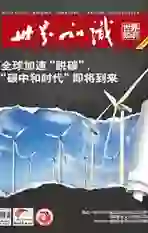聊聊希腊的电影与电影人
2021-04-30沈健
沈健

“言必称希腊”,此言耳熟能详。
20年前美国好莱坞制作了一部爱情喜剧片《我的盛大希腊婚礼》,描述了一位希腊裔二代移民女性违背家庭传统,嫁给非希腊裔人士所引发的连串家庭风波。片中的父亲和母亲是第一代希腊移民,在美国经营一家希腊餐馆,深为自己的血统而骄傲,以致百般阻止女儿嫁给非希腊裔,令人忍俊不禁。
希腊人是有理由骄傲的。古希腊文明在哲学、文学、天文、建筑、体育等诸多方面对欧洲乃至世界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曾感慨“我们都是希腊人。”
希腊电影也拥有辉煌历史,一代又一代希腊电影人骄傲地记录了自己国家的文明。希腊电影的开拓者、摄影师马纳基亚兄弟没有像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那样拍摄《火车进站》《工厂大门》之类的“时代新奇”,而是将镜头伸向神像、庙宇、陵寝、奥林匹克仪式等文明遗存。
希腊电影人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于20世纪50年代重启希腊电影,该国导演米哈利斯·卡科伊亚尼斯成为这一时期享誉世界的电影大师,他于1954年拍摄的喜剧片《意外之财》享誉戛纳电影节,次年创作的《斯泰拉》获得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卡科伊亚尼斯的代表作《希腊人佐巴》创作于1964年,展现了希腊民族的乐观与智慧,一举获得当年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七项奥斯卡提名,最终捧回三座小金人。
1974年,希腊结束君主统治确立共和制。隨着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以安哲罗普洛斯、乌尔加里斯为代表的一批希腊导演重新开展对“希腊精神”的探索,由此开创了“新希腊电影”。
安哲罗普洛斯于1975年创作的《流浪艺人》被公认为希腊最杰出的史诗电影。影片用高超的摄影技巧将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浓缩在80个镜头之中。1998年,安哲罗普洛斯拍摄了《永恒和一日》,讲述了一名旅居意大利的希腊诗人为参加独立战争而回到祖国的故事,主人公意欲创作却发现已失去母语写作能力,表现出深深的忧伤,本片摘得戛纳金棕榈大奖。
进入新世纪,一批希腊青年导演崭露头角,寇斯塔·卡帕卡斯的《薄荷的滋味》、拉金斯·帕帕史塔西的《假面人生》、瓦西利斯·杜罗斯的《月光提琴手》、潘妮·潘娜尤特普鲁的《难说再见》等尽管十分商业,仍保持着希腊民族的骄傲。
2007年,一部投资超过千万美元的影片《埃尔·格列柯》成为希腊电影史上的新里程碑。影片再现了希腊画家埃尔·格列柯的艺术人生。“格列柯”一词本身的意思就是“希腊人”。导演雅尼斯·斯玛拉格蒂斯成功塑造了一位敢于同无知和黑暗作斗争的希腊英雄,成为“希腊精神”的现代写照。
1981年希腊加入欧盟后,其人均GDP曾持续增长,在2008年达到3.2万美元。但在2009年,希腊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经济连续八年下滑。尽管经济萧条,希腊电影人却没有沉沦。欧格斯·兰斯莫斯执导的《狗牙》在获得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大奖后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之后,兰斯莫斯又接连拍摄了《阿尔卑斯》《龙虾》《圣鹿之死》《宠儿》等影片,被誉为“最具希腊历史底蕴的现代派电影人”。2014年,中国观众通过《小英格兰》一片认识了希腊当代著名导演潘多利·佛加瑞,这部影片在第1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三项大奖。
2020年9月,希腊议会批准中希两国政府签署的电影合拍协议。
今年3月,希腊将隆重庆祝独立200周年。为此,希腊政府专门成立“希腊2021委员会”,其主席杰洛普洛斯·达斯卡拉奇说:“周年纪念不仅是要回顾历史,更要让我们了解并记住希腊从何而来,去向何方。”
2019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时说,“中希友好不仅是两国的合作,更是两大文明的对话”。2021年是“中希文化和旅游年”,两国人员交往受新冠疫情影响一时难以恢复正常,好在两大古老文明的对话仍将通过电影等桥梁得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