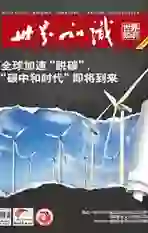新冠疫情凸显中东欧罗姆人融合难题
2021-04-30徐凤江
徐凤江

很大程度上說,人类历史是一部人类与瘟疫之间的斗争史。在疫情面前,最无助和脆弱的当属社会边缘群体。罗姆人是欧洲最大的少数民族,也是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外的欧洲公民群体。世界各地对罗姆人的称呼不尽相同,他们还被称为吉普赛人、茨冈人、波希米亚人、辛提人和阿什卡人。有研究表明,罗姆人属于印欧语系的白人种族,原生活于印度拉贾斯坦邦,中世纪后逐渐向欧洲迁徙。欧洲约有一千多万罗姆人,大部分生活在中东欧和东南欧,巴尔干也被称为罗姆人的“第二故乡”。一直以来,罗姆人的社会融合是多数中东欧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此次新冠疫情的蔓延和升级,罗姆人被边缘化的处境、潜在的生存危机和融合难题日渐显露。
从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大流行以来,罗姆人饥饿、流浪以及缺乏正常社会生活的情形频见于报端。众多依靠沿街叫卖、艺演、废品回收等为生的罗姆人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更为重要的是,有关罗姆人遭受种族歧视的事件在中东欧多国发生。罗姆人从西欧国家返回中东欧尤其是东南欧国家后须接受有区别的严格检测。同时,斯洛伐克、希腊、保加利亚以及罗马尼亚等国对境内罗姆人社区进行军事化强制封锁和隔离,个别国家还出现了暴力执法现象。这些管控措施不仅反映了中东欧国家罗姆人的生存危机,也将罗姆人融合难题再度放大。
中东欧罗姆人遭到社会排斥和孤立的根本原因在于该地区盛行的“反罗姆人主义”。在该地区,罗姆人经济能力、社会地位以及融入水平较差。在欧盟国家中,约有30%的罗姆人居住在没有自来水的房屋里。在西巴尔干地区,这一比例还要更高。在中东欧多国,很多罗姆人未接受教育、就业或者培训。同时,由于居住地没有供电、互联网,或者无力购买电脑等电子设备,在疫情影响下多数罗姆人学生无法参加在线教学。再以医疗为例,中东欧医疗体系充斥着“反罗姆人主义”,使得罗姆人无法得到治疗,其也没有能力购买药物。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拥有养老保险的罗姆人分别约占总数的45%和54%。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地区16岁以上罗姆人获得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只有27%和10%。在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罗姆人遭受的医疗歧视也颇为严重。
在原住国得不到正常保障的巴尔干罗姆人将移居西欧作为“出路”之一。据统计,在2007年至2017年十年间,欧盟国家收到超过20万来自阿尔巴尼亚、波黑、黑山、北马其顿、塞尔维亚以及科索沃地区的罗姆人避难申请。但是,随着西欧国家移民政策日益收紧,“劳工移民”越来越正规化,能够成功实现移民西欧的罗姆人并不多。一些国家或实施驱逐令,或以所谓的“奖励手段”将罗姆人赶离。新冠疫情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
尽管实现罗姆人社会融合是中东欧各国当局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各国基本都出台了相关政策,但真正落到实处特别是消除“反罗姆人主义”却十分困难。一个显著的例子是,2009年欧洲人权法院作出的关于波黑塞迪奇—芬奇法案(波黑罗姆人和犹太人两大少数族群争取同波什尼亚克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三大主体制宪民族的同等权利)判定迄未得到执行。由此,有评论指出,政客们将罗姆人排除在政策规划和决策之外,即使是讨论罗姆人问题也并不是同罗姆人直接对话,而是同罗姆人问题专家磋商。多年来,欧盟在西巴尔干国家入盟年度进展报告中一直重复着“罗姆人受歧视”的陈词滥调,但欧盟方面做出的表率和努力也羞于被提及。
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这样写道: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2020年德国辛提人和罗姆人中央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欧、东南欧的极右翼和民族主义的政客们正在利用当前疫情危机将种族主义的立场合法化为政府行动并予以贯彻”。也有不少评论指出,罗姆人不仅在正常时期为一体化进程所忽视,而且在非常时期被一体化决策者和政治精英所排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东欧乃至整个欧洲罗姆人的社会融合问题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