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诺:写一根手指头力量的书
2021-04-28张宇欣
张宇欣

图/本刊记者 梁辰
“我没有办法去劝人家读书,尤其是现在的台湾。”唐诺说。
這个45岁才开始出书的人当了大半辈子文学编辑。“(读者)就是不断减损的,”电话里,他说起一个调查,中国台湾超过一半人,七年没买过一本书。
两年多前接受《十三邀》采访后, 唐诺日日去读写的咖啡馆算是火了。他的节奏也没变。咖啡馆开门,他进去坐下,待到下午两点左右。一些报道里,他被形容为隐士一样的人。他说自己是很无趣的,“大概不太会变。”只是最近写作脚步放得比较慢,不见得每天都书写。他也不把自己视为作家。
1977年,19岁的唐诺和朱天心、朱天文、丁亚民等友人创办文学杂志《三三集刊》。他的同辈亲友很快在文坛影坛脱颖而出,而他多年来做的就是读书、编辑。在不同的书和不同的采访里,他说自己是一个姿态“往后退”的人。站在像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所谓的“没利益、无兴趣、不相干”这样的位置,他埋首写文学,写社会、经济、政治。至于作品的效用,写下来,东西就交付出去了, “自己能够得到一些理解和反省,大概就是这样而已,没什么特别的。它的遭遇就跟你没什么太大关系了。”
图书从酝酿到写作、出版,再到海峡这头,与唐诺现在的所思构成时间的错位。“抱歉,请问出处是什么?”——采访原本的话题之一是《声誉》(2021)这本书,我引述不止一个他书中的句子时,他很不好意思地反问。“我不太看自己写的(东西),也不确定当时前言后语心里所指是什么,如果这样光秃秃地来看的话”——他解释完一通,再来回答。
这本书2018年在台湾出版时名为《我有关声誉、权势和财富的简单思索》,他笑着说,很多他以为有价值的东西大家慢慢不再那么关怀,“怎么讲,有些东西,可能的话,如果代价不是很大,如果不是很难的话,你还是希望它能够被留住,比方说一棵老树、一个古迹,类似这样的,包括多年来你比较相信的一些价值,人的善念、正义感、对抗阴影的勇气,你还是希望尽量在人的世界里能看到这些东西,大概是从这样的一种关怀出发的。”对这个老编辑来说,将这些抽象价值具体来谈,最趁手的容器还是书籍。“某些作品对我来讲非常珍贵。”
卡尔维诺、博尔赫斯、格雷厄姆·格林、契诃夫、加西亚·马尔克斯、昆德拉、三岛由纪夫,这些作家反复在唐诺的文章中出现。他曾认真地说,重读才是真正的阅读。“唯有在不同生命阶段的一次次重读中,作品的伟大才会一点一点显现,一次一次给予我们启示与勇气,面对生活的琐细与生命的虚无。”
多年前在香港书展的一个讲座上,唐诺把读者大略分成三类:正确的读者、假装的读者、错误的读者。去掉后两者,他觉得两岸加起来,他的读者应该是500个左右。对那些“当下一个冲动或误信书名买错的”,还有像他年轻时那样“不见得读但会假装在读或读过”的消费者,他屡次表示歉意。听说他当嘉宾那期《十三邀》播放量是节目开播以来的一个低谷,但也有两千多万,“把我吓坏了,因为那就是台湾总人口数。”
传播能量更大的媒介负担了更大成本,必然对讲述者有更多要求,“你要说给100万人听,跟你只说给两三个人听,你的话语会不同。”所以这些年他只选择以文字为载体——他的同辈亲友能够给他很多进入影视媒体业的机会,他都没考虑过。这是一个“很理性的选择”,“你不用去扮演、说出一些你并不一定想说出来的话,也大概通常比较接近自己想写的、放在心里头的、常年比较关心的一些事。”
他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文字的故事》(2010)是他读《说文解字》的产物,漫游似的讲造字、象形字、转注假借、甲骨文。他在《阅读的故事》(2010)里讲阅读的困惑、方法,“阅读是很生物性很本能性的,就跟你体内缺什么营养会不自觉想摄取什么样的食物一般,就跟养猫养狗的人晓得它们会自己跑野地找某种草吃一般,”他说。接着,《世间的名字》(2012)又从文学荡开去,讲人间世相,烟枪、骗子、拉面师傅、网球手都单独成章。《重读》中(2015)他尽写作家绝非最佳的作品,比如格雷厄姆·格林的《一个烧毁的麻风病例》、福克纳的《八月之光》。
唐诺的每篇文章都很长,主题难以概括,好像有几股线头以不同速度出发、互相缠绕,直到“事物在此一实然世界的确实停止之处”(这是唐诺对“尽头”的定义),长句绵密而少气口。“很多人认为我很啰嗦,东拉西扯,但是我想精确描述整个思维,包括复杂的想法。重点不是那句话说什么,而是我们怎么到那里,重点不是那个点,而是抵达那个点的思索线路。”他在《十三邀》里自我形容。在不同的书中,他耐心地对他的观点来处一一加以指明(哪怕已经反复引用),到了让读者可能不耐烦的地步。
在《声誉》之后,唐诺又写完了一本《年纪,阅读,书写》。你能从书名看出他的所写所思(他说书名也可能叫《刻舟求剑》)。他补充,讲的总归就是加入年纪的因素后,他的阅读书写可能会“产生怎么样的一点点微调,一些稍稍不同过往的理解、认识和关怀。”今年,他又在写一本新书,不那么规律,断断续续的,“有点无聊,要不要说?”他又笑了。
上了许知远的节目后,出版品牌“理想国”找他做音频,比方做50集一小时(每集文字大约4000字)的音频、一个题目可以讲两集之类。他回绝掉,但记下了这个体例,现在试着用这个思路,规定24个单位、每篇8000字,写他喜欢的书。
《声誉》还是由他熟稔的作家和思想家串联,讲声誉在权力与财富的夹击下受到的影响。“声誉很脆弱,也经常会被污染,我们毕竟是靠着这个东西,才能够联系到过去一些值得珍惜的人或事物。”
在这本书中,唐诺讲台湾“大选”、讲社会问题,讲财富的力量如何凌驾于政治、强大的资本主义如何压迫年轻世代。采访中,他会从大的话题絮絮聊到身边事。他是家中厨师,每天两点多离开咖啡馆后,都会从旁边的全联超市买菜回家——这家成功的企业以几乎不装潢的店面和廉价打垮台湾若干生鲜超市,挤压了小菜贩的生存空间,改变了一点点唐诺的生活秩序。
“我对未来经济比较沉重的一个忧虑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变得太大了,宽松货币的政策会不断延伸。我们对白领的理解现在是要重新调整的,马克思讲过很多,不断的分工会造成记忆的丧失……没有不可替代的人了。人的价值会消失。分工让这些都变成一个动作。这个变化会使得就业者在与资方的拉锯战里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接下来就是AI了,那样非常麻煩……贫富不均会越来越严重,会产生非常多的变化。”
主动削减读者群体后,他又消解了他书籍可能会有的影响力。他说,自己写的绝不是“劝人读书的书”:“你去写一本书,劝告那些从不读书的人,希望他们能够读书。这不就是一个悖论吗? ”哪怕是在他框定的很小的读者圈子,他认为有读书意愿的人也未必会实践。“我们生活里毕竟有时候会被打断,会想说等忙完什么再来。我在想,在像这样的一个时候,如果有人在他背后轻轻推一下,可能他就坐下来看看这本书。所以我也想写一本这样一根手指头力量的书,是吧?就是在他背后推一下的、一根手指头的力量的书。”

“人的不同流向,让它(文学)产生价值序列的变化”
人:人物周刊 唐:唐诺
人:你说过契诃夫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自怜自伤的医治者?
唐:我现在已经六十好几了,契诃夫只活了四十几岁,对我来讲他的全部作品都是年轻人(的作品)。年轻时看契诃夫:了不起的短篇小说大师;现在我的想法是,(这个)年轻人实在太了不起了。
这样的农奴出身的人,十六七岁到莫斯科,在那么冰冷的地方,一边读医学院还要一边赚钱寄钱回家还债,一直到40岁以后才慢慢脱离贫穷,然后就得肺病死掉了。而这样一个生命遭遇的人始终心态这么光亮,从来不会抱怨,从来不会觉得生命对他不公,从来不会自怜自伤,他的作品充满了那种好的笑声。所以有些时候你会想,你这样的一点点委屈、一点点被人家误解、一点点不幸运算得了什么呢?在契诃夫面前如果你太自怜的话你会觉得自己很不好意思哎,不是吗?
我刚刚说下一本书一个大的主题是年纪,是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我看的都是年轻人的作品。张爱玲不讲后来的《雷峰塔》这三本,以前大家熟知的华丽的张爱玲都是她30岁之前的作品。鲁迅沈从文的这些名著,(是他们)年轻时候写出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不到40岁。托尔斯泰的我觉得可能是小说史上完成度最高的《安娜·卡列尼娜》是四十几岁写的。三岛由纪夫也是四十几岁就死了。
台湾曾经有一个小小的谣言,说唐诺不看年轻人的作品,我说胡说八道,我现在全部在看年轻人的作品。
人:这个“谣言”是不是也指向你说过的一个观点,你对台湾年轻一代人的书写比较悲观,说台湾的几支笔(骆以军、朱天心等)后没有继承者。
唐:到现在还是一样看法。(笑)

三三文学社团,左一唐诺、左二朱天心、右一朱天文、右二马叔礼
人:降低了标准还是看不到?
唐:也很难降低标准了,当然你可以带着同情,(说)这可能是初学者嘛,但那是一个总体性的现象,并不见得是我对中国台湾的严厉指责。事实上堕落得更快的是日本。现代小说是在欧洲发生的,我们都是所谓的小说输入国,(其中)日本的成就是非常惊人的。(但)差不多到三岛由纪夫那个年代,日本严肃文学几乎是断绝了。日本现在正统的小说书写非常不好,某种程度来讲还不如中国台湾。你也问到所谓后书写时代,这是米兰·昆德拉说的,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大陆的发展跟其他地方的发展还有一点不一样,这个再说。所以我心里会跑出一个题目来,大概在我目前书写的最后的一篇里会讨论这个问题:那些人都哪里去了?会无聊地问这个问题。
人:为什么说是无聊的问题?
唐:因为有点空想意味,就好像你在想象、思索一个并没有发生过、不可能发生的事。你如果看奥林匹克项目,就会知道美国的跳高这些项目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 一种简单的可能的解答,就是那些可以练跳高的人都跑去NBA打篮球了,把他们的天赋用到了另外的舞台上。这是一个时代。当它产生某种位移的时候,人的不同流向,让它产生了价值序列的变化。
在某个时代里,文学书写被奉为较有价值、或者是比较珍贵的一个行当,厉害的人会往这边来。当这个地方的光彩暗淡了,收入也比人家低,声名也比不上别人,你当网红、歌手、影星,都远远超过这些,这些人就去打别的球了。我就只好无聊地问,那些原来可以成为好的书写者的人,他们在哪里呢?
“动不动几百万字,可能只在中国的网络小说里完成了这件事”
人:你大概7年前在和大陆的年轻作家对谈时,判断他们处于一个可能困难尴尬的转换时刻。现在你再判断,大陆文坛是不是也快到了像中国台湾或者日本这样的境地?
唐:还没有,还好吧。我比较过台湾和大陆的畅销书单,比方说“当当500大”(当当图书畅销榜TOP500),大陆目前书单还蛮漂亮的。只有一个,大陆好像是新书替代率太低,一是新的作者大家还是看不上眼;另外就是大陆对过去的所谓比较定论的经典作品——不管是世界名著还是中国老一代作家(的作品),比较遵从,稳定度就高。台湾新书替代率高得不得了。大家不看死去的人的东西,慢慢不看老年人的东西。
那大陆的书写暂时来讲,因为读者支撑,使得一些严肃的作品待遇远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要好。日本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日本的中生代作家都穷得不得了,到了你不可思议的地步。现在只是说,大陆影视的力量起来了,它的吸纳性会不会(导致)作品往冲突(性强的方向)去跑? 但一定不只是如此;写小说的人,我要不要写一个比较容易被连续剧改编的书,而不是去处理一个现代小说? 写法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那时候在大陆开讲座,有一个读者在现场举手说,大家不写厚重的东西,现在的东西轻薄短小。我说不见得是这样,大陆现在的网络的小说,动不动就上千万字。因为都是套路、公式,大陆这几年的什么战狼电影、杀马特电影,包括女总裁这样的题目,大概都是如此。
人:你也关注大陆网络小说的发展套路?
唐:大陆的网络小说我看了四五百本,几乎都是吧。过去很多人希望网络小说能得到更宽阔的创作路线,可是到后来它可能不是我们期待的。你可能必须立刻抓住大家的眼睛,必须把声音放得很大,必须动作写得非常夸张强烈,然后你会看到作者不断出来拜托求撒花求什么这些东西;你不敢中断,什么对不起老婆昨天发高烧,我电脑昨天宕机了。一天六七千字甚至上万字地写,年轻的初学者没有人经得起那样的,所以最后逼着他不断使用已被接受的基本情节套路——原来的笔都会写坏掉的。有时候是很可惜的。
你会看到有一些(作品)其实一开始写的是有意思的,尽管是一个通俗作品,它是可以成立的,可是大概进行到一定长度就会瓦解,因为作者撑不下去,好不容易抓到一个题材,他就要不断重复。全世界有什么小说动辄三四百万字?我们回顾文学史,不管是通俗的或者正统的小说,动不动几百万字,可能只在中国的网络小说里完成了这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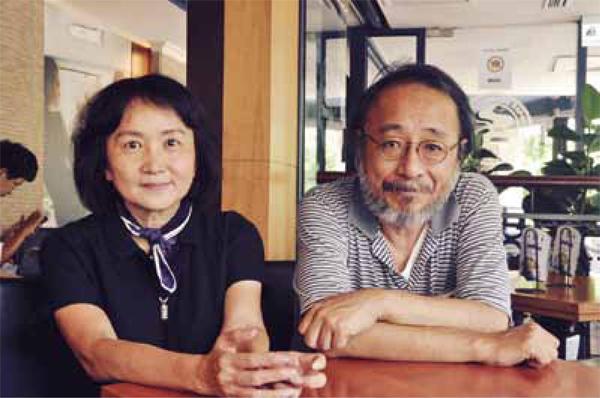
唐诺与朱天心。图/受访者提供
人:我想到《尽头》里说,你不担心小说会写完所有可能,但觉得在那之前,“小说大概已成为一个说着自己难解语言,没人听懂也没人愿意再试着听懂的古怪东西,在它用尽自己之前,就已先被遗忘、先被驱赶出这个犹有阳光照临的世界”。
唐:那就是另外一面的东西,现在消费者的意识越来越强,人们失去了耐心,对较为深刻的、稍远一点的东西不尊敬不耐烦,所以即使有好的小說,也没有人去看。我所说的就是(小说)后来就密码化了,现在很多时候我所知道的读者反映他读不懂一本书,好像是书写者的错误,为什么我都看不懂?
我们的年代不是如此,那时候的阅读某种程度本来就是想知道一些你原来不懂的东西,当你还是不懂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丢人、惭愧,会觉得我程度怎么这么差,怎么会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在消费者意识里,就跟你去一个店里食物我不满意(一样)。
深刻的作品的确不好读,你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怎么会是好读的作品?文学史会骗你吗?这是一部烂小说吗?当然不是,可是今天,都没有花费一天时间思考的人就可以在这上头大方解释。可能只有在文学的圈子,好像在专业上跟世界有较大冲突。你一天物理学都没学过的人,去批评量子力学是乱讲,这话说得出口吗?但是你今天对乔伊斯、普鲁斯特说这样的话,好像不会很惭愧。
“韩国的少女时代,是比三岛由纪夫的小说看起来舒服得多”
人:文学变成消费品,书写者地位下降、边缘化,这个事会让你难受吗?
唐:怎么讲,你年轻时要进入世界,你就知道要改行了。在台湾功课很好的甜美的女生,过去问她的梦想,就是说想当歌星,不行的话才考虑去哈佛念书,就变成这样。我没有在所谓批判,只是很平和地去理解这个世界。台湾20年前,滚石那些唱片公司最强的时候,我们随便讲,江蕙的一场演唱会,说要几支弦子,就是小提琴的意思,我这次要用24支,光小提琴手就动用(这么多)。有些时候我心里头怪怪的很难释怀。说江蕙也就罢了,尤其是有一些歌都唱不好的,所谓的女团。
人:你也关注女团,现在的选秀?
唐:对。(笑)从韩国开始,腿很长的,裙子短一点的,可能三个月就可以训练出这样子来,可是他们所使用的在后头比方说拉小提琴的这些人,可能需要15年20年的练习。久而久之,那个世界慢慢就没有人进去了。通常不是老一代快速消失,而是新生一代不进来了,因为他们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我才会问,那些人如今都在哪里?
鲁迅讲原来是没有路的,人走着走着才有了路。但从另一个方面讲,本来是有路的,慢慢人不走了,路又消失了。那个东西(音乐、文学)某种程度来讲跟培养一个偶像、名模不一样,要相当的时间来锤炼。所以我就说为什么声誉产生变化时,这些东西会跟着改变。我会觉得惋惜,某些我们曾经达到的,又退回来了,大概我们就留它不住了。现在以及未来的世界,已经不适合它生长,大概是这样。
人:现在在大陆,以前在日韩就非常流行的女团男团选秀,可能很多网友、粉丝也会觉得他们或多或少在一个体系里付出了很多努力。不管是模特还是偶像,你不会觉得他们是这一时代新的有价值的产物吗?
唐:应该比较困难。当然事实上已经证明了大家比较爱看女团,韩国的少女时代那种,是比三岛由纪夫的小说看起来舒服多了,你在自我的生活里完全可以做这样的自由选择,可是不能够讲它们是一样的。因为完成这件事必须投入的东西、产生的方式、所留存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人观看之后所产生的内在影响的程度和方式,都不一样。我没有蛮横到说要告诉人家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但你不要认为它们是100%可以相互替代的。当横向的位移产生时,我们去感受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思考)我们因此得到什么,因此可能还会再丢掉什么,我们可能往哪里去,可能哪个地方关闭了?这样你才得到对世界的一个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