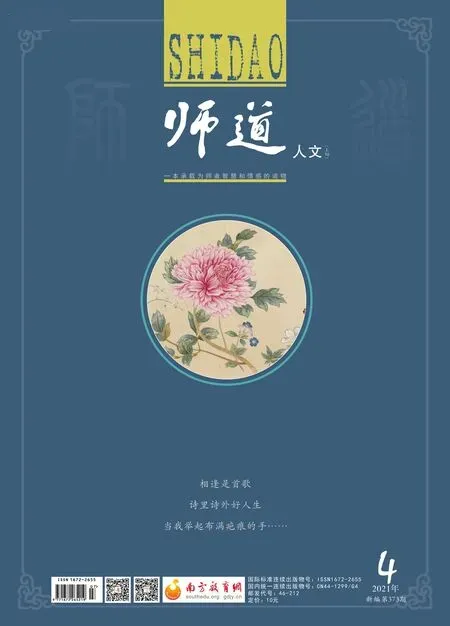悲凉为什么美?
——读《故都的秋》
2021-04-25辜玢玢
辜玢玢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将秋天的特点概括为“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他主观地过滤掉热闹的、喧腾的秋景,留下的是那些“带着浓厚的颓废色彩”的秋。教师们通常会以此为线索,将文章分解为几幅秋景图,进而引导学生通过解析秋景的要素来感知其美。事实上,学生很容易从视觉直观上感知到这些秋景图是美的,但再追问一句——为什么是美的,以及什么样的大自然能够称之为美,似乎就难以言达其意了。关于“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么解释的,“美,甘也”,由此“美”无论是指形貌好看、美好还是范式理想,都殊途同归地指向了褒义的、向上的词义。显然,从词义上理解,郁达夫笔下的秋与词典中的“美”的定义似乎是不匹配的。那么在郁达夫笔下,或者说在文学史中, “美”究竟该如何定义?
一、重新建构美的空间
我们先重返美的发生现场。不难发现,郁达夫笔下的秋有既定的空间范畴,特指不同于南国的北平城,因而文本中会反复出现“北国之秋” “北国的” “北方的”之类的空间所指,但有意思的是,文章标题却是 “故都的秋”。那么,“故都”与“北国”除了地理空间意义上的重叠以外,二者何以联系?不妨看看两个例子。
例如, “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一处。按照常理,郁达夫到北平借宿在朋友家或者暂住旅舍并不是件难事,但郁达夫为什么偏选择去“租”,且租的是“一椽破屋”? “租”意味着暂时隔绝旧日的伦理关系,以纯粹个体的方式存在;而“破屋”强调屋之破,其中自然不乏传统文人趣味,但似乎也有隔绝旧日生活空间的意味。他似乎决意在偌大的北平城重新开辟一块能够暂时与世俗逻辑相区隔的空间。也就是说,此次对秋天的审美与其说是一次自然而然的生活事件,不如说是一次有意为之的审美实践。

再例如, “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一处。 《红楼梦》妙玉请茶时,刘姥姥说“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惹得妙玉白眼。在此刘姥姥不过是充当乡下的俗人角色罢了,但也透露出浓茶显然不在品茶范畴之中。那么,郁达夫既然已选择了清晨泡茶这样略带闲适之事,为什么又挑选了“一碗”这样粗陋的茶具,以及“浓茶”这样粗俗的茶类?这其中存在着一层错位,即大雅与大俗的错位。但凡郁达夫此刻稍具知识理性,就会意识到这其中的不兼容,有意思的是,郁达夫偏偏让大雅与大俗以参差的状态存在着,似乎是有意撇开知识性的审美理性,而彰显出纯粹的感性向度。
由此,郁达夫构建出一个新的审美空间,一个既超拔于俗世,又联系着俗世,既指向精神性,又不乏日常性,既强调感性,又隐匿着理性的审美空间。 “北国”指向了具象的世俗世界本身, “故都”则具有超越性,指向文学性的审美空间。通过从“北国”到“故都”的转换,郁达夫完成了美的发生现场的建构。
二、 “赏玩”:重构审美立场
确认了空间的建构,我们来看郁达夫对空间的布局。可以发现,与其说郁达夫是在描写秋景,不如说是在构思一幅文人写意简笔画,并有意识地在层层叠叠地晕染衰颓气息。可以注意到,他对于秋景的要求是十分严苛的。他细致地限定种种秋物的形态,赏牵牛花, “以为以蓝色或白色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者最下”;赏秋草,则“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赏秋果,则需是“显出淡绿微黄的时候”。这些无不在强化秋的悲凉意味。事实上,在“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文学传统中,描摹萧瑟衰败的秋景并不少见,甚至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思维定势,但不同之处在于,在此类文学传统中,悲凉的秋往往是作者悲愁情感的投射物,该季节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苦痛命运的象征性符号。在郁达夫笔下,目之所及的仍是带着悲凉色彩的景与物,但充满周遭空气中的不再是浓重的愁苦或者悲哀,而是若有若无的等闲视之,犹如摄影机一样,空镜头一一掠过,仿佛这种悲凉早就成为了朴素生活的常态。
为什么悲凉的秋从特殊的象征性符号转变成了生活的常态?究其根本在于郁达夫对秋所秉持的立场发生了转变,由“先入为主式”转变为“饱尝一尝” “赏玩”。所谓“赏玩”即欣赏,而后玩味,甚至是抚玩。具体地说,欣赏一方面意味着作者剥离了秋在传统文学中固有的象征色彩,它仅仅是作为独立的风景而存在;另一方面,当秋成为独立风景时,个体主观情感的投射被中止了。玩味或者抚玩则意味着其背后的主体情感显然没有托物言志来得那么庄重严肃,它显得更为暧昧,甚至带有几分风流气息。
郁达夫由此解构了秋历来所承载的文化符号,完成了对文学传统中过分强调主观感受的审美立场的颠覆,重新确立了无功利的审美立场。此时聚焦于秋并不是出于投射情感的功利需求,而仅仅是出于无目的性的审美需求。故而郁达夫以一种节制且散淡的笔调来勾勒秋物的轮廓,然后以静物静置的方式呈现其存在,不加评论。
三、物哀:对生命极度热切的注视
正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享受美好是再自然不过的审美常态,那么,享受悲凉会不会成为病态的审美?在郁达夫这显然是不会的。举个例子,郁达夫写秋天的槐花,关注的是“落蕊”,即凋谢之后自然飘落的花蕊。在生物学意义上,落蕊是无生命的,已然终结了生命的状态,但这种衰亡的落蕊为什么在郁达夫看来恰恰成为了“秋来的点缀”?他写道, “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极细柔软的触觉。”按道理,如此纤细柔弱的槐花,尚且不具备声音和气味的特质,更遑论隔着鞋子后脚踏上去的触觉。试想,如果不是感官极度敏锐,何人能够感受到这“一点点极微极细柔软的触觉”?而敏锐精细的感觉则来源于对生命极度热切的注视。因为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因为对万物倾注了深邃的情,故而能够在绚烂中见其凋零,在凋零中感其绚烂,在瞬间的绚烂中悟其永恒。
同样的,郁达夫还写到了“秋蝉衰弱的残声”、秋果“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趋向衰败的二者共同指向了生命必然遭受的荣枯盛衰的轮回。而郁达夫之所以尤为关注衰亡中的秋物,不过是试图在死亡中窥视生,从有序的生命周期中了知无常。通过对有“序”自然的亲近,俗世的无常与幻灭所带来的焦灼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可以说,郁达夫对于生的积极认知实质上是借由生的反面,即死亡来实践的。
这种看似“向下”的审美,其精神内核实际上充满了对“向上”的执着,所谓堕落即上升。借用《源氏物语》的话,即“为情而感,是为物哀”。虽然是“哀”,但其底色是“多情”,是“美”,并借由“多情”与“美”唤醒了纤细的、潜意识层的个体生命体验。因此,美学意义上的美,它与物质形态无关,但与主体的情致相关。而郁达夫对于日常生活的细腻感受,以及对万物的深邃情致重新赋予落蕊以新的生命活力,物质形态上的消亡反而获得了审美范畴上的美。如此,能够对一草一木“情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的审美,何来病态?
四、耽溺:生命维度的拓宽
在这个时候,个体的生命维度无形中被拓宽了,这意味着人不仅可以理性冷静地思考判断,也可以抛开理性,选择耽溺于感性。
我们不妨回到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现场来探讨此问题。在儒家文化圈,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可谓是对文学存在的典型定义,不论是“载道”,还是“言志”,实际上均强调文学的实用性和目的性。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陈独秀、胡适等先驱者们都致力于改革旧的文学机制,创设新的文学机制,但悖谬的是,这场文学运动实质上是被政治所催生的,而非被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驱动,故而新文化运动虽然革新了文学的表达方式,但反过来又强化了传统的文学观内核。正如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所概括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政治变革的诉求使得“启蒙与救亡”成为时代文学的主题,也使得新文学的创作整体带有不同程度的理性色彩。
在这样一个科学与理性、责任感与使命感、启蒙与救亡成为至高真理的时代背景之下,郁达夫却反其道而行之,反而故意回避了理性,选择耽溺于审美。这意味着大时代中被迫驱逐流放的感性灵魂终于借由悲凉美的体验得以暂得回归,人得以从实用的、功利的理性桎梏中暂获解放,去五官开放地感受美,即便那美是无用的。当人的灵魂被美浸润,变得丰盈之时,即便悲凉,也充盈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