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妆奁一支簪
2021-04-21沈梅丽
沈梅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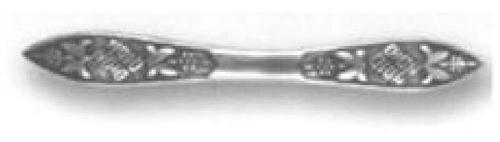

1931年,衡山聂氏出《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年谱主人崇德老人为曾国藩之女曾纪芬。曾纪芬生于咸丰二年(1852),这部年谱是她的八十岁自述,也是一部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名门女性视角下社会生活礼俗变迁的口述实录。文中记载了曾国藩规定子女婚嫁资费限二百金之事,被当时人据以赞誉文正公“持躬之俭、治家之严”。1932年,《兴华》及《纺织周刊》等先后刊载的曾纪芬《廉俭救国说》,更为详细记录了二百金奁资使用情况:“先公所定章程,子女婚嫁,皆以用二百金为限,衣止两箱,金器两件,一扁簪,一挖耳,一切皆在此二百金中。”曾家婚嫁购置扁簪与挖耳两件金器的做法,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史信息,有传统社会里名门富家等家族规约里对妇女装饰的约束,有传统婚俗中首饰购置习惯,也有明、清妇女发式与首饰工艺美学变迁的内在关系等。
古训以俭为美德,司马光在《训子孙文》开篇说:“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而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曾国藩在《谕纪鸿》中,以他二十年为官“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泽吾不敢也”的自处之道,告诫其子纪鸿在学习和生活上要“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成为一个“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俭约作为传统修身和治家的实践之道,往往是被贯彻于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中。清代乾、道年间,杭州府仁和县人沈起潜所著《沈氏家训》“治家门”中指出治家第一从俭,并从日常生活的饮食、交游、出行及服饰等多方面规约子弟言行,其中对家族妇女穿戴的规约为:“妇女不许胭脂涂嘴唇……除出金簪、金钏、珠花、耳环、翠钿、宝玉外,其余镂细摇曳、轻盈艳冶之物,不许插戴。”清蜀中黄氏家族所制《黄氏宗谱》“族议节俭家规”载:“服饰所以彰身,然不可过分……妇女首饰,富贵家只戴手圈、簪环、线草花、挖耳。中富家戴簪环、挖耳、花草;贫者耳环、花草。”
“服饰所以彰身,然不可过分”,作为黄氏家规所言的不“过分”的妇女首饰,簪与挖耳属于当时女性常佩之物,民国早期文人笔记中亦有记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小报《金刚钻报》连续刊载海上漱石生的《沪壖话旧录》,据其记载在海禁未开时,上海妇女所佩戴的日常首饰多以金银制成,如手镯、压发、挖耳以及茉莉簪、莲蓬簪、荷花瓣簪等。珍贵首饰则是以珍珠为最,一副价值连城的全副珠头面,包括珠结子、银花、珠花、珠棒,还有珠压发、珠梅花簪、珠荷花簪、珠茉莉簪、珠挖耳簪等约十几种。所谓日常与珍贵首饰的区别主要是在于材质贵贱,首饰品类形制上则大体相近。
簪、挖耳是传统婚俗聘礼中的常备之物。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民俗卷记载北宋开封府“相媳妇”风俗,男方亲戚若看中了女方,即以钗插冠中,谓之“插钗子”。明代张岱《陶庵梦忆》卷五“扬州瘦马”,记述扬州人若娶妾,由媒人牙婆介绍,如果看中了某位瘦马,“用金簪或钗一股插其鬓,曰‘插带”。男女相悦,以簪钗定情,是明、清戏文小说中常见桥段,明传奇《玉簪记》“秋江哭别”中,陈妙常买棹追舟,送簪潘必正:“奴有碧玉鸳簪一枝,原是奴家簪冠之物,送君为加冠之兆,伏乞笑纳,聊表别情。”传统相亲、私约要插送簪钗,正式结婚嫁妆首饰中簪钗、挖耳也是不可缺少的。《清稗类钞·礼制类·大婚礼节》载:“皇后梳双凤髻,戴双喜如意,御双凤同和袍。俟皇上、皇后坐龙凤喜床,食子孙饽饽讫,由福晋四人,率内务府女官请皇后梳妆上头。仍戴双喜如意,加添扁簪富贵绒花,戴朝珠,乃就合卺宴。”黄山歙县蓝田村叶国安家藏民国初期嫁资抄存底单共七十七种陪嫁,首饰十三种,其中压发和扁方两种、挖耳一种:“翠珠冠髻成品,镀金爪腿成顶,翠珠花竿成吉,镀金扁方成对,镀金手镯成对,银镶藤镯成对,镀金压发成吉,镀金挖耳三根,镀金耳钏三对,镀金蝙蝠镶玉钏成对,玄纹银针成吉,镀金戒指成套,镀金条龙戒指成吉。”
还有一种特殊民俗里使用的奁目,即冥婚嫁妆单,其首饰名目一般与当地俗世奁目大抵相同。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王鲁彦小说集《柚子》,集中短篇小说《菊英的出嫁》以浙东乡村冥婚为背景,讲述一位乡村妇女,女儿菊英八岁时夭折。在时间流逝中,这位母亲念女之情愈加浓烈,十多年后倾其所有为女儿冥婚准备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其奁目内列簪、钗、挖耳、耳环、手镯及戒指等六种共二十四件首饰:
尽她(注:指菊英的母亲)所有的力给菊英预备嫁妆,是她的责任,又是她十分的心愿。
哈,这样好的嫁妆,菊英还会不喜欢吗?人家还会不称赞吗?你看,那一种不完备?那一种不漂亮?那一种不值钱?
大略地说一下:金簪二枚,银簪珠簪各一枚。金银发钗各二枚。挖耳,金的二个,银的一个。金的银的和钻石的耳环各两付。金戒指四枚,又钻石的二枚。手镯三对,金的倒有两对。
簪与挖耳之所以成为古代女性常备首饰,缘于古代留发和洁耳习俗。两种首饰的历史皆可溯至商代,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玉笄有二十八件、玉耳勺两件;1980年出版的《殷墟妇好墓》將玉笄归为“头饰”,耳勺与玉梳等归为“生活用具”。笄,即簪,《文选》卷二十一张景阳《咏史诗》有“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句,唐李善注:“簪,笄也,所以持冠也。”作为头饰,簪的功能主要是约固发、连冠,《周礼·夏官·弁师》:“皆五彩玉十有二,玉笄朱紘。”宋朱申解:“玉笄朱纮:以玉为笄,横贯于纽。以朱为纮,缀于笄之两端,而结于颔下。”先秦时,簪是男子用以固发、连冠于发的饰具。同时,也是女性发饰,《后汉书》:“《列女传》曰周宣王尝夜卧,后乃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历代制簪材质有玉石、金银、象牙及荆竹木等。玉簪,《西京杂记》:“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宫人搔头皆用玉,玉价倍贵焉。”妇好墓出土的鱼形黄玉耳勺,或即后世所谓的挖耳、耳挖,是古代洁耳工具,考古文献多将它与梳等归在生活用具类。先秦挖耳形制已比较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为流行首饰。
簪的历代形制变化与发髻盘梳方式、首饰材质及其相应的制作工艺美学有关,总体来说是传承中新变。先秦时簪的功能主要是男子用以横插连发冠、女性以簪饰发,多以玉制,其形多呈长针形,由簪首、簪挺(身)组成。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战国云纹玉笄长十点三厘米,笄首边长零点九厘米。总来的来说,历代簪头重在体现装饰性,如龙凤、鸡、花卉、佛像、蝴蝶字纹、宗教、故事等各类表现吉祥意蕴的艺术造型。随着历史发展,簪头纹样愈加丰富,簪挺变化相对要小,仍以圆锥体针型、细长条形为主。到了清代,簪体扁片状的扁簪开始流行,这与清代妇女发式关系密切。曾纪芬在回忆咸、同时期至民国初八十年里妇女发型演变时,提到咸、同年间妇女多在脑后盘髻,用扁簪约固:“大抵咸同年间,妇人之髻多盘于脑后,而为长形,略似今北方乡妇之髻,中须衬以硬胎,其约发处饰以红丝,固以扁簪。”
许地山《近三百年来中国的女装》介绍:自光绪末至民国初年,时尚的头式有螺髻、元宝髻、连环髻、香瓜髻、一字髻等。这些髻式因盘梳方式不同而造型各异,但和如今妇女的梳髻形式已没有太大的区别,髻上饰物多为横插一簪,名“压发”。富家用金,贫家用银或镀银。髻边插戴物有耳挖、牙签等。江南妇女也喜欢在发髻上插一些时令鲜花。
许地山所记压发的“横插”法,可见于1892年成书的《海上青楼图记》,这本晚清上海青楼笔记,以图文方式绘制了数量丰富的沪上青楼女性流行发式、服饰图画,其中可见到压发簪横插图(图1)。

图1:(海·上青楼图记)压发簪(横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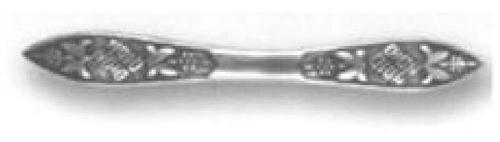
图2:喜字葡萄纹银质压发扁簪
压发簪流行于清末民初的上海,以上海洋场生活为背景的《海上花列传》、《海上繁花梦》、《九尾龟》等小说所记青楼女性首饰中,压发簪几乎是人人必备。南京市民俗博物馆藏喜字压发扁簪(图2),两头椭圆形、收腰,簪体呈“3”字形弯曲。簪子两端图案对称,两串葡萄果实中刻有双喜字,葡萄寓意多子多福。这类中间收腰的扁片形簪子(图3),明末出土文献中已出现,汉族桃形扁簪,长十四点五厘米,宽五点七厘米。簪为桃形,簪两头是装饰重点,花草人物随形而设,纹样为《白蛇传》故事情节,四周为蝴蝶花卉。压发簪形制一般是两端宽尖、中间收腰特点,区别主要在于两端细节。《北京考古史》记载北京地区出土了数十种清代压发扁簪,其簪体两端有“宽扁、簪首弯曲”、“扁平尖锐”、“呈三角形、两尖端下垂”、“为圆弧尖状,内弯”等几种情形。

图3:明代汉族桃形扁簪
除押发外,还有一种称为徽扁的扁簪。南京市民俗博物馆藏的花卉纹银质扁簪(图4),上下一样宽、略呈弧形,顶部做了弯曲处理,簪身为立体缠枝花卉纹。这类扁簪属汉族风格,最早在南京晚清墓葬中已出现,其尺寸一般远小于满族妇女使用的扁方。一般多称之为徽簪,主要流行于徽州地区。北方出土文物中也出现过,河北平泉县出土的阳刻花纹黄金扁簪,即徽簪形制,簪体残长十点三厘米,重二十克。簪头卷起,面上贴一云头纹。簪身为平面长条形、微鼓,包金,面上面刻“寿纹、梅花、荷藕纹”,背素面。过去,这种上下宽度均匀的高纯度金扁簪还可弯曲成手镯,这主要是纯度高的金比较软。如意簪是流行于江浙地区的扁簪,江西安吉昆铜三城出土金蝠头如意簪(图5),簪体为中间收腰、扁平如意状,底纹錾刻珍珠地,两组花卉纹。簪头为蝙蝠纹。除上述两种扁簪外,还有一种明代已流行的挖耳扁簪。现藏首都博物馆的一对明代花蝶纹白玉扁簪(图6),长十八点六厘米,头宽一点九厘米。簪挺上半部分为扁片形,镂雕宝瓶、花草和蝴蝶,顶部圆凹成耳勺形,下端簪柄尖细。這种簪、挖耳合体的挖耳簪、耳簪,即近代俗称的一丈青,其历史可溯至魏晋。

图4:花卉纹银质扁簪

图5:金蝙头如意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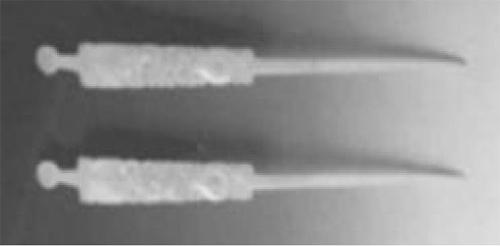
图6:明代花蝶白玉纹扁簪(一对)
压发、徽簪、如意簪及挖耳簪皆可归名于“扁簪”,都是晚清女性常用固发饰物。从晚清民初各画报及文人绘画来看,压发簪、挖耳簪更为流行时尚。行文至此,根据曾纪芬对咸、同年间妇女发式及固发扁簪的记述,以及曾、聂两家的地位,曾氏奁目所购扁簪或为压发。李渔《闲情偶记》谈及首饰时说:“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然而,近代的西风东渐,使得曾繁华于传统女性发髻上的各种簪钗饰物,也都失去了用处。海上漱石生在《沪壖话旧录》提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妇女皆时装截发,簪钗等遂成为无用之物”。稍早的民初奁目尚多为传统首饰,二十年代后的奁目已时见西式首饰。在沈从文以湘西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男子须知》(1929)中,有一份山大王石道义拟出的“聘礼饰物单”,即是一份中西融合的饰物礼单,礼单中的发饰都是传统发式所佩戴的,而颈饰、胸饰等则是西式饰物,名目大致为:金钏镯一对,赤金戒四枚,赤金丝大珍珠耳环一对,赤金簪压发各一件,各类项链共三件,手表一枚,婚戒与胸饰、扣针各一枚,法国香水两瓶等。到了1933年,张元济在女儿树敏出嫁时写的奁目单中,有寝室木器、被褥床毯、碗碟箸壶等各类食饮之具,甚至有意大利雕石像一座,以及Hillman汽车一辆,只是已经没有了簪与挖耳,也没有了其他传统发饰。奁目单最后,张元济说:
余族祖客园公家训有言:“冠婚巨典,礼从义起,勿矫勿靡。”余何亦敢靡?昔王荆公嫁女,家人制一青纱帐,荆公嫌其侈;曾文正公归于聂氏仅给二百金。余今遣嫁树敏,具奁物如右,虽曰无多,然以视王、曾二公,则愧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