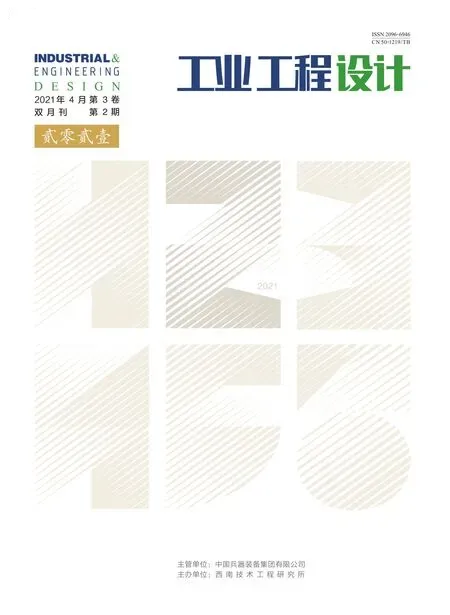民国旗袍的“人衣空间”
2021-04-19李迎军
李迎军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几乎都穿着“西式服装”——无论衬衫、西装、连衣裙,还是领带、皮鞋、牛仔裤,无一不是西方服装发展的产物。西方服装文化主导当今国际服装流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着装体验也以西式服装为主。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传统服装文化只存在于博物馆与历史书里,西方服装文化似乎成为当代服装的代名词。的确,历史上曾经一度强盛的中国服装文化体系在现代社会基本退出了日常生活领域,中国虽然有着辉煌的服饰文明,但服装领域流传至今的“传统”却屈指可数。春秋时“邯郸学步”的故事用来提醒世人不要在学习他人的同时迷失了自己,但如今的现状恰恰反映出人们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于传统服装文化认知的迷茫。
从装饰过剩的传统“重装”进化到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轻装”是服装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西方人用了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逐步实现了服装的现代化过渡,而中国则在传承过程中出现了断档,最终发展成几乎“全盘西化”的状态。但回望中国百年前的服装发展历史不难发现,面对相同的时代背景与社会需求,中国的部分传统服装也曾经同样实现过从历史到现代、从重装到轻装的转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服装就是民国旗袍①自清代旗人的袍服算起,旗袍发展至今主要经历了4个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清代满人的袍服,也称“旗装”。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旗袍,也称“民国旗袍”。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旗袍,也称“港台旗袍”。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旗袍。整个发展历程实现了旗袍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民国旗袍的现代化嬗变,无疑是思考传统服装当代传承问题最值得深入剖析的案例。
一、以穿的行为塑造空间
民国旗袍区别于西式服装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二维与三维形态的转换——经由人穿着后的服装是三维立体的,脱下来就恢复成二维平面的形态,这种因穿与不穿而呈现的三维与二维的空间转换是中国人玩了几千年的游戏,与西方的构筑式服装相比,东方服装这种要靠穿才能体现出形态与价值的不确定性恰恰成为了特点与优点。
西式服装具有极强的构筑性,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服装外廓形上,还表现在为了塑造外廓形而施加的“内功”上。例如欧洲服装西班牙风时期(1550—1620年)曾经流行大量使用填充物,男装的肩部要用填充物垫平,胸部、腹部、袖子乃至短裤里面都要塞进填充物来塑造最理想的服装造型,这种强行填充、刻意塑形的手法在西方服装发展中流传甚久,到了现代社会服装完成了从传统重装到现代轻装的简化之后,这样刻意塑形的观念依然存在,只是从厚重的填充物转化成了垫肩、胸衬等新的形式而已。西方的这些“刻意而为之”的服装造型就像一个充分满足塑形理想的壳,规范着着装者的身材。梁实秋曾经在文章中作过比较,他把中装形容为“变形虫”,因为中装可以随着穿着者的身体来进行相应变化,也更加舒适。而西装则像“戴枷系索”[1],把人体束缚在了服装里面。
从民国旗袍的着装形态看,服装的领与袖相连首先塑造的是肩部造型,民国旗袍传承的中国传统十字型结构使服装自然地由肩部垂下。一方面,旗袍的肩部将会因为穿着而产生相应的褶皱,这正是用于手臂运动的活动量,基于这一点来说,的确较西式绱肩袖的造型要舒适很多。另一方面,旗袍的衣料顺着人体的颈、肩、手臂的结构垂下,自然地顺应了着装者的肩宽,呈现出柔和的肩部轮廓,同时由于服装上没有明确的肩宽位置限定,所以对于着装者肩的宽度也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也同严格按照着装者肩宽尺寸制作并添加了垫肩塑形的西式服装有着本质的差别(见图1)。林语堂曾经由此感慨道:“但这一层,我们就可以看出将一切重量载于肩上令衣服自然下垂的中服是唯一的合理的人类的衣服[2]。”自然的肩部造型是中国传统服装的主要特征之一,也因为很好地适应了东方黄种人的身材曲线而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这种自然的肩形在东方宽衣文化圈得以发扬光大,形成了与西方刻意塑造的肩形截然不同的东方风格。

图1 柔和自然的旗袍肩部造型
顺应人体结构是中国传统服装的主要特征,这也是中国服装穿着舒适的主要原因。于是,“穿”成为解读中国服装传统的首要关键字。木心在《只认衣衫不认人》中,曾明确提出“要人穿衣,不让衣穿人”[3]的观点,一语道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宽衣文化中的人、衣关系:人是着装的主体,衣的价值在于“穿”的行为介入。
穿的行为揭示了东方服装观念里人与衣相互协调的本质关系,而人穿衣的最高境界是人衣一体。张竞生在《美的服装和裸体》中把这种境界称为:“衣服不是为衣服而是与身体拍合一气,然后才是美丽的[4]。”胡兰成在《山河岁月》中也写到中国服装的这一特点:“中国衣裳则随人的行坐而生波纹,人的美反而可以完全表现出来。”在中国的传统服装观念中,着装的美是同人与衣的“拍合一气”而呈现的,这种美是一种超越物质的自由,是人与衣服、与自然、与世界完全协调、“拍合一气”的自由。
与西方已经确定形态的构筑式服装相比,中国传统服装文化中追求的不是服装构筑式的立体形态,而是蕴含于二维平面中的三维立体,是随着服装从二维向三维转换而出现的空间变化,是穿的行为赋予服装空间的“二次设计”,也是自然的适应人体、顺应人体的着装观念。所有的服装都将随着被脱下的行为而回归二维的平静,同时又在孕育着新的转变——变成三维的“穿”。
二、“以实为虚”的物理空间
当年曾经对中装与西装都有过着装体验的诸多文学大家都曾针对衣与人的空间关系做过比较。1928年,徐志摩在赴美途中写给陆小曼的信中曾经提到穿着西装使人的行动受到很大的约束,他形容为脖子、腰、脚全都上了镣铐,完全没有中式服装穿着舒适。认为西装约束人体的还有林语堂,他控诉西装马甲“压迫呼吸”、西装衬衣“紧封皮肉”,这种束缚的感觉似乎已经强烈到让穿着者皮肤的毛孔都无法呼吸,而中国服装则完全没有这种束缚感,“不但能通毛孔呼吸,并且不论冬夏皆宽适如意,四通八达”[2]。两人提到的中装与西装分别是长衫、旗袍与西式衬衫、领带、西裤、西式驳领上衣。从民国时期的长衫形态来看,当时完成现代化演进的长衫已经从清代宽大的长袍脱胎换骨成具有时代精神的“进步男装”,服装的造型已完全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除了儒雅的气质延续了传统文人精神外,服装的松紧度也传承了中国传统的服装空间观念——为了适应社会生活而“适度地收紧”。尽管当年的社会状况给服装提出了由重装到轻装、由宽松到合体的变革要求,但在徐志摩与林语堂的眼中,合体的服装同样需要满足宽适如意的着装需求,因此需要适度地收紧,这恰恰是“中国衣服之好处”,如果服装追求的合体使人行动感到拘束,那就“事理欠通”了。虽然两位文人的表述并不能代表当时全体国人的看法,但作为对中装与西装都有过着装经历的体验者,两人的态度还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尤其是两人观点中流露出的“面对合体的概念时中国与欧美对待衣与人之间物理空间的尺度差异”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近百年后,日本设计师山本耀司在他的书中也表达了近似的观点:“西方的服装强调贴合身体。他们的着装理念认为,只有体现人体曲线的合体裁剪才是完美的设计,而我与此一直背道而驰……我的设计一定会让空气在身体和衣服之间微妙地流动[5]。”
山本耀司谈到的身体和衣服之间的“空气”正是东方人衣空间的反映,这也是东方服饰文化的典型特征。在《中国潮男》一书中,同样提及了中国传统服装中的气:“西方时装设计师通过裁剪的方法重塑身体,相信衣服紧贴身体就是美。中国服装理念则不同……中国人相信气,气的流动是万物的根源,因此身体与衣服之间应该存在着空间,让空气流动。”事实也的确如此,20 世纪初西方的审美观念进入中国,当中国人也开始追求紧身适体的服装造型时,民国旗袍的发展依然延续了传统的人衣空间观念。于是,进入中国的西方“绝对合体”观念经由数年的消化,转化成了中国的“相对适体”。两者的差别在于,尽管民国旗袍已经随人体结构呈现出非常婀娜的曲线,但并不等同于西方的塑形手段,而是仍然保留了人与衣服之间的气的流动——民国旗袍的合体并不是紧裹身体使行动受到约束,而是感觉上的合体,对于合体的意的追求显然强于形的强求。西方习惯于运用立体的手法塑造服装实体的外型,追求服装与着装者身体之间合体的空间,即使两者之间不绝对紧贴而是留有空间,这个空间也是相对均匀分配的。而民国旗袍的适体则体现出一种不平均的物理空间尺度,其目的是引发合体的联想,而非塑造一个真正合体的造型。通过对当年旗袍的尺寸分析发现,一些旗袍腰部最瘦处并不在腰节线上,而是上提到胸下(见图2),这个做法既可以保证日常生活中对活动量有更高要求的腰围部位有更多的松量,又可以提升视觉重心、营造优美的胸腰曲线。同时,民国旗袍相对更加宽松的臀围松量,也是在充分满足人体活动所需求的放松量的同时,与腰围形成了对比更加强烈的围度差,从而在视觉上加强了腰部的“收缩感”——这正是中国传统美学“虚实相生”观念的充分体现。宋人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中说:“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此其难也。”化景物为情思,这是对艺术中虚实结合的正确定义。以虚为虚,就是完全的虚无;以实为实,景物就是死的,不能动人;唯有以实为虚,化实为虚,才有无穷的意味,幽远的境界[6]。显而易见,西方服装的造型手法是“以实为实”的,而当年的手工艺人在完全了解西方造型手法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着中国传统的“以实为虚”的服装物理空间塑造方式。显然,当年旗袍的适体不仅仅体现在物理空间上的“合适”,更为重要的是隐含着精神层面的诉求。

图2 旗袍最细处收在腰线以上的造型
三、“不似之似”的美学空间
丰子恺先生以用中西融合画法创作漫画、撰写散文而著名,他同样不主张中国的服装过于“紧”。在《率真集》里丰子恺先生肯定了西方服装的合体之美,但他不赞同中国人盲从于西方,书中提到穿着西方合体服装的时髦女士就像是一条蛇,把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的效果被他形容为:犹如把袜子套在脚上,导致身体每个部位的原形都清晰直白地暴露出来[7]。丰子恺的观点将衣与人空间尺度的中西差异从物理空间上升到了精神空间。中、西方对服装的紧的理解与表达的不同,实际上是源于审美的差异。林语堂在《论西装》中也谈到了中装的美与西装的差异:“因为中国服装是比较一视同仁,自由平等,美者固然不能尽量表扬其身体美于大庭广众之前,而丑者也较便于藏拙,不至于太露形迹了[2]。”由此看来,中装不仅不会使人行动感到拘束,而且还可以“藏拙”,这是林先生所说的中装和西装在哲学上的不同之处,也正是中国传统服装观念的独到之处。

图3 旗袍上的长开衩造型
中、西艺术的显著区别正是对于“神”与“形”的不同追求。西方艺术一直强调艺术对自然的模仿关系,重视对透视法与解剖学的研究。达·芬奇(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曾把画家的心比喻为一面镜子,强调高明的画家就应该用艺术如实再现自然界的一切客观形态[8]。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同样延续着前辈的艺术传统:“以艺术大师们为榜样,继续运用客观自然不断向我们提供的无数形象,诚心诚意地去再现它……去画吧,写吧,尤其是临摹吧!像对待一般静物那样[9]。”西方艺术家对于美的认知建立在写实观念的基础之上,画家们看待人体美的标准同样体现在理性、严谨的科学方法上,认为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要符合标准的比例。中国的传统人体审美则是完全不同的路数,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写到:“一个女性体格的全部动律美乃取决于垂柳的柔美的线条,好像她的低垂的双肩,她的眸子比拟于杏实,眉毛比拟于新月……这种诗的词采在欧美未始没有,不过中国艺术的全部精神,尤其是中国妇女装饰的范型,却郑重其事地符合这类词采的内容[10]。”相对于西方艺术追求严谨的形,中国显然更加看重形背后蕴涵的东西。宗白华在《论素描》中曾经对比中、西绘画的差异,他强调西方绘画的特点在于“把握坚固的实体感觉”,而“中国画则以飘洒流畅的线纹,笔酣墨饱,自由组织,(仿佛音乐的制曲)暗示物象的骨骼、气势与动向”[6]。其中对于西画与中国画的形容竟然完全能够与西式服装同民国旗袍的比较相对应。元代的倪赞曾说自己画竹“不求形似”,而是“聊以写胸中之逸气耳”②倪赞在《清閟阁遗稿》中曾经谈到形与神的关系:“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余之竹,聊以写胸中之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否,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石涛也以“不似之似似之”流露出艺术超越“形”而表达“自我”的观点③石涛在《画语录·山川篇》的观点为:“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在《题画跋》中则简洁明了地指出:“不似之似似之。”。显然直白的“似”在中国传统观念里远远不及“不似之似”。《美学散步》中曾经提到18 世纪名画家邹一桂对西洋透视画法的逼真程度表示大为惊异,然而他的评价却是:“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6]。”清末的林纾在评价西画时也发表过相同的见解,他对西画的写实性大为赞赏,称其“状至逼肖”,但也认为西画“似则似耳,然观者如睹照片,毫无意味”。西方服装自收紧腰身开始,就一直延续了一条“科学地”包裹人体的发展思路,尤其在女装发展上,曾经盛行几个世纪的紧身胸衣以复杂的衣片塑造了西方人理想化的立体造型。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一直不希望直白、刻意地“塑造”人体与服装的形态,即使到了20 世纪初期,尽管当时的社会变革要求服装走向合体化道路,中国人所追求的服装也与西方理性、科学地贴合人体的思路不同,依然在寻找旗袍合体的“不似之似”,当时“看似”合体的旗袍在腰围部位留有的空间量一方面充分满足了坐、卧活动所需要的功能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不似之似”思想的直接反映,当年旗袍上高高的开衩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20 世纪30 年代开始流行的长旗袍上,侧缝处装饰有极长的开衩,当时最长的开衩造型几乎开到了腰线,高高的开衩极大地提升了服装整体的视觉重心,拉长了着装者腿的视觉长度,使身材娇小的中国妇女在穿着高开衩旗袍之后也能呈现出完美的身材比例。然而,通过对旗袍实物及当年照片中旗袍形态的分析发现,当时长旗袍的高开衩上,真正的“衩”大多数都没有开到腰线,而是到膝盖左右就缝合了(见图3)。这个开到膝盖的真正的衩是为了满足着装者走路时能够迈开腿的功能需求,而直通到腰线的“假衩”则是一个旨在引发观者无限想象的“美丽的谎言”,这也正是数千年来中国艺术所追求的不似之似的境界。
四、结语
木心在《只认衣裳不认人》中曾经提及人与旗袍的物理空间与审美空间:“旗袍并非在于曲线毕露,倒是简化了胴体的繁缛起伏,贴身而不贴肉,无遗而大有遗,如此才能坐下来淹然百媚,走动时微颸相随,站住了亭亭玉立,好处正在于纯净、婉约、刊落庸琐[3]。”这段精彩论述揭示出民国旗袍含蓄、独特的造型背后隐藏的中国传统“人衣空间观念”。相比而言,西方立体造型手法表现的“贴身贴肉”的服装在中国传统美学观念里是“不入画品”、“毫无意味”的。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服装设计师仍困扰于传统的当代性表达。作为完成了中国传统服装现代化演进的“活化石”,民国旗袍蕴含的“以实为虚”、“不似之似”的传统人衣空间观念无论从设计层面还是思想层面都搭建起一座回归传统的桥,指引当代中国服装设计师回归传统思考序列。徐志摩与梁实秋这两位积累了多年中装着装经验的文学家曾经对西方服装极度不适应,或许当年他们没有想到,几十年后的中国社会竟然是由他们所“痛恨”的“西装”一统天下,而他们认为“暗中与中国人性格相合”的中装则几乎消逝无存了。历史已远,未来已来,中国的服装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