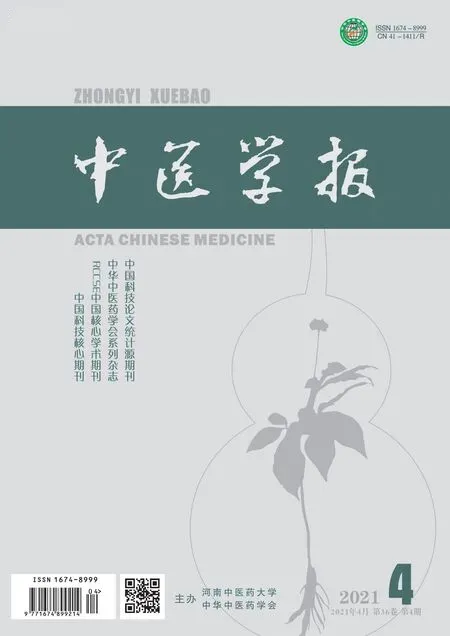清热、温阳、养阴为消渴病三大基本治法*
2021-04-17屈杰温娜杨景锋李小会陈丽名
屈杰,温娜,杨景锋,李小会,陈丽名
1.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712046;2.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 咸阳712046
消渴是以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为主要表现的气血津液病症,相当于现代医学的糖尿病[1]。现代医学对本病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目前治疗该病主要以口服降糖药物以及胰岛素治疗为主,短期降糖效果明显,但对慢性并发症效果较差。中医认为,消渴病位主要涉及肺、胃、肾,其病机主要是阴津亏损、燥热偏盛,治疗以清热润燥、养阴生津为大法,兼顾三消病证。消渴病日久,阴损及阳,阴阳俱虚,加之消渴病日久常并发白内障、雀目、耳聋、肺痨等病,治疗比较复杂[2]。目前,临床报道多局限于某一单纯治法或者方药,缺乏从宏观的角度理解消渴病治法产生的渊源以及发展。厘清其治法脉络,对于细化辨证论治,提高临床疗效很有指导价值[3]。消渴病治法的产生、发展、完善经历了漫长的学术争鸣和临床实践,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 清热法
消渴病的病因比较复杂,有饮食辛辣炙煿动火之物、有多服升阳金石之剂,致使内热偏盛,胃肠燥实,消耗津液,出现消谷善饥、大便坚、小便数。诚如《金匮要略》所言:“趺阳脉浮而数,浮即为气,数即为消谷而大坚。气盛则溲数,溲数即坚,坚数相搏,即为消渴。”热邪日久,营卫壅滞,发为疮疡,消渴病最易出现内障、雀目、疮疡、淋浊等病。治疗遵循《黄帝内经》“热者寒之”为立法依据,火热偏盛者,苦寒折热;热壅毒盛者,清热解毒。
1.1 清热泻火生津法清热泻火生津治疗消渴病,其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伤寒论》中使用石膏、知母、天花粉等清热泻火、养阴生津,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使用清热泻火法治疗消渴的方法。《伤寒论》第170条曰:“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以及其他条文如第168条、第169条多次描述了外感邪气化热入里,津气两伤之消渴症的表现是“大渴”“口燥渴”“渴欲饮水”。白虎汤是清热泻火、益气养阴复方。方中石膏辛甘大寒、知母苦寒质润,既能泻火,又能养阴;甘草、粳米可以防止寒凉伤中。此外,《伤寒论》中的竹叶石膏汤也是清热泻火、养阴生津的代表方,也被后世广泛应用于消渴病的治疗中[4]。现代药理研究证实,白虎加人参汤具有解热、抗炎、降血糖的作用[5]。金元时期医家刘河间阐发《黄帝内经》消渴病脏腑传变之余绪,认为“燥热偏盛,热气怫郁,玄腑闭塞,荣卫清气,不能升降”是消渴病病机关键,强调从“燥热立论”,善用苦寒泄热、宣通玄腑之药,如《三消论》中所载三黄丸(大黄、黄连、黄芩)主治“男子、妇人五劳七伤,消渴”,是清热泻火法的代表[6]。刘河间还善用石膏、寒水石、滑石、大黄、连翘、栀子、瓜蒌根等清热泻火治疗“烦热烦渴”以及消渴并发之“目瘴、痈疽、疮疡”。后世医家李东垣传承了其清热泻火法治疗消渴病的经验,提出了消渴病中消若见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硬、小便数,选调胃承气汤、三黄丸治疗。李东垣认为,以寒治热是消渴病热证基本治法,但必须三因制宜,若苦寒过量,可以导致“上热未除,中寒复生”弊端。所以李东垣使用清热泻火之黄连、黄柏时,剂量较小,且配以地黄、知母、石膏以甘寒养阴,同时佐以炙甘草、升麻黄、柴胡、荆芥、防风等辛温升阳,鼓舞胃气,防止寒凉伤中,这对规范临床使用清热泻火法治疗消渴确有指导价值[7]。
1.2 清热解毒法清热解毒法作为治法体系出现于秦汉时期,代表方药是葛根芩连汤、白头翁汤、黄芩汤等,当时主要用于湿热下利或热毒下利,仲景尚未将清热解毒法用于消渴病治疗中。刘河间提出了消渴病的并发症为:“周身热燥郁,故变为雀目、内障、痈疽、疮疡。”在甘寒养阴、生津润燥的治疗基础上,常加入黄连、大黄、栀子、薄荷、连翘、天花粉等清热解毒之品。刘河间特别擅长使用天花粉。《神农本草经》谓:“天花粉,味苦寒无毒,治消渴、身热。”后世也用天花粉解毒排脓,所以天花粉一药两用。此外,清热解毒之良药黄连,也有治疗消渴的作用。如《神农本草经》中载其“止消渴、大惊……治口疮”。后世医家张子和在《世传神效诸方》中载“治消渴黄连二两,水煎顿服,立止”,为后世从清热泻火解毒治疗消渴病奠定了基础。朱丹溪常在甘寒养阴基础上加用黄连、天花粉以泻火止渴[8]。仝小林教授擅长大剂量使用清热解毒之黄连及其复方如葛根芩连汤、黄连解毒汤、半夏泻心汤等治疗糖尿病[9]。李东垣在《脾胃论》中详细记载了“三黄丸”适应证,其中包含了消渴病火毒炽盛导致的口疮、痈疖疮痍,为后世应用清热解毒法以及三黄丸治疗消渴并发症指明了方向[10]。研究表明,葛根、黄连、天花粉等药具有较好的降血糖作用,其机制与改善胰岛素抵抗、增强胰腺分泌功能、调整机体内环境有关,此外,上述药物还有抗感染、抗细菌毒素等广泛药理作用,对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如感染(肺部、膀胱)也有较好的治疗作用[11-13]。
2 温阳法
消渴病的病机主要是阴津亏损、燥热偏盛,治疗以清热润燥、养阴生津为大法,兼顾三消病症,所以温阳法并不是消渴病治疗大法。但是,消渴病病程较长,患者体质不一,再加上治疗不当等,仍有阳虚的情况[14]。温阳法在消渴病中主要有温补脾阳法、温补肾阳法。
2.1 温补脾阳法脾是后天之本,主运化,为胃行津液。若脾阳不足,不能消磨水谷,津液无从化生,亦能发为消渴病。此时若单纯润燥生津,不仅不能解渴,反而加重脾虚。从文献来看,温补脾阳法治疗消渴出现较晚,是由清朝陈修园提出。陈修园认为:“人体津液不能自化,一由脾气运化,一由肾阳火化,若见渴止渴,徒选养阴生津之药,最为误事,若能使用七味白术散、理中丸等健脾气,温脾阳,则津液自生[15]。”清代医家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认为,对于中焦虚寒而见小便频数者,可以使用理中丸加益智仁健脾温中,收涩缩尿治疗。后世医家单纯使用温补脾阳治疗消渴的较少,多温清并用。如现代中医学家朱进忠对上燥下寒、湿郁不化之消渴善用经方柴胡桂枝干姜汤以润燥温脾治疗;对于中焦虚寒之消渴症见胃脘痞满、脉浮紧、舌苔薄,服用清热养阴药无效者,选用附子理中汤合五苓散温运脾阳获效[16]。笔者在临床上对脾阳虚之痰饮病患者(症见口渴、喜热饮、苔白滑、脉沉细)多使用苓桂术甘汤加天花粉健脾益气,生津润燥获效。
2.2 温肾助阳法温肾助阳法始于张仲景之肾气丸。《金匮要略》云:“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该法开创了从温补肾气治疗消渴病之先河,但是金元时期,以燥热立论盛行,不少医家反对使用温阳法治疗消渴病。如刘河间在《三消论》中言:“凡见消渴,便用热药,误人多矣。”直到明清时期,随着温补学派兴起,肾气丸为代表的温肾法重新受到了重视。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言:“夫命门为水火之宅,凡水亏证固能为消为渴,而火亏证亦能为消渴。”进一步解释道:“水火失调,水不济火,火游于上可以发为消渴或阳不化气,水精不布,有降无升,直入下降,小便频数。”也可以导致消渴,阐明了肾阳不足致渴的原理。张景岳主张使用八味地黄丸、右归丸等温补肾气,阴中求阳治疗。之后的医家赵养葵等进一步阐发了肾气丸治疗消渴病的机理,认为“桂枝、附子辛热壮少阴之火,灶底加薪,枯笼蒸溽,槁木得雨,生意维新”,即肾气丸不是单纯的温阳药,而重在滋肾以化气,以滋化源[17]。使用肾气丸温肾化气,蒸津上润治疗消渴病自此受到了许多医家的高度重视,体现了消渴病治法向经典的回归。此后如俞昌、尤在泾、沈金鳌等积极倡导此说。现代医家桑景武在温阳法的影响下,对于久用养阴清热治疗消渴无效而见舌淡齿痕、苔滑白、脉沉细之阳虚消渴者,善于使用真武汤、四逆汤等温里药治疗,认为此法有“不生津而津自回,不滋阴而阴自充”之妙[18]。
3 养阴法
养阴法,又称为滋阴法,主要是针对阴津不足,燥热内生,虚火不降而设。消渴病多见口渴干燥,渴喜冷饮,舌红少津等阴虚燥热之象,所以根据《黄帝内经》“热则寒之”“燥则濡之”以及“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治法,常选甘寒养阴生津之麦冬、天冬、生地黄、百合或佐以天花粉、葛根、黄连等养阴降火止渴。而消渴有三消之分,上消在肺,中消在胃,下消在肾,所以治疗有所偏重,分述如下。
3.1 养肺阴肺主一身之气,为水之上源,燥热灼肺,肺热为急,则见口渴多饮,气短乏力,小便频数,治疗以养阴润肺,兼以清热生津为主。张仲景之白虎加人参汤、竹叶石膏汤开创了养阴生津治法的源流。元代朱丹溪麦门冬饮子(麦冬、天花粉、知母、甘草、五味子、生地黄、葛根、人参)是滋补肺阴代表方药。此外,朱丹溪之地黄饮子(甘草、人参、生地黄、熟地黄、黄芪、麦冬、天冬、泽泻、石斛、枇杷叶)、玉泉丸(麦冬、人参、茯苓、黄芪、乌梅、甘草、栝楼根、葛根)也是养肺阴代表方药,而且还能补肺气、滋肾阴,为后世从“金水相生”治疗本病提供了思路。程钟龄所创之二冬汤是补肺养阴之良方。后世单纯使用本法较少,多与清热泻火、滋补肾阴、益气健脾结合起来使用。
3.2 养脾阴脾胃同居中焦,升降相应,燥润相济,消渴病中焦实火责之于胃,虚火责之于脾,脾能胃行津液,养脾阴也是治疗消渴病的重要方法。其渊源应是仲景创立的竹叶石膏汤、白虎汤治疗伤寒热病所致肺胃津气两伤。刘河间创立的人参散(石膏、寒水石、滑石、甘草、人参)以及钱仲阳之七味白术散以及后世张锡纯之玉液汤皆能体现出健脾养阴,润燥止渴的治法。现代著名中医学家施今墨治疗消渴病,以健脾益气,养阴生津为主,善用生脉饮、增液汤、黄芪、山药、苍术、玄参等,医林所称道,其中苍术善于燥湿健脾,玄参善于养阴生津,堪称经典配对[19]。
3.3 滋肾阴肾主水,藏真阴真阳,久病及肾,出现小便浑浊如膏,伴腰酸乏力,头晕耳鸣、脉细数,古人将此类消渴病又称为“肾消”。所以滋补肾阴也是消渴病特别是下消常见的治法。滋肾法治疗消渴病的代表方是六味地黄汤,最早由金元医家李东垣提出,其言:“下消者,燥烦引饮,耳轮焦干,小便如膏,以六味地黄丸治之[20]。”朱丹溪、张景岳、赵养葵均积极倡导。赵养葵认为,水火失调、气血失养发为消渴,治疗不应局限于三消之说,以治肾为急,当选六味地黄汤滋水降火,突出了从滋补肾阴治疗消渴病的思路。清代著名医学家程钟龄善用地黄汤生脉散合用治疗下消病,滋肾润燥,补肺益气,金水相生,使肾水得养,肺气充沛,津气化源不绝,发展了滋肾润燥法,为后世从“滋化源”治疗本病奠定了基础[21]。
4 总结
消渴病的治法除了以上清热、温阳、养阴以外,还有行气、收敛、活血、祛风等法[22-23],但是以上3种治法是治疗消渴病的基本大法。诚如李东垣所言:“虽方士不能废其绳墨而更其道也。”也反映了中医对消渴病病机与治法的主流观点。熟悉消渴三大治法产生的时代背景、源流、发展历程、代表方药对我们全面继承古代中医学治疗消渴病的精华,指导临床辨证施治,新药研发,防病治病以及理论创新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通过文献学习,应该注意到,消渴病有本病、有并发症,患者病机多虚实夹杂,脏腑相连,若徒受一病一法,一病一方,则执一不通,病不能除[24]。在古代社会,医疗条件、技术相对落后,消渴病呈现自然病程变化,“三多一少”症状十分突出,所以古代以“三消”立论,治疗重在泻火养阴为主[25]。随着科技发展,医疗条件改善,得益于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目前我国消渴病大部分“三多一少”典型症状不多。近年来,消渴病患者并发症日益增多,其病机往往虚实夹杂,病理因素常有阴虚、气虚、湿热、络瘀等,需要谨守病机,知常达变,灵活施治。在消渴病的治疗中,单纯的治法较少,而以益气养阴、滋阴清热除湿、滋阴温阳、益气活血等复法较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