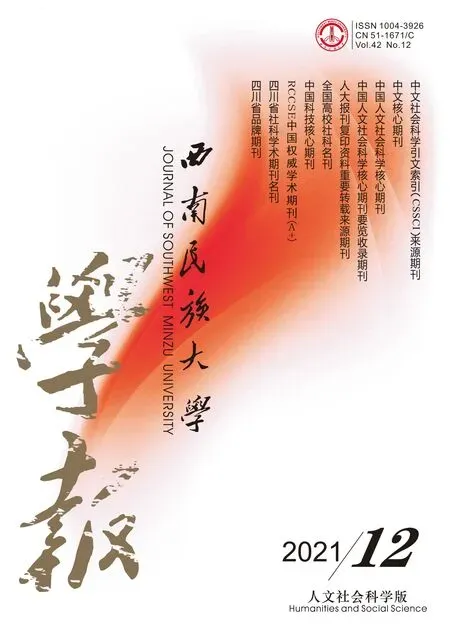重构藏地乡村的精神图谱与历史记忆
——从《空山》到《云中记》的文学启示
2021-04-17吴雪丽
吴雪丽
[提要]从“机村传说”始,阿来开始讲述20世纪后半期藏地乡村的历史,在思考小历史与大历史、村庄与国家、个人与时代、创伤经验与历史记忆的关联时,也标示出他之于藏地乡村历史变迁的复杂的情感地图与情感结构。阿来试图超越“在地”的、“实在”意义上的乡土历史书写,走进乡村的内部去探寻个体和乡村的精神图景与文化记忆,通过对藏地乡村的人物图谱的深描、对藏地村庄精神图景的重构、对族群传统和文化记忆的打捞,显示出他的乡村书写所可能达到的广度与深度。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阿来以对他的故土家园嘉绒藏地的书写而著称,以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为原乡,阿来建构了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学地图和小说世界。从《空山》、“山珍三部曲”到晚近的《云中记》等,阿来执着于对个人的生命经验、村庄的精神图景、族群的文化记忆的书写,在个人精神史、乡村史和国族史的复杂纠葛中探寻个体、村庄、族群精神重建的可能。阿来成长所经历的历史变迁和他小说念兹在兹、不断书写的藏地乡村有着时间上的同构和情感上的复杂关联,这使阿来的乡村写作呈现出不一样的特质,那就是,他试图超越“在地”的、“实在”意义上的乡土历史书写,走进乡村的内部去探寻个体和乡村的精神图景与文化记忆,通过对藏地乡村的人物图谱的深描、对藏地村庄精神图景的重构、对族群传统和文化记忆的打捞,显示出他的乡村书写所可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
一、对藏地乡村人物图谱的深描
在阿来的藏地乡村书写中,有一系列的人物在他不同时期的小说中是有延续性的,从阿来始终关注的某一类人或者某一种生活方式、生活经验的演变,可以看到他小说中复杂的张力结构和深层动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或者说有自己在大历史中规定性的来处和去处,但在每一个个体和他者,和他们成长、生活于其中的乡村共同体、族群共同体及国家共同体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阿来写作视野的逐渐打开和拓展,他慢慢地从与大历史的紧张关系中走出,开始从人的精神和心灵的意义上尝试打开和历史对话的多重空间,从抗议、争辩到对话,尝试超越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伦理性要求,进入一个更开阔的历史场景,重构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阿来的乡土系列小说中,个体和历史的关系更具体的是在个体与自己生活的村庄构成的关系中得以呈现的,换言之,个体和国族历史的关系是通过“村庄”这一“在地”的生存空间进行转译的。对于阿来小说中那些生活在藏地乡村的平凡、普通的个体而言,他们大多数人的生命里并没有机缘和外部的大历史产生直接的身体关联,比如通过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国族叙事的现场,但正是在连接和凝聚了具体的个人经验的乡村空间中,他们和村庄的关系具体而微地呈现了大时代对个体生活的规训以及个体的疏离与僭越。
少年是阿来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类人物,比如“机村传说”中的少年格拉、少年兔子、少年达瑟,《三只虫草》中的少年桑吉……少年叙事常常让我们想到成长,但阿来小说中的乡村少年并不是成长小说中历史转换中的个体成长,而是以相对内在的、具有自我完满性的少年叙事拷问着历史转换的伤痛,而且,他们以更具象征性、隐喻性的精神性存在和村庄构成对话。在《随风飘散》中,生于洁净的雪天的兔子,是一个几乎和雪一样纯洁、脆弱的孩子,而少年格拉是不知从哪里沦落到机村的私生子,他们的存在映照的是机村传统伦理的日渐衰微。在机村少年中,只有兔子愿意和没有父亲的孩子格拉做朋友。在隐喻的意义上,兔子可以视为那个过去的、传统的机村的缩影,阿来通过兔子这一个纯净的孩子的形象向过去的机村告别。在阿来回望的视野里,属于过去的时光记录的是藏地乡村的淳朴与善良,人们收留了不知来自何方的桑丹和格拉母子,并供给他们基本的衣食。但新时代来临,人心逐渐变得坚硬,“在机村,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猜忌构成了生活的主调”[1](P.127)。少年格拉生活在被驱逐与被侮辱当中,在鞭炮把兔子炸伤后,根本没有在场的格拉被所有的村人指认为凶手,格拉不仅失去了唯一的朋友兔子,而且在机村人的冷眼中死去。兔子和格拉的生命都永远停留在了他们的少年时代,停留在有关孩子的所有纯洁和美好的隐喻和日益污浊的世事对比之中。虽然,这种有关藏地过往的记忆也许并不可靠,但这种有关过去的情感结构和对“美好往昔”的诗意建构不过是为了讲述今天的“变”,而今天的“变化”不是自为的而是被迫对外部历史的敞开,在某种意义上,“机村传说”以两个纯净的孩子的死亡打开叙事空间,是一种伤悼也是一种质疑!
在“机村传说”的开始,兔子、格拉离开人世,属于过去的藏地乡村的传统也日渐“随风飘散”。而在《达瑟与达戈》中,延续着机村的这一叙事脉络的是书呆子达瑟。达瑟和他的村庄在精神上依然是游离的,他离开村庄到城里去上学,而最后带回来的只有几箱书,《百科全书》上的知识使他重新认识了机村的自然、地理,也使他知道了机村之外的“世界”。但这个常驻于树屋上的少年的知识无法和机村的现实对话,在机村人眼里,他是一个多余的怪人,而机村人在特殊岁月中的疯狂也让他觉得不可思议,而且,他所看到的机村现实“和书上说得不一样”,他困惑于“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不该杀死那些猴子,却偏偏要对它们痛下杀手?”“为什么聪明的人尽干愚蠢的事情,愚蠢的人却问出了聪明的问题?”[2](P.127-128)达瑟的问题质疑和拷问的是他生活其中的机村人,更是指向荒谬与疯狂的人心和历史。可以说,从少年兔子、格拉到达瑟,阿来建构的藏地乡村的这一人物谱系,并不具有“在地”或者说现实意义上的生长性,他们更多是在超越“在地”和“实在”的精神、伦理的意义上质疑着藏地乡村某种美好的东西的日渐流失。
这种具有某种超验意义的、无法落地的精神性书写在阿来后来的写作中开始落地生根,日趋开阔、明亮。在《三只虫草》中,同样痴迷于《百科全书》的孩子桑吉,健康、聪慧、活泼、善良,他热爱读书,并在虫草季节用自己从学校学来的“概率”帮助爸爸选到了执勤的好日子。一部同样的《百科全书》连接起两个不同时代的孩子,达瑟这个懵懂的智者,无法用他的“知识”和机村对话,但同样渴望知识的桑吉,则隐喻了藏地乡村一种开放性的未来。兔子、格拉和达瑟都是内在于机村的,在机村的内部,他们的人生得以展开和终结。但是桑吉通过《百科全书》,不仅在知识和精神的意义上打开了自己的生命空间,而且在实践的意义上为了寻找《百科全书》走出了自己原本封闭的乡村世界,看到了外部世界的善与恶。而且,在他终于可以走出乡村来到更广阔的世界时,回望过往的生活,他以宽容与爱向过去告别。校长曾经不肯借《百科全书》给桑吉,桑吉还目睹了《百科全书》被校长的孙子当成玩具,但到了城里读书的桑吉终于有机会得到了《百科全书》。在《三只虫草》的结尾,桑吉在给多布杰老师的信中说:“我想念你。还有,我原谅校长了”[3](P.115)。这是一个携带着藏地乡土的丰厚与善良走向外部世界的故事,求知若渴、美好明亮的桑吉,作为阿来小说中新时代的乡村少年,越来越茁壮成长,并逐渐在藏地乡村与外部世界之间搭建了一座有可能通向更为开阔的未来的桥梁。
如果说,阿来小说中的少年人物图谱逐渐打开了一种更为开阔的藏地乡村叙事,那么,阿来小说中那些更具有主体性的成年人的选择,则显示了他构建的藏地乡村人物图谱和村庄历史、族群精神之间更为丰厚的联系。《轻雷》中的拉加泽里人生中的两次重要选择都是具有主体性的选择,高中快毕业时,因为家里贫穷,成绩优异的他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到两江口寻找发财的机会,在人们靠乱采乱伐倒卖木材一夜暴富的神话下,拉加泽里也铤而走险,最后入狱。在“机村传说”的最后一部《空山》中,多年后,带着巨额的财富和赎罪之心回到机村的拉加泽里,开始用自己的钱义务植树,希望家乡变回青山绿水。更重要的,他的小酒吧成为了机村在逐利时代最后的精神汇聚之地,这种对故土的回归和持守,使他和机村之间构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再生关系。《蘑菇圈》中的斯炯,曾经因为在工作队帮忙有机会到城里去上学,又因为哥哥从寺庙逃跑被送回机村,而且生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在机村受人轻视,但斯炯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并且在饥荒的年代里,靠自己养护的蘑菇圈帮助村人度过了饥荒之年。她坚韧、安宁、心地善良,而这样的善正是一个族群生生不息的源泉。如果说《天火》中的央金和《达瑟与达戈》中的色嫫对机村的逃离是对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的向往,是封闭的藏地乡村被迫打开后被激发的欲望的迸发,那么,斯炯这个“藏地乡村的女儿”在阿来的小说就具有了那种坚韧、生长性的力量。威廉斯在论及哈代的小说时说:“‘受人轻视,坚韧顽强’:这并不是哈代这种人的故事,不是那种遥远的、有局限的、美丽如画的故事;而是人物在他们成长的挣扎中受到轻视——他们挣扎着去爱,去做有意义的工作,去学习,去教导;他们在这种共同的冲动中坚韧顽强地生活着,这种冲动会冲破并超越特定的分割和失败。这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的延续,而且是一段历史和一个民族的延续。”[4](P.292)在《蘑菇圈》中,斯炯的“受人轻视、坚韧顽强”显示的正是在艰难世事中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力量。阿来在谈到他的“山珍三部曲”时曾经说过:“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5]“生生不息”的人性的温暖和良善,在阿来看来,不仅可以使人们度过物质上的饥荒,而且借此可反观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无尽的贪欲与剥夺,在《蘑菇圈》的结尾,斯炯阿玛的蘑菇圈还是被无人机发现了,人心还会变好吗?这是阿来新的忧患,是藏地乡村的,也是整个中国的。
在晚近的关于地震的小说《云中记》中,祭师阿巴和村庄的关系更是一个典型的精神与心灵重构的故事。地震后,云中村因为坐落在滑坡体上无法重建而整体搬迁,但在离开五年之后,阿巴归来,履行一个祭师的职责:祭祀祖先和抚慰鬼魂。阿巴为什么要执意回到云中村并和云中村一起消失,一方面,原始苯教信仰和祭师身份使这一选择具有了逻辑上的合理性,但小说更为重要的是,它讲述了一个人在精神挂空之后所经历的艰难的重归和重建过程。如果说在阿来以往的小说中,个体和村庄的复杂关系背后是他的历史关怀和历史疑问,那么,《云中记》中个人身体和精神的劫难都不是外部的历史带来的,而是自然,是不可抗拒的自然之力,是突然降临的无妄之灾。面对无妄之灾,个体如何重建与过往自我的关系?如何重建自我与村庄的关系?《云中记》是一个向死而生的叙事,地震是一场失去了反抗对象的集体灾难性记忆,是一个在实在的层面上无法修复的创痛,在地震五年之后回到已成废墟的云中村,是“记忆”拯救了阿巴心灵的荒芜和无所适从的惶惑,通过在回忆中重建个人的过往和村庄记忆的过往,阿巴在过去的生活中寻找到“归来”的意义。“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6](P.82)对自我和村庄过往生活的回忆,是重新找回精神与心灵归属的重要媒介,在时间的河流中,阿巴把一个因灾难而分裂的自我重新聚合,借助于回忆中的自我和村庄里那些曾经鲜活的众生,阿巴再次确认了自己归来的意义,并最终在罂粟花开、鹿群归来、天地万物一片清明中重新理解天地万物的关系,与灾难和解,与命运和解,与世界和解。
从阿来小说绘制的藏地乡村的人物图谱,可以看到他持续探寻的那种具有某种内在的、稳定性的个体与乡村整体性生活之间的不同的情感结构。每一个个体都被困于不同的时代和命运之网中,他们几乎都不是具有抵抗性力量或者与时俱进的力量的强者,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阿来藏地乡村中的个体往往是历史中的弱者、卑微者或者边缘者,但阿来小说的意义也可能恰恰在这里,那就是他在讲述藏地乡村变迁时更为关注那种精神性的因子以及这种精神性存在和乡村历史的复杂关系,那些民间智慧的、良善的微光既拷问着历史的冷硬,也保留了那个族群得以生生不息的力量。
二、对藏地乡村精神图景的重构
从“机村传说”始,阿来不断回到他的嘉绒故土,通过重构乡村记忆和乡村图景,追问藏地乡村的来去与出处。他的乡土写作一方面从带有自己生命经验的乡村出发,追问20世纪后半期以来藏地乡村的历史命运及其现实境遇,叩问大历史叙述对民间沉默无言者的遮蔽,让底层发出声音。另一方面,他的写作始终在“实在”与超越“实在”、在“此在”与超越“此在”的意义上,在精神上的回望与想象中的“寻根”中,构建藏地乡村的精神图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贾平凹对他的陕南故土的书写、莫言建构的高密东北乡的纸上故乡,苏童回到枫杨树乡的精神还乡等,都有不同的写作旨趣与精神诉求。而阿来的藏地乡村叙事,不只是丰富了当代文坛上这种地方性书写和拓展了它的地域边界,而更应看到,他对边地中国乡村的精神探寻所显示的乡土写作可能达到的深度。
当威廉斯反思田园诗对风景的文学幻想时说:“只有牧羊人生活的宁静展现在观者的眼前,还要掩饰或者隐藏起这种生活的卑贱,同样也只展示它的纯真,而藏起它的痛苦。”[4](P.26)他进而追问,这一承载了视角危机的叙述者是谁?他们又在对谁说话?从“机村传说”开始,阿来想要逃离的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外在”于藏地的视角,远离那个关于藏地神秘和神圣之所的书写,他不仅要展示“生活的宁静和纯真”,同时也要展示“生活的卑贱和痛苦”。这种文学传统既是赵树理式的,也是孙犁式的,当然,在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说,在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和孙犁构建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学传统:政治性的乡土书写和抒情式的乡土书写。当我说阿来的乡土书写既是赵树理式的又是孙犁式的时,我想说的是,阿来进入了乡村的内部,以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的深情,书写着乡村的历史苦难和个体的情感创伤;同时,他又试图超越这种“在地”的苦难,在精神和心灵的意义上,在抒情和浪漫的脉络上,重建藏地普通人的精神图景和心灵诗学。
相对于阿来的成名作《尘埃落定》那种浪漫传奇式的历史书写,他关于藏地乡村的书写回到了写实的民间叙事立场。在“机村传说”中,外边的世界以不容置疑的方式进入了机村的历史,带来了机村人不能理解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毁坏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在《随风飘散》中,新时代来临,寺庙里的神像被摧毁,僧人还俗,但恰恰是还俗僧人恩波最先欺凌了无依无靠的外来者格拉。额习江奶奶这样描绘了她看到的机村:“可是,你们知道我们机村是什么吗?一个烂泥沼,你们见过烂泥沼里长出笔直的大树吗?没有,还是小树就在你泥沼里腐烂了。知道吗?这就是眼下的机村。”[1](P.19)在《达瑟和达戈》中,达戈对色嫫的爱情幻灭,映照了那个“一切都变得粗粝”和“美好爱情被毁损”的时代。机村人甚至撕毁了和猴子的千年契约,向在秋收后到田野里觅食的猴子射击,人心变得疯狂而坚硬。在《天火》中,无边的天火燃起,色嫫措湖被炸毁,传说中护佑机村的野金鸭飞走了。“机村传说”是一个藏地乡村渐次破碎的历史,阿来不只讲述了机村现实层面上的森林被砍伐、神湖被毁、土地流失的悲怆,他更是讲述了藏地乡村所遭遇的精神和心灵意义上的毁灭和创伤。机村的过去和“美好往昔”联系在一起,而机村的现在被时代的风潮卷入了疯狂和毁灭当中。有关过去的是某种确定性的生活方式和乡村伦理,但这种有关过去的记忆已经无法凝聚现在,甚至于在被迫改变或者无法抗拒的时代转换中,也已无法传递一种温暖的社群和族群情感。
阿来讲述一个乡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颓败,但他并不止于民间史对大历史的无声的抵抗,他更想探寻的是一个乡村在被损害、被剥夺之后的精神重建的可能,并进入乡村和族群历史的内部寻找这种精神重建的历史资源。这就使阿来的小说不是在现实的层面上而是在精神和心灵的层面上获得了不一样的视野。他首先追问的是,这种变化的缘起在哪里?在《天火》中,“机村人至今也不太明白,他们祖祖辈辈依傍着的山野与森林,怎么一夜之间就有了一个叫做国家的主人。当他们提出这个疑问时,上面回答,你们也是国家的主人,所以你们还是森林与山野的主人。但他们在自己的山野上放了一把火,为了牛羊们可以吃得膘肥体壮,国家却要把领头的人带走。”[1](P.142)可见,在历史的层面上,阿来首先追溯的是“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争辩,是民间伦理在应对国家伦理时的惶惑、不安与不解。但如果我们只是在国家话语对民间话语的压抑与伤害的脉络上解读阿来的乡村写作的话,那么,他并没有逃离1990年代以来新历史主义写作的民间叙事伦理,阿来的不同不仅在于他书写的是边地中国,更重要的可能是,他始终追问人的精神困境与乡村的伦理传统遭遇创痛之后重建的可能。于是,从《荒芜》开始,当机村因为树林被砍伐、火灾和接踵而来的泥石流淹没赖以谋生的土地之后,人们向古歌吟唱中的祖先之地寻找土地,觉尔郎古沟里肥沃的土地,使机村人度过了饥荒之年。《空山》中,觉尔郎古沟已经被开发为旅游胜地,规划中的水库将淹没机村,在面临“空山已空”,机村即将不在的时刻,人们发现了达瑟当年藏在夹墙中的书籍和他写下的诗歌,发现了色嫫措湖底几千年前的祖先遗址。“已经中断的、仅留下痕迹供人触摸的前历史对于一个后来的时代来说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当这个后来的时代把那个过去当作它自己时代的规定性的基础加以认可的时候。”[7](P.357)人们重新发现的觉尔郎古沟、达瑟书籍和色嫫措湖底的古代村庄的遗址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这些远古历史的遗迹重新激活了机村人关于祖先与家园的记忆,围绕着这些沉默的废墟,新的机村故事将被讲述,族群共同的文化记忆将被召回。
如果说“机村传说”中的机村依然是一个社群意义上的村庄,它历经天火、泥石流后,青山不在,人心不古,但它依然还在,依然还有重生的可能。但在《云中记》中,地震来临,云中村罹难,时间断裂,空间荒芜,云中村在现实的意义上已经无法获得重生。机村的灾难是天灾人祸,历史和其中的人们都是历史的人质,但云中村面临的是无妄之灾,人们无法抗议与控诉,这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一种绝望的存在方式。那么,面对废墟,如何反抗这种绝望的生命体验?如何修复这种深渊般的创伤记忆?阿莱达·阿斯曼认为古老的废墟往往兼具了双重的符号意义:“它们既编码了遗忘,也编码了回忆。它们标志了一个过去的生活,这个生活已经被消除、被遗忘了,已经变得陌生了,消失在历史的维度里,它们同时也标志了一个回忆的可能性,回忆将在记忆的维度里重新唤醒被时间撕裂和消灭的东西,并且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使之获得生命。”[7](P.36)阿巴回到已成废墟的云中村,借助回忆和宗教的精神性力量,重新唤醒了废墟中的村庄,那些可见的遗留物使得关于一个村庄的过去的记忆重新变得可触可感,血肉丰满。阿巴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村庄里那么多各有性格的人家,如沉埋于地下的火花重新照亮了云中村的历史。在深埋了鲜活的个人记忆和村庄记忆的空间里,村庄历史的地形学变成了有温度的日常生活编年史。在众志成城与多难兴邦的地震叙事中,阿来留下了一份关于一个人、关于一个村庄的精神影像,这一精神影像,映照着人类对创伤记忆的修复与超越的可能。
所有的文学传统都具有选择性,在对藏地乡村的书写中,阿来选择的不是牧歌式的田园诗传统,也不是把藏地神圣化的乌托邦书写,而是忠实于自我与族群的生命经验。他不是一个乡土的怀旧者,而是敏锐地观察到乡村在新的历史中不曾预料的生存和价值危机以及和新的生活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冲撞。他既根植于那片土地,同时又因为从乡村到都市、从藏地到汉人聚居区的离散经验,使他的视点具有了某种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打开了更为开阔的叙事空间,使他的藏地乡村叙事呈现出复调的叙事特征:其中既包含了对被视为“进步“的历史变革的不解与游移,对脱离旧有的生活方式后的迷茫与伤感,同时又体认到藏地”变革“和向新的历史敞开的必然性;既有对“实在”意义上的乡土变迁的讲述,又有超越“实在”、重构新的乡村精神图景的努力。
三、对族群传统与文化记忆的打捞
一个村庄也是一个地方和文化的共同体,对于阿来小说中的藏地乡村而言,同时也是族群和文化的共同体。杨·阿斯曼认为,每一个族群和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凝聚性结构’可以把人和他身边的人连接到一起,其方式便是让他们创造一个‘象征意义体系’——一个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这个空间起到了连接和约束的作用,从而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并且为他们指明了方向。”[8](P.6)这个“象征意义系统”把一个族群的昨天和今天联系在一起,在历史和社会的层面上凝聚一个族群的文化记忆和现实认同。那么,在阿来的藏地乡村叙事中,这个“象征意义系统”是什么?它又是怎样让“我”认同“我们”的“乡村”和“族群”呢?这就涉及对村庄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的不断重写与重构,使这个村庄成为“我们”的村庄,铭记“我们”的历史记忆。
“机村传说”在族群和文化的意义上讲述的是一个族群传统和文化记忆逐渐“随风飘散”又重新打捞与复活的故事。在“机村传说”中,始终存在着两条并列的纪年与纪事方式,一是公元纪年的方式,记录的是“国家”进入机村的大历史叙事,一种是属于机村自己的民间生活的纪事方式。在古老的循环的时间观念中,机村人祖祖辈辈过着没有什么变化的生活,但在以现代的时间纪年的岁月中,一切都变得飞快,机村慢慢失去了自己的记忆。杨念群在论及近代以来国家意识形态对乡村社会的逐步渗透时,指出:“政治的强力乃至暴力的支配也许能从‘地方性逻辑’的角度加以别样地理解。现代政治对地方社会的塑造从规模和力度上都是空前的,‘政治’不仅在形式上摧毁了地方传统赖以生存的核心组织,也大量毁灭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9]在“机村传说”中,现代政治运动以无坚不摧的方式打破了乡村原来封闭的社会结构和静态的生活方式,在机村的现代历史进程中,最先被摧毁的是对于族群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庙里的佛像倒塌,僧侣被迫还俗。而随着宗教信仰的被摧毁,是人心的逐渐坚硬,兔子生病,人们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无辜的外来少年格拉的身上,直接导致了格拉和母亲再一次的颠沛流离。当然,“从表面看,‘上层政治’已无可争辩地取代了地方传统的位置”,但根植于民间传统的“地方性逻辑”依然如潜流涌动。在《随风飘散》中,格拉母子归来的那个午后,愧疚的机村人在门口摆满了他们送来的食物。在《天火》中,巫师多吉从监狱中逃跑,村长格桑旺堆隐藏了这个天大的秘密,并派人给多吉疗伤。在《荒芜》中,“机村人因为贡献出森林而失去了土地,因为泥石流毁掉了土地,种不出果腹的粮食而感到屈辱与愤怒。”[2](P.294)这种“屈辱与愤怒”来自古老的民间传统中对土地、粮食的谦卑。那么,这种根植于民间的地方性逻辑如何展开?被喧嚣的时代淹没的族群记忆又如何被唤醒?村庄和族群的创伤记忆如何被修复并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进入新的重建中?
阿来选择的是回到祖先的记忆和族群的文化传统中重新寻找这个民族得以度过劫难的历史资源。在《荒芜》里协拉顿珠的古歌中,祖先的丰腴肥美之地开始显影,作为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以梦境的方式再次召唤着机村人。在古歌的传说中,数百年前,那里曾经是一个神秘的王国,一年四季鲜花飘香,五彩的鸟群永远飞翔,河里流着金子和玉石……杨·阿斯曼认为,“神话是(主要以叙事形式出现的)对过去的指涉,来自那里的光辉可以将当下和未来照亮。”[8](P.75)古老的神话传说以世代吟唱的古歌的形式保存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机村人在近乎荒芜后的绝望中向祖先的家园寻觅,遥远的过去的英雄时代成为了族群的新的乌托邦。“神话是与认同联系在一起,神话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从哪里来和‘我们’所处何处这些问题给出了答案。神话中保存和传承的神圣的内容,是一个集体用来建筑其统一性和独特性的基石。”[8](P.148)对祖先的传说之地的寻找,重新凝聚了机村疯狂的人心。如果说《荒芜》中觉尔郎古歌的族群神话和历史记忆指向现实的巨大匮乏和族群再生的历史资源,那么,在《空山》中重新被发现的达瑟的诗集则以文字记载的方式再现了这个民族的精神和心灵力量。在机村人都疯狂地扩建房屋以求得到更多的补偿时,是达瑟家夹墙里发现的藏书和他写的诗,拯救了疯狂的人们,让很多人逃脱了一场因贪欲而可能带来的劫难,从此,“机村人正处于某种难以理喻的境况下时,就会想到那个刚刚发现的达瑟的本子。就要想想,那个本子里是否有什么话可以援引。”[10](P.285)曾经被淹没的、失踪的、在隐喻的意义上代表族群精神的记忆终于穿越遗忘的帷幕再度归来,参与了新的机村伦理的重构。
在《云中记》中,祭师阿巴之所以能够在记忆中重构云中村作为一个村庄的地理意义与精神意义,也是依靠这个族群集体记忆中两种重要的传统:宗教与仪式。宗教信仰常常给人们一种看待生活的方式,那些信仰也深深地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经验中。面对已成废墟的云中村,祭师阿巴内心的孤独与绝望一度让他倍感虚弱,对于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天崩地裂,生灵涂炭,语言是如此的苍白,无力穿透甚至无法触碰,“因为语言属于所有的人,因此那些无与伦比的、特殊的、绝无仅有的东西都无法进入其中,更不用说一种绝无仅有的持续的恐怖的经历了,但是恰恰是创伤需要言语”,但“这些语言不再是回忆和讲述的语言,而是招魂和巫术的言语:‘回忆是招魂,有效的招魂是巫术’”。[7](P.295)祭师阿巴回到云中村,就是要履行自己作为一个祭师的职责:“我是云中村的祭师,我要回去敬奉祖先,我要回去照顾鬼魂。我不要任他们在田野里飘来飘去,却找不到一个活人给他们安慰。”[11](P.46)回到云中村的阿巴击鼓摇铃,召唤和安慰那些漂泊不能安息的灵魂,他要把云中村的亡魂集聚起来,和村庄一起消失。阿巴最终和世界和解,以众生平等、万物归一的方式弥合了创伤记忆:“不要怪罪人,不要怪罪神。不要怪罪命。不要怪罪大地。”“这个世界不欠我们什么。我们也不会去祸害这个世界,我们只是自己消失。”[11](P.344-345)
一方面通过招魂安抚那些飘荡在云中村的亡灵,一方面通过祭山的仪式汇聚集体记忆并再次确认族群的身份认同,云中村在象征的意义上重生。地震前,在每年祭祀山神阿吾塔毗的日子里,离开云中村的人们都会千里迢迢赶回来,盛装出行、纵情歌舞。“节日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晦暗的存在重新照亮,神亲自将因忽略和遗忘而变得自然平淡的秩序重新擦亮。”[8](P.5)云中村人对神山的祭祀,既是对神勇的祖先阿吾塔毗后代的身份确认,也是凝聚族群记忆和文化传统的有效方式。保罗·康纳顿认为社会记忆的重要方式之一即是不断重复与创新的仪式感,“仪式之所以被认为有意义,是因为它们对于一系列其他非仪式性行动以及整个社群的生活,都是有意义的。仪式能够把价值和意义赋予那些操演者的全部生活”[12](P.50)。一个社会、社群或者族群共同体的认同背后是他们共同的集体记忆,当然,因为对于过去的记忆在不同的个体那里有分歧,因此并不能完全共享经验和记忆,尤其是在不同代际之间,族群记忆会受到阻隔,那么,仪式就成为凝聚认同感的重要形式。“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载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6](P.335)虽然回忆以前的热烈与喧闹,一个人的祭山让祭师阿巴倍感凄凉与哀伤。但阿巴终于了悟:“其实,只要有一个人在,世界就没有消失。只要有一个云中村的人在,只要这个人还会想起云中村,那云中村就没有消失。”[11](P.358)阿巴的招魂和祭山仪式因此而具有了双重的意义,它标示了一个过去的、已经消失、永远不可能再次归来的生活,同时也标示了一种通过宗教仪式对族群记忆和族群认同再次确认的可能。
捷克作家克里玛曾经说:“我写作是为了保留对于一种现实的记忆,它似乎无可挽回地跌入一种欺骗性和强迫的遗忘当中。”[13](P.40)对阿来而言,藏地村庄携带着他个人的生命经验和族群的生命经验,从记忆中打捞和重构村庄记忆和族群文化,对他来说,是为了纪念,也是为了延续。当很多当代作家对古老、淳朴的传统文化日趋消失而深感无力时(典型的如贾平凹的《秦腔》),阿来深入到藏文化的内部试图打捞族群历史和文化记忆,寻找族群文化重铸的可能,这种努力在今天的文学写作中显得弥足珍贵。因此,阿来的写作之于藏地乡村书写,具有了某种特别的意义,他是嘉绒藏地正在经历着变化的乡村历史记录者和编年者,同时也是一个持续地对藏地乡村精神重建的探寻者和实践者。
结语
从“机村传说”始,阿来开始讲述20世纪后半期藏地乡村的历史以及不同的个体在时代变化中怀旧、伤感、游离等不同的情感谱系,在思考小历史与大历史、村庄与国家、个人与时代、乡村历史与创伤记忆的关联时,也标示出作家阿来对藏地乡村历史变迁的复杂的情感地图与情感结构。对阿来来说,藏地乡村埋藏着他所有的童年和少年记忆,同时,藏地乡村在阿来那里也已超越了私人的意义,成为一个蕴藏了一代人、几代人、一个村庄、一个族群的历史命运和精神图景的地理空间。但在这种个体与历史、个体与村庄的同构关系中,我们也需要思考那个讲述者的位置,正如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指出的:“在乡村写作中,我们需要看到的不仅仅是乡村社群的现实;还要看到观察者在其中的位置及其态度;这也是那个被探索的社群的一部分。”[4](P.232)那么,在对藏地乡村的书写中,阿来这个讲述者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呢?
吉尔兹在论及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时,认为应该使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人类学家应该使用原材料来创设一种与文化持有者的文化、习俗等相吻合的诠释。“它既不应完全沉溺于文化持有者的心境和理解,把他的文化描写志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是一个真正的巫师写得那样;又不能像请一个对于音色没有任何真切概念的聋子去鉴别音色似的,把一部文化描写志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一个几何学家写的那样。”[14](P.73-74)阿来从故乡到城市,从藏地到汉地,回望自己的故土家园,讲述自己的族群故事时,努力秉持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他既是本族人,也是一个获得了现代视野的外来者,既是一个藏地乡村的体悟者也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在成为一个个人记忆和族群记忆的记录者的同时,又尽力跳出这一位置给予“超在地性”的解释。他带着一种流动的身份和视角进入藏地乡村,努力跳出“自己编织的含义之网”,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讲述个体和族群的生命体验与命运遭际,重构个人和族群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在这个意义上,阿来的写作对当代文学史中的乡村书写是具有某种启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