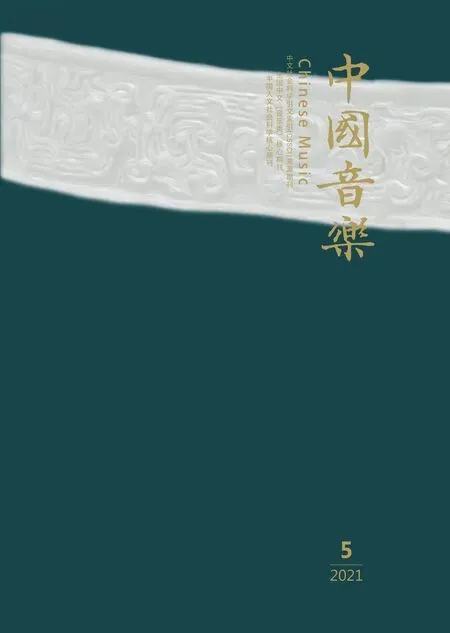忆德海
2021-04-17樊祖荫
○ 樊祖荫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瞬之间,德海兄①刘德海先生出生于1937年,比我大三岁,故称“兄”。但平时我们相互间都直呼其名,习惯了,后文不再加“兄”字。离开我们已整整一周年了。
在我辈之中,德海的身体素质原本是最好的一个:每年到小汤山医院做体格检查,他的各项指标大都正常,而其他人不是这几项高,就是那几项低,当大家夸他时,他总是以微笑应答,不经意间流露出些许得意;平时走路,他都能挺直腰板、脚步轻盈。记得前两年在学校多功能厅举行的那场音乐会,轮到他的节目时,他从观众席快步上前,临到舞台的一霎那,竟大步跳了上去,赢得满场的喝彩声。要知道,其时德海已年届八十了。可谁也没有料到,德海会走得如此之突然。他的离世,使中国和世界失去了一位最优秀的琵琶艺术大师,也让我痛失了一位至亲好友。
我与德海相识已逾半个世纪。1964年,我们分别从中央音乐学院与上海音乐学院来到新创办的中国音乐学院;“文革”时期我们的住所都被安排在恭王府(中国音乐学院的初期校舍)“九十九间半”的西侧楼上,成了邻居。他给我们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勤学苦练,从他房间里传出的琵琶声以及板鼓声,可说是成天不绝于耳。何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此乃是最好的诠释!我曾问过他苦练板鼓的原因,他说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练手腕的功夫,与琵琶相通;二是掌握中国式的节奏,奥妙无穷。
1970年他调到中央乐团任独奏演员,其间,他与作曲家吴祖强、王燕樵等共同创作了享誉全国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后于1984年返校任教。1987年德海出任负责教学的副院长,其时,我还在教务处长的任上,他虽成了我的直接主管,但很少过问日常的教务工作。几次约谈,总想听听我对“如何才能办出真正的中国音乐学院”的意见,他自己说得虽不多,但从话语和表情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对办学现状的忧虑和无奈,并不止一次地流露出不想再做行政工作的念头。果不其然,约莫过了一年时间,他就决然地辞掉了副院长之职;不久,我也因工作调动的原因,离开了学校。
1991年夏,我奉调返校主持学院工作。当时,“六四”政治风波之后不良的社会风气严重地影响到学校,使学校的管理工作遇到了很大的难处。但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件碰到的真正棘手的事,却是德海坚决要求离开学院到他校任教。他说:“这是我几年前就提出了的,不针对任何个人。”为挽留他,学校班子成员曾几次三番集体上门规劝,但收效甚微。见此状,我只好另寻门径,别谋他策。沉思良久,想起不久前他曾告诉过我正在构思创作一套新的琵琶曲的事儿,心想,也许以此为切入点,谈话可以深入进行下去。于是,以后的家访,我就有意绕开调动的话题,主要谈琵琶的创作与教学。为便于交谈和沟通,我还预先准备功课,了解与琵琶相关的各种学术动向。一谈到琵琶,一谈到他的创作,他的兴致就很高,不仅为我演奏了已完成的《天池》以及构想之中的《陀螺》《昭陵六骏》等乐曲的片段,还提到他的整个创作计划以及他新的观念和技法创新的构想。在交谈之中,他虽曾多次征求我的意见,而我因对他的新作构想尚处于了解过程之中,因而除了对个别乐曲的结构布局说点想法之外,大多数时间都只专注于听他讲述,向他请教,且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宗教、哲学的深刻理解和散发着独特智慧的话语中,受到了很多启示和教益。后来,我们的谈话又很自然地从他的创作转到了民族器乐等的教学改革问题,他认为:我们当前的器乐学习面太窄,传统音乐中许多重要的东西没有学。譬如,全国各地有许多不同的乐器组合和独特风格的乐种,那是中国传统器乐的宝库,不少器乐名家都是从乐种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但它们在我国的音乐院校中却没有地位。中国音乐学院不仅应该率先开设乐种课,而且由于这些乐种大多具有室内乐性质,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学习传统乐种,另一方面也可以多搞一些室内乐的创作与教学,将传统与现代衔接起来。前些年,我们就曾搞过弹拨乐器的室内乐教学,“五朵金花”(即由杨靖、李玲玲、林玲、黄桂芳、魏蔚组成的中国弹拨乐五重奏团)就是那时涌现的成果。我对他的想法深表赞同,并深深地被他的敬业精神,以及他为中国音乐事业、为中国音乐学院的教学模式所做出的思考和努力所感动、所钦佩,遂应承他把他的想法纳入将要开展的教学改革之中;同时我又就学校整体改革的思路,特别是各专业加强中国传统音乐学习的设想与他商量,不仅得到他热情的回应,而且还提出了不少积极的建议和意见。在这种和谐的交谈氛围中,他再也没提起过调动之事,这件曾让我整日心神不宁的大事总算平静地过去了。经过好几个月的接触和深入交谈,我们彼此间在增加信任的同时,也加深了友谊,这种友情一直保持始终。他后期的一位博士生葛詠所选的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刘德海琵琶创作研究》,德海点名要我担任开题和论文答辩的评审委员,他找到我说:“你是搞作曲理论的,也是最早知道我写作这批新作品想法的人,了解我的观念和构想。请你来,希望你为她的论文把把关。”虽然到最后德海没能亲自参加葛詠的论文答辩会,但葛詠的论文通过对德海不同时期琵琶创作的个案分析,并对其创作的路径、特点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研究,深入地挖掘了他对传统琵琶曲的继承、发展、创新的创作观念与规律特点,总结了他的作品成为中国当代琵琶创作典范的缘由。论文的材料丰富,观点明确,分析得当,立论有据,很有说服力,博得全体答辩委员的一致好评,其成绩被评定为“优秀”。这是大可告慰于德海的。
2001年,德海再次出任器乐系系主任②刘德海先生于1987年任副院长时曾兼任过器乐系系主任。之后,带领全系师生积极推行他早有思考和谋划的民族器乐教学改革的各种实验,其中,他所提出的旨在建立民族民间音乐教学乐库建设的“1”行动计划(即一年一个民间乐种的采风学习,十年十个乐种),是一个包括从观念到行动、从内容到方法、从理论到实践的教学改革的系统工程。第一年,他就亲自带队远赴广东学习潮州音乐,在民间音乐家们热情细致的指导下,师生们经过几个月不同方式的刻苦学习,积累了独奏、重奏、合奏等不同形式的多种曲目,掌握了岭南文化哺育下的独特技法和艺术风格,回京后举行的汇报音乐会,受到了校内外观众极其热烈的欢迎;随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的“刘德海‘1’行动计划专题研讨会”上,又得到了全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行动计划的实施,可以说是对过去学校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学方式、对前些年学校提倡开设乐种课等教学改革措施的发展和深化;同时,它又扩展了学校的教育功能,让高等音乐学府成为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基地。
所遗憾的是,这个对教学改革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行动,由于种种原因只实施了短短的两年而未能坚持下来。但德海并未因此而气馁,也从未停止过对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自1998年开始,德海受邀参与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民族器乐教学的改革,在中国少年民族乐团,特别是少年弹拨乐团的建设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与附中的老师们一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业过硬、理想坚定的青少年音乐人才。德海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倡导的民族室内乐建设,如今已成为民族器乐领域发展最为蓬勃的艺术形式,成为全国高等音乐院校和艺术院团业务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器乐走向世界的标志性文化事件。一次又一次的教学改革探索,生动地展示出他对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模式和对中国音乐学院办学模式深层次的思考与付诸实践的勇气。时至今日,我院正围绕“双一流”的办学目标,开展着又一轮的教育教学改革,深信这次的改革定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更能突出中国音乐学院的办学使命及其特点,那将是对德海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