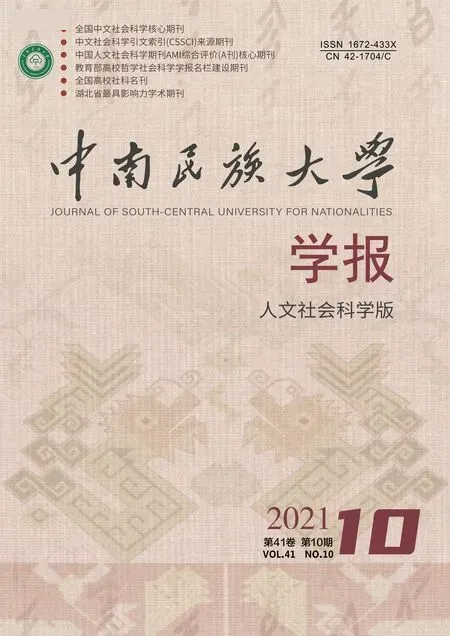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与启示
2021-04-17赵智娜中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4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崔 榕, 赵智娜(.中南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序幕。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下,我国“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1]264。与此同时,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相互撕裂,在反击日本侵略的态度和策略上并没有达成共识。
在寇深祸亟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措施,激发起各民族人民团结御侮的巨大能量,奏响了气壮山河的时代强音,极大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2]1032回顾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程和经验,可为当前全面展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中国各民族、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命运与共,共克时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汇聚了各方爱国力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极力促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道路。1935年,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呼吁:“无论各党派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1]265由此,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方针。此后,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倡议与国民党合作抗日。1936年,党中央明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应当尽早建立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3]435-436。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产生了极大影响。1936年12月,党中央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主张。翌年9月,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促进国共合作的同时,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励、号召我国各族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1937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来参加抗战”;“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 1938年,毛泽东强调:“抗战是全民族的紧急任务,……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5]62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凝聚起各族人民众志成城为中华民族前途命运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2.“中华民族”成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话语。在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使用“中华民族”话语进行社会动员,鼓励各民族团结抗战。这一话语体系使得“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实体性和共同性特征更加凸显,也使得各族人民在家国利益面前,更加清楚自身的身份与责任,从而为各族人民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华民族”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话语。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3]71,不过当时并未对其含义作出明确界定。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国家危机的加重,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成为首要任务。大敌当前,“中华民族”一词成为最能激发各族人民爱国情感和力量的时代话语。
193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6]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含义视为等同。1935年《八一宣言》中提到:“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7]28-29东北数十万武装抗日战士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7]30。其中,中国共产党将“我民族”“中国民族”“中华民族”并用,充分表达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危难之时,极力促进家国一体、各民族一体的明确政治诉求。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抗战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复杂,中国共产党在动员各民族团结抗战时,更为注重“中华民族”话语的使用。1937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华民族”一词高频率出现。例如: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就是“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我们伟大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8]219。可见,此时“中华民族”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使用其来指代我国全体同胞的同义词。
在“中华民族”话语的感召下,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极大唤醒,各族儿女勇敢地选择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捍卫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完整和尊严,“中华民族已经团结得像一个巨人一样,燃起了民族解放的烽火”[9]。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转折点。此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多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肯定了抗战对于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作用,认为“16个月来的抗战,是我中华民族发展中的伟大历史事件,造成了我中华民族空前未有的团结和进步”,证明了“中华民族有抵抗外寇的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7]222。根据抗战总结与抗战形势,文件还提出“全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应当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具体任务”之一应当是要“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7]226。该决议案明确了“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统一指称。自此以后,“中华民族”作为我国各族人民的统称,经常出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讲话以及相关文件、社论当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战叙事的主流话语。
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一词使用的轨迹可见,中国共产党从本土实际出发,正确选择和积极构建中华民族话语,肩负起动员各族人民参与抗战的使命。在建立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阐释与创新,从而使“中华民族”的话语界定日益清晰,内容更加丰富,成为最能打动人心、争取人心,促进各民族团结的动员话语。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了人心和力量,成为各族人民浴血奋战、生死相依的坚固堡垒。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使用“中华民族”的话语来进行社会动员,将各族人民纳入统一国家建构的框架体系中,明确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主体,赋予了每一位中华儿女挽救国家危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引导下,各族人民生死与共,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着国家的尊严,中华民族精神也在抗战烽火中得到了淬炼与升华,中华民族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命运共同体。
二、维护各民族政治权利,建设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有组织、有秩序的实体,必须建立在国家政治制度、政治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之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革命的中心任务,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建构与民主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在各项政策中规定各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坚决贯彻实行民族团结政策,为中华民族成员的生命安全、平等权利、人格尊严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构建了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
1.开展民主政治运动,激发各族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为充分调动各族人民抗战积极性,提高各族人民抗日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广大军民对日寇展开英勇作战的同时,还积极引导根据地的各族群众参与民主政治改革运动。
中国共产党相继出台相关文件政策,切实保障各族人民的政治权利。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规定:“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6]1601937年,陕甘宁特区积极开展民主政治运动,其纲领措施中就包括实行民主普选制度,发扬各种民主措施,保证工农群众已经取得的各种权利,保护人民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民主自由等。1940年,毛泽东提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不分阶级、民族、党派、男女、信仰和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0]751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发动群众抗战与民主政治建设联系在一起,领导开展民主政治活动,调动了各族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1937年下半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便开展了第一次普选活动。针对村民文化程度低,对民主政治不理解的情况,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各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深入开展普选宣传活动,如通过喊口号、发传单、贴标语等方式进行宣传动员。此外,抗日根据地各级政权还不断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切实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
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的基层民主政治运动取得了明显成效,各族人民在政治参与的实践中,政治意识不断加强,社会各界团体抗战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以及统一战线的政权基础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2.落实民族平等政策,保障各民族政治地位。民族平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基石,促进各民族平等是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前提和基本内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多元”,并非界隔分明的独立单元,而是相互依存并具有不断融汇集中的趋向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征,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共同御敌,使得各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在抗战过程中得到了不断加强。
抗战之前,由于边疆与内地之间缺乏交往交流交融的机制与条件,地域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较为缓慢。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实施大汉族主义政策,对少数民族存在一定的偏见,导致“他们历来受着汉族的军阀、官僚、地主、商人、财富佬的残酷压迫与剥削”,从而“促成了他们对于汉族的民族仇恨”,也破坏了“他们内部的团结”[11],民族间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各民族政治诉求存在较大分歧。此外,日本法西斯以建立“满洲国”“开发西北”“准许内蒙古独立”为幌子,大肆宣传欺骗,处心积虑地分裂中国,挑拨离间我国民族关系。
针对上述情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共同团结抗日的实践中,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充分调动各族群众的力量抵御外辱,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中国共产党制定和颁布的民族平等政策,是实现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政治基础,因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关键环节。
1931年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凡是居住苏维埃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劳动者,在汉人占多数的区域,亦须和汉族的劳苦人民一律平等,享有法律上的一切权利义务,而不加以任何限制与民族的歧视。”[12]171中国共产党在具体的民族工作中,也出台了一系列民族平等政策。如1934年明确提出“我们对瑶民(或苗民)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汉族压迫与剥削”,肯定“汉民与瑶民的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13],号召苗瑶同胞追求平等权利。
1937年“卢沟桥事件”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鼓励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参加抗战,制订了一系列民族平等政策。在《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1937年8月12日)、毛泽东《论新阶段》报告(1938年10月12日)、《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年4月4日)、《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1940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1940年7月)等文件或领导讲话中,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平等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政策规定,使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与平等地位有了政治保障,对于唤醒少数民族政治意识和动员各族人民共同抗战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3.坚持实施民族团结政策,促进民族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将坚持民族团结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在根据地建设中结合革命任务,推进民族团结。此后,随着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更需要发动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御侵略、救国图存,以避免亡国灭种的危机和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中,以促进各民族团结、壮大抗日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摸索和总结实践经验,通过实施一系列民族团结政策,来巩固各民族同生共死、甘苦与共的血肉联系,为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建构与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1931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极力号召广大群众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与侵略。1934年,中国共产党发出倡议:“一切抗日的民众,都是我们的同胞,一切抗日的武装,都是我们的同伴,我们都要联合起来。”[6]5201935年,中国共产党呼吁“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苗、瑶、黎、番等)兄弟们”加入抗战队伍。1936年,毛泽东号召“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14]。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文件中明确使用“民族团结”一词虽然并不多见,但也不难看出,“民族团结”的理念已经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具体政策主张当中。
1937年“卢沟桥事件”之后,抗战形势进一步发展,民族团结的现实意义更为凸显,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也更为明确和丰富,“民族团结”一词的使用明显增多。例如1937年,《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提出:“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8]2171938年,毛泽东提出:“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5]621毛泽东的此次讲话,对于鼓舞士气,促进民族团结,坚定各族人民抗战信心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政策发展的新起点。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建设过程中,也坚决贯彻和执行了民族团结政策,在促进改善民族关系、团结抗战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如1940年《晋察冀边区目前的施政纲领》中特别指出:“我们边区境内各民族,保持了亲密的团结,破除了彼此间的隔阂……”[12]672随着抗战进程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思想及相关政策变得愈加明确和深刻,促进民族团结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日宣传活动的重要任务和目的,其重要意义也得到了普遍认同。
总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政策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内容也日益丰富。这些政策的实施,获得了全国各族同胞的衷心拥护,促进了各族同胞亲密团结,并肩作战。血与火的共同经历,又使各族同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觉醒和增强,各族同胞已深刻感受到中华民族同根同源,只有各民族紧密团结,才能战胜日寇、拯救国家。
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建设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
发展民生是保障各族人民生存利益,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团结抗战的主要方式。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群众抗击日寇,不仅要在军事与政治方面展开激烈较量,而且还要进行经济方面的抗衡,加强经济保障能力,建设与巩固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来源于广大基层,“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10]692。要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就必须关心群众民生,“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15]。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也要求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要“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12]597。因此,与老百姓朴实的民生愿望结合起来,促进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坚定各族人民群众长期坚持抗战的信心,就必须不断发展经济,增强物质储备,不断满足各族人民群众的民生需求。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根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民生政策和措施,在极其险恶、困难的情况下,与各族人民同甘共苦,发展生产,为最后战胜日寇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
在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将改善民生作为施政方针和目标。例如,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就已经注意到改善工农群众民生状态的重要性。1934年2月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明确规定了颁布劳动法、土地法,制定度量衡、币制、税率以及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事业的发展规划。
中国共产党还根据抗日形势的需要,围绕农村土地、捐税制度、工商业发展等主要内容,提出了一系列促进民生改善的措施,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获得现实的经济利益,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例如,1935年《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实行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制度,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取消一切军阀地方的捐税等主张。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开始转向民族抗日战争阶段。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深入群众生活,充分了解群众民生需求。为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决定将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其中,改善边区民生状况成为模范区建设的主要目标。如1937年6月20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发布《民主政府施政纲领》,提出了改善边区民生的一系列有力措施。此外,针对回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面临的危机局势,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回、蒙等抗日力量,提出“一定要争取,要努力地争取,多方地争取,不但要争取下层,并且要注意争取上层”[16]。通过制定和实施发展民生的务实政策,帮助改善回、蒙等民族的生活,激发他们的抗战热忱,极大凝聚了人心。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日本侵略者对各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清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面对异常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国共产党除了带领广大军民与日寇英勇作战外,还积极动员各族人民群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开荒种地,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相关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极大提振了边区各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家庭手工业和农村副业等均有了较大发展,改善了边区各族人民的生活。1943年各根据地因日寇封锁、扫荡而造成的生活困难得到了基本克服;1945年在山东开荒面积达34万余亩,基本上消灭了荒地[17]192-193,有纺车50万辆,织机8万张,平均每30人有一辆纺车,每200人有1张织机,纺织业达到自给或半自给状况[17]279。
各族同胞在民生改善过程中,家国共同利益观念和爱国主义情感也得到了激发与培育,为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
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设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各族人民命运与共、生死相依的精神纽带,是各族人民共同执守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文明经久不衰,薪火相传的不竭动力。自抗战爆发开始,为削弱我国军民抵抗意志,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对我国进行军事侵略,而且极力宣扬所谓的“文化亚洲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共存共荣”“日中亲善”等思想,企图弱化、割裂我国各族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为了抵制文化入侵,唤醒与巩固各族人民的文化自觉,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断加强文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
1.大力做好宣传动员工作,鼓励各族干部群众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毛泽东曾多次谈到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建设是战胜日寇的重要法宝,“在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2]847。1938年,毛泽东又提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0]533-534,要求党员干部加强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应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洋八股必须废止……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0]534。1939年,毛泽东再次畅谈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10]622-623字里行间,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华文化的深厚情感,也启迪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热爱。
1940年,毛泽东围绕中华文化建设目标展开了深刻论述,他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此外,朱德也提出,文化宣传工作要面向群众,面向生活,做到大众化和通俗化,要“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18]。张闻天也撰写多篇文章,对中华文化建设的性质、内容、目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极大鼓舞了各族群众的抗战斗志,成为巩固文化统一战线的思想武器。
2.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报刊媒体等媒介向各族群众宣传中华文化。为应对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所造成的中华文化认同危机,让广大军民更加深入地了解、学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报刊媒体向各族群众宣传中华文化,加深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如《解放》曾刊发多篇文章,包括张闻天的《论待人接物问题》、吴黎平的《中国共产党与道德》等,积极倡导各族人民群众学习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此外,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不少报刊也不遗余力地宣扬中华文化认同,凝聚抗战精神。如湖南《力报》在这方面表现突出,该报通过言论、报道、副刊等多种方式来传播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仁人志士事迹和地域文化等,重建和强化各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进而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激发全民抗战精神。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宣传工作,增强了各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危机感和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社会责任感,激发了全国各族同胞团结抗日意识。
3.大力发展基层教育事业,进一步提高各民族群众的文化水平。教育是唤醒各族群众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围绕抗战任务,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政策。例如,1935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1]266的主张。1937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抗日的教育政策”,号召废除旧制度和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40年3月中国共产党发布《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明确指出开展国民教育是抗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实行义务教育,展开“扫盲”运动,发展民众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素质。
总之,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发起文化教育运动,不仅促进了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目标,实现了中华文化的重塑和革新。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各族人民坚持抗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及各族人民抵御外侮的不屈精神,依靠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优异之价值”和“力量”[19]。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发起的文化教育运动,唤醒了各族群众的革命意识,激发了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为中华民族抗战的彻底胜利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建构,奠定了共同的文化基础。
结语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历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不断增强和巩固,为全体中华儿女坚韧不拔、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场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抗战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时期,抗日战争的胜利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功实践,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第一,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最积极、最有力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自觉承担起建立并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重任,通过创新中华民族话语、倡导民族平等团结、改善民生、发展教育等途径,唤醒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增强了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性,凝聚了人心,开创了各民族紧密团结、共御外侮的新局面。第二,各族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要依靠。各族人民群众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主体,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创造者和建设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山河破碎、家国沦陷的惨痛和苦难,但这一份苦难深重也正为彻底唤醒中华民族精神,推动各族人民投身于抗战的洪流拉开了历史的序幕。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意识到,这场战争是中华民族进一步由“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转折点。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群众,发动群众,激励群众,“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8]219。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因而也赢得了群众的衷心拥护,各民族人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各民族群众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56个民族血流在了一起,情融在了一起,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在血与火的淬炼中不断牢固和强大。第三,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政策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保障。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教育、民生等方面政策,规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内容、手段和途径等。中国共产党在实施这些政策过程中,始终不忘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各族群众命运前途相结合,因而这些政策有效调动了各族人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凝聚了各族人民的力量和智慧,为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总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功实践,对于新时代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