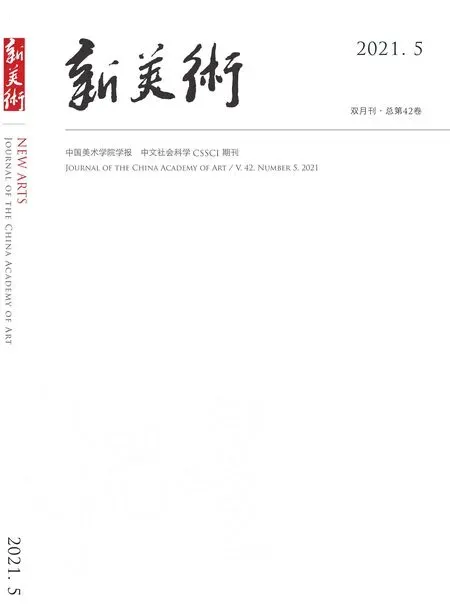画史之外 十五世纪的画坛常态及其转折
2021-04-16庄明
庄 明
熟悉中国古代画史的人自然知道,沈周是一位多么伟大的画家。他被视为上承董巨元四家、下启吴门画派,开有明一代画坛新貌的大师。16世纪的苏州人王稺登称这位同乡“当代第一”,1[明]王稺登,《国朝吴郡丹青志》,“神品志”第一人“沈周先生”,载《中国古代书画全书》第三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第918 页。董其昌将他选为本朝能“遥接(南宗)衣钵”的人,2[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画源》,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61 页。此后人们对此坚定不移。我们的画史正建立在这种知识之上,罕少受到怀疑。
怀疑?怀疑什么?怀疑沈周的伟大,还是董其昌的眼光,又或者怀疑眼前的杰作如何配得上历史中的名声?还是,怀疑这种伟大到底是基于绝对的价值、抑或仅仅是一种个人偏好?我们不太担心附庸风雅者的疑问,他们总是试图以所见匹配所知,并把知识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实加以自我催眠。我们害怕的是那些一无所知者,或者认为审美纯粹是主观之事的人,以及那些对历史与经典这种人造物心存警惕和疑虑的同行,他们一个简单的发问就能触动艺术史的地基:如何证明一位画家的伟大?贡布里希身兼艺术家与批评家的朋友昆廷·贝尔[Quentin Bell]就曾问他:你说米开朗琪罗很伟大,但我不喜欢他,我不认为他的作品一定比其他画家更有价值。贡布里希回答说:我对他的敬畏与我的“喜欢”并没多少联系。3E.H.贡布里希,〈视觉艺术的准则和价值:与昆廷·贝尔的通信〉,载《理想与偶像:价值在历史和艺术史的地位》,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178―192 页。他的意思是,艺术史需要大师,而艺术史家必须说明一位大师为什么伟大。对艺术史家而言,大师的重要性毋庸讳言,因为他们总是需要用伟大的画家为锚,再牵连起锚与锚之间的锁链,以形成画史的叙事。但阐释这种重要性绝非易事,以何人为锚,如何缀珠成线,从来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何况近些年这种重要性本身也在遭受普遍的怀疑。贡布里希深谙艺术与历史间的种种奥义,他自然拥有绝对的自信。但对于中国美术史而言,自15世纪逐渐成形的传统画史像一座危楼,如今又被各种理论装点一新。它曾深刻地影响了17世纪之后的画史观念,却让我们在理解此前的画史时,难免陷入时代错乱;它选择了一批画家作为规范,却未能提供足够的事实予以支撑,让画史从历史变成了话语。此外,文献与图像中还游离着大量复杂的事实,无法被纳入画史的叙事中。于16世纪初编就的绘画鉴藏工具书《图绘宝鉴续编》就是一例,在这本书中,画史大师沈周不过是百余位当代画家中的一员,谈不上多么伟大,至少不像后来的画史中声称的那样重要。那么当时画坛的实际情况如何?沈周因何具有其画史地位?这些问题的尚且模糊,也许正说明:艺术史的许多基本问题仍须检验,历史要比画史复杂得多。
一 意外
对于16世纪的北京人韩昂来说,沈周算不上什么伟大的画家。他在正德十四年(1519,距离沈周下世仅十年)续编《图绘宝鉴》时写道:
沈周,字启南,号石田,姑苏人。博学有奇思,为诗清新,皆不经人道语。字亦古拙。学黄大痴,法其善处,略其不善处,遂自名家。因求画者众,一手不能尽答,令子弟摸写以塞之,是以真笔少焉。4[明]韩昂,《图绘宝鉴续编》之“沈周”,载《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第837―838 页。
编者韩昂用冷漠的笔调将沈周描绘为一位能诗、博学、善书的苏州人,扬长避短地学习了黄公望的画风,自成一家,颇受欢迎。因求画者过多而令弟子作摹本,俨然与一般画家无别。这与我们熟知的画史大相径庭。韩昂言语中隐含着轻视与批评,他是否了解沈周?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对苏州画家所在地的陌生程度、以及对画风师法概念性的理解来看,沈周对他而言不会与东吴地区的其他画家有太大分别,这可能与他远在北京有关。他之所以要提到“子弟摹写”“真笔少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本书作为鉴藏工具书的性质,并且后一句并非空穴来风。弘治二年(1489)吴宽就抱怨京城沈周伪作颇多,5[明]吴宽,《家藏集》卷十七〈题石田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126 页。而纵容伪作的行为将有损声誉,祝允明曾忧虑地劝沈周停止这种行为。6[明]祝允明,《祝枝山文集》之〈沈石田先生杂言〉,《祝枝山诗文集》,王心湛校,广益书局,1963年,第51 页。
正德十四年(1519)韩昂受吴麟之托,7吴麟受锦衣卫苗增所托,因进士考试之故,转托韩昂。见《图绘宝鉴续编》韩昂自序。续编元人夏文彦编撰的《图绘宝鉴》,他增补了从洪武到正德年间(横跨了整个15世纪)的百余位画家,名《图绘宝鉴续编》(以下简称《续编》)。尽管历代对夏文彦的《图绘宝鉴》不乏批评,8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图绘宝鉴》前后错乱,遗失殊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图绘宝鉴》每代所列,不以先后为次,每每倒置,体例亦未尽善。”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图绘宝鉴》)最疏失者,即仅分朝代,而不按画人时代,重其编次。盖先就一书载,依次抄录,然后更及他书。其原书体例如何,绝不顾虑。”(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但元人与明前中期的人对夏文彦之书持肯定态度,比如陶宗仪称其“搜潜剔秘,网罗无遗”。可见,不同时期人的知识资源并不对等,明中期之前人的画史知识是比较匮乏的。但这不妨碍它成为明代鉴藏家与书画爱好者必备的工具书,它汇总元以前画家源流,全面而简明,为快速把握前代画家的信息提供了极大便利,明人了解绘画知识多会翻查此书。譬如杜琼在《题大痴画卷》中所提及的黄公望生平就基于《图绘宝鉴》的内容增补;9参见石守谦,《从风格到画意:反思中国美术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42 页。晚明藏家冯梦祯鉴藏时的参考书,仍是《图绘宝鉴》。10[明]冯梦祯,《快雪堂日记》“万历二十五年十月五日”条,凤凰出版社,2010年。而据这本《续编》编撰的发起人锦衣卫苗增说,正是因为平日用于查证藏品真伪的《图绘宝鉴》旧本太过模糊,才令吴麟重刻,新增当代名士,以资鉴藏。11《图绘宝鉴续编》之“序文”,第835 页。因此,《续编》继承了《图绘宝鉴》全面简明的优点,是对那些活跃在15世纪画坛中的当代画家记录最全面的一本书。尽管如韩昂所说,只略及姓名出处,对画家的所在地亦多模糊,12《续编》中常出现东吴人、江东、浙人、江浙人等概称。对画家所擅题材也未必全面,对风格更不太关心,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我们管窥15世纪明代画坛——这个在画史中只剩下几个名字、似乎在为某个“巅峰时代”做准备的一百年——的绝佳样本。
二 统计学的观察
《续编》共记录了153 位书画家,除去三位帝王与三位纯书法家,13帝王即宣德帝、成化帝、弘治帝,书法家即吴宽、祝允明、王宠。共计画家146 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社会身份、擅长不同的题材。我将以统计学的方式做一些观察。
先从地域上来看,这是最显著的差别。除去未记录地域的24 人,若以南北划分,则16 人来自北方,占13%;103 人来自南方,占85%;3 人来自西南(包括寓居1 人),占2%。这与我们惯常认为的南方在文化与经济上远胜北方相符。其中,北方的16 人较平均地分布在北直隶、山东、河南三大省,地区间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南方,南直隶有58 人(包括苏松常镇四府42 人、应天7 人),浙江25 人,福建7 人,湖广6人,广东3 人,江西3 人,广西1 人,吴中人占全部画家的34%,浙江人占20%,浙派风格画家聚集的闽、浙地区加起来占22%,吴、浙、闽三地加起来占61%,培养了全国超过半数的画家,仅东南一隅就占三分之一。14韩昂对画家所在地的记载常常混用行政区名称、古称与俗称,如东吴、姑苏、长洲、吴。统计中所有的“东吴”计入“苏松常镇”中。可知画坛中画家确实多来自吴与闽浙地区,地域因素对绘画人才的培养有很大影响。
那么,这146 位画家的身份又是如何?韩昂记录了其中72 人的身份,包括宗室、宫廷画家、官员、文人与僧人。在146 人中,11 人是宫廷画师,29 人是官员,5 人是宗室成员,2 人是世袭职官(钦天监),5 位僧人,1 名太监,19 人是文人(即有教养而无官职者,包括3 名举人、2 名生员这种中途放弃举业的人)15我以诗文写作和书法能力作为判断文人与否的依据。我将文徵明也纳入此类,他因荐任职翰林待诏两年而归,实在算不上正式的官员。此外这个数字比实际要小,比如韩昂就没有提到陈淳能诗善书。。而在29 位官员中,10 位曾任中书舍人(一般为有教养的善书者)16指翰林院中书舍人。关于明初中书舍人的研究,参见Hou-mei Sung Ishida,“Early Ming Paintings in Nank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Wu school.”Ars Orientalis,vol.17,1987,pp.73―115。明初翰林院中书舍人通常由翰林学士举荐,是他们的助手,无须举人,不必经过礼部,从七品,工作内容为抄录公文,对书法有要求。王绂、金钝、夏昶、卓迪、张子俊、陈宗渊等都曾任此职。,3 位是翰林官员。据此可估算出,宫廷画师占8%;文人占13%;官员与宗室占23%;僧人、太监与世袭官职占5%;其他画家占51%。这组数据不算严谨,但很能说明问题,它提示我们:
第一,画坛中的画家至少有一半以上既非有教养者,也非宫廷画师,他们虽以绘画为业(即我们说的“职业画家”),数量众多,却为画史隐没,他们是画坛的主体。但对画家个体的研究无法关照到他们,他们需要被作为群体看待;
第二,有相当数量的官员业余从事绘画,他们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业余画家17这里的“业余画家”的“业”,指的是官职,据此区别于无主业而有绘画活动的人,主要包括元代特殊的政治环境造就的一群无官职的擅画文人(他们中大部分其实都力求走上仕途),以及坐拥大量田产的乡绅地主。,其数量甚至超过了宫廷画师;18当我们阅读翰林官员的文集时,这一点是非常清晰的。
第三,参与绘画实践的有教养者并不在少数,其数目可与宫廷画家分庭抗礼,但这些人中只有极小一部分是处士,大部分则走上了职业画家的道路。19职业画家有:金文鼎、杜堇、陶成、史忠、唐寅、周臣、朱铨、杜君泽、高松、张路、张誉、张鹏。我不能确定的有:雷鲤、刘传、王人佐、王谦。处士有:沈周、米应祥、文徵明。这个名单可以佐证我在第五节得出的结论。
在包括《续编》在内的16世纪以前的大多数绘画类书籍中,风格不是关注的要点,著者对于画家的描述并不通过风格、而是通过画题(或称画科)。这种陈规在暗示我们,藏家对风格的认识很有限且并不关心,而普通画家对风格的选择或许也没有现代人想象中的自由度。时至今日,美术学院的中国画专业仍延续着这种传统的分科方式,即人、山、花。技法是设色还是水墨、风格是马夏还是元四家,都在考量的次要位置。我们先看一看不同画科中画家的人员比例,排除韩昂未记录与只擅长书法的人后共计126 人,其中山水类61人,人物类45 人(其中2 人擅长写照,8 人擅长释道人物),花果翎毛类25 人,花果类28 人(其中有9 人画梅花,6 人画葡萄,2 人画菊花),松竹石类31 人(其中13 人只画竹石,1 人只画松),画马2 人,专科画家2 人(一位以漆绘屏风,一位专画鬼判官)。
直观看来,山水画占据了绝对优势,但事实并非如此。明中期的山水画不同于我们今天的理解,它常常与人物画结合,称“人物山水”,实际只是人物画的背景。从事“人物山水”的画家有32 人,超过了山水科的一半,他们大多使用马夏风格,这是当时画坛的主流。20当时画坛主流是马夏风格,比如金文鼎在《胜国十二名家》后写道:“今好事者所收册页,皆绢本,即马夏刘李之辈。”([明]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二十,《中国古代书画全书》第五册,第1180―1181 页)祝允明在《祝子罪知录》卷八写道:“又如言学,则指程朱为道统;语诗,则奉杜甫为宗师;谈书,则曰苏、黄;评画,就云马、夏。凡厥数端,有如天定神授,毕生毕世,不可转移。”([明]祝允明,《祝允明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84 页)徐有贞对谢缙的评价是:“笔迹兼师董李间,不独区区论马夏。”([明]徐有贞,《武功集》卷五〈题蔡孟颐所藏谢廷循山水图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八四,第202 页。)均可为证。此外,还有一部分山水画指的仅仅是云山画,这类绘画没有复杂的构图,韩昂特别指出3 人画的是“云山”,但结合出土文物与翰林官员的文集,这个数字必然被低估了。21关于王镇墓出土绘画与翰林官员绘画活动的讨论,详见第三节。因此,使用“元四家”风格的山水画的数量只可能占非常微小的比例。22第三节对翰林官员绘画活动的讨论将佐证这一判断。在花鸟一科中,区分为花果翎毛和单画花果,其人数基本相当。区分的原因是,花果翎毛是传统画科,而单擅花果中包含更多业余画家,不宜合并。人物画中又细分出两个专科:写照与释道神像,人数相对少很多,这说明这两个画种不同于一般人物画,需要特殊训练。23写照画家大部分属于工匠,少数技术超群的会跃升为画家。在特定画科中存在身份的重叠,如写照和释道人物是职业画家与工匠重叠的领域,云山是业余画家与职业画家重叠的领域。这些现象值得更多讨论。写照在明代十分流行,文人每逢升迁、雅集、生日都喜欢让画家为自己画像留念,与今天的拍照留影异曲同工。意外而不必惊讶的是,三科之外绘制松竹石的画家数量是如此之多,几乎可以挑战任何一个单独的画科,更重要的是,这31 人中,有14 人只擅长此类题材。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兼擅”的问题,画家不是仅仅能从事一种题材的创作。在这126 人中,58 人能至少兼善两种画题,占46%。其中,44 人只兼擅两种画题,其中兼擅山水、人物的有32 人,兼擅人物、花果翎毛的有10 人,兼擅山水、花果的有12 人;24兼擅两种画题的数字只会更大,因为韩昂本人不了解苏州画家,比如他就没有记录下沈周兼擅山水与花果翎毛,而陈淳也能绘制山水。14 人能掌握三种画题,而同时兼擅人、山、花三科的有10 人。这10 人是:戴进、杜堇、吕纪、王问、李著、沈硕、朱铨、朱端、汪肇、张誉。25能兼擅人、山、花三科的画家人数也可能更大,比如陶成存世的《云中送别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说明,除了韩昂记录的山水、勾勒竹、兔、鹿外,他也可以画人物。这个名单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当时画坛上的明星,亦在画史中赫赫留名。专科画家会不会与其他画家配合完成作品不得而知,似乎大部分画家都是独立工作(区别于工匠以团队形式工作)。但画家有时会与文人相互配合,可见的两例是王绂为边景昭《竹鹤双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添画竹石,倪瓒为王绎的《杨竹西小像》补画松石。26还有两个佐证的例子,其一是倪瓒曾为写照画家王绎所绘的《杨竹西小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补松石;其二是杨士奇《东里集》中有“邑萧生为余写小像,因求朱中书添竹数杆,以示不忘东皋之意”。([明]杨士奇,《东里集·续集》卷六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七八,第545 页。)可知擅画文人为画家补画松竹石(这恰是业余画家所擅画题)是一种惯例。请注意,王绂与倪瓒应该都是以文人身份参与这场合作,这说明了题材和身份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其原因我们稍后再论。更常见的情况是文人以书法、诗歌等本行与画家相配,如杜堇与金琮合作的《古贤诗意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代中期后流行的诗意图册基本都属此类。27其形式通常是诗画对页,相互参照,是吴门绘画的流行样式,如陆治《唐宋诗意图册》(苏州博物馆藏)。
基于以上统计,我们可尝试做出一些判断:
第一,明中期画坛,擅长人物画一科的画家在人数上占据优势;28宋后楣指出,明代宫廷人物画家地位尤其高,明代能够画人物的画家与非人物画家获得三品(锦衣卫指挥)的比率是7:3,擅长人物的画家地位尤其突出,如商喜、刘俊、周全、林良、吕纪、朱端、吕文英皆三品官。见宋后楣,〈明代宫廷画家与浙派〉,载《明代浙派绘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11 页。
第二,花果是最受欢迎的题材;
第三,山水画十分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具有最佳的兼容性;
第四,花卉与松竹石这样的小画科在画坛中实则占据半壁江山,这大概来自它们的实用性;
第五,画家通常需要兼擅两种画科,这能帮助他们适应受画人的不同需要,而能够同时掌握三种画科,是一个画家成功的重要因素。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这些画家中有16 人来自绘画世家。多为父子相传,也有兄弟相传,有的能传及三代。以家族形式传承技艺在古代社会非常普遍,除了工匠(匠籍)世袭并常以家族为单位联合工作外,经术、书法等也常会通过家族相传,一些技术型官职同样必须世袭(比如军户武职、钦天监与医官),这既能保证家族在某个领域中的优势,也能保证某个行业中技术的稳定。可见艺术与学术虽轻视工匠,但都有作为技术(手艺)的一面。
最后,我们将上述三种考量因素——地域、身份、画题——结合起来,看看能不能发现更有意思的现象:
第一,6 位画葡萄的画家中有4 位是僧人;
第二,画松竹石的画家只有2 位北方人,在单画松竹的13 位画家中,有5 位中书舍人,4 位东吴人;
第三,在兼善两种以上画题的画家中,只有2 位官员、7位文人,也就是说基本都是职业画家。
第四,与画家的身份对应的不是风格,而是画题。29此处给出两个佐证:其一,王绂、卓迪、张子俊同为业余画家中书舍人,王绂使用的是苏州地区的元四家风格,卓迪是闽浙风格,张子俊作画媒介为绢。([明]杨士奇,《东里集·诗集》卷三〈以绢问张子俊求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七七,第363 页。)可推测为宋人一路,三人风格各异,但均擅山水,兼作松竹。其二,沈周的学生中包含职业画家与文人,王纶、孙艾学花果(二人均能写像),而文徵明学的则是山水。业余画家会与职业画家共享一些简单的画题,如松竹石和云山,但大体不会涉足职业画家的题材,这是不能、不为,还是兼而有之?
利用统计学的方法,我们捕获了一些“意外”现象,它们有的佐证了我们的既有认识,有的则不能像拼图那样嵌入画史的叙事之中,抵牾之处即为问题所在,是谁的问题?但现在,定量研究要就此打住,我们都知道统计学带来了错误一点不比正确少,但我认为这不失为有益的尝试。并且,如果能将发现的现象与历史材料相互参证,或许将有助于我们恢复当时画坛的常态,借以修正我们对画史的认识。
三 十五世纪的明代画坛
面对历史,留下名字已是一种成功。《续编》中的这些画家,尽管在画史上难称大师,却是自己时代的佼佼者。巨星背后,群星闪烁。可以想见在他们身后,还有更多试图成为他们的人,是他们共同构成了画坛。
正如上文所见,15世纪的明代,不同社会身份的人——贵族、官员、宫廷画家、文人、职业画家、庶民、僧人、道士……(工匠被排除在外)虽然社会等级不同,但都画画,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画家”。本文中的“画家”即泛指所有绘画实践的参与者,本应在开篇指明,但在此指出更利于明晰这种身份的复杂与兼容。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不会选择将绘画作为职业,因为他们已有本职,多为官员或宗室贵族,可称为“业余画家”;另一些人则以画为业,成为了“职业画家”,这其中包括有教养的人。30这两个概念在本文中的定义与学界通常使用方式不同,一般而言,“业余画家”几乎可等同于“文人画家”,而“职业画家”等同于“画师”,这组对立关系的建立源自16世纪之后画坛针对风格与流派问题的一系列讨论。但当我们考察具体历史情境时,难免感到这个两个概念实际包罗了相当复杂的群体。本文对“业余画家”概念的界定参见注17,即强调“业余”相对着“本业”。而由于明代存在大量的文人无法从事本业而被迫从事副业,才产生了“文人―画家”这一特殊现象,详论见第五节。几个需要说明的社会基本事实是:一、明代是身份等级社会;二、社会身份与服饰、行为、职业、礼仪等紧密挂钩,可一目了然;三、尽管明代社会的职业流动性较前代明显提高,但多属横向流动,而非纵向社会等级的升降。31何炳棣区分了两种社会流动方向,即纵向流动与横向流动。前者是社会地位的上下流动,后者是在大体平等的职业间的流动。何氏认为在明清社会中,科举仍是唯一的社会上升通道,财富本身不是权力,而必须转化为官员身份。(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但是,何氏忽略了绘画相较于其他职业的特殊性,从工匠画到职业画家乃至宫廷画家,存在明显的社会地位的提升,明代宫廷画院的建立给予以画为业者一定程度上改变社会地位的途径,但不可无视宫廷画家与士大夫之间仍存在显著的地位差距。一言以蔽之,以画为余还是以画为业,是画坛中这些身份各异的画家间最本质的区别,二者对应着不同的行为模式与画题惯例,不易混淆且互相区别。
那些试图以画为业的人,大部分来自经济文化发达的南方地区,尤以苏州周边、两浙和福建居多。对绘画技术的学习一部分来自家族传统,一部分则受益于地方文化。选择以画为业的原因,很可能是出于家庭贫穷、无产或破产,必须另谋出路,比如金氏兄弟32[明]沈周,《沈周集·石田先生文钞》(中册)之〈长洲金恺母蒲孺人墓志铭〉记载:金恺与金潮兄弟之所以以画为业是因为其父早堕,不能事所产,第1111―1112 页。、郭纯33郭纯,字文通,永嘉人。[明]黄淮,《介庵集》卷九“阁门使郭公墓志铭”:“产业薄,不足以致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7 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50 页。与沈周的学生陆萱34陆萱,字允晖,常熟人。陆萱家贫,妻子去世后无钱娶妻,无后,亦无地葬亲。跟随沈周学画。见《沈周集·石田先生文钞》(中册)〈陆允晖墓志铭〉,第1100―1101 页。;另一些人则是意图寻找举业以外出人头地的方法,如范暹35范暹,字启东,吴人。昔为儒生,受姚广孝荐入画院,供奉三十余年。、谢缙36谢缙,字孔昭,吴人。读书习儒,能诗,早年曾多蒙乡贤提举,后寓居南京求仕未成,又曾往来北京,很可能以卖画谋生,晚年回到苏州。谢缙在南京其间,与苏州籍的官员往来很多。见[明]谢缙,《兰庭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八三。、沈遇37沈遇,字公济,吴人。习儒业,为画工世家。早年曾在南京宫廷中发展,得到过太子的赏识,后因为健康原因返回苏州。见[明]杜琼,《沈公济先生行实》,载[明]钱榖辑,《吴郡文粹续集》卷三十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三二五,第269―270 页。、杜堇38杜堇,又名陆堇,字臞男,丹徒人。能诗,成化中举,进士不第,遂绝志进取,以画为业。见[明]朱谋垔,《画史会要》卷五,《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第566 页。、张路39张路,幼年读书,能诗,通过了乡试,进入了县学,又做了太学生。但后来放弃举业,以绘画游公卿。见《画史会要》卷四,第569―570 页。、徐霖40徐霖,字子仁,吴人,曾补弟子员,客居南京。曾受司马垔赏识用事,因性格不羁在人忌,受诬被黜削籍。后以绘画、篆书、乐府游公卿。见[明]过庭训纂集,《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十三“徐霖”,《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五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97 页。、陶成41陶成,字懋学,宝应人。曾以经术取南几乡贡。善画,言王公求之不可得。见[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十五〈北观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九一,第439―440 页。、郭诩42郭诩,字仁弘,曾为博士弟子员,后中辍举业,以画为生,曾被徵入画院。见《画史会要》卷四,第560 页。等,沈周离家远游的堂弟沈橒也属此类43沈橒,字才叔,后改名观大,沈周伯父沈贞第三子。沈周有《怀橒弟远游忘归》,沈橒的“远游”应该是选择做职业画家谋生。见《沈周集》(中册),第831 页。。绘画是明代社会中除科举之外为数不多可供攀爬的上升阶梯,职业画家的最高成就是供职宫廷,能享受不错的俸禄、品阶和名望,其中佼佼者如谢环,甚至能一步登天,与翰林学士为伍,与皇帝交流艺术,44[明]杨士奇,《东里集》卷四“翰墨林记”:“宣宗皇帝妙绘事,天机神发,不假于学,供奉之臣,特奖掖庭循,万幾之暇,恒侍左右,间承顾问,率以直对,上嘉其诚,屡书御制诗赐之,及金币衣服之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七七,第421 页。不可不谓具有现实的吸引力。但供职宫廷常需倚赖朝中相关官员的举荐45参见赵晶,《明代画院研究》第二章第五节第一小节,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前期由翰林大学士负责,后期则由内务部宦官负责46参见Hou-mei Sung.“From the Min-che Tradition to Che School”,此文指出,推举画家权力从大学士转向宦官是在宣德年间,谢环是受大学士举荐的画家的代表,而戴进是受宦官举荐的代表。),因此要求画家能结交同乡的翰林官员。明代前期翰林院由江西、浙江籍官员把控,浙江籍画家因此受益不少,如浙江画家陈宗渊、谢环、陈叔起俱由浙江籍大学士黄淮举荐。47同注46。与此相比苏州画家则劣势很多,唯天顺年间徐有贞得势一时却不过昙花一现,48徐有贞《武功集》中有不少题画诗,相当一部分就是为苏州籍画家所题,如金文鼎、谢缙、王绂、倪瓒、徐贲。徐有贞在天顺元年(1457)夺门成功前久不受重用,夺门成功后一年(1458)即谪金趾。在弘治之前,尚未出现一位苏州籍的翰林高官,苏州籍画家如谢缙、沈遇,难免前途暗淡。49据笔者目力所见,苏州画家仅范暹由苏州籍官员姚广孝推荐入画院。王绂、夏昶均以书法而非绘画任职中书舍人,而王绂受到了江西人胡广的照顾。成、弘间杜堇在北京的活动多依靠吴宽。无法成为宫廷画家的职业画家大多湮没无闻,成为画史中面目模糊的大多数。
前文我们在依照画家所属地域统计数据时,忽略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流寓。韩昂记录的是画家的籍贯,但出身南方居多的职业画家为了寻找合适的赞助人,通常会在成年后离家远游北上(或称“游江湖”50如[明]王鏊编,《姑苏志》卷五十六“张观”条:“少游江湖,志尚古雅,工画山水。”又如金恺“懋迁江湖”。当然游江湖不仅仅是画家的行为,古董商、中间人常常也会出游江湖,比如赵中美、汪廷器等。此外,这种行为和道士丹客也多类似,而职业画家中,不少人以“道人”自号,并题于画上,此中关系有待阐发。),寓居他乡,汇聚于官员贵胄云集的地区(尤以两京为多),行走于公卿大夫门下。譬如宫廷画家会寓居北京,吴伟、史忠等在南京活动,戴进、杜堇都有北上京师谋求发展的经历。两京地区才是职业画家真正的活动场所,而晚年他们又会回归家乡。画家的地域性及其在地域间的流动,相应地形成风格的地域性特征与地域间的相互影响及竞争。譬如戴进在家乡杭州与寓居地北京引领起对马夏风格的推崇,而吴伟则在南京形成一种迅疾挥洒、水墨淋漓、具有表演性的风格,颇受此地画家青睐。这两种风格都对苏州地区的绘画产生了影响。
在这些职业画家中,有一部分人因早年受过教育、或中途放弃举业而具有文化教养,从而更易与士大夫为伍,跻身官僚贵胄之间,以便获得声望。他们往往会特别看重生前身后的形象,希望让自己更“像”文人,从而隐藏实际的职业身份,并经由文人为他们撰写的小传或墓志,成为一种“事实”。这类文章的惯例是强调他们喜爱读书且富有才情,而将那些属于职业画家的行为,小心地遮掩在诸如此类的文辞之下:如沈遇在南京时“遨游公卿间”51《吴郡文粹续集》卷二“杜琼 西庄雅集图记”,第47―49 页。“矩卿硕儒往候之”52《吴郡文粹续集》卷三十九“杜琼 沈公济先生行实”,第269―270 页。;徐霖在南京则是“王公大人迎致宾礼”53见注39。此外确有徐霖与公卿交往的记录,如与魏国公徐天赐。“城南富豪往来供用”54[明]王兆云,《白醉琐言》卷下“金琮字学”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8 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231 页。;陶成是“王侯争延之”55同注41。;谢缙“往佐藩垣定见之”56[明]徐有贞,《武功集》卷五〈题谢庭循画送周颂〉,第214―215。,等等。将此与写照画家蒋廷恩“十五便向皇都游,往往放笔图公侯”57[明]沈周,《沈周集》(上册)〈赠画生蒋廷恩〉,第238 页。、职业画家金恺“恺懋迁江湖,博古多识,获襄王知重”58同注32。相比,再参照上文对“流寓”问题的讨论即可知,挟技游于公卿门下完全是职业画家的所作所为,类似于方技、幕宾或门客,真正的文人是不屑为此的。这在当时应是一种人尽皆知的修辞惯例,文献有时以委曲的方式反映真实,但倘若读者不察,常常会造成误读和错认。59比如杜琼为沈遇撰写的《沈公济先生行实》、吴宽的《跋沈氏写山楼诗文后》就会强调沈遇的文人特征;谢缙也通常被视为文人画家;程敏政称陶成是贡士,学之余作画,高居翰根据风格判断陶成是文人业余画家(见高居翰,〈中国绘画史三题〉,载《风格与观念: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文集》,中国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38 页),等等。但反过来说,这也是那些沦为职业画家的下层文人努力留下的一个不希望被拆穿的背影。但是文化教养对绘画本身是否会产生直接影响,目前我没有证据说明。
对职业画家来说,受画人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在明代社会,图像与其象征的意义、适用的场合间的关系清晰而稳定,职业画家需要的是掌握并熟练使用、甚至尽可能多地兼擅业已成熟的绘画资源,而非创造。一位职业画家至少需要熟练一种画科,通常是写照、山水人物或者花果翎毛,它们足够满足大多数用途,诸如祝寿、升迁、致仕、送别、营宅,等等。能否兼擅两种甚至三种,则决定了一位职业画家能否成功。60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画史载杜堇“山水、人物、草木、鸟兽无不精妙”,他亦擅长人物画,曾为李东阳、王鏊写照,亦能画楼阁台宇。陶成据说能画山水走兽,在他的《云中送别图》中,我们发现他也会画人物。谢环的《杏园雅集图》展示了他绘制人物、禽鸟、花木的能力,画中的一块小屏上还有一幅云山。“雅集图”正是职业画家综合能力的体现。一些复用性极强、且技术难度较低的画题,诸如松、竹、梅、花果、云山,画家大多可以信手拈来,它们被普遍作为文官间的应酬礼物,但业余画家通常只擅长这些题材。还有一些有教养的职业画家会掌握特殊的书写技能——篆书,这种书体被广泛用于为藏家题写引首。61《续编》中画家若擅长篆书会特别注明,这说明篆书实际上是职业画家的一种特殊技能。如陶成就“工篆行草”,徐霖以篆书傲世,南京地区的藏家喜欢邀请他写引首(如王绂《湖山书屋图》《俞紫芝临十七帖》等)。沈周的学生王纶也擅长篆书,弘治十三年(1300)山东孔庙火灾后的重修工作,王纶就北上去题写新碑(《沈周集》(中册)〈送王理之赴孔林书新庙碑〉,第953 页)。因此,大多数时候根据画家擅长的画科与画题,再结合特定的行为特征,如流寓、出游江湖、与公卿富豪往来,或者迅疾挥洒、富于表演性的作画方式与放纵不羁的个性62这一点本文没有论及,对于这种作画方式和行为特征讨论见:高居翰,〈唐寅与文徵明作为艺术家的类型再探〉,载《风格与观念: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文集》);石守谦,〈神幻变化:由福建画家陈子和看明代道教水墨之发展〉,载《美术史研究集刊》第二期,1995年。,就足够判断一位画家是否是职业画家。
明代能画的士大夫数量不可小觑,他们是业余画家的主体,通常是低级文官,尤以中书舍人居多63永乐年间中书舍人善画问题,已被学者提 及, 如Hou-mei Song.“Early Ming Paintings in Nank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Wu school”,专门论及中书舍人的问题。赵晶在《明代画院研究》中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二人共同认为,中书舍人授予的是善书者,而非善画。至于中书舍人为何普遍善画的问题目前未见讨论。。永乐之后,收藏绘画、以至染翰戏墨逐渐在文官间形成风尚。文官之间历来有一种惯例,送别时要赠予礼物,但此时诗歌已了无新意,绘画配上题诗则成为备受欢迎的佳制。如徐有贞所言:“送人之行而赋之诗,古有之矣,今则加盛焉;送人之行而绘之图,古所罕也,今则常常有之。”64[明]徐有贞,《武功集》卷四〈潞河别图诗序〉,第141 页。但这些官员中除极少数人,大多不具备较高的绘画水平,只能点染一些简单的松竹梅石,少数画技超群者,如王绂、金问、张子俊,便会成为备受士大夫推崇的画家,并被誉为有“士气”,也即绘画品评中喜欢说的“文人气”。但下一节我们将能意识到,这种修辞在文官间指的既不是内容也不是风格,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恭维的套话。
1987年淮安明代王镇(1424―1495)墓出土的绘画作品可作为当时画坛的一个缩影,帮助我们验证前文观察的效力。65关于王镇墓出土书画的情况,可参考徐邦达,〈淮安明墓出土书画简析〉,载《文物》,1987年第3 期;尹吉男,〈关于淮安王镇墓出土书画的初步认识〉,载《文物》,1988年第1 期;高居翰,〈浙派还是写意?关于淮安墓出土书画的一些看法〉,载《风格与观念: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文集》,第174―198 页。在王镇拥有的16 幅时人画中,山水8 件(其中3 件是云山)、花卉翎毛1 件、枯木竹石3 件、兰花1 件、菊花2 件、人物山水1 件。而在有落款的画家中,张懋丞是道教天师,何澄、戴浩、胡正是中级官员兼业余画家66根据尹吉男〈关于淮安王镇墓出土书画的初步认识〉一文,何澄在1433―1437年间任江西袁州知府;戴浩曾领乡荐,1435年出任山东东昌府通判,后迁广东雷州府,又改湖广永州府;胡正,字端方,江西吉水人,长于文辞,工草书,曾入太学,宣德间授监察御史。,陈宪章、夏芷、马轼、李在是职业画家67陈宪章,会稽人,以画梅为长;夏芷,钱塘人,从戴进游;李在,莆田人,以云南行取来京,四方重之。此三人著录于《续编》中。马轼,字敬瞻,嘉定人,正德《姑苏志》载其“与戴文进同驰名于京师”,可知亦为职业画家。见《姑苏志》卷五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二五二一,第1059 页。,谢环是宫廷画家。王镇的收藏几乎涵盖了当时最流行的画题,它们是当时那些用于应酬、作为礼物的绘画最普遍的存在形态,无论是职业画家还是业余画家,绘制这样的作品想必是工作常态。这些作品的千篇一律验证了我之前的判断,职业画家的成功在于精通,而非创造,这也是成功画家与大师间的根本区别。以我们现在的画史看,这些作品或许会被当作令人“惊讶”的例外,68徐邦达与尹吉男二文均认为,宫廷画家使用逸笔草草、墨戏与米氏云山的风格是有违画史知识的特例。但高居翰认为这些作品属于当时用于应酬的类型化作品,具有普遍性。我同意高高居翰的看法。却实为当时画坛的常态。
更多例证将能继续推动我们对画坛常态的重建,以备进一步探讨古代画坛的结构(我相信这一结构在长时间中保持稳定而非变化),以及这些题材和门类所对应的绘画模式,但本文不足以讨论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想要看看画坛的主流趣味,借以考察晚明人用以建立画史的文人画传统,在当时画坛的实际影响力。
四 翰林官员眼中的绘画
与诸多职业画家相比,美术史中常说的“文人画家”——通常指擅长绘画却不以画为业的有教养者,与“文人画”风格——通常指以“董巨-元四家”为传统的山水画,在15世纪的画坛实则并不常见。此时,判断画家的业余与否并不基于风格,而山水通常是高士画或人物故事画的背景,延续着马夏风格,“元四家”仅限江南一隅,谈不上超出地域的影响力。但在16世纪中期之后,我们又能发现,这种江南文人式的风格和趣味俨然已成为时尚,甚至塑造了此后人们对于画史的理解。
是什么造成了趣味的改变?这个问题很难用一篇文章回答。一个更直接的角度是,谁是画家们重要的受画人?明人文集中大量的题画诗说明,官员,尤其是翰林高级文官,自明初起就成为日益活跃的绘画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作为最重要的权力机构的成员与真正的文化精英,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均是文化领袖式的人物。此外他们也是宫廷画家的举荐者,业余画家们的同僚,能同时接触职业画家、业余画家与收藏家,多多少少,他们自己也是藏家。这些都可说明,这些高级文官对绘画的认识和趣味,对画坛应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一般文人对绘画的普遍理解,足以作为一群合适的观察对象。我选取了不同时期的四位人物。
洪武时期的重臣宋濂(1310―1381)曾作〈画原〉一文论画,69[明]宋濂,《文宪集》卷二十五《画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六三,第361―362 页。在宋濂看来绘画的历史就是“古意”丧失的历史,其“古意”指的是绘画所具有的道德教化功能。自9世纪时张彦远通过肯定绘画“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而使画获得了等同于文的价值后,艺术道德化的观点一直是士大夫们的主流态度。17世纪时顾炎武仍持此论:“唐以前名画未有无故事者,皆有考订,无草草下笔,非若今人,任意师新,鲁莽减裂,动辄托之写意而止也。”70[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一六四,第837页。受这种观念影响,以宋濂为代表的洪武士大夫普遍偏爱(唐宋)古画与人物故事画,71实际上不独洪武士大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论画也持此论。熟悉16世纪文人论战的人应该知道,以詹景凤为代表的支持宋代绘画的文人,大多也是相似观点的拥护者,而持史家立场的批评家,如王世贞,通常也持此观点。这个观点的流行程度,从历史长度看,应该胜于对以元四家为代表的文人画风的推崇。强调绘画的功能性与道德价值,《宋学士全集》中的题画诗就是最好的证明。对山水画则没有什么兴趣(提及的山水也基本都是云山),对于“元四家”他只提到过一幅王蒙的作品72[明]宋濂,《文宪集》卷三十二《蛟门春晓图歌(并序)》。值得注意的是,此《蛟门春晓图》即上海博物馆藏王蒙《丹山瀛海图》,蛟门即浙江宁波东北甬江口外柱门岛,此画是王蒙为句章(今宁波)人王景行所作,根据宋濂诗意可知道所绘为海上丹山,此画题有明显的神仙道家内涵。凌利中〈赵孟頫相关研究二题〉一文推论《丹山瀛海图》所绘为四明丹山,所论无误,惜忽略了这条关键文献。。因此,当宋濂盛赞一位“旁通绘事”的读书人“有士韵而无俗姿”时,73同注69。我很难相信他眼中有“士韵”的画和我们后来说的文人画有什么关系。这和李东阳初看沈周画时的评价如出一辙,但李东阳说得坦率:予不深于画,爱屋及乌。74[明]李东阳,《怀禄堂集》卷四十一文稿二十一,原文为:“予不深于画,每爱启南之诗,见其屋乌,若无不可爱者,故为一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八九,第445页。
永乐之后改变开始出现。在永乐朝负责选拔宫廷画家的大学士黄淮(1367―1449)的文集中75关于黄淮负责选拔宫廷画家,参见黄淮,《介庵集》卷九“阁门使郭公墓志铭”,同注32。,花果翎毛、梅兰竹菊与人物故事画依旧是主角,但新的画题“四景画”已经出现。76[明]黄淮,《介庵集》卷二〈题四景山水四首〉(第545 页)、〈题四时花鸟〉(第550 页)、《题四景山水》(第552 页)、〈题四景画〉(第552 页)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 册。黄淮没有提过“元四家”的作品。而在洪熙、宣德、正统三朝阁臣杨士奇(1365―1444)的《东里集》中,对古画的爱好继续延续,一个显著的改变是:今人之画数量增加,当代画坛开始活跃(亦与王镇墓出土作品相互印证)。鉴赏的对象不再只是古代名家,宫廷画家与业余画家的身影多了起来,77职业画家如:陈叔起、朱孟渊、谢环、戴进等;业余画家如:王绂、金文鼎、张子俊、何澄、陈宗渊等。绘画开始频繁地被作为官员之间互赠的礼物,送行图变得非常流行,78如〈题山水图赠胡存渊南归〉〈题鄂渚赠别图送人归庐陵〉〈题山水小画赠康甥归西昌〉〈题溧阳先生归荣图〉〈杨学士以海棠双鹊图赠其弟归求题〉,等等,不一一列举。主题通常是梅、竹、兰、竹石,有时是云山,尽管如此,人物故事画依旧是主流。而他的同僚们也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对收藏的兴趣和绘画的能力,79如〈题勉仁学士草虫图〉〈题勉仁学士岁寒图〉〈题王孟杨检讨鹅鸰图〉〈题孙给事画〉〈题曾学士竹〉〈为钟舍人题孟端竹〉〈题杨学士画〉〈题李检讨梅花〉,等等,不一一枚举。虽然谈不上高超,但作为政治生活的一种高雅调剂品,作为将自身与其他官僚胥吏相区分的一种文化手段,绘画在士大夫中日趋流行。但是,“元四家”同样没有进入他的视野,他只提到过一张倪瓒的画。80[明]杨士奇,《东里集 诗集》卷三〈题倪元镇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七七,第367 页。
程敏政(1446―1499)是成化后翰林学士的代表,兵部尚书程信之子,神童出身,自幼浸淫翰林。他虽曾两次致书沈周求画,并多次为沈画题诗,却坦言自己对书画品茗这类风雅之事并不熟悉81[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七十二〈郭忠恕雪霁江行图为沈启南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九二,第522 页。。我们比较一下安徽人程敏政和苏州人吴宽的丁忧生活:一个忙于宗族事务,一个忙于游山观画,可知书画鉴赏仅是苏州一地的风尚,其他地区文人虽艳羡但无从效仿。在《篁墩文集》的题画诗中,也确实没有展现出与前人的区别,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程敏政曾为两位武官的藏画题诗。82即卷九六十八〈为赵守御题溪云居士水墨龙〉,第476―477 页;卷六十九〈题蔡挥使所藏林良双鹊〉,第484 页。此外,他曾提到过一幅倪瓒的小景与两幅王蒙的画。83[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六十三〈题倪云林小景〉(第406 页)、〈黄鹤山樵山水为杨考功宗器题〉(第406 页),卷七十二〈黄鹤山樵为沈兰坡作小景,兰坡孙启南求题〉(第523 页)。
这四位高级文官正是当时中国最有学识与权力阶层中的一员,然而他们并不具备关于绘画的专门知识,和中国文人对许多事物的理解一样,儒家的道德准则有效地阻止了他们对“多余”之事产生专业认知。他们基本未脱出《历代名画记》为绘画定下的道德教化功用,止于描述画面内容,和翻查工具书指出作者是谁(这正是《图绘宝鉴》的用途),他们不关心也不理解风格,更谈不上审美趣味,只看重对绘画知识的把握,这或许是学者的通病。他们对绘画价值的判断基于两点:题材与古今(当然,如果画家恰巧也是一位和他们一样的有教养者,则是另一码事)。即使存在一些差别,但他们总体单调一致的趣味说明,知识阶层分享着相似且陈旧的意见。显然,他们既有的知识结构不足以鉴赏由宋至明绘画间的种种变化,也产生不了能改变主流趣味的观点,毋宁说,画坛的主流趣味一直就和他们的趣味保持着一致。因此,明代前期画坛存在一种悖论:士大夫偏爱人物故事画,却看不上绘制此类题材的职业画家;受士大夫称赞“有士韵”的同僚业余画家,大多却只能画简单或单一的画题,无法应付复杂的需求。在一位能兼长多种画题的文人出现、并将这些画题“文人化”之前,这种局面很难获得改变。看来,这些喜欢知识且富有历史意识的学者们,亟需被传授一套全新的、符合他们教养的绘画知识,他们需要的不是业余画家,而是足够“业余”的文人。
五 打破边界
上文中林林总总,是我们企图重建15世纪画坛的常态。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讨论开篇的问题:沈周在当时画坛的处境如何?有什么特殊之处?这和他的成功与伟大有什么关联?先看三段有关于他的记载。
第一则是《明史》中的沈周传记,其中记录一个流传广泛、但实际可能是清人编造的故事:
有郡守徵画工绘屋壁,里人疾周者,入其姓名,遂被摄,或劝周谒贵游以免,周曰:“往役义也,谒贵游不更辱乎?”卒供役而还。已而守入观,铨曹问曰:“沈先生无恙乎?”守不知所对,漫应曰:“无恙。”见内阁李东阳曰:“沈先生有牍乎?”守益愕,复漫应曰:“有而未至。”守出,仓皇谒侍郎吴宽,问:“沈先生何人?”宽备言其状,询左右,乃壁画生也。还谒周舍,再拜引咎。84[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九十八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隐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六〇,第167―168 页。
故事尽管虚构,却反映出真实的社会结构。短短132 字中戏剧性地叠加着三次“受辱”:让庶民从事低贱的工匠的事,令庶民受辱;有教养者不被恭敬地邀请,却要自己登门拜访权贵,令有教养者受辱;中级官员因畏惧高级官员,而向比自己身份低贱的人道歉,令官员受辱。这个故事的逻辑正如前文所论,是基于古代社会结构中存在身份等级这一事实。画坛中虽有职业与业余画家,但二者等级悬殊、泾渭分明。更重要的是,当一个人从事比自己身份低贱的事、或被认为是比自己身份低贱的人时,就是受辱。85在等级社会中这种现象普遍存,V.S.奈保尔在《幽暗国度》中记录了他的印度之行,其中写道:“在旅馆负责整理床铺的服务生,若被客人要求打扫地板,他肯定会觉得受到侮辱。在政府机关办公的文员,决不会帮你倒一杯开水。……如果你要求一个建筑系学生画图,他肯定会把它当作奇耻大辱,因为在他看来,身为建筑师却从事绘图员的工作,不啻自甘作践。”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当一个文人从事画家之事、或者被视为画家时,正是这种情况。因而在古代“文人画家”这种概念是不可想象的。
就此而论,当文人画画,他们应该像业余画家一样,专注于本职,避免错认。过去他们的确如此行事,小心地避开任何可能让他们被当作画家的行为、题材或风格,这不仅出于不能,更出于不为。86可以举一个例子:[元]余阙,《青阳集》卷二〈高士方壶子归信州序〉记载,余阙在幽州时遇见北上“远游”的方从义,余阙下意识认为方从义是“名利之人”,即画家,对他不屑,后来才发现方从义的画需要“以礼求之”“非若世俗之区区而至也”,转而以礼待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五三,第384―385 页。)然而,如果真的发生了越界行为,触犯了社会的默认规则,则会令本人感到羞耻、令他人感到不安,这种心态直白地表露为两个概念——文人与画家——间对立的状态。我们可以看一看沈周的朋友杨循吉,在他的一幅画后写下的一段满含忧虑的题跋:
石田先生盖文章大家,其山水树石特其馀事耳。而世乃专以此称之,岂非冤哉?予每见人从千里之外致幣遣使,索先生画者,而先生之文章不下于画多也。人虽好值,未闻致幣遣使于数千里外之者也。是人之爱画而不爱文章如此乎?夫先生之在今时,主张风骚,操持大雅,则于所系,亦不小矣。是固宜时之名公达人,时时遗问,存礼荐达之夜。乃区区爱及绘画之事,不过一位堂壁之障而已,岂非先生之所深不欲者哉?因观此画,三叹而题焉。87[明]沈周,《沈周集》中册《附录君谦题辞》,第1125 页。
杨循吉担心沈周被视为画家而非文章家,并非不解风情,而是迫于这种规则。就连以离经叛道著称的祝允明,也有相似顾虑。这种不安弥漫在沈周的朋友圈中,他们赞美沈周的绘画却否认沈周是画家。88如文徵明称沈周“稍辍其馀,以游绘事”(《文徵明集》(增订本 中册)卷二十五〈沈先生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82 页。)、“岂可以艺名哉”(《文徵明集》(增订本 中册)补辑卷第十二“题吴嗣业藏石田先生画”,第1050 页。),吴宽言:“启南诗馀发为图绘,妙逼古人,或谓掩其诗名,而卒不能掩也。”(《家藏集》卷四十三〈石田稿序〉,第385 页。)显然文人口中的“画家”,指的就是本文的“职业画家”。89这正说明,职业画家,即以画为业者,是画家中绝对的多数,明人默认画家就是这类人。杨循吉还提到,人们不远千里购买沈周的画。但令杨循吉不满的不是购买行为,而是购买的对象。这自然让我们联想到关于文人画的一种经典叙事:强调作品的非功利性。这种行为由来已久,但作为一种经典叙事却很可能在15世纪的苏州才开始流传,即朱存理所藏的《云林子逸事》中的一段:倪瓒知道有人要买他的画,大怒说:“急持去,吾画不可以贿得也。”但我们往往遗落了前一半:倪瓒看见别人给他钱是十分高兴的,因为他误以为对方要买文章,一旦发现要买的是画,才发了脾气。90[明]朱存理撰,《楼居杂著》之〈云林子逸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九〇,第601―602 页。类似故事亦见《明史》中倪瓒与王绂的传记。这类故事或多或少促成了后世对于绘画是人格的载体、或文人画家“不食烟火”的想象,并引发了将艺术品视为“物”的社会学视角,以期祛魅。事实上,卖文、卖书法、坐馆、行医都可算文人的正当营生,文人排斥的不是“功利”,令他们恼火的真正原因是,卖画行为会使他们看上去“像”低贱的、以画谋利的画家。即使现实中他们果真如此行事,语言却须遵循惯例,造成文本与图像、事实间的错位。正如上文中画家希望被误认为文人,而这里文人怕被视为画家。
第三段文字是沈周向杨循吉做的自我辩白,他回应说:
君谦仪部为予称冤者,似略予画而谓有文章可重耳。予何文愿辱仪部之知耶?画则知于人人者多,予固自信。予之能画久矣,文则未始闻于人,特今日见知于仪部,予固难自信也。盖仪部爱之深而昧其陋,饰其陋而溢其美也。然画本予漫兴,文亦漫兴,天下事专志则精,岂以漫浪而能致人之重乎?并当号予为“漫叟”可矣!91[明]沈周,《沈周集》(中册)〈跋杨君谦所题拙画(壬子)〉,第1124 页。
沈周用一种谦虚、真诚且非常大胆的态度表明,他自认就是画家。
将沈周与上文所论的画家们相比,我们方能意识到他的态度与行为的独特,与当时社会中固有的三种身份——文人、职业画家、业余画家——均不类同。不同于一般文人,他不拒绝画家的行为:无心仕途,以绘画作为毕生追求,并以此得名;他也不反对身份低贱的人求画,或者用他的画换取经济报偿;92[明]沈周,《沈周集》(上册)〈十一月望日至西山,徐永年与徐襄陪宿山农陆逵家,月下作此〉,第348 页;〈题蕉〉,第439 页。在他的前辈师长中,沈遇、谢缙、陈暹都以画为业,而他的学生中,陆萱、吴麟、王纶等都是职业画家;他绘制了大量的花果杂品,这在当时是职业画家专擅的画题;他甚至会为伪作落下自己款。93同注6,这段记载也被王鏊写进了《石田先生墓志铭》。不同于业余画家,他罕见地能驾驭职业画家擅长的大部分画题,完全符合我们所论成功画家的特征,佐证了吴宽、韩昂对他在15世纪末流行程度的描述是出于实情。他甚至主动回避了业余画家专擅的梅兰竹菊。不同于职业画家,他不需要靠卖画谋生,因此不必完全迎合藏家的需求,山水画是他擅长的主要画科,并能题诗其上。苏州地方的绘画收藏为他提供了职业画家所不具备的视野,而学者的修养赋予了这个地区的文人敏锐的历史感,使他能够在不同的传统和风格间来去自如,跳脱画坛流行的程式;另一方面,也使他能去影响士大夫,教会他们何为真正的品味。此外,他追求并赋予绘画超越于功用与技艺之上的无用价值,只不过这种价值在价值一元化的古代很难获得应有的重视。这些都清晰地显示出与主流画家的极大差别,使他在画坛中看上去既像个“异类”,又像个革新者。正如吴宽所论:
近时画家可以及此者,惟钱塘戴文进一人,然文进之能止于画耳。若夫吮墨之余,缀以短句,随物赋形,各极其趣,则翁当独步于今日也。94[明]吴宽,《家藏集》卷五十二〈跋沈石田画册〉,第481 页。类似的,史鑑在《观陆允晖所藏沈启南诗画》中也持相似观点,认为古之画者不能诗,唯赵孟頫能兼二者,沈周也是“全其二者”。([明]史鑑,《西村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九八,第811 页。)
吴宽认为沈周能在当代画坛“独步今日”的原因,在于沈周在绘画技术上与画坛第一人戴进旗鼓相当,而文化修养远胜于他,并能用文人的趣味重新创作职业化的题材,从而使通俗主题被文人化95其花果题材绘画即可为例。。另一面,沈周也为元代高度语言化了的绘画形式注入了世俗的经验。这种越界使他大受欢迎,也令画坛焕然一新。在沈周之后,文人与画家的边界被彻底打破,画坛悖论消失,山水压倒了人物,风格压倒了内容,自然压倒了道德,文化精英们改变了对绘画的认识。而一位成功画家,自然能吸引来越来越多的效仿者,苏州风格遂逐渐成为16世纪全新的画坛风尚。
应该注意到,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画家和画画的文人,画家与文人间的对立也并不新鲜,但15世纪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文人从未集体地、深入地涉足绘画,因而文人也从未大张旗鼓地批评画家。随着有明以来越来越多的文人,尤其是下层文人,转而以绘画为业,文人与画家间默契保持的边界被彻底打破,这不仅诞生出一个全新群体,文人的特性也为长期保持稳定的画坛带来了一系列新变化。一方面,学者特有的历史意识配合以收藏、鉴赏与绘画实践,促使绘画在古今之间、在风格观念与视觉表现之间形成具体的关联,这不仅使他们在风格上拥有了视野与自由度,使新风格在此际产生,也促使他们对古今之变做出历史性的把握,亦即促使一条关于他们自身的画史脉络在15―17世纪间逐渐成形,这种画史认识也很容易被与他们教养相似的知识精英吸收,在17世纪之后成为一种“普通知识”。另一方面,文人因涉足绘画而产生的不安情绪,转变为对重新界定画家与文人之间界限的急切,亦即“文人之画”与“画家之画”究竟有何区别。这种区分促成了16世纪之后的绘画批评与画史写作,尽管议题在行家与戾家、宋人与元人、浙派与吴派间不断转换,但我们能清楚地看见,画家与文人的对立赋予了这些写作一种鲜明的两极化的态度。无论如何,这两种倾向在16世纪晚期汇聚成一种现在看来过分独断的画史叙事,也为艺术价值的评判找到了一劳永逸的方法。但我想这绝不是古代画坛的实际情况,而是文人对画坛情况的一种反应。而文人与画家这组概念的两极状态,也阻止人们以折衷的态度去理解画坛中许多新现象,尤其当言说必须倚赖概念时,语言就会极易误导无论古之论者、还是今之论者,对于实际历史情况和实际艺术实践的理解(反倒恰恰是画家们最容易逃脱语言的罗网96如[清]恽向言:“南北派虽不同而致,各可取而化。故予于马、夏辈亦偶变而为之,譬如南北道路,俱可入长安,只是不走错路可耳。”载[清]陈撰,《玉几山房画外录》卷下,黄宾虹、邓石如辑,《美术丛书》初集第八辑,台北艺文印书馆,1947年,第66―67 页。)。也正是因为对文人身份的珍视与对画家身份的抵触,画坛的转变并没有能在明代社会发明出一个全新的、精确的身份概念,将过分陈旧且南辕北辙的“画家”与“文人”合而为一,而是继续沿用这些“像硬币一样在使用中早已失去明晰轮廓”的概念,“文人”泛道德化的习惯无可避免地影响到绘画批评,新的风格实践也不得不困在旧观念中难以获得主流的认可。现代美术史学者们习以为常的“文人画家”一词,对古人和今人都充满危险。
六 余论
我的论述应该到此为止,因为每每涉及文人画的问题,就极易陷入概念论的泥潭,在不知不觉中时代错乱、因果颠倒,忽略真实的存在。我认为一种解决方法是,尽可能地探讨画坛、画家与绘画在历史中的实际情况,并在个案之上寻求整体认识。这是本文写作的原因之一。
本文开头说,人们对于传统画史的接受坚定无疑,不曾怀疑,这实际上言过其实了。至少在20年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就已对传统画史这座危楼感到怀疑,各种各样的新方法被应用于修补或者重建这座大厦,在这其中,形式分析遭遇了实证的危机,此后艺术社会史大行其道。但遗憾的是,它擅长在旧框架中充塞空隙,使其看上去愈发庞大,却未能创造出一个整体、精简的叙事,使董其昌的宏论黯淡无光。并且,艺术品虽然被丢回了原境,但更多的是它作为“物”的那一部分,风格与价值的考量却被遗落一旁。
20世纪之后艺术史的写作常常把传统画史树立成靶子,在瓦解传统叙事的同时,顺带也使根基于这种叙事的、被树立为风格规范的大师变得岌岌可危,因而艺术史写作向着对象的去经典化与价值的相对主义转移兴趣,对风格规范确立的讨论,也让位给经典在话语中的建构,即所谓“经典化”的问题。本文中我对画家的评价使用了“成功”和“伟大”两个概念,二者基于不同的时间维度和价值尺度,“成功”指向当代,指在当时的画坛中、相比于他的同行,获得更高的声望与作品更加流行,这是一种历史事实;“伟大”指向历史,指在艺术史中被艺术史家赋予规范性地位,这是一种需要被发掘的历史事实。当然,一位成功画家不一定伟大,反之亦然。但我认为当我们声称一位画家的重要性时,他所在的历史环境,与历史中对他的评价,同样重要。忽略前者,“伟大”很容易沦为一种话语。这是本文讨论画坛常态并希望重新考量沈周画史地位的另一个原因。
最后需要指出,本文将沈周的成功不仅视为他个人的作所为,也视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如何发生——换言之,为什么在15世纪的苏州;这个事件有何影响,比如江南文人的趣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知识精英对绘画的认识;这个新群体、新风格是否真正、或者又在多大程度上撼动了画坛的结构,影响到主流画家的实践,均需要进一步研究。而本文对“伟大”的讨论未涉及作品、也即风格的层面。但这不妨碍我认为,艺术的价值最终不在艺术所在的历史,而在艺术本身的历史之中。我们至今无法完全否定董其昌的理论,或许因为明人是通过真实的观看与实践,建立起画家与画家间、作品与作品间的关联,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思考,这种努力也许并不应该被宣告失败。只不过这已超出本文所能讨论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