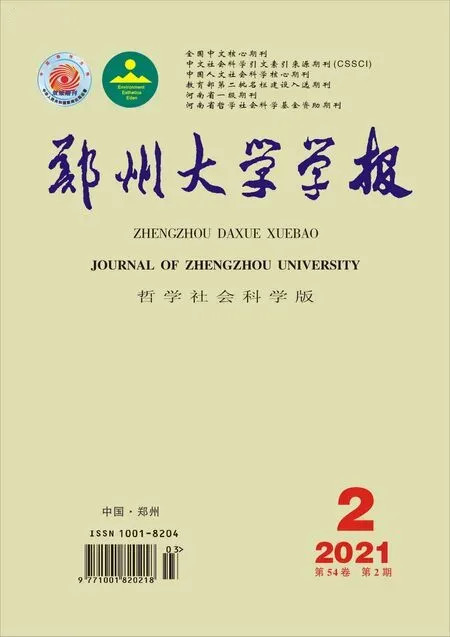传播学视角下中国传统书院学礼研究
——以宋代为例
2021-04-16张兵娟
张兵娟 李 涵
(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在传统教育过程中发挥着传授知识、教化一方的重要作用,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礼制度。从传播学视角看,书院学礼传播以相对封闭的自然空间为传播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传播效果。以儒家经典和经史子集为主要传播内容,促成立志明心、希圣希贤[1](P1)的群体认同。以书本和现实中的各类圣贤为榜样,塑造传播者的多样性。以各类语言非语言符号为传播载体,在“庙学合一”的独特建制中发挥仪式的情感性和强化性。以对儒生德性和德行的影响为传播目的,实现修己成人、经世济民的培养目标。书院学礼传播是在师生互动过程中运用符号实现意义共享,进而达到影响人、改变人的目的,即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眼中传播的“传授”功能。从传播学视角对中国书院学礼进行再阐释,有助于明确书院学礼的独特优势和效果机制,为当下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书院学礼的传播实践:学规与祭祀
学礼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贯穿着中国古代教育尤其是儒家教育的整个过程。书院学礼作为礼的一部分,主要包括祭祀先圣先贤礼仪、会讲礼仪、敬师礼仪、射礼等程式化、仪式化的典礼等[2](P2),其背后承载的是儒家的教育理念。宋代理学家们在书院的教育实践中,不断衍生出儒家文化新的价值内涵,也丰富了学礼的精神内核。
从传播学的视角看,书院学礼更像是一套完整的传播规范,其学规学礼和祭祀学礼分别对应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既从知识传授过程中的传播者、受传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等环节做出规定,也在祭祀这种仪式化传播中凸显无言之教的力量与作用。
(一)传播传递观下的学规学礼
书院学规,又称学约、学则、训规、馆规、规约、规例、揭示、条约、条训等,既是思想层面的书院办学方针,也是维持书院发展的制度保证[3](P118),更是行为层面的具体化教育途径。
传递观是传播的最主要方面,可以阐释为传授、发送、传送或把信息传给他人[4](P4),它强调的是信息和意义的传播。从这个角度看,书院学规既是书院极具特色的一种规程,体现了书院学礼的教育内容,又是书院学礼传播的规章手册,规定了谁来传播知识内容、谁能接受知识传播、传播何种知识、依托什么方法传播知识以及传播知识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
中国古代书院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是两宋时期达到繁盛的“四大书院”。本文试结合四大书院的具体案例阐释书院传递观下的学规学礼。
1.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的学规学礼
作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的范仲淹曾执掌应天书院教席,他在学规学礼中确立了德智并重的传播内容。由于宋初急于依靠科举选拔改变贫弱局面,社会上产生只注重考试而不加教育的应试倾向。范仲淹认为这样“不务耕而求获”的做法,只会助长生徒投机取巧、钻营名利的不良风气。他提出“为学次序”和“读书次序”,强调在备战科举的同时,更应在学礼传播的内容方面注重价值性,传播道德意义,德性应与学问并重,把做人和治学结合起来。范仲淹主张自学为主、指导为辅,突出了人内传播、自我传播的传播方式在教育中的作用。“自我传播”是个体对信息的加工过程,即个体自我进行的思维活动,是将所接受信息和意义与自身原有信息模型相融合的过程,也是教育过程中自我吸收、消化、真正将知识内化于心的关键步骤。范仲淹将学生放在教育的主要位置,提倡充分发挥其学习能动性,培养独立思考和钻研能力,教师指导则只起辅助和引导作用。
范仲淹在学规学礼中扩展了受传者范围。他主张打破藩篱、实行开放办学,只考察生源的品德和学识,不做年龄、地域、身份的限制。入学后,学生可以自行择师,甚至随意流动[5](P105)。这在客观上扩展了儒学教育的受众范围,有助于形成包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学术传播氛围,为实现教化一方、化民成俗奠定了传播的基础,也为学礼传播参与社会价值建构提供了现实路径。
应天府书院的教育盛况,标志着书院这一中国独有的教育形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范仲淹的教育实践为学礼传播思想开拓了道路,也使中国教育闪现出独特的价值火花。
2.二程与嵩阳书院的学规学礼
作为宋代理学的重要代表,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在学规传播的内容方面,嵩阳书院以二程思想为传播的主要内容,要求通读四书,达于六经,并借取佛道的相关思想,建构起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的有机联系。“理”是二程学礼传播的内容核心,他们将“理”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和万物本源[6](P147),强调“物我一理”即万物之理与我心之理的一致性,提出“性即理”的观点[7](P47),将人与自然通过“理”联系起来[8](P125)。在学规传播的路径方面,二程首先倡导“格物致知”。“格物”是对“理”的穷尽性探索,是关于外界知识的学习;“致知”是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是人心固有的情感,如仁义礼智信。二程还强调了教师作为传播者身体力行的示范传播效果,“……讲学于家,化行乡党。家贫,疏食或不继,而事亲务养其志,赒赡族人必尽其力”[9](P333)。此外,二程在注重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提倡学术自由。他们与弟子在书院学习中的问答过程和讲课记录,被其弟子编入二程《遗书》《外书》之中。在学规传播的目的方面,二程尊崇孔孟思想,强调教育在道德提升方面的作用。他们将有关“理”的思想延伸至学规学礼的传播目的中,认为并非所有人都能达到“天下之理一也”的境界,只有圣人才能“统之以一”,致“一”即“理”明,而兴办书院的目的,就是培养此类圣人,进而实现“行之有常、天下化之”的目的。他们将获得理想人格进而成圣成贤视为学习修身的最终目标,也是学规学礼传播所追求的最终效果[6](P148)。
二程洛学的书院学礼传播活动,不仅使书院学礼的内容更加丰富,也使社会教化的传播效果更加凸显,通过宣扬儒学、劝善惩恶,培养淳朴民风,解决社会问题[8](P128)。
3.张栻与岳麓书院的学规学礼
作为宋代著名理学家,张栻的学规学礼思想主要见于《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它奠定了岳麓书院的办学方针和指导思想,体现了岳麓特色的学礼传播特点[10](P15)。首先,张栻将“明人伦”而非“重科举”作为学规传播的目的和宗旨。张栻旗帜鲜明地反对仅以培养应付科举考试、具言语文辞之工“人才”为目的的教育,代之以“传道济民”的学礼传播目标。张栻认为,思想境界高于学识能力,“其所以学者,何也?明人伦也”。人才培养要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标准,即遵循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行为准则,这也成为岳麓学规中的核心传播宗旨。其次,张栻倡导传播者运用身体力行、行为示范等非语言符号代替讲授和灌输完成意义传递。他认为一位好的老师不能抱有“欲为人师”的心态,而应在日常生活中以自身的修养学行对学生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夫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致于饮食起居言动之际,谓道而有外夫是,乌可乎?”这其实是对传播学中非语言符号,尤其是与学者雷·伯德惠斯托所提身势学异曲同工。非语言符号在传递信息时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面对面交流时则能不受语境限制表达言外之意,有时甚至比语言和文字更具有感染力和表达力。爱德华·萨丕尔认为非语言传播是“一套精致的代码,但人人都能意会”[11](P69)。此外,张栻强调“博而后约”的传播方法。这与朱熹只“博”不“约”、陆九渊重“约”轻“博”很不一样。张栻认为博约相须,“约”是目的,“博”是手段,博学是为了求约。这种观点体现了他在学礼传播中重视知识、意义积累的过程性,提倡循序渐进,注重量变,反对急于求成、超越阶段[12](P84)。
张栻的书院实践和学礼思想影响到一大批理学家的治学路径,拉开了理学史上“乾淳之盛”的序幕,为书院学礼的丰富与完备,为更好实现更有效的传播效果提供了有利条件。
4.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学礼
宋代理学家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治学期间,颁行《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教规》),为各个书院学校竞相引用,垂范后世,是书院学礼的灵魂和精髓,学礼传播特点的集中体现。首先,朱熹重视德育为先、修己成人等基础性学礼传播内容。朱熹提倡德育为先,通过增加德性传播内容在书院教育中的比重,实现确立人生目标、规范日常言行、提高道德修养、实现品质磨练的学礼传播效果,进而提升全民素质,达到塑造崇高社会理想道德的目的。其次,朱熹提倡学以致用、经世济民的学礼传播目的。朱熹提倡通过自学为主、辅导为次、相互问难、释疑解惑的学习方式,深刻领悟书本知识,并将其付诸日常生活和国家政治实践。朱熹还重视现实问题的教育,他曾多次邀请外国传教士利玛窦到书院讲授天文、历法、数学、机械等理工科知识[13](P96)。此外,朱熹注重传播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和及时反馈。反馈是传播活动中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传播内容是否被准确接收、传播效果是否达成,都需要依靠反馈进行检验[14](P111)。在书院教育中,朱熹注重师生间的教学相长,提倡交流讨论、自由辩难、共同切磋、互相启发的学风。这种互动和反馈充分体现了口语传播的优势,有利于拉近传者和受众间的关系,在频繁交流中修正对传播内容意义的理解,构建共同经验,搭建益于意义传递的话语平台,是对书院学礼传播环节的有益补充。朱熹这种传播思想的最好体现即他开创了“讲会”制度。尽管与陆九渊存在学派差异,但朱熹仍欢迎后者带领生徒访学白鹿洞,探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即理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双方在批评、扬弃的过程中吸收对方观点,丰富自家学派,为湖湘学派和闽学的进步发展提供动力,进而推动了整个理学思想体系和学礼思维的完善[15](P50)。
(二)传播仪式观下的祭祀学礼
除了通常意义上大众理解的传播的传递观,传播还有着仪式观。不同于传递观对传播内容、信息传播、意义表达等传送的强调,仪式观更注重“分享”“参与”“联合”等方面的含义,强调对“共性”“共有”“共享”的重视。因此,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4](P7)。以此观之,中国古代书院学礼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学规中,更体现在祭祀学礼中。
台湾学者高明士指出,伴随着庙学制的形成,祭祀成为书院学礼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祭祀作为一种仪式,主要是指向神灵、祖先、圣贤等崇拜对象行礼,以表达内心的崇敬,进而祈求庇佑。由于书院祭祀独有的示教于生、立志明心、彰显道统、移风化民作用[16](P34),许多学者将其视为书院学礼的独特标志[17](P47)。祭祀学礼丰富了学礼传播的媒介形式,以具身感、体验感和参与感完成浸入式传播,由行为规范上升至情感共鸣,让学子们在读圣贤书的同时如见其人,拉近了与典范的距离,产生亲近感,更为直观的感受圣贤精神气质,形成见贤思齐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书院祭祀将学礼传播的意义范围由“重视信息接收的效果和功能以达到对人实现控制的目的”,扩展至“通过集体参与和共享创造共同信仰,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的文化世界”,实现了更好的传播效果[18](P2)。
1.非语言的传播符号:书院祭祀的礼仪形式
虽然“庙学合一”制度并非书院独有,但书院在祭祀仪式的确立中建构起一种集体的、公开的、重复的、表演性的独特程式,构成了专属于书院学礼的祭祀礼仪形式。按照祭祀学礼的礼仪形式,书院祭祀可分为释奠礼和释菜礼。前者是一种比较隆重的入学之礼,一般是指学子初入学时所举行的祭祀先圣先师的一种仪式活动,特别是唐朝时期,释奠礼是“官学学礼的核心”,是传播国家观念和信仰的重要途径[19](P13)。进入宋代,书院将此礼仪承续下来,成为书院祭祀学礼中最为隆重的部分。释菜礼较为简单,指学子从师学艺、敬奉师傅的一种活动,一般用野生蔬菜祭奠先师,以表尊师重道。
祭祀学礼有着独特的传播特点。第一,祭祀学礼中的仪式符号具有“共时性”,而非语言符号的线性顺序,仪式中陈列摆放的物品、材料、色彩、形状等通过共现形成表意的符号簇,共同营造情感和意义。第二,祭祀学礼中的仪式符号不像语言符号那样只作用于单一感官,而是通过听、视、嗅、味、触觉甚至运动感觉的综合收受实现表意象征功能。第三,仪式符号多通过形象表达非逻辑概念,营造特定的氛围,向置身其中的受传者传播含义[18](P38)。
祭祀学礼通过行为化、具身化、情感化、仪式化的礼仪形式发挥无言之教的作用。它将个体汇聚在特定的仪式中,塑造庄严肃穆的祭祀氛围,通过视觉、听觉、嗅觉等媒介渠道和恭敬拜祭的行为实践产生希圣希贤的情感共鸣,进而引发认同乃至追崇,达到学礼传播效果。朱熹于1180年3月白鹿洞书院完全修复时,“率宾佐合师生修释菜之礼”,庆贺书院落成。他还在白鹿洞书院为周敦颐立祠,配以二程,又建“五贤堂”祭陶潜、刘涣之、刘恕、李公择、陈了翁等,期望在庄重严肃的祭祀氛围中,学生能够产生群体性的情感共鸣,实现自我身份的认知与群体情感的认同,继承意志、崇圣崇德[20](P92)。
2.多样化的对象选择:书院祭祀学礼的传播主体
根据仪式表演理论,书院祭祀学礼是一种具有表演性质的仪式。它通过时间和空间,将表演事件和日常其他事件区隔开来,以特定人员、特定程序、特定场景营造专属于某一群体的意义空间,祭祀对象也是这场表演的参与者,更是学礼传播中无声的传播者,通过将祭祀者和被祭者联系起来,传达和保留某种信念,发挥被祭者榜样示范的作用,树立标杆,使祭祀者见贤思齐,实现学礼传播效果。
一般而言,书院祭祀对象主要有先圣先贤、历代名儒大师、有功于书院发展建设的名人,以及当地文化名人等。正是对象的多元,才让祭祀的意义更加丰富。第一,“先圣”在书院祭祀中专指孔子,“先贤先师”指孔子著名的门人弟子。第二,对“历代儒学大师”的祭祀表明了书院对儒学道统一脉传承的肯定,如自宋代始白鹿洞书院将周敦颐、二程、张载、陆九渊等儒学大师放在重要位置,将其视为正统的儒学继承人和发展者。第三,对书院建设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也在祭祀之列。如在岳麓书院的祭祀对象中,既有创建者潭州知州朱洞,又有扩建者潭州知州李允,还有重建者湖南安抚使刘珙[21](P86),对他们的祭祀表明了岳麓书院对自身历史发展的重视,形成了独特的岳麓一脉,更能强化书院师生的身份认同。第四,书院还祭祀历史文化名人。如白鹿洞书院的忠节祠就是用来祭祀诸葛亮和陶渊明,以崇二位先贤的忠节。第五,对支持本学院发展的人,例如书院重建者、山长、洞主等也在享受祭祀的范围之内。第六,书院祭祀对象中加入了当地名人,这有助于扩宽书院传播范围,在当地社会中形成认同,大而化民,教化一方。如岳麓书院的祭祀声势浩大,一度成为万民瞩目的区域文化活动,无疑加强了民众与书院倡导的儒家文化的精神联系,宣扬崇文尚儒的价值导向[22](P13)。
二、书院学礼的传播特点
从传播学视角看,宋代书院的学礼传播体现出一种潜移默化的教化过程。从传播内容看,学礼传播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不仅注重学识传授,也强调道德修养。从传播方式来看,学礼传播既包括外部灌输的明示,也含有潜移默化的熏陶。从传播过程看,学礼传播既有专门的教育活动,也包括无处不在的生活实践,更有仪式性的祭祀活动,是一种浸润性、全方位的影响。从传播对象来看,学礼传播不仅着眼于微观个体的知识和修养,更放眼宏观社会的价值导向和道德提升,侧重化民成俗,“教成于上而易于下”[23](P114)。
(一)传播者:垂教于生的“示范性”
书院学礼传播中的传播者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现实中的书院教师,二是儒家经籍和书院祭祀的先贤名士。两者分别在日常实践和特殊情景中,体现学礼教化的示范性。名儒士人作为教学活动中与生徒直接交往的传播主体,其言行和思想对书院学生影响巨大。正如张栻所阐述的学礼思想,“今夫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致于饮食起居言动之际,谓道而有外夫是,乌可乎?”认为教化是在目视耳听、手持足行的生活实践中完成的,好的老师不应只注重讲解书本知识,更应在日常行为中进行身教,规范言行,树立榜样,完成对学生的教化和影响。
存在于儒家经典和书院祭祀中的先贤名士同样是书院学礼传播的重要主体。朱熹曾说:“使天下之学者,皆知有所向往而几及之,非徒修其屋墙,设其貌像,盛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为观美而已也。”[24](P3806)意思是要让天下的学子都知道这些名人,将他们的画像挂在墙上,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呈现在学子的面前,不是为了让他们观赏,而是为了时刻以他们为榜样,汲取他们的思想精髓,在潜移默化中融入自己的观念中,目的在于激励后生继承、发扬其学统及精神品格。
在书院学礼的传播中,这种由感而化的过程,能够唤起学生内心认同,从情感本位出发,实现非强制的规范行为。
(二)受传者:立志明心的“认同性”
对学礼传播的对象书院生徒而言,学礼传播有着“正道脉而定所宗”和“尊前贤而励后学”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生徒对书院学礼的认同实现的。
立志明心的认同性产生于书院活动的各个方面:在讲学方面,学礼体现为对儒学书籍和教学内容的选择,两者作为文化符号和媒介载体,承载着儒家文化的道德要求。生徒对其的学习和研读,即对儒学的感知和认同,对先贤的敬仰和推崇。在藏书方面,书籍的内容、种类是经过人为选择的,在这一选择的过程中同样体现儒家文化的原则和价值取向。在祭祀方面,敬拜体现了对祭祀对象行为、思想的认同感和崇拜。
正是由于书院生徒多方位、长时间的接受儒学知识积累和价值观念影响,他们的人生追求、行为取向会逐渐趋于一致,即向儒家伦常所倡导的理念靠拢,进而确立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亚文化圈,明确儒生身份,生成儒学信仰,产生对儒学和本学派的认同感、归宿感和优越感[25](P104)。
(三)传播方式:体知体察的“践行性”
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学礼从来都不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修炼,而是积极入世、言身合一的身体力行,这种践行性体现在个人和国家两个传播层面。首先,在个人层面,学礼传播通过体知体察、格物致知的日常实践来实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说文解字》)“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荀子·礼论》)这些阐述都突出了礼具有实践性。孟子认为,身体行动是内心道德、情感的外化体现,一个人的品质可以通过躯体行为表现出来,也只有实际行动才最能诚实的反映内心想法。因此在学礼的传播中,只有把所学所思转化为具体行动,在日常生活中依靠身体在场和具身性实践,才能实现学礼的意义和价值。其次,在国家层面,学礼传播更要依靠经世致用的政治实践来实现。学礼文化倡导心怀天下、家国一体的教育理念,书院所培养的正是具有忧国忧民情怀的儒生士人。只有将这种情怀付诸行动,才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如岳麓书院至清代发展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局面,其中许多士人儒生活跃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国家实践中,甚至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
(四)传播内容:德智并重的“非功利性”
书院学礼不以科举成名、入仕为官为传播内容,而是强调德智并重、学而为己[26](P3)的非功利性教育。在学礼传播的内容方面,德占据了主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7](P47)在四大书院,为学修德是书院学礼的重要内容,甚至超过智识教育。学礼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教化内容,以忠、孝、廉、节、仁、义、礼、智、信为重要标准,培养有责任有担当的儒生士人,以达到德智并重、学思并举的教化目的。
在学礼传播的方式方面,讲究由内而外、先内后外的影响顺序。具体体现为在修德过程中,教师讲授居次要地位,而学生思考居主要地位。“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正是在这种自我对话与交流中,儒生们完成了对自己的审视和研判,提高了个体的道德修养,完成了内心“德性”的建构,为践行“德行”奠定基础。因此,学礼教化功能的实现,是以修身为起点,而后才是家、国、天下,内圣才能外王。
(五)传播效果:移风易俗的“情感性”
全祖望曾提到,当书院形成“从者如云”的盛况时,其所“陶成”的,不仅是八方来学的生徒士人,更是社会上的一般民众[28](P291)。书院的学礼传播不仅以就学其中的师生为对象,还对书院所在地方的社会民众产生教化作用,助益当地的文化积累、人才培养和民智开发,实现开化民众、移风易俗的教化目的。书院学礼的传播特征之所以为教化而非教育,在于礼文化的浸润性、情感性和非强制性。儒家伦理的本质是“示范伦理学”而非“规范伦理学”,强调情感、思想方面的影响,而非行为的命令和规范,从而生成思想认同和行为服从。因此,学礼的传播效果是建立在“情”的基础之上,“以情安礼”(《荀子·修身》),形成自然的引导和规训,实现传播效果。
基于上述原因,书院学礼对民众的教化作用,尤其体现在祭祀活动中。书院的祠宇具有开放性、自由性、文化性与公共性,为书院学礼教化功能的实现奠定基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信仰的产生,往往与特定的场合、氛围、情景有关,而书院祭祀活动正是通过种种方式,制造一定的情景、氛围,引发对儒学的信仰。”[22](P13)书院祭祀通过民众的日常参观祭拜,或对祭祀活动的围观参与,将行为引导上升至情感维度,在特定空间和仪式中,建立民众与学礼的联系,进而使民众对书院学礼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内涵产生认同和敬仰,自觉以圣贤为榜样,以达到开化民众、移风易俗的目的,建成通圣达礼的理想儒乡。
三、书院学礼传播的当代价值
纵观中国教育发展史和宋代的书院学礼传播实践,不难看出书院学礼传播所蕴含的价值意义,是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的中国方案,是承载中华文化精神内涵的中国智慧。因此,对书院学礼传播的思考与复归,实现学礼传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助于回归中华文化本质,重塑中国教育品格,应对时代变局中的教育转型,帮助思考和回答在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问题。
(一)培根铸魂,增进家国天下的担当意识
书院学礼注重在传播中培养学生立志明心的认同性,这种认同既是对儒家思想的认同,更是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在中国这一家国同构的社会体系中,书院学礼传播将微观的个人成就与宏观的国家命运充分贯通,以培养忧国忧民、有担当有理想的士大夫为目标。在当下教育中,我们应注重发挥学礼传播培根铸魂的根本性作用,将家国情感和民族自信融入其中,弘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爱国情怀,增强学礼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和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人才。
(二)以德为先,强调德智并举的价值导向
孔子所言“成人之教”,是书院学礼的核心精神。所谓“成人”就是全面发展的人,即在智慧、意志、德性(即智、仁、勇)等各方面均得到发展,同时还要掌握各类文化知识,成为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人格的培养。
价值引领是学礼传播的根本任务,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是学礼传播的重要原则。我们应秉承书院学礼中“德育为先”的传播理念,对青少年进行人格教育。其中忠、孝、廉、节、仁、义、礼、智、信既是古代儒家极力倡导的,又是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的重要精神内核,可谓是青少年的人格教育的源泉。我们要继承德育为先的学礼传播内容,不仅要关注专业性、知识性内容,更应注重具有价值引领作用的德性内容,坚持树立理想信念、涵化人文精神,实现立德为先、德智并举的学礼传播目标。
(三)知行合一,激发学以致用的实践精神
书院学礼传播不仅重视对书本内容的学习,更强调在此之上的躬身实践,知行合一,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社会建设和现实实践中去,进而实现经世济国的伟大抱负。当今之世,我们应传承和发扬书院学礼中的力行实践以实现传播效果,践行“认知-态度-行为”的传播效果路径,按“由知而信,由信而行”的过程展开教育,注重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与了解,使之产生认同感、归属感,进而引导学生将理想转化为现实行动,学以致用,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热潮。
四、结语
书院是中国教育中独特的组织形式,传播学视野中的传统书院学礼传播在人才培养和教化民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培养了大批治世之才,他们或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担当起家国大任,或退居乡野归隐田园,承担起教化之责,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中“尊德性而道问学”的精神理念。中国书院学礼传播承载着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内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近些年来,在多方共同支持与参与下,我国书院复兴之势一片盎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5000多所机构被贯以书院之名,真正将复兴传统文化作为重要内容的书院就有2000多所[29](P92),另外,还有很多的学校也和书院进行了合作。以清华大学为例,其在2020年5月公布的招生简章中设立至理、未央、探微、行健、日新五大书院,统筹推进强基计划,培养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通识教育人才。从这些书院的命名可以看出清华大学对“修齐治平”“格物致知”“自强不息”等教育目标的期待,也体现着其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坚持国家至上、人民为先的教育理念。
重回书院既是对当下教育转型的路径探索,也是对文化复兴和文化自信这一时代课题的具体回应。我们应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书院学礼,探寻学礼传播中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传承书院精神,培育当代人才,增强文化自信,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和中国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