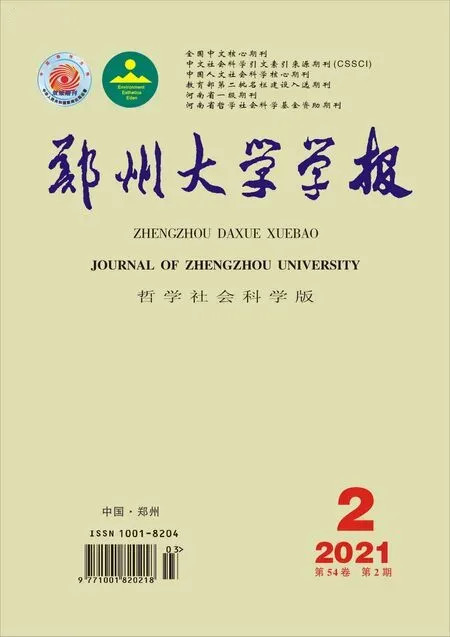明清时期中原地区的城隍文化建构
2021-04-16张民服李颖骅
张民服 李颖骅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城隍信仰在我国历史久远,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时期。明初朱元璋将城隍祭祀列入国家祀典,朝廷对城隍祭祀进行了系统化规定,如官员上任、升迁必先敬谒城隍、每年春秋合祭城隍与风云雷雨山川神、祭厉邑坛主城隍神等,城隍神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清代比附明代祭祀城隍。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主体的中原地区与城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密切关系,城隍文化在中原地区的演变与发展尤为显著。中原地区的地方官吏在迎合最高统治者对城隍的尊崇和倡导的同时,也利用城隍文化维护地方的管控与治理,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城隍文化原有内容或赋予城隍文化新的内涵。信仰城隍的民众,也利用朝廷对城隍的尊崇,将民间的其它信仰杂糅其中,城隍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发展。本文以明清时期中原地区与城隍相关的社学、乡约、救灾、赈灾、司法、诉讼、合祀、淫祀等现象为例,探讨明清时期中原地区官民对城隍文化的共同建构。
一、明清时期中原地区教化内涵引入城隍文化
城隍神作为地方保护神本身并不具有教化百姓的职能,但明清时期随着城隍祭祀列入官祀,每岁与其相关的祭拜络绎不绝,祭祀期间民众也围绕城隍开展各类活动,如参与进城隍出巡并举办城隍庙会等。城隍庙成为城镇以及周边乡村官民生活中频繁进出的场所。地方官员利用城隍的影响力,将社学、义学以及宣讲乡约圣谕等地点设于城隍庙内,在利用城隍庙加强地方治理的同时赋予并强化城隍的教化作用。
社学是古代农村启蒙教育的一种形式。明代各府、州、县皆立社学,以教化为主要任务。清初令各直省的府、州、县置社学,每乡置社学一所,社师择“文义通晓,行宜谨厚”者充补。社学数量的多少受制于城乡里居的疏密,社学规模之大小则受制于城乡人数的多寡。一般情况下,社学在城市或乡村有自己独立的场所,在中原地区,城隍庙则成了开展社学的重要场所。如在山东德州,“城隍庙添立义学一座,每岁修补由知州李天锡捐廉,支发有案”[1](P7509)。在济南章丘,清康熙年间知县将义学建在城隍庙东侧,之后义学经过不断的重修扩大为书院,“义学在县治西城隍庙东,康熙三十五年知县戴瑞建并置地二顷三十七亩零,考功司郎中邑人焦毓栋有记立石。乾隆十九年知县张万青重修,改名阳邱书院,道光七年知县张廷镜重修”[2](P161-162)。河南长垣县“义学八处,一在城内城隍庙侧”[3](P847)。沈丘县“社学在城隍庙西房三间”[4](P114)。汝阳县社学“在城隍庙西,知县邱天英置”[5](P261)。兰阳“新增义学城隍庙一处”[6](P174)。在仪封县,“嘉靖二十五年,知县谷凤皆以学地许民筑室,纳课移学城隍庙”[7](P130)。
社学中的学习对象多以儿童为主,将社学设于城隍庙,生徒们在学习社学所规定的知识之外,长期置身城隍庙之中,耳闻目染,自然就会对城隍神有所了解,加之参与祭祀城隍的活动,或多或少就会受到城隍文化的影响。地方官员将社学与城隍相关联,借助城隍的神力,更能达到兴教化、厚风俗的目的。
乡约学习的对象是更为广泛的民众。乡约制度具有教化百姓、稳定社会、约束不规的作用。明清时期最高统治者也十分重视乡约制度。明代朱元璋以“圣谕六言”推行乡约。“上命户部下令天下民,每里各置木铎一,内选年老或瞽者,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8](P3677-3678)康熙时的《圣谕十六条》、雍正时的《圣谕广训》皆为清代乡约宣讲的主要内容。“颁发直省督抚学臣,转行该地方文武各官及教职衙门,晓谕军民生童人等,通行讲读。”[9](P315)从明清最高统治者推行乡约的地点和内容来看,乡约制度与城隍文化本无关联,但是一些地方官员为了更好地贯彻和执行乡约制度,借助了城隍神的威力,使乡约与城隍产生紧密的联系。中原多地均将乡约所设在城隍庙中:汲县,“乡约所在府城隍庙前”[10](P151);叶县,“乡约所在城隍庙内”[11](P149);泌阳,“月朔望,于邑中城隍庙为乡约所,以老成公正一人为约正,按期□所部民宣讲”[12](P366)。乡约设于城隍庙,更加强化了对民众的教化功能,南乐县志记载:“孔庙有修以崇正学,城隍有修以警愚俗,治教莫有大焉者也。”[13](P278)一些地方官员在城隍庙中进行乡约的宣讲仪式,审理乡约中的善行恶行,借助神道观念移风化俗。人们频繁参与乡约活动,把对城隍敬畏之情和乡约联系起来,乡约得到神明的护持,推广更加顺利,有利于被民众认可、遵守。如仪封县官吏将在明伦堂对学生的讲书和在城隍庙的讲约进行对比,认为城隍庙比文庙明伦堂等地更适合聚集乡民进行教化。“乡约:讲约读法之遗也,其治宜于今,其风近于古。县官每遇朔望谒庙后,诣明伦堂讲书,所以训士子。讲约,所以迪乡氓,近亦有行之于明伦堂者,于义未协,盖学宫为造士之地。讲约则村农野老群至环集,教之以孝悌,课之以耕桑,城中庙宇、城外关厢,轮流宣讲。……俾共见共闻,知所遵守凡县城厢及各大乡镇俱立讲经之所。……本县讲约之所,附城关厢六处,至期轮流,搭厂设案,城中城隍庙一处。”[4](P294-295)淅川县“讲约:月之朔望日,于公所城隍庙设香案,文武宫俱至,公服礼生唱序班,行三跪九叩头礼,兴退,齐至讲所,礼生唱恭请开讲司讲诣,香案前跪恭捧《圣谕广训》,登台宣读,毕礼生唱请宣讲毕退。设约正一人,值月三四人,置二籍,德业可劝者为一籍,过失可规者为一籍,值月掌之月终,则告于约正而授其副,岁终汇册报厅,以俟劝惩”[15](P164)。
乡约有利于巩固统治者的权威,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控制,成为地方官员施政的重要方式,也成为一些乡居士绅进行地方自我管理的一种手段。地方官吏利用城隍对百姓的震慑力来增加乡约的权威性,乡约的推行借助了城隍文化的力量。城隍神享官方祭祀,既代表朝廷意志,又是庇佑一方民众的保护神,受民众崇祀。城隍庙作为官方祭祀场所,由官方组织修建、维护,将乡约所设于城隍庙,使乡约制度和城隍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加强化了教化百姓的功能。
二、中原地区城隍文化中救荒赈灾内涵的强化
城隍作为地方保护神,承载着保佑一方土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功能。明清时期,中原多地官员将用于积谷备荒、救济赈灾的常平仓、社仓、义仓、预备仓等常设置在城隍庙内及其周边,既利用城隍神的威望方便收粮、管理,也进一步强化了城隍文化中救荒赈灾的内涵。地方官吏将义仓设于城隍庙,城隍的救荒赈灾功能也与乡约制度中的内容契合。乡约制度和义仓相结合,用仓收粮的机会,组织乡民宣讲圣谕,并依照乡约对乡民进行奖惩,通过义仓的方式传递其教化的思想。“嘉靖八年题准:每州县村落为会。每月朔日。社首社正率一会之人、捧读圣祖《教民榜文》申致警戒。有抗拒者、重则告官,轻则罚米、入义仓以备赈济。”[16](P248)山东夏津“明义仓三间,在城隍庙西”[17](P140)。济南齐河“雍正八年建县志云,预备仓在城隍庙东”[1](P1316)。河南柘城“社仓在城隍庙”[18](P654)。孟县“劝捐社仓二所,一在城内城隍庙东凡十二间,一在城西十六里西虢村凡三间”[19](P376)。永宁县“义社仓三座,一在城内城隍庙”[20](P948)。嵩县“义社仓二座,一在城内城隍庙”[17](P949)。兰阳“预备仓,旧在城隍庙左”[21](P153)。登封“城隍庙,预备仓西,赵兴重修”[22](P55)。伊阳“常平仓,在城北街城隍庙东,旧名预备仓”[23](P173)。宝丰“劝捐社仓,分贮各里,由绅民等自行经理。宝一里社仓二座,宝一里在城关帝庙一座,在城隍庙一座”[24](P208)。
更有地方逢凶年灾荒在城隍庙设置粥场,赈济民众。山东淄川县志记载:“光绪元年、二年比岁大饥,请于邑宰偕诸绅富捐赀,于城隍庙内设厂煮粥两次。”[25](P208)在菏泽县,“(乾隆)五十年,春无雨至于六月始雨,岁大饥。知县王绩着请赈设粥厂于城隍庙。穷民就食者五六千人,至明年五月止”[26](P829)。河南宝丰县将官吏赈灾的碑文立于城隍庙,“邵建封,四川富顺举人……万历己酉任。岁饥赈救,殚尽心力其倡义劝输”[27](P812)。晚清《项城县志》记载,张安雅在《答袁筱坞书》中提到河南饥荒期间城隍庙中煮粥救济:“河朔三郡暨荥汜郾舞以西,流民提携东徙道经里门者,自八月至今襁属不绝,一路如此他路可知。其老弱不能外逃者,率皆沦为沟殍俟……尚有仓谷煮粥于城隍庙。”[28](P1132-1133)信阳县志中记载,咸丰年间邑绅乐善好施,“唐国鼎……性仁慈好施与。咸丰六年岁大饥,道殣相望,国鼎与邑绅禀承知州设粥厂于城隍庙”[29](P1111)。光绪年间,信阳粥厂仍设在城隍庙,“信阳向属富庶之区,谋生较易……光绪三年,西北数省连年荒旱,饥民来信阳者无虑数万人,地方官绅曾筹款办粥厂二,一设于城内城隍庙,一设于东北乡洋河镇”[29](P398)。
明清官吏在城隍庙设粮仓积谷赈灾,在潜移默化中将城隍威望和赈灾救济结合,使民众产生敬畏感,不听从管理的逆民被罚米入义仓,顺应乡约规则、听从政府管理的民众荒年能在城隍庙得到救济。利用城隍信仰进行奖惩,在客观上达到了劝善惩恶、整饬社会秩序、维护统治稳定的效果。解决自然灾害对百姓造成的困难,地方官员在城隍庙开仓赈灾,一方面突显了城隍神的威灵,使普通的救灾行为,增添了无限的神圣性,另一方面体现了城隍神与统治者的意志一致性,彰显统治者地位的正统,以及“爱民”“仁政”的救灾理念。由此,城隍文化中城隍神作为保护神的功能得以延伸,进一步演化为城隍神具有救济赈灾功能。
三、中原地区城隍文化中司法职能的强化
明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已有大量城隍神断案的传奇故事,但正史并未记载。直至明代初期,城隍参与断案的事迹出现在方志中。明清官方赋予城隍神监察地方官吏的职能,继而城隍参与司法断案的职能进一步得以强化。
古代地方官员既要处理行政事务,也承担司法审判工作。而民间传统观念中城隍神本是神界设立的地方守护神,普通百姓礼敬城隍,以求得庇护。地方官吏则将民间基层的司法、诉讼的实践有机地与城隍崇拜相结合,在案件多发时便会考虑求助城隍。如山东长清县志记载,明隆庆年间县令断案时常向城隍汇报,其德政深受下属和百姓敬佩:“刘启汉,邢台人,举人,有德政……隆庆间任知县……听讼若流、案牍无滞审、均徭诣城隍庙。里胥凛然,服其公且明焉。”[30](P358)在河南鄢陵,官吏将命案减少归功于祷告城隍。“汪为熹曰,予初莅邑,命案甚多……明年春,率阖署斋戒、城乡断屠、作疏吿于城隍之神,自后命案渐稀……惟因事疏吿于城隍之神者向多。”[31](P577-579)汝州官员深信城隍感应,遇见盗窃、越狱等案屡屡在城隍庙祈祷,并在破案后立下感应碑。“时州库被盗,官银苦鞠典守者弗及辩明,侯虔吁于神,不数日,有稚子郡戏于南城垜下,见一山鹊地走逐之几步许,遂入隙穴,就其中捕鹊不见,因获官封银一包,执以闻于侯典守者,遂得宥。其罪贼囚越狱而走,众意其远窜无踪,侯祷之,未浃旬不捕自获,夫神之于,宋侯屡祷屡应,捷于影响,由是四民歌谣于野,官吏胥庆于庭,皆曰,神感郡守之诚而其神亦因致应而益灵也。”[32](P343-346)官吏遇到疑难案件时,借助城隍威严,在城隍庙中审理案件,利用当事人惧怕城隍惩罚不敢弄虚作假的心理,查明案件事实。《汝南县志》记载:“王庄刘宽心家小康,恶族刘三乘夜偷杀其一家九口,而假以其族人面皮呈官报案,冒充原告求为宽心伸冤。知县茫然莫知所措,向府请示。公知其中有诈,乃与县计,入夜私进城隍庙内,高产堂皇发签向县提案。案到果疑为城隍阴审,刘三尤恐惧战栗一一吐出实情,案遂结。”[33](P292-293)
城隍神具有与地方官员共同承担一邑之中伸善抑恶、澹灾兴福的责任。秦蕙田曾概括说:“则唯城隍……衔冤牒诉,辨谗曲直,疫病死亡,幽冥谴谪,丽法输罪,亦莫不奔走归命于城隍。”[34](P1154)民众认为城隍神作为保护的地方神灵,当晓阳间讼案真相。在遇到难以查明的案件时常在城隍庙中祷告,希望借助神力沉冤昭雪。如在修武县,“正德十有四年冬十一月夜,有杀人者迁其尸埋之文庙西庑,童生见而怵焉,以吿众趋视之,乃知程家子也。时领起运粮价故图其财,云其家意夜与饮者并学宫之旁,三十余家诉于县,县贰不能决。众且惧祷于城隍,未几又诉于当道,怀庆府节推张公鞠焉佥曰,夜与饮者姬淸也,必杀之。不服众,益惧号泣于城隍。日朝夕张公诱出赃物狱遂成。众以神之佑”[35](P979)。民众深信城隍神保佑一方安宁,可惩善扬恶,将案件查明归功于城隍神感应。
四、合祀与中原地区城隍文化范畴的扩展
明清时期,城隍列入官祀,城隍祭祀由此系统化、正规化,成为中央对地方管控的一种形式,城隍神的人格化不断削弱。洪武三年取消城隍诸神的封号。“今宜依古定制……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各处府、州、县城隍,称某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5](P1034-1035)城隍庙的建筑亦仿照地方官署的等级、规模及其什器配置,原先的城隍塑像则以木主牌位取代。“(洪武三年)六月戊寅,诏天下府州县立城隍庙,其制高、广各视官署厅堂,其几案皆同,置神主于座,旧庙可用者,修改为之。”[5](P1050)民间祭拜城隍与官祀不尽相同,出于祈福的功利心,民间对城隍的理解更加世俗。城隍神必须具有福佑生民的各种具体功能,在城隍庙所供奉的神位上,也出现了众多能为民众带来现实生活利益和精神慰藉的人格化的神灵。尤其明中期以来,中原多地城隍庙经过不断重修,不仅出现了官方禁止的城隍神像,也逐步出现了其它神合祀现象,这是城隍神功能扩展、泛化的具体表现。
首先,在城隍庙中出现了大量的官民合祭现象。城隍庙中合祀土地神、龙神、刘猛将军甚至包公、皮场公等人物的现象在中原地区相当广泛。明初曾划定正祀范围:“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著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16](P815)因此,八蜡、刘猛将军、龙神、土地神等与城隍职能相关的神灵在无专属庙宇的情况下出现在城隍庙中。
古代百姓认为城隍神与土地神有从属关系,在中原地区的城隍庙中也多合祀土地神。山东济阳“城隍庙内附土地祠……惟城隍庙曁土地祠以士庶信仰之故,不时修葺奉作一方保障”[39](P1733)。河南陈州“城隍庙在府治西南……弘治六年,知州倪诰所建土地祠、钟鼓楼、牌坊、照壁墙”。永城“土地庙,在城隍庙内”[37](P581-582)。信阳“蒿林山都土地祠,本无山一名大马厂,相传以蒿盖屋得名。在平昌关东六里,庙甚古,额曰天下都土地庙。明万历三十二年,张实重修正殿,都土地神,左有圣公圣母,右有土子土孙,又有三曹神,曁城隍、关帝等像”[29](P216)。
明清官方的祭祀中,城隍和风云雷雨、山川神合祀以祈祷风调雨顺。清代,在城隍庙、龙神庙祈雨是常例,但是大多数城隍庙与龙神庙各自独立。而在中原的一些地方则有龙神庙在城隍庙内的现象,如河南浚县“城隍庙在城外山上。龙神庙在城隍庙内。有祈雨成功记载”。山东章邱县“龙神祠在城隍庙内”[38](P184)。将龙神合祀于城隍庙中,更加凸显了城隍神保佑风调雨顺职能。
明清时期中原地区的蝗灾严重,而粮食生产与民众生活、国家税收息息相关,是地方政务中的头等要事,为此,一些地方将与蝗灾相关的八蜡祠和刘猛将军祠建在城隍庙内。如河南长葛“八蜡祠原在城隍庙,乾隆六年知县许莲峰修,乾隆九年预祭文致祭”[39](P87)。获嘉“刘猛将军庙在府城南关,雍正三年知县高辑建获嘉县庙,旧附城隍庙内”[40](P663)。密县“刘猛将军祠在城隍庙内,雍正间奉文创建”[41](P156)。官员遇到蝗灾,甚至会到城隍庙祈祷,并留下祷告文章。如河北广平府志记载:“张耀,江夏举人,康熙二十八年知永年县,值大旱飞蝗徧野,捕之不胜。乃具牒祷于城隍庙,翌日蝗皆自毙。一时惊为神异。”[42](P2777)山东《茬平县志》记载:“张铨……回任宁陵时,值飞蝗入境,作驱蝗文祷于城隍庙,是夜大雨蝗皆溺死于河。”[43](P474)
皮场作为明初朱元璋设立整治贪腐剥皮的场所,扶沟县将皮场公祠建在城隍庙内,“皮场公祠,即灵贶侯,祠在城隍庙中”[44](P307)。武陟县“包公祠,在城隍庙”[45](P404)。在城隍庙中祭祀皮公和包公,表达着警戒贪官、褒扬清官的意愿。
其次,在城隍庙中出现了大量的民间淫祀。明清时期,国家有明确规定不得擅自祭拜淫祠:“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毋得致祭。”[49](P1306)国家规定的祭祀为正祀,不在正祀范围内的民间祭祀则为淫祀。城隍祭祀为正祀,但在中原地区城隍庙中出现了大量的供奉民间信仰的神灵,淫祠合祀于城隍神庙的情况屡有发生。一些城隍庙有不享官方正祀的瘟神与城隍合祀。中原地区长期居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受中央的管控力度最大,因此,百姓往往是以国家祭祀为庇护,巧妙地将民间信仰的神灵供奉于城隍庙之中,以与城隍合祀的方式,保护不被官方认可的所谓的淫祀神灵。如此一来,既使地方官吏拆毁淫祠也不至于将城隍庙拆毁。如登封“城隍庙,在县治西……为东西两角门,门外西为瘟神殿,东为钟楼”[47](P166)。宜阳县“五瘟殿,在城隍庙内”[48](P335)。“广生殿,在城隍庙后楼东偏。鲁斑殿,在广生殿前。咽喉殿,在城隍庙内。五瘟殿,在城隍庙内。”[48](P355)禹县“城隍庙,官斯土者,岁时致祭,朔望展拜,罔敢亵越。余承之,禹郡下车谒见……又东西有两神像,心窃疑之询之,庙祝曰,此非城隍之神,裴山神也。裴山何神,曰,司痘之神也,民间婴儿串痘疹皆祈祷于此”[49](P901-904)。
百姓根据日常生活需求,借杂神合祀城隍庙,赋予了城隍更多的功能。如山东菏泽“观音观在郡城隍庙……鲁班庙在县城隍庙内,灶王庙在城隍庙内”[26](P143)。长葛县城隍庙在同治十二年重修后,出现了佛、道与众多民间信仰神灵合祀的现象。“山门内东廊列望乡,插蜡、确捣、磨研,锯解金桥,劝戒赏善,察照,咽喉、筋骨、脏腑、财神、三曹等司,西廊列灶君、瘟神、阎罗、酆都、速报、现报、五道、即报、斗称、寒冰、增福财神、贤孝、包公等祠。又北胥吏房,东西各三小间。又北戒心坊一座,又北正殿四楹,外有卷棚,站台。殿中列城隍像,两旁列牛首、阿旁诸神像。殿东偏广生祠,两楹西偏,火星祠两楹,殿后阁五间东耳房,城隍眷属,城隍行像阁东西有月门,阁东偏院玉厨祠,两楹,祠南眼光殿,西偏院菩萨殿两楹,罗祖殿两楹,又西偏道房院两处。”[39](P83-84)城隍庙中不仅有与城隍司阴相关的望乡、阎罗、酆都、城隍神、城隍眷属等,也有灶君、瘟神、财神、包公等民间常见的神灵。甚至出现佛教菩萨、罗教的罗祖。城隍庙无疑成了淫祠甚至官方明令禁止的民间宗教的庇护所。
一些地方官员有时尝试制止民间淫祀,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也会顺应民情做出妥协。禹县官吏认为在城隍庙祭拜痘神违制,但未敢拆毁,只是将其神像移入大殿西侧。“余讶其不伦,将迁神于他室,而改为寝宫。……于是割俸首倡,鸠工庇材,移两神女像另立祠于大殿之西以祀之。”[49](P901-904)《郏县志》记载,洪武三年城隍革去城隍神封号、塑像,城隍庙建置如公廨,城隍庙屏去杂神的规定,甚至否定城隍诞辰。“嘉靖初,礼部尚书倪岳疏正祀,兴言城隍本非人鬼,安得诞辰?”[50](P239)尽管官方多次反对,但迫于强大的民间风俗,依旧无法改变民众对城隍神和杂神的祭拜。“塑像如故,仍旧号称显佑伯,以三月十八日为诞辰,而东西庑诸司之神,塑像林立,揆之王制礼典,或以为非,然俗之所尚,故仍其陋云。”[44](239)
再者,在城隍庙中出现了地方名臣的合祀。明清时期虽对淫祀有严格的规定,但对有功于国家的忠臣烈士仍加以祭拜,《明会典》载:“令有司时祀祀典神祇。其不在祀典而尝有功德于民、事迹昭著者,虽不祭,其祠宇禁人毁撤。”[16](P815)清代也有相关记载:“其祀典之可稽者,初循明旧,稍稍褒益之。”[51](P2484)中原地区城隍庙中合祀的地方官吏多为明代受民众爱戴的地方官员。一些官员因仁政廉洁爱民死后虽未设立专祠,但被奉祀在城隍庙中。基层官员利用城隍庙合祀地方官吏以及与辖地相关的名人,借助城隍信仰与忠君爱国、廉政爱民的思想结合,用以教化百姓。如河北涉县“阳公祠在城隍庙二门内,祀明令阳冲”[52](P160)。河南登封“邑令侯公生祠,公到任,祛民害省民财,节民力救民生,一以保民为心。故民感德争立生祠以奉祀,耆老王文等立祠于东关,王廷玉等立祠于城隍庙右”[53](P59)。尉氏县“杨祥……正德十六年任。政多仁恕,视民如伤,民甚爱戴之……卒于官,百姓如丧考妣,立像于城隍庙之西廊,岁时致祭不替”[54](P139)。“王光前,清慎廉明,厘剔时弊……士民感其德,邑东邑北俱立生祠……祠废,像在城隍庙祀名宦。”[55](P416)一些官员因在战乱中保卫城池有功,也立祠城隍庙。考城“孙忠,考城人,明崇祯十三年,李自成攻汴……忠出迎战,力竭阵亡,邑人义之,呼为孙将军。清道光八年,知县吴拱辰奉其主于城隍庙中”[56](P890)。许州“杨礼,临颍人……有刘九兄弟剽掠一方,礼擒治之。死后士人为之立祠于城隍庙西廊,俗呼杨五庙”[57](P668)。一些志士为平息叛乱战死,虽未在城隍庙立祀,但享城隍神主祭厉坛时的附祀,如项城“厉坛祀……附祀五人,以报捍卫之功焉,怀庆卫同知,刘公义勇,吴顶官舍,袁公,张公,信阳卫百户景端。正德六年守备项城时,流贼剽攻城陷端死节焉,事闻赠昭勇将军,指挥使附祀袁贵良少卿后之子,被流贼执不屈,而苑事闻附祀”[58](P172)。
一些地方官员也将与当地有渊源的历史名臣在城隍庙立祠祭祀。如扶沟县洧阳侯祠祭三国时期的名臣郭嘉,“魏封郭嘉为洧阳亭侯,祠在城隍庙中”[44](P307)。郭嘉与城隍信仰并无关联,因其为历史名臣,在当地城隍庙中专祠供奉。考城县城隍庙中立于公祠供奉明将军于谦。“淸光绪十五年知县郭藻为立碑纪其事,文曰,阳湖吕君耀辅摄考篆之……为前明于忠肃公祠。按《明史》载,公河南人……不言其发源何邑。……凡公一生事迹较正史为详,其系出考城,亦良确末载。”[56](P585-587)新郑城隍庙有明高拱祠,“高文襄公祠在北街城隍庙西,祀明大学士赠太师高文襄公拱。……可与本邑先贤郑子产、许鲁斋媲美,二公皆有专祠,而高公止从享乡贤典祀,无乃有阙乎,因详请两院题,准特祀永着为令典,仍准奉祀生员二名。……俱于每岁春秋仲上戊日致祭”[59](P512)。山东曹县的方志中甚至记载了庠生张籍生前受人尊敬,去世后化身为河南归德府城隍的传闻:“张籍,字二酉,庠生,榆林里人。天资慨爽志气刚方,平生急公好义,能为人所不能,为士林胥敬礼之。临终闻空中乐作,迎为归德城隍,子孙岁时往祭,俱有灵应云。”[60](P1227)类似的传说虽然在明清小说中比比皆是,但因内容不可考,记录在地方志中较为罕见。方志中评论此类事情多有传闻,并且认为品德高尚的名人贤臣去世后成为一方城隍神、继续保佑地方百姓的做法合情合理:“论曰,士有端方正直为一方所钦重,殁后传为某邑城隍,其事盖恒闻之。窃思幽明一理,幽暗中建官亦曰惟贤,岂光天化日狐鼠尙容混迹,固宜佩符鱼拥鼎钟循良传,不能殚述名臣录不及备登也。”[60](P1227)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中原地区,城隍文化经官民的诠释,城隍神作为地方保护神,除了官方赋予的监察断案、祈风求雨的功能,也被民众赋予了治病救人、保佑财产、保佑相关行业等神圣职能,城隍庙甚至成为其它民间宗教的庇护所。地方官吏一方面顺应民风民情,一方面将本地官员和历史名臣供入城隍庙,对城隍文化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这些地方官吏和名臣生前所为或和城隍神的职能契合,或在历史上有较高的名望,均是一方民众崇敬的楷模,在城隍庙立祠享受民众和官方奉祀不仅深化城隍神御敌捍土、保护民众的观念,也为执政的地方官员作范例榜样,官民同祭,利于借助城隍文化提高地方荣誉感,维护地区的稳定。
五、结语
古代中国上层意志往往无法直达基层社会,统治阶层运用政治手段和精神手段维护社会的统治秩序,精神手段多以体系化的神灵信仰控制百姓的思想。城隍文化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这和统治阶级的重视并将其加以利用有密切关系。城隍神作为神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即具备安定地方的神性,明清时期城隍纳入制度化的祀典崇拜,城隍庙代表政权统制的所在,官祀城隍是朝廷意志在地方的象征,城隍信仰不仅得到官方认证,也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中原地区受中央的管控力最强,中原文化长期居于正统文化地位,对偏远地区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因此明清时期城隍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演变具有较高的探讨价值。
明清期间随着社学、乡约制度的推行,城隍被官方赋予并强化了教化百姓的功能。社学、乡约作为用于启蒙、教化的重要组织形式,其活动地点设置于城隍庙中,民众长期频繁地在城隍庙学习听讲,进而对城隍文化耳濡目染,城隍掌管一方事务的形象深入人心。官方继而增强城隍救济百姓的功能,在城隍庙设义仓粥场,即肯定城隍的威严又借城隍神彰显统治的正统地位,利用城隍信仰在客观上达到了劝善惩恶、整饬社会秩序、维护统治稳定的效果。官吏将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司法诉讼与城隍崇拜相结合,在遇见疑难案件或案件多发时求助城隍,借城隍威严维护地方秩序。民众认可城隍的司法断案功能,一方面忌惮城隍威严服从地方治理,一方面遇到无法伸冤的不公事件时寄托于精神世界向城隍神控诉。政府利用城隍文化整顿地方吏治,起到维系封建法律和道德观念,制约官吏、警戒百姓的功用。
城隍文化兼容民间与官方的双重要素,在二者交叠的模糊地段亦有不同立场的各自表述。这体现在城隍文化的合祭与淫祭中。官方将与地域相关的历史名人以及能彰显忠孝、仁政爱民的官吏合祭于城隍庙,在管控力有限的基层借城隍的神性巩固统治的正统,在潜移默化中教化引导百姓,维护社会安定。被官方赋予其功能的同时,城隍文化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各有所求的百姓赋予了城隍更多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职能,认为城隍可以惩戒贪官及保佑风调雨顺、粮食丰收、身体健康等。城隍信仰世俗化,成为民众参与政治空间的一种方法。明清时期官民对城隍信仰的建构,使其范畴更加丰富,形成了独特的城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