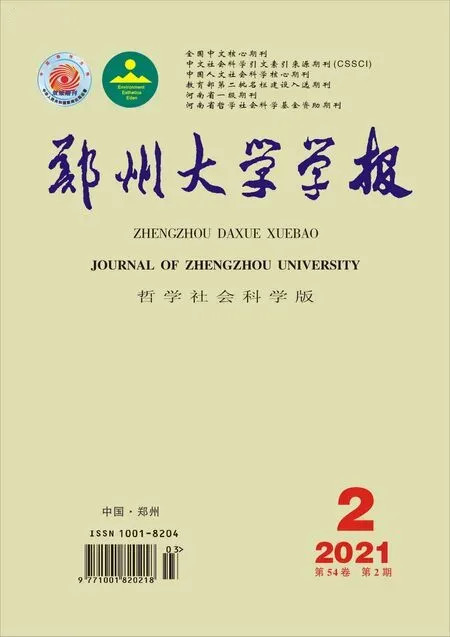《庄子》寓言故事中生命学说的四个层次
2021-04-16杨允
杨 允
(渤海大学 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保全生命、养护身心是道家重要的主张。老子重生贵身,首言“摄生”[1](P256)。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将生命、生存置于其理性观照的核心范围内,在《养生主》《庚桑楚》《达生》等篇章中明确提出了“养生” “卫生” “达生”等观念,并通过生动丰富的寓言故事,从主客观两个角度、四个层面深入阐释了生命的护卫与养护,形成了较完整的“卫生摄养”学说。
“卫生”即护卫生命,“摄养”即养生,“卫生摄养”是庄子的重要论题。《庄子》一书的很多篇章围绕这一论题展开,各篇之间虽然没有严格的论辩逻辑,但所论的基本内容皆围绕生命、形体、精神所构成的生命的自我意义展开。“庄周傲世,洸洋寓言。文穷万妙,学守一玄。”[2]从保身全生到形神兼养的各个层面的思想内涵,体现出庄子对生命学说的探索和思想阐发,而这些思想观点皆寄寓在生动的寓言及隐喻中。本文以《庄子》中的寓言为切入点,将文学研究与哲学思考相统摄,通过发掘庄子生命学说的四个层次,揭示文学符号下寄寓的生命之思。
一、栎树的梦呓:求无所可用以终天年
庄子散文“寓言十九”。《人间世》中,庄子以“栎树之梦”等寓言阐释了养护主体生命、规避外界伤害的艰难。明确要树立自觉的生命意识,规避外在世界对自己生命的戕害,求无所可用以终天年。
作品描写了一棵巨大的栎树长在社坛中,围观的人很多,看它的外观,欣赏它的宏大、壮美。石木匠看它的材质,考量它的价值。从人需求的角度考量栎树的用途,认为它是毫无用处的散木,用它做船、做棺材、做门、做用具,都不行,是不成材的树木,所以才能长得这样高大、长寿。石木匠的评论表现为人类社会和外部环境对栎树超越自身生命的诉求,即要求它对人们有用,能够满足外部环境的需求,否则,就是不成材,就是无用。
夜里,栎树进入石木匠的梦中,对石木匠阐述了自我的生命诉求,阐述了它的生存同人与外部环境需求之间的对立。从栎树作为生命主体的角度看,有用、成材等价值判断都是人类和外部环境强加于栎树的,是蔑视栎树生命的苛求。在栎树的阐述中,凡是被人类视为成材的、有用的树木,都因其有用而被挫折:文木因有用、被砍伐,制成各种用具。果树的水果成熟了,就会被世人采摘、攀折。这些树木因其有用、成材而早早被“重视”死了。反之,在人类价值体系中被视为无用、不成材的栎树,从主体的视角看,却是树木生命的大幸。栎树在梦中表示:“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3](P172)“无所可用”恰恰是栎树寻求的生存之术:它们因遭到人类的鄙视唾弃,而保身全生,得终天年。
类似的寓言故事还有“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南伯子綦前往商丘,见到一株异常高大的树,上千辆四匹马拉的车子在树阴下纳凉。子綦认为这树虽然有特殊的材质,但在许多方面仍然是“无用”的:“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椁;咶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3](P181)在世人眼中,这棵大树树枝“拳曲”,树根“轴解”,不可为栋梁,不可为棺椁,“此果不材之木也”[3](P181),因无所可用,“以至于此其大也”[3](P181)。
“栎树之梦”和“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体现出庄子对生命意识的探索。他深刻地揭示了生命、成材、有用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有用、成材等价值判断的局限性,将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放在理性的平台进行换位考量,阐释了对生命价值判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普遍性与有限性。栎树和商丘大树作为主体,人类则是其生存的外部环境。在庄子看来,主体同其环境所认定的“有用”“无用”的内涵相反,人类或社会的价值判断同栎树、商丘大树作为生命主体的自我价值判断是截然对立的。它寻求自身生命的有用,也就是人类社会价值判断的无用,从而确保自己生命的安全。拒绝有用,拒绝成材,不接受尊宠,甘于冷落寂寞,自处于边缘化境地,无用之用,乃是规避戕害的理性之路,这是庄子对生命意识的集中阐释。
围绕这一生命意识,庄子还进行过反面的阐释。与“不材之木方能成其大”“以至于此其大也”相反,有用之木即遭摧折。《人间世》中“宋有荆氏者”寓言则表达了这一思想。宋国有一个姓荆的人家,种的都是楸树、柏树、桑树等有用的树木:“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椫傍者斩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3](P177)
通过“栎树之梦”“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宋有荆氏者”三则寓言,庄子从正反两个方面生动阐释了有用易致祸、无用乃存生的道理。不仅树木如此,庄子还指出,在祭河神的时候,毛色、身体有毛病的牛、猪和人都不能用作祭品,因为这意味着对神不虔诚,不敬,这样神非但不赐福,反而会产生愤怒进而导致不祥。因此,形体缺陷对于祭祀是不利的,但对于牛、猪和人来说却是保身全生的“大祥”。与之相反,能制作器物的楸柏,能照明的油脂,可食用的桂树,可用的漆树,都因它们有用而招致伤害。“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3](P192)这是庄子保身全生的重要命题,体现出他的生命学说的独特思考。
“无用之用”是身处乱世的庄子对于主体全躯保身的生存策略思考,是他“尊生”理念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他看来,重视生命,安全存世,就要防止外在环境对自己生命的加害。庄子将这一认识践行于自己生活中,并通过“庄子濮水垂钓”以及“牺牛衣食”的寓言故事形象地传达了这一理念。
在《秋水》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途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途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途中。’”[3](P603-604)神龟长寿,可长达千年、万年。但它被制成龟甲,用于巫卜吉凶,刻成甲骨文,被珍藏起来,供奉于宗庙、殿堂上,这样的珍视、珍藏、敬重,对神龟来说都是死后的事。神龟获得死后的尊荣,其龟板作为占卜的灵物藏在庙堂之上,十分高贵,但它的生命却早早结束了。在泥水中爬行、游戏的龟,其生存环境是恶劣的、卑下的,但它自得其乐,“曳尾于途中”,自在自为地活着。庄子以“神龟”之喻形象地告诉使者,我宁愿做下等的龟而自适地生活,也不愿为身后的虚荣而死去。
《列御寇》载:“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3](P1062)庄子谢绝楚王的尊宠聘用,不肯为楚王效力。他将受聘为丞相比作牺牛,虽享受尊宠、荣耀、高贵,但在统治者需要时却将其生命、躯体供奉于祭坛。
“牺牛”与“孤犊”是饱含着庄子对生命思考的两类意象,前者意味着不由自主地受制于外部环境而丧生,后者意味着拒绝尊宠,自求边缘而全身。在这些形象生动的论述中,庄子表现出对作为生命主体的、自我的人生旨趣和人生价值的追求,体现了庄子对生命意义的冷峻思考。
二、“隋珠弹雀”的隐喻:避免“危身弃生以殉物”
庄子认为,如上寓言故事中所隐喻的拒绝外部力量对主体生命的利用、伤害仅仅是“卫生摄养”学说的一部分,在防范外部伤害的同时,还要从生命、生存的角度考量自我价值的观念和行为,理性地掌控自我的人生走向,合理解决生命内在的需求同身外之物的关系。《逍遥游》云:“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3](P24)庄子认为这是生命的基本需求,是生命存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超过“一枝”“满腹”之外的物质都不属于生命所必需的,是多余的,应予否定的。庄子从养护生命的角度将人生的行为分为全身养生和危身弃生两个趋向。庄子认为,“全身养生”,以满足生命的自然需求为限。修道就要懂得养护天性和生命的根本,不能本末颠倒。各种各样的物欲、名利都是身外之物。那些奔波追求物欲的人“多危身弃生以殉物”,是陷于困惑的,也是十分可悲的。庄子将这一理念巧妙地熔铸在“隋珠弹雀”及“尧让天下于许由”等寓言中。
如《让王》篇云:“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且有人于此,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夫生者,岂特隋侯之重哉!”[3](P971-972)庄子以隋侯之珠隐喻生命的价值。如果有人用价值连城的隋侯之珠做弹弓打鸟,世人都嘲笑他。那些“危身弃生以殉物”的行为比用隋侯之珠打鸟还要荒唐,生命之重岂是隋侯之珠所能比!
“隋珠弹雀”的寓言,旨在告诫人们,伤害自己的生命而谋取各种物质利益的行为时时发生在人们身边。“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3](P323),人们在外界利益的诱惑下丧失本性,甚至追名逐利而丧命。“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3](P323)形形色色的人都奔走驱利,“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3](P323)。各种各样的名缰利锁困扰着人们,人人沉迷其间而不悟。
《盗跖》中,庄子指出了富人的六种祸患:“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今富人,耳营钟鼓管籥之声,口嗛刍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遗忘其业,可谓乱矣;侅溺于冯气,若负重行而上阪,可谓苦矣;贪财而取慰,贪权而取竭,静居则溺,体泽则冯,可谓疾矣;为欲富就利,故满若堵耳而不知避,且冯而不舍,可谓辱矣;财积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满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谓忧矣;内则疑劫请之贼,外则畏寇盗之害,内周楼疏,外不敢独行,可谓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遗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尽性竭财,单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故观之名则不见,求之利则不得,缭意体而争此,不亦惑乎!”[3](P1012)奢侈的物质生活,听的、吃的、珍藏的、宠爱的都追求极致。没有时,煞费苦心地算计如何得到;拥有时,日夜焦虑,唯恐失去。怕内鬼偷窃,怕恶人抢劫,在家中时时防范,外出时不敢单独走。提心吊胆地生活,无一日安宁。财富带来了享乐,也带来无尽的忧患。财富的奢求必然导致六个方面的祸患,即神智昏乱、身心劳苦、肥甘阻滞、炫富自辱、患得患失、畏盗惧劫,终日惴惴不安。
在庄子看来,物欲驱动下的人生不仅得不到幸福,反而充满烦恼。《至乐》中,他论述了与人们快乐和苦恼相关的五个方面: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得不到这五方面享受便“大忧以惧”[3](P609)。庄子认为,这些都与“卫生摄养”的思想不相容,是应予否定的。
在庄子看来,圣人修道养中,提升心灵悟道的境界,就要认清外界物质诱惑的害处,要让功名,去利禄,削迹捐势,隐遁避世,清虚淡泊。功名利禄不是幸福之源,而是人生之累。“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堕,名成者亏。”[3](P680)终生沉迷于名利、权势之中的人被称为“天之戮民”,即精神被天所残杀的人。
庄子从生存和生命延续的基本保证看待物质需求,认为需求应以生命的自然状态为限,任何对生命、生活状态的格外追求,都不合于生命的自然状态。为此,他在《天地》篇中,将世俗梦寐以求的长寿、多子多福也视为同追求功名利禄一样,是烦恼的根源。庄子将自己的这一主张寄寓在尧与封人对话的寓言中。
尧将长寿、发财、多子孙视为人生之累,进而拒绝这些祝福,并说:“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3](P420)尧拒绝长寿、财富、多子孙,表现出对物欲的否定,这是修道进程中对“卫生摄养”的认识。守地界的封人则从更高的思想层面论三者未必带来烦恼。封人认为多子孙就要给他们安排差事,有了财富就同人们平均享受。圣人像鸟那样饮食,自由飞行。天下有道,就同万物一起昌盛;天下无道,就修德隐居。长寿千岁、厌弃尘世生活,就超脱成为神仙,驾乘白云,到天帝身边。“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3](P421)封人认为长寿、财富、多子孙对于寻常君子来说,是养生的负担,而对于圣人来说,则是从修道的高度处理物质生活,应对社会的有道、无道,特别是千岁升仙,更是养生的极致。
在生命的需求与对生命的戕害之间,庄子主张要摒却温饱等基本物质需求之外的欲望,去利、去欲,因为“身外之物”,诸如华服、美食、高官、厚禄尽管对世人有着极大的诱惑与吸引力,但从生命养护的角度看,所有超出人基本需求之外的欲望皆会成为加重人生命负荷的枷锁,会伤害人的生命及自由,是不值得以损伤人的生命为代价来追求的。
财富、权势、声名可以带给人尊荣显贵,但在追逐这些事物的过程中往往会带来血腥与杀戮。而自三代以来,天下多以身殉名或殉利,这是令庄子担忧的地方。《庄子·骈拇》云:“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3](P323)
在庄子的思想中,被视为身外之物而应否定的功名利禄,还包括各种功业,就连居君主之位,拥有天下臣民,也被归于不利于生命、生存的额外负担。《让王》篇,庄子通过尧让天下于许由的寓言形象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尧把天下让于许由,许由不接受。又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说:“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3](P965)在世俗的眼里,天下乃是“至重”,可是在许由、子州支父看来,即便是天下这样的“大器”,也不能与自己的卫生摄养相提并论。“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异乎俗者也。”[3](P966)
《庄子·让王》载,越国人连续三代君主被杀,王子搜很害怕,不愿做君主,逃到南山洞中(此用郭象说)。越国人要立他为君,到处寻找,找到山洞。王子搜不肯出来,越人用艾草薰洞逼迫他出来,用君王的车接他。王子搜被迫上车,却不愿做国君,害怕因此而伤害生命。“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生矣”[3](P968)。
值得强调的是,这里庄子视君位、天下为人生之累,反对“弃生以殉物”,其所阐述的对生命的伤害并非外界势力强加于主体,而是士人君子要自觉地、理性地认清并处理好生命同外物的关系。他所谓的“弃生”“易其性”指生命需求之外的奢求,所谓的“殉物”则涵盖各种物质的、精神的诱惑,两者揭示的都是养生与欲望的关系,比前文所揭示的生命存在与社会价值的关系又深入了一层。而庄子的这些思想,通过“隋珠弹雀”以及“尧让天下于许由”等寓言巧妙地进行了传达。
三、广成子南首而卧:“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
在庄子看来,“卫生摄养”包括主客观两方面的内容。首先,主观上要重视生命,要树立自觉的尊生意识与生命守护观念,抵制外部干扰,禁绝生命基本需求之外的欲求。同时,还要反观自身,寻求养生之术。庄子认为,身体是生命的承载之物,“有生必先无离形”[3](P630),万物皆“以形相生”[3](P741),因此,从生命本身来说,养生首先需养形。养形即是养寿,亦即保身全生、益寿延年。对此,庄子通过“黄帝问道广成子”以及彭祖养形等寓言故事,清晰传达了养形长寿之道。
《在宥》云:“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来!吾语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心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女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女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常衰。’”[3](P381)
黄帝立十九年,天下已治,听说广成子在崆峒山修炼,遂往问“至道之精”,即道的秘诀。广成子批评他说:你所问的是事物的自然本质,而你所做的却是任用百官,分管各方面事物,就是对事物的摧残。自你治理以来,各类事物都日趋衰败,你怀着这样狭隘的心怎能问道呢?黄帝采纳批评,放弃天子之位,单独建一座房屋,避喧嚣,守清静,诚心修道。然后,再次入山求道。
首先,庄子认为,为了维持生命,要有基本的物质之需,即“养形必先之以物”[3](P630),但只需保持最基本的物质之需即可,过多的摄取则是对生命及本性的伤害。庄子指出:“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3](P453)都是养生的大忌,故养形必须心静。上引庄子通过黄帝问道广成子之寓言,清晰地传达了这一理念。
其次,庄子指出保身、全生的关键要是“缘督以为经”,即保持中虚之道。《养生主》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3](P115)“督”,即督脉,身体背部正中沿着脊柱走向的经络。因其为身体背部之中轴线,行于脊里且上行入脑,故郭象认为“缘督以为经”,意谓“顺中以为常”[3](P117),即顺守中道。王夫之则认为:“奇经八脉,以任督主呼吸之息。身前之中脉曰任,身后之中脉曰督。督者,居静而不倚于左右,有脉之位而无形质。缘督者,以轻微纤妙之气,循虚而行,止于所不可行,而行自顺,以适得其中。”[4](P120)养中必“缘督”,即凝神顺守督脉,以身体虚空为常法。庄子认为人的生命乃是“气”聚而成,“人之生,气之聚也”[3](P733),因此,“缘督以为经”亦有顺守生命的中虚之道、养气以为常之意。
再次,庄子还认为“养形”要顺阴阳、和四时,因为阴阳不调、四时不至、大喜大怒,都会损伤人的形体,《在宥》云:“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3](P365)因此,“养形”要顺阴阳、和四时,循自然之道。在庄子看来,阴阳之气不畅,则会给身体带来疾病。“夫忿滀之气,散而不反,则为不足;上而不下,则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则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当心,则为病。”[3](P650)同时,不要让身体过于疲劳,因为“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3](P542)
这里论述的是“养形”的问题,即保身全生、益寿延年的方法。在庄子的时代,有神仙家说,有养生长寿之说。《刻意》篇论述了山谷之士、朝廷之士、江海之士等五种类型的士人,其中就有养形长寿一类,庄子称其为“道引之士,养形之人”[3](P535)。这类学说的信奉者创立辟谷、道引等养生秘诀,“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3](P535)。在庄子看来,辟谷、道引等都属于养形长寿的方式,仅是“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3](P535)。可见,庄子通过如上寓言故事所揭示的养生与养形的关系,比前文所揭示的养生与欲望的关系又深入了一层。
四、豚子食于死母之寓:“纯素之道,唯神是守”
庄子认为,形体是生命存在的依托,因此养生需要“养形”。但养生绝非仅仅在于“养形”,因为生命是形与神的结合体,“神”若不存,徒有其“形”,亦不可谓全生。《德充符》中庄子通过小猪寻求亲情的寓言生动阐述了生命学说中的形神关系,揭示出了其生命学说的最高境界。
《德充符》云:“仲尼曰:‘丘也尝使于楚矣,适见豚子食于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弃之而走。不见己焉尔,不得类焉尔。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3](P209)
小猪依偎在母猪身边吃奶。母猪死了,形体虽在,其精神已经消亡,于是,小猪纷纷离去。庄子指出,小猪“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3](P209)。生命的养护中,养形只是初级的,养神才是“卫生”的高级阶段。但是世俗多以养形求长生,对此庄子感叹道:“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虽不足为而不可不为者,其为不免矣。”[3](P630)
全生以修道,庄子要超越“养形”而重在“养神”。“纯素之道,唯神是守”[3](P546)。庄子要将世俗的养生引向更高的境界,要“德全而神不亏”[3](P538),即重在养德养神。在庄子看来,德充足于内,物响应于外,心合于造化,迹混人间,与物迁移,唯有德不可变。因此,“卫生摄养”的最高层次是德有所长,形有所忘。
《德充符》篇记述了几位“形残德全”之人。这些人虽然形体有残缺,但却闪耀着德性的光辉,比“形全德不全”者更让人肃然起敬。庄子通过形残群像的文学预设,深刻传达了养德重于养形。王骀被砍掉脚,形体残缺,却是道德精神的伟人。他的弟子众多,与孔子门徒相等。他体悟“道”,实践“道”,失去一只脚就像丢掉身上的尘土一样,“受命于天”,得天地之正,得性命之正,以至于死亡都无法改变他。申徒嘉被砍掉脚,为此遭到师兄弟子产的鄙视。他将子产同老师对自己的态度进行比较:老师以德净化自己的心灵,从不关注形体是否残缺。子产“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3](P199),即口头上以德相交,实际上却看重外形,因形体残缺而鄙视自己。在庄子笔下,申徒嘉形残而德全,子产是形全而德残。文章以子产为陪衬,彰显出申徒嘉摄养修道的境界。叔山无趾也因刑致残,他反思自己经历,“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3](P202)。痛悔不重视保身全生之道,轻率地谋求名利而被砍掉脚趾。形体被摧残之后,他领悟了问道修德的可贵。他批评孔子追求名利,是将枷锁戴在自己身上,是老天加给他内心的刑罚。庄子指出,各种各样追求名利的人形体虽全,而其精神却带着桎梏,是“天刑之”[3](P205),是精神、心灵残缺的人。庄子认为,修道应遗形弃知。“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3](P217),批评一切智巧,主张“独成其天”[3](P217),即一切顺应自然,反对用智、用巧、牟利之事。
《德充符》中记述这些“形残德全”之人旨在说明形体完好固然必要,但德性的养护、精神世界的护卫对于“养生”更为重要。因为“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3](P436)。可见,道、德、形、神乃是庄子“卫生摄养”观的核心。生命的养护重在养德,重在循行“圣人之道”。
在庄子看来,“抱神以静”乃是修道养德的关键。物欲引起的感情波动,都是对人的心神的干扰,不利于修道养德。“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德之失。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3](P542)。养神必须心静,必须阻绝外物对感官的诱惑,“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3](P284),无欲无念,“虚而待物”[3](P147)使心神处于澄澈宁静的状态。
庄子以自然界中水静则清的现象比喻修道:“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惔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3](P544)即告诉人们,恬淡无为、虚静守一乃是生命养护之道,养德养神之道。
《庚桑楚》篇借老子和南荣趎对话的寓言故事,阐述了“养神之道”和“卫生之经”的要义。“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儿子乎?儿子终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南荣趎曰:‘然则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谓冰解冻释者,能乎?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来。是谓卫生之经已。’”[3](P785-786)
在庄子看来,婴儿无欲无求,纯真适性。“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抱道守一,虚静其心。“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来。”超然物外,忘己忘物,知足知止,此即是“养神之道”,亦即“卫生之经”的核心要义。
综上,庄子以一系列寓言及隐喻,生动地阐述了生命的主体存在与社会价值、养生与欲望、养生与养形、养生与养神的关系,形成了生命学说的四个层次。庄子将这些思想观点寄寓在生动的寓言故事中,通过寓言中奇幻的梦境、虚构的各色人物事物、历史传说、完整的情节以及人物对话等委婉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生命理念及哲学思考,这种独特的话语表达方式及高超的文学艺术手法,无论是在先秦说理散文中,还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都是别具一格且极其可贵的,虽经两千余载,仍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