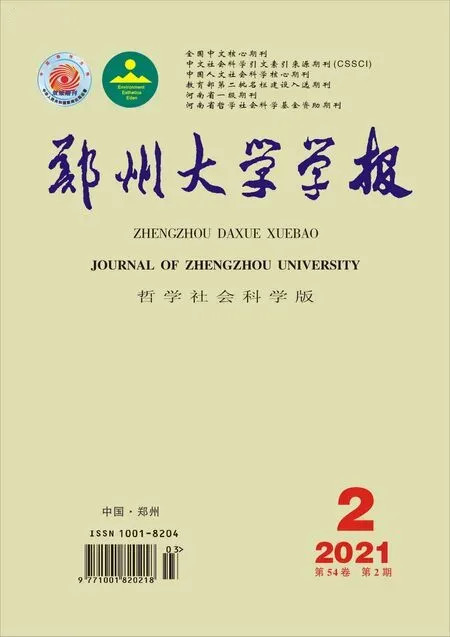传统礼乐的美学重构:以朱光潜和宗白华为例
2021-04-16易冬冬
易 冬 冬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100084)
中国传统礼乐文化在近现代是一个解体与重构的双重变奏过程,如果辛亥革命是传统制度形态的礼乐的解体,那么新文化运动则是传统观念形态的礼乐的解体。礼乐在传统政治、伦理和思想的战场上似乎在“节节败退”,至新文化运动时期,真可谓“一败涂地”。但是,在礼乐遭遇解体的同时,其自身的制度和学术思想的重构也一并开启。对应上面的传统礼乐制度和思想的解体,无论是孔教会的社会性的礼乐宗教制度构建的设想,还是梁漱溟将礼乐视为一种道德化的艺术而对之进行“心”学的阐释,抑或随后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制礼作乐”活动,都是传统礼乐在现代学术思想和制度方面的现代化过程。而这一解体和重构的交响与变奏,共同构成了传统礼乐的现代化进程的全貌。在学术思想领域,自王国维、蔡元培开始,传统礼乐就开始在现代学术思想观念中获得诠释,而礼乐的美学和艺术诠释尤为知识界所青睐。礼乐,在蔡元培、王国维那里获得美学的学科自觉,经过梁漱溟、冯友兰、王光祈的推波助澜,在朱光潜、宗白华那里获得美学的学科建构,最终在贺麟先生那里获得系统的哲学美学的理论奠基。当然,这里的礼乐的美学和艺术诠释,始终与礼乐的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诠释密不可分。现代知识分子在将礼乐视为一种美和艺术的同时,始终注意到其同时具备的宗教、道德和政治属性。本文将致力于探索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两位美学家——朱光潜和宗白华如何以美学的方式重构传统礼乐,而这种美学的重构,亦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史变迁的一部分。
一、礼和乐:儒家思想系统“一以贯之”的精神
朱光潜先生早年留学英国和法国,相较于其他一些学人,如梁启超、王国维和蔡元培、梁漱溟等人,他接受了现代西方的系统的学术训练,对现代西方的美学更是有着精深的钻研。自其回国,便开始用西方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诠释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化,而在抗战期间,则深入到儒家礼乐文化中,并对礼乐精神进行了更全面的学术定位。朱光潜认为,儒家学术思想涉及的伦理道德观念既有仁义礼智信,又有智仁勇,有中庸、忠恕、孝慈等,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设教,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经典体系,从现代学术来看,涉及到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以至于宇宙哲学与宗教哲学,看起来非常纷繁。但他认为,这里面却有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礼的观念和乐的观念。儒家正是从礼和乐“这两个观念的基础上建筑起一套伦理学,一套教育学与政治学,甚至于一套宇宙哲学与宗教哲学”[1]。在朱光潜看来,礼的观念和乐的观念构成了儒家文化的根基。儒家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个人、社会到宇宙并不是一个相互割裂的过程,而是一个同心圆的外推的过程,而整个同心圆则被礼乐照亮。在这里面,朱光潜重视的并非是形式意义上的礼和乐,而是精神意义上的礼和乐。他说虽然乐的精神是和、静、乐、仁、爱、道志等,礼的精神是序、节、中、文、理、义、敬、节事等,但括而言之,乐的精神就是一个和,礼的精神就是一个序。
(一)礼乐的一体性——礼与乐的相应相摄
朱光潜论述了礼乐的相互涵摄、互为前提的一面,即其一体性的一面。首先,他认为礼是达成乐的条件,序是和的前提,即乐中有礼。所谓乐中有礼,就是礼的精神渗透到乐中,所谓“乐者通伦理者也”“知乐则几于知礼”。他解释荀子的“凡礼始乎悦,成乎文,终乎悦恔”这句话时,认为“文”就是条理,秩序,“悦恔”就是一种快乐的精神,所以礼的最高目标是乐。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关系,也是各得其理,才能最终和,也就是先有礼的秩序,才能达致乐的和谐[1]。朱光潜从手段和目的角度论述了礼是乐的条件,他强调在乐的境界中有礼的精神在,依靠礼的秩序才能达到乐的和谐。其次,他用内和外、和与敬、情与理、本和文、素与绘、质与文,对应乐和礼,又强调礼中有乐。如果礼失去乐,那么礼就会变异。“内不和而外敬,其敬为乡愿;内不合乎情而外求当于理,其礼为残酷寡恩;内无乐而外守礼,其礼必为拘板的仪式,枯渴而无生命。”[1]在素与绘、质与文所对应的乐与礼的结构中,由于绘必然后于素,文必然后于质,这就意味着礼必然后于乐。在这里,他又强调,乐就是礼实现的基础。最后,他又用仁来统合礼乐,认为礼和乐都出自儒家所公认的最高美德——仁。有了仁,才能内和外敬,才能内静外文。“就其诚于中者说,仁是乐,就其形于外者说,仁是礼”[1]。礼和乐是一体的,总是内外相应、不可偏废。儒家举乐不废礼,举礼不废乐,言说其中一项,也总是涵摄另外一项,说一统二,说二归一。这便是朱光潜阐述礼乐的相寓相应,相互渗透与涵摄的一体性的三个层面。内与外、和与敬、情与理、内涵与外观、灵魂与躯壳、实质与形式、本与文、素与绘、质与文,当礼乐相对待理解时,强调二者的相互渗透和涵寓,可以拓展对礼和乐的理解。事实上,礼乐的一体性,其精神层面的相互涵寓,源于西周的礼乐文明传统。因为在西周的礼乐传统中,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与礼这种象征仪式融合无间,所以当它们都高度抽象化为一种精神形态时,亦是相寓相摄的。
(二)礼乐的差异性——礼与乐的相反相成
礼和乐的相互渗透,且以仁统合,体现的是传统礼乐的一体性。朱光潜又从三个方面诠释了礼和乐的差异性:第一个方面,从个体的理性与情感的角度,乐着眼于情志的表现和流露,是在发扬和宣泄,让人生气洋溢,使人活跃,而礼则是对人的言行举止进行规范,使得制度文为有条理,使人敛肃,其用在节制,在于使人生气发扬的同时不致于泛滥。乐的精神是任其自然,而礼则是控制自然。乐是浪漫的,礼是古典的。第二个方面,从社会的和谐与秩序方面,乐是在冲突中求得和谐,而礼则是在混乱中求得秩序。乐引起人们情感的共鸣,礼则是显出等差分别。乐在综合,礼在分析。乐在化,礼在别。例如在一场典礼中,作乐时,无论尊卑长幼、亲疏远近都能感到自己属于一个和气周流、无所分差的团体中。而行礼时,人们各就各位,依照一定的程式,揖让周旋莫不中规中矩,显出位分的差异和纪律条理。第三个方面,从境界与功夫的角度,乐主和、仁、爱,这些是修养所成的一种自然的境界。而礼主序、节和文,是修养所需要的人为的功夫。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乐的自然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原始的自然,一个是人文自然,即修养所达成的自然境界。上述第一个方面所涉及的乐的任其自然,就是一种原始的自然,但是这种自然极其容易滑转,所以需要礼的节制,需要礼的功夫,而这种节制和功夫的作用,是为了成就一种更高的自然境界。礼虽然是人为,是对人的自然情感进行节制,但并不是排斥自然,而恰恰是为了成就自然。朱光潜先生在文中并没有明言乐的这两种自然精神的区别,但是他的确看到了乐作为一种修养所成的自然与未经功夫修养的自然的不同。他提到,儒家本来非常看重乐,但是后来更多地言说礼,这是因为乐代表的和的精神,是修养所成的胜境,礼则是达到这种胜境的功夫。言说功夫,是为一般人说法,可以对人的指导更为切实[1]。我们可以看到,礼和乐的差异性,恰恰促使它们相反相成,或者说礼和乐的这种差异性背后有着统一性。
(三)礼和乐的现代学科定位
朱光潜是在抗战时期,在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潮下,以现代学术诠释传统礼乐精神。作为一个现代学者,他认为儒家正是在礼和乐这两种精神的基础上,建筑起了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和宗教哲学以及宇宙哲学,而伦理学又是儒家教育学、政治学和宇宙-宗教哲学的基础[1]。例如,就伦理学层面而言,他认为儒家礼乐只是调节情欲达致中和,而并不主张摧残和禁止。就教育学和政治学层面而言,他认为礼乐的最大的功用并不是个体的修养,而是全民的教化。就个体修养而言,是教育学的,但就全民教化而言,是政治学的。儒家正是通过礼乐之教而达致政治的和谐与有序。儒家纳政治于道德之中,而道德正是依靠礼乐对个体人格的修养。就宗教-宇宙哲学层面而言,他认为儒家将人间的礼乐所透显的序与和的精神,推及到天地宇宙中去,以乐配天,以礼配地,主张孝天敬天,推崇祀天的仪式[1]。在此,朱光潜从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宗教-宇宙哲学诸方面,对礼乐进行现代学术定位。然而他自身首先是一个美学家,以美学研究为核心,但礼乐难道会在美学领域缺席吗?在笔者看来,他不仅对传统礼乐进行了现代美学的学科建构,更是看到了礼乐美学之于礼乐的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宇宙-宗教哲学的更为基础的地位。换言之,传统礼乐在现代学术中的定位,美学才是其更为根本的定位。朱光潜立足于美学,将礼和乐视为一种艺术,一种将伦理、政治、宗教和哲学内蕴其中以实现一个更广远的文化目的的艺术。
在朱光潜看来,儒家的礼之乐是一种艺术,不过美并不是这种艺术的唯一规定,这种艺术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善,实现人际社会的和谐的效果。而对于礼,朱光潜同样认为它是一种艺术。在谈及礼乐之于修身的伦理学意义时,他提出了礼的艺术性。他认为礼有三层含义,分别是“节”“养”“文”。“节”讲究的是对自然的情欲进行节制,使过和不及之情都能复归于中道,所谓不偏不倚。“养”侧重的是,不是戕害情欲,而是以礼养之,礼不但使得情欲“适乎中”,更使之“得其养”。前者是后者的方法,而“文”则是“节”与“养”的结果,内含“序”“理”“义”在内。义是事之宜者,有理有序,自别人看来就是“焕乎有文”。“从‘序’与‘理’说,礼的精神是科学的;从‘义’与‘敬’说,礼的精神是道德的;从合四者而为‘文’说,礼的精神也是艺术的。”[1]于是,他强调,礼其实就是合真善美于一体,“儒家因为透懂礼的性质与功用,所以把伦理学、哲学、美学打成一气,真善美不像在西方思想中成为三种若不相谋的事”[1]。礼的真善美之合一,在梁漱溟那里只是萌芽,尚未直接言明,而朱光潜却明确点出,礼是真善美合一的。对于传统的礼,不能立足于西方真善美分离的视域下看待,因为礼并非单纯的美,也非单纯的善,更非单纯的真(哲学、形而上学),而是伦理学、美学和哲学的合一。朱光潜在其后来的一篇《中国古代美学简介》一文中,也肯定了礼作为艺术的存在,该文虽非作于抗战时期,但这里面所明确表达出来的礼作为一种艺术的观点,是与抗战时期是一致的:“中国儒家是从礼、乐这两个概念,推演出他们的理想国(即所谓‘王道’)。作者基本上是从政治观点来考虑美育的……不但把乐看作艺术,实际上也把礼看作艺术……礼、乐不可互离,其真正涵义是艺术反映政治而且为政治服务。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广义的艺术,因为乐求和谐,礼求秩序,秩序与和谐都是艺术所不可少的。”[2](P557-558)
在这里,礼和乐都是一种艺术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而且这种艺术是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礼乐之教作为一种美育,最终是要实现政治的目的。礼乐的美学,是礼乐的政治学的起点。而礼乐作为一种艺术,就是对情欲的陶冶,使之达致中和。就目标来讲是伦理学的,就手段来讲是美学的,礼乐伦理学是建立在礼乐美学的根基上的。朱光潜又强调说:“儒家的教育就是政治,他们的教育学与政治学又都是从伦理学出发的。”[1]由此,可以充分说明,在朱光潜这里,儒家礼乐在现代美学中的定位,是儒家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的起点,或者说礼乐艺术是一种融伦理、教育和政治于一体的文化艺术。更进一步,朱光潜还论述了礼乐的宗教-形上的一面。儒家看整个宇宙也是有序有和,或者说有礼有乐,看到繁复之中的序,这需要科学的精神,而看到变动中的和却需要一股宗教的精神[1]。这是谈儒家乐有其宗教性的一面。与此同时,他强调儒家最重要的丧祭之礼,同样是一种宗教仪式,以孝天敬天的祭天仪式为顶点,这是在谈礼乐的宗教性一面。他认为礼乐有其宗教神秘性,但是它的企图却是哲学的与科学的[1]。宇宙中的秩序与人间的伦理秩序是同构的,都可以称为一种礼乐秩序。礼乐的伦理政治学放大为礼乐的宗教-形上哲学,并以后者为本体论根据。由此,作为礼乐伦理政治学根基的礼乐艺术,又有其宗教-形上的一面。在此,我们可以打一个比喻:这就像是一个同心圆,最内的圆就是美学,然后往外扩充为伦理学、教育学,又扩充为政治学,再扩充为宗教-宇宙哲学,而这个同心圆都被礼乐所照亮,而圆心可以称为礼乐艺术。
综上,朱光潜对传统礼乐进行了系统性的现代学科定位。基于礼和乐的精神,现代学术可以重构儒家的美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宗教-宇宙哲学,而美学则是礼乐精神最核心的区域。礼乐可以被视为艺术,涵容伦理、政治、宗教、哲学于一体,乃是一种文化艺术。可以推论的是,礼乐艺术乃是儒家文化的标识,礼乐美学乃是儒家学术的核心,礼乐的伦理政治学乃是儒家学术的社会目标,礼乐的宗教-宇宙学乃是儒家学术的终极之维。朱光潜先生在现代学科框架和学术观念中,为传统礼乐进行定位,这是一种现代思想的诠释。其礼乐观念既是传统的,更是现代的。在他这里,礼和乐的精神包蕴从个体到社会、宇宙的方方面面,可谓“致广大”而又“尽精微”,儒家思想观念的一贯性正是奠基于礼和乐的精神,这是他最独到的发现。作为一个美学家,他将礼和乐都看作艺术,但同时看到了礼乐艺术的丰富性和深邃性,将文化涵容其中。正是通过礼乐,儒家的整个文化思想系统都具有了美学色彩。
二、礼法的真精神与礼乐的天地境界
同一时期,宗白华也对儒家礼乐进行了美学的诠释。1941年1月,他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并在当年4月增订此文,发表在《时事新报》上,附题为“增订稿”。在增补后的文章中,作者自称主要是添加了一节《晋人的道德观和礼法观》。他说自己之所以深入到魏晋人的道德观和礼法观中去,是要为他们由于受到正史的轻视而给予新的评价。他认为魏晋名士对礼教的抨击,彰显的其实是一种发扬人格的真解放和真道德的精神,是一种创造的心灵,一种深厚的强健的自由生活,是对秦汉以来“乡愿主义”的反叛,而这种精神恰恰是与全民抗战所表现的那种伟大的热情和英雄主义是一致的,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是自由且美的[3](P267)。在他看来,魏晋人的道德观和礼法观,恰恰符合孔子所赞赏的那种狂狷精神,是儒家道德和礼法的真精神。
他认为孔子作为一个民族的礼法和道德体系的建立者,是真正了解这道德和礼法的意义的人。“孔子知道道德的精神在于诚,在于真性情,真血性,所谓赤子之心。扩而充之,就是所谓‘仁’。一切的礼法,只是它托寄的外表”[3](P280)。在孔子那里,礼法不过是诚,是真性情,是真血性,是赤子之心这些道德精神的外在呈现而已。在传统社会,礼法是一体的,都有教化的意义。但又有所区别,礼主要是依靠礼仪和道德(礼义),法主要是依靠行政和惩罚,礼法的核心在礼,法不过是保证礼实施的社会底线,“出礼则入刑”。作为美学家的宗白华,在这里所谈及的礼法,当主要指礼,包括礼仪和礼义(可以进一步抽象为道德规范)。他强调,孔子自始至终都强调道德礼法的真精神,孔子本人就有一颗伟大的同情心作为其道德的基础。孔子自始至终都痛恨那些舍本逐末、徒有其表甚至假借礼法而行私欲的乡愿之辈。尤其是孔子死后,汉代以来,支持中国社会的就是这种乡愿主义,这种妥协的、折衷的与苟安的人,这种只讲究礼法的外表而忘却其中的真意的人,这种在虚伪化和形式化的礼仪中得过且过的人。而魏晋人正是要以狂狷精神来反抗这种乡愿,反抗那桎梏人心灵的礼教,反抗士大夫阶层的庸俗主义,“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3](P281)。至此,可以看出,在宗白华眼中,魏晋人士之反抗礼教,恰恰是真正的“礼教中人”,这一点也为鲁迅所认同。他们的反抗,恰恰符合孔子本意,因为他们都主张礼教、礼法能够建立在个体的仁心真情之上,必须建立在内心对那些礼仪规范和道德原则的情感悦纳上。
宗白华的这一思路,与梁漱溟先生也是一致的,是礼的“心”学化、性情化,或者说礼的“乐”感化、艺术化。礼法规范的基础是诚,是仁,是真情实感,这种礼法道德也因其“情感”性而进入了审美状态。因为强调礼的仁心真情的基础,而仁心真情就是礼之乐,宗白华进一步将礼乐纳入到现代美学的建构中。1947年,宗白华发表《艺术与中国社会》一文,这是对其之前探索儒家礼法真精神的延续。前面提到,宗白华强调礼法的真性情的基础,无非是呼唤礼的仁心的基础,强调礼的“乐”感化,因为礼之本——仁,也是乐的精神。“礼之本在仁,在于音乐的精神”[3](P413),这一点他与朱光潜先生是一致的。他将礼和乐都视为艺术,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教育就是以礼乐艺术教育教化为主,着眼于以情动人,于潜移默化之间培养了心中的性格与品德,深切而且普遍。如果说诗和乐是直接打动人心,陶冶性灵,那么“‘礼’却在群体生活的和谐与节律中,养成文质彬彬的动作、步调的整齐、意志的集中”[3](P410)。他进一步说,礼和乐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的艺术,让整个社会形成一种秩序条理,乐的艺术则滋润着群体的内心,使之和谐并形成一种团结的力量。然而礼和乐的最后的根据,则是在形而上的天地境界中。他说中国人能够感到整个宇宙在其生命的大流行中,感受其生生之条理,感受其节奏与和谐,并将这种“最高度地把握生命和最深度的体验生命的精神境界”[3](P411)贯注到社会的实际生活中,而能使之“端庄流丽”,这就是诗书礼乐的文化。故而,传统社会生活中的礼和乐,就映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其最终根据就在这民族的宇宙意识中[3](P413)。礼和乐的艺术并不是外在于社会的实际生活的,而是融汇其中,它本身就是“端庄流丽”的社会生活。传统中国人是在宇宙意识中来安排自己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要模仿宇宙本身的和谐与秩序,而在宇宙与社会之间,就是中国人所创造的礼乐艺术。这种礼乐艺术一方面反射着宇宙本身的和谐与秩序,一方面在形态和实践上,又连接着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因为礼乐艺术中的一切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人们通过这种礼乐艺术的不断实践,而真诚地相信具体的现实生活正逐渐走向和谐与秩序,逐渐按照宇宙本身的模样创化着。
而礼乐艺术所渗透的社会生活是非常广泛的,包括个体人格、社会组织乃至最形而下的物质器具中,这就形成了一种礼乐文化(艺术):“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3](P412)礼乐本身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其展开需要种种美和艺术的成分,如服饰、器物、建筑等,而这些东西又都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但是由于要符合礼乐的精神,这些东西又不同于生活中的用具,而有其别样的形式,如在色泽、造型、材质等方面不用于生活器具,这就是美的形式。它们的美不在它们自身,而是以这种独特的形式之美,传递一种“政治的权威”和“社会的亲和力”,表现一种天地人神的宇宙之思。礼器乐器,这些器具在其本源上讲,都来自于人们的物质劳动实践,但是一旦穿过礼乐生活,便以其独特的形式之美,直达天地境界。不独器物,包括衣食住行,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诸层面,一旦进入一种礼乐生活,进入到礼仪的氛围和情境中,一切无不变成一种“端庄流丽”的美。但是它们的美不是单纯自在的,而必须是为了礼乐的道德-政治-形上的目的。而正是因为有此礼乐文化,使得人的社会生活就表现出了某种道德追求、宇宙意识和天地境界。
宗白华先生试图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与其宇宙情调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这个联系的中介就是礼乐文化艺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无论是人格仪容,还是衣食住行、社会组织,常常透显出一种超越性的宇宙精神,这是因为这种社会生活礼乐化了,或者说中国人将礼乐精神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中。换句话说,在宗白华看来,礼乐本身作为艺术,并不是一个脱离生活之外的供人观赏的艺术形态,其自身反射了天地的节奏与和谐,而又融汇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于是,从最形而下的器具,到形而中的人格行止、社会组织,都礼乐化了,也艺术化了。而这种礼乐化、艺术化的过程,同时表现了天地的精神和宇宙的情调。在此,天地精神、礼乐艺术、社会生活,三位一体。
三、朱、宗对礼乐的美学重构之比较及其意义
朱光潜和宗白华先生都是在抗战时期,试图通过美学的方式对传统礼乐进行重构,并在重构中彰显了他们的礼乐观念。当代学者金浪认为,他们对传统礼乐的诠释,既有共同性的一面,也有差异性的一面。就共同性一面来讲,二人的出发点是试图建构出有别于西方美学的中国美学,也就是说有着共同的学科意识。二者都将儒家礼乐与美育结合在一起,借此打通了道德与审美的领域,因为朱光潜和宗白华都强调儒家的礼法道德并非只是外在的束缚,而是建立在仁心真情的基础上的。他们对礼乐的这一美学化诠释,翻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礼教的负面评价。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传统礼乐的现代诠释,都有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文化支撑的意义。然而他们的差异性也是明显的,那就是他们礼乐诠释的不同的文化-政治路径。他认为朱光潜集中诠释的是礼乐贯通个人修养与社会教化层面的“以教统政”的观念,形成的是美学-伦理学-政治学的进路。而宗白华则集中阐释礼乐在贯通天地境界和物质生活中作用,形成的是美学-文化学-象征的进路。简而言之,一个更关注礼乐的政治伦理性,一个更关注的是礼乐的文化形上属性[4]。金浪试图从二人所受的不同的西方美学理论影响来探究他们对礼乐进行美学诠释的不同进路,其关注点在二人对中国美学的建构上,认为他们对礼乐的关注,是抗战时期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
笔者认为,朱光潜和宗白华通过礼乐的美学诠释表达了他们的礼乐观念。朱光潜认为礼和乐的精神,是儒家整个思想学术的根本,可以在现代学术中转换为美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和宗教-宇宙哲学,而其中美学是最为根本的。礼乐都是艺术,涵容儒家伦理、政治和宗教-宇宙哲学,是一种文化艺术。宗白华试图通过礼乐艺术,在中国人的天地精神和社会生活(物质和组织)之间建立联系,如此,礼乐艺术既是天地精神的象征形式,又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的文化艺术、生活艺术。二人都强调了礼乐艺术的社会性和形上性的一面,认识到礼乐艺术并不是一种纯粹美的艺术,而是与传统的社会和生活紧密相连的。朱光潜对礼乐的政治性和伦理性的关注,也绝不比对礼乐的形上学的思考更少,因为他专门探讨了礼和乐的精神何以也贯通了儒家的宗教-哲学观念。而宗白华虽然关注礼乐所负荷的形上的天地境界,但他作《艺术与中国社会》一文本身,就是要探讨礼乐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只不过其着重点是放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个体人格、社会组织和日常器具),何以通过礼乐文化艺术而具有了形而上的天地境界。就礼乐观念而言,二者大同小异,因为他们都是在现代美学视野下看待礼乐。而他们对礼乐的美学诠释进路的不同,固然是由于他们所受到的西方美学的不同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但也是儒家礼乐本身的丰富性的影响。至于二者将儒家礼法道德建立在真性情的基础上,将礼法、礼教“心”学化、“乐”感化的美学诠释,更是对“五四时期”梁漱溟、王光祈等人的礼乐观的延续。朱光潜和宗白华对礼乐进行中国美学的营构,一方面是学科自觉以及抗战时期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对蔡元培、王国维、冯友兰等人对传统礼乐进行现代学术诠释的接续。
总之,中国传统礼教注重教化的感性特质、象征性和乐感性,这是礼教在现代人文观念和学术视野的观照下能够进行美学重构的关键所在。当然,学者们同样意识到礼教的道德性、宗教性的维度,所以也对之进行了伦理学和宗教学的重构,但是这是在与美学重构的互动中展开的。自晚清以来,礼乐开始在制度和理论两个层面,经历着解体和重构的双重变奏。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学人对礼乐的解构,恰恰扫清了礼乐在应用层面僵化的形式和恶劣的结果,而将礼乐的真面目以否定的方式呈现出来,呼唤新的重构。这种重构其实在蔡元培和王国维那里就已经开始,而由梁漱溟、冯友兰推波助澜,最后由朱光潜、宗白华和贺麟完成。
而礼乐现代学术重构的完成,也意味着传统表述礼乐的那一套话语的解构,甚至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传统礼乐思想的许多方面的解体。因为对礼乐的现代学术重构,绝不只是一种话语的转换,这种学术的观念和方法的背后,是一整套的现代思想系统。所以,传统礼乐的现代学术重构本身,亦是近现代礼乐思想变迁的一部分。这一对礼乐的现代学术思想重构,以美学为核心,而朝着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乃至宗教-宇宙哲学层层扩展。礼乐的本质,如果必须在现代人文观念中进行观照,必须以现代学术思想进行重构,似乎只有在美学和艺术这里才能找到它的生根之处。甚至连试图用儒家“六艺”之学涵盖中国全部学术,乃至涵盖西方一切学术的马一孚先生,也赞赏辜鸿铭先生对礼进行翻译时,用Arts这个词[5](P1038)。他自己则这样说道:“西方哲人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5](P23)可见,乐固然可以是美和艺术,礼亦可以为美和艺术。这一美学重构的过程,本身就是礼乐思想变迁的一部分。在此,中国近现代美学史与思想史,在礼乐层面就具有了某种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