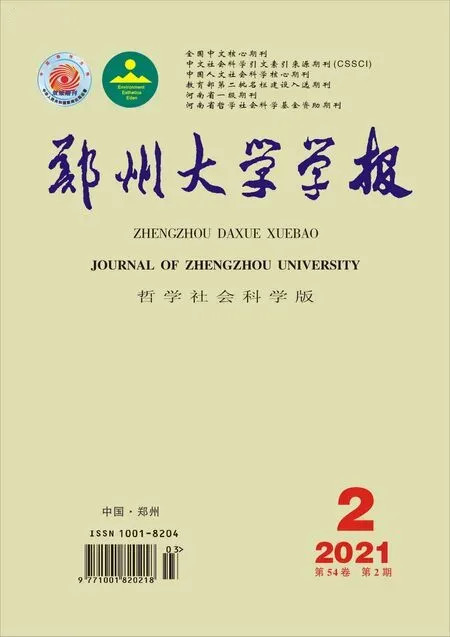中国美学史中的天下观与审美地理学
2021-04-16王燚
王 燚
(河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在中国历史上,天下具有多重含义,一是政治意义上的,二是哲学意义上的,三是文化意义上的,四是地理观念上的。与之相关,天下观则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从制度上来讲指向朝贡制度,从政治上来讲暗含着王朝大一统的理想诉求,从文化上来讲体现出王朝文化对于边疆及其他民族的渗透,从时间上来讲是天下观念的历时性继承和发展,从空间上来讲表明王朝统治的疆域及其之外的地理认知与互动。尽管当代学者对天下观的研究是多视角多方面的,但把它作为美学问题提出来并纳入到中国美学史之中,却显得相对滞后。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需要思考并解决几个相关问题:一是天下观是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亟需补充的重要问题;二是如何理解中国美学史中的天下观;三是天下观与诗性地理之间的美学建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在中国美学史、天下观与诗性地理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既丰富中国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又为中国美学史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方向。一部丰富多元的中国美学史,应该包含天下观与诗性地理的内容,至少也要从天下观和宇宙观视角出发去呈现历史上与之相关的美学问题。
一、天下观:一个亟需弥补的美学问题
受西方美学影响,以往的中国美学史多关注传统文化中的美学思想、美学范畴、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等问题。这种范式固然可以使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美学思想形成一种关联和对接,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那就是为了达成这种结果,往往会从某种程度上对传统固有美学思想形成歪曲或者误解。近年来,当代美学家越来越感觉到需要重回中国历史本身,探寻一条展示中国美学独特魅力的研究之路,这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国美学来说非常重要。那么,天下观作为传统文化和美学中的重要内容,也应该被重新审视和建构。为什么天下观要被纳入到中国美学史之中,这里还需进一步讨论。
首先,研究范式的转变,致使中国美学史中的天下观问题显现出来。近年来,随着美学原理与美学史观的变化,中国美学史在研究对象与建构体系方面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当代学者不只是研究中国美学中与自由精神与人性解放这种主体性相关的审美意识、审美范畴、审美观念与美学思想等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外在于主体性的礼乐、环境、生态、器物、时空、地理等问题。如张法教授认为:“在中国美学史本有的整体框架中,加上与物质形态-制度文化-思想观念-语言概念铸成相关联的美感的建立和演化这样一个核心,就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中国美学史书写中的点和面。这样,从远古到清末,整个中国美学史的写作,就会有一个新的、更为丰富、更接近于中国古代原貌的展现。”[1]要想达到这一目标,中国美学史应该在研究范式方面有所变化,把关注的对象由内在审美认知转向外在审美对象。其中,天下美学体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随着研究的深入,天下观及其相关美学问题一定会逐渐伸张出来,而中国美学史的框架和体系也会越来越坚实而饱满。当然,这种方式并不是抛弃或否定传统的研究成果,而是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新的美学史图景。
其次,天下体系可以成为中国美学史中一个理论生发点。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丰富多彩,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其中最精彩的部分,给予最准确的定位,从而为世界美学的发展贡献中国审美智慧。21世纪以来,一些美学家试图冲出以往的美学研究范式,构建一种多元一体的美学史。在此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忽略的美学问题需要被重新纳入到研究视阈之中。这对于中国美学史向纵深发展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整体来看,天下观就是被忽略的美学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要用感性的、审美化的物体系去彰显出来的。可以看到,古代的天文、宫殿、都城、地图、墓葬、山岳、地理等感性形式,无不暗含着丰富的天下观思想。以西周洛邑为例,当时周公把它作为成周的新都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居于天下之中,可以成为周天子统治天下的象征。它既用雄伟而广大的形式向世人展示王朝的实力,更是用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呈现出周王朝的天下观念。由此来看,我们在研究中国美学史过程中,应该揭示这些有意味的感性形式所内蕴的天下美学问题。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中国美学史一定会有新的理论体系建构出来。
再次,天下观及相关美学问题的进展与中国美学史的充实。近些年,天下观及相关美学问题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张法教授认为,古代中国天下观应该是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一个缺失的问题[2]。而中国古典美学中尤为重要的一维,就是“与中国天下观相连而来的特点”[3]。他在研究秦汉美学的整体面貌时,还专门涉及到天下观的美学问题[4]。在《中国美学经典》中,他也把这一问题的相关资料单列出来[5]。刘成纪教授则试图以天下问题为视角重建中国美学体系[6],深化和拓展了中国美学史中的时空视阈问题。他还重点分析了传统美学和传统天下地理观念之间的承载与塑形关系[7]。刘晓达从秦始皇时代的都城与陵墓、汉初的上林苑与祭祀场所等方面进行考察,用视觉艺术去证实秦汉时期的天下观[8]。这些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切入天下观及相关美学问题,拓展、深化和充实了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内容。当然也要看到,这一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尤其需要一种历史的体系性建构。做到这一点,才能从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美学史呈现出符合历史原貌的、多元一体的美学史景观。
综言之,当代学术视野的拓展与理论的进展,使得天下观重新回归到学术理论之中来。当然,不同的学科对天下观的阐释是不同的。中国美学史立足于美学理论与历史语境,对天下观进行重新审视,发现它应该是自己亟需补充的重要问题。从学术发展来看,天下观应该是当代中国美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新趋势。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使天下观自身的内涵及外延更加充盈,而且还使中国美学史的内容及面貌更为丰富。
二、如何理解中国美学史中的天下观
既然天下观可以成为中国美学史的新领域,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美学史中的天下观就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天下观一直被视为中国传统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主要呈现的是,自古以来王朝统治者对于天下一统的认知模式。其实,从古代文献来看,天下观的内涵要更为丰富。当代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去认知它时,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内涵,这就使得它成为一个非常有意思又具有挖掘潜能的问题。就中国美学史而言,古人对于天下的认知蕴含着审美的特质。天下,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思想或观念,而是由一整套感性体系去呈现的一种审美化认知。我们如何理解美学视阈下的天下观,这里还需进一步阐释。
第一,中国美学史中的天下观是基于认识论的审美化而言的。从美学学科来讲,鲍姆嘉通将它定位为“感性认识的完善”,把感性、审美的因素纳入到人认识世界并获得知识的最基本要素。康德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把审美特性纳入到人认识世界的先验领域。这就赋予审美在人类知识中的先验存在。尼采走得更远,认为人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就是一种隐喻,这就承认现实、世界和真理在总体上具有审美的属性[9](P45-52)。这些观点为我们论述古代天下观的美学问题找到一种理论根基。也就是说,人对世界万物的认识先天地具有审美性质。古人对天下观的认识很好地体现出这一点。可以看到,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以主体感知经验为基础。如《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0](P298)古人对天、地、鸟兽及诸物的感性化和审美化认识是形成理性观念的基础。因为,早期人类对天下的认识具有直观性和经验性特点。人们最初是以最直观的地理图景对天下进行划分的,形成“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11](P165)和“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12](P6-7)的天下情景。这也是以感性的、经验的地理州隩与山川泽海为基础,对天下形成一种统摄性认识,进而构建一种天圆地方式的认知模式。这种天下观,尽管是一种理性观念,但先在地内蕴着感性和审美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天下观,就会发现,它是中国美学史中不可缺少的研究内容,而且对传统审美文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二,中国美学史中的天下观对时空的显现具有审美化意味。在古代,由于人们对天下的认知是处于时空之中,那么由此形成的天下观与时空先验地具有一体化的结构关系。当然,时空本身就具有审美的特质,它在向人的生成过程中,是以感性和美的形式来显现的。所以,天下观的审美问题也就由感性化的时空形式显现出来。所谓感性化的时空形式,主要表现在宇宙之中的四时物候与地理空间。正因为如此,古人总是顺应着时空秩序来显示对宇宙天下的认同。如《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以及《大戴礼记·夏小正》等,记载了人们在不同的时间与季节去如何顺应宇宙时空的种种行为。其中也讲到,天子在不同的时间要处于相应的空间或场所。天子的活动总是与宇宙时空的律动保持一致,不仅用天人合一的方式彰显一种由天而来的神圣性,而且也用躬身作则的方式使公卿大臣和黎民百姓获得一种生活的范式。对古人而言,“空间、时间合成他的宇宙而安顿着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从容的,是有节奏的。对于他空间时间是不能分割的。春夏秋冬配合着东西南北。这个意识表现在秦汉的哲学思想里。时间的节奏(一岁,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率领着空间方位(东西南北等)以构成我们的宇宙。所以我们的空间感觉随着我们的时间感觉而节奏化了、音乐化了”[13](P431)。这种时空一体的天下观是乐感的,也是审美的。
需要看到,天下乃王朝之天下,由此,天下观念的空间构建本身也暗含一种政治性。可以说,它是政治的感性化和审美化表达,也是权力空间化的现实展示。如《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14](P167)可以看出,三代至秦代,人们对天下之五岳四渎的认知,是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尤其在秦代,由于王朝权力和都城定位的变化,所谓的天下之五岳四渎处于统治的东方。于是,秦王朝不得不对天下地理进行重塑,这种做法就是为了从地理观念上寻求秦王朝对天下统治的合法性。所以,由空间到天下到权力的过程,就是一个由具象到抽象再到象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天下秩序逐渐被纳入到空间认知之中,也逐渐形成对权力的一种表征。所谓天下与时空的审美化,其实就是大一统王朝的理想目标。这种天下观对个体、社会乃至王朝的审美观和艺术创作都有重要影响。
第三,中国美学史中的天下观蕴含着一种想象性与人文性。由于人对天下的认知是从直观经验出发的,那么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在直观经验之外应该如何去认知。这当然会利用一种想象,以弥补直观经验之外的、模糊的空间认知。这样,天下观又因其想象性,更加彰显出自身的美学意味。可以看到,从三代至秦汉,统治者所形成的天下观念,就是随着自身统治的强弱而不断向外延展。处于中心位置的当然是王朝都城以及王畿区域,然后是王朝统辖的诸侯国,再次是诸侯国之外的蛮夷戎狄之地。按照这个逻辑,外邦之外还有外邦,那就只能凭借着传说与想象去进行认知。如《山海经》把更为遥远的地方称之大荒,其中的内容蕴含传说与想象的成分更多一些。这种对天下未知地理的想象性,从现实和文明的角度来看或许作用不大,但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则是充满着无穷的魅力,它使得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在地理抒写与精神追求方面具有一种审美性和无限性。
与之相对,人文性也是天下观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天下是基于人对自然地理的认知,在此意义上,它呈现的是一种自然人化的体系。这样,天下因人的参与而拥有了人文价值。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的天下观,由此也具有了人文性。在李宪堂看来,天下观的逻辑起点在于人们对农业历法需求发展起来的“测天步地术”(古天文学),并逐渐形成一种天圆地方的空间秩序。当这种天地四方的观念被一个意义贯通为整体之时,那么它在历史过程中一定会成为王朝统治的制度和文化世界[15]。这种观念随着朝代的更迭而不断加固,逐渐成为一种具有人文和历史特质的思想体系。可以看到,离统治越近的区域,越是文明或文化发达的地区。离统治越远的区域,则成为野蛮或文化不发达的地方。如汉代人对匈奴的印象就是“苟利所在,不知礼义”[14](P635)。这种观念是以中原文化的先进性为基础的。再如,汉代王朝对于天下的认知充满着想象力,这主要表现在,它组入了与方位和数字相关的阴阳五行与天干地支之类,使得当时的天下体系意蕴深长。从这一点来说,天下观是人文化成的结果,也必将因此而具有审美性。近年来,刘成纪教授从时空配置、乐感宇宙与礼乐教化等方面研究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6],确实抓住了天下观中人文性与审美性相统一的本质特征。
第四,中国美学史中的天下观需要人类学视野。一般言之,天下观念在历代王朝中总是与万民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王朝统治的根本。天下既是皇帝的天下,又是由百姓支撑起来的天下。天下观本身就内在地蕴含着人类学的特点,它不仅关注王朝统治之内的区域,而且还要关注统治范围之外的区域。从人类学视角来看,以往的中国美学史更多地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美学思想与美学观念,往往忽略其他文化中的美学思想与美学观念。所以,张法教授认为,中国美学史应该加上少数民族的美学,如此才更显得完整。其原因就在于,古代中国并没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但它所展现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念。“中国美学史应当写今天观念框架中的少数民族美学,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一少数民族美学不应从今天的观念框架中去套,而应从古代中国的民族原貌中去呈现,让中华民族自远古以来的多元一体的特色和历程得以呈出。”[2]要想做到这一点,应该纳入人类学相关内容,建构一种在天下观与宇宙观影响之下的中国美学史。这样一种美学范式,更多地涉及“京城、华夏、四夷、八荒”之间的文化和美学互动。总之,中国美学史要想更加丰富而完整,就应该从人类学出发,弥补天下观视阈下的少数民族美学。
众所周知,早期人类之所以确定以中原为中心并向五服八荒进行蔓延的地理认知,主要还是基于中原的政治地位与文化特质。这种中心清晰、边缘模糊的方式,使传统的天下观具有浪漫主义的特性。当然,在现实中,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真空式的存在,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与外族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的结果。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了对付外族,进行军事和文化上的改革,即胡服骑射。他还引入胡人的歌舞、医药、语言等文化形式,使之在赵国普及开来。《史记》《汉书》记载了匈奴、东夷、南蛮、西南夷、西域、朝鲜等民族的历史事实,其中就涉及到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美学问题。再如,北魏孝文帝变革自己民族的风俗和文化,对汉族文化进行最大限度的接受。后来,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建立王朝之时,都离不开对汉文化的吸纳、接受甚至改造,这些都很好地诠释了中国美学史具有汉族美学与其他民族美学相融合的特质。所以,“华夏美学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核心区的地域文化的美学,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代表中国型的宇宙和天下的美学,正如汉族乃多民族融合的结果,华夏美学中本就内蕴着四夷美学的内容。它所体现的不仅是华夏,而且是一个作为整体的天下观的美学”[3]。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天下观。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很好地解决在人类学视角下的中国美学史如何才能更为完整的问题。
总之,要想理解中国美学史中的天下观,应该从多个视角出发去挖掘其中的美学意蕴。从认识论角度看,人们对天下的认识先验地带有审美因素。这种认知意味着,天下观本身是一个美学问题。从时空角度看,天下并非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有着感性事物支撑的、充满生机的天下。在此视阈下,人的活动与天下万物的感性化和审美化互动,是天下观成为美学问题的现实依据。从历史角度看,古人对天下的认知并非科学意义上的,而是根据自身经验进行的。而人的经验认知又是有限的,超出经验范围的认知,必然会带有想象的成分。由此,天下观又因其想象性和人文性而具有审美意味。从人类学视角看,中国美学史在天下观视阈下,应该关注少数民族美学,至少要关注少数民族美学与汉族美学之间的互动与融合问题。在此四重视角下,天下观的美学问题被揭示出来,从而在理论上可以被纳入到中国美学史的研究范围之中。
三、中国美学史中的天下观与诗性地理建构
在古代,人们对天下认知所形成的理论,并没有像现代学科那么精细,这就需要我们从多学科或交叉学科出发,对它进行一种综合性分析。很多学者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如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说:“一般地讲,今天我们正在意识到,不同的领域与学科取决于相互之间缠绕不清的关系,这与现代的区分理论和分隔教条所想象的方式是截然对立的。这需要思维由分隔的形式转变为相互缠绕的形式。学科的纯粹主义和分离主义已变成陈腐的策略,超学科性与横向分析正在取代它们的位置。”[9](P66)这就说明,现代学术确实需要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如此才能激发出新的理论势能。但是,当代学者对天下观的研究多单纯地从政治、制度、文化、地理等方面入手,往往忽略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言之,中国美学史中的天下观并不是虚无依靠的泛泛而论,而是有着基石般的存在,那就是诗性地理。也就是说,天下观最重要的还是要落实在大地之上。这就需要美学与地理学的交叉融合,从而激活中国美学史被忽略的部分。
从文字学来看,许慎对“地”的解释为:“地,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16](P682)《白虎通》的解释为:“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地者,易也。万物怀任,交易变化。”[17](P420)在古人看来,天和地的产生具有本源一体性,那就是元气。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而大地乃承载万物者也。这种解释具有哲学的意蕴,同时也赋予大地以坚实的品格。许慎对“理”的解释为:“治玉也。从玉,里声。良止切。治理玉石。”[16](P15)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顺玉之文而剖析之。”[18](P498)这就是说,加工玉石需要顺着纹路把玉从石中剖分出来。“理”多指事物的纹路、条纹。由此解释,所谓地理就是大地的外在纹路形式。它一方面因元气之浊而下降为地,并承载万物,另一方面又外显为一种纹理,显示出其审美的品质,这是古人对地理的一种感性的、审美化的认知。这种认知为审美地理学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所以,地理本身就是一个美学问题。人们对大地之纹理的认识,正如对艺术之形式的认识一样,都是在一个意象世界中体验一种真正的美。
当然,地理的审美化在西方思想世界中也是存在的。维柯在《新科学》中对诗性智慧的论述中就谈到了“诗性地理”问题。在他看来,“诗性地理无论就各部分还是就整体来说,开始时都只限于希腊范围之内的一些有局限性的观念。后来希腊人离开本土跑到世界其他地方去,地理的观念才逐渐扩大,直到它所流传到我们的那个形式”[19](P417)。可见,希腊人对天下与地理的认知也是保持在经验范围之内。他们用史诗的形式对当时的天下、地理及诸神之行为给予精彩的描绘。在此情况下,“各民族在这些神话里通过人类感官方面的语言以粗糙的方式描绘各门科学的世界起源”[19](P435)。所以,古希腊神话包含了“各门科学的世界起源”,与此相应也使诗性地理突显出来。维柯之后,西方现代审美地理学对此也有深刻论述。后来,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福柯等主导现代美学的“空间转向”,使文化地理学有了哲学基础。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主张人本主义地理学,产生较大影响。这些代表性研究使审美地理学具有理论深度。由此看出,天下观、诗性地理与空间理论在西方美学思想中也是很早就联系在一起的。与中国一样,它们是同时存在且互相补充的重要美学现象。
也要看到,所谓的地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观的自然地理。就这一点来说,如果是纯粹客观的话,那么对于人来说就显得毫无意义。应该说,它是客观的同时,必然向人呈现,才能显现出自身的价值。自然地理本身所具有的生命灿烂、物象呈现与生态和谐,也会使自身的审美价值显现出来。这是因为,人与自然地理都是生命的一种绽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与契合性。当然,这需要人的发现与照亮,才能形成人与自然的生命审美化。二是主观的人文地理。地理虽是客观存在的,但也是属人的。也就是说,人赋予地理一种主观性。由于人的参与,使地理具备了人文的特质,彰显出一种审美化特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地理,要抓住这种审美性,才能使对古代地理的认知更贴近历史。早期人们对天下的认知是建立在地理空间的人文意义之上的,这是中国古代地理的特点。我们不能用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地理认知去反观古代地理,否则就会形成对古代地理认知的误解。正如唐晓峰所言:“中国古代地理学的成就,人文方面远远地大于自然方面。因为就基本世界观来说,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是生活在‘天下’‘华夏’‘中国’‘九州’‘四海’之内,其本质是一个人文世界。中国古代地理学在论证这个人文世界上,有一整套的作为。对于这个地理学体系,可称之为‘王朝地理学’,在古代王朝地理体系中,自然环境的地位不高,而人文原则却是决定性的。古代学者对于人文地理探讨的程度大大深于对自然环境的探讨。”[20]由此,古人对地理的认知并不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认知,而是带有属人的性质。应该说,地理深深烙上了人的经验性和想象性印迹,并因之而具有了人文性。
所以,古代的天下秩序是人们对地理空间经过加工或组合之后的结果。如在汉代,人们对整个宇宙的构想,主要包括天地、时空、阴阳、五行等方面,然后重新整合形成一个有序而统一的天下体系。这里的地理空间并非单纯的客观存在,而是在阴阳五行的变化中增添了五方、五味、五嗅、五色、五音等[17](P166-187)内容。此空间秩序尽管具有一种理性化特点,但是最终还是用感性化的东西来呈现的,如方位、味道、嗅味、颜色、音律等。这种空间秩序的审美化,可以使天下观变得活色生香。王朝统治者这么做的目的,还在于用一种审美化形式来寻求政治上的一统。这种由一而多的方式,正如一个王朝权力由一而多的发散性分配。这样,天下、地理、美和艺术等,都会统一到王朝的统治体系之中。也要看到,人们对王朝的地理空间认知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王朝的更迭以及势力的强弱而有所变化的。在此背景下,由美和艺术构建的传统地理认知模式也在不断地转换。从历史来看,这种转换模式大概有三种:一是上古时期的圆形模式,二是中古时期的东西模式,三是近古时期的南北模式[7]。这些模式在中国传统国家地理空间建构中,构成了天下观的审美认知。也可以说,天下观与地理空间的互动变化,构成了传统艺术和美学的变化。正是如此,天下、地理、艺术共同彰显中国美学中的审美空间问题。
总之,所谓天下首先是普天之下,它所暗含的空间地理意义较为明显。天下是基于地理之上的天下,而地理则是基于天下的地理。在天下美学体系构建和彰显出来之时,地理空间是不可或缺的维度。天下因地理空间变得具有坚实性,地理空间也因天下被赋予人文性。这样,天下与地理形成一种新的美学关系。就是说,天下观的美学问题最具奠基性的就是人对地理的诗性认知。认识到这一点,不仅使天下观的美学问题得到一种坚实的理论支撑,而且还可以从地理意义上呈现出不同于以前的、切合历史语境的中国美学史。
四、余论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天下观应该是中国美学史中亟需补充的问题,它是通过人对天下万物、政治理想、地理疆域与时空经验的审美感知建构起来的。天下观并非一种玄空的观点,而是通过人的感知显现出来的。在此视阈下,传统的美和艺术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特点。天下观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它包含了政治、文化、制度、地理、时空、审美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并在现代性的多学科之中全方位地展现出自身的价值。单就中国美学史而言,天下首先是一个美学体系,然后才是一个政治观念。它是人从感性与审美出发,对天下万物与地理空间的一种整体认知。但毕竟人的经验是有限的,天下观也会暗含着想象的因素。由于人的参与,它又具有一种人文维度。当然,天下观还应该具有人类学视野。它不仅关注汉族美学思想,而且还要有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尤为重要的是,天下观与诗性地理具有内在一致性。我们之所以把中国美学史中的天下观与诗性地理联系起来,目的在于揭示天下观并非一个虚无缥缈的问题,而是具有客观的地理空间作为基础。可以这样说,天下与地理的相映互动,将构成中国美学史的一个重要维度。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人们对天下的认知有一个由模糊而清晰的过程。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活动范围和自身经验的限制,人们对天下和地理的认识更多地立足于经验但又渗透想象的成分。随着各个王朝的统一与分裂,人们对天下和地理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它所导致的结果是,天下和地理的审美因素有所减弱。在此情况下,天下和地理的审美化就会用另外的形式来呈现。首先是天下和地理自身的自然性被重新认知,它们因自身的自然特质而显现为美。其次是天下和地理经过自然的人化,用地图、山水画或文学艺术去展现那种审美意蕴。从这一点来看,天下与地理并非一种固化审美形态,而是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也要看到,中国美学史研究要想一种新的理论阐发,必须走出以往的研究范式。长期以来,中国美学史更多地涉及美学思想、审美意识、审美观念、审美范畴等方面的内容,却忽略了由美出发并关联礼乐体系、时空审美、诗性地理与家国天下等方面的内容。尽管这种研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美学的理论高度,但并不能形成完整的或符合历史语境的中国美学史。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把忽略的部分补充进来,这样既拓展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视阈,也形成了切合中国历史原境的中国美学史。现在我们关注中国美学史中的天下观与审美地理学问题,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尝试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