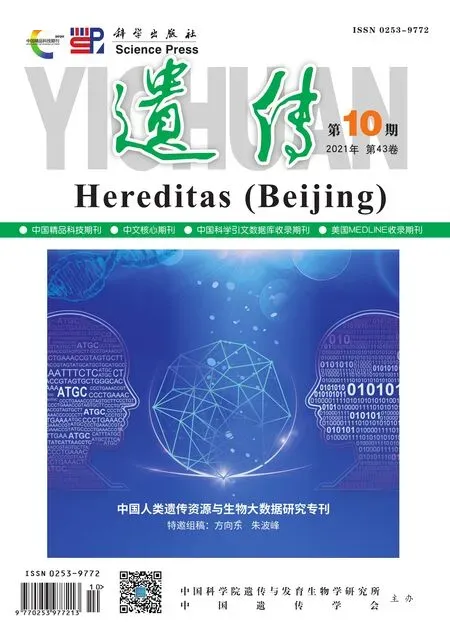生物安全视野下的法医学研究
2021-04-15郭瑜鑫赵兴春
郭瑜鑫,赵兴春
观 点
生物安全视野下的法医学研究
郭瑜鑫1,赵兴春2
1. 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陕西省颅颌面精准医学研究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004 2.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北京 100038
近年来,生物科技在人类生产生活中越来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随之而来的生物安全问题也日益显著。本文基于生物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梳理了在传统法医学和现代法医学研究中涉及到的生物安全内容,分析了在生物安全视野下,法医学研究中面临的风险、机遇及挑战,并以此为基础,从对法医工作者的保护及工作准则的建立、法医学研究对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促进支撑作用等多个方面,对生物安全体系中法医学研究进行了展望,以期为未来法医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生物安全;法医学;技术发展
现代生物技术在人类生产生活、公众健康、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国防建设等多个领域均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衍生出大量的生物安全问题,但不同学科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从法医学研究的角度,探讨了该领域在生物安全视野下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
1 生物安全的内涵与外延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民生、健康、经济、安全和军事等领域的发展。既往认为生物安全是全球化时代国家有效应对生物及生物技术的影响和威胁,维护和保障自身安全与利益的状态和能力[1]。狭义上的生物安全是指人类的生命和健康、生物的正常生存以及生态系统的正常结构和功能不受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活动侵害和损害的状态[2]。广义上的生物安全则是指生态系统的正常状态、生物的正常生存繁衍以及人类的生命健康不受致病有害生物、外来入侵生物以及现代生物技术及其应用侵害的状态[2]。2021年4月15日起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定义生物安全是指国家有效防范和应对危险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生物技术能够稳定健康发展,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系统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生物领域具备维护国家安全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早期的生物技术发展相对落后,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生物安全问题主要局限于健康安全和公共卫生层面。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便利用生物技术解决食物问题,例如驯化谷物、利用发酵技术酿酒酿醋、制作面包等;生物技术也用于治疗和预防疾病,例如用霉菌治疗创伤、接种活病毒预防天花等。而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以及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生物危害的来源变得更加广泛,形式更加多样,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日益严峻[3],其中与法医学相关的生物安全问题也日益增多。
2 法医学研究中的生物安全内容
2.1 传统法医学涉及的生物安全问题
作为与尸体近距离接触的职业,法医在尸体解剖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多种传染性疾病感染的尸体[4],会面临极大被感染的风险。在尸检中常见的病原体包括血源性的,如艾滋病毒[5]、乙型肝炎病毒、梅毒螺旋体、拉沙热病毒等;气溶胶性的,如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结核杆菌、非典型性肺炎病毒等。我国乙型肝炎病毒的携带者在人群中约占10%,在吸毒人群中则高达70%;结核病和艾滋病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也显示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6]。Lehmann等[7]报道了一名法医工作人员因处理感染了拉沙热病毒的尸体后感染拉沙热,证实了职业暴露导致的获得性感染。
在人体宿主死亡后,病原体的存活时间根据其性质及所处环境等存在较大差异。Ball等[8]对病人死后尸体内的艾滋病毒进行检测,发现死后11天的尸体仍可检测出艾滋病病毒呈阳性,提出尸体在死后至少两周内仍具有传染性。而有些病原体的活性更强,如阮病毒,在4%的甲醛溶液中仍能保持部分活性,甚至在组织被制成蜡块后仍保持一定的传染性[9]。多个研究结果均证实,多种病原体在经过存放、特殊处理后仍能保持活性,会给法医工作者带来极高的感染风险。
面对死前已知或疑似某种传染病感染致死的尸体,法医工作者会在尸检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个人防护,而实际工作中更多的情况是在尸检中或完成后才发现尸体携带传染病,此时再想要进行防护则为时已晚。此外,法医的工作不仅要面对尸体,还需要进行活体的伤情鉴定,在近距离接触被鉴定人时也有可能面临疾病传染的风险。除了在法医病理及法医临床鉴定中有面临感染的风险,法医在进行法医物证鉴定及法医毒物分析时,时常与血液、唾液、尿液、人体组织等检材相接触,也存在被病原体感染的风险,因此全方位加强法医的生物安全意识和做好防护工作刻不容缓。
2.2 现代法医学涉及的生物安全问题
除了上述传统法医学所涉及的生物安全问题以外,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现代法医学对生物安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宏基因组是指特定环境中全部微小生物遗传物质的总和[10]。近年来,宏基因组学成为法医学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其在个体识别、人员特征刻画、死亡时间推断等多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法医学的深入研究和快速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然而微生物也包括细菌、病毒、真菌等潜在的病原体,因此研究人员进行科研工作时仍面临病原体感染的风险。同时,实验室中的微生物泄露也威胁着其他相关人员的身体健康。
法医动物学是法医学门类下的新兴分支,随着与动物相关的司法实践案件增多,例如打击非法走私、生物物种的扩散和入侵检验等,使得该领域的研究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当前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成果指示病毒源有可能来自野生动物[11],也提示了动物所携带的病原体对人类的极大威胁,而作为法医动物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则更有可能接触携带有传染风险病原体的动物。
我国有56个民族,14亿人口,构成了丰富独特的遗传学资源,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12]。群体的基因组数据是法医学领域进行个体识别、亲权鉴定、祖源推断等研究的基础,因此,法医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获取了大量的我国群体遗传数据,并且为了提高刑事侦查的效率,我国也构建了大型的法医DNA数据库。人类遗传资源的收集、保存和应用为科研和法医实践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存在基因组数据泄露的风险,这也是生物安全防控所关注的问题。
3 生物安全体系中的法医学研究展望
3.1 生物安全时代背景下,对法医工作者的保护及工作准则建立
面对法医学领域所涉及的多方面的生物安全内容,已经有部分管理办法和从国家层面出台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多种生物安全隐患。此外,对于没有针对性解决的案例,还可以参照具有类似情况的其他领域出台的法律法规[13]。
首先,要将法医在尸检中面临的感染风险降到最低,法医工作者需要对尸体的状况进行综合考量,甄别尸体感染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如果判断其为已知或疑似某种传染病致死的尸体,则应严格参照《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尸体解剖查验规定》(卫生部令第43号)进行尸检。同时,针对不同的尸体和其生前所感染的疾病不同,有时还需要参照特定的法规。例如,处置当前新冠肺炎感染的尸体,须严格遵守公安部《关于规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现场勘查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特定人群个人防护指南》(WS/T 697-2020)以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遗体处置工作指引(试行)》(国卫办医函〔2020〕89号)等相关指导文件。
第二,在进行与微生物相关的研究时,为了保护研究人员安全和防止病原微生物外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令第424号)对病原微生物的分类和实验室管理进行了明确规定。《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16号)和《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机构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68号)也对实验室高危的微生物的保藏进行了明确详细的规定,确保实验室病原微生物保管安全,避免生物安全事故发生。
第三,对于法医学涉及到的动物研究和相关鉴定,防止其所携带病原体感染,也应对实验动物进行严格检疫,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对动物疫病实施分类管理,并对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动物疫病实施强制免疫。需要引进实验动物时,《引进陆生野生动物外来物种种类及数量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37号)对行政审批及申请材料、引进物种及后代标记、防范外来物种入侵预警等均进行了规定,应严格执行。最后,群体的遗传信息数据是法医学研究的支撑,确保珍贵的人类遗传学资料不外泄是研究人员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国令第717号),对重要的遗传家系和特定地区人类遗传资源实行申报登记,并且人类遗传资源的采集、保藏、出境都应当进行报批,有效保护我国的人类遗传资源。
3.2 法医学研究对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促进支撑
法医学研究的开展离不开生物安全内容的指导,防范和应对生物安全风险也需要法医学成果的促进支撑,例如传染病致死的尸体检验可以揭示其病理改变特征、发生机制和发展规律;种属鉴定的研究对打击盗猎和甄别外源生物物种,防止生物入侵有重要作用;宏基因组在个体识别中的研究则可应用于病毒源个体的追踪识别。
通过尸检可以直观地观察尸体的变化和明确死亡原因,是法医鉴定的重要依据。我国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率先开展并发布了关于新冠肺炎的病理解剖结果[14~16]。通过病理解剖揭示的病理改变特点,有助于从根本上探寻该病的致病机理和致病、致死原因,这对于患者的救治和疫情防控有重要意义。
近年出现的法医DNA检验技术,如DNA条形码,实现从分子水平进行种属鉴定,可以准确鉴别动物亚种,并可以推断物种的来源地[17,18],在打击盗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防止外来生物入侵、追溯动物病毒源、完善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身体状况以及所处环境等因素影响,不同个体的微生物群落存在差异,且表现出宿主特异性、部位特异性和时间稳定性[19],因此可以根据微生物群落的差异进行个体识别、人员特征刻画等。该技术也可以应用于携带病毒个体的追踪识别,进行准确溯源,有望成为疫情防控中不可或缺的技术。
3.3 法医生物安全的发展展望
在生物安全时代背景下,对法医学实践和科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在涉及生物安全的法医学实践中,都应认清工作中可能面临的危险因素,不断完善应对措施。如提高个人防护意识、提升应对能力和水平、加强实验室监管力度;
(2)提高各类法医案件处置过程中的个人防护手段,建立和使用生物安全保护等级较高的实验室;
(3)加强法医生物信息数据安全监管,构建生物安全的大数据体系;
(4)基于跨学科视野,利用多种学科的交叉,创新研究更多的法医学成果,使其在防范和应对生物安全风险中发挥重要作用。
4 结语
21世纪被称作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时代,生物科技的变革为法医学领域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生物安全问题,如何在新环境中提升是法医学未来长期面临的挑战。同时,生物安全作为全球复杂政治经济生态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与其相关的政策法规和法律纠纷亟待修订和完善,法医学领域的研究内容将为其提供促进支撑。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力争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发展,在生物安全视野下充分发挥法医学的优势。
[1] Zheng T, Tian DQ, Zu ZH, Zhu LH, Huang PT, Shen BF. Biosecurity is a living-project essential to national strategies., 2014, (2): 90–93,97.
郑涛, 田德桥, 祖正虎, 朱联辉, 黄培堂, 沈倍奋. 生物安全是国家战略必需的生命工程. 军事医学, 2014, (2): 90–93,97.
[2] Yu WX. On biosafety legislatio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9: 17.
于文轩. 生物安全立法研究.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17.
[3] Liu J, Ren XB, Yao Y, Chu X, Yu X, Su RH. Tendency and strategy of China’s biological security., 2016, 31(4): 387–393.
刘杰, 任小波, 姚远, 褚鑫, 易轩, 苏荣辉. 我国生物安全问题的现状分析及对策.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 31(4): 387–393.
[4] Brooks EG, Utley-Bobak SR. Autopsy biosafety: recommendations for prevention of meningococcal disease.2018, 8(2): 328–339.
[5] Schmid I, Kunkl A, Nicholson JK. Biosafety considerations for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infected samples.1999, 38(5): 195–200.
[6] Wang SJ, Zhang GZ, Cong B. Study on occupational risk prevention of forensic pathology., 2020, 41(5): 618–620.
王松军, 张国忠, 丛斌. 法医病理职业风险防范研究. 河北医科大学学报, 2020, 41(5): 618–620.
[7] Lehmann C, Kochanek M, Abdulla D, Becker S, Böll B, Bunte A, Cadar D, Dormann A, Eickmann M, Emmerich P, Feldt T, Frank C, Fries J, Gabriel M, Goetsch U, Gottschalk R, Günther S, Hallek M, Häussinger D, Herzog C, Jensen B, Kolibay F, Krakau M, Langebartels G, Rieger T, Schaade L, Schmidt-Chanasit J, Schömig E, Schüttfort G, Shimabukuro-Vornhagen A, von Bergwelt-Baildon M, Wieland U, Wiesmüller G, Wolf T, Fätkenheuer G. Control measures following a case of imported Lassa fever from Togo, North Rhine Westphalia, Germany, 2016., 2017, 22(39): 17–88.
[8] Ball J, Desselberger U, Whitwell H. Long-lasting viability of HIV after patient's death.1991, 338(8758): 63.
[9] Nolte KB, Taylor DG, Richmond JY. Biosafety considerations for autopsy.2002, 23(2): 107–22.
[10] Handelsman J, Rondon MR, Brady SF, Clardy J, Goodman RM. Molecular biological access to the chemistry of unknown soil microbes: a new frontier for natural products., 1998, 5(10): R245–9.
[11] Calisher C, Carroll D, Colwell R, Corley RB, Daszak P, Drosten C, Enjuanes L, Farrar J, Field H, Golding J, Gorbalenya A, Haagmans B, Hughes JM, Karesh WB, Keusch GT, Lam SK, Lubroth J, Mackenzie JS, Madoff L, Mazet J, Palese P, Perlman S, Poon L, Roizman B, Saif L, Subbarao K, Turner M. 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2020, 395(10226): e42–e43.
[12] Chu JY.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of human genetic resources in China., 2020, 72(2): 5–10.
褚嘉佑. 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的研究和管理. 科学, 2020, 72(2): 5–10.
[13] He R, Tian JQ, Pan ZQ, Zhang LQ.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biosafety in China: status and prospect., 2019, 40(9): 937–944.
何蕊, 田金强, 潘子奇, 张连祺. 我国生物安全立法现状与展望.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2019, 40(9): 937–944.
[14] Liu Q, Wang RS, Qu GQ, Wang YY, Liu P, Zhu YZ, Fei G, Ren L, Zhou YW, Liu L. Gross examination report of a COVID-19 death autopsy., 2020, 36(1): 21–23.
刘茜, 王荣帅, 屈国强, 王云云, 刘盼, 朱英芝, 费耿, 任亮, 周亦武, 刘良.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尸体系统解剖大体观察报告. 法医学杂志, 2020, 36(1): 21–23.
[15] Xu Z, Shi L, Wang YJ, Zhang JY, Huang L, Zhang C, Liu SH, Zhao P, Liu HX, Zhu L, Tai YH, Bai CQ, Gao TT, Song JW, Xia P, Dong JH, Zhao JM, Wang FS. Pathological findings of COVID-19 associated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2020, 8(4): 420– 422.
[16] Yang M, Chen S, Huang B, Zhong JM, Su H, Chen YJ, Cao Q, Ma L, He J, Li XF, Li X, Zhou JJ, Fan J, Luo DJ, Chang XN, Arkun K, Zhou M, Nie X. Pathological findings in the testes of COVID-19 patients: clinical implications., 2020, 6(5): 1124–1129.
[17] Alacs EA, Georges A, FitzSimmons NN, Robertson J. DNA detective: a review of molecular approaches to wildlife forensics., 2010, 6(3): 180–194.
[18] Tobe SS, Linacre A. DNA typing in wildlife cri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pecies identification., 2010, 6(3): 195–206.
[19] Xia XQ, Niu QS. Forensic potential of skin microbial community., 2019, 44(3): 195–200.
夏旭倩, 牛青山. 皮肤微生物群落的研究进展及法医学应用. 刑事技术, 2019, 44(3): 195–200.
Research in forensic medicine under the view of biosafety
Yuxin Guo1, Xingchun Zhao2
In recent years, biotechnology is gradually getting popular and is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human productivity and life. The consequent biosafety problem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biosafety,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biosafety contents involved i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orensic medicine research and analyzes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facing forensic medicin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safety.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of legal medical experts, the establishment of working standards, and the promotion and support of research in forensic medicine on biosafety field and other aspect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spectives of forensic medicine research from a biosafety point of view, and provides the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for a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forensic medicine practice in the future.
biosafety; forensic medicin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2021-07-05;
2021-08-16
郭瑜鑫,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法医物证学。E-mail: guoyuxin004@163.com
赵兴春,硕士,主任法医师,研究方向:法医遗传学研究及科研规划管理。E-mail: zhaoxchun@sina.com
10.16288/j.yczz.21-119
2021/9/24 19:02:56
URI: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1913.R.20210923.1509.001.html
(责任编委: 方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