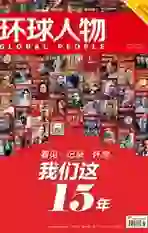“阿拉伯之春”西式民主实验品的悲剧
2021-04-14焦翔黄培昭
焦翔 黄培昭

2011年12月6日出版总第167期
2011年12月,“阿拉伯之春”的野火已经烧向叙利亚,我们推出了《生死存亡叙利亚总统》封面报道。从那时至今,中东多国历经政权更替,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卡扎菲、穆巴拉克等强人或死于非命,或身陷囹圄。
虽然10年前就面临生死存亡,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却是唯一依旧挺住的中东强人。医生出身的他,历尽剑与火的淬炼,在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下苦撑危局。他在内战和大国博弈漩涡中沉浮,亲证了中东和平的命运多舛。他的国家被战火摧残,他的脸庞也写满沧桑。当初高举“自由、民主、人权”大旗、策动“颜色革命”的西方政要,尝到了人道主义灾难蔓延的苦果,但还欠中东民众一个道歉。
3月,花的芬芳开始浸润温柔的暖风,大马士革的春天又来了。哈梅迪亚市场熙熙攘攘,商贩们开张营业,与10年前仿佛并无二致。只是,现在售卖的商品价格后要多缀上一个或两个零,即便如此,也只有蝇头小利。
叙利亚危机已10年了,战争阴影仍然笼罩着这个国家。曾经意气风发的总统巴沙尔,伴着时局跌宕起伏,从“不惑”步入“知天命”。3月8日,叙官方宣布巴沙尔夫妇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任何人感染新冠病毒都难免恐惧,但对巴沙尔来说或许这算不了什么,因为过去10年,他一直都是在生死存亡的钢丝上独舞。
3月初,以色列的导弹再次袭击了大马士革。像这样一国对另一国首都的公然袭击,显然触犯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但在巴沙尔、在大马士革民众、在全世界民众眼中,似乎也只剩无奈。对比2012年《环球人物》记者在大马士革时,昼夜不息的炮轰、爆炸,以及一天少则数十、多则上百枚从天而降的迫击炮弹来说,形势真的已经 “好”多了。
靠民心和盟友苦撑10年
巴沙尔1965年出生在大马士革。他是家中老二,上有哥哥巴希尔,下有弟弟马希尔。三兄弟中,巴希尔对政治最敏感,作风硬朗甚至有些霸道,被内定为总统接班人;马希尔勇敢坚韧,有军事才华,早就进入叙军服役。唯独巴沙尔儒雅、安静、好学、勤勉。他精通英语和法语,在伦敦学医时考试总排班里第一,他的老师舒伦博格后来回忆:“他很安静,从来都不装腔作势,在病床边对病人的态度无可挑剔。”巴沙尔的家人也支持他从医的志向,答应他留在英国当眼科医生。只是造化弄人,巴希尔1994年因车祸去世,巴沙尔被说服回国,开始了从政之路。

左图:2020年8月12日,巴沙尔在叙利亚人民议会发表演讲。右上图:2019 年10月22日,巴沙尔(中)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哈比特镇接见政府军人员。右下图:2012年2月18日,巴沙尔的支持者在叙利亚驻德国大使馆附近的集会上挥舞着印有他肖像的旗帜和标语。
他就任叙利亚总统时只有35岁,悬壶济世的医学精神对其从政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在西方世界成长的经历也让他对所谓西式民主一度抱有幻想。上任伊始,他一改父亲在任时的强人作风,主张和解、开放、包容、民主,在叙利亚各领域掀起了一场破旧立新的风潮。但理想与现实是遥远的,作为一位年轻的国家元首,他对历史沿袭、人心人性、领导艺术、国际政治等的认知都显得过于单纯,改革四处碰壁,无果而终。
2011年,西亚北非政局动荡。在最初的焦点还集中于突尼斯等国时,巴沙尔已意识到要防患于未然。他释放在押政治犯,严惩执法中的暴力,主动开启和解对话等。这再次暴露了他政治上的天真——西方哪里是想要在叙利亚推行所谓的民主,无非是打着民主的幌子,行推翻政权、搞乱国家之实。作为俄罗斯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和伊朗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坚定盟友、作为阿拉伯世界最坚定抗击以色列的国家,叙利亚触碰了美西方太多底线,不应再有幻想。
很快,叙利亚从拥有阿拉伯国家最高效的情报系统和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体系的地区大国,被一点点蚕食、瓦解,陷入战争深渊。最危急时,《环球人物》记者所在的大马士革城内守军只有3万余人,围攻城市的反对派武装多达5万人,巴沙尔政权命悬一线。但在大马士革城内,记者却感受到各方对巴沙尔的坚定支持。与精于算计、长袖善舞的老牌中东强人穆巴拉克、卡扎菲等人相比,巴沙尔以不屈不挠和真诚勇敢,赢得了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民心。
即便是在2015年,巴沙尔实际控制领土仅为叙全境1/3时,民调仍显示有70%的叙利亚民众支持(至少是不反对)他继续执政。“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今巴沙尔已度过最难的日子。目前,他已重新控制叙利亚约90%的土地,反对派主要集中在与土耳其接壤的伊德利卜省,大马士革等地面临的压力已大为减少。但叙利亚战争的复杂在于,这是一場发生在当代高技术条件和高度互联互通背景下的代理人战争。这10年巴沙尔坚强地挺立着,用自己的亲历映照出西方的私欲与伪善,用自己的坚韧回击着西方的自负与傲慢,却也还要继续忍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并面对落后就要挨打的残酷现实。
局势在胶着中走向缓和
“叙利亚危机爆发将满10年,叙利亚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和牺牲,捍卫了民族尊严,维护了国家独立和主权。当前,叙利亚局势总体走向缓和,但要恢复全面安全稳定仍任重道远。叙利亚的未来应当由叙利亚人民自主决定。”这是来自中国的正义之声。
在巴沙尔身后的主要是俄罗斯和伊朗。2015年,应叙政府要求,俄罗斯出兵,帮巴沙尔政权夺回并巩固了战场主动权;伊朗始终明里暗里支撑叙政府的军事行动,间接与美以对抗。此外,黎巴嫩真主党等地区组织派别也派人参战,成为巴沙尔一方重要的助力。
美国、土耳其、以色列既从幕后支持叙反对派武装,又对叙境内目标直接发起攻击,构成了反巴沙尔政权最大的政治势力。但他们之间因存在着利益纠葛和不同考量,分歧严重。比如,美国支持叙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土耳其则一直防范并打击这股武装,美土之间因此产生了不少嫌隙;再比如,土耳其和以色列在长期的阿以问题、近期的纳卡冲突中都存在分歧,在争夺地区主导权方面存在激烈竞争;美以关系也因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不同的政策倾向而存在变数。
原本致力于推翻巴沙尔政权的诸多欧洲国家,随着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溢出效应和自身安全考量,特别是在美国有所保留、态度暧昧的情况下,整体立场回撤明显,目前多以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出台反巴沙尔政权提案、施加经济制裁等为抓手体现存在感。而阿拉伯国家内部分化进一步加剧,对巴沙尔整体有利,其中沙特、卡塔尔等国因国内外形势变化,对反对派支持力度下滑,苏丹、阿联酋、巴林等国已通过不同形式向叙政府抛出橄榄枝。
不过,考虑到错综复杂的历史、地缘、种族、宗教等因素,短期内叙利亚还是很难看到和平曙光。这个国家已千疮百孔——约1200万(超过该国总人数一半)人流离失所,其中560万人成为难民。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称,目前叙60%的人口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对叙年轻人的调查显示,半数受访者称有亲友在叙内战中丧生,1/6称父母被打死或重伤,12%受访者本人受伤……更悲哀的是,一份国际组织的调查显示,79%的叙利亚难童称“不希望返回祖国”。《阿拉伯新聞》的评论感慨:“叙利亚残酷冲突开始10年后,整整一代叙利亚人不见了。”
日薄西山时,大马士革红霞映满天空,壮观无比,这是这座紧邻沙漠与雪山、眺望着地中海的千年古都最迷人的时刻。哈梅迪亚市场里的商贩们开始收摊回家,有人忙碌一天只挣了4000叙镑。2012年,这么多钱足够全家任选餐厅大快朵颐,如今只够买一根香蕉。但对商贩们来说,人活着、有工作,就值得高兴了。

左上图:2011年6月5日,以色列军队向试图从叙利亚进入戈兰高地的示威者开火。右上图:2021年2月15日,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民族解放阵线成员驻扎在位于叙利亚伊德利卜省东部的战壕里。下图:2021年3月3日,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卡赫村的孩子们在难民营里无聊地坐着。
“阿拉伯之春”早就变冷
叙利亚经历的风雨,是中东动荡的缩影。
自从“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环球人物》一直关注着那个地区的政要与民众命运,做了一系列的封面报道。2011年3月的《卡扎菲最后一战》,5月的《拉登及家人的隐秘生活》,8月的《穆巴拉克雄狮末路》,2013年7月的《政治强人撕裂埃及》,将一卷中东政坛风云变幻、治乱兴替的长图徐徐展开。
??? 回顾这10年,突尼斯“地中海丝路组织主席”巴斯利不胜感慨:“除了叙利亚政权没有发生更迭外,其他国家的统治者都变了,突尼斯等国产生了多任领导人,每任都有自己的主张,令人目不暇接。”在他看来,这些国家没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钥匙,贫困国家依旧贫困,而像突尼斯这样原本富庶的国家也倒退了。“这些被所谓革命风暴洗礼的阿拉伯国家,这些年几乎没什么变化,或者说,送走了原来的独裁者,却迎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环球人物》记者曾数次赴突尼斯采访,“革命”后,许多东西像被格式化过一样,让人不习惯。比如“革命”前突尼斯民风纯朴,即便在偏远小镇,也不用担心东西被偷。然而,记者2018年去突尼斯时,兜里的钱却在路上被贼偷了。这是以前不会发生的事情。
发生在突尼斯的自焚事件是整个“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由于突尼斯盛产茉莉花,这场动荡也被称为“茉莉花革命”。2010年12月17日,小贩布阿齐齐在西迪布济德市政府门前自焚,以抗议市政管理员没收他卖水果蔬菜的小拖车。《环球人物》记者曾去过离首都突尼斯城3个多小时车程的西迪布济德,那里有大片橄榄园,风光不错。据当地人介绍,涉事的管理员是个中年女子,穿着蓝色制服在两名男同事陪伴下巡视街市。她对布阿齐齐恶语相向,粗暴地没收了后者的小拖车和水果蔬菜,还扇了他耳光。出租车司机嘎努西说:“如果管理人员是个男的,情况可能还好些。被女管理员扇耳光,这让布阿齐齐深受刺激,觉得受到很大的侮辱。”
去年年底,就在“阿拉伯之春”爆发10年之际,突尼斯南部的贫穷城镇再次爆发抗议,人们走上街头,对失业、物资短缺等表达不满。而在西迪布济德,曾和布阿齐齐在同一条街卖水果的布阿利,依旧在政府办公楼后忙碌,手推车里装满苹果和香蕉。他说,卖水果的钱养不活他的两个孩子,但他没有其他的选择。
被“革命”重创的利比亚,“伤口至今仍在淌血”。反对派借西方干预,推翻卡扎菲政权,也把国家带进动荡的大泥潭。西方视卡扎菲为独裁者,认为随着他的暴毙及其政权终结,“民主、自由、统一和开放的利比亚”将诞生。然而,今天的利比亚是个烂摊子——政治动荡、经济萎靡、民生凋敝、社会治理失败。
《环球人物》记者常驻的埃及,2011年1月25日爆发“革命”。记者记得,那天先是数百民众在市中心游行,接着数千人加入,他们从市中心的解放广场走到农业部附近的杜基广场。出门办事的记者发现路上根本走不动,不时可看到停在路边的警车。早在几星期前,埃及反对派人士就定下这天为“愤怒日”,呼吁民众上街抗议物价上涨等。
开罗街头游行示威规模不断扩大,官方实施了宵禁和军事管治,气氛越来越紧张。警察与民众时有冲突,造成伤亡,更增添了紧张气氛。白天,开罗大街空空如也,晚上更是空无一人,只有解放广场日夜有示威民众聚集,他们高喊“打倒穆巴拉克”等口号,打破黑夜的沉寂。当时,还有来埃及旅游的中国游客滞留,他们心急如焚地找开往机场的出租车,却半天都打不到车。从1月28日起,埃及政府切断了网络和移动通信,记者只有座机还勉强能用。
埃及“革命”18天后,穆巴拉克被迫下台。然而,动荡远未结束。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尔西上台后,数次审判穆巴拉克,使埃及民意分裂、民心涣散,政治和社会凝聚力下滑,由此引发的深层矛盾一度将埃及推向风口浪尖。最终,以塞西为代表的埃及军方将穆尔西推翻,执政至今。
塞西曾在“阿拉伯之春”7周年时讲话称:“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允许埃及再出现这样的动荡。”他说,这场“革命”导致100多万人死亡,1500多万人沦为难民,给基础设施造成巨大损失。他的话说出了很多埃及人的心声。人们都在反思“革命”带来了什么。正如中东媒体指出的,“革命”打破固有社会秩序,已成阿拉伯国家“不堪承受之重”。记者翻看近年刊发于《环球人物》的相关报道,也有一个印象:“阿拉伯之春”没有通向春暖花开,而是早就变冷了。(完)
《环球人物》以中东局势为主题的部分封面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