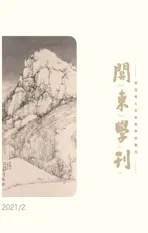重建本体论和自然观的问题
——NSTS与STSE
2021-04-14刘华杰
田 松 刘华杰
田松(2020-06-10T22:20,深圳塘朗山下):答辩结束,假期临近,终于可以做自己的事儿了。一直惦记着跟你聊一聊这个话题。
我们两个合作比较多,三观一致,有些想法也有共通之处。2018年10月27日石家庄第七届全国科学社会学年会上,我在大会发言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从STS走向STSE,E指环境,或者生态。一回到北京,就发现你在说NSTS,N是自然。当时就想就这个话题跟你聊聊。没有想到,一拖一年多。
2017年,我接到了《文化纵横》的稿约,谈现代科学和技术,于是生出一个念头,把以前的想法整合一下,写一篇宏观全景的反思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科技产业污废链”,把它作为工业文明的运行机制之一。另一个是我以前提出来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食物链”。我还把以前论述过的一些想法进行命名,诸如“工厂生态学第一原理”“科技产品污废周期律”“科技红利”等。这样讨论起来更加方便。
“科技产业链”是我们熟悉的“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科学-技术-产品-产业这个链条。可以说,这是我们专业以往的经典研究对象。所谓推动社会发展,就是让这个链条转起来,越快越好,越多越好。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STS(科学-技术-社会)过程。但是我强调,这个链条不是在真空里运行的,也不是在实验室里运行的,它必然是在一个具体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中运行的。于是就会遇到“工厂生态学第一原理”,再加上“科技产品污废周期律”,我论证,科技产业链其实是一条科技产业污废链,运行越快,污染越严重,产生垃圾越多。这就是工业文明的死结。
我在几个地方做了关于科技产业污废链的报告,接到科学社会学年会的邀请,我专门给李真真老师打了一个电话,要求作大会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我正式提出,仅仅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是不够的,必须拓展到环境(environment)和生态(ecology),正好这两个词的字头都是E。这样,我把STSE作为一个研究纲领,作为一个方法论。虽然正式提出还不到两年,但是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理论框架。我的几个学生已经在这个纲领下开展了工作。
我很想听听你的NSTS是怎么提出的,以及如何界定,如何实操。
刘华杰(2020-06-11,北京肖家河):疫情持续了小半年,学生都宅在家里,按理说我们教师也能轻松一点,实际上却不是。上网课把老师都变成了主播,录网课比当面授课要花更多的精力。此外,即使有些空闲,这期间不能到山野里走动,首先是郊区各村庄路口被封锁,根本不让通过;另外,北京人也不能随意出京,那样的话可能有去难回(因返回时要隔离)。经过最近的一年,你也终于迈出人生的一大步,从北京师范大学彻底到了南方科技大学。
你说的STSE和我说的NSTS,有相通之处,或许就是一回事。如果写法稍变一下,看起来可能更直观:STS-E和N-STS,这里STS是共同的。你在后面加了一个E,我在前面加了一个N。
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是在传统的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少在中国是这脉络。STS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者大学科,目前已经相对成熟,国际上有专门的学会,定期召开各种学术会议。“STS早先并不反思科技,后来有不同程度的反思,却仍囿于学科相关的局部问题论道,并未回到文化、文明、生存层面来反思和行动。推进STS和科学史研究的一种建议是,把STS扩展为NSTS,其中N指自然(nature)。”(1)刘华杰主编:《西方博物学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83页。STS前面为何要加上N(自然)呢?这究竟是一种前进还是一种倒退?
为何会有这样的疑问?因为熟悉早期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和学术的人清楚,那时候的讨论是包含N的。这里的“早期”,可以指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那时的自然辩证法教材一般包含三块,其中第一块谈的就是N,从宇宙演化一直谈到地球演化、物质构成、遗传密码等,具体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夸克的分类、大地板块构造、遗传漂变等具体科学问题。这部分理论上叫本体论、自然观,实际上像浓缩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史,美其名曰“自然科学总论”。讲得抽象点,叫哲学;讲得具体点,叫科普。学界对自然辩证法三大块的这一块一直有意见,在后来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淡化。后来专业期刊基本上不刊出只讨论这方面内容的稿件,在高等学校的教学上一般也不再讲这一部分。新编的教材,已经把这一部分大大压缩,甚至取消。STS研究者早期相当多从业者是理工科背景,后来文科背景者也增多,他们对长篇累牍讲述自然科学的结果,兴趣也不大。
几十年过去了,好像没有其中N这一块,也没什么问题,一切运作正常。STS继自然辩证法、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之后,迅速崛起。但是,经过一段抛弃之后,在自然辩证法或STS中,N又不得不成为重要主题。环境史的兴起和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展开,提供了新的学术平台,让人们有机会重新考虑N。比如拉图尔(Bruno Latour)就写了一本《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中译本麦永雄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
我个人也较早思考STS与N的关系,以及自然科学与N的关系,想来也有十几年了,但一直没有专门写东西,主要是没有考虑清楚。你知道,只要提出相关问题,就表明对某些东西有所质疑了。像江晓原当年提出“科学可不可以被研究”这样的奇怪提问时,就已经包含了对唯科学主义的质疑了。类似于布鲁尔(David Bloor)之SSK强纲领示意的,试图用自然科学的办法去研究自然科学,表面上看一切OK,甚至有唯科学主义的嫌疑,但是已经潜藏着巨大的危险了。只要允许认真研究科学,就会引火烧身,暴露出科学内部、科学运作的一系列“鲜为人知”的事情,令人对原本清晰的“科学本性”产生疑问。
先说到这,今天上午我要赶高铁去上海,这将是今年疫情爆发后我第一次出远门。
田松(2020-06-12T00:34,深圳塘朗山下):终于能出门了,真是不错。我下周也打算回北京一趟。不知沿途情况如何,是否要一直戴着口罩?
你一说我才意识到,原来你的N来自于自然辩证法。咱们同行基本上都教过自然辩证法,我可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在北师大十几年,没有讲过自然辩证法课程。这是一种意外的机缘。我对自然辩证法的印象已经十分久远了,上大学时学过,考博的时候也复习过,我还记得,自然辩证法的第一个版块讲自然观。我读博士的时候,中科院和社科院都没有给我们开设自然辩证法课程;政治课是另外一门,忘了名字了,两边好像都是系列讲座,请来的都是当时的大牛学者。
科学技术哲学这个专业的前身是自然辩证法,后来演变成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然后是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最后是今天的科学技术哲学。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所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已经不是必读书。真是惭愧,到现在我也没有把这本书从头到尾地读过一遍。所以在我的知识谱系和思想资源里,自然辩证法这部分是非常稀薄的。而你不一样,你应该是经历了全部过程吧?
记得去年,你还发表了一篇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文章,强调自然辩证法不是科学辩证法。这篇文章与NSTS关系密切,你是否还记得,在时间上谁先谁后?
刘华杰(2020-06-13,上海虹桥):北京疫情又出现新情况,你近期恐怕回不了北京啦!
中国自然辩证法界的演化我也只亲历过一小段,但比你久一些。今天讲了六个半小时的课,有点累,手头也没有计算机,用手机简单回复一下,回北京后再细说。2020年第1期《自然辩证法研究》上我的文章《回到恩格斯:焦点从科技回到大自然》,是根据2017年12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当代科技哲学前沿系列讲座(之八)的演讲稿——《回到恩格斯:博物作为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录音稿压缩而成。此文有几个新提法,你说的焦点变化是其一。在文章中我说:“牢牢抓住了‘科技’,却冷落了‘自然’。”
自然辩证法的关键词不应当是科学、技术,而应当回到大自然,这样就容易克服唯科学主义了,讨论生态环境问题也方便。第二,怎样访问、讨论大自然?以自然科学为中介是一种办法,但不是唯一可能性。
田松(2020-06-13T24:00,深圳南山):新冠是个新事物,我们用以往的认知模式去框它,总是框不住,像个幽灵。不久前,我们刚刚讨论过,新冠病毒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无论是啥,都属于STS的研究对象。对于这个对象,STSE怎么研究,我心里是清楚的。NSTS怎么研究,我倒是想听听你的看法。
忽然想起来,其实前年,我曾经给北师大地理学院的一个在职研究生班讲过一轮自然辩证法,为此我还特意买了新版的《自然辩证法》,还有刘大椿老师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教材。的确如你所说,自然科学总论这部分似乎不见了。这门课我是万般无奈才接下来的,第二年对方再请我上,我坚决推辞了。
刘华杰(2020-06-14,北京肖家河):下午乘高铁回到北京,气氛果然变了。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地昨天确诊36人,今天确诊8人。北京之外多地开始严查北京人。
在讲座和文章中我说:“‘自然辩证法’并不等同于‘科学辩证法’或者‘科技辩证法’。《中国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1995年)也认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是‘自然和自然科学’。注意是两个而不是一个,研究对象中是包括大自然的,也就是说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是可以直接关注、探究大自然,既要做二阶工作也要做一阶工作!一阶工作不能全部依赖于科学家。对象的范围,看似无关紧要,此时看来却十分关键,这涉及后文要说的博物的事情,即博物的合法性问题。”(2)刘华杰:《回到恩格斯:焦点从科技回到大自然》,《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1期。
理论上,自然辩证法界是可以直接探究大自然的,但是实际上在过去大家基本上放弃了这一权利,而是通过科学家的工作间接了解、讨论大自然。自然辩证法界后来也比较关心环境、生态问题,按理说应当突破约束,直接介入对自然的讨论,实际上还是主要依赖于他人(科技工作者)的成果,引用些洋人的理论,加些自己的评论,自己不观察世界,不做经验性调查。在自然辩证法、STS领域中,如果某个学者直接谈到大自然的某些方面,反而显得不正常。而我觉得,这才不正常。自然缺失了,被悄悄隐藏了!也就是说其中的N已经不在学术视野之中。
我的意思是,要重新关注N、探究N,把探究N与STS结合起来。我们这些学人需要直接重新关注自然观、本体论。
但是,这样考虑也面临一个问题:是否有“自然本体化之误”的问题?吴国盛很早就讨论过。国盛的想法是:反对把科学的世界图景看成是本体论上优先的,反对科学主义,试图引向某种新的科学哲学;试图把科学的世界图景还原到特定时代的观念史背景上,比如关于运动、宇宙、物质的概念史研究。这相当于给当今掌握话语权的科学技术画出了边界:你的“图景”确实很厉害,但是未必是我要无条件接受的。国盛在序言中说:“就本书所涉及的自然哲学而言,从前是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控制和规范自然科学,后来则反过来,匍匐于自然科学之下,被自然科学所控制和规范。”今日思考“自然本体化之误”,有两个方面需要考虑:一是反思科学主义,这个我们都注意到了;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在考虑NSTS或者STSE时,会不会因为我们运用的资源的狭隘性,而导致另一种意义上的本体化之误?何谓自然?我们如何能令人信服地认知自然、建立自然观、设置本体论?
病毒的结构、测序、分类、生理生化,不属于自然辩证法、STS或博物学研究的范围,但病毒如何与人相遇、病毒检测与控制的方法论、群体免疫可行性以及人如何与病毒和平共处,是应当研究的。
田松(2020-06-16T00:54,深圳塘朗山下):原本预计这个星期五回北京的,这几天北京新冠重来,感觉大事不好。果然,上午听到了南科大疫情管控新规,下午看到了正式公文。“原则上教职员工不得赴北京出差,确因工作需要赴北京出差的教职员工,各单位要从严审批,注明事由,往返安排等信息,经分管校领导审批同意后方可安排,返岗返校前应按本通知有关规定进行居家健康观察和核酸检测。”以前部门领导批就可以了,现在要校领导。返回深圳后,前两周刚把检测两次核酸降为检测一次,现在又要检测两次了。
昨天夜里就看到了你发回来的对话,终于了解你提出NSTS的来龙去脉。我发现,在这件事儿上,我们走的完全是两条路。殊途同归。
你的NSTS的着手点是自然辩证法。从大的层面考虑,你是要推动学科的范式转化;从小的层面考虑,你要赋予博物学以合理性。
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我们以前也讨论过,虽然从学理上,科学技术哲学这个学科就是要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进行批判的,但是现实中,这个学科的大多数从业者,应该说,是保留着比较强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其标志性的部分在于,是否承认科学及其技术在当今社会中存在着整体性的问题。记得我们有一次听肖显静的讲座,他提出了“第三种科学”这个说法。他认为古代科学(博物学和地方性知识)是第一种,“环保不经济”;近现代科学是第二种科学,“经济但不环保”;他倡导的第三种科学,则是“经济又环保”(3)肖显静:《走向“第三种科学”:地方性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当时有很多人反对他,比如认为他的第三种科学是虚无缥缈的,或者认为第二种科学是不能否定的。我们的发言都对他的出发点表示赞同,我们都认为,肖显静看到了当下数理科学及其技术的整体性问题,这一点我们与肖显静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我们并不同意。不同意的原因在于,他“反科学”反得不够彻底。有些人认为他太激进了,而我们认为他反思的力度还不够。
我觉得你的NSTS也有为整个学科指出一个新方向的意思,但是你的论证方式,又显得像是回归传统。如你所说,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和技术,只做二阶研究,不能直接面向自然。这使得这个学科总是跟在科学家的后面,比如这个学科中的经典领域—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如果相应的学科没有变化,相应的研究就失去了对象。按照惠勒的说法,物理学已经半个多世纪没有革命性的变化了,这使得物理学哲学都还在研究上个世纪初的那些老问题。哪怕是被认为是约束科学技术发展的科学技术伦理,也要围绕着具体的科学和技术进行伦理研究。科学和技术的变化,尤其是革命性的变化,才是这个学科最大的动力。而你强调的是,我们这个学科不需要围着科学和技术(家)转,可以直接面对大自然,并且,我们这个学科的前身本来就是这样的。这当然是中国语境下的特殊情形,欧美的科学技术哲学并没有一个自然辩证法作为前身。所以这个前身,恰恰为我们转身提供了一个便利。这也是因为你熟悉这段历史,可以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获得资源。所以,NSTS也可以解释成一种回归,向着自然辩证法原典的回归。在中国语境中,也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直接面对自然,靠什么呢?已经有一个现成的东西在了——博物学。经过二十年来的努力,博物学现在已经在社会和学界都扎下根来了。新博物学运动直接的思想资源中,并没有自然辩证法。但是,现在自然辩证法竟然意外地成了新博物学运动的一个思想援军。
而我的STSE,则完全与自然辩证法无关。这个STSE是我沿着科学批判到文明批判的路线,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刘华杰(2020-06-16,北京肖家河):据我所知,肖显静对科学主义是有很好的反思的,他在生态哲学和新生态学的建设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但也如你所述,他提出的“第三种科学”依然对未来科学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如果我们持乐观主义的看法,假设科学界终于认可了韩启德先生提出的“人文把握方向盘”,或者说经全球合作有某种综合性的办法克服科技的疯狂,那么剩下的或者新成就的东西是不是还叫科学?按你曾讽刺过的“好的归科学”,或许那时候社会上还流行这种法术,某领域的人把大家努力的成果据为了己有。但我想,恐怕未来的“智识结构”不会是那样,可能是一种多元相互制约的架构,称作“科学”的部分依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许加强了一点自我约束。
我的思路并非延着自然辩证法而来,我从来不属于那个体系、进路。只是因为2017年年末受邀到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暂时从那个角度考虑一下问题。严格讲,我不会称“我们自然辩证法”,只会称“他们自然辩证法”,或大伙儿的自然辩证法。的确,我对恩格斯本人的思想是非常看重的,我始终认为他是优秀的科学哲学家、STS学者,虽然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界以及在西方科学哲学界和STS界一般不这样认为。恩格斯的作品我在复习准备考研究生的1987年秋季就开始仔细读,198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硕士,工作后又仔细读过。可以说三十多年,我对恩格斯的敬佩从未动摇过。他有一点点科学主义,但不强,他对科学界也有很多批评,或者说对科学主义(虽然那时不这样称呼)也有反思!
我的思路还是源于现实问题:科学技术已经带来诸多问题,而且现在仍然在加速把人类和大自然的生态引向可怕的境地。对于此问题,传统科学哲学、默顿科学社会学对此都贡献不了什么实质工具,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遇到布鲁尔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我才找到一种好的批判工具。但这也只是解释和批判,谈不上建设;光批判不行,还得着手提出解决方案。这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和波兰尼的“个人知识”概念给我极大的启发。“生活世界”是相对于“科学世界”而言的。而博物学可以在生活世界的范围内行动,为我们重建新型本体论提供资源。“个人知识”似乎与SSK强调的知识的社会形塑相矛盾,其实两者谈的不是一回事,两者恰好都能为我所用,“个体致知”和“默会知识”提供第一阶段准备,而集体建构和社会意识形态提供第二阶段的成果呈现、展示、接受。两个阶段在实际中交织在一起、滚动运作,只是分析起来勉强划分出一前一后。
复兴博物学,在我这里是个立体的“事业”:从一阶具体实践到二阶思想凝炼,还包括社会启蒙。为何叫复兴博物学?首先有一个发现古老博物学的过程,这个非常重要。我是带着现实问题去找思想资源,找来找去觉得博物学最有可能发掘出来。为何不重新创立一个新东西来解决问题?我对新的东西不看好,反而希望从传统中找现成的线索,因为传统更有“根”、有根据,比如你说的历史依据。重新找到某东西是一种发现过程,肯定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但两者有相通之处。
实际上我的进路最后还是回到了历史,不仅仅是科学史,而是文化史、文明史、天人系统演化史。恰好,在国外,从20世纪90年代起博物学文化(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变得火热,相关学者差不多都有科学史、SSK的背景或基础知识。如果要把NSTS归类的话,我宁愿把它归于“博物学文化”。它与新型科学史、科学文化史关系密切。我觉得,环境史、自然文学研究、博物学文化、深生态学、环境伦理学是高度相关的学术追求,虽然原来各有所依所从,此时边界却模糊且开放,依据它们或许可以重建某种本体论。不过,目前西方的博物学文化研究热衷于具体问题研究,对于科技、文明的反思并不很强,或者说在进入这一领域之前已接受了相关“洗礼”。
2019年你发表了一篇《科学史的坐标系》,主要是谈中外科学史职业化的区别和联系。在结尾处你写道:“长期沉溺于以往的科学史,常常会强化缺省配置中的科学主义,产生一种进步的幻觉。比如在美国科学史的创立者萨顿看来,只有科学是进步的,所以科学史就是文明史。而如果结合环境史看科学史,或者通过科学史看环境史,很快就可以消解这种对科学进步的幻觉。因为环境史,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环境史,直接呈现就是科学及其技术的负面效应所带来的全球性灾难。”(4)田松:《科学史的坐标系》,《科学文化评论》2019年第2期。我很赞同你的分析。这是否意味着“环境史”在你的STSE中占有重要地位?或者全球史、大历史的思路在STSE中扮演重要角色?
田松(2020-06-17T02:34,深圳塘朗山下):如此说来,你的NSTS直接对应的是你倡导的博物学,而不是自然辩证法。现在我对这个概念更清楚了,也了解了你与自然辩证法的关系。本来我以为,从时间上看,你读硕读博,都应该是在自然辩证法的范式下,所以先入为主地认为,你也与这个学科一样,经历了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的全过程。
以前也几次听你讲过波兰尼个人知识和胡塞尔生活世界,我都非常认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学术气质相通的地方。直接面对现实问题,展开自己的思考。大师也好,同道也好,哪一点对我们有启发,便拿过来为我所用。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六经注我,我不注六经。你借用生活世界这个概念,但并不专门研究胡塞尔;用个人知识,也不专门研究波兰尼。
在不久前的文章中,我把你近二十年来的从事的活动称为“新博物学运动”。这个说法也不是我发明的,我记得就是从你本人那儿来的。在你昨天的对话中,你使用“复兴博物学”这个说法,对“新”表示了质疑。而我之所以倾向于使用“新博物学运动”,是因为,时间一维,过去无法重现,我们今天所呼吁的博物学也不是以往的博物学,语境不同,关注对象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不知道你现在对这两个名词怎么看?
《科学史的坐标系》主要是想要梳理一下科学史和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有一种给科学史指路的野心。我主要的感觉是,国内科学史研究的视野相对固定,不够开放,好的说法是,有自己的范式,但是从另一面,用比较时尚的话说,有了自己的舒适圈。一方面承认科学史不是科学,是历史;但另一方面,却与历史学很少有交集。科学史领域的学者,长期以来不知道历史学领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比如环境史的概念,可能很多人听过名字,但是未必知道环境史是什么。
我最初接触环境史是在2007年,我在伯克利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正好赶上历史系一个年轻教师讲环境史,我出于好奇,旁听了一个学期。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如同阿里巴巴打开了宝藏,我忍痛砸下大笔美刀,买了十几本环境史经典著作。你知道我很早就关注垃圾问题,蒋劲松称我是垃圾哲学家。我试图寻找我的同道,结果发现,最早关注垃圾问题的人文学者恰恰是环境史家。环境史是史学走向环境的一个直接表现。
不过,环境史并不是STSE的思想资源,当然,环境史是一个背景,在STSE的具体操作中,也要引入一部分环境史。
上一轮对话,我们刚刚说过讲故事。我一直强调讲一个完整的故事。STS关注的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在以往的观念中,这大概也算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了。科学发展、技术变革、社会进步,环环相扣,顺理成章。但是,这个过程好像是在真空里,在实验室里发生的。一旦把这个故事放在具体的自然环境中去讲,就有了STSE。这个故事的最后一个环节,也可以说嫁接了环境史。当然,也可以说,整个故事就是环境史。不过,STSE还是偏向于哲学和社会学,重点不在历史上。简单地说,是把STS的范式拓展到环境上。
当然,在我这儿,STSE并不是对STS范式的简单拓展,而是要开出一个新的范式,一个新的叙事策略。并且,我把STSE作为我所倡导的“文明研究”的一部分。
刘华杰(2020-06-17,北京肖家河):现在谈博物学,一些人觉得本身就怪异,我说出的博物学,自然与原来的不全一样,因为大背景变了。我可能也偶尔用过“新博物学”的说法,更多时不用“新”字,因为不需要强调“新”,自然“新”。只要能续上那个伟大的传统,一切都值得。那个传统没有断,也一直在自我更新,每个时代的博物学与前面相比都有所差别。我们常提“人类世”,此时是在人类世背景下讨论STS及STSE和NSTS。人类世的概念在地质学中只是提出还没有实锤,但早已传播到各个领域,将来即使地质学界最终没有确认它,这个词及其意义也无法消失。我刚接受了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的一个采访,也说到是在何种境况下恢复博物。
有许多哲学专家,比如康德专家、胡塞尔专家、海德格尔专家,这些人的研究颇受学者尊重。我们也尊重他们,不过把精力完全奉献给那类工作可能不适合我们。搞清楚他们思想产生的背景,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其含义,是必要的,但是终生纠缠他或她是不是那个意思,某某误读了某某的意思,可能不是我们追求的。直面时代的一个或几个关键问题,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思想资源,并尽可能通过亲自调查、感受来体验问题的性质,着手给出判断、思考,这才是要做的。
关于环境史研究对于你个人进路的影响和意义,你讲得很好。我本人也从环境史研究中受益颇多。特别是纳什和沃斯特的工作,我也让我的研究生务必注意他们的研究。
但是,你我的职业兴趣可能还聚焦于哲学,不在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虽然常从它们汲取营养。可是,我们做的又不是正宗哲学,当下正宗哲学是学院哲学,类似过去的经院哲学。可能有的人觉得“经院哲学”名声不好。不是不好,而是好极了,因为它曾经是正统。在我们的不正宗的哲学思考下,也需要本体论的重建,目的是澄清世界是怎样的,我、我们在其中是怎样的。本体论不会一劳永逸,而是要不断重建。近代以来认识论和方法论彰显,本质论被隐藏了,实际上也藏不了太久,经过一段时间就会显露出来。重建本体论是为了暂时打好基础,准备再出发。“深生态学”提供了关于重建本体论的一种极富想象的思路,比如在奈斯(Arne Naess,1912-2009)那里。他比写《哲学走向荒野》的罗尔斯顿三世(Holmes Rolston III,1933-)走得更远。我也特别欣赏“自然全美”思想的提出者卡尔松(Allen Carson),还有盖娅假说的提出者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这四位都可以算哲学家,不是正宗、单纯的哲学家了。
田松(2020-06-26T11:58,深圳塘朗山下):一下笔才发现,距离你上次的回应,已经过了十天了。这十天里不断有急事儿插入进来,写评议书、改作业、面试,又连续关注了一桩案子,就那个案子写了几篇公号文章,强调公民社会的常识,并借此讲解我之所谓人文学术基本功,就把这个对话给耽误了。
已经过了十天,当时的思路都断了。文气一断,再接总是不大容易。再看已经快一万字了。咱们各自总结几句,就可以收尾了。
这次我们大体上把NSTS和STSE各自的缘起和意图大致梳理了一下,我现在的感觉是,这是两个彼此独立的体系,但是在理念上有巨大的交集。下面我很期望看到的是,在各自范式之下的作品,再放在一起比较一下,会非常有意思。
刘华杰(2020-06-27,北京肖家河):讨论本体论和自然观问题,即使在哲学中或者其他学术中不再时髦,在作出各种判断时,仍然无法回避。简略地说,目前大概有这么几条进路涉及本体论和自然观。1.广义的STS进路。主要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后来又融合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科技人类学等,特别是拉图尔提出的“政治生态学”颇有新意。2.大写的自然科学的进路。这是比较传统且正统的道路,其进展缓慢,但也非常重要。许多论题原来不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围,逐渐变得合法。对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保护生物学等许多问题或领域的科学研究,本来属于小写的复数科学(sciences),但在科学主义的背景下,它们要服务于一个假定的、大写的科学(SCIENCE)。3.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生态运动进路。此进路直接影响社会实践,并一定程度上牵涉政治议题。此领域的行动者有时借用科学、类科学、宗教的观念为行动辩护。4.环境史研究进路。此类研究不断展现的或者承诺的本体论、自然观,非常独特,有可能成为一种学术“良识”。环境史研究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领域,其人物研究和专题研究提供了海量的信息,展现了丰富的历史、社会、文化细节,其本体论、自然观虽然不被强调,却清晰可见,似乎成为此领域工作者的一种缺省配置。
你和我的进路,都不直接出现于上述四类,虽然与它们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