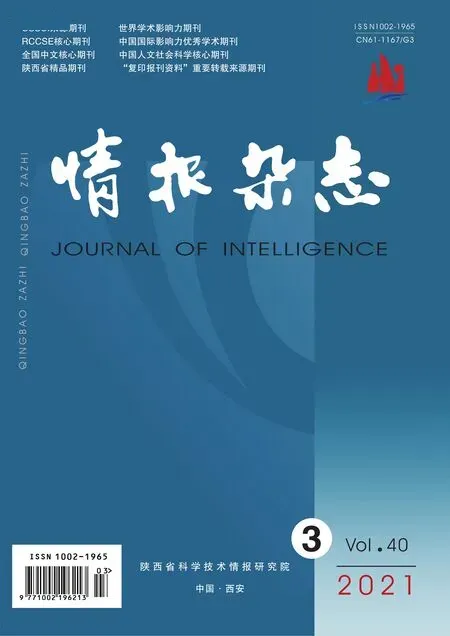21世纪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动因研究*
——基于“利益与风险”协同框架
2021-04-07邹纯龙马海群
邹纯龙 马海群 王 今
(1.黑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哈尔滨 150080;2.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3.吉林大学商学院 长春 130012)
The Motivation of U.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in the 21stCentury——Based on the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of "Interests and Risks"
Zou Chunlong1,2Ma Haiqun2Wang Jin3
(1.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2. Research Center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3. Business School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Since the 21stcentury, industrial society and risk society are intertwined and overlapped. How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o effectively allocate information resourc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lution to overal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takes America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bining with the event system theory, risk society theory and related research, constructs the motivation framework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event attribute, interest factor and risk element. By introducing 22 representative cases of America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it analyzes determinants with the help of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ests and risks, the study reveals three kinds of combination factors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Result/Conclusion]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Chin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system, explore and design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so as to better manage the information work, optimize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achieve the double goals of expected interest demand and risk control.
Keyword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event system theory; risk society theory; reform motivations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1],该理念的提出,对情报管理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1世纪以来,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交织重叠,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催生着社会、生活、文化种种领域的变迁,却也不断加剧各领域的差距,人类社会的异质性逐渐凸显,各种风险事件层出不穷[2]。因此,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情报工作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而如何完善情报管理制度以有效的配置情报资源,是统筹安全与发展的重要解决之道。所以,把握情报管理制度变革过程中的重要驱动因素,对优化现有体系结构和运行机理,实现情报资源最优配置意义重大。与此同时,“9·11”事件的发生使全世界陷入到风险世界的焦虑中,而后的反思也使美国情报界展开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3-5]。因此追溯其演进历程,探究美国情报管理制度的变革路径及驱动因素,对于完善中国情报管理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6]。
鉴于此,为探究何种因素在推动情报管理制度变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将结合事件系统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和相关研究,从事件属性、利益要素和风险要素三个维度,构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引入22个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案例,借助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推进动因进行考察。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的驱动因素,推动情报工作发展迈向专业化进程;另一方面,引入定性比较分析(QCA)有助于开拓更多探索情报制度变革的途径,为后续探究我国情报管理制度建设予以方法支持。
1 文献梳理
1.1内涵辨析本研究的对象是美国情报管理制度的变革动因,核心内涵是情报管理制度,因此首先对制度的概念进行充分理解。制度的内涵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其中非正式制度是动态自发成长演进形成的惯例习俗、约定规范等,依靠成员的理性认同与行为自律而自觉遵守;正式制度则是人为设计的规范,依靠强制性约束组织成员遵守。本研究的情报管理制度是一种正式制度[7]。在已有研究中,制度、体制和机制三者因密切相关又内涵近似,而常常被混用。因此本研究对这三者进行辨析。体制指维持工作有序化的组织形式,主要包括机构设置、领导角色、情报机构的职能分工等[6]。机制指制度的运作模式及功能的实现方式。因此,从本质上说体制和机制都包含在制度的范畴内,制度是体制和机制的根本。
情报管理制度是一个复杂系统,涉及问题广泛、机构众多、人员庞杂。申华提出,美国情报管理制度由总统、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情报主任四层管理主体构成,该国以宪法作为主要管理依据,管理对象包括美国的情报界及其相关的情报业务与行政事务领域[8]。胡荟以法律政策为视角,分析了美国情报管理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特点,以及各类法律政策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方式[9]。
结合上述文献,本研究认为情报管理制度是一种维持情报工作有序化的组织形式与运行机制,主要包括组织机构的形式、权责分配、成员及情报活动要素的组织方式和过程等。这些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对情报工作的总体安排与顶层设计,以及国家领导对情报的认识水平等。一般来说,合理完善的情报管理制度能够优化情报资源的配置效率,提升情报管理的动态能力,对现有情报问题给出积极的解决思路[10]。
1.2理论基础
1.2.1 利益与风险的辩证逻辑 本研究中所依据的利益与风险协同分析框架主要源于风险社会学理论。该理论由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这一著作中提出,诠释了后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及其原因[11-12]。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相关研究,刘兆鑫从“利益—风险”双路径视角诠释了风险社会对政策的影响。他提出利益主张与风险责任的对等现实是塑造“负责任的主体性”的关键。过分主张利益诉求而不关注风险责任的承担就会出现不可治理的局面。反过来,过分强调责任担当而不顾及正当的利益需求也同样不可取。利益与风险之间经常形成一种制衡关系,从而影响社会成员的选择。因此他提出了“利益—风险”双轨分析模型,以更好的解释风险社会的问题并给出有效的解决方式。
具体来说,在利益与风险的协同分析框架中,利益就是满足生存和发展需求的社会资源,对公共政策讨论总是会涉及到利益调整的问题;风险是不确定的损失和可能发生的灾难,是影响政策主体行为与选择的重要因素。利益和风险在讨论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应该予以同等关注,促进利益视角与风险视角的双向反思。不仅要在利益诉求过程中保持敏锐的风险意识,防止利益主张的片面和过度,也要以风险意识与责任反思利益诉求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在推动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的过程中,每个参与政策制定的主体不仅要就国家情报安全的利益需求进行表达,也同时需要将国家情报安全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考虑。
“利益—风险”的内在辩证逻辑,为本研究探究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的动因提供了重要的思路。通过利益和风险的协同对变革动因进行分析,不仅给予国家情报利益与国家情报安全以同等关注,亦能促进利益视角与风险视角的双向反思。一方面,现有社会中的风险分析是呼唤制度调整,是重新分配资源的起点;另一方面,在政策制度调整过程中,总是需要探求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利益矛盾的解决。因而风险与利益的协同分析在制度变革中存在不容忽视的叠加作用。所以结合该“利益—风险”协同分析模型,本研究将结合利益和风险两个维度,构建形成本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寻找21世纪以来,影响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的重要组合因素。
1.2.2 事件系统理论 较早提出事件系统理论的是学者Morgeson等,他们提出事件是实体的外在动态经历,包含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实体在动态过程中总是受到关键事件的影响[13]。关键事件是指那些对组织来说是优先事项并且可能对该组织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14]。Beeler等在研究中表明新颖、颠覆性、关键事件能够推动组织结构变化和组织内部新规范形成[15]。并且,关键事件还会影响团队的运作,刘东等则进一步提出事件越新颖、持续时间越长、距离实体越近,对实体影响越大[16]。
可以发现,事件系统理论为我们探究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从事件的角度探索驱动制度变革的因素,制度变革可视为参与者社会互动的集合。根据事件系统理论,当事件关键性强度越大,影响越大,对实体特征和演进的作用效果也就越强。事件关键性会影响制度变革的状态及参与者的行为选择以及参与者之间未来可能的互动,这些因素共同驱动着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的演进方向。
而且综合上文情报管理制度变革动因研究,不难发现诸如“9·11”事件和伊拉克等关键事件确在推进情报管理制度的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的驱动过程中,事件的新颖性、颠覆性、关键性等属性越强,对制度变革的特征和演进方向的影响越大。因此,本研究依据事件系统理论,一方面可以从理论层面解释关键事件对情报管理制度动态演进的作用机理;另一方面,可以据此构建科学研究框架,提出影响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的重要变量。
2 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动因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文献研究可知,自21世纪以来,美国情报管理制度的变革过程与“利益”和“风险”二元要素息息相关。利益是满足各利益主体生存、发展和享受这些资源的需求[17],本研究有关于国家情报资源分配的利益主张;风险是不确定的损失和可能发生的坏处,本研究有对国家情报安全威胁的考量。而制度的调整和变革正是为了解决资源有限性造成的冲突,重新调整分配以防患安全威胁的过程。社会主体既有追逐好处的本能,也有避免坏处的动机。因此,对利益和风险两类要素的交错影响和叠加分析,能够为揭示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的驱动因素提供重要的理论框架。
本研究提出和选择变量的依据如下:a.基于风险社会理论,按照“利益—风险”协同分析模型将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的动因划分为“利益要素”和“风险要素”两个维度,再结合事件系统理论引入“事件属性”这一维度。b.文献回顾。本研究结合国内外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研究文献,构建出包含事件关键性、风险负担、风险责任、风险分配、利益需求、权利主张、利益分配等七个原因变量的美国情报管理制度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具体构建的分析框架和原因变量的选择如下所述:
2.1事件属性对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的影响分析现有研究表明,事件属性是案例研究中应当加以考量的重要变量[18],尤其针对当前研究多采用单案例回溯,未充分考察焦点事件属性差异而导致结论普适性和解释力不足的问题。研究表明美国的情报管理制度进行大规模改革,主要源于情报机构对重大灾难和关键事件的发生未能有效预警。因此,更应聚焦关键事件的驱动作用。参考刘东等[16]的研究,认为关键性体现为事件是重要的、基本的,关键性事件往往会触发更多的分解和变化。因为事件的关键性一般会决定实体需要对该事件倾注的关心程度及实体应对该事件需要调配的资源。并且,当事件的关键性越强,对实体的特征、行为以及可能出现的新事件的影响越大。
在本研究中,实体的特征即为情报管理制度的特征,而制度变革过程中各要素如何博弈,进行再分配资源即为互动状态特征。而随着事件的发展,实体自身的行为以及互动中的新事件,他们共同构成了整个过程的演进,也就是美国情报管理制度的变革。因此,本研究首先考量事件属性的影响。认为对经济、社会构成极大影响的关键性事件会推进美国情报管理制度的变革。
2.2利益要素对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的影响分析管理制度的重构或变化往往依赖具体政策实现,而大量研究表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社会各种利益冲突的集中反映[19]。陈庆云更是提出,在政策全过程的研究中,人们会发现离开了利益问题的讨论、利益关系的调整、利益矛盾的解决,几乎什么都讲不清楚[20]。这是因为,政策的制定就是各种利益主体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输入到政策制定系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策主体依据自身利益的需要,通过相互博弈,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再调整[19]。现有关于美国情报工作的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美国通过信息霸权和信息干涉推行强权政治、干涉地域冲突的霸权行为,逐渐成为其利益诉求的关键及情报工作的重点[21],基于此美国情报界也会通过情报机构改革来适应不同时期工作任务的调整[22]。与此同时,美国在强化信息霸权的同时与该权利相关的一系列制度也在不断升级,通过将单边利益诉求上升为政策法规,能使其霸权主张得以合法化。因此,本研究将利益需求和权利主张纳入到研究变量之中。
此外,张康之等[23]的研究表明,政策议程中涉及管理制度的调整时,总是会引起原有利益格局的变动,若不能有效的解决利益冲突就会造成政策终结。结合美国两党政治结构的特征,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本就存在价值判断的差异,其参政两院的激烈斗争更会加具利益冲突矛盾的程度。因此,无论从美国情报管理制度的政策议程出发,还是从情报机构之间的资源争夺和资源优化来看,其权利斗争的根底都是为了获取利益,这就是说,只有从满足利益分配才是厘清美国情报管理制度不可或缺的方面。综上,本研究将利益需求、权利主张、利益分配纳入到利益要素的维度进行考量,作为本研究重点探讨的变量。
2.3风险要素对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的影响分析基于风险视角思考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逻辑,因为风险是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现象。如潜存的风险隐患,应对风险的能力不足等都是造成风险负担的关键。谢海星认为当现有的风险使缺陷突出地显露出来,才能迫使决策层重点关注这一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推动情报变革[24]。因此,本研究将风险负担纳入到考量范围。另外,情报工作的开展在当今社会总是依赖飞速发展的技术,隐藏在其中的安全风险不断积聚[25]。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的风险,责任制度的模糊不清甚至缺失会导致各参与主体本能推卸责任造成“集体不负责”的结果[26]。因此,对风险治理任务或风险过错方的合理设计是具有前瞻性的,能够化解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从而成为推动情报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本文将风险责任纳入到研究框架之中。最后,刘兆鑫的研究表明,在统筹管理、协调情报机构和权利分配关系的过程中,应该具备风险意识,对危机进行合理的控制。同时,也应该看到风险创造机遇,形成一种面向未来的共识或者集体行动。当这些有关风险的思考内化为政策内容,并转变为合理的权利与责任分配时,风险的生产与分配能够被有效控制[27]。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风险分配可能是推动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的又一重要成因。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风险负担、风险责任、风险分配纳入到风险要素的维度进行考量,作为本研究重点探索的变量。
3 研究设计
3.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是美国学者拉金所创,在其1987年出版的著作《比较研究法》(The Comparative Method)中首次提出,并由后续学者在近三十年的研究和不断完善中形成较为系统的方法。QCA方法主要探究跨多个案例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思路,进行多案例研究,不需要大样本检验,只基于小样本(2~10)或者中等样本(10~100)的案例进行分析。
本研究选取定性比较分析中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处理变量为二分赋值的变量,即设定条件变量后,在具体的每一个案例中显现或不显现,分别赋值为1或0,这些条件变量或称为原因变量的集合路径,即为所要研究的结果,或者是复杂社会现象发生的明确原因组合,本研究试图寻找影响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的原因组合,故选取此种方法。
在具体操作中,本研究根据“利益—风险”协同分析模型和事件系统理论提炼出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动因的路径因子;然后选取从2000-2020年间22个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事件案例;最后,进行QCA运算得到分析结果。本研究共选取从2000-2020年间22个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案例,具体见表1。

表1 21世纪以来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事件

续表1 21世纪以来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事件
3.2变量编码本研究按照“利益—风险”协同分析模型将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的动因划分为“利益要素”和“风险要素”两个维度,再结合事件系统理论引入“事件属性”这一维度,构建出包含事件关键性、风险负担、风险责任、风险分配、利益需求、权利主张、利益分配等七个原因变量的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动因的分析框架。
本研究将变量采用二分进行处理,变量取值为1或0。取值为1的代表某条件发生,取值为0的用“~”代表某条件不发生。比如事件关键性,主要考察是否存在对经济、社会构成极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当突发事件对经济、社会构成极大影响并对情报管理制度变革产生作用,则编码为1,反之,则编码为0;利益需求,主要考察是否为维护霸权的情报工作调整需求,如果该情报管理制度变革是出于为维护美国霸权的情报工作调整需求的动机,则编码为1,反之,则编码为0,其余变量编码则以此类推,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编码及判断说明
4 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通过对fs/QCA3.0的运行,可以获取复杂解、中间解和简单解三种原因组合结果。其中,复杂解完全遵循所设定的变量进行统计并得出结果,因此,本研究采用复杂解的运算结果进行具体分析(见表3)。在QCA方法中主要通过一致性指标和覆盖率来进行判断。一致性指标可以用来判断原因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必要关系或者充分关系,具体公式如下:
Consistency(Xi≤Yi)=Σ[min(Xi,Yi)]/ΣXi
(1)

表3 原因组合分析
覆盖率主要指原因变量对于结果的解释力,具体公式如下:
Consistency(Xi≤Yi)=Σ[min(Xi,Yi)]/ΣYi
(2)
从表3显示的结果可见,整体一致性和整体覆盖率均超过0.9,说明这些结果对于解释所选取的22个案例有较强的力度。因此本研究将分析该3种原因组合及其所含变量,得到推动情报管理制度变革动因的3种组合方式:
原因组合一:~事件关键性*风险负担*~风险责任*风险分配*利益需求,该原因组合是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所有驱动因素中最主要的组态形式。这组原因表明,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的驱动,主要出于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考虑和维系霸权统治的利益需求,国家情报工作的开展与资源的优化需要通过顶层设计以实现对权利与责任的风险再分配。不难发现,在未发生重大事件或未受到重大事件影响的情况下,无需考虑相应的风险治理任务或风险过错方,所以情报管理制度变革更体现为一种主动性的变化调整,需要协同安全威胁与利益需求双元因素,对情报管理制度进行探索性的调整,勾勒出权责分明的管理模式。
原因组合二:事件关键性*风险负担*风险分配*利益需求*~利益分配。在该原因组合中,可以发现重大事件对推动情报管理制度变革起到重要的作用。当发生重大事件时,焦点将主要转移到与风险威胁相关的考量,工作重点将围绕如何进行国防安全的情报收集工作,并围绕这些需求建构权利与责任的风险分配机制。而此时,情报管理制度变革较少考虑各个机构之间的情报分配与共享。
原因组合三:~事件关键性*风险负担*风险分配*利益需求*权利主张,该原因组合体现为,当未发生重大事件或未受到重大事件影响的情况时,情报管理制度变革会受到风险负担、风险分配、利益需求三元因素的驱动,这与原因组合一的情况一致。但除此之外,制度变革还会受到维护霸权的情报立法和制度需求的影响。一般来说,制度分为两个层次,一种为以机构调整、政策和规章为主,具有契约性;另一种为具有较强控制力和约束力的法律法规。权利主张意味着将探索性调整部分的情报工作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程序化工作。因此,可以看到,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在非重大事件的影响下,会通过自身的制度优化机制,从政策规则方面的探索型尝试,逐渐过度形成具有法律效力和约束的法律法规,实现对情报管理顶层设计的完善。
综上所述,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的组合原因主要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风险负担、风险责任和利益需求是贯穿各种原因组合的关键要素。即在非重大事件影响时,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是一种自我进化驱动模式,主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对国家风险安全的考虑,以及围绕霸权的情报管理。在风险威胁与利益需求二者之间,更偏重于对国家安全的需求,其制度的调整更偏向于对权利与责任的风险再分配。
第二,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自上而下”的自我优化模式,历经了探索式学习到利用式学习的过程。先针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快速反应、进行持续改进,进行规则制度的政策性调整,逐渐基于法案要求改革制度机制,最终形成程序化、可操作的法律法规。
第三,在重大事件的影响下,美国情报管理工作会以安全为主要议题,并据此进行政策调整,然而这种制度变化是暂时的,当事件的影响结束,就会再度回归到霸权逻辑的利益需求。因此,围绕重大事件的制度调整较少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
5 启示: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中国情报管理制度建设
在上述讨论之后,本部分基于对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动因的分析,讨论该国在制度构建和改革实施过程中的特点,并进行审视与反思,以期探索并设计符合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的情报管理制度,从而更好地管理情报工作、优化情报资源配置过程,实现所期望的利益需求与风险控制双重目标。根据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的原因组合一、原因组合二和原因组合三可以看出,风险负担、风险责任和利益需求是贯穿各种原因组合的关键要素。
首先,从风险负担、风险责任要素可以看出美国的情报管理制度变革侧重于对情报安全威胁和风险防控的思考。自2000年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以反恐为核心,对情报管理制度进行重新架构,自此之后,国家安全问题成为情报管理制度架构的逻辑起点和重要驱动因素。随着技术的变革和时代的发展,国家安全的外延内涵从范围上和内容上均不断受到挑战,如今大量与美国利益相关的地区都被纳入美国决策者以安全为核心的情报管理制度建设议题[28]。因为安全,尤其是信息时代的数据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是每个国家都时刻面临的综合性挑战[29]。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了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方略,这一指导思想将安全上升到战略层面。这与美国情报管理制度以安全为主导的发展动向吻合,也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最优策略。从外部来看,我国仍然受到西方国家的霸权威胁,以及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从内部看,涉及民生的信息安全问题屡见不鲜,而国民的信息安全素养和意识仍需加强。为应对诸如此般的综合性挑战,我国应该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加强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等在内的各类情报管理范畴界定,同时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等,做好各方面的情报工作建设[29],树立科学的大数据观和配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情报工作认知[30],以期为情报管理制度的维护构筑起一座安全为基石的堡垒。
其次,从利益需求要素可以看出美国情报管理制度变革主要受到霸权逻辑的影响。然而与传统霸权不同,美国的霸权是全方位的,不仅强调权力因素,更强调制度因素。因此在情报管理制度建设中,情报霸权成为最根本的推动力。然而,这一霸权主义思想是以损害他国利益为发展要义的利己行为,与我国战略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背道而驰。在全球化进程中,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应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也要尊重他国的价值主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1]”。因此面向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大环境,未来的国家情报管理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如何提升在国际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成为情报管理的重点与制度建构的关键因素。
最后,从原因组合一、原因组合二和原因组合三可以看出美国的情报管理制度变革道路体现为自上而下且层级分明的垂直优化模式。由于情报工作存在隐蔽性与客观的专业规范性[31],其管理制度变革的方案大多为精英阶层提议并推动。一般来说,在重大的突发事件中,现有制度的缺陷会暴露,相关负责人则会围绕问题的解决对制度进行优化或重组;另一方面,以国家安全和利益需求为核心,相关负责人会依照法定程序,对现有的情报管理制度进行结构优化,最终形成程序化和可操作的管理体系或制度。这种优化的过程,前期多为探索性的尝试,针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小范围的快速调整、迭代改进。后期,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再基于法案要求改革制度,最终上升为法律法规。纵观这一改革路径,其制度体系调整的及时性和处置流程的规范性仍然值得中国借鉴,而且“自上而下”的推动过程,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政府部门为决策主导和行动主体,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指挥——控制”处置方式相适应。因此,可以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以安全发展为核心有效组织调动政府资源,为情报工作的迭代创新予以组织上的支持,并为情报工作的顶层设计及法律制度层面的优化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