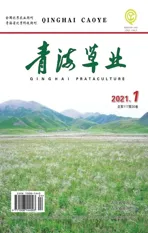青海湖流域天然草地资源年际动态分析
2021-04-07杨培宏李积德周华坤
杨培宏,郭 婧,李积德,周华坤
(1.海南州林业站,青海 恰不恰 813099;2.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省寒区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青海 西宁 810001;3.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生态环境研究所,青海 西宁 810000;4.海东市乐都区中岭乡人民政府综合服务中心,青海 碾伯 810799;5.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青海 西宁 810001)
前言
青海湖流域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是我国西北干旱区、西南高寒区和东部季风区的交汇区,青海湖是青藏高原生态的重要水体,并对整个青海西部沙漠化起到屏障保护作用,是维系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1,2]。青藏高原广泛分布着高寒草甸、高寒草原、温性草原等草地生态系统[3],青海湖流域是青藏高原东北部重要的牧区,也是青海省畜牧业生产的主要基地[4,5]。草地监测是对草地资源动态监控的基础,国家自 2005 年起即对全国草原实行大范围监测,目的在于为当地政府农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本文对 2010~2019年草地生产力监测数据进行分析,旨在为高寒地区植被恢复、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概况
青海湖流域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系南麓,是青藏高原东北部最为重要的自然地理区域,流域总面积为29 661km2,地理位置介于36°15'~38°20' N 与 97°50'~101°20'E之间。地形复杂,四周环山,海拔在 3 242~5 279 m 之间。青海湖流域属于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年均温度-5~8.5 °C,年均降水量为50~550 mm,降水集中在6~9月,年平均蒸发量达到1 300~2 000 mm[6]。青海湖湖水补给来源为河水,雨水及地下水,每年获得径流补给主要来自布哈河、沙柳河、乌哈阿兰河和哈尔盖河。植被类型有草原植被(温性草原和高寒草原)、灌丛植被(温性河谷灌丛与高寒灌丛)、草甸(高寒草甸、盐生草甸)和高山流石植被以及荒漠植被(高寒荒漠类和温性荒漠类)等[7]。其中以草甸和草原为主,面积分别为16 557 km2和4 599 km2,占流域总面积 71.3%。草甸覆盖了流域的大部分区域,草原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偏北部区域。灌丛、高山稀疏植被和荒漠在流域分布较少,分别占流域总面积的5.7%、3.2%和 3.0%[8]。
1.2 样地设置
青海湖流域草地生态监测区设在环青海湖的共和县、天峻县、刚察县和海晏县的25个乡镇。根据青海湖流域草地生态监测的目标和草地类型监测站点布设技术要求,在自然区域共设11个草地监测样点,涉及5个草地类,分别是温性草原类的芨芨草型,西北针茅、细叶苔草型,西北针茅、青海固沙草型,西北针茅、杂类草型4个草地型;温性荒漠草原类的短花针茅、青海固沙草型,短花针茅、杂类草型2个草地型;高寒草甸草原类的高山嵩草、紫花针茅型;高寒草原类的紫花针茅、杂类草型;高寒草甸类的高山嵩草型,矮生嵩草型,高山嵩草、杂类草型,禾叶嵩草型,高山嵩草、异针茅型等5个草地型。
1.3 监测方法
草地植被监测方法:设置固定样地,其面积不小于10 hm2。一个样地内布设3个1×1 m样方,样方间隔距离不超过250 m。植被监测于牧草生物量最高峰即7~8月进行。首先,详细记载样地的基本特征,包括样地所在行政区、草地类型、海拔高度、地理位置、地貌一般特征、土壤一般特征、水文和水文地质条件、利用方式和利用状况等。草本及半灌木草地布设样方的面积1 m2,每个样方3次重复,小乔木及灌木草地布设样方的面积为100 m2,不做重复。具体如下:
草层高度:测定草地植物自然状态下,草丛叶层集中分布部位的平均高度。
植被盖度:样地内取1×1 m样方3个,采用一个面积为1 m2并用细线分割成10×10 cm方格网的样方置于草地上,按不同植物冠投影占有的方格数的方法统计盖度[9]。
生物量测定:2010~2019年植物生长季7月上旬~8月上旬调查测产,采用齐地面刈割,鲜草装袋称重。
2 监测结果
2.1 草层高度
2010~2019年青海湖流域自然区域草地植被草层高度(指植物营养枝高度,下同)历年平均统计,温性草原类草地为10.3 cm,温性荒漠草原类草地为5.4 cm,高寒草甸草原类草地为5.3 cm,高寒草原类草地为9.4 cm,高寒草甸类草地为6.5 cm。10a监测结果表明,天然草地植被在温性草原类和高寒草原类长势最好,草层高度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图1)。除高寒草原类的草层高度与2010年相比变矮(降低47.31%)外,其它4种类型草层高度均不同程度的高于2010年。草层增加幅度温性草原、温性荒漠草原、高寒草甸草原、高寒草甸平均分别是24.19%、20.00%、66.67%、18.10%。

图1 监测年度各类型草地草层高度变化
2.2 草地植被覆盖度
与监测起始年2010年相比较,在各年份各草地类植被覆盖度中,温性草原类草地在2014年和2018年高于监测起始年,增幅4%~12%,其他年份均低于监测起始年3%~34%;温性荒漠草原类草地2015年与2010年持平,2019年和2018年高于监测起始年4%~10%,其他年份均低于监测起始年5%~26%;高寒草甸草原类草地均高于监测起始年32%~46%;高寒草原类草地分别在2013年、2014年、2015年、2017年、2018年和2019年间高于监测起始年,增加1%~25%,其他年份低于监测起始年3%~9%;高寒草甸类草地2015年高于2010年1%,2012年、2014年和2016年植被覆盖度与监测起始年持平,其余年份均低于监测起始年3%~15%(表1)。
从植被覆盖度年际动态变化来看,监测年度草地植被覆盖度与2010年相比各草地类型呈现明显的波动变化(图2),其中温性草原类的植被覆盖度分别在2014年和2018年达到最高值(均为77.0%);温性荒漠草原类的植被覆盖度呈折线形变化趋势,在2018年达到峰值,为86.0%;高寒草甸草原类从2011年起植被盖度变化幅度较小,整体上植被覆盖度保持在81%以上;高寒草原类则呈现“M”型动态变化,分别在2013年(94.0%)和2017年(88.0%)达到阶段性最高值;而高寒草甸类的植被盖度在监测年度内均较高,达到79%以上。

表1 青海湖流域各类型草地植被盖度年度对比

图2 监测年度各类型草地植被覆盖度年际变化
2.3 草地生物量年度动态变化
青海湖流域自然区域草地监测10a期间,历年平均产草量统计,温性草原类、温性荒漠草原类、高寒草甸草原类、高寒草原类和高寒草甸类草地历年平均产草量分别为3 165.89 kg/hm2、2 323.41 kg/hm2、3 093.73 kg/hm2、3 361.41 kg/hm2、4 434.34 kg/hm2。2019年青海湖流域自然区域各草地类型产草量分别与历年均值、监测起始年(2010年)、2018年相比得出温性草原类、高寒草原类、高寒草甸类3种草地类型均呈现不同程度的降低。例如,高寒草原类草地产量分别与历年均值、监测起始年、2018年比较,分别降低25.03%、13.55%、46.68%;高寒草甸类草地产量则分别降低25.97%、31.60%、49.05%。而温性荒漠草原类草地产量分别增长60.18%、44.55%、22.43%;高寒草甸草原类草地产量同样分别增长39.64%、14.41%、38.91%(表2)。
草地鲜草产量,高寒草甸类和高寒草原类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且高寒草甸类除2018年度有所增长外(34.27%),其余各监测年度产量呈现下降趋势,下降幅度3.20%~31.60%;高寒草原类在监测年间的波动状态整体呈现“M”型,分别在2012年和2018年达到峰值;上升幅度0.33%~0.54%;温性草原类、温性荒漠草原类和高寒草甸草原类均呈现出不规则的折线形波动,其中温性草原类2013年、2019年产量分别下降50.89%、31.55%,在2018年产量上升了18.89%;温性荒漠草原类在2017~2019年出现上升,幅度为20.47%~39.90%;高寒草甸草原类分别在2017年、2019年产量增加,达到30.60%和12.60%(图3)。

表2 青海湖流域各类型草地产草量

图3 监测年度各类型草地生产力年际变化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0a的监测结果显示,青海湖流域与2010年生态保护工程实施以来相比,草地生态环境恶化局面得到了初步改善,草地植被生长状况,无论是植被覆盖度还是产草量均有提高。具体如下:
(1)2019年青海湖流域自然区域草地5个草地类草地植物平均高度为6.7 cm,植被平均总覆盖度为80.3%,草地总产草量平均为3 301.21 kg/hm2。
(2)10a监测结果表明:草层高度不同程度增加。温性草原类、温性荒漠草原类、高寒草甸草原类、高寒草甸类草层增加幅度平均分别是24.19%、20.00%、66.67%、18.10%。
(3)草地植被覆盖度,温性草原类、温性荒漠草原类、高寒草甸草原类、高寒草原类、高寒草甸类草地分别为63%、67%、86%、76%、90%。
(4)温性草原类、温性荒漠草原类、高寒草甸草原类、高寒草原类和高寒草甸类草地历年平均产草量分别为3 165.89 kg/hm2、2 323.41 kg/hm2、3 093.73 g/hm2、3 361.41 kg/hm2、4 434.34 kg/hm2。
3.2 建议
草地虽然受自然环境因素温度、水分、光照等支配,但是同时也受人为因素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作用的影响[10]。因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积极实施生态保护工程,改善草地生态环境,以解决草畜矛盾突出的问题。二是建立健全草地监测机制,依据草地生产力监测结果,下达减畜计划,对超载的牧户,限当年内调减到规定适宜的载畜量范围。三是加快牧区富裕劳动力转移力度,减缓草地承载压力,抓住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资源开发、发展特色旅游、文化等产业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劳动就业培训,使农牧区有技能的富裕劳动力成为专业化的产业工人和职业化的服务员工。四是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提高监测技术水平,加强草地监测技术人员的长期培训工作。针对基层草原监理站技术人员开展定期野外监测培训,使当年参与野外工作的人员深入了解地面监测内容并熟练掌握操作技术规程,提高监测数据的精确度。五是利用“3S”技术等先进手段进一步建立草地生产力、草地退化以及草地灾害等的数据模型。进一步加大草地监测投入,利用“3S”技术建立起完善的草地监测预警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