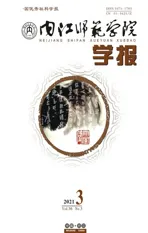《琴经》作者托名诸葛亮考辨
——兼论汉文典籍流播云南的途径
2021-04-02茶志高
茶志高, 雷 玥
(云南民族大学 民族文化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诸葛亮南征和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和治理,影响极大,留下众多遗迹、传说、崇拜等,吸引了众多学者以不同视角和方法进行了研究。正因为其影响力,历代有众多传说和遗迹不断累积,也就造成了一些真真假假、穿凿附会的成分,需要辨明。本文从《滇略》等载《琴经》作者托名诸葛亮撰的记载入手,梳理历代公私书目和史志文献对其真伪问题的讨论,认为《琴经》确为托名诸葛亮之作。同时考察古代汉籍在云南流播的主要途径。
一、《琴经》为托名文献的相关考辨
在明代有关云南的史志资料中,可以看到有关诸葛亮撰《琴经》,教滇人识琴、造琴、鼓琴的记载,如明谢肇淛《滇略》卷十“杂略”载:
丞相亮征孟获,入滇。滇人未知琴,亮居南,尝操之。土人有愿学者,乃为著《琴经》一卷,述琴之始及七弦十三徽之音意。于是滇人始识鼓琴。又从征者冬暮思归,各与一砖曰:“卧枕”。此即抵家。从之,果然。不用命者,终莫能归。因号“鸡鸣枕”。又尝用炊釜自随,不炊自熟,以防不时之需。[1]
明代刘文征天启《滇志》卷三十一“杂志”第十三“琴经鸡鸣枕”条[2]、明代诸葛元声《滇史》中亦有记载,文字稍有差异[3]77。雍正《云南通志》:“《琴经》,三国、汉诸葛亮南征,尝抚琴,滇人有愿学者,乃著《琴经》一卷,述琴之始及七弦十三徽之音意,于是滇人始知琴。”[4]《滇黔志略》引雍正《云南通志》较为简略[5]61。初读这些载记,就会产生一个疑问,诸葛故事多有附会,在诸葛亮著述问题上,有没有存在伪书的可能?这是值得进一步考察的。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五”有《诸葛氏集目录》,包括《开府作牧》《权制》《南征》《北出》《计算》《训厉》《综覈上》《综覈下》《杂言上》《杂言下》《贵和》《兵要》《传运》《与孙权书》《与诸葛瑾书》《与孟达书》《废李平》《法检上》《法检下》《科令上》《科令下》《军令上》《军令中》《军令下》共“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6]929。陈寿在目录后的一段文字,清楚记载了整理诸葛亮著述的经过,“臣寿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书监济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奏,使臣定故丞相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之有伦也。辄删除复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6]929-930陈寿对诸葛亮的著述做了整理,尤其注重“删除复重、随类相从”,就是典型的目录学工作,但陈寿所编《诸葛亮故事》或《诸葛氏集》,偏重法律类、政令类和议论散文,并非诸葛亮全集[7]。即便如此,诸葛亮著作中亦未见《琴经》。
正史艺文志中著录《琴经》首见于《隋书》。《隋书》卷三十二载:“《琴经》一卷。”[8]此外有《诸葛集》二十五卷,《论前汉事》一卷,《武侯集诫》二卷,《兵法》五卷,《武侯诫》一卷。《隋书》所著录的《琴经》并不清楚撰著者姓名。郑樵《通志·艺文略》“乐类”引《隋书·经籍志》著录《琴经》一卷,无撰著人姓名。随后同卷又著录:“《琴经》一卷,崔亮。”[9]很显然,《通志》著录了同名著作,其中有一部注明作者为崔亮。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无名氏撰《琴经》和崔亮《琴经》是否为同一部?此较难以考证。但第二个问题,崔亮写过《琴经》是否有据也值得探讨。
自宋以后的目录学家及其著作,就《琴经》是否为诸葛亮所作问题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尤袤《遂初堂书目》“乐类”著录《琴经》,不录撰著人姓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音乐类”著录:“《琴经》一卷,托名诸葛亮。浅俚之甚。”[10]宋代国家藏书目录《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一“乐类”著录“诸葛亮《琴经》一卷”,此书宋绍兴中改定,清叶德辉考证。叶德辉按语曰:“陈录入子部音乐类,云:‘托名诸葛亮,浅俚之甚’。”[11]从陈振孙言《琴经》作者托名诸葛亮是“浅俚之甚”的评价看,至少在宋代就已存在托名这个认识。马端临关注到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对《琴经》作者托名诸葛亮的意见,《文献通考》:“《琴经》。陈氏曰:‘托名诸葛亮,浅俚之甚。’”[12]似认同陈氏意见。
明代开始,《琴经》的作者又变得混乱起来,一说张羲轩,一说诸葛亮,一说崔亮。明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张益孚羲轩《琴经》一卷。不知时代。”明陈耀文《天中记》、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三十四引《中兴书目》著录:“《琴经》一卷,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所象之意。”[13]明代董说《七国考》卷一“大夫”条:“《琴经疏》。聂伯为韩大夫,出使于秦,作怨离之曲,别老母稚妻也。”明陆釴嘉靖《山东通志》卷三十四:“崔亮《琴经》一卷,东武城人。”又曰:“《琴经》一卷。陈氏曰:‘托名诸葛亮,浅俚之甚。’或曰魏武城崔亮撰。”焦竑《国史经籍志》:“《琴经》一卷,崔亮。”后言“备录其书,以俟考订”[14]。查《魏书·崔亮传》未见著录,《崔亮传》:“崔亮,字敬儒,清河东武城人也。……常依季父幼孙,居家贫,佣书自业。时陇西李冲当朝任事,亮从兄光往依之,谓亮曰:‘安能久事笔砚,而不往托李氏也?彼家饶书,因可得学。’亮曰:‘弟妹饥寒,岂可独饱?自可观书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于冲,冲召亮与语,因谓亮曰:‘比见卿先人《相命论》,使人胸中无复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记之不?’亮即为诵之,涕泪交零,声韵不异。冲甚奇之,迎为馆客。”[15]1604李冲后推荐崔亮为中书博士,转议郎,迁尚书二千石郎。后兼吏部郎,太子中舍人、迁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最后官至尚书右仆射。从崔亮的传记看,其先人有《相命论》,可以说有一些知识背景,但家贫,以“佣书自业”,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常见的以抄书作为职业的社会现象。紧随《崔亮传》后《魏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五十五《崔光传》:“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15]1604崔光起初也是靠“佣书”维持生计。《后汉书》《三国志》《南史》《北齐书》《宋书》《高僧传》等均见“佣书业”的记载,“佣书业”使官私藏书不断丰富,且书籍得以迅速广泛流传。崔亮、崔光等通过“佣书业”由贫困卑微的底层人物,变得博通恰识,最后获得高官。不知言崔亮作《琴经》依据为何?值得关注的是明末方以智把诸葛亮撰《琴经》的流行说法进行了有力反驳,《通雅》卷三十:“《中兴书目》有《琴经》一卷,诸葛亮撰。此伪必矣!余尝见杨大经所得《琴经》言‘十三徽中音为主,在七徽两头各六。琴身分三断,各七音而七弦十三徽,又细分宫、商、角、徵、羽转声之处。’南海陈乔生曾刻其略,今不见有此书。崔遵度《琴笺》亦言其端矣。大经教人先唱琴,如学箫先唱五六工之例,故易得节奏,方与诸乐器合。”[16]按照方以智在杨大经处所见《琴经》以及其追溯到北宋古琴家崔遵度《琴笺》的内容,判断诸葛亮撰《琴经》是“伪必”的。按照《天中记》《广博物志》和《通雅》对《中兴书目》著录《琴经》的线索,反观前文所言陈振孙“浅俚之甚”的批评,应是针对《中兴书目》所录而言的。
清代因乾嘉学术考辨风气,辨伪工作取得巨大成就。仅就诸葛亮著作的整理和研究论,清代学者据自己所能见到的版本进行了校勘,取得了巨大进展,尤其对宋代以来《琴经》的托名问题进行了纠正。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存目”著录《永乐大典》本《十六策》一卷、浙江范懋柱家阁藏本《将苑》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心书》一卷,题“诸葛亮撰”,均为伪托。四库馆臣指出:“盖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明以来术数之书,多托于刘基。委巷之谈,均无足与深辨者耳。”[17]认为这些书是晚出的伪书。《将苑》最早见于《遂初堂书目》著录,《古今伪书考》以来清人考证认为乃宋人托名诸葛亮之作品,根据聂鸿音先生的考证,其存世本最早不过明代。英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译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书初编面貌[18]。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对《诸葛氏集》做了全面考证,并胪列明代张澍所辑《诸葛忠武侯文集》四卷附故事五卷目录,认为“网罗极博,足淹前修,而刺取片语单词,未免纤碎”,《诸葛忠武侯文集》中有“《琴经》见《中兴书目》一卷,今佚”[19],然对《琴经》没有特别说明其为伪托。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著录蔡邕《琴操》二卷,后有按语曰:“《日本国书目》:‘《琴经》一卷,蔡伯喈撰。’似即此书。”[20]通过援引《北堂书钞》中蔡邕《琴赋》以及王昶《揅经室外集》载从惠栋手抄本过录的《琴操》二卷,内容上与《日本国书目》所载《琴经》一卷相似,似为同一书。仔细辨别梁章钜所言《中兴书目》所载已亡佚之《琴经》和姚振宗所言《日本国书目》载蔡伯喈《琴经》,自然不是指同一书。进一步考察,姚振宗参考了陈振孙对《琴经》作者的看法,《三国艺文志》:“宋《中兴书目》有诸葛亮《琴经》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托名诸葛亮,浅俚之甚。’今不录。”[21]显然已经采纳了前代目录学家的辨伪成果,因此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又云:“《琴经》一卷,不著撰人。按唐《日本国书目》有《琴经》一卷,蔡伯喈撰。似即此书。阮文达《揅经室外集》曰:‘《琴操》二卷,蔡邕撰。从征士惠栋手钞本过录。上卷诗歌五曲一十二操九引,下卷杂歌二十一章。《文选·演连珠归田赋注》引蔡邕《琴操》云云。’其诗歌操引篇数与王氏所辑孔衍《琴操》同,特惠氏归之蔡伯喈耳!又《书录解题》云:‘《琴经》一卷,托名诸葛,浅俚之甚。’似非此书。”另注明:“《孙祠书目》:‘《琴操》三卷,蔡邕撰。一读画斋刊本,一星衍校本。’”[22]今人孙猛《日本国在见书目详考》中留意到了《中兴馆阁书目》及《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但仅言“录以备考”[23]。清唐晏《两汉三国学案》载《隋书经籍志》《琴经》一卷[24]394,但未加考辨,这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秉持的观念有关系,“近代讲西汉学者,例多自我作古。……故余所引古书不加解释,欲人之自得之也”[24]6。本来古人就喜欢“自我作古”,而后学之人不作辨别,那只会讹上加讹。从文献辨伪的角度来讲,作伪一般或“因秘本偶然发现而附会”,或有“引古人以自重的动机”。好古托名以自重在梁启超看来是“儒家的特别精神”,“好古成为了儒家的特别精神,儒家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极其伟大。儒家好古,所以后来的人,每看见一部古书,都是非常珍重。书愈古,愈宝贵。若是后人所作,反为没有价值。有许多书,年代不确,想抬高他的价值,只得往上推;有许多书,分明是后人所作,又往往假托古人名字以自重”[25]。观历代目录所著录之情形,古书一般不自著姓名,秦汉以前古书尤为明显。汉以后“然仍无于篇题之下,自标某人撰之例”,故著书无“自序”,“文中不自称名者,久之或竟无可考”[26],时代风气使然,一旦历经久远,必淹没不可详知,均为著者不自题姓名之故。古人的这些做法,为后人作伪或附会留下了“可发挥”的空间。
从诸葛亮是否精通古琴音乐乐理,是否在实践层面擅长演奏古琴也可以进行适当探讨,有助于思考诸葛亮有无撰著《琴经》之可能。《诸葛亮传》中记载:“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6]911学界对“好为《梁父吟》”多有讨论,就作者问题亦有争论。“梁父吟”是乐府曲调,本可吟唱,而在此曲调下的基本感情基调是“悲凉”“伤悼”“惋惜”。“梁父吟”也被认为是有着思乡的主题,而《滇略》“鸡鸣枕”所载“从征者冬暮思归”,呼应的是“思乡”这一主题,把“琴经鸡鸣枕”放在一条,似乎别有寓意。诸葛亮本传中与“乐”有关者,仅只能依据“好为《梁父吟》”来看,并没有直接记载诸葛亮精通乐理,从汉以来所著录的关于古琴制作、演奏之书的记载,说明会演奏古琴应该不是很难的事。至于明确说诸葛亮会弹琴,《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讲孔明“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显然这是小说家的演绎,但演绎也非无依据。“孔门礼乐并称,故知礼者必知乐,未可离而二之也”[24]396,诸葛亮是一个儒者,作为儒者,知礼懂乐应是题中之义,小说中安排弹琴这一细节,不显得突兀,反而展现出孔明运筹帷幄,气定神闲之态。既然诸葛亮会弹琴是合情理的,那诸葛亮撰著《琴经》就有可能,也就是说,将《琴经》的作者托名给一个懂得乐理,会演奏古琴的人,那诸葛亮是合适人选。明代以后典籍中著录《琴经》作者为诸葛亮,或受到了《三国演义》“武侯弹琴退仲达”一回的影响。
二、诸葛亮南征史实在民间传说及好古崇德风气下的文献伪托
诸葛亮南征既有史实,更有附会传说。谢圣纶称:“黔中古迹,诸郡邑率因武侯南征,遂多援引附会之处。夫山川胜境,因人而彰。晋、唐、宋、元,迨近千年,殊少明贤踪迹;至明而拓地开疆,同于内地,名臣宿将与是邦之文人杰士相互照耀,遂多可纪之迹焉。”[5]328袁嘉谷也说:“武侯名所莅地,附会古迹。既未莅地,亦有之,皆难轻信。”[27]26层层累积,显得扑朔迷离,“地方史志、小说家言、云南传说交互错杂,丰富多姿”[28],在滇西、滇西南民族地区甚至缅甸的众多传说,多为有名无实,当系传播流传所致。
《琴经》作者为何会托名诸葛亮,实可以从民间传说中对诸葛亮的敬畏、诚服和认可的角度来看。诸葛亮平定南中,学者认为与庄蹻入滇、赛典赤行省云南是云南历史上的三次开发,对云南社会生产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29]。史籍记载诸葛亮经营南中,利用大姓或部曲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管理,实行富有特色的分类统治策略[30],重视农业生产,“丞相在南中,劝彝筑城堡,务农桑,诸彝感慕德化,皆自山林徙居平壤,出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终其世,彝悉改襟贡賨不复反”[31]41。而这些措施是否赢得当地一些势力的拥护,实可以从民间文本中略窥一二。《西南彝志》第八卷讲到妥阿哲世系后,有《助孔明南征》一篇:“蜀汉皇帝时,孔明先生出兵,征讨南方,与叛帅交战时,祖先妥阿哲,出兵助汉皇,供给军粮,为其后援,攻无不克。汉皇帝说:‘妥阿哲此人,是一位忠臣,将长官职位,赐给妥阿哲,加上红印敕命,一并赐给妥阿哲。’汉皇帝之时,妥阿哲成长官,皇帝又给晋爵,叫他攻打南方,其地一攻即破。北向扯勒地推进,到恒那达地,所属地方,重到北部扯勒地方,从四方攻占其地。勿阿鼐创见基业,妥阿哲发展基业,住在慕俄勾。”[32]流传于景东曼等区的彝族民间故事《孔明大战山神》讲述孔明和山神斗法的故事[33]52,景东文龙区三岔河乡流传的彝族民间故事《陶府的封地》讲诸葛亮征战西南边疆时,陶虎去投军做了诸葛亮手下的一名官员,从曹操营地找到了一本其在慌乱间掉了的《法度经》献给诸葛亮,诸葛亮每翻一篇,曹操的兵马就死去一大批,诸葛亮获胜,陶虎因此获得封地[33]61-62。这些民间故事中的论述,至少说明当时当地民众支持诸葛亮,与此同时在地方也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和基业。
流传于大理永平杉阳的传说《杉阳地区供奉老爷神》,和明清史志文献材料“鸡鸣枕”有些类似,应为同源异流关系。“传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结束,准备凯旋。为了不惊动当地黎民百姓,就把各种兵马召集起来,露宿在荒山野坝远离人户的地方。诸葛亮传下号令:‘马头朝东喂,人头朝西睡。第二天京城赶早饭。’本来,马头朝东方,天边一泛白,马就会踢腿喷鼻而动,一动就会惊动士兵,人头向西睡,天边一泛白就会照醒人,这样,人马即刻就悄悄出发。一些吊儿郎当的士兵偏不这样做,偏把马朝西喂人头向东睡。结果,大队人马悄悄开拔走了,不听话的那些士兵被丢在了荒山野坝。日子一长,这些人饿的饿死,病的病死,成了孤魂野鬼,孤魂野鬼入不了阴间、天堂,也进不了南天门,都被赶了下来。”[34]83“用命”和“不用命”,“听话”和“不听话”,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富有意味。流传于大理巍山县《孔明南征的传说》(《巍山八大旗的来历》)中载巍山百姓在红河源头(阳瓜江)放“莲花碗灯”的习俗,来源于孔明率领西蜀大军进军并攻取蒙舍川营盘山的故事,讲述孔明为了征服人心,避免伤亡,在战术上做了精心研究。在此故事中,在解释巍山汉族的来源和以“旗厂”命名村庄的来源时说,“平定蒙舍川后,一天晚上,孔明下令说,今天晚上,人朝东睡,马朝东喂。当时,大家都不了解这是什么意思,于是有的照着做了,有的仍然胡乱躺下。谁知到了第二天早上,坝子里许多兵营都不见了,只留下了八面军旗,八座军营。这八个军营里的兵马也少了许多。据说,这些头朝东的兵马都被孔明作法摄回去了,而头朝其它方向的却摄不回去,只好留了下来。于是兵将门创建村庄,培植家园,屯田植树,生产繁衍,一直到现在。”[35]而根据史料记载,此八个村子是明初沐英征云南、屯田治边时所留置。传说与史实有时会出现不一致的现象,“移花接木”是传说演进过程中的常见手法。流传于永平新田村的《救兵粮》的故事,其中有一段诸葛亮向当地猎人的解释:“刘备是刘邦的后裔,是仁君。平夷的目的是平息叛乱,安定后方,好集中精力北上讨奸贼曹操,统一中国……”[34]117此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边疆百姓对王朝国家“正统”观念的认同。《华阳国志》载诸葛亮为夷作图谱,又与瑞锦铁券,“夷甚重之”,师范《滇系》、袁嘉谷《滇绎》等均承袭此条。师范对诸葛亮之治绩和德行有一段论述:“吾读常道将《南中志》,而愈叹诸葛公之德如此,其深且远也。当是时,蜀得汉郡之一,吴得四五,魏得七八。自公经营南中,收用其豪杰,简料其士马,而师以武。转输其货贝,储峙其仓廪而国以富。不独视作苑囿且仗为库藏,遂克支吴魏而不至大衄,即姜伯约之九伐,犹有所资焉。”[36]诸葛亮对内励精图治,对外威惠远播,《滇绎》“孔明”条载“佧瓦”与“华人”的对话:“我本大朝之人,西人来诱我,弗听。但大朝之孔明阿公今犹在乎?”[27]25也体现出对“大朝”(汉)和诸葛亮的认可。根据学者的研究,诸葛亮信仰在历代都有极广泛的体现,尤其在清代表现出“世俗化”倾向,其主要的文化意义体现在“确立了统治者‘立教化民’的模范榜样、寄托了士大夫‘君臣契合’的功业理想、丰富了民众‘娱神娱己’的世俗文化”三个方面[37],清代前期把诸葛亮视为“纯臣”“纯儒”而入中央的祭祀体系当中,与之相应的民间信仰也出现“百姓巷祭,戎夷野祀”的现象,提起诸葛亮,星辉云烂,“彝众感悦”,从这样的角度去看,民间传说、地方史志将《琴经》伪托给诸葛亮,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汉代非常重视以“礼”“乐”治邦安民的教化作用。《汉书·艺文志》:“《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皇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38]《琴经》本来就是讲“乐”的,诸葛亮治南中,自然需要“移风易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假托诸葛亮作《琴经》,把诸葛亮教夷众识“乐”作为教化一方的途径和表现,自然也可。
三、汉以来汉文典籍流播云南的途径
上论述《琴经》为伪书的基本事实,又论托名诸葛亮的缘由。还需要关注的另一话题是,既然有托名或者附会的空间,那么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至少在明代以前,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地区接受汉文化或者中原地区对它的了解都是较为困难的,受到很多因素的阻隔和影响而被“双面遮蔽”。年代越往前,地域越封闭,典籍越稀缺,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托名的可能性。“滇南风气,至前明始开。迄我朝崇儒重道,文治光昭,超越前代,士类奋兴,骎骎乎媲于中州矣。汉唐以降,叛服不常,或姑事羁縻,或干戈相寻,或摈为异域,大都以夷制夷,宫墙芜废,视今之庠声序音、人文丕振,则瞠乎远也!”[5]61就云南地方文献记载和文人看来,云南真正地实现“人文丕变”,始于明。
文士进入西南带入传播儒学是汉文典籍流播西南地区的早期记载。《大理府志》载:“武帝元光五年,以司马相如持节,入西彝。至若水,叶榆盛览、张叔闻之,皆往受学,文教于是乎始。”第二条渠道是西南地区的读书人进入中原地区学习,将儒家文化带到西南地区。
“蛮夷犷悍,不知礼义,喜即从服,少拂意称兵相向,迄无定岁,非儒教不驯之。而汉自置郡以来,为政者沿习夷俗,故滇人犹未知书。今王阜实开其始。后蒙氏晟罗皮据滇,倡立孔子庙于国中,未必非阜启之也。”[3]56又载:“汉桓帝年,滇人有尹珍者,字道真,牂牁毋敛人也。自耻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负笈远游,入中国,从汝南许慎(字叔重)、应奉(世叔)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于是南土之人始知学焉。珍又劝谕蛮夷,倡兴诗礼,渐迁其俗。”[3]60诸葛元声按语认为:“滇人之从儒教,自楪榆张叔学于司马相如,归授乡人,为滇西乡献之始。况有太守如王阜者劝学兴礼,以倡率之乎!抑余寓滇久,益知中国文明之始必酿于儒教,而二氏终非治国之正也。夫滇西密迩西方,被释化最先,故土人至今居室以佛为香火。然自汉以往,变乱相寻,迄无宁岁,汉末始知从儒。蒙、段继伪,仍袭陋风,一隙之明,未克沦浃也。故仅能合异为同,率龌龊幺麽,无足观者。幸我太祖混合区域,列滇省于历代帝王舆图之内,一体视之。以故文治彬彬,家弦歌,户诵读,人人衣冠礼让,喜谈先王,绝无恫挢虔刘,如向罗罗爨僰旧俗也。虽有奸萌,不扑自灭。此岂菩提能使然哉!仲尼木铎之余响也。”[3]60-61许叔、尹珍、张叔、盛览等是汉代离乡入“中国”求学者。《广舆记》载汉昆明人许叔“元狩中,入中国,受《五经》归,教授本郡”。“尹珍,字道正,牂牁郡母敛县人。珍自以生于荒裔,未渐声教,乃从汝南许慎受《五经》、应奉授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知学。汉桓帝时,珍以经术选,历尚书丞郎,荆州刺史,而应奉为司隶校尉,师生并显。”[5]273清人冯甦更认为盛览作《合组歌》《列锦赋》为“滇中文学之始”,尹珍、许叔入中国受经书而“人文渐盛”[31]11。又《广舆记》卷八“张叔,叶榆人。天资颖迈,过目成诵。俗不知书,叔每疾之,思变其俗。元狩间,闻司马相如至若水,遂负笈往,从之受经,归乡教人。”关于张叔籍贯为叶榆人之说,傅光宇的考证认为史籍记载的张叔是成都人,张叔为叶榆人之说源自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同时指出史籍记载的盛览是小说家言,出自《西京杂记》。云南儒学、文学也不兴盛于西汉[39]。在傅文讨论的基础上,廖荣谦对盛览的籍贯有进一步考证,指出言盛览为“牂牁”人是无疑的。作者在考辨的基础上阐明“虽然盛览从司马相如受学及盛览为叶榆人等说法并不完全可信,但由此可以看出,与贵州同处荒服之地的古代云南人民对中原文化的异常倾慕和对儒家正统思想的高度认同,尤其是对司马相如开发西南夷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40]。而关于盛览著《赋心》之说,则见《太平御览》引《西京杂记》,《北堂书钞》补引出自《十六国春秋》,袁嘉谷对此有专门讨论,“今滇人传长通,多失其真,相如友人而曰弟子,牂牁名士而曰叶榆人,且曰:览退之而作《赋心》四卷,王畴五先生又以为十卷。皆缘《地志》增饰之故,长通卓卓可传,增饰奚为?”[27]6综上述一些讨论,实质上可以隐约看出汉代巴蜀学派对南中地区的辐射,“汉晋时期的封建势力以巴蜀为据点来统治南中。由于政治上南中称为巴蜀附庸,儒学也与巴蜀是分不开的”[41],另外,中原移民的大量迁入,自然为南中地区促成了儒学的传播。《滇黔志略》所载尹珍事迹,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卷十二《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名目录》“文学”载“荆州刺史尹珍,字道真,毋敛人也”。《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载龙、傅、尹、董等均为“大姓”,尹珍即尹氏大姓中的突出代表,《华阳国志·南中志》有详载,滇东地区的大姓大部分都是汉族移民。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汉魏时期对西南地区有很好的经营,但有效的治理范围依然有限,儒学的影响也并不见得广泛。至唐代有昆明人张志成,“太和中入成都,学羲之草书,归教国人”。据载滇人有知王羲之而不知孔子,“初,滇俗以王逸少为圣人,不知有孔子”。于是赛忠蕙于至元十一年镇抚西南时,“首建文庙于昆明、大理两处,购置经史”。元宗开元元年,蒙氏晟罗皮立孔子庙于国中。《滇史》认为:“蒙氏未兴之先,南蛮莫盛于爨。汉以来染王教,多从儒书,识义理,名通上国。”[3]99而认为“至祀孔子而黜佛,尤为高识。今蛮有此举,宜其奕世昌大,卒有全滇”[3]116。具有包容开放的高识积极学习儒学,将孔子当作至圣先师,是蒙氏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开元十二年,南诏遣喜州张建成朝唐。入觐,明皇厚礼待之,赐以浮图像并佛书而归。张建成过成都大慈寺,学佛书,归授滇人。晟罗皮奉浮图像、佛书,特建道胜寺藏之。可见当时除了儒家典籍外,还有佛教典籍流入云南。唐阁罗凤筑大理城,从蒙舍迁至太和城,此后郑、赵、杨、段氏均将太和城作为都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礼仪大略本于汉唐。“滇人自尹道真受经归教,始知有诗书,然其君长莫能崇尚,故诵读者少;及郑回宣扬儒术,文教始振。元和中,昆明有许叔者,笃志经术,复入中国,受五经归,教授郡人,诸夷益知向学。”[3]172宋“徽宗崇宁二年,段正淳遣高泰运入朝求经籍,得六十九家”[5]62。徽宗政和年间,“云南使李紫琮过湖南,闻学校文物之盛,请于押伴,求诣学瞻拜宣圣像。郡守张察许之。遂往遍谒诸生,出,乞观御书阁,举笏扣首”[3]228。“乾道癸巳,有大理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有法,所须《文选五臣注》《五经广训》诸书,及浮量缸器并碗诸物。”[5]62此材料出自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除上述二部典籍外,还有《国语》《初学记》及医书,为大理商人李观音等求购,当时北宋疏离大理国,致“不复通于中国”,因而所求购之书为“邕州官吏姚恪暗中予之,但不敢让朝廷得知”[42],滇人到外地求学过程中所带回经籍,无疑对地方社会立学改俗又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云南社会中汉文典籍的流传情况也可以根据一些载记略知一二,对典籍的收藏保存也颇为重视,“乾道中,南诏使者见广南人,言其国有《五经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张孟押韵集》《圣历》诸书。吕东莱曰:‘唐太宗《帝范》十二篇,五代丧乱,书遂缺。今上征云南,僰夷始出以献,旧二十篇复完’”[5]62。说明按以上记载看,以王逸少为圣人而不知孔子的说法,人为地将云南与中原的交往以汉代作为历史割裂点,追溯历史不过汉代,过于夸张,有挂一漏万之嫌,甚至《元史》采入此说,显然也不够严谨。云南澄江府知府章尔佩《重建澄江府明伦堂记》认为此说为诬,不辨自明。“《元史》称云南不知尊孔子,以王逸少为先师。至张立道任劝农使,始立学建孔子庙。此说予尝疑之。孔子之教,自汉高帝具以太牢奉祠天下,已翕然成风。殆武帝尤好儒术,而滇于此时正通中国。其后王阜守益州郡,以建学致白鸟之祥。晋、宋之间,虽治乱相仍,尚设官奉正朔,学校之制,当不谬于一统。王右军生东晋,踪迹不出江左,何至滇之人舍孔子而尊师之?此不待辨而知其诬也。”[43]另外,滇通中原较晚,孔子生活至少时代远,而王羲之离得近,滇人对王羲之较为熟知,倒是情理之中。除了自发求学求书之外,王朝亦逐步重视在地方设孔庙,兴儒学。元至元十一年,以赛典赤赡思丁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其“设郡县,改置令、长,重婚姻,行媒妁,用棺椁,行奠祭,教播种,修陂池,建文庙,购经史,授学田,夷风丕变。”[3]243办学校的关键节点之一就是从王朝层面明确给读书人都什么样的书的问题,故“购经史”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使地方学校能够读到儒家经典,但赛典赤所购“经史”细目是哪些,现无从得知,却无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44]。大德二年设立的云南诸路学校,教官均以蜀士充补。明代朱元璋还专门诏令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云南、四川皆有土官生,日本、琉球、暹罗诸国亦皆有官生入监读书,辄加厚赐,并给从人。”[45]1677西平侯沐英镇云南亦“兴学校”,“退食朝夕讲玩《大学衍义》《通鉴纲目》诸书”[3]293,洪武二十年后,滇中教化大行,民俗丕变。“洪武二十三年,乌撒土知府阿能,乌蒙、芒部土官,各遣子弟入监读书”[45]8005“嘉靖元年赐播州土司儒学《四书集注》,从宣慰杨相奏也。”[45]8044据史籍记载,永乐九年,始命监察御史巡按云南,始诏云南布政司开科,取举人洪诚等二十八人。滇中文教渐开,士人诗赋埒于中土。永乐间以诗名家者,有平、居、陈、郭,杨林隐逸诗人郭文,论者认为其诗有唐人风致。到永乐二十三年,乌撒土知府阿能,乌蒙、芒部土官各遣子弟入监读书。开儒学以教乡俊,建文庙而祀夫子,则体现出王朝治边“用夏变夷”之训。
从清代开始,崇礼先师,王朝对云南学校的兴复加强,修学校,育人才,昆明、大理两地书院得到极大发展。顺治二年,定谥号“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十四年,改“至圣先师孔子”,设卧碑,颁行各学。康熙十四年,颁御书“万世师表”匾额,悬大成殿。四十一年,御制“训饬士子文”,颁天下各学。雍正元年,追封先师孔子五代为王爵,启圣祠为崇圣祠。五年,颁御书“生民未有”匾额。尤其应注意的是,雍正十一年,“奉旨,省会书院各赐帑金一千两资其膏火,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并颁《图书集成》一万卷于滇省书院”。《古今图书集成》的颁布,是朝廷层面向云南赐汉文典籍的标志性举措,是以往学者对《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者、成书、刊刻等研究以外对其如何流播所忽视的一个重要节点,学界关注明清以来王朝如何对云南兴教化、讲儒学,文献典籍的刊播层面不容忽视。这批典籍数量不少,按雍正《云南通志》《滇黔志略》所载,《古今图书集成》计六汇编五十二典六千一百九部,共一万卷,五百二十函五千一十八本。目录四十卷,共二函二十本。内容所涉颇广,主要有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典籍汇编,另有经史子集共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四、结语
《琴经》为诸葛亮撰之记载自《中兴书目》始,《直斋书录解题》对此持否定态度,至明代此说又较为流行,亦不断有学者纠正,应和明代编纂诸葛亮集的风气有一定联系。清代大部分的目录学家和史学家,对《琴经》为诸葛亮所著之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而民间或地方史志的记载却更加愿意将《琴经》的著作权归于诸葛亮。这其中显示出植根于深厚的民间信仰和作为科学而严谨的考据学家研究成果间的不同取向。总体来看,诸葛亮撰《琴经》,是托名。但在《琴经》托名诸葛亮的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诸葛亮在西南地区所获得的认可和对其的信仰。在地方史志资料中反复转载“琴经鸡鸣枕”条,似乎也隐含着人们对诸葛亮故事的热衷和喜爱,诸葛亮是一个王朝的代言人和化身,认同“诸葛亮”,就意味着认同王朝国家。